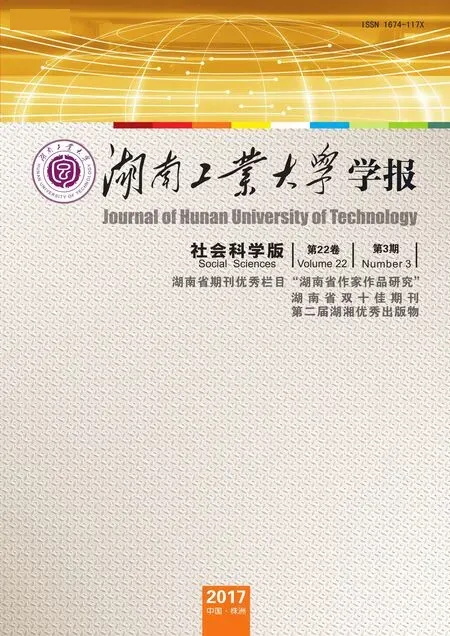阳明学者的良知与知觉之辩
——以聂豹与欧阳德、王畿的争论为中心
2017-02-23董甲河黎文雯
董甲河,杨 瑾,黎文雯
(1.江西农业大学 政治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2.江西农业大学 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3.南昌理工学院 公教部,江西 南昌 330044)
阳明学者的良知与知觉之辩
——以聂豹与欧阳德、王畿的争论为中心
董甲河1,杨 瑾2,黎文雯3
(1.江西农业大学 政治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2.江西农业大学 人文与公共管理学院,江西 南昌 330045;3.南昌理工学院 公教部,江西 南昌 330044)
在阳明学者中,关于良知与知觉之辩分化出两种不同的致思路向。一种以聂豹为代表,主张良知是未发之中,知觉是已发之和,由知觉转向良知本体。一种以欧阳德、王畿为代表,主张良知既是未发之中,亦是已发之和,从知觉处见良知。双方互相指责,聂豹认为欧阳德、王畿从知觉处见良知,易出现义袭逐物之弊;欧阳德、王畿认为聂豹由知觉转向良知,易出现向内禅定之弊。双方固守不同的支援背景,都认为遵循阳明致良知学的理路,实则聂豹遵循朱子学体用二分思维方式,走立体达用路径;欧阳德、王畿遵循阳明学体用一源思维方式,走即用达体路径。
聂豹;良知;知觉;立体达用;即用达体
在阳明学者中,聂豹与欧阳德、王畿关于良知与知觉之辩是阳明后学中一个重要议题。学界关于双方争辩的研究已产生一些成果。吴震先生认为,聂豹把良知与知觉的体用关系视作“立”与“生”的从属派生关系,“这就有可能导致割裂体用”。[1]彭国翔先生认为,双方论辩,“在体用思维方式上一元论与二元论的不同以及对这种不同缺乏自觉,是造成双方不免自说自话的根源所在。”[2]388林月惠先生认为,双方对良知与知觉的论辩,虽然都认同“良知是未知之中”,但聂豹从未发、已发二分,欧阳德、王畿等从未发与已发一体,“依不同思路来了解此一命题的含义”。[3]433本文在前辈学者的基础上,从双方支援背景研究激烈争辩的焦点出发,对此问题作深入的探索。
一 聂豹:良知是未发之中,知觉是已发
据费纬祹《聂贞襄公传》载,聂豹因夏贵溪所恶被逮,“狱中闲久静极,忽见此心真体,光明莹彻,万物皆备,乃喜曰:‘此未发之中也,守是不失,天下之理皆从此出矣。’”[4]628林月惠先生认为,聂豹的悟道体验是“一种具有‘高峰经验’的特征,而又比‘高峰经验’层次更高的‘高原经验’。透过这种经验,我们能回归‘真我’,我们也能觉知存有本身,甚至自己的根源。而世界的对立面之矛盾与冲突,也随之溶化为一。”[3]628-629聂豹通过这次狱中体验,建构良知学说皆围绕“未发之中”展开。
聂豹认为,儒门圣学一脉相传,皆以未发之中为主线。他说:“豹病废山间,钻研是书,历有岁时,而于诸家之说,求诸心有未得,虽父师之言不敢苟从。窃以孔门之学,一以贯之,孔之一即尧舜相传之中。中者,心之本体,非大学之至善乎?”[4]53未发之中出自《中庸》。在《中庸》中,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这是著名的未发与已发、中与和的经典阐述。聂豹认为:“未发本是性,故曰‘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而曰性之体用则中节之和,不知又是何物也。中是性,和是情,中立而和出焉,体用一原也。”[4]402意谓他主张未发之中是天命之性,发而中节是已发之情,体用一原。他不能理解王畿的性之体用为中节之和。王畿认为:“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发而中节之和,此是千圣斩关第一义,所谓无前后内外、浑然一体者也。”[5]130王畿以良知指称未发之中与发而中节之和,不分未发与已发,其思路来自王阳明。王阳明认为:“‘未发之中’即良知也,无前后内外而浑然一体者也。……未发在已发之中,而已发之中未尝别有未发者在;已发在未发之中,而未发之中未尝别有已发者存。”[6]64在王阳明看来,良知是未发之中,也是发而中节之和,无有内外前后之分,浑然一体。欧阳德亦赞成王阳明此说,认为:“良知念念精明。其未发之体无少偏倚,故谓之中;发用之节无少乖戾,故谓之和。”[7]188
比较聂豹与王阳明、王畿、欧阳德在中和问题上的分歧可知,聂豹不赞同王阳明以良知贯通中和的思路,而是以未发之性、已发为情贯通中和。这背后涉及体用一源的分歧。王阳明的体用一源是“即体而言用在体,即用而言体在用”。[6]31他认为体用不可分,有良知之体,就有良知之用;有未发之中,就有发而中节之和。这是体用相即的体用一源观。聂豹的体用一源是“未发非体也,于未发之时而见吾之寂体;发非和也,言发而吾之体凝然不动,万感因之以为节,故曰中也者,和也”。[4]246他认为,在情之未发之时见体,在情之发时见情合乎中节。这种分未发与已发的思维方式来源于朱子的心统性情说。朱子认为:“性以理言,情乃发用处,心即管摄性情者也。故程子曰‘有指体而言者,‘寂然不动’是也’,此言性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是也’,此言情也。”[8]在朱子看来,未发之中指性,已发之和指情,心统性情。他认为程颐以心统性情诠释寂然不动与感而遂通。彭国翔先生指出:“同样是‘体用一源’,朱子是以二元论为基础,阳明则可以说是一元论为前提”。[2]336聂豹继承朱子体用一源观,认为体用相离,未发之中指性体,发而中节指情和,以心分体用统贯中和,在大本大源上与王阳明、欧阳德有极大分歧。
聂豹在体用二分的体用观下严分性情,进而区分良知与知觉。他认为:“心之虚灵知觉,均之为良知也。然虚灵言其体,知觉言其用,体用一原,体立而用自生。致知之功,亦惟立体以达其用,而乃以知觉为良知而致之,牵己以从,逐物而转,虽极高手,只成得一个野狐外道,可痛也。”[4]277意谓良知包括心之虚灵与知觉,但其中有分别,虚灵指心之体,知觉指心之用。他区分心之体用为虚灵知觉,来源于朱子的“心之虚灵知觉,一而已矣”。[9]之所以区分良知与知觉,是因为他看到学者错认知觉为良知,牵己逐物,沦为义袭。从未发已发来看,“夫以知觉为良知,是以已发作未发,以推行为致知,是以助长为养苗。王霸、集袭之分,舍此无复有毫厘之辨也。”[4]239良知指未发之中,知觉指已发。以已发作未发,误入助长之弊,“不知中之为独也,而别求知觉;……不知良知之为虚灵也,而以知觉之能辩乎是非善恶者之为良而致之。要其所至,不过行仁义而袭焉者也。义袭之见作,而允执之学亡。”[4]536他看到世间学者误以知觉为良知,致知觉而行仁义,远离良知之虚灵,在已发上做实功,徒成义袭。
聂豹区分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已发是知觉,其主要目的在于由已发转向未发,由知觉转向良知,进一步归结于“未发之中”。他认为:“‘良知是未发之中’,先生尝有是言。先生曰:人只要成就自家一个心体,则用在其中,自然有发而中节之和,自然无施不可。”[4]376他以心分体用诠释王阳明的“良知是未发之中”,认为王阳明主张在心体上用功,自然可以发而中节。王阳明指出“良知是未发之中”,意谓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亦是发而中节之和,并不区分心之体用。聂豹以心分体用的思维方式看待王阳明此说,主要看到良知是未发之中,确证心体的重要性,严分未发之中为体,发而中节为用。可见两者并不在同一诠释视域之中。然而,聂豹抓住了王阳明致良知学说主要在心体上做实功这一最重要观点。王阳明认为:“吾良知二字,自龙场以后,便已不出此意。只是点此二字不出。于学者言,费却多少辞说。今幸见出此意。一语之下,洞见全体,真是痛快,不觉手舞足蹈。”[6]1170王阳明于百死千难中体认到生命本源就是良知,是学问头脑所在。他在四句教中说:“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前者指心体,后者指意动。聂豹对比在心体与意动两者上分别用功之差异,认为“若在意上做诚的工夫,此便落在意见,不如只在良知上做诚的工夫,则天理流行,自有动以天的机括,故知致则意无不诚也。”[4]343在意上用功,意有善有恶,无有停当,而在心体上用功,顺其天理流行,动以天,其效果比在意上用功更好。他体认到王阳明致良知的核心在于良知本体,意味着只有在良知本体上用功,才能真正回归生命本源,而在意上用功,变化多端,不能凑泊。然而,他虽然看到致良知的大方向,但选择以未发之中为主旨。探讨未发之中,必然涉及发而中节,关联性与情、中和等十分细微的问题。朱子有中和旧说、中和新说,最终以心统性情,性是未发,情是已发确认中和学说。王阳明并没有走体认未发之中之路,其主要原因在于,在未发与已发上思索,容易成头脑测度,忽略致良知是要做实功。聂豹开始问学于王阳明,探讨勿忘勿助问题。王阳明认为:“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悬空守著一个勿忘勿助,此正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渍水下米,而乃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吾恐火候未及调停,而锅已先破裂矣。”[6]83在王阳明看来,与其在勿忘勿助上思索,不如在事上磨炼,因为只在勿忘勿助上思索,容易成悬空测度,离事物,如烧锅煮饭,无有水而专烧,后果不堪设想。王阳明认为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已发之和,已弥补宋儒纠结于未发与已发的弊端,不在未发与已发上思索,而是转向格物致知做实功。然而,聂豹向来求之于心,若未得不敢认同他说,也没有继承王阳明良知贯中和的思维方式,却偏向于朱子心统性情、体用相离的思维方式,在未发与已发、良知与知觉等一系列问题上与同门之间有分歧。
二 双方争辩的焦点:从知觉返回良知,还是从知觉处见良知
聂豹把他与其他王学士人在良知与知觉之间的差别,概括为“今之讲良知之学者,其说有二。一曰良知者知觉而已,除却知觉,别无良知。学者因共知之所及而致之,则知致矣。是谓无寂感,无内外,无先后,而浑然一体者也。一曰良知者虚灵之寂体,感于物而后有知,知其发也。致知者,惟归寂以通感,执体以应用,是谓知远之近,知风之自,知微之显,而知无不良也。夫二说之不相入,若柄凿然。主前说者,则以后说为禅定,为偏内;主后说者,又以前说为义袭,为逐物。”[4]94-95在聂豹看来,讲良知说有两种,一种以知觉为良知,致知觉为致良知,不分寂感、内外、先后而浑然一体;一种以心之虚灵为良知,感于物而后有知,知其发,心之虚灵为未发,知觉为已发。主前说者以后说为佛教禅定,偏向内在,主后说者以前说为义袭,偏向逐物。聂豹言外之意,他属于后者,其他王门士人属于前者。
在阳明后学中,聂豹与欧阳德在良知与知觉问题上争论最多。欧阳德认为:“夫知觉一而已。常虚常灵,不动于欲,欲动而知觉始失其虚灵者。虚灵有时失,而知觉未尝无,似不可混而一。然未有无知觉之虚灵,而不虚不灵,亦未足以言觉,故不可歧而二。然此皆为后儒有此四字,而为之分疏云耳。若求其实,而质以古圣之说,则知之一字足矣。”[7]132他这样区分良知与知觉,可见一方面虚灵会被欲动所蔽,而知觉不会,知觉与良知不可混而为一;另一方面虚灵离不开知觉,又不可歧分为二。他认为,没必要如此分疏,知之一字可代表良知与知觉,一念之知,常动常静,常虚常灵,无有体用先后之分。他对良知与知觉的看法来自王阳明。王阳明认为:“心不是一块血肉,凡知觉处便是心,如耳目之知视听,手足之知痛痒,此知觉便是心也。”[6]121知觉是心,并非指心是知觉,而是意谓从知觉处解心。这是指点语。王阳明称知觉处为心,就是王畿所说“良知非知觉之谓,然舍知觉无良知”。[5]234王阳明、欧阳德、王畿等认为从知觉处见良知,知觉是良知之用,良知无形无相,然与外界接触,必然发用。这是他们强调良知不离知觉的原因。
聂豹不赞成上述王学士人从知觉处见良知的思路,指出:“浚原者,浚其江淮河汉所从出之原,非江淮河汉为原而浚之也。根本者,枝叶花实之所从出也。培根者,培其枝叶花实所从之根,非以枝叶花实为根而培之也。今不致感应变化所从出之知,而即感应变化之知而致之,是求日月于容光必照之处,而遗其悬象著明之大也。”[4]242他以本源与支流比喻良知与知觉关系,认为良知是江淮河汉之源头,知觉为江淮河汉之支流,主张应从江淮河汉之源头治理,而非从水之支流入手。以此看良知与知觉,知觉为感应变化之知,良知为感应变化之体,须致感应变化所从出之知,而非即感应变化之知而致之。聂豹与欧阳德在良知与知觉关系上最大的分歧在于,聂豹主张从良知源头入手,主宰知觉,立体达用;而欧阳德主张从知觉处见良知,虽然良知为知觉之体,知觉为用,但离知觉无从致良知,可谓即用达体。这是两者最大的分歧点。
聂豹认为:“良知本寂,感于物而后有知,知其发也,不可遂以知发为良知,而忘其发之所自也。心主乎内,应于外而后有外,外其影也,不可以其外应者为心,而遂求心于外也。故学问之道,自其主乎内之寂然者求之,使之寂而常定也,则感无不通,外无不该,动无不制,而天下之能事毕矣。譬之鉴悬于此,而物来自照;钟之在虚,而扣无不应。此谓无内外、动静、先后而一之者也。”[4]241良知本寂,指良知本体,感于物而后有知,指知觉,为心之已发。聂豹区别于欧阳德等人的地方在于,他强调知觉的源头,认为心主乎内,应乎外为影;以应乎外为心,就是义袭。这是聂豹指责欧阳德以知觉为良知的原因。为了避免求心于外,他主张主乎寂,寂而常定,可以感无不通,犹如镜子悬挂,物来则照,物去则镜子依然在,认为这样无有内外动静先后,一以贯之。
如果说,聂豹与欧阳德关于良知与知觉的争论还停留在一般讨论,他与王畿的讨论,显示出他要在良知学说上与王畿展开一番较量,证明学说的合法性。在阳明后学中,聂豹显得太孤单,好友罗洪先认同此说,刘文敏晚而信之。聂豹非常看重与王畿的讨论。王畿在王阳明逝世后,几乎成了王阳明学说的代言人,邹东廓、欧阳德皆受其点化,连罗洪先也是终生配合王畿思考良知学说,可见王畿慧解超人,不同凡响。聂豹在孤立无援之下,意图与王畿争辩,展示其学说并不特立独行,也符合王阳明学说。
聂豹在良知与知觉问题上,对王畿的良知见在说展开批判。他在答复陈九川的书信说:“窃疑其以灵明发见为良知,则今之以知觉为良知者,实本于此。”[4]299聂豹把今人以知觉为良知的主要原因归于良知见在说,其代表是王畿。王畿认为:“先师提出良知二字,正指见在而言。见在良知与圣人未尝不同,所不同者,能致与不能致耳。且如昭昭之天与广大之天,原无差别,但限于所见,故有小大之殊。若谓见在良知与圣人不同,便有污染,便须修证,方能入圣。良知即是主宰,即是流行,良知原是性命合一之宗。故致知功夫,只有一处用。若说要出头运化,要不落念、不成念,如此分疏,即是二用,二即是支离,只成意象纷纷,到底不能归一,到底未有脱手之期。”[5]81在王畿看来,王阳明的良知二字指见在。他认为圣人与凡人的良知皆见在,差别在于能不能致良知。他举例说,圣人与凡人的差别犹如昭昭之天与广大之天,因限于所见,故而有大小之别。他认为良知即是主宰,即是流行,换言之,是知觉之主宰,故而致知只在一念之知处用功,以此看待不落念、不成念,就是支离,意谓良知之体与发用之念打成两截,未能归一。他主张良知见在说,用功于一念之知,体用不可分,来源于王阳明。王阳明认为:“只存得此心常见在,便是学。过去未来事,思之何益?徒放心耳!”[6]24王阳明亦主张良知见在说。这里见在指现在,或者当下。过去已逝,未来还没来,良知只有在当下显现。王阳明认为,学者随各自分限致良知,扩充也好,开悟也好,皆是从见在或当下入手,此是精一之学。良知见在,就会发用出生生灭灭的念头,即“有善有恶意之动”,故而从见在致良知,在一念之知处做功。王畿亦主张于良知见在下手,只要念念为善去恶,方是致良知。他以良知见在说的立场反对分裂良知与念头,认为只保持良知之主宰,而忽略念头是支离。这主要针对聂豹。聂豹区分性体与念头,由生生灭灭的念头回转于不生不灭的性体,避免在念头上以任情为率性之病,但在王畿看来,聂豹分裂性体与念头,因为念头是性体之发用,两者不可分离,如果仅持守性体,忽略念头,落入支离之病。
聂豹不认同王畿的良知见在说,多次指责良知见在说之病。他说:“今人不知养良知,但知用良知,故以见在为具足,无怪也半路修行,卒成鬼仙。”[4]351又说:“尊兄称祖师三十年,今日自信其果为君子乎?为尧舜乎?岂无一念自反而得其本心之时乎?日月为云雾所翳,亦必雷动风散,雨润日晅,而后云雾始开。愚之可使为明,柔之可使为强,非困心衡虑,百倍其功,而能庶几于仁智者,鲜矣。若谓一念自反为进为之端,则可也。”[4]391他认为王畿一念自反之功太简易,并称王畿类似于禅宗学徒,称祖师30年。在聂豹看来,为学须渐修,不可能一念自反,便得本心。聂豹与王畿无法在顿悟路线上对话,偏向于渐修路线。他亦以这样的态度看待王阳明致良知说,他说:“师云:‘良知是未发之中,寂然大公的本体。’但不知是指其赋异之初者言之耶?亦以其见在者言之也?如以其见在者言之,则气拘物蔽之后,吾非故吾也。譬之昏蚀之镜,虚明之体未尝不在,然磨荡之功未加,而递以昏蚀之照为精明之体之所发,世固有认贼作子者,此类是也。”[4] 267聂豹对王阳明的“良知是未发之中,寂然大公的本体”产生疑问,这究竟是指人之初所赋异,还是指见在?如果以见在言之,人被气拘物蔽,犹如镜被昏蚀所遮,须磨荡方可恢复镜子之明,而世人却以昏蚀之照为良知所发。
三 双方争辩的原因:立体达用与即用达体的差异
比较聂豹与欧阳德围绕良知与知觉之间争论,表面上看,如罗洪先所说:“譬之于水,良知,源泉也;知觉,其流也。流不能不杂于物,故须静以澄汰之,与出于源泉者,其旨不能以不殊,此双江公所为辨也。”[10]聂豹主张从水之源头治理。从水之源头治理,可保证水之支流清洁吗?反过来说,欧阳德主张从水之支流治理,可保证水之源头清洁吗?仅从逻辑分析,聂豹与欧阳德的争论,谁也无法说服谁。聂豹有狱中体验做支撑,任凭欧阳德强烈争辩,皆不为所动,显示出他强大的自信,连好友罗洪先都说他有卫道情结。欧阳德多番与聂豹书信来往,不厌其烦,争论的焦点为良知与知觉。
由于聂豹与欧阳德的支援背景不同,导致他们各说各话,不能对话。聂豹继承宋儒朱子体用二分的思维方式,看到知觉或情在已发之后无法保证良知之先天义或圆满义,故而由已发退回未发,由知觉退回良知,主张良知即是未发之中,便自然能发而中节。他强调良知对于知觉的主宰义,以良知之体立知觉之用。欧阳德继承王阳明体用一源的思维方式,看到良知虽然圆满,但必须发用在事事物物上,表现为知觉或情,不能仅追求良知之先天义,良知必然表现为后天,故而由未发走向已发,由良知走向知觉,主张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即是已发之和。他强调良知在知觉上的发用义,由知觉之用见良知之体。聂豹是由体达用,欧阳德是即用见体。聂豹与欧阳德的对话不在同一视域之中,故而他看待欧阳德“今夫以爱敬为良知,则将以知觉为本体;以知觉为本体,则将以不学不虑为工夫。其流之弊,浅陋者恣情玩意,拘迫者病己而稿苗,入高虚者遗弃简旷,以耘为无益而舍之。是三人者,猖狂荒谬,其受病不同,而失之于外,一也。先师阳明子恫天下以闻见为学而不知,豫吾内以利乎外也,于是自吾性之虚灵精实者挈以示人,不谓其误而以知觉易闻见也。以知觉易闻见,均之为外也”。[4]78笔者认为,聂豹对于欧阳德的批评不合理。这里需要做区分的是,聂豹指责以知觉为良知,是欧阳德等王门士人遵循王阳明致良知之思路,还是当时一般学者以知觉为良知,这个区分十分重要。如果说,世间一般学者听闻王阳明致良知说,人人闻知良知,在事上磨炼,但容易误以知觉为良知,从已发来看,良知与知觉不好区分,对于一般学者来说有难度。聂豹一再指责“今人以知觉为良知者,真是以学术杀天下后世,此处不省,莫若别寻门路,不必再讲良知也。良知是未发之中,知觉乃其发用,犹云性具天下之有。《传习录》中若无此一线命脉,仆当为操戈之首。往往告诸同志,未有以为然者,岂予一人独病狂乎?若以为众论果是,仆亦尝是之,而今始知其非也”。[4]419阳明后学出现诸多争论,一方面是因为指责对方学说有缺陷,一方面是因为看到世间学者有流弊。这两方面他们往往不加区分,把一个学者的学说及其世间学者的流弊都认为是一个学者的学说所致,故而需要大加讨论,往往书信来回多番,为各自学说争取合法性地位。聂豹指责今人以知觉为良知,如果说一般学者对王阳明致良知说有误读,这种情况极有可能存在,毕竟心学由于高度精致化,很难让世人个个都能理解,从理论上讲,上智下愚皆可致良知。然而,阳明后学士人往往从现实中流弊出发思考学说的合法性,可见他们更从致良知说的效应入手,考虑如何修正王阳明的致良知说。聂豹严辨未发与已发,在阳明后学中引起极大争议,显得有些孤单,后来有好友罗洪先才认同此说,可谓孤调同弹。他之所以引起阳明后学士人极大反对,其主要原因在于,他没有像欧阳德、王畿等一样,在王阳明致良知说的大范围之下更加精致化。王阳明致良知说的最基本底线为体用一源,体不离用,用不离体,可以说王阳明致良知说的圆融特质在聂豹那里消减了。聂豹从开始问学王阳明关于勿忘勿助问题,显示出他偏向于思索,后来狱中体验更加树立起对于未发之中的强大自信,王阳明在世都不能说服聂豹,更何况在王阳明逝世之后,其他同门多次与他争论,都难动其心!聂豹没有理解欧阳德与王畿的理路,认为他们以知觉为本体,其流弊为恣情玩意,任知觉为率性,助长义袭,逐物而失心。王阳明看到世人以闻见之知为良知,故而提倡返回人之内在,格物以致知。聂豹看到知觉与闻见皆求之于外,却忽略人不仅有知觉,也有良知,诚如欧阳德所说,良知与知觉从理论上可分解,良知知是知非,知觉知痛痒,从实践上两者不可分。欧阳德与王阳明等人更从实际出发,人必然与天地万物相接触,一方面知觉起作用,一方面良知起作用。他们在格物之中致良知,保持良知之常惺惺,知是知非。聂豹指责欧阳德,表明他没有理解欧阳德的理路,实际上他们不在同一条路线,最终谁不能说服谁。
反过来说,欧阳德认为聂豹分心之体用,以良知为心之体,知觉或情为心之用,强调良知即是未发之中,容易落入禅定或偏内,这样的指责对于聂豹来说亦不合理。欧阳德立足于良知不分体用的立场,看待聂豹区分未发与已发,认为聂豹犯了分裂体用的大毛病,落入悬空之中,良知即是未发之中成了空壳子;然而,从聂豹的体用二分来看,他以良知指未发之中,保证良知之先天义,以知觉指发而中节,以良知之先天义主宰后天之知觉,聂豹所谓的未发之中并非测度空想的本体,而是与知觉相关联的本体,只不过以良知为主宰,以知觉为用,不会落入悬空之中,故而不会出现欧阳德指责的支离之病。
聂豹反对王畿的良知见在说,认为王畿良知见在说以见在为具足,这是对王畿良知见在说的误读。张卫红先生认为:“龙溪所谓的见在良知, 既包括常人当下的一念善端, 也包括念念安住于心体的一念之微。”[11]她分析双方关于“当下一念”的差别,指出王畿着重念念安住于心体的一念之微,聂豹从常人当下的一念善端理解当下一念,容易被私欲障碍,因此不能认同良知见在说。王畿强调从良知见在处用功,背后思维是良知不分体用,良知与知觉皆在发用处。王畿以昭昭之天与与广大之天说明圣人与凡人皆有良知本体,差别在于圣人能致良知,凡人不能致良知,聂豹却将其理解为人人以良知本体为具足,并且以知觉为良知。聂豹认为王畿主张不起意,乐超顿而鄙坚苦,崇虚见而略实功,可见他不能契入王畿的良知见在说。王畿主张不起意,动心起念,念念不迁流,是顿超直入良知,走顿悟之路。聂豹指责王畿崇虚见而略实功,这也是极大的误读。王畿的良知见在说难以理解在于,把良知与知觉皆统摄于见在或当下,从当下入手,以良知观照当下,既有来自王阳明良知见在说的理论根据,也是须念念致良知的实际要求,怎么说崇虚见而略实功呢?聂豹不能理解王畿的路径,认为“尊兄高明过人,自来论学,只从混沌初生、无所污坏者而言,而以见在为具足,不犯做手为妙悟。以此自娱可也,恐非中人以下之所能及也。”[4]377王畿高明过人,是阳明后学大部分士人对于王畿的评价。他喜从混沌初生、无所污坏处讲述,指良知之圆满义,无论致不致良知,良知皆在每个人身上,并且时时见在,处处见在,这是良知的本然状态。至于聂豹指责王畿不犯做手为妙悟,说中了王畿顿悟之路的特质。王畿良知见在工夫须一念自反,反身而悟良知本体,不能有思虑加杂。聂豹不能理解与认同王畿的顿悟路线,认为这非中人以下之所能及,这涉及修道中根器问题。王阳明认为四句教可以囊括上中下三根之人,上根之人一悟良知本体,本体即工夫,中下之人走渐修之路,即工夫以达本体,皆可以致良知。王畿是上根之人。他初入王阳明门下,王阳明为他开辟静室,不久即体证到心体,可见他属于早慧之人。聂豹好于思索,翻检古圣先贤书籍,求之于心,未可得而终不信,适于走渐修之路,聂豹与王畿在走何种路径上分开了。
综观聂豹与王畿在良知与知觉上的争论,聂豹主张良知为主宰,知觉为良知之所发,由知觉回转于良知,致未发之中;而王畿主张良知与知觉皆为一体,知觉处便是良知,良知必然发用,良知见在,一念自反,便得本心,念念为善去恶。由于两人的支援背景不同,聂豹走立体达用路径,王畿走即用达体路径,因此在良知与知觉问题上不能沟通,自说自话,找不到契合点。
由上面的辨析可见,阳明学者关于良知与知觉的争辩,基于各自的不同支援背景,发生激烈交锋。今天我们重新来看待这场争辩,可以得出双方的支援背景不同,导致双方无法从对方的视域来同情地了解对方,而是在固守各自的支援背景之下,一味地指责对方悖离了王阳明体用一源的圆融路线。双方对话的共同基础就是王阳明心学,恰恰面对共同的阳明学文本,却导致双方采取了不同的路向,一个是立体达用,一个是即用达体。这是为何呢?双方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是看到了当时王阳明致良知学虽然已经遍布天下,但学者们却面临着如何处理良知与知觉关系的难题。双方都认同个体生命不能分离良知与知觉,这是双方对话的共同背景,然而在如何下手处却产生了分歧。聂豹看到欧阳德、王畿等走即用达体路径,从良知与知觉一体下手,这样易造成“以知觉为良知”,有义袭之弊,遂而由外向内退,由知觉转向良知本体,先体证“未发之中”,再以良知本体观照知觉,运用朱子体用二分的思维方式。欧阳德、王畿固守王阳明体用一源或者舍知觉无良知的圆融思维方式,走即用达体路径,从知觉处致良知,既可体证良知本体,亦不会忽略知觉,其思路真是太圆融了!在他们看来,如果良知与知觉分离,由知觉转向良知,易出现向内静守,忽略向外格物的功能。欧阳德、王畿起点就是遵循王阳明体用一源的圆融思维方式,聂豹起点却悖离了这一圆融思维方式,这引起了欧阳德、王畿的警觉,他们强烈意识到了王阳明致良知学的危机,遂而联合起来保卫王阳明,与聂豹几番争辩,意图使他回心转意,重回王阳明圆融路线。非常有意思的是,聂豹面对同门的指责,反而认为自己坚持了王阳明致良知学,并且以《传习录》上部分作为自身学说的合法性依据,强烈反驳欧阳德、王畿的指责。结果双方谁也没有说服谁,欧阳德、王畿成了同盟,聂豹被孤立。
如今解读这一阳明后学的重要学案,“意为学术公案”[12],可以看出正是聂豹没有真正遵循王阳明圆融思维方式,树立强大的自信,不顾欧阳德、王畿的多次反对,才使得阳明后学百花齐放,为后来致良知学者提供了更多的借鉴途径。王阳明终生本就多变,更遑论阳明后学那么多学者呢?阳明学者多从纠正阳明心学被接受中的弊端为起点,采用不同的下手处,最终都向往进入王阳明心学的化境,只不过他们各自固守不同的支援背景,在阳明心学这个交叉点上越走越远,以致产生激烈争辩。
[1] 吴 震.聂豹 罗洪先评传[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9:84.
[2] 彭国翔.良知学的展开:王龙溪与中晚明的阳明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
[3] 林月惠.良知学的转折:聂双江与罗念庵思想之研究[M].台北:台湾大学出版中心,2005.
[4] 聂 豹.聂豹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5] 王 畿.王畿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6] 王阳明.王阳明全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7] 欧阳德.欧阳德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
[8] 朱 熹.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2011:94.
[9] 朱 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8:14.
[10] 罗洪先.罗洪先集[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474.
[11] 张卫红.当下一念之别:阳明学现成良知之辨的关键问题[J].浙江学刊,2007(4):44.
[12] 关永礼.学案体的创立、完善与嗣响[J].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学报,2016(1):58.
责任编辑:黄声波
Debate on Conscience and Perception of Yangming Scholars:Centered on the Debate Between Nie Bao and Ouyang De, Wang Ji
DONG Jiahe1,YANG Jin2,LI Wenwen3
(1. School of Political Science,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5, China; 2.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Public Management, Jiangxi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chang 330045, China; 3. Public Teaching Department, Nancha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Nanchang 330044, China)
Among Yangming scholars, the debate on the conscience and perception differentiates two different ways of thinking. Nie Bao,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one school, advocated that the conscience is neutralization, while the perception is harmony, and perception turns to conscience. Wang Ji and Ouyang De, as the representatives of another school, advocated that the conscience is not only neutralization, but also harmony, and conscience is found in the perception. Both schools criticized each other. Nie Bao thought that it was easy to lead to the drawback of chasing foreign objects since Wang Ji and Ouyang De looked for the conscience from the perception. While Ouyang De and Wang Ji thought that it was easy to cause the drawback of inward meditation since Nie Bao looked for the conscience from the perception. The two sides stuck to the different supporting backgrounds, and both followed Yangming’s learning principles. In fact, Nie Bao followed Zhuzi’s thought of separating ontology and function, and took the path from ontology to function, while Ouyang De and Wang Ji followed Yangming’s thought that ontology and function are of one origin, and took the path from function to ontology.
Nie Bao; conscience; perception; from ontology to function; from function to ontology
10.3969/j.issn.1674-117X.2017.03.013
2016-10-25
江西省社会科学“十二五”规划项目“江右王门良知学研究”(15ZX12);贵州省高校社科基地贵阳学院阳明学与地方文化研究中心招标项目“江右王门欧阳德思想研究”(2015JD099);江西省艺术科学规划项目“江右王学大生命观研究”( YG2016216)
董甲河(1984-),男,山东泰安人,江西农业大学讲师,博士,研究方向为宋明理学; 杨 瑾(1980-),女,江西上饶人,江西农业大学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 黎文雯(1981-),女,海南海口人,南昌理工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儒家哲学。
B248.2
A
1674-117X(2017)03-0067-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