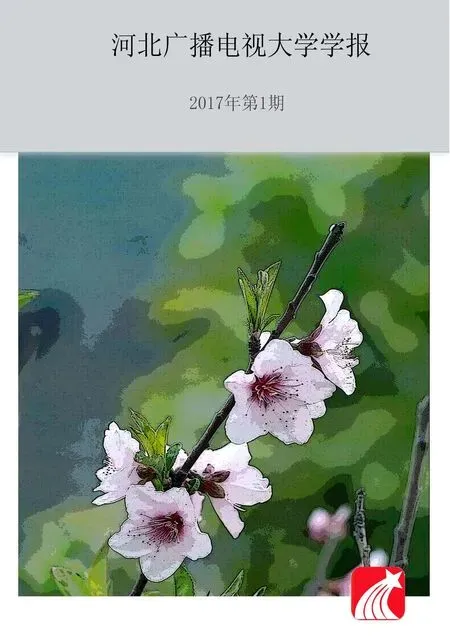地理景观对汉语的影响研究
——以“山”“河”为例
2017-02-23贾文红尹铂淳
贾文红,尹铂淳
(1.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2.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地理景观对汉语的影响研究
——以“山”“河”为例
贾文红1,尹铂淳2
(1.湖南科技大学 教育学院,湖南 湘潭 411201;2.湖南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语言表征可视为说话人心智中概念框架元素映射至外界的产物,探究它们的关系,有助于更深入地了解语言、心智、客观世界三者的本质关联。山、河是人们最早,也是体验最多的两种地理景观,于语言层面必存留其之“印记”,故以二者为例,探究地理景观对汉语的影响。汉语地理景观词语的语义演变受制于人们关于地理景观的概念框架(知识结构)。地理景观的概念化产物多被作为语言形式化的“原料”,其语用目的为增强表达的艺术性、经济性和形象感,且生成的表达亦受制于人们关于地理景观的概念框架(知识结构)。
地理景观;汉语;语义演变;语言形式化
地理景观指四周为天然界线所围绕的、性质上与其他区域有显著区别的地表区域,地理景观丰富多样,既有山、平原、河流、湖泊、海洋、森林、草原等自然景观,也有农田、工厂、矿山、道路、建筑等人文景观。
人在体验相关事物或事件后,会将关于它们之经验加以概念化,获得相关概念结构、系统或框架*概念框架可析为事物概念框架和事件概念框架,前者如“木头”“书本”“精神”,后者如“我吃饭”“我有一本书”“老虎生活于此”;事物概念框架又可进一步析为具体与抽象事物概念框架,分别如“木头”“灵魂”,事件概念框架可进一步析为行为、领有、存现、状态事件概念框架,分别如“我吃饭”“我有一台手机”“老虎生活于此”“你很帅”。,并存于心智之中;在对其他事物或事件进行语言形式化、象征化或语词化时,调动这些概念结构、系统、框架或称知识结构,并辅以相关认知操作,最终,生成语言单位,且这些语言单位中必然存留了些许上述概念的“印记”。山、河是人们最早,也是体验最多的两种地理景观,于语言层面必然存留了其之“印记”,即二者对汉语相关表达究竟存在哪些影响,引起了笔者的注意。
海山、高娃指出,在人类改造自然的过程中,经常会产生与地理环境相关的思想和情感,而它们需要用语言表达,故自然环境对语言有着巨大的影响。[1]马小梅对比了汉、英语与地理环境的关系,从地理位置、地形、气候和自然资源四个层面,细致探究了地理环境对语言的影响,并指出,语言文化处处保留着地理环境对它的烙印。[2]前贤的研究成果丰硕,但仍存可完善之处:于微观层面,缺乏对具体地理景观之于具体语言现象影响的探究;于认知语言学视角,缺乏对结论的进一步逻辑归纳、体系化。
基于前贤的研究成果,本研究以“山”“河”为例,拟解决以下问题:地理景观山、河对汉语地理景观词语*地理景观词语为词语的一种,是词语次范畴化的产物,其表征了事物概念框架“地理景观”。语义演变的影响有哪些?地理景观山、河对汉语表达概念框架元素语言形式化的影响有哪些?
一、 理论基础
1.隐喻
传统修辞学指出,隐喻为一种修辞手段,用以建构出具有较强修辞性的表达,认知语言学则更多地将其看作人类心智中的一种认知操作或思维方式、思维机制。Lakoff指出,隐喻的工作机制为:借用相对具体的、熟悉的事物或事件去说明或理解相对抽象的、陌生的事物或事件,且二者间存在相似性。[3]
2.转喻
同隐喻一样,认知语言学将转喻看作人类心智中的一种认知操作或思维方式、模式、机制。转喻的工作机制为:利用事物或事件易感知的、熟知的一个或多个元素去指代该事物或事件(部分代整体),亦或是用以指代隶属于它们的其他元素(部分代部分);再或是用事物或事件去指代隶属于它们的一个或多个元素(整体代部分),参与转喻的概念或元素间具有邻近性或相关性。[4]
3.语言形式化
经验经过概念化,成为概念,或称概念结构、系统、框架、知识结构。一个概念框架中,存在诸多元素,经由认知操作之加工,部分元素被凸显,其他元素被隐略,最终,被凸显的元素匹配以对应的语言单位,这个过程叫语言形式化。
一般来说,语言形式化可析为两大阶段——概念阶段和形式阶段。于概念阶段中,经由认知操作之加工,语言生成者,即说话人心智中概念框架中的元素部分被凸显,其他被隐略;接着,还需基于语言使用模型或语言构式,将被凸显之元素进行排序,最终以组合的形式存在;于形式阶段,将已排好序的概念组合匹配以对应的语言单位,最后一步,将概念框架投射于该语言单位,即以后者去标记或表征前者。
还需注意,语言形式化存在两种方式:一是以语言生成者心智中的概念框架为起点,如上所述;二是以语言单位为起点,首先,语言单位需激活一对应的概念框架,经由认知操作之加工,框架内的部分元素被凸显,其他元素被隐略,接着,被凸显之元素匹配以对应的语言单位。如,汉语网络缩略语“不明觉厉”,它的语言形式化过程如下:首先,语言生成者的心智中需存在语言单位“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但却觉得很厉害”,由此激活复合行为事件概念框架“虽然不明白为什么,但却觉得很厉害”,为了标新立异,以及模仿汉语四字格成语,故选择凸显该复合事件概念框架*复合事件概念框架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件概念框架进行整合的结果,且这些框架间存在诸多逻辑关联,如并列、因果、转折等。中之元素“不”“明”“觉”“厉”,凸显的方式为:以框架内的四个元素代整个框架,即转喻;接着,基于事件发展的自然顺序,辅以排序;然后,获得概念组合“不明觉厉”,最终,匹配以语言单位“不明觉厉”。再如,“白富美”的语言形式化过程:“高富帅”迅速且广泛地流行开来,吸引了网络语言生成者的注意,喜爱标榜个性、追求创新的他们定会尝试去仿造类似的语言单位,仿造过程如下:首先,经由语言单位“高富帅”激活一个浅层概念框架“高大、富有、帅气”,和一个深层概念框架“高大、富有、帅气的男性”;接着,凸显语言生成者心智中的事物概念框架“高挑、白净、富有、美丽、有气质、成功的、万人拥戴的女性”中的元素“白净”“富有”“美丽”,隐略其他,凸显的方式为类推,即通过“高富帅”中凸显的属性元素的类别和顺序,确定“高挑、白净、富有、美丽、有气质、成功的、万人拥戴的女性”中潜在的凸显元素及其顺序,即“白富美”;然后,以该元素组合代整个框架,最终,将该元素组合匹配以对应语言单位。[5]
二、对汉语地理景观词语语义演变的影响
地理景观对汉语地理景观词语(表征了地理景观概念的词语,如“山”“海”“河”等)的语义演变存在较大影响,详述如下。
1.对“山”语义演变的影响
“山”的本义为“地面上由土石构成的隆起部分”,即“山”,为一名词,如:
“山,土有石而高。”(《说文》)
“山,土之聚也。”(《国语·周语》)
“如山如阜,如冈如陵。”(《诗·小雅·天保》)
接着,本义进一步演变为“形状像山的东西”,如:
“刃树剑山。”(《南齐书·高逸传伦》)
此例中,首先,需确立“山”同“形状像山的东西”具有形状上的相似性,接着,前者将其与后者具有相似性的元素映射至后者,造成后者中具有相似性元素的凸显,语义层面,获得新义项“形状像山的东西”。
本义还演变至特指义“五岳”,如:
“奠高山大川。”(《书·禹贡》)。孔传:“高山,五岳。大川,四渎。”
“山”标记的为一事物概念框架“山”,“五岳”为“山”的具象体现,即前者隶属于后者,接着,以前者代后者,获得新义项“五岳”。
“山”还可作形容词,意为“大”,如:山嚷怪叫,太吵人了。演变的方式为转喻。于事物概念框架“山”中存在诸多元素,如“大”“仙人”“隐居之处”等,依靠框架,以“山”代“大”。
可见,倘若缺乏对地理景观山的概念化产物——事物概念框架“山”的足够了解,便难以发生上述隐喻和转喻,地理景观词的语义也不能成功进行演变。
2.对“河”语义演变的影响
“河”原专指黄河,如:
“河阳之北。”(《列子·汤问》)
“三豕涉河。”(《吕氏春秋·慎行论》)
其后泛指所有的河,如:
“南方无河也,冀州凡水大小皆谓之河。”(《汉书·司马相如传》)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春望》)
语义演变的方式为转喻,因“黄河”为“河”的具象体现,故“黄河”隶属于事物概念框架“河”,故以“黄河”代“河”(框架内一元素代整个框架)。
其后施指河洲,如: 河津(河边的渡口)、河润(指沿河湿润之地)、河濆(河边,沿河的高地)等。演变的方式为转喻,因于事物概念框架“河”中存在元素“河洲”,故以“河”代“河洲”(框架代其之元素)。
“河”义后演变至“天河”义,如:
“秋河曙耿耿。”(《诗》)
语义演变的方式为隐喻,因“河”同“天河”具有相似性:皆绵延不绝、清澈、具备流动性等,故“河”可将其与“天河”具备相似性的元素映射至后者,造成后者中相关元素的凸显,最终,以“河”去概念化“天河”,获得语义“天河”。
除了对“山”“河”语义演变有影响,对其他汉语地理景观词语的语义演变亦存在影响,仅以影响较大的二者为例进行论述。
如前所述,倘若缺乏对地理景观河的概念化产物——事物概念框架“河”的细致了解,便难以发生上述隐喻和转喻,地理景观词“河”的语义也不能成功进行演变。
综上,人们关于地理景观山和河的概念框架(知识结构)中的元素成为“山”和“河”语义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前提、基础,纵然拥有丰富的认知操作,倘若缺乏关于地理景观山和河的概念框架(知识结构),也是无法将“山”和“河”的语义进行演变。
三、对汉语表达概念框架元素语言形式化的影响
如前所述,在对其他事物或事件进行语言形式化时,调动心智中的概念框架,辅以相关认知操作,生成语言单位,且这些语言单位中必然存留了些许上述概念的“印记”,可知,在体验过山、河后,人们必然会将关于它们的概念框架的部分元素投射至所匹配语言表达之上,故本部分拟探讨山、河对“山”“河”相关表达概念框架元素语言形式化的诸多影响。
1.对“山”相关表达概念框架元素语言形式化的影响
“自认为‘山高皇帝远,砍树赚歪钱’,勉县新铺镇农民黄某乱砍滥伐林木,被依法取保候审。”(西部网2016年5月19日)
说话人欲表达概念“不会受到任何阻拦”,倘若缺乏与“山高”和“皇帝远”相关的知识结构,便不会以“山高皇帝远”去语言形式化上述概念。语言形式化的方式为转喻,因于行为事件概念框架“不会受到任何阻拦”中,位于逻辑第二层次的行为的原因为“山高”“皇帝远”等,依靠框架,以“山高”“皇帝远”代整个框架(行为的原因代整个框架)。
“中国和巴基斯坦之间比山高、比海深的传统友谊得到了两国历任领导人的悉心培育与推动。”(国际在线2015年4月17日)
说话人欲表达概念“程度很高”,可用的语言表征的数量很多,而说话人选择以“山”和“海”去语言形式化前述概念,在他看来,山是很高的,海是很深的,两个对象都是程度高的典型代表,即于状态事件概念框架“程度很高”中存在“比山高”“比海深”两个典型元素,接着,以后二代整个框架(框架内两个元素代整个框架),故语言形式化的方式为转喻。
“蟹状元阳澄湖大闸蟹:师恩重如山,致谢不如致蟹!”(楚北网 2016年9月9日)
说话人欲表达概念“老师的恩情深重”,此处为隐喻,将“恩情”比作“实物”。再者,于作者的心智中,最重的莫过于山,佐证为汉语表达“泰山压顶”,《西游记》中,神通广大的孙悟空也是为山所压。基于此,才有了表达“师恩重如山”。此处,语言形式化的方式为隐喻,首先,确立“师恩深厚”同“山很重”的相似性:程度皆高;其次,后者将具有相似性的元素映射至前者,导致前者相关元素的凸显。
“美网男单八强出炉,小德穆雷稳如泰山。”(乐视体育 2016年9月6日)
此处,说话人欲表达的意思为“八强对阵名单出来了,由于小德和穆萨水平高外加分到的对手实力不强,故可提前认定他们的位置非常牢固,不会被淘汰”。说话人并非直陈进行表达,而是选用了隐喻,实现机制如下:于事物概念框架“泰山”中,存在诸多元素,如“很高”“十分雄伟”“极重”等,其与事物概念框架“小德和穆雷的地位”具有相似性:皆是“重量”级的事物,接着,说话人将前者作为源域,用以概念化目标域“小德和穆雷的地位”,方式为隐喻。
山东因居太行山以东而得名,山西在太行山以西,故称“山西”。这也无不折射出概念的语言形式化的“原料”为地理景观的概念化产物,且受制于关于地理景观的概念框架(知识结构)。
2.对“河”相关表达概念框架元素语言形式化的影响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好汉歌》)
事物概念框架“河”中存在诸多元素,其中之一便是“向东流”,依靠框架,说话人/词作者才得以将概念语言形式化为“大河向东流”,而非“大河向西流”或其他,即关于“河”的概念框架中的元素决定、制约了语言的表征形式。
“河清海晏,时和岁丰。”(《日中有王子赋》)
“河清海晏”中,“河”施指黄河,“晏”意为“平静”。其字面义为黄河水清了,大海没有浪了。说话人欲表达概念“天下太平”,于状态事件概念框架“黄河水清了,大海没有浪了”中,存在对状态的评价“天下太平”,依靠框架,以前者代后者(框架代其之元素即对状态的评价),方式为转喻。
“俄美军再商空中相遇规则,确保‘井水不犯河水’。”( 新华网 2015年10月12日)
说话人欲表达概念“互不干犯”,可以选择语言表征“X不犯Y”,“X”与“Y”于人的经验中,处于一种“联系非常小”的关系之中,说话人选择以“河水”和“井水”作为“原料”,理据是说话人常体验河水和井水,并深谙其之关联“几乎无关联”。最终选择语言表征“井水不犯河水”。语言形式化的方式为转喻,因于行为事件概念框架“互不干犯”中,存在诸多元素,“井水不犯河水”隶属于其,故以后者代前者(框架内一元素代整个框架)。
“警营论坛:莫当暴虎冯河者。”(新华网2013年5月16日)
“暴虎”指空手搏虎,“冯河”指涉水过河。说话人欲表达的概念为“有勇无谋,鲁莽冒险”。于复合行为事件概念框架“空手搏虎,涉水过河”中,位于逻辑结构第二层级的行为的评价为“有勇无谋,鲁莽冒险”,依靠框架,以整个框架代“有勇无谋,鲁莽冒险”(框架代其之元素即行为的评价),故语言形式化的方式为转喻。
“历届四小花旦总能吸引万众目光,然而时光不会因一次评选而停止,漫漫长河女星发展史是谁一枝独秀?谁却江河日下?”(搜狐网 2016年10月13日)
“江河日下”指江河之水逐日流向下游。说话人欲表达的概念为“衰落”,于行为事件概念框架“江河之水逐日流向下游”中,位于逻辑结构第一层级的施事为“江河之水”,行为是“流”,于逻辑结构第二层级行为的方向为“向下游”,行为的评价为“衰落”,依靠框架,以整个框架代行为的评价“衰落”,语言形式化的方式为转喻。
和山东一样,如今,中国的省名多是以名山、大川的概念产物作为“原料”进行语言形式化,譬如,以黄河为界,语言形式化了“河南”“河北”,以洞庭湖为界,语言形式化了“湖南”和“湖北”。
综上,“山”“河”类表达较直陈表达更具艺术性、经济性和形象感,但倘若缺乏关于“山”和“河”的相关概念框架(知识结构),纵然说话人拥有丰富且复杂的认知操作,也难以生成“山”“河”类表达,即对周遭事物、事件的丰富体验是语言表达的前提和基础。
四、结语
语言表征可视为说话人心智中概念框架元素映射至外界的产物,故心智中关于地理景观的概念框架元素多被掺杂、糅合进入了语言表征,探究它们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更深入地了解语言、心智、客观世界三者的本质关联。本研究值得注意的结论如下:
人们关于地理景观的概念框架(知识结构)中的元素成为汉语地理景观词语义演变的决定性因素、前提和基础,纵然拥有丰富认知操作的人,倘若缺乏关于地理景观的概念框架(知识结构),也是无法将其之语义进行演变。
人们在表达一个概念时,可以选择直陈,亦或是找一个众人皆熟悉的认知参照点,去进行曲折表达,地理景观作为普及度极广的事物,可将其概念化的产物作为语言形式化的“原料”,语用目的为增强表达的艺术性、经济性和形象感,且该曲折表达主要受制于人们关于地理景观的概念框架(知识结构)。
“山”“河”语义演变的方式多为转喻,少数为隐喻。“山”“河”相关表达概念框架元素的语言形式化方式亦多为转喻,少数为隐喻。
因能力有限,本研究存在不足:未与英语相关语言现象进行比较或对比研究;地理景观定不止山和河,缺乏对其他之考察。这是下一步研究的方向和重点。
[1]海山,高娃.地理环境对语言的影响[J].经济地理,1998(2):124-128.
[2]马小梅.谈地理环境对语言文化的影响[J].西安外国语学院学报,2005 (1):35-36.
[3]Lakoff, G.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10.
[4]Ungerer, F. & Schmid, H. J.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1:114-116.
[5]尹铂淳,宋欣雄.“湘菜”概念框架元素的语言形式化研究[J].长江师范学院学报,2016(2):40-44.
Study of the Influences of Geographic Landscapes on Chinese Language ——The Case of “山”“河”
JIA Wen-hong1, YIN Bo-chun2
(1.Hunan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Xiangtan,Hunan 411201; 2.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Linguistic representations can be regarded as the products of the concept frame elements in speakers’ mind mapping onto physical world, exploring their relationship will help to gain a dee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essential relationship between language, mind and the objective world. Mountain and river are the two earliest physical objects people experience, in the linguistic level their “marks” must be retained in the language. So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influences of natural landscapes to Chinese by taking mountains and rivers as examples. The semantic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ic landscape words is constrained by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knowledge structure) of geographical landscape. The conceptual products of geographical landscapes are mostly used as “materials” for formalization of language, and their pragmatic purpose is to enhance the artistic, economic and visual sense of expression, and the generated expression is also subject to the conceptual framework (knowledge structure) about geographical landscapes.
geographic landscape; Chinese language; semantic evolution; linguistic formalization
2016-12-05
湖南省语言文字应用研究专项课题《汉语网络缩略语规范化研究》(XYJ2015GB13)
贾文红(1994-),女,湖南常德人,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学科教学(地理)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地理教学、普通语言学研究。
H0-05
A
1008-469X(2017)01-006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