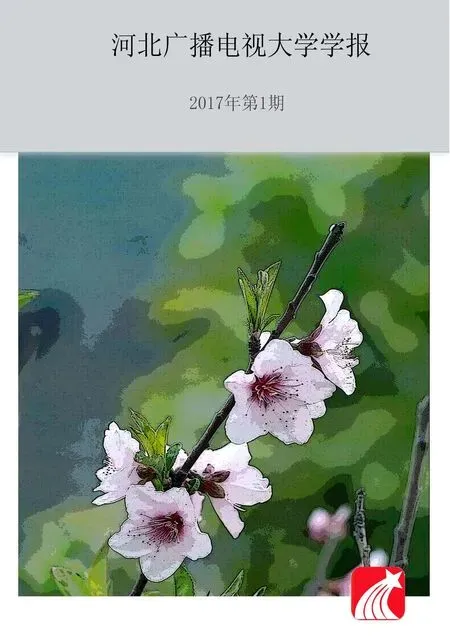论杜甫诗歌中仕与隐的矛盾性
2017-02-23焦丽波
焦丽波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论杜甫诗歌中仕与隐的矛盾性
焦丽波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杜甫的诗歌被称为“诗史”,足见其诗歌与时政的密切关联,他以敏锐的眼光、热忱的胸怀去关注时事,写下了许多动人诗篇。而这些诗歌,也恰恰反映了他的人生态度。通过他的诗歌,探寻其中体现的诗人对政治生涯的追求与现实仕途失意之间的冲突,虽使其萌生归隐之意,但内心却始终不能完全摆脱向往政治上有所作为的矛盾心理。杜甫诗歌所体现的诗人对于政治生涯与人生道路的选择,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他的人生态度,而反过来又对进一步理解其诗歌提供便利,并可以认识到他崇高的人格魅力。
杜甫;出仕;归隐;矛盾;统一
杜甫作为唐代诗坛乃至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位巨星,其诗作不仅数量颇丰,且质量上乘。他离世不久,就享受到崇高赞誉:元稹在为杜甫撰写的墓志铭中就表达了对他的赞赏,认为他是中国最伟大的诗人,甚至把他置于诗仙李白之上。其后更是有众多诗人追随他,以他为楷模,从其诗作中汲取营养。然而,相比他逝去后的辉煌,他的生前可以说是相当凄惨的。在他的一生中,贫苦交加、颠沛流离,空有一腔抱负而无法实现,而正是这种处境,使他不得不通过诗歌来排解内心的忧愁愤懑,留下了一首首脍炙人口的经典诗篇。他的诗作被人们赋予“沉郁顿挫”的风格,正是与他的生存状况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他的诗作常常浸透着忧愁、绝望,却能给人无限的斗志与抚慰,是后人在逆境中最爱阅读的诗作。文天祥在狱中就专读杜甫的诗,并借其诗句抒发情怀,把他的五言诗集成了二百首五言绝句。杜甫一生中漂泊无定,或仕或隐,他的一生就是在追求仕途与求而不得,无奈退隐又心系天下的矛盾中度过的。关于杜甫仕隐矛盾的研究,对我们更进一步地理解杜甫的诗歌,可以提供一定的帮助,也让我们对杜甫的人格魅力有更深的把握。本篇文章主要从三个方面阐释杜甫思想中仕与隐的矛盾,探究其产生的原因、表现的阶段性及在诗歌中的体现,以期对这两者有一个全面清晰的认识。
一、坎坷的经历、复杂的思想是杜甫仕隐矛盾产生的缘由
杜甫在文坛被称为“诗圣”,不仅是因为其诗歌艺术方面的成就,更重要的原因是他诗歌中蕴涵的关怀家国天下的爱国精神,这正是儒家所提倡的。张戒在《岁寒堂诗话》中说:“然子美诗,读之使人凛然兴起,肃然起敬,《诗序》所谓‘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者也。”孔孟提出的恻隐之心、治世情怀,深刻地影响着杜甫,这是杜甫被称为“诗界圣人”的重要原因,而这种情怀也正是导致杜甫仕隐矛盾产生的重要缘由。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思想使其孜孜以求于仕途,想要有所成就,而现实的坎坷、仕途的曲折却使其求仕之路困顿难行。遭受挫折时他头脑中的释道思想促使其产生归隐的念头,却又隐而不得,因其心中的一腔热忱,使他难以做到抛却世事、游走于人事之外。他的诗歌反映的始终是民生,而非单纯的模山范水,他心系百姓,借诗歌以抒怀、以泄愤。可见,坎坷的经历和复杂的思想是其仕隐矛盾产生的缘由。
杜甫的思想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汇。他出生于一个有悠久传统的“奉儒守官”家庭,为晋代名将杜预的第十三代孙。他的祖父杜审言也是女皇武则天时期的著名诗人和官吏。[1]他对于先辈十分崇敬,尤其是十三世祖杜预,十分钦羡其建功立业的不菲成就。家族传统对他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使他自始至终都抱有济世为民的宏愿。他在《进雕赋表》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矣。”[2](P1)然而,现实总不及理想美好,他屡试不第,虽因诗才及忠心获得过一些小官职,但总是不能施展抱负,也不懂得为官之道,最终只得弃官不做,四处漂泊。他的儒家积极入世的心态是显而易见的,然而他的治世之才却不及其诗才那样光芒万丈。他怀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纯”的美好愿望,但现实中动荡不安的政治环境却无法给这株嫩芽一片肥沃的土壤。清人杨伦道:“自是腐儒大言,在他人亦不敢说。”唐人往往敢说大言,而李杜尤其如此。说他们是“腐儒”,就因为他们不知审时度势,对所处时代与自身环境缺乏清醒的认识。[3]后来即使他被赐予官职,仍因刚直不阿,直言极谏而被贬,在被贬地,因当地环境恶劣,仕途不顺,心情烦闷不堪,遂弃官不做。可见,他追求的仕途不是满足于小官小吏,而是想官至宰相,像诸葛亮那样获君主信任,好施展一番抱负。然而,这只是他的自我催眠,世事不与野老便,总有豪情也枉然。在这样一个战乱横行、朝政腐败的年代,杜甫不得志的结局已经注定,但他怀抱的一腔“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热忱,便使其命运更具有悲壮性,更容易令人产生共鸣。于是,在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境况下,他思想中道、佛因素的影响,便显现出来。如果说道教的影响还与仕途、朝政有关的话,那么他后期受佛教思想影响时,便可以说已经对世事的无奈与无常有了深刻体会。他不再意图迎合皇族对于道教的崇拜,也不再幻想炼丹圣术以求长生不老,他渴望的是远离世事的纷繁复杂,寻一净土,以慰余生。然而,他头脑中的儒家思想始终占了主导地位,即使在他生命后期,对佛教的兴趣很浓,但仍然难以割舍家庭和世俗生活,去脱离尘世、遁入空门,“未能割妻子,卜宅近前峰”。在他心中,儒家的伦理道德仍然高于一切,是他必须遵守的准则,难以割舍。
杜甫自幼因家庭影响而抱有济世宏愿,且他前35年都生活在中原河洛之地,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深厚且纯正,坚守又持久,因此不管他身处何种境地,都能够保持一颗忧国忧民的热忱之心。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隐逸思想大多因用世不得而产生,并且产生有着这样的轨迹,即用世不得而转向愤世,愤世不过是徒增痛苦罢了,于是又转向避世乃至于忘世。这在哲学上就表现为从孔子儒学走向道家庄学。[4]而杜甫之所以想要隐逸,也不是出于自愿或者功成身退,而是不得志、对政治失望而远离朝野,这只是其愤世之举。当他在成都草堂居住了一段时间后,又不安于现状,终于还是选择离开草堂,回归中原,他的内心始终难以摆脱“学而优则仕”这种思想的影响,始终是想要于政事和百姓有所裨益。当他远离朝野、飘零无依之时,仍能由己及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古人云:“在其位,谋其政。”杜甫虽是一介草民,却仍能心怀天下,不计较自己的利益得失,怎能不令人为他的人格魅力所倾倒。
儒释道三种思想并存于他心中,彼此斗争,处于此消彼长的状态,然而儒家思想始终占主导地位,支配着他一生的道路选择,不论他在朝在野,都心系天下,胸怀百姓,忠君爱国。正是他思想中这三种因素的斗争支配着他的人生路始终在仕与隐中徘徊。当然,这三种因素是与他遭受的仕途艰辛共同起作用的。在杜甫士气高涨,誓有一番作为之时,他头脑中的释道因素就会潜伏,满心地想要出将入相,报效朝廷,尽己所能献计献策。在杜甫仕途受挫时,他头脑中的释道因素才迅速膨胀,压制儒家思想,起到较大作用,促使其产生归隐的念头。但归隐终究不是他的心愿,他始终想要于政事有所作为。坎坷的经历使他为官而不得,复杂的思想却令他于坎坷仕途中可做短暂停歇,使他能够在后半生的漂泊中内心有所寄托,有所追寻。在释道思想的守护下,儒家思想始终影响杜甫,终身追求于民有益。
二、杜甫思想中仕与隐的矛盾纠葛在各时段的表现
杜甫一生中安定的时日无几,但漂泊流浪的日子颇多,积极入世的热情在遇到现实打压时他确实萌生过退意。在他的人生中,有几个时段都出现了退隐山林的念头,其中包括壮游时期、“度陇客秦州”时期和成都草堂时期。[5]这几个时期,他的归隐念头都一度压制住了出仕的幻想,使他能暂时放下济世救民的夙愿,寻一幽静地休养生息。但他的隐居不同于陶渊明与政治彻底决绝后的归隐东篱,也不同于王维倾心佛教的退隐山野,他的心中始终都对国家人民有着不可割舍的牵挂。仕途失意时愤世远游,但又因心系天下而再次踏上寻求仕途之路。要说他思想中的仕与隐是一对矛盾,其实两者之间更为统一,归隐只是仕途不顺时的栖息,是出仕前的蛰伏。
1.壮游时期思想上的回归儒家
杜甫在735年末736年初,初到京兆,参加科举考试,自视颇高的杜甫在这次科考中却败兴而归。失败是始料未及的,他只能“独辞京兆堂”。在他35岁(746年)再到长安之前,为求学和游历阶段,靠父辈宦途积蓄,生活过得颇为得意,“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
壮游时期的他曾与李白过有一段寻仙访道的日子。这一时期经历过科考失意的杜甫深受道家思想影响,于山水间自得其乐,暂时抛弃了追求仕途的念头。此时杜甫心中的隐逸思想显然是占据上风的。然而寻找仙丹的失败、思想中儒家意识的回归,和他对政治、对人民的热情,使他最终放弃了这种生活。这种寻仙访道的日子,毕竟过于缥缈,他劝诫李白道:“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表现了对求仙生活的怀疑。可见,壮游时期出现的隐逸念头是极不成熟的,甚至可以说是在仕途中稍有挫折之后的暂时逃离,是借蕴藏心中的道家思想来实现的一次游离。因此,在道家理想破灭,儒家出仕理想又生之后,他再到长安,以期获明主垂怜。
2.“度陇客秦州”时期的失意退隐
又入京兆的杜甫意气风发,誓有一番作为。他渴望有明君来发现他这个人才,给他一个报效国家的机会。然而屡试不第,使他感到现实的黑暗与生活的困顿。前途并非一片光明,明君不再,奸臣当道,贤人进仕无路。而他却是百折不挠的,尽管在长安的求仕生活过得十分艰难。“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他也始终怀有儒家积极入世的心态。在天宝十四年(755年)夏,杜甫历经9年求仕,终于因“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6]当年,又逢安史之乱爆发。次年,杜甫在赴任路上被叛军抓住,但他逃出之后,并非去寻个战火未波及之处避难,而是风餐露宿,潜奔凤翔投奔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朝廷悯生还,亲故伤老丑。”可见,杜甫远把家国利益置于个人安危之上。
这一时期的杜甫,一心求仕,即使仕途艰难,仍不屈不挠。杜甫以其一片赤诚之心,获君主垂青,授官左拾遗,但在同年五月,耿直正义的杜甫就因上书为房琯说情而触怒了肃宗,几被处死,幸得宰相张镐、御史大夫韦陟相救获免。后奉墨制放归鄜州省亲,十一月始得返朝。杜甫始终不得重用,在华州司公任上时终因华州旱灾,无以为生,加上世途险恶,心情苦闷而辞去官职,远赴秦州,开始了长达12年的避难生涯。在此之前,他都是专注于仕途,然而世事艰辛,他终于为仕途艰难所击退,萌生了退隐的念头,他头脑中的出仕之心暂时被归隐之意压倒。杜甫在《立秋后题》中,表达了归隐之意。“罢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唐书》本传:甫为华州司功,属关辅饥,弃官客秦州,此诗盖欲弃官时作。[7](P228)但这未尝不是诗人的自我说服:罢官也不过是由我做出选择罢了,什么事能拘束我的身体,我的自由。然而这样的事不少啊,隐居后的经济来源,对朝政对百姓的关怀,这都牵绊着他,即使远离朝廷,内心仍激荡着对政事的关怀,仍不能完全脱离世事纷扰。尽管决定隐退,他内心中仍为世事牵绊。
杜甫经历了仕途的艰辛,认识到了世态炎凉、政治昏暗,见到百姓们流离失所、艰难维生,他写下了一首首记载史实的诗篇,尽管对朝政失望,但仍心系黎元,为陷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百姓发出不平的呐喊。《三吏》《三别》道出了他对穷苦人民的深切同情。虽然他提出了想要归隐田园的愿望,但秦州并没能留住杜甫,薪资的匮乏使其连归隐生活也难以维持,而又无厚禄故人可托,使他不得不又开始辗转流浪的日子。《空囊》曰:“翠柏苦犹食,明霞高可餐。世人共卤莽,吾道属艰难。不爨井晨冻,无衣床夜寒。囊空恐羞涩,留得一钱看。”生活如此凄苦,尚能自嘲解愁,非胸襟广阔之人不能至此。秦州非桃源之地,杜甫不得不另觅他处。于是他取道赤谷、铁堂峡、寒峡、青阳峡、凤凰台,迁居同谷,后又辗转至成都,开始了浣花草堂的一段轻松时光。
3.成都浣花草堂时期的离世定居
杜甫在浣花草堂居住了共有5年之久,虽然中途离开过一段时日。这是他一手创造的世外桃源。蜀中之地,远离战火,又有友人的资助,杜甫得以安顿下来。杜甫在这里的生活可以说是怡然自得,因此他心胸开朗,创作也带了许多活泼明朗的色彩,他在这里创作的诗作一改前期的沉郁顿挫、悲愤幽怨,而色彩明丽、清新动人。杜甫在友人的资助下,寻地、建草堂,向友人索要喜爱之物,也乐于施予他人。他写了很多向友人索物之诗,《从韦二明府续处觅绵竹》曰:“华轩蔼蔼他年到,绵竹亭亭出县高。江上舍前无此物,幸分苍翠拂波涛。”《又于韦处乞大邑瓷碗》曰:“大邑烧瓷轻且坚,扣如哀玉锦城传。君家白碗胜霜雪,急送茅斋也可怜。”他有一颗扶危济困之心,在穷困时安心接受别人的帮助,也更能体谅艰难度日的穷苦百姓的处境。他自己常怀恻隐之心,也劝诫别人能有一颗容人爱人之心。《又呈吴郎》中便展现了他对穷苦大众的体谅与感同身受。“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须亲。即防远客虽多事,便插疏篱却甚真。已诉征求贫到骨,正思戎马泪盈中。”他认为人人都应有恻隐之心,既有余力,便要助人,因此他安心接受别人的帮助,毫不见外,而自己也非一味索取,而是以己之力去帮助那些更弱小的贫民。他从内心体谅他人,若不是穷困到无以为生,怎么会到别人家打枣果腹呢?可见,杜甫是拥有高尚灵魂的,他虽常怀一颗求仕之心,但不是为了一己的荣华富贵,而是想要国家安定,百姓生活富足。在他穷困潦倒时,甚至还高唱:“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这慷慨悲歌怎能不令人为之动容。
在草堂,他拥有众多淳朴而善良的邻居,这不是老子理想中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那种虽安乐但又稍显冷漠的社会,而是像一个大家庭似的左邻右舍相处甚安的村落。杜甫闲时会四处游荡,享受着大好春光,欣赏着湖光山色,感受着邻里和睦,维系着人间温情。《北邻》《南邻》是杜甫描写邻里相处的诗作。“时来访老疾,步屟到蓬蒿。”邻人来访,老迈的杜甫身心愉快。“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7](P329)秋水初生,偶出同游,至月上而归也。有时兴致来了,也会漫步江畔,在融融春光中独步寻花,远邻黄四娘家花已满蹊,那千万朵花充满了生机与活力,引来了翩跹的蝴蝶,在黄莺娇俏的歌声中自在起舞。这一派美景、乐事都使经历过战火洗礼、见识过人间惨境的杜甫那布满伤痕的心得到了抚慰。蜀中之地的清幽生活,是诗人喜爱的,这段时日,他内心得到安歇。除邻人之外,杜甫的诗名也吸引了不少在蜀地避难的高官文士前来探看。《宾至》《有客》写出客人时来拜访。“岂有文章惊海内?漫劳车马驻江干。竟日淹留佳客坐,百年粗粝腐儒餐。”沈云:二句自谦,实自任也。[7](P319)杜甫门前宾客不息,实在非真正的归隐,虽仍未完全放下求仕之心,但此时的杜甫内心之中归隐的想法占据了上风。“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虽家贫但在客人面前却不卑躬屈膝,而是真诚地拿出浊酒来招待,并且此时还不忘自己的近邻,“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在他心中,人无高低贵贱之分。他与文人官吏交好,也和平民百姓亲近。这里有良好的人际关系,有充足的经济支持,还有美好的风土人情,杜甫的忧国忧民之心终于可以得到些许慰藉,就连看到下雨,他都会喜不自禁,赞叹道:“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一草一木、一滴雨一片云都能让他感到快乐。
这段浣花草堂的隐逸时光可以说是杜甫自35岁寻求仕途生涯以来久违的安宁时光。然而令人感到遗憾的是,杜甫始终没能真正归隐,不过这也是他本性中那忧国忧民情怀的体现。他在远离战火与朝政的地方,在生活安定的情况下,心中仍有苦闷,内心充满斗争。试看《江亭》一诗:“坦腹江亭暖,长吟野望时。水流心不竞,云在意俱迟。寂寂春将晚,欣欣物自私。故林归未得,排闷强裁诗。”他的内心始终是惆怅的。万物各随其性,而自己却飘零他乡,唯有以诗排解忧愁。在唐代这个儒释道并行的社会中,仕与隐之间的对立已逐渐消弭。魏晋时仕与隐绝对对立的状态已经得到了改善,当时仕与隐是一种政治抉择,一旦未做好选择,便有可能遭人耻笑。而唐代,仕与隐却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孟浩然在《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中写道:“欲济无舟楫,端居耻圣明。坐观垂钓者,徒有羡鱼情。”在山水诗中也呐喊贤人举荐,可见入世心态多么强烈。杜甫作为这个时代中儒家思想根植脑中的诗人,在安逸的生活中又生出出仕之心。后由于故人去世,他又担心时局,思念故地,生出了北归之心,求仕之心又占上风,最终离开成都,但终因百年多病而在下峡途中去世,充满凄愁悲怆的一生就此画上了句号。
三、杜甫仕隐思想在其诗作中的代言者——诸葛亮与陶渊明
杜甫有很多咏史之作,借古人事迹抒自我情怀,他的人生态度、仕途选择也借这些诗传达出来。他一生中不得志的时间居多,因此在忧愁凄怆的生活之中便不免思及前代得志或不得志的仁人志士,以排遣自己的忧愁愤懑。诸葛亮和陶渊明是杜诗中经常出现的两个历史人物,杜甫在诗中多次提及他们,尤其是诸葛亮。诸葛亮与陶渊明实际上是代表杜甫仕与隐思想的理想人格,是抒发其理想的代言人。
1.杜甫诗中仕的代言者——诸葛亮
诸葛亮是杜甫积极求仕思想的代言者。他是三国时蜀国的丞相,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辅佐刘备及幼主竭心尽力,因此得到后人的高度赞扬与推崇。尤其是在蜀地,人们更把其崇高化。杜甫在成都草堂期间,多次游访武侯祠等地,并写下了多首赞美诸葛亮的诗,拔高了诸葛亮的地位,并且使他的形象得以定型。“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杜甫如此歌颂诸葛亮,除了受当地传统影响之外,更重要的是诸葛亮的遭遇令他感同身受。诸葛亮在北伐失败后的挫败感和无力感,激发了杜甫的认同和共鸣。杜甫为诸葛亮感到惋惜,更感慨他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与毅力是如此悲壮与崇高,诸葛亮出师未捷身先死的宿命是颇符合西方古希腊文化中的悲剧精神的。
杜甫为他的悲惨结局感到痛心,但也钦羡其得遇明君。在《谒先生庙》一诗中杜甫渲染和赞扬了诸葛亮与刘备的君臣“鱼水情”,[8]《诸葛庙》也描写了这种君臣情:“君臣当共济,贤圣亦同时。”刘备作为君王的完全信任和诸葛亮作为宰相的绝对忠诚,多次为我们的诗人所提及。[9](P153)杜甫渴望明君,希望有志之士都能得明君赏识,以建构一幅明君贤臣的和谐画面。这些诗主要作于成都及他移居夔州之时,而成都草堂的生活是他的隐居时期,如此看来也只是蛰伏时期,而并非真正想要隐居,他仍然渴望着明君贤臣,渴望着仕途顺遂,功成名就。出将入相是他一生的夙愿,然却始终不得志。
2.杜甫诗中隐的代言者——陶渊明
陶渊明是杜甫归隐思想的代言者,他作为“古今隐逸诗人之宗”(钟嵘《诗品》),创造了世人心向往之的“桃花源”,后世归隐者或多或少都受其思想和诗作的影响,杜甫也不例外。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的崇高气节也正是杜甫所推崇的。杜甫性格耿直,不畏权贵,不与恶势力同流合污,与陶渊明何其相似。他更是学习陶渊明的亲力亲为,在隐居期间躬身劳作,而不是像很多隐居的士大夫一样整日纵情于山水之间。他在隐居时和百姓始终保持一种友好的人际关系,对百姓寄予深切的同情和关爱,比陶渊明更加贴近百姓的生活。
杜甫避难蜀中时,刚经历仕途挫折、生活失意的他决心隐逸。仕途无望,只能饮酒遣兴,这和五柳先生不谋而合。杜甫与陶渊明在精神上有很多共鸣也是可想而知的。正如《可惜》一诗中所说:“花飞有底急,老去愿春迟。可惜欢娱地,都非少壮时。宽心应是酒,遣兴莫过诗。 此意陶潜解,吾生后汝期。”[10]远离政事纷扰,可惜又已年纪老迈,感叹春光易逝,只有异代的陶渊明才能理解自己的落寞之感。浣花草堂时期他的创作也多借鉴陶诗的典故,甚至化用整篇入诗。然而,杜甫毕竟不像陶渊明那样“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杜甫本性就是“奉儒守官”的,因此也就不能像五柳先生那样彻底地和朝廷决裂,不为五斗米折腰,他始终想为朝政为百姓效力。因此他虽然想要追寻陶渊明隐居的那种世外桃源的日子,但内心终究有所牵挂,不能完全与世隔绝。最终又踏上了北归之路,死于途中。
3.杜甫诗中仕隐矛盾的见证者——孔子
除了诸葛亮和陶渊明以外,孔子也是杜甫诗中不可忽视的一个人物形象。杜甫早期自视甚高,“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凤凰是典型的的儒家人格的写照,杜甫追求的是像凤凰一样光照大地,为国为民带来祥瑞。但杜甫空有一腔热忱,在政治上却基本是失败的,且不说“志君尧舜”的理想未能实现,自己的生活有时都难以维持。当他仕途坎坷,为皇帝所疏远之时,他开始表示出对儒家思想的愤激与怀疑:“伤哉文儒士,愤激驰林丘”(《送韦十六评事充同谷郡防御判官》),“儒术于我何有哉,孔丘盗跖俱尘埃”(《醉时歌》),“兵戈犹在眼,儒术岂谋身”(《独酌成诗》)。然而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始终是不可拔除的,尽管仕途中存在着坎坷,杜甫在短暂休整后终是难忘家国,又踏上求仕之路。孔子形象的刻画是见证其思想中仕与隐矛盾的斗争的。杜甫甚至提出了“吏隐”一说,“浣花溪里花饶笑,肯信吾兼吏隐名”(《院中晚晴怀西郭茅舍》),“闻说江山好,怜君吏隐兼”(《东津送韦讽摄阆州录事》),[2](P4)想要实现对儒家的超脱,在关心家国的前提下,实现内心的解脱,使内心得以安歇。但他的忧国忧民思想使他终难得到真正的解脱,始终是百姓的代言人,写出了首首可歌可泣的佳作。
不论是仕是隐,杜甫的心中终究无法彻底割舍对朝廷的向往,他始终走在求仕的路上,尽管有时会因为仕途坎坷,有所停歇,却从未止步,他始终在路上,为了国家,为了黎民,用自己的心血谱写了一曲曲壮美的诗歌。
四、结语
杜甫的一生中有太多坎坷,但这种种挫折也促成了他的创作,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大家地位。这仕与隐的矛盾贯穿了他的一生。洪业先生在其杜甫研究的著作中说道:“终其一生,他始终在两个相互矛盾的愿望中徘徊:退隐山林间,或是置身庙堂上。贫穷和家庭责任感始终是妨碍第一个愿望的重要原因,不良的健康状况和忠言直谏的责任感则是第二个愿望的阻碍因素。”[9](P149)尽管杜甫有过归隐的努力与实践,但其内心中却始终抱有出仕的热忱,这是他深受儒家思想熏陶的必然结果,也是其忧国忧民的本质所致。他的一生,不论是穷是达,都记挂着百姓的安危,始终想兼济天下。他始终都是把家国利益置身于个人利益之上。他崇高的人格魅力和悲惨命运形成了巨大反差,而他却能于苦中作乐,自嘲着笑对人生。其光辉形象确实有动人心魄的魅力,吸引着后世众人向他学习、致敬。
[1](德)莫芝宜佳.《管锥编》与杜甫新解[M].马树德,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161.
[2]鲁克兵.论杜甫儒释道思想的消长[J].玉溪师范学院学报,2008(5).
[3]杨景春.杜甫人生态度与文化渊源[J].湖南城市学院学报,2009(1):41-47.
[4]刘长东.论杜甫的隐逸思想[J].杜甫研究学刊,1994(3):21-22.
[5]顾勤.浅谈杜甫的归隐情节[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008(6):127-129.
[6]邓乐群.杜甫流寓梓州的浣花草堂情节[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3):126-131.
[7]杜甫.杜诗镜铨[M].杨伦,笺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8]符丽平.杜甫对诸葛亮形象的完美化及原因[J].襄樊学院学报,2012(4):12-16.
[9]洪业.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M].曾祥波,译.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10]辛晓娟.何处觅桃源——论陶渊明对杜甫蜀中诗的影响[J].文艺界(理论版),2012(1):132-133.
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Choices of Being an Official or a Hermit in Du Fu’s Poems
JIAO Li-b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China)
Du Fu’s poetry is called “the history of poetry”, which shows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poetry and the current affairs. With a keen eye and warm heart he paid much attention to current affairs and wrote many moving poems. These poems just reflect his attitude towards life. His poems show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pursuit of political career and the frustration of the official career. Although he had the intention of seclusion, he couldn’t completely get rid of the ambivalence of being a good officer. The choice of the poet’s life path and political career reflected in Du Fu’s poems can help us to better understand his attitude towards life and, in turn, to facilitate the understanding of his poems and realize his lofty personality charm.
Du Fu; to be an official; seclusion; contradiction; unification
2016-11-14
焦丽波(1992-),女,河北阜平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硕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典文献学研究。
I207.227
A
1008-469X(2017)01-005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