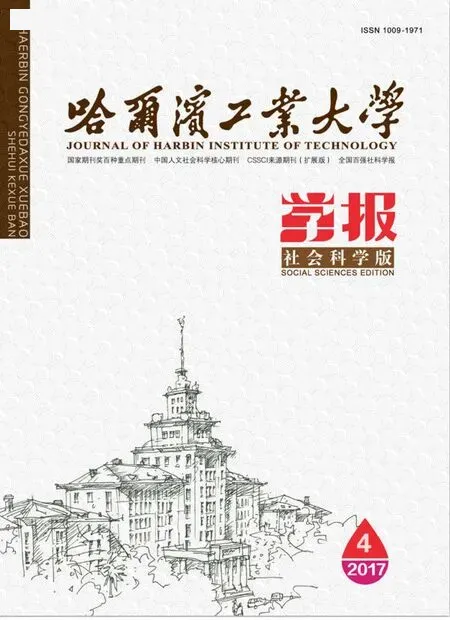生活记忆及其方法价值
2017-02-23赵丽娜
赵丽娜
生活记忆及其方法价值
赵丽娜
(江苏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江苏镇江212003)
生活记忆是指人在生命历程中追寻生命意义的行动体系的自我再现和经验认知,它融主观性与客观性、个体性与集体性于一身。常人方法学、扎根理论、口述史等方法的研究均证明,生活记忆是探寻过往社会结构样貌、了解社会变迁动因的有效路径。对生活记忆的探讨是将个体再一次在意识中置身于过去某一特定时空的一次叙事,是对特定时空中的“经验人生”和“生活体验”的重现,因此基于生活记忆探寻社会发展历史,能够做到研究起点、过程与终点的本土性,并且为未来社会发展寻找根基,保持社会文化的历史连续性。如果把生活记忆融入空间研究,能够使得对空间的诠释更加饱满、灵动,且能够解决就空间而谈空间建设与规划所导致的区域特色消失的问题。
生活记忆;口述史;本土化;地理空间
生活是个体与社会的中间纽带,也是社会的本源。它对社会结构而言具有基本的建构功能。正是基于此,当研究社会动态历程、尤其对过往社会结构与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的回溯,生活记忆尤为重要。从生活记忆中,不仅能够以虚拟在场的状态审视社会的变迁和某一时空下的社会结构,同时鉴于社会的连续性,从生活记忆也能够找到合理的社会发展未来之路。已有学术研究中指出了研究生活记忆的几个视角:从文学作品中研究作者对某种生活的记忆[1];从历时态的角度研究某一地域内人的生活记忆的变迁[2];将生活记忆概括为民居建筑、市井生活、美食等[3]。但是关于生活记忆内涵与外延的学术界定较为鲜见。在缺少清晰概念的背景下,对于生活意义的方法层面价值讨论就非常少见。本文从生活概念开始界定生活记忆的内涵与特征,并讨论其在方法中的意义,分析它对于社会科学研究而具有的本土性视角价值,最后结合当前备受关注的空间记忆讨论生活记忆的丰富性和人文关怀。
一、生活记忆的内涵与特征
为了给予生活记忆以明确概念,需要从生活定义入手。所谓生活是指人的特有生命形态的社会性存在、展开和实现形式及其意义追寻的行动体系[4]。基于生活的内涵,所谓生活记忆便是指人在生命历程中追寻生命意义的行动体系的自我再现和经验认知。其中,关于形式的记忆是具有典型表象的,属外显浅层记忆;关于意义追寻行动体系的记忆则是深层内隐的记忆。生活记忆的这两个层面决定了其具有如下特征:
其一,客观与主观的综合。生命的展开与实现不能脱离物的支持,生活记忆中必然有物的痕迹。关于物的那些记忆具有一定的客观性,比如食物、房屋、服装、生活空间样态等。但是,由于涉及意义的追寻,所以在生活记忆中会有所追求的意义对记忆主观的导向。人们会着重甚至放大与自身的意义系统相关的方面,忽略甚至回避那些与自身的意义取向无关的内容。由于这样的主观性,记忆可能会存在片面、放大甚至遗漏。恰如心理学研究所表明的,关于生活的记忆会因暗示性面谈、想象、误传等生成错误记忆,带来“想象膨胀”[5]等主观性问题。当然,关于记忆表述中伴随的主观评价也正为社会发展寻找正确方向提供了契机。
其二,个性与共性的综合。记忆既是个体的,也是集体的。“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由具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的‘异质性’人群组成的,但人们在同一个社会‘屋檐’下生活又必须具有‘共同性’,因此社会是‘异质共存’的组织体系”[6]。在生活记忆中,每一个人对过去的生活(包括生活的样态、环境、意义指向)都会有属于自己的理解和期待,因此每一个人的生活记忆都是自己的而非他者的。不能否认个体记忆因主观性往往具有杂乱、破碎的表征,但是不应因此就主张作为私人叙事的个体记忆与作为宏大叙事的集体记忆之间是对立的或支持集体记忆覆盖、涂抹个体记忆。个体的差异并不影响城市生活记忆的集体性。在同一时空下的群体,对该城市在该时间段上的记忆总是会有共性特征,这些共性特征是那些客观的物质和时代背景所决定的。更多的事实表明,不同个体之间在生活记忆上的协商会产生共鸣的集体记忆,同时私人叙事的多样性为我们审视集体记忆,发现集体记忆的有待协商之处,尤其“记忆微光”为我们更全面地研究、审视记忆提供了契机[7]。
二、生活记忆在方法层面的重要价值
虽然由于出身受到自然科学影响以致诸多社会学理论流派都偏离了生活本真,但是方法视角对生活、生活记忆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本源性的关注却并不少见。“加芬克尔的本土方法论(又称常人方法学),坚定地把社会学的立足点转移到日常生活领域中,明确主张要用日常人的方法来研究社会现象”[8]。本土方法论对生活世界的关注将人作为主体并将主观性研究提升到了主体地位,并坚定地认为对生活的研究是本土性的研究。扎根理论则更进一步,在探寻基于经验资料建立与创新理论的道路上,它强调“研究材料的经验性和日常生活性是非常重要的,一切资料必须源于日常生活,研究是为了解决日常生活中的实际问题”[9]。本土方法论与扎根理论从方法意义层面强调了生活的核心价值。
法国学者布罗代尔在考察15—18世纪资本主义发展时指出,社会的变迁要到日常生活结构中去寻找源头[10]。从社会发展的真实进程来看,自然仅仅围绕“日常生活”是不够的,但是结合日常生活中的生命存在、展开与实现形式,以及非日常生活的生命意义系统来回顾社会变迁、认识社会进程却是可行而且具有重要价值的。对此,口述史的研究方法直接揭示了生活记忆对社会科学研究、尤其是对史学研究的重要性所在。应当说,鉴于需要有一定量的口述者存在,并且是对大量访谈记录整理基础上的深入研究这样的条件限制,决定了口述史与访谈是绝不相同的,作为一种生活化的研究方法,口述史试图通过对已转化为大脑记忆的生活世界的语言回顾,再现一个社会结构或某一独特情景,毫不夸张而言,生活记忆是口述史的根基。以英国口述史研究的应用为例,“主要应用于社会史领域,特别是农村史、城市史、妇女史、家庭史、儿童史等,都是采用口述史学方法,从日常生活史的角度研究一个地区、一个社会群体、一个阶层的人们的社会生活状况”[11]。在汤普逊关于口述史的价值论述中,说到“口述史课题不仅能够激发人们的智力,而且有时也能够通过走进他人的生活发现深层的、活生生的人类经验”[12]。因此,在运用口述史进行研究中,他人的生活记忆是起点,寻找到与他人生活记忆的共鸣之处是深入展开的关键。对此,在进行口述史研究方面,也需要满足的是:“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因此,这种过去的事实只要和现在生活的一种兴趣打成一片,它就不是针对一种过去的兴趣而是针对一种现在的兴趣的”[13]。可以认为,生活记忆从微观细节着眼,在被研究者的回忆中,研究者在某种程度上以一种在场的感受经历了过往社会细节。这一切都如同雷蒙·威廉斯在“感觉结构”概念下所指出的:“各种不同的人们通过自己生活历史的片段,以及由学者们以口述历史、日记、自传和小说等文本来建立这种感觉结构,因而产生某种地方感,由此塑造出一种乡土、宗族、民族等文化思想和情感空间”[14]。
三、生活记忆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本土视角
如果说方法论陈述了生活记忆的重要性,那么一些学术研究的分析中,呈现了生活记忆对研究社会及社会结构变迁的本源性价值。费孝通先生对他研究中国农民生活的动机和时代背景的阐释直接指明了生活的本土性。他说:“在国内是军阀混战、经济衰落、民不聊生的时期。社会学开始提出中国化的要求。”[15]也可以理解为费孝通先生是想通过生活的研究找到中国社会研究的本源入口。
将对生活的关注具象到生活记忆,其本土性更加突出。作为对人与社会互构过程与结果的记忆,是通过叙事的手段对过去的“经验人生”和“生活体验”的回溯,是将个体再一次在意识中置身于特定时空的一次叙事。叙事本身的过程与结果清晰或混杂地再现了不同个体或群体在空间中如何通过行动展开和实现生命并建立起独特符号以呈现或确认自我身份,进而可以挖掘出过往生活的场域(如政治与文化情景等)。当然,如若简单来说,地域范围内的生活记忆具有本土性这是多元要素共同制约的结果。生活内嵌于文化,受制于历史,且受制于具体的经济、政治,它不仅仅是地理要素所制约的。因此生活记忆是此地、此文化、此历史共同规约的结果,它所呈现的是本土的历史与变迁脉络,是本土的风土人情与文化框架。在叙事中通过对生命展开、实现形式以及一追寻系统的回溯,可以挖掘到那时那地的社会本真。如胡俊修在其研究中,讲到“理发”这一生活活动时举例:“在老武汉的记忆里,民国初年武汉男子革命彻底,在剃头担子处拿掉辫子,就剃光头,直到后来西洋飞机头流行,富家公子趋之若鹜,进理发店剪新式发型,穷人也纷纷效仿,再耻于剃‘和尚头’;而平民女子在解放前总是蓄辫梳头,那些阔太太、小姐则请专门的梳头女上门给自己扎辫子花样,一些阔太太、小姐、高等妓女还经常光顾理发店烫发,让人侧目相看,而当时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因为头发太长梳不动,到理发店把头发剪短后,被母亲打了一耳光,告诉她‘那是婊子才去的地方’,后来幸亏邻居相劝,这女孩才免遭一顿痛打”[16]。从这样的生活细节记忆中,可以看出武汉社会变迁中所经历的这一特殊时期的阶层、群体生活差异,社会政治样态,价值观念的隔离,等等,这所呈现的是该地域空间的样貌,必然与其他地域空间有所差异。
进一步以城市研究为例,来理解生活记忆为社会科学研究提供的本土视角。对城市现代化建设的反思和后现代城市建设的思路,提出了对生活记忆这一本土特色视角的研究需求。如果说现代性带来的是全球化、同一性,尤其表现在城市建设方面,忽视地理区别的钢筋混凝土搭建,高楼大厦拔地而起,那么后现代的城市建设则对现代化结果进行了全盘反思,并提出了本土性的要求。经验证明,无视自身特征的追求现代化建设带来了诸多城市问题,包括隔离、矛盾、历史的消逝、归属感的剥夺等。而以生活记忆来审视城市变迁历程,恰能够找寻造成城市问题的那些根源,追溯城市的历史挖掘存在之根,找到符合本土本地现实情况的城市未来建设之路。对于城市研究而言,生活记忆的价值体现在以下方面:
首先,生活记忆对城市历史的呈现是以全景视图的方式实现的。一方面,生活记忆可以呈现定点时间段内的城市生活全貌。以金岳霖先生回忆录中的一段话为例:“从1932年到1937年夏,我们住在北总布胡同,他们住前院,大院;我住后院,小院。前后院都单门独户。30年代,一些朋友每个星期六有集会,这些集会都是在我的小院里进行的。因为我是单身汉,我那时吃洋菜。除请了一个拉东洋车的外,还请了一个西式厨师。‘星(期)六碰头会’吃的咖啡冰激凌和喝的咖啡,都是我的厨师按我要求的浓度做出来的。”[16]从这段回忆中我们从城市某一小群体的生活主体、客体、样态(形式)可以窥见那一特定时期的城市文化、建筑、关系网络等的状态。如果我们能够获取更多主体在该城市中、在那段历史时期的生活回忆,通过回忆文本的归纳、比较、演绎便能够呈现社会发展全貌。另一方面,生活记忆是城市历史动态路径的再现。如日本的“地域社会学”借由对生活变迁的研究,发现了社会变迁的历程,指出通过洗衣、做饭等生活行动从家庭成员承担到依赖于洗衣店、食品加工点的变化,社会的生活供给结构经历了从家庭自给到市场化的转变,并进一步指出“生活社会化”所带来的结果是国家作用越来越强、家庭功能趋于缩小和社会共同体趋于衰亡[17]。通过对过往生活供给环境、生活具体行为、生活意义系统的回忆,能够梳理出社会(包括城市社会)的动态变迁历程。
其次,生活记忆是城市未来发展保持本土方向的保障。城市是生活的空间,生活是城市自我彰显的路径,更有学者通过指明城市化是一种生活方式[18],从而指出城市与生活的不可分割性与一体性。Jones M J.,Wilson E.,Bridenbaugh C.,王雅林,王伟武等人的研究[19-23],指明了生活研究对城市研究的重要意义。当然也暗含了城市动态中对生活动态研究的必要性。然而,立足于芒福德的“城市是靠记忆存在”的观点回顾已有关于城市的研究,尤其对城市历史的研究,一些成果由于缺乏对生活的关注,使得研究中呈现的城市更像是一座空城,且无个性[24]。可以说,纵向流动的生活链构成了生活记忆流。通过对生活记忆来研究城市的变迁是一个有价值的视角。原因在于,生活记忆是纵向的积累,所经历的历史脉络是此地每一时点的流;从生活记忆来看城市的变迁能够揭示城市过去发展的本土特色。同时,因生活记忆提供了社会认同与文化的连续性,在全球化背景下,只有通过对过往生活记忆的回溯才能够使我们重新构建自我,才能够找到未来回归到本土特色的发展方向。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只有生活记忆能够帮我们扭转雅各布斯提出的西化世俗空间对城市的洗劫,找到城市本真与本源的个性特征。因此城市研究中,在本土化探索的进程中生活是有效的切入点。
我们看城市的变迁与发展,是在从本土的需求来探索变迁的路径、经验和寻找未来的合理之路,而这一切都是针对内部主体的生活而展开的。因此无论我们想要形成具有本土性的经验,还是要抽象本土的需求,甚至对未来的规划,都应关注生活记忆。
四、生活记忆与地理空间的关系
生活与空间不可分割,也可以说空间与生活的研究不可分割。空间研究当然也涉及生活空间,涉及生活区隔,等等。而生活研究则必然涵盖了空间问题,尤其人们从其生活需求或欲望视角审视的空间。生活记忆必然包括了空间背景记忆——从前台空间和后台空间对生活的“空间”记忆进行研究,讨论城市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的结构与构成的变化,分析空间的特色与功能的变迁。如纪录片《北京记忆》在对空间进行诉说时,是结合着生活记忆着手展开的。如在“东区西区”中的一段话:“西区宁静内敛,东区热情开放,两个区,两种生活……这些90年代后陆续出现在东区的豪华建筑,当年曾经是高档生活得象征。甚至连建筑本身也曾经对当时的年轻人产生过吸引。……东区生活彻底改变了北京城的生活方式,它成为北京人心目中现代化、国际化生活的示范区。”在研究中,生活记忆视角的空间研究能够给予城市地理空间以实质意义。
生活记忆的融入能够弥补单纯空间记忆的单维性。之所以要将生活记忆和空间记忆结合梳理,主要原因是目前对城市空间的研究较为热点,人们从城市地理学、空间社会学等视角展开城市空间的研究,然而缺乏主体的空间记忆往往是空洞的。生活的融入能够使得空间记忆饱满、灵动。原因在于,空间依托于地理展开研究,探讨空间物理结构基础之上的社会蕴意,这具有起点的单维性。不可否认起点的单维性具有双向意义:一方面有利于研究的聚焦,可以就空间布局与结构而叙事;另一方面却容易陷入无法全面揭示城市全貌的困境之中。而且只回顾空间结构不应当成为空间研究的终点。虽然空间记忆的物理基础决定了其客观性的一面,但是没有内涵意蕴的空间回顾总是不足的。生活记忆具有多维性,生活的生命实现形式记忆与意义追求行动体系记忆是多层面的,涉及了在城市中生活的基础表现形式及自我感知。这个层面的记忆是客观与主观的融合。当从生活回忆中挖掘空间历史,不仅能够再现空间布局,更重要的是能够从生命存在、展开与实现的形式和生活意义的追寻维度,探知空间历史形成的原因与社会性价值。
生活记忆以“人”的关怀为出发点,弥补了单纯的空间研究从物的关怀入手的不足。空间研究与实践的历史证实,虽然社会发展中一再声称本着人性关怀而进行空间改建,但是以城市为例,可以发现,无论是已经发生的城市美化运动、田园城市建设还是城市规划等,都完成了空间的隔离和在某种程度上拒绝多样性,尤其是抵制或消解了多样性的融合。以规划图纸或地图形式体现出来的空间分配所表征的是权利与经济的合谋,在城市中这种合谋尤为突出。直至晚近时期,关于空间分配的社会学研究才崭露头角,但是影响甚为有限。相比较而言,生活记忆从人的关怀开始。通过对生活记忆的追溯,不仅能够描绘出人所感知的城市空间布局,更能够通过人的主观性观点的介入发现人所期望的城市空间样态,从中能够找到空间的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差异所在和弥合之路。尤其当社会发展朝向人的生活福祉而努力迈进的道路上前进,人从生活视角对城市过往的回顾是未来城市空间规划建设的有利依据。有这样一个例子,“据报载:一位海外朋友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某位政客在拉选票时,不停地谈论今后会怎样为当地搞更多的钱。在场的一位老太太听着听着就插话说,我们的钱已经够花了,现在最需要的是我们的孩子还能够到海边捡贝壳”[25]。恰是这种对过往生活的感怀向往,提出了空间建设中的未来前景,那就是需要保障孩子嬉戏的空间场所,空间建设不能破坏美好童年的生活体验。
无论如何需要认识到,单纯地就空间而谈空间建设与规划,容易走向现代主义的共性取向,其结果是造成了空间建设的统一性,类似于美国城市建设经验中的高楼建筑、街道规划等得到广泛推广。于是越来越多的城市在空间外观上形成了无差异化的局面,生活于城市中的主体在游走于不同城市之间时往往抱怨“千城一面”。在已经形成的同一化现实下,生活记忆是回归本土特征道路上的有力动力。生活的特性决定了它更倾向于后现代主义的和欧洲化的本土性,从生活记忆入手寻找城市建设的方向与特色,能够做到起点的本土性和归点的本土性。
而在基于地理空间区隔的生活记忆比较分析方面,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深入探讨。生活记忆研究从属于微观研究,对生活世界的关注从个体入手,从微观而细微的日常“自在性”生活,或追寻意义系统的“自为性”非日常生活入手,那些记忆具有琐碎性,因此需要从琐碎的对象中抽离出系统线索。而空间研究则具有宏观—中观—微观的综贯特征。基于这一特性,地理空间对生活记忆具有一定的规约作用,主要体现为不同空间区位的记忆主体会有显著的生活记忆差异。包括芝加哥学派的一系列研究指出了城市地理区位具有区隔功能,区隔之下的亚群体对城市生活的记忆必然有差异。这是空间制约的生活记忆。
生活在不同地理区位的居民对公共空间的感知不同。处于设施齐全、便于获取优势资源区域内的居民,与生活在棚户区或贫困者聚居空间内的居民,在城市生活的记忆上会有巨大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空间仅是一个载体,很显然它更多地是由空间所承载的资源、权力、文化价值等所决定的。同时,生活在不同地理区域中的公民,在区隔之下对自身生活记忆的重点有所差异。在空间与权力的区隔之下,生活于不同空间中的居民对城市生活记忆的重点会有选择性的不同。疲于应付生存问题的社区中的居民在城市生活中更多的会去记忆那些与生存相关的事项,并会选择记忆那些体现了生活不平等问题的事项。而掌控资源社区中的居民,在生活记忆中更可能会频繁呈现自我优势与不同。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探讨了生活记忆的抽象概念与内在特征,并从方法层面对其价值进行了讨论。客观与主观、个性与共性的纠缠,在创造了生活记忆特殊性的同时,也为生活记忆作为方法基础奠定了根基。其方法价值不仅体现在对口述史的支撑,还表现在它的本土性价值和对空间研究的补充。生活记忆的回溯为社会科学的本土化研究提供了有效路径,其有效性体现在它的全景视图及居民期望的兼顾与呈现。诚然,在探讨空间研究中,生活记忆的研究与空间纠缠不可分割。从生活记忆视角切入空间研究能够赋予空间以丰富而灵动的内涵与价值。然而,必须看到本文所探讨的内容是宏观叙事,它指明了生活记忆研究对于本土化研究需求和地理空间研究所具有的现实意义。然而,宏观叙事需要能够落入微观叙事的具体问题视域中,如何能够在微观叙事中将基于生活记忆的城市本土化研究具象化,是值得深入探讨和研究的,这也是本文没有指明的。
本文在生活记忆与空间研究的关系讨论中,指出了生活在不同地理区域中的公民,对自身的行为方式与意义系统的记忆会有差异,并且针对差异的存在原因进行了一些猜想式的分析,但是,这些猜想是否全部成立?是否优势地理区域内的居民,更多的时候会合理化自我行为并为他们所追寻的意义系统建立官方辩护渠道,而生活于不利地理空间中的居民,他们的生活记忆我们猜测更多地会表现为在回忆中寻找生活不利的外部因素,并会阐明他们所践行的意义系统的被动地位?对于这一问题是需要通过实证来检验的。
[1]唐菁.追寻乡土之美——华兹华斯与海子的乡土生活记忆[J].文学界:理论版,2011,(7):46-48.
[2]陈薇.城市“历史·记忆·生活”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及求解[J].世界建筑,2014,(12):50-51.
[3]周翔,李智.街巷里的生活记忆中的景观——成都铁像水街设计与营造[J].城市建筑文化,2015,(5):212-215.
[4]王雅林.生活范畴及其社会建构意义[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5):1-12.
[5]张磊,郭力萍.基于日常生活的记忆研究进展[J].心理科学,2002,(3):347-349.
[6]王雅林.“生活论”研究范式的构建——日本社会学研究的启示[J].社会学评论,2015,(4):19-29.
[7]刘亚秋.从集体记忆到个体记忆——对社会记忆研究的一个反思[J].社会,2010,(5):217-242.
[8]刘少杰.现代社会学理论承诺与理论原则的矛盾[J].社会学研究,2002,(2):64-71.
[9]文军,蒋逸民.质性研究概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230.
[10]FERNAND BRAUDEL.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15th-18th Century[M].Berkeley,CA: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11]梁景和,王胜.关于口述史的思考[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10-15.
[12][英]保尔·汤普逊.过去的声音:口述史[M].覃方明,等,译.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204.
[13][意]克罗齐.历史学的理论与实际[G].何兆武.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5221.
[14]李凡,朱竑,黄维.从地理学视角看城市历史文化景观集体记忆的研究[J].人文地理,2010,(4):60-66.
[15]赵旭东.费孝通对于中国农民生活的认识与文化自觉[J].社会科学,2008,(4):54-61.
[16]胡俊修.口述史:武汉城市社会研究的“活材料”[J].江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12):75-79.
[17]蔡驎.地域社会研究的新范式——日本地域社会学评述[J].国外社会科学,2010,(2):12-19.
[18]AMIN A,THRIFT N.Cities:Reimagining the Urban[M].Polity Press,2002.
[19]JONES M J.Cities and Urban Life[M].Baston:Pearson Education,2012:162-92.
[20]WILSON E.The Sphinx in the City:Urban Life,the Control of Disorder,and Women[M].California:Univ of California Press,1992.
[21]BRIDENBAUGH C.Cities in Revolt:Urban Life in A⁃merica,1743-1776[M].Oxford:Oxford Univ Pr,1971.
[22]王雅林,董鸿扬.构建生活美:中外城市生活方式比较[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03.
[23]王伟武.杭州城市生活质量的定量评价[J].地理学报,2005,60(1):151-157.
[24]吴静,忻平.城市化与社会生活——“历史记忆与近代城市社会生活”学术研讨会综述[J].2011,(10):121-126.
[25]王雅林.中国学术:与生活同行[J].哈尔滨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1):1-4.
Life Memory and Its Value
ZHAO Li⁃na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Jiangs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Zhenjiang 212003,China)
Life memory refers to the self-reproduction and empirical cognition of the action system in which people pursue the meaning of life in the life course.This memory is subjective,but it is also objective.Although each person has his/her own life memory,there are common characteristics existing among everyone's life memory in a certain society.Ethnomethodology,grounded theory,and oral history studies show that taking advantage of life memory,we can detect reasons for social change,and reveal past social structure.Meanwhile,asking someone to remember his/her life memory means putting this specific individual in a cer⁃tain native past society.All the life experiences being native,this can make sure the study is native.Combi⁃ning life memory with space can help space study to be more personalized and space design to be more color⁃ful.
life memory;oral historiography method;localization;geospatial
C913
A
1009-1971(2017)04-0050-06
[责任编辑:唐魁玉]
2017-04-13
江苏省教育厅2016年度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一般项目(2016SJB840012)
赵丽娜(1982—),女,黑龙江七台河人,讲师,博士,从事城市发展、文化资本、消费行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