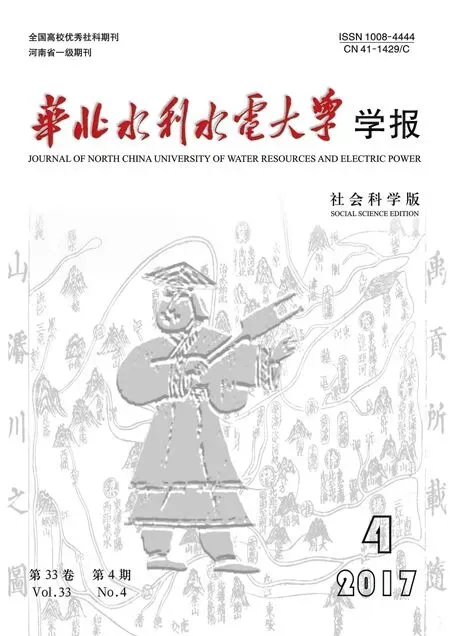国际政治中安全困境的理论分析
2017-02-23耿进昂
耿进昂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国际政治中安全困境的理论分析
耿进昂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首先从国际政治理论中安全困境的概念入手,分析安全困境的内涵和本质;再从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和建构主义等学派的不同角度,分析国家之间安全困境产生的原因;最后依据不同学派的理论和观点,寻找国际关系中安全困境的出路。
安全困境;现实主义;无政府状态
国际政治学领域中经常提到的安全困境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基础性概念,也是国际政治学者研究国际关系规律的一个核心概念。安全困境普遍存在于国际社会的过去和现在。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只要主权国家仍然是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还会持续存在,并仍将极大地影响着国际关系的发展和稳定。
一、安全困境的概念
安全困境这一重要概念首先由美国学者约翰·赫兹在20世纪50年代初提出。其《自由主义者的国际主义与安全困境》一文详细而深刻地阐述了国际政治中安全困境的概念。赫兹认为,安全困境是一种社会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下,当权力单元(如国际关系中的主权国家)在国际体系中共存时,它们会发现没有超越它们之上且能规范其行为并保护自身免受攻击的权威。在这样的条件下,从相互恐惧和相互怀疑而来的不安全感迫使这些单元为寻找更多的安全而进行权力竞争,由于完全的安全始终无法求得,这样的竞争只能导致自我失败[1]321。
身为历史学家和权力政治学家的英国政治学者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将安全困境称为“霍布斯主义恐惧”。他这样描述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在这样一种局面下,你会对其他国家有现实的恐惧感,别国也会对你有着同样的恐惧,也许你对别国根本无伤害之意,做的只是一些平常的事情,但你无法使别国真正了解你的意图。你无法了解别国为什么会如此的神经质。反之亦然,在这种情况下,双方都以为对方是敌意的、无理性的,都不肯作出可以使大家都获得安全的保证。军备竞赛的不断升级,就是这种状态的产物。”[2]57英国政治学者肯·布斯也认为,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就是存在于国家间的互相猜疑、互不信任,乃至互相敌视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恶化源于一国对另一国军事准备的疑虑和恐惧[3]30。
国际政治中的安全困境与囚徒困境具有某种相似之处。处于囚徒困境中的国家互不信任,相互疑忌,唯恐对方加强军备是针对自己。为了避免受挫、在国际争端中处于劣势,每一方都作出扩张军备的战略决策,武装力量成螺旋状上升,从而导致安全局势更加恶化,还导致地区安全局势恶化。如果博弈的双方都是国家集团,囚徒困境(安全困境)会导致世界安全局势恶化,甚至爆发世界大战。一战前的协约国和同盟国、冷战中的华约和北约就是囚徒困境中的博弈双方,只是前者双方引起了世界大战,而后者双方都慑于核武器的毁灭性才让世界逃过一劫。
在国际关系实践中,往往是某一个国家努力追求自身绝对安全,想方设法拥有军事上的优势,认为只有如此才能获得自身安全的绝对保障,而另一国家(尤其与前一国有历史恩怨和领土纠纷的国家)就会同样增强军备;除非一国在追求自身国家安全时,确实没有把他国当做假想敌或竞争对手,并且这种“真诚态度”能够为他国准确感知和理解。
二、国家间产生安全困境的原因探讨
在国际关系中,权力单元(主权国家或地区)之间为什么会产生安全困境呢?传统现实主义认为,人性恶导致人与人之间存在“霍布斯主义的恐惧”(安全困境)。同样,任何国家也都是自私的,国家的对内、对外政策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国家利益而对别国有所防范,所以国家与国家之间存在安全困境。
与传统现实主义观点不同的是,美国学者约翰·赫兹与结构现实主义领军人物肯尼斯·华尔兹都认为国际关系中的无政府状态才是导致安全困境的根本原因。肯尼斯·华尔兹认为:“在无政府状态下,一方聊以自慰的源泉就成为另一方为之忧虑的根源。因此,一个国家即使是为了防御的目的而积聚战争工具,也会被其它国家视为需要做出反应的威胁所在,而这种反应又使前者确信,它是有理由为自己的安全担忧的。”[4]5
著名的美国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杰维斯则强调国家关系中的“理解”(perception)和“误解”(misperception)是导致安全困境产生的主要原因。另一位美国学者汤姆斯·先林则从心理学的角度去考虑安全困境的起因,他认为互不信任和沟通失败是造成安全困境的主要原因。
按照国际关系的历史和现实,国际政治学家们从不同角度针对安全困境的内涵和原因的分析与解释,都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但也存在各自的局限性和不合理性。从安全困境的理论基础上讲,以上各种阐释都有缺陷,彼此不能完全令对方信服,这就造成长期以来在国际政治理论界争论不断、各持己见。下面我们对以上三种观点一一剖析。
首先,学界关于人性论中“人性本恶”这个观点本身就存在巨大争议。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抛开社会属性去抽象谈论人性是没有意义的;故而,把人性恶作为解释国际政治安全困境的理论基础是值得怀疑和商榷的。无论从宗教还是哲学的角度,现实主义学者都认为人性本恶,而作为人的集合体的国家同样具有“恶”的特性。马基雅维里是意大利权力政治学先驱,人性恶论是其政治学说的基础,这一点在其名著《君主论》中展露无遗。英国著名哲学家和政治学家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概念更是以人性本恶论为理论基础。他的“自然状态”是指,任何一个人首先考虑的都是怎样保护自己的生命安全,而保护自身生命安全的最好办法就是自己支配别人,使别人害怕自己甚于自己害怕别人。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人性恶论是赫伯特·巴特菲尔德与霍布斯的共同理论基础,他们都认为安全困境的内在根源就是所谓的人性恶。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国际社会和国际体系中,虽然主权国家依然是最基本的权力单元,都极力捍卫自己的国家利益,也都有其自私的一面,但却并不具有向恶的本性。有时主权国家之间的一方虽然无意威胁或损害另一方的国家安全和核心利益,但还是会引起对方的敌意,从而导致国家间安全困境的出现,显然这不能归咎于人性本恶和国家自私。
其次,结构现实主义分析安全困境产生根源的观点也不是无懈可击,也有其理论的局限性。肯尼斯·华尔兹认为,一个主权国家即使出于自卫和防御目的而提升军费和军力,也一样会被其他国家当作安全威胁并作出回应;而恰恰另一方的这种回应更加使前者确信,自己加强军备是抵御威胁的正确行动。肯尼斯·华尔兹从国际结构的无政府角度分析安全困境成因的观点, 有其独到和可取之处,但并非没有瑕疵,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人类自从有国家这个强力机构以来,无政府(无世界政府——笔者注)就是国际社会的常态,但事实上并非任何国家之间都有安全困境。也就是说,处于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之间并非必然存在安全困境。如果国家间彼此信任,尤其是国家利益有广泛交集时,安全困境就不会产生。总之,把国家间产生安全困境和冲突的本质原因完全归于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其说服力显然不足。
最后,罗伯特·杰维斯把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归咎于国家之间互不信任和沟通失败,有其合理的部分,也有偏颇的地方。比如,当两个国家之间的核心利益严重冲突、不可调和时,安全困境的出现就不能完全归于沟通不畅和互不信任了,因为互信的基础不存在了。
总而言之,以上对于安全困境成因的三种传统解释都有瑕疵,也都有可取之处。安全困境既可能源于一国对别国的不信任及彼此的沟通不畅,也可能源于对自身国家安全的无止境追求,导致国家间的疑忌不断加深。
三、安全困境的种类
依据对国际政治中国家之间尤其是大国之间的关系史的分析,再依据国际政治学领域的研究成果,从国际结构的角度出发,可以把安全困境分为以下两类。
(一)一般性安全困境
此类安全困境是指处于国际体系中的主权国家之间的一种常见的相互关系状态。此类安全困境的危险程度各有不同,因国而异,因时而变,因势而变。按照结构现实主义的观点,只要国际体系中还没有一个最高的权威机构(比如世界政府)实施统一管理,主权国家之间的一般性安全困境就会长期存在。这种一般性安全困境的危险度一般来说都是可控的,导致主权国家之间爆发冲突的几率较小,但如果国家间各种核心利益冲突升级,导致关系恶化,也会爆发冲突。
(二)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
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一般产生于特定历史时期中的特殊国际结构。此类安全困境经常源于挑战国对霸权国主导下的国际秩序的不满。比如,19世纪初期崛起的拿破仑帝国就是挑战国,当时的英国就是霸权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德国是挑战国,英国是传统老牌霸权国。这种安全困境既来源于挑战国对霸权国的不满,也源于霸权国对挑战国的疑惧,这是一个相互刺激、双向激化的过程。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也可表现为国家联盟之间的对抗关系。比如,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同盟国与协约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同盟国与轴心国、冷战时期的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和以苏联为首的华约等。
从世界历史来看,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中的对抗双方在国家和国家集团的根本利益上存在冲突,因而双方处于一种零和博弈状态。频繁发生的危机是结构性对抗安全困境中对立双方之间的常态,这种安全困境的危机很难消减,除非其中一方解散或彻底改变其战略目标。这种安全困境的结束源于对立双方危机的总爆发或者一方的失败。
四、安全困境的出路
英国霍布斯提出的“自然状态”理念,是国际政治理论中安全困境概念的源头。自从安全困境被用于国际政治研究以来,摩根索的经典现实主义、华尔兹的防御性(结构性)现实主义、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学派及约瑟夫·奈的新自由主义学派,都认同它的客观存在性,但就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能否彻底解决和怎样解决,认识上还有很大差别。
首先来看现实主义的观点。经典现实主义与结构现实主义都认为国家间的安全困境是不可能有解决方法的。经典现实主义认为,人性恶决定了国际社会的安全困境,而人性是不可变的,所以安全困境也是无解的。结构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决定了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而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又是难以改变的,因而安全困境就不可能有任何解决渠道和出路。比较极端的米尔斯海默的进攻性现实主义则认为:“最好的防御就是有效的进攻。只要国家生活在无政府状态中,就几乎不可能采取任何措施改善安全困境。”[5]49然而,在当今国际社会建立一个国际中央政府性质的“世界政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建立康德主义式的“世界政府”有一个必要的前提——世界上主权国家的自主权的转让,但这是非常难以实现的目标。即使我们克服种种困难,建立了能够保护所有主权国家安全的“世界政府”,但是我们能够完全保证这个怪兽级的政府始终为全人类服务吗?它不会有自己的利益诉求吗?如果这个超级“利维坦”给我们带来更严重的安全问题呢? 既然这种可能性无法排除,那么世界政府论也很难付诸实践。
其次来看自由主义学派的观点。自由主义学派领军人物、美国著名政治学者约瑟夫·奈认为:“国家可以通过合作,来避免出现这样的安全困境,也就是说,它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即双方都不增强国防力量,这样对大家都有好处。”[4]23他还认为:“现实主义和复合式相互依存(自由主义)在现实中都不存在,它们都是理想的模式。现实主义者看到的是一个由很多以武力追求安全的国家组成的世界,复合式相互依存的鼓吹者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世界上还有非国家行为体、经济手段、福利目标,它们比安全更重要。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是两个极端的观点。”[4]340约瑟夫·奈认为,两种理论——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思考这个国际社会,观点可以互相补充,互相借鉴,这样更有利于我们理解这个不断变化的世界[6]340。
按照约瑟夫·奈的自由主义学派(包括理想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逻辑分析,国际关系中主权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是可以缓解的。自由主义学派认为国际社会中并非只有主权国家这个唯一行为体,还有联合国等国际组织;国际社会虽然无政府却有秩序和规则;每个主权国家的决策都不是领导人的个人意志,都是国内各个利益团体博弈的结果;主权国家寻求自身安全保障,仅是其努力追求的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并且追求的只是相对的安全而不是绝对的安全。各个国家之间的各种交流往来,以及国际规则和制度的存在,都为国家之间的沟通、理解和信任提供了可能和机会。
最后来看建构主义的观点。新兴的建构主义学派对安全困境的见解有其独到之处。各个主权国家对国际社会性质和各个国家的身份认识不同,导致追求自身安全的行为也不同。国家之间的所谓安全困境就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也是各个国家领导人心中的一个魔障:你把对方的行为理解为对你安全的威胁,那对方就真的成为你的威胁;你不把对方的行为作为对自身安全的威胁,那对方就不是你的威胁。建构主义常举一个例子:即使英国拥有500件核武器,美国也不会把英国当做对自己的安全威胁;即使朝鲜有一件核武器,美国也会认为这是对美国安全的巨大威胁。新兴的建构主义学派认为,安全困境的互动双方在身份和角色认同上有很大的主观性和随意性。他们认为,国家行为体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角色和利益的社会建构和文化认同,与安全困境的形成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历史的、心理的、国内国际的各种因素都极大影响了对对方角色和身份的认同,而一旦认同与实际发生错位,就会造成利益判断的失误。如果国际体系中冲突的双方在交往互动过程中,实现角色和身份的合理认同,双方就会形成共有观念(知识)的共享,就会实现对彼此行为后果的明确预期,并主动约束自己。换句话说,行为体(主权国家、国家集合体等)之间的理解、期待和认知的分享程度越高,各个行为体之间就更加相互信任。
五、化解安全困境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至关重要
如今的国际社会仍处于无政府状态,许多国家之间存在安全困境,甚至某些国家之间的安全困境还有相当的危险性。我们要承认安全困境的存在,并努力去化解它的危险。国家之间只要存在共同利益,就能找到合作的空间和机会。每个国家都要努力与其他国家寻求共同利益。这样主权国家之间通过彼此的合作与沟通,寻求彼此之间的交集,求同存异,就可以突破国家间的安全困境,提升合作空间。
我国经过近四十年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获得极大的提高,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是,我们离这个伟大目标还有一段较长的路,还需要和平发展和周边安全稳定。我国与周边多个国家都存在着安全困境,比如中美安全困境、中日安全困境、中印安全困境等。这些安全困境都存在某种不安定的因素,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就会导致我国与别国的争端,就会影响我国的和平发展。所以,我们一定要在不损害自己国家核心利益的情况下,努力化解周边的安全困境,从而给我们的发展营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我们一定要有国际政治大战略,要有国际政治定力,决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我们要与世界各国一起打造世界命运共同体,一起构造和谐世界。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我国只有坚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只有同世界各国一道维护世界和平,中国才能实现自己的目标,才能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7]263。
[1] HERZ J.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 the Atomic Age [M].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9.
[2] 王逸舟.全球化时代的国家安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 WHECLER N, BOOTH K. Dilemmas of World Politics: International Issues in a Changing World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2.
[4] 华尔兹. 国际政治理论[M].信强,译.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
[5] 米尔斯海默. 大国政治的悲剧[M].王义桅,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6] 奈. 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M].张小明,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7] 中共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M].北京:学习出版社,2016.
(责任编辑:李翔)
A Theoretical Analysis of Security Dilemm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GENG Jinang
(School of Marxism, North China University of Water Resources and Electric Power, Zhengzhou 450046, China)
First of all, the author starts from the concept of security dilemma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theory, analyzing the connotation and essence of the security dilemma. Then, the author from the different perspectives of realism, liberalism and constructivism analyze the causes of security dilemmas among countries. Finally, the author tries to find out the way out of security dilemma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ccording to different school theories and viewpoints.
security dilemma; realism; state of anarchy
2017-04-25
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当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问题研究”(2016BKS012)
耿进昂(1969—),男,河南滑县人,华北水利水电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法学硕士,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
D80
A
1008—4444(2017)04—0044—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