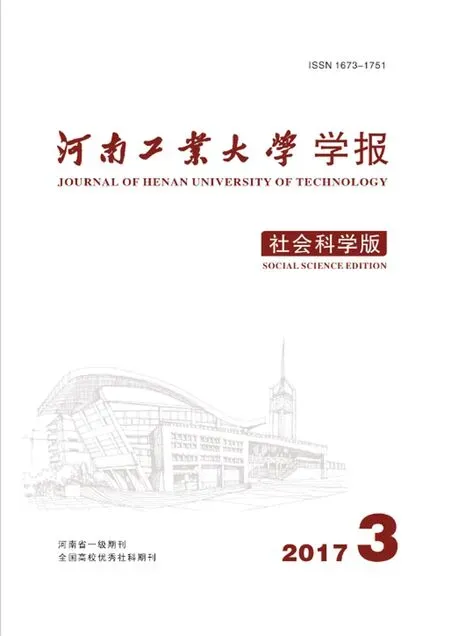转型期熟人社会视角下农村治理探究
2017-02-23吕承文高韩桔
吕承文 高韩桔
(1.宁波大学 法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2.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转型期熟人社会视角下农村治理探究
吕承文1,2高韩桔1
(1.宁波大学 法学院;浙江 宁波 315211;2.复旦大学 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上海 200433)
熟人社会是我国传统文明孕生的社会基础,在农村的表现尤为显著,对我国农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其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历史的必然性。当下农村熟人社会出现了诸如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导致农业经济的凋敝、农村社会互信系统虚弱以及农村社会法律保障不足等异质化问题,根本困境体现为农村熟人关系日益减少。解决对策是重建与恢复农业经济、推进农村公共文化教育设施建设、实现农村熟人社会的法治化,最终推动农村社会熟人关系由传统向现代转型。
转型期;熟人社会;农村治理
1 何谓熟人社会
有关系,便有社会;有熟人关系,就有熟人社会。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社会有两大含义,一方面是指人类结群的集合体,另一方面则指人与资源的集合体,它具体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空间上行动的现象。社会对熟人社会具有广义上的内涵意义,也就是说,熟人社会是社会万花筒的其中一个镜像而已。社会既可以是熟人构成的,当然也可以是陌生人构成的;况且,熟人与生人只是个相对的概念,这也决定了社会关系本来是辩证的。只有存在熟人关系的地方,熟人社会才被认为是存在的。不同于西方的生人社会夹杂着不可避免的熟人社会,我国社会现状是占大比重的熟人社会中附生着生人社会;毕竟,自人类社会诞生以来,纯粹的生人社会或者熟人社会是不存在的。
熟人社会问题是我国本土生成的政治问题,牵涉国家与社会互动问题乃至国家与社会变革问题。学界主流结论是中国社会“一盘散沙”。自费孝通先生通过对其家乡吴江开弦弓村的调研,并在其学位论文《江村经济》中系统探讨中国熟人社会问题始,我国的社会问题才被正式贴上“熟人”的标签,受到了中外学人的密切关注。“目的确是要了解中国社会,而且这不只是这个小村所表现出来的中国社会的一部分,还有志于了解更广阔更复杂的‘中国社会’”。[1]熟人社会形成的根基是建立在血缘与地缘之上的熟人认同,表面显现为情分或“面子”,深层里确实凸显为将熟人之间紧紧联结在一起的利益关系,这种情形早在中国古代村落由聚居的宗族、大家族与国家制定的宗族连坐法中就已注定。而且,在中国的“国家”形态建构中,血缘关系不但没有被摧毁,反而得到加强[2]。
家族组织是近晚年以来中国古代的客观存在,是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之基础[3]。这使得长期在家族中生活的人们之间构成了由于彼此熟识而产生了相互依赖的利益关系,这种利益关系可以分为几种:第一种是其中一人飞黄腾达,则与之相熟识的人也会由于这层熟识关系而得到各种好处,这也就是平常所说的“关系”人情网;第二种是如果其中一个倒霉遭殃,比如触犯国法,那么与之熟识的人也会受此牵累,进入连坐体系;第三种是这个群体若出现了内讧现象,由一人或一批人去构馋陷害另一个人或另一批人,那么这个熟人群体的利益撕裂会变得非常显著。
熟人社会以利益为内核,却以关系为根本。有关系的地方,熟人社会容易表现出来。熟人社会中成员之间通过彼此之间的各种相互利益联结而形成一种复杂微妙的熟人关系网络状态。由此,人们在各自的交往圈里可以通过朋友的熟人关系来发展更多的朋友熟人关系。熟人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4]。从微观角度观察,熟人社会中每个成员时刻处于一种复杂而精妙的熟人关系网络之中,并且其在认知与行为上具有独特特征,通常有亲疏内外之分,这是中国人行为的一般特点。中国人办事,不是翻规章,而是找关系、托熟人,找不到关系,便打通关节,用请客送礼来铺设关系[5]。在农村“出门遇熟人”的印象让人们总是感觉熟人社会的无处不在,感觉在熟人社会中只要能够接触就可以产生熟识的感觉,这样也为后来的办事提供了方便。由此观之,熟人社会更是一个以关系为主导的社会,人们之间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来配置及调节资源与利益,处理大量社会关系成为熟人社会中人们的重大生活任务。具体来看,熟人社会有以下三大构成基础。
第一是经济基础。任何政治事务、现象及活动都必然存在与之相适应的经济基础来推动内在的利益支撑。马克思政治学原理告诉我们,农村熟人社会的经济基础是与农村、农民相适应的农村活动(部分乡村工业活动应被认为是农业活动的延伸,比如农业加工业、采矿业、畜牧养殖业等)。经济利益对社会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熟人关系)必然是人们之间交互过程中各种利益关系的现实体现。囿于传统认知,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多好谈“义”(伦理)而非“利”(利益),实质上并不能掩盖社会中各种利益关系客观存在的事实。熟人社会的现实状态实际是由其根本的利益基础所决定的,具体表现在各社会成员之间利益交互关系的历史演化之中。
第二是文化基础。文化昭示着一个社会的价值导向,是社会成员愿意相互结识与生活共处的观念与信仰标志。在熟人社会中,正是由此才使得社会成员之间贴上了“熟人”的标签。熟人社会是中国本土文明生成的现象。昔日“礼尚往来”的礼制理念与将人束缚于地域的现状塑造了中国意义的熟人社会。礼自身具有的等级化的特征表现为“辨异”或“别异”[6]。乡土社会中人们由熟悉而产生信任(不管理性与否)。传统礼俗文化为乡土社会的稳定与有效维系提供支持[6]。传统熟人社会正是旧礼制文明的产物,由于不能摆脱“旧礼”的影响而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并对之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性作用。
第三是法治基础。如果文化可以包括道德与伦理的话,而道德与伦理亦可被认为是广义的社会秩序维系工具,那么随着现代社会的快速发展,法律遵守的成本经济性将自然取代深刻受到人性自利影响的道德自觉性。因为法律是“人类社会中得以规范行为,形成相互合作关系所必要的共同信息。”[7]并且,现代社会必然也会是一个法治社会。转型期熟人社会应顺应时代要求而全面实现自身的法治化。
熟人社会是由个人交互关系(即熟人关系)通过网络化形式,基于社会成员共同的现实与心理利益,结合而成的具有以关系认同为现实表现的别规范于道德框架中的稳定心理意识的结构共同体。熟人社会的外形在于道德人伦,内在本质在于经济利益,需要外在的经济与文化的法治保障。礼崩乐坏,乱在人心。以关系为取向的社会里,利益潜伏在社会深层,容易为各种投机现象所俘获,对社会公平造成巨大冲击,导致社会分配秩序的败坏,最终影响整个国家的治理。
2 转型期农村中熟人社会存在的合理性
国家治理包括城市治理与农村治理,其中,农村治理涉及以广大农村区域为主要范围的基层政权的稳定与巩固。转型期,农村社会问题重重,考验着我国农村治理的社会效果,从熟人社会角度出发,或许可以在改进农村治理过程中另辟蹊径。所谓“农村治理”是指在农村领域推行的旨在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繁荣的各类治理活动,是一种法治的多元治理模式[8]。
在农村中,熟人社会的存在感更是强烈,这是由于农村的乡土区域比较小,乡民活动范围有限,很容易使人们互成熟识的乡里,消息也容易在乡村中散播。这种熟人社会的特征感在县城、城市、都市之间依次递减。农村熟人社会是一种传统的、尚未异变且最为典型的社会类型。农村熟人社会的构成要素包括了宗族、家族与街坊、邻里等,由于这些构成要素已然涵盖了非常强的建立于血缘与地缘之上的熟人关系,使得农村中的熟人社会类型,更具有原始传统的气质。所以,“传统中国在乡土基层上是一个熟人社会,是生成礼俗文化的社会。”[7]
在农村,熟人社会关系形成的基本途径是通婚,包括了村内婚姻与村外流动婚姻,一旦村里村外都结成了亲家,则熟识与认同感更为深入,此后两姓之间互通有无、互帮互助,则成了默认的熟人义务。此外,熟人社会关系形成的另一种途径是人口流动与家族迁徙,无论是当下的行政村还是自然村,一姓之村已经由杂姓混居的情形逐步取代,只要人与人之间获得了相处的前提,自然会形成日久相识的熟人关系,村上村下基于熟人(邻里)关系的情分上,红白诸事互相帮忙也变得寻常。农村熟人社会的原始特征是熟人关系封闭(由于姻亲同住一村或隔壁邻村),邻里之间的相互信任与互帮互助(由于农村生活简单,乡民性格淳朴厚实),而且姻亲关系十分显著。
探讨农村治理问题,可以单从农村或农民个体、群体抑或农业经济等相关角度入手,然而,农村熟人社会的存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及衍生出来的历史必然性,这使得农村治理亦可以拥有熟人社会的思考视角。一方面,改革开放的经济变局并未有真正触动农村社会的熟人社会核质,而且农村的继续发展也只会强化熟人社会,与城市相比,熟人关系只会加强而不会减弱。另一方面,即便农村开始突显现代化转型,也只会带来与现代农村经济相适应的熟人社会,而非完全铲除熟人社会,将之变成西方式的生人社会。再一方面,熟人社会作为农村传统的社会形态,是农村千百年农业文明支撑起来的社会基础,尽管在当前的工业文明时代出现了许多不适应的症候,但是只要中华文明的底蕴并未发生实质性变化(不为西方的“快餐式”文明所取代),熟人社会就有自身独特的存在合理性。
从本质上来看,熟人社会催生了一种高于法律制度的道德框架,来促进社会整体上的和谐。“社会结构格局的差别引起了不同的道德观念”[4],在熟人社会中的传统道德约束下,人们在行为上总是倾向于主动地向他人提供帮助来显示这种道德义务所引发的善举。其实,熟人社会中的各种互助行为都是指向于内在的社会利益基础,从而通过这种关系处理模式来协调社会利益分配秩序,从根本上促进农村社会经济的进步与发展。农村经济是农村熟人社会的经济基础,只要农业经济不消亡,农村中的熟人社会就会仍旧存在,而且,熟人社会还会反过来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在农村,农耕作业使得人们生活在土地之上,熟人社会中,各成员之间彼此因具有共同的利益基础而结合成庞杂的熟人关系网络。
熟人社会是一种具有共同利益基础的熟人关系网络集合体,其内在的道德框架是社会秩序自我维稳的重要能量源。熟人社会的最重要优势是可以不借助法律而只需依靠伦理道德就可以达到有效约束其成员行为,达到自我秩序安定的效果,并且可以更深层次地促进成员获得不同程度的安全感及社会认同。熟人社会这种内生的道德秩序框架存在的目的是巩固根本的社会利益基础,并公平地维系好社会分配秩序。熟人社会中,成员之间由于彼此熟识,通常都以一种平等关系来处理彼此之间的事务,这就要求社会中能够以公平正义的方式来解决各种社会矛盾。一般情况下,人们之间更趋向于维护各自之间良好的熟人关系,而不会轻易去损害彼此之间的利益;由此,熟人社会才会带给我们一种上下有序、相亲相爱的和谐融洽景象。从表象上看,这是道德性;实质上,这是利益;人们若不如此进行道德自律,就会导致其中一条或若干条熟人关系的破裂,最终在社会道义舆论的压力下失去熟人社会给其带来的一切“福利”。人们如果想依照自己的方式来追求自身的自由和幸福,前提是自己的努力不能妨碍到他人的自由和幸福的实现[9],这也成了熟人社会存在的秩序目标。
从国家治理与农村治理的角度来看,皇权和职业官僚系统并不鼓励甚至限制其下层官员介入乡里的日常生活,这就使基层社会享有相当程度的自治性。这催生了地方绅商的官僚化,并形成了士绅—乡民的稳固关系,变成了国家政权扩充和渗入村庄的重要工具[10]。而且,国家与社会之间的政治—法律关系其实是在社会与个人之间的交互关系的政治—法律化过程中形成的,由是应当在国家、社会和个人之间形成密切紧凑的家国同构体。尽管王朝末年的腐败会导致汤武革命与农民起义,但是由于士绅—乡民的结构关系依然被很好地保存下来,帝国体制可以周期性得以恢复和重建[11]。总而言之,熟人社会可以从整体上保障各个社会成员的合法权利,并公平正义地增进彼此之间的利益,这决定了即便在转型期,熟人社会在农村的存在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它的时代性发展也具有历史的必然性。
3 熟人社会异质化:农村治理的改进立足
从外表形式来看,两千年前国家的机构便形成流水形态,可是其下端却粗率而无从成长发展。整个国家无法脱离一种被安排的环境,即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12]。中国农村经济生活水平自晚清以来都未出现重大的改革,只有到了新世纪的转型期才出现了今日所见的翻天覆地之变化(随着农民外出务工与三农建设等新形势出现),也已然使得农村熟人社会出现了异质性突变。农村随着现代经济的同步发展,也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这种现象被称为“异质化”。熟人社会的异质化是转型期农村在面临现代化、城镇化与法治化(“三化”过程)时自身出现的难以与当代时代特征相符合的发展性危机,如果熟人社会能得到适时与有效的改造,则农村将得到良善的治理;如若不然,则会成为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及政治秩序稳定的主要障碍。这个问题应当引起我国农村治理者的高度重视。因此,农村熟人社会异质化现象的讨论也是农村治理一个重要的立足点。
3.1 农业经济的凋敝,大量农村劳动力外流,农村熟人关系减少
计划生育并未给农村带来独生现象,而只是起到了一定的节制人口增长的效果。在农村,多生现象十分普遍,一家数个子女所带来的后果可能是重返贫困或者子女因为贫困而陷于辍学。这是一种矛盾的社会现象。国家计划生育的初衷并不是为了节生节育而节生节育。如果计划生育并不能带来农村家庭富裕与人口素质提高的话,那么计划生育政策在农村的执行效果是要打折扣的,这进而影响到农村里的熟人关系存续。一方面由于计划生育而破坏了和谐的熟人关系(强制熟人去做节育手术的计生干部本质上还是村里的熟人,这样做肯定会大伤情分与面子);另一方面村中一旦有人不顾情分面子而去“通风报信”,也会造成熟人关系的破裂。
后来的本地婚(村里或村外的流动婚)也随着现代交通的便利与农村社会经济结构的变化而逐渐为外来婚所替代,许多外来的(很多是双方户籍各在遥隔千里的省份地区,甚至还不排除跨国籍的婚恋)女婿或媳妇进入村庄,在一定程度改变了传统而封闭的熟人关系,过去的五服关系中也会迎来一定的生人姻缘,原先局限于狭隘区域的老表亲也出现了瓦解的趋势。另外,农村里大量的年轻壮丁外出务工,农业劳动力也由此大量外流,传统农业经济陷入萧条的地步,同时城市昂贵的生活成本也造成了与之共存的留守儿童问题。农民的这些贫困化问题,会直接影响他们与村庄组织以及国家政权的关系,弱化对国家的支持[7]。
这些在转型期特有的社会问题虽未真正触动农村熟人社会的关系内核,但事实上却正在异化着农村熟人社会的经济基础。一是农村熟人社会关系赖以维系的利益基础已经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熟识的冷漠取代熟识的信任,彼此之间的利益联结不再像过去那般紧密。二是农村熟人社会的熟人关系由传统的封闭化逐步向现代的开放化转变,纯粹的熟人也被学界所说的半熟人社会所取代。三是远隔千里的姻亲之间由于不再像过去那样可以频繁走动串门而难以进入传统的农村熟人社会关系网络中。
3.2 道德维系框架的破坏,乡民之间的互信感减弱
传统乡村的既有社会力量格局发生基本变化,从而引发社会改组。现代化进程加剧了城乡文化梳理,使传统乡村社区丧失凝聚力[7]。社会成员依据各自势力的强弱,凭借公共权力肆无忌惮地侵害其他社会成员的合法权益,并最终破坏社会公共秩序的局面。当社会成员的利益诉求发生混乱乃至不顾道德而互相伤害时,社会分配秩序的有失公允伴随着社会利益基础的紊乱化而演化成社会道德危机。当社会只计权利、利益,不知义务、责任时,社会成员之间的关系显然难逃功利化的趋向;人们之间不再自觉地在社会普遍的道德约束体系下调整各自利益行为,反而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不惜将人际关系庸俗化成利用关系,由此,民风奢谈纯朴,世道难望清平。
费孝通认为,传统农村里存在着一种“长老统治”,那些被认为是德高望重的“长老”们通过掌握教化权力来维系农村熟人社会中的礼制习俗[4]。但是,“文革”的“破旧”活动直接冲击了这种原本封闭保守的礼俗社会。有些年长者多被激进的年轻人批判为“反动守旧,打压新人”的社会坏分子(“地、富、反、坏、右”中的任一种),这虽给农村带来了变革,却也造成了对礼仪的记忆衰减乃至消亡。
关系作为熟人社会的自然现象,无可避免,但是一旦突破各种道德的、法律的约束框架之后,它邪恶的一面由于人们行为目的的异化而不断暴露出来。日趋功利化的社会关系使得社会成员之间的不信任、不安全感倍增,以致在所谓的熟人之间也不可避免地会染上戒备的心理。这样将会导致两种衍生性后果:当人们感觉自己在交往过程中利益受到损害时,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报复心理,从特定的施害人乃至蔓延到整个社会,最终导致具有社会报复性质的暴力事件发生,给社会秩序造成巨大的破坏;继而,这种不信任感随之蔓延到整个社会,社会中的人们大都倾向于认为自己就是潜在或实在的利益受害者,以致人情冷漠,最终将社会搅成一盘散沙。
3.3 社会公共资源流失,且国家对农民的法律保障不足
农村公共服务资源原本十分稀缺,这给农村的留守儿童的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心理健康、人身安全等方面带来了严重的隐患。尤其是20世纪以来,国家行政权不断向乡村社会延伸,逐渐形成了“资源汲取型”和“全能型”的乡镇行政管理体制,这种体制已不适应农村市场经济发展与扩大基层民主政治的需要,且在实践中衍生出诸多矛盾与问题[13]。从法理上看,农村熟人社会其实反映的是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公法关系。这也是乡村治理需要处理的重要政治关系[8]。这种庞杂巨大的熟人关系网络将单个社会成员主体的局域性熟人社会现象共同联结结合成所有社会成员主体的广域性熟人社会理念,并在与国家的互动过程之中,对国家产生基础性的支撑作用。熟人社会作为中央国家的社会基础,就必然将各种个人熟人关系放大到国家与社会及社会与个人两对照应关系上。
当礼制遭到破坏,而国家法律又未能及时进入时,农村的许多公共资源处于流失状态(为富裕地区或者城市剥夺,国家的法律保障一直不能生效),国家与农民之间的公法关系也自然陷入失衡的困境。农村熟人社会的适时改造是当下影响基层政权稳定的农村治理的根本社会问题。“社会腐蚀”卷走了“上层关系”(多年培养出来的农村精英:战争与迫害、考学,结果混混、无赖填补了农村权力真空),乡村大地日益荒芜[7]。自古以来的“皇权不下县”局面已被村里建起的党支部所取代,这昭示了国家的政治系统正式进入到农村,同时也表明传统熟人社会适应性转变的时代必然性。
在过去,农村里遵守的多是风俗与习惯,只要没有重大的违法犯罪,国家法基本不进入农村,但是随着农村人际关系的时代变化,越来越多的陌生人(外来人)进入农村,如果用过去的习俗规则来处理这些发展的人际关系,就显得力不从心[8]。事实上,农村的熟人社会是“三化”过程中出现的一个发展悖论。一方面,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导致了社会资源由农村急剧向城市渗漏,直至最终“撇脂化”,绝大部分资源集中于城市,这无异于釜底抽薪式地摧毁了农村熟人社会的农业经济基础。另一方面,农村熟人社会的道德框架崩溃,亟须国家宪法与法律系统的正式介入来促进农村政治经济社会秩序的稳定,从而建立全国统一有序的法治体系。但是,国家若要通过政策的方式来抑制市场经济的撇脂现象,通常会给农村施加更多的政治干预,反而会阻碍熟人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这是个两难的困境。
3.4 农村治理改善的对策思考
本文的结论是农村熟人社会应当得到改造,而且这种改造须顺应我国的现代化与法治化建设的基本要求。阿尔蒙德认为现代社会结构都具有高度分化的特征[14],这给农村熟人社会的改造提出了政治要求。转型期的农村出现了农业经济转型、农村社会结构滞后所带来的政治困境。这也是一个秩序难题,必须得到解决才能改善农村治理。
农村当下的经济(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凋敝是市场经济调节的不良后果,这需要一定的国家调节与政治干预才能避免改革开放30年来“孔雀东南飞”的极端区域发展现象。农村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落后势必会给农村治理带来严重的政治影响,但这可以通过对传统熟人社会的一定现代化改造得到有效解决。可以想象,一个富裕文明、经济发达的农村一定能够重新吸引劳动力资源的正常流动性回归,实现农村熟人社会的恢复与重建、发展,并且长足改进农村治理。熟人社会应当能够将其内在的利益基础通过在政治制度层面上的整合实现规则化、制度化,并推动与之相适应的外在道德约束框架的建立,使得现代社会中各种熟人关系被有效地约束于法治框架之中。
总体而言,通过改造农村熟人社会来实现改进农村治理,不失为一种理性的对策思考。当前需要重点处理好熟人异质化问题,才能顺应时代需要,以改造熟人社会,使之符合“三化”发展的历史要求。
第一,重建与恢复农业经济。首先可以通过农业科技的普及与推广,来促进传统的农业经济向现代的规模农业(产业现代化)转化,建构现代规模农业,盘活农村经济,迅速使农民致富,确保农村熟人社会赖以维系的利益基础得到巩固。其次,可建议国家逐步恢复适宜的农业(产品与流通)税来刺激农业经济的复苏与振兴。再次,开发一种异于城市化(城镇化)的农村建设方案,确保城市发展的背后依然拥有现代化的整齐划一、文明有序的乡村体系作为后方经济腹地。最后,还可以依托已有的“三农”政策,重新将农民身份转化为现代社会中必不可少的正式职业,这样农村熟人社会才能重新具备稳定的农业经济而重新获得生机。
第二,重点投资农村公共文化教育设施,使得传统文明与现代文化并轨入村,借此来重建农村中熟人社会的文化基础,增进农村中乡民之间的互信感,加强对农村公共服务设施的基础投入,特别是农村公共教育,确保农村学生也能够就近在家享受到与城市学生同等优质的学校教育,使得农村熟人社会向着现代化与文明化的方向发展,从而长远地推动熟人社会的现代转型。
第三,加大在农村的普法力度,使得国家对农民的权利保障体系可以通过法令的形式进入农村,确保农村的各类熟人关系最终都可以进入到现代法治框架的规范之中,这样可以有效推动农村熟人社会的法治化。
[1] 费孝通.社会调查的自白[M].北京:知识出版社,1985.
[2] 易中天.帝国的终结[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3] 卜工.历史选择中国模式[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4] 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5] 曹锦清.黄河边上的中国[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00.
[6] 瞿同祖.法学论著集[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
[7] 朱新山.中国社会政治分析[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3.
[8] 温晋锋,王楠.泥土上的经纬——以M镇的法治调查为分析视角[M].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9.
[9] 约翰·密尔.论自由.[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10]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1986.
[11] 孙立平.中国传统社会王国周期中的重建机制[J].天津社会科学,1993(6):57-63.
[12] 黄仁宇.中国大历史[M].上海:三联书店,1997.
[13] 张新光.论中国乡镇改革25年[J].中国行政管理,2005(10):16-19.
[14] 阿尔蒙德.比较政治学[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A STUDY OF RURAL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QUAINTANCE SOCIETY IN THE ERA OF TRANSITION
LYU Chengwen1,2, GAO Hanju1
(1.SchoolofLaw,NingboUniversity,Ningbo315211,China; 2.SchoolofInternationalRelation&PublicAffairs,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The acquaintance society is the social foundation of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ivilization and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especially in the rural areas of China, the existence of which has certain rationality and historical inevitability. At present, there are some heterogeneity problems in the rural acquaintance society such as the decline in agricultural economy caused by the outflow of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labor forces; the weak mutual trust system and the insufficient legal protection in rural community. The fundamental dilemma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ural acquaintances is decreasing day by day. The solutions to these problems are as follows: rebuilding and restoring the agricultural economy,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rural public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facilities, realizing the rule of law in rural acquaintance society, and finally promoting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rural acquaintance society to modern society.
transitional period; acquaintance society; rural governance
2017-01-18
浙江省教育厅2016年度一般科研项目“转型期浙江地区婚姻成本承担及重构对策研究”(Y201635347)
吕承文(1987-),男,江西都昌人,博士,讲师,主要研究方向:法治政府与地方治理。
1673-1751(2017)03-0085-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