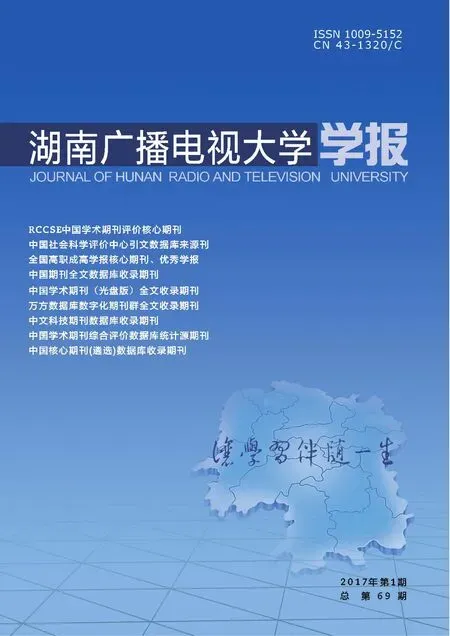神性失落与形象降格
——《神笔马良》改编剧的比较研究
2017-02-23姜云峰
姜云峰
(上海市嘉定区国家税务局,上海嘉定 201800)
神性失落与形象降格
——《神笔马良》改编剧的比较研究
姜云峰
(上海市嘉定区国家税务局,上海嘉定 201800)
3D电影《神笔马良》与木偶剧《神笔》形成了一个相互映射、彼此关联的开放性对话关系。在这跨越60年的对话中,神笔神性的失落和马良形象的降格展现了现代人对主宰自身命运的希冀,也暴露了人被消费文化所异化的危机。
《神笔马良》;消费文化;改编剧;互文性
1955年,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根据《神笔马良》制作了一部木偶动画片《神笔》,该片由靳夕、尤磊担任导演,原著作者洪汛涛任编剧。2014年,由迪士尼中国创意技术支持,秦浩编剧,钟智行导演的《神笔马良》同名改编3D动画电影上映。
在这一甲子的岁月变迁中,两部由不同艺术手段呈现的《神笔马良》作品,彼此互相指涉、关联,其文本意义互相交织而形成互文性的对话关系,并且通过跨越时空的交流共同构建了一个少年拥有神笔的故事。两部改编剧的前后意蕴变化,对文本内容进行了丰富的延伸,在影响读者观影效果的同时,更投射出当代人的内心写照。在面对不可捉摸的命运时,人们的内心中充满了焦虑与不安,在以一笑解千愁的方式中,荒诞的手法使得内心的压力得到暂时放松,但在这场狂欢的背后却隐藏与压抑着更为严重的失落与空虚。
一、失落:从神笔到魔笔
神笔是贯穿故事的核心线索,无论木偶剧还是电影都围绕马良得笔、护笔、失笔、寻笔的程序展开,并通过神笔威力的展现,承接了惩恶扬善的价值立场,满足了人们对英雄崇拜的阅读心理。在《神笔》中,穷苦少年马良对画画有着浓厚的兴趣。但是在他的求学过程中,其求笔学画的愿望却被地主、官员耻笑,遭到阿谀画师的拒绝:穷孩子只配去放牛,没有资格学画。于是,受辱的少年马良立下了“只为穷人画画”的誓言。日后,他勤学苦练,自学成才。正是这种不怕困难,肯用功的精神感动了老神仙,从而实现了他求笔作画的愿望。自此,神笔终于登场。首先,神笔作为神仙的赐予而极富有神秘色彩,代表着天命的认可。其次,神笔作为马良刻苦学画精神的嘉奖,具有道德评价的功能。最后,老神仙再次强调了马良“为穷人画画”的誓言,从而确定了这只神笔作为反抗压迫与剥削的武器。木偶剧《神笔》紧扣阶级斗争的生活背景,展现了劳动人民与封建官僚之间美丑性格的对立,并且以马良为代表的广大劳动人民用淳朴“人性”来驾驭神笔无所不能的“神性”,神笔被用来扶危济困,惩恶扬善,展现绝对的利他性。但在3D电影中,神笔却发生了颠覆性变化。
电影中的神笔在外形上发生了显著的改变,木棍顶端处的滚珠使其看上去更像一枝西式的魔法棒。顽童形象的马良只要任意挥舞画笔,所想之物就自然出现。这里,画画能力的取得过程变得随意。在神笔失落为魔笔的过程中,神性被遮蔽,魔力成为主导。但这里的魔性并不是站在神性的对立面,而是成为一种超能力的魔力。在价值无涉、道德中立的立场上,神笔的魔力用之正则正,用之恶则恶,其关键取决于使用者。
于是,画笔的魔力不再为马良所独有,而这点却正是原著中进行道德批判的重要手段。在木偶剧中,神笔只有在马良手中才能发挥作用。地主和县令因为不会画画,所以画笔被交给了趋炎附势的画师使用。当为富人作画的画师手持神笔时,神笔所画之物只能是普通的图画。而在电影中,神笔不再对使用者的身份、能力与目的作额外的限制。当大将军抢到神笔时,无需交给画师,任意涂抹之下,心中想要之物也能出现,唯一的区别是他画出来的事物是黑色的。电影对此给出的答案是人心使然,黑心人画出东西都是黑的。
对此,我们发现神笔发生了这样的变化:在神笔的使用中,使用者无需任何绘画技能,可以不劳而获;持笔人心想之物随笔而出,可以心想事成。值得注意的是,电影中所画之物不再是木偶剧中所强调的现实之需,而是被替换为心中所要。从绘画技能的丢失,从“需要”到“想要”,欲望替代需要成为使用神笔的主导性力量,而神笔道德评判功能的丧失,使之更彻底异化为一只魔笔。
正是由于神笔的异化,由画成真之物也变得古里古怪,其展现的特征与传统印象形成倒置关系,如画出的牛偷懒,拒绝耕田;画出的猫怕老鼠,装死逃避;反倒是画出的老鼠,似一名大侠,与鼠王“划下道”,最终解决了店家的鼠灾。这里,狡猾的耕牛、侠义的老鼠等一系列事物形象都对我们日常认知形成挑战,似乎在告诉我们传统眼光的偏见。与之相对应的是神笔服务对象的异化,木偶剧中的神笔只能被用来“为穷人画画”,解决百姓们生活中的疾苦。但电影中的百花村生活祥和,百姓富裕,影片中的马良需要满足村民的需要已是五花八门:变得更美,要得更多,激发出的是潜在人心底深处的欲望,于是这些村民变得陌生而可怕!
“神笔在整个故事中的精神支撑作用是巨大的,它既是神话般的非现实形态,又最终着落在一个十分现实的社会环境中。”[1]神笔最终“失落”在人的欲望之中,使人变得不劳而获,迷醉于一个又一个的物欲之中。
二、降格:从英雄到孩童
在神笔失落的背景下,马良作为英雄的身份识别似乎变得可有可无。在童话中,“马良不再是神话中的‘超人式英雄’,而是‘移位’成民间故事中通常的‘常人式英雄’”[2]。在木偶剧中,洪汛涛自始至终都没有让马良用“神笔”来获取过“私利”,马良一直处在贫穷的生活处境,靠放牛、打柴度日。他的两次被抓也皆因助人而暴露了神能与身份。因此,少年马良拥有高度理想化、道德化和成人化的人格。而在电影中,少年马良则被还原为一个胖乎乎,带有些雀斑的孩童马良。马良的孩童化,使他作为一个轻松的、真实的孩子形象呈现在观众面前。他有着普通孩子的一切特点,如天真烂漫、淘气顽皮等。他的神笔来得莫名其妙,他的魔力用得随心所欲,他更像是一个好莱坞式的个人英雄,在命运和时势施加的巧合下完成了“自我觉醒”和“保护家园”的使命。
在后现代语境中,衍生出的种种新生意义往往是对既定传统意义的颠覆。马良从木偶剧中的理想人物被电影降格为一个搞怪诙谐的超能力者,从而抛弃了最初厚重、严肃的意义追寻,转向对生活趣味的探索。于是,坚毅果敢,倔强不屈的英雄马良消弭了,取而代之的是各种颠覆与移置的戏仿。如动物形象颠覆,又如狗狗小皇帝。小皇帝作为一个“皇”二代,天性浪漫,跟原作中的皇帝有着巨大差别,这里的根本矛盾不再是因阶级上的剥削与压迫关系而导致的对立,而是移置为对权威与上位者的嘲笑,包括对权势虚伪性的种种挖苦。这里“戏仿的文化价值需要做一分为二的分析,既要肯定其政治批评和文学创新价值,也要警惕过分张扬其非理性和滑稽的一面,以致使其蜕变为恶搞”。[3]
如今,成为商品的文艺作品从沉重的社会责任中解脱,卸下了原先社会教化、道德批判的“面孔”,休闲娱乐功能则成为了新的主导。于是,木偶剧中的阶级斗争含义被剥离,故事开始了一种“祛魅化”的叙事模式。当马良使百花村村民们梦想成真后,人们变得欲求不满,哪怕是最初的小伙伴也变得陌生而可怕。占有物的多寡并不改变人们内心中的空虚感,反而似乎失去了对物的实体功能(使用功能)的直接感受,沉溺于物品被赋予的意义中,如黄金象征财富,更多的黄金意味更多的财富,但更多的、超负荷的黄金又能对个体产生何种积极作用呢?“我们已经从原来为物所役使转变为被符号所支配和困扰。”[4]在电影中,无论是掌权的大将军,还是马良拼死守护的村民,都有着明显的人性弱点。当神笔无限制地满足人们欲望时,迷失物欲的人们形成了主动的集体式狂欢。影片用烟火、盛装等色彩缤纷的画面展现了一种景观社会,一个“已经物化了的世界观”[5]。马良被吓得落荒而逃,他的不解、困惑与迷茫正是当代人面临的现实困境。物质的丰富并不能真正实现个体追求幸福的愿望,却产生了焦虑、怀疑与不安的心理问题,继而形成精神世界的虚弱与无助。
在大将军为谋取更多黄金而“强拆”百花村的行动中,真正反抗的只有孩童马良。与他并肩作战的,也只是那些用神笔画出来的事物。孩童马良其实是孤独的,这是个人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在电影中,马良笔下的动物们发挥了巨大作用,并且他所画之物,哪怕如摇钱树、水壶等物品也都能说话,有着明显的个性特征,发表着自己的看法。若按照影片定义,所画之物由绘画之人的心灵所决定。那么,我们完全可以把这些能说会道的牛、猫、鼠、摇钱树等视为马良多重自我的展现,那是一个个虚幻而真实存在的“马良”。他们在观点上的认同与分歧,在性格上的淳朴或狡诈,皆源自马良的自我意识。同时,这些善恶美丑在相互交锋中构成了一种对立统一。正是同一个体的多重人格之间的对话、博弈,形成了多元、流动的自我,最终推动了孩童马良的成长与情节发展。
最后,当马良被大将军用神笔困在一张白纸内,四下空无一物,撇去了所有外在的修饰,被迫直面自己的内心。这里出现的“拯救者”——泼墨仙人作为他内心中神性“超我”的代表,启发他要追求“心中要有美丽的图画”。其实,马良对自我的认同问题源自对自身所处生存环境与生命意义的追寻。“认同不仅作为一种事实性存在,同时还是自我的辨别结果,即自我需要辨识自己究竟是否具有同一性,是一种在什么意义上的同一性。”[6]
但这种自我叩问式的救赎并没有成功,他最终还是通过小伙伴的帮助才逃脱了这个心灵拷问。值得一提的是,泼墨仙人在后面被称为“一块肥肉”和被恶搞为时尚达人,这里的神性“超我”也被降格,所要表现的仍是对现世快乐的肯定。
三、救赎:可能与不能
“所有这些互文文本让我们在一段看似天真无邪的文字后面,读出更深层次的内在体验。”[7]从神笔神性的失落到马良形象的降格,文本表面上烂漫的叙事风格背后隐藏着对人类社会人性问题的批判和反思。
“读者被互文吸引体现在四个方面:记忆、文化、诠释的创造性和玩味的心理”。[8]以《神笔》为代表的童话主人公都是真善美的代表,但电影中的形象却与读者阅读期待形成一种悖反,挫败了读者的阅读趣味和期待。影片中马良成为了小胖墩,甚至还带有那么点猥琐和愚蠢,并以神笔的失落为代表,童话的温馨记忆被打破,使其更像一次无厘头的狂欢游戏。
新的影视文本是将既成的、传统的东西打碎加以重新组合,用一种“貌似”而“神离”的戏拟手段赋予了故事以新的意蕴内涵。这里的戏拟往往与解构、讽刺联系在一起,在“时空错位”和“语言戏仿”中进行古今杂糅,带有鲜明的游戏精神和后现代主义倾向。不同于原作透明、线性的阅读体验,在观影中,如“房价太高了”“水沟油捞面”“打了我的鸟”等恶搞式的碎片话语,分明把人拉出了童话世界,击中了一些人性上的脆弱关节。电影消解了《神笔》所承载的崇高志向,淡化了友情的分量,甚至模糊了善恶的界限,当愿望变成了欲望,淳朴村民分明变得和大将军一样面目可憎。它不仅打破童话的美梦,还充分展现了人性自私、庸俗甚至残酷的非理性一面。正是基于两者的互文性比照,观众纷纷直呼“毁童年”。
该影片的豆瓣评分只有5.6分,可谓惨淡。但《神笔马良》如果原汁原味地呈现,那也注定是失败的作品。原著背景与当代生活的联系并不紧密,反压迫的斗争话语在当今的消费语境下并不适宜。其实,人们之所以对《神笔马良》恋恋不舍,很大的一部分原因在于那只能梦想成真的神笔。
“意义不可能被抛出,抛出的必须是一个感知,因此代替意义出现的物,或空白休止这样可感知的实体”。[9]回到神笔的象征意义上,作品正是用这只可见之笔来试图描绘看不清的神秘世界,阐释一种蕴含复杂隐秘的感性体验,并最终用来解释这个世界的奥秘。神笔所扮演的正是现实世界向超验世界过渡的一个沟通媒介。它超越了理性和语言表达的限度,从非理性、直觉和想象等多角度丰富了我们的表达能力。神笔表达的是对现实世界的不满情绪,它似乎要给我们提供一个救赎的途径,但更强调的是一种对现实的破坏性力量。
无所不能的神笔其实打破了童话故事中的“被拯救”情节,成为自我救赎的意义替代物。神笔与以往故事中的老神仙、小仙女等形象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主人公不必把自身命运依附在茫茫不可知的神秘自然,而能够自如掌控超越现实的力量。在神笔马良的故事中,遇到危机的马良凭借神笔就能轻易实现从“常人”到“超人”的逆袭,化被动为主动,从而主宰自身命运。电影正是基于此,把那只神笔的救赎性发挥到极致,成为了无所不能的魔笔。在神笔的使用上,电影不再“迂腐”地限制神笔的使用,使它真正成为一股改写生活、改变世界的巨大推动力。
但电影也借助神笔无所不能的特性,隐喻了现代性的消费危机,警告个体在消费社会下的心灵危机。本该带来幸福的神笔为何成为人们异化的魔障?当下人们所处的消费社会“是与新型生产力的出现以及一种生产力高度发达的经济体系的垄断性调解相适应的一种新的特定社会化模型”,[10]其通过制作日新月异的消费行为来缓解现代工业化生产(神笔)的过剩危机。基于此的消费文化成为新的社会规训力量,个体消费的不是物品本身,而是物品被赋予的外在意义。消费不再是享受,而是种被符号编码的规训。人们越是消费,反而越是空虚。并且消费文化还通过技术更新和时尚更迭来折旧物品的使用价值、抽离商品的时间价值,从而加速原商品的灭亡,驱使人们对新商品的消费行为。当个体的欲望依附在这套系统内,就会随着它的生产逻辑而无限增殖,如影片中的村长等人,个人的欲望需求远远超越了个体对物的实际消耗能力。
现代工业的日趋发达,个体对物质需要的满足与前人相比已是跨越式的进步,尤其是随着3D打印等高新技术的不断发展,我们亲切地称“神笔马良”即将成为现实。从这个角度来看,神笔变成魔笔,其价值无涉的立场变得可以理解。但是,当面对技术的高速发展,我们不再去过问目的,而一味地追求技术的精巧,这本身也会成为一种疯狂。正是基于现代消费语境,《神笔马良》3D电影对《神笔》木偶剧进行了有意义的填补与扩充。这让我们不由得思考,在物质条件极大改善的今天,我们又该如何实现诗意的栖居?
[1]王丹彦.事倍功半还是事半功倍?——从《神笔马良》的改编说起[J].中国电视:动画,2014,(6).
[2]李学斌.原型结构及其文学意义——洪汛涛经典童话《神笔马良》的当代解读[J].兰州学刊, 2011,(2).
[3]李玉平.互文性:文学理论研究的新视野[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171.
[4]孔明安.从物的消费到符号消费——鲍德里亚的消费文化理论研究[J].哲学研究,2002,(11).
[5]德波.景观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3.
[6]吴玉军.现代社会与自我认同焦虑[J].天津社会科学,2005,(6).
[7]朱莉娅·克里斯蒂娃,黄蓓.互文性理论与文本运用[J].当代修辞学,2014,(5).
[8]蒂费纳·萨莫瓦约.互文性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2002:82.
[9]赵毅衡.反讽时代:形式论与文化批评[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80.
[10]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72.
Divine Loss and Image Degradation: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dapted Version of The Magical Brush & Ma Liang
JIANG Yun-feng
The 3D movie, The Magical Brush & Ma Liang, and the puppet show, Shen Bi, form a dialogical relationship. The magic loss of the magical brush and the degradation of Ma Liang show modern people to dominate their own destiny and also expose the alienation of consumption culture crisis.
The Magical Brush & Ma Liang; consumption culture; adapted drama; intertextuality
2016—11—27
姜云峰(1994— ),男,上海市嘉定区国家税务局科员。
J954
A
1009-5152(2017)01-0050-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