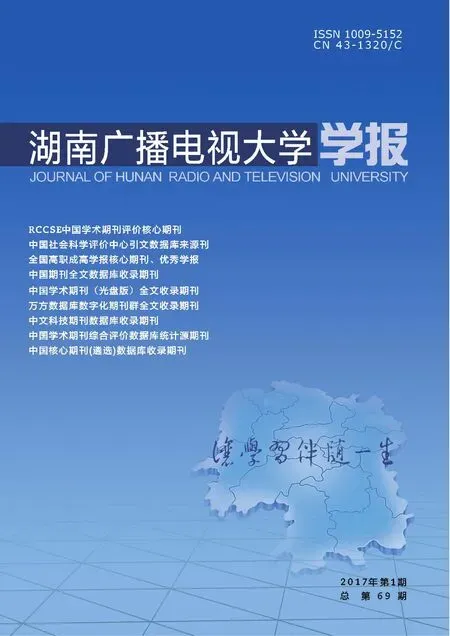《龙性堂诗话》批评视野中的苏轼诗歌
2017-02-23夏新秀
夏新秀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龙性堂诗话》批评视野中的苏轼诗歌
夏新秀
(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江苏徐州 221116)
《龙性堂诗话》对苏轼予以高度重视,在对其诗作品评中,抓住了用典、曲折、神似、奇趣和天趣等审美取向,基本体现出苏诗的内在特征,为后世进一步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批评条件。
《龙性堂诗话》;苏轼诗歌;理论批评
苏轼,是我国北宋时期具有多方面艺术才能的诗人,其诗作对宋诗体质的最终形成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在明末清初“诗必盛唐”的学术背景下却受到前所未有的冷遇。间有所评也应门户之见而有失公允,如刘绩《霏雪录》云:“唐人诗一家自有一家声调,高下疾徐,皆合律吕,吟而绎之,令人有闻韶忘味之意;宋人诗譬则村鼓岛笛,杂乱无伦。”[1]在此环境下的叶矫然却颇喜苏诗:“予最喜读昌黎、长吉、义山、子瞻四公诗。”①于《龙性堂诗话》中更对苏诗进行细致品评,揭露出其好用典使事以及追求曲折、神似、奇趣、天趣的审美取向,有一定理论意义,为后人进一步研究苏轼奠定了基础。
一
用典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一种惯用手法,即创作者在诗文中引用一些有来历的故事、语言,形成超越文本本身的意义内涵。苏诗好用典故众所周知,以才学为诗是其创作的显著特征。对苏诗的这一创作取向,历来文人分歧较大。
其中激烈反对苏诗用典的如宋朝张戒、严羽和明朝王世贞等人,当然,也有支持苏诗的如清初王晓堂,其《匡山从话》卷五:“用事琢句,妙在言其用而不言其名,大家中备有此法,惟荆公、东坡、山谷三公知之。”[2]指出苏轼用典不拘泥于原典的特征。叶矫然在《龙性堂诗话》中对苏诗用典的态度更是颇为允当:“……义山不然,有来历,有根据,用僻事而实一一可考,唯坡公可以继之。坡公之诗未易读,彼其傀儡古人,调和众味,命意使事,迥出意表。”他指出李商隐诗歌用典是有来历、有根据、经过深思熟虑的,而此方式惟有东坡可以继之。义山与苏轼用典的相通,叶矫然还有其它论述,如“子瞻七律好用典实,自是博洽之累,或曰其源实本之义山,良然。”“子瞻诗包罗万象,一由我法,集中一种烟云满纸、咳唾琳琅者为最,清空如话者次之。至有时斗韵露异,不无小巧,求真得浅,未免添足。退之、香山、义山亦时时有之,要不碍其为大家。”宋人论及李商隐,多指斥其对西昆体的负面影响,叶氏此处却论东坡沿袭其诗用事繁多、深僻的创作倾向,可谓眼光独到。“其源本之于义山”,笔者认为根据还在于苏诗中有大量典故化用于义山。如陆游《施司谏注东坡诗序》就言苏诗“五亩渐成终老计,就重新扫旧巢痕”是化用李商隐“昔祖宗以三馆养士,储将相材。及元丰官制行,罢三馆。而东坡盖尝直史馆,然自谪为散官,削去史馆之职久矣。至是史馆亦废,故云‘新扫旧巢痕’。其用事之严如此。而‘风巢西隔九重门’,则又李义山诗也。”[3]
苏轼不仅继承义山用典之有来历、有根据的取向,且具有“傀儡古人,调和众味”的高超能力。何为“傀儡古人,调和众味”?即能灵活运用故实,广泛吸取前人长处为己所用。笔者认为,苏轼之所以能成一代大家,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他博采众长、善于学习的精神。如《游诸佛舍,一日饮酽茶七盏,戏书勤诗壁》:“示病维摩元不病,在家灵运已忘家。何须魏帝一丸药,且尽卢仝七碗茶。”②这首七言绝句,句句有典,分别引自《维摩经》《传灯录》《折杨柳行》《谢孟谏议寄新茶》。分看四典毫无关联,但整合起来却别有风味。作者寄情茶道,表现自己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又如诗作《送子由使契丹》:“云海相望寄此身,那因适远更沾巾。”化用杜甫《南征》诗“偷生长避地,适远更沾襟”,表现自己旷达乐观的情怀。这些典故的使用均进退自如,或改易、或裁减、或融化于无形。
除了具有博采众长的高超能力,叶矫然指出苏诗用典还能取得“命意使事,迥出意表”的审美效果,此命题突出苏诗之创造性。他在《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五首》提出:“紫驼之峰人莫识,杂以鸡豚真可惜……用之如何在我耳,入手当令君丧魂。”在苏轼看来,好的典故就像是驼峰,但可惜的是它混杂在鸡豚中难以辨认。但假使有“我”这样的高手能够识出,加以运用,自然能达到“令君丧魂”的至高境地。具有这种审美境界的诗歌有很多,如《和刘景文雪》:“那堪李长侍,入蔡夜衔枚”,这是引用唐代李愬的事典。诗人由大雪想到李愬雪夜入蔡州,读者又可凭借这一故事来想象出大雪纷飞的意象,这也就实现了典故的再创新。再如《和前安道寄惠建茶》,粗看诗体极为平淡,细析即可看出苏轼竟在诗中以人的典故喻茶,新颖独特,故纪晓岚评:“将人比物,脱尽用事之痕,开后人多少法门。”[4]
当然,如果不理解一些典故的含义,自然也就读不懂苏诗,故叶矫然也提出“坡公之诗未易读”的命题,只是此瑕不掩瑜,苏诗用典的方式,在当代仍值得我们学习。
二
中国传统美学历来讲究“曲”,而反对平铺直叙,认为文章应该有起伏、有波澜、笔笔生情而力避板滞。这种观点从古至今,贯穿于诗、词、曲等各体文学作品的创作之中。刘勰就曾指出:“深文隐蔚,余味曲包”(《文心雕龙》)。袁枚也说:“凡作人贵直,而作诗文贵曲”,“文必错综见意,曲折生姿”(《随园诗话》)。只言片语中道尽了文章之“曲”的重要性。苏诗就具有这种“曲折”的审美特点。
《龙性堂诗话》评:“今人学古而徒求之曹、刘、沈、谢,学今体而徒求之李、杜、高、岑,皆从门入者,不能至也。东坡教人作诗熟读毛诗与离骚,曲折尽在是矣,亦至言也。”此中运用比较的手法突出东坡教人作诗方法的合理性。又有“坡老《题张竞辰所居》诗云:‘清江萦山碧玉环,下有老龙千岁闲。知君好事家有酒,化为老人夜扣关。’此与《后赤壁》末段梦鹤一景,变化相似。因想子美《寄韩谏议》诗:‘美人娟娟隔秋水,濯足洞庭望八荒……’等语,文心幻淼,直登屈、宋之堂。苏公又尝教人作诗之法,当熟玩《离骚》曲折,良有见乎此也。”叶矫然于此揭露出苏诗创作以毛诗、离骚为旨归,追求诗文的曲之审美倾向。他认为,今人作诗单纯的学习谢灵运、李白、杜甫等人是不能达到至高境地。
毛诗、《离骚》的曲折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比兴寄托手法的运用,苏诗明显也具此特征。汪师韩评《次韵张昌言喜雨》:“寓讽于颂,又援古为说,真能以《三百篇》间者。”在对《画鱼歌》《鱼蛮子》《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的品评中更是直接揭示出苏诗比兴寄托的特点。这样的诗歌还有很多,广为人知的《饮湖上初晴后雨》就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其中苏轼不是把山水当做一般的自然外物,而是将其化为诉诸自己内心的媒介。
与这种“曲折”创作方法相关,苏诗也体现出一种“幽”的审美趣味。叶矫然在《龙性堂诗话》中就将苏轼与杜甫诗歌进行比较,通过例举苏诗“江云有态清自媚,竹露无声浩如泻”,“微风万顷靴纹细,断霞半空鱼尾赤”,揭示出其诗“语以幽胜而实奇”的审美特征。何谓“幽”?《说文解字》中释:“幽,隐也。”段玉裁注曰:“幽,从山,犹隐从阜,取遮蔽之意。”据此,笔者认为,苏轼诗歌之“幽”与刘勰所谓“隐”(《文心雕龙·隐秀》)有异曲同工之处,二者均能达到“文外之重旨”的审美效果。在诗歌创作活动中,其审美意象的创造不是将情感宣泄无疑,而是深藏其中,寻求一种“曲折”的表达,这种表达给读者留下了广阔的体悟空间。
三
神似与形似历来是中国古代文论中讨论的重要问题,叶矫然于《龙性堂诗话》中也有所涉及:“诗贵神似,形似末也。……东坡云:‘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徐熙画花卉,意不在似,有高于似者,是谓神似。诗曰:‘惟其有之,是以似之。’神似之谓也。”叶矫然首先就标明自己的主张:贵神似而轻形似,后以引用论证、举例论证的方式来显示自己观点的合理性。
那神似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其和形似究竟有何区别?关于答案,我们可以追究到庄子。庄子乃道家代表,他重神不重形,在代表作《齐物论》中有一段经典论述:“南郭子綦隐机而坐,仰天而嘘,答焉似丧其耦。颜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5]他认为人心是可以和形体分离的,这里的“心”,也即“神”。晚唐诗人司空图也大力提倡“不知所似神而自神”的艺术境界,主张诗歌创作要得象外之象、韵外之韵。这实际也就是追求“离形而得神似”。后代学者在探讨此问题时,有的提出“形似是表现事物细节的真实,神似则是表现事物本质的真实。”笔者认为,这样的说法基本正确。
叶矫然说:“徐熙画花卉,意不在似,有高于似者,是谓神似。”他将绘画与诗歌创作联系起来,强调作画、作文的目的不应在于形似,而要高于形似以达到神似。之后,他又结合具体诗歌对苏诗的这一审美特征进行细致分析。他将杜诗与苏诗并提,首举杜诗《题王宰山水图歌》以及《刘少府山水障歌》,评其为“笔底生烟,力透纸背”,认为这两首诗歌的审美境界无人能继。后又举苏诗《题三丈大幅图》及《画竹石壁上》,认为其能和杜诗比肩,评其为“手快风雨,笔下有神。”这并不是叶矫然在自相矛盾,而是他抓住了苏诗“有神”这一关键之处。苏轼的这两首诗歌都有一些对细节的忽略,但这仅是为了更好的表现其内在精神。
其实苏轼本身在论诗时就是重神轻形,正如叶矫然上引“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所以在研究苏诗时,一定不能仅着眼于其修辞等外在形式,而应注重其艺术的内在含蕴。关于苏轼的《慧崇春江晚景》一诗,历来有学者对其中的河豚初上意象发出质疑,认为其不合逻辑。王水照先生在《生活的真实与艺术的真实——从苏轼〈惠崇春江晚景〉谈起》中指出:“诗歌中的自然形象,不是诗人对客观事物一般属性的简单模拟,而是他心灵中对自然美的扑捉和再现,是人的本质的对象化。”[6]这是对神似与形似差别的最好诠释。
四
洪亮吉在《北江诗话》中云:“诗文之可传者有五:一曰性、二曰情、三曰气、四曰趣、五曰格……趣亦有三:有天趣、有生趣、有别趣。”[7]他将“趣”与诗文中其它几种重要因素并列,标示出“趣”的核心地位。惠洪也将“趣”进行过细致的划分。叶矫然在《龙性堂诗话》中则是通过例举具体诗句以揭示出苏诗的两种审美取向:奇趣与天趣。
上文已提及叶矫然评苏诗是“语以幽而实奇”,说明在他看来,“奇”是苏诗的本质特征之一。又有“予欲合子美、子瞻七言古体,梓为一集。盖此体中之神通广大,无如二公,杜奇而壮,苏奇而秀,千古双绝。”叶矫然于此又一次将苏轼与杜甫并举,指出二者的七言古体神通广大,虽一个是奇而壮,一个是奇而秀,但二者都具“奇”这一共同特征。“奇”,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注为“不群之谓”[8],也即偏离常规、不合正统之意。苏轼对“奇”也有过深刻阐释,他在柳宗元《渔翁》后评:“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熟味之,此诗有奇趣。”此评以“反常合道”四字最为重要。从字面上来看,即怪异新鲜而又合乎常理,表现为别开生面及奇特而含机趣。总的看来,《渔翁》一诗宁静淡泊,其中并无奇字奇句,其“奇”主要在于意境。诗人在日常生活中体会到渔翁的与世无争,主体并不是高人雅士,体会到的却是一种纯任自然的淡泊,在不可能之处领悟到的却是奇妙的道理,这就是“反常合道”的本质含义,也是“奇趣”的根本来源。对于陶渊明,苏轼评曰:“如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覆不已,乃识奇趣”(《书唐氏六家书后》)。他在此处从接受美学的角度,揭示出“奇趣”的产生并不是瞬时性的,而是需要反复阅读、认真体会方有所得。
对于苏诗之“天趣”,叶矫然在诗话中论述的就更为详彻,其用类比论证,将画与诗并举。原文如下:“陈用之善画,宋迪谓曰:‘汝画信工,但少天趣。当求一败墙,张素倚之,朝夕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为山,下者为水,显者为近,晦者为远。神领意造,恍然见有人禽草木飞动之势,则随意命笔,自然境皆天就,不类人为,是为天趣之笔。’试取而论诗,诗至天趣,亦难言矣。求之古人,其唯谪仙、坡公乎?”叶矫然将宋迪对陈用之绘画的品评运用于诗歌创作,揭示出“天趣”这一境界的难以到达。
“汝画信工,但少天趣。”笔者看来,实质上是对画工与化工的比较。何为画工?即对事物的细节精心描绘,以追求形似。何谓化工?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说:“诗画本一律,天工出清新。”此处的天工也即化工,指的是一种自然入妙、浑然天成的审美境界。苏轼也曾提出过一个著名命题:“合于天造,厌于人意。”天造即化工,人意即画工。这说明真正优秀的创作需得自然之神韵。
“当求一败墙,张素倚之,朝夕观之。”即主张艺术创作首先要重视亲身体验。一个画家想要创作出真正符合自然的画作,就必须长期深入到大自然中细心观察。随着时间的积累,就会产生“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的效果。而后将这种心得体验加以发挥,使得“高者为山,下者为水,显者为近,晦者为远”。在这一过程中最为重要的是“神领意造”,此乃“不能不为之”的非理性心理状态,创作主体摆脱了社会功利的束缚,心灵达到一种纯净的自由。
“随意命笔”这个命题,如果借用西方当前的文学术语来表达,相当于“思维地图法”和“头脑风暴法”。“思维地图法”是教人一个个地域的联想,“头脑风暴法”是给人的思维以极大的自由性。这两种思维方法都没有给人设任何限制。当然,此命题也可用中国古代文论中的其他命题来作替代,如苏轼提出的“随物赋形”。他说:“吾文如万斛泉涌,不泽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水无常形,遇物可以转换自己的形态来适应。在苏轼看来,诗人的才思就如水,一旦有所感发,便可以“应物而动”“循理而发”。总的来说,叶矫然将宋迪论画应用于文论,可谓贴切之至,于当代仍具有很大价值,值得重视。
注释:
①本文所引《龙性堂诗话》中内容皆出自:郭绍虞,富寿荪.清诗话续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②本文所引苏轼诗歌均出自:王文诰辑注.苏轼诗集[Z].北京:中华书局,1982.
[1]陈伯海.历代唐诗论评选[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526.
[2]王水照.苏轼研究[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266.
[3]周振甫.周振甫讲古代诗词[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601.
[4]朱靖华.苏轼论[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7:96.
[5]郭象.庄子注疏[Z].北京:中华书局,2010:23.
[6]王水照.唐宋文学论集[M].济南:齐鲁书社,1984:326.
[7]洪亮吉.北江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22
[8]段玉裁.说文解字注[Z].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204.
On Su Shi’s Poem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ticism in Long Xingtang Poetry?
XIA Xin-xiu
Long Xingtang Poetry highly appraised Su Shi. In the comment of Su Shi’s poetry, it used allusions, turns, similarity in spirit, romance, and natural aesthetic orientation, which basically embodies Su Shi’s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and provides a rich theoretical criticism condition for the further research in future.
Long Xingtang Poetry; Su Shi’s poems; theory criticism
2016—11—06
夏新秀(1994—),女,江苏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
I207.22
A
1009-5152(2017)01-0042-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