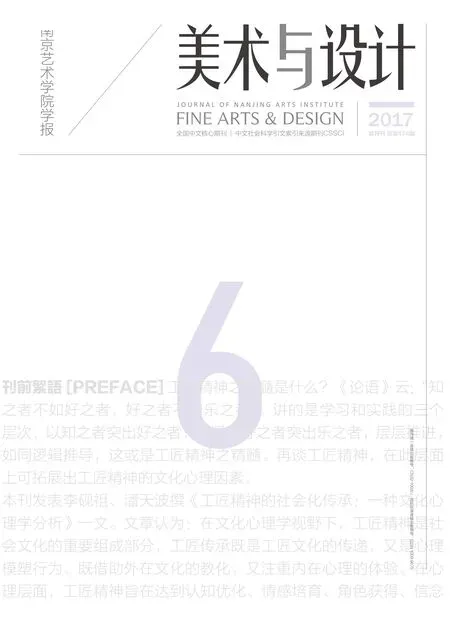艮岳:奢华缥缈难成观止
2017-02-17倪祥保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江苏苏州215123
倪祥保(苏州大学 凤凰传媒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艮岳:奢华缥缈难成观止
倪祥保(苏州大学 凤凰传媒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艮岳的建造其实处于内忧外患之际,又因强制性经营而显得仓促与缺乏从容。它的存世时间只有5年,很快就荡然无存,甚至寻找不到遗迹,人们只能通过太多溢美之词的《御制艮岳记》才对它有一点间接的模糊了解。因此,近来对它的大加赞誉,其实是建立在对其别梦依稀一般奢华景观基础上的盲目崇拜。900年来,艮岳本身给中国园林留下的主要印象只是奢华的缥缈,其最具特色的垒石叠山造园技艺也并不具有开创性,因此事实上少有垂范后世之经典的实际效果。
艮岳;中国园林;垒石叠山;纪录片《园林》;《园冶》
今年是艮岳建造900周年。关于艮岳,中国古代园林研究者一般都会涉及,但是通常展开不多,也深入不了。造成这个情况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它的存世时间只有区区5年,很快就荡然无存,甚至寻找不到遗迹,而且不可能有相关的照片或烫样,也没有相关画幅。除了直接参与的建设者和少量游览过的人们,其余人都只能通过太多溢美之词的《御制艮岳记》才对它有一点间接的模糊了解。有感于央视纪录片《园林》等对它的特别青睐和格外推崇,笔者觉得关于艮岳的关注和研究需要秉持实事求是的态度,不应该在虚无缥缈间将其捧到天上去,毕竟它与存世很多的精美的宋代山水画在中国艺术史上的影响很不一样,更不能与依旧存世的精美园林(哪怕像圆明园那样有迹可寻的遗址)相提并论。
一、建于内忧外患之际
艮岳始建于宋徽宗政和七年(1117),至宣和四年(1122)竣工,初名万岁山,后改名艮岳、寿岳,或连称寿山艮岳,亦号华阳宫,1127年,金人攻陷汴京后被拆毁,很快就荡然无存。关于艮岳的建造,南宋人张淏所撰《艮岳记》开篇有这样一段论述:
徽宗登极之初,皇嗣未广,有方士言:“京城东北隅,地协堪舆,但形势稍下,傥少增高之,则皇嗣繁衍矣。”上遂命土培其冈阜,使稍加于旧矣,而果有多男之应。自后海内乂安,朝廷无事,上颇留意苑囿,政和间,遂即其地,大兴工役筑山,号寿山艮岳,命宦者梁师成专董其事。①本文所引张淏撰《艮岳记》和宋徽宗的《御制艮岳记》的内容,均来自百度百科《艮岳记》词条。
通过这个记载,可以了解建造艮岳初心或初衷的两个方面内容:第一,为了“皇嗣繁衍”,这具有子孙万代永坐江山的意思,所以初名叫“万岁山”,又名“华阳宫”;第二,皇上因“海内乂安,朝廷无事”而“留意苑囿”,具有盛世造园的表白。就第一点来说,古都汴京所在地为黄河冲积平原,缺少丰富的自然地貌,更缺少具有护卫屏障样态及功能的山冈,所以,从有关国家长治久安的风水角度来看建造艮岳的初心或初衷,就是非常自然合理的。就第二点来说,说宋徽宗“留意苑囿”应该是真的,因为他喜欢琴棋书画,需要有良好的生活环境来满足他的艺术活动;说“海内乂安,朝廷无事”,那只有从无心政治、不懂军事的宋徽宗角度而言才是真的——这就像10年后他成为阶下囚那样千真万确。这就是说,关于宋徽宗因“海内乂安,朝廷无事”而“留意苑囿”,只是宋徽宗自己的认识,其实未必符合当时客观的历史现实,这句话其实很可能遮掩了当时北宋王朝面临的政治与军事实情。历史地看,艮岳开始修建前夕及建设期间,辽国、金国之间争斗不断,战事频发,并且经常牵涉宋王朝。期间,女真人金太祖完颜阿骨打与宋王朝暗中签订盟约,共同消灭辽国——其实这为女真人灭辽之后有能力腾出手来全力灭宋打下了基础。艮岳开始建造后不久的1119年,爆发了特别有影响力的宋江带领梁山好汉的造反起义,1120年,又爆发了直接反对“花石纲”的方腊起义。这说明当时北宋王朝所面临的国内外社会政治形势其实都很不稳定。
正是因为艮岳建造于北宋王朝遭受灭顶之灾的前夕,所以它的被建造过程自然是很不从容的,经常被打乱计划(比如发生在各地的劫“花石纲”),很多预定的建筑材料都无法正常运送到汴京(如滞留在苏州的冠云峰、瑞云峰和滞留在山东的八音石等)。尽管艮岳在《御制艮岳记》中被描写得规模空前巨大,美轮美奂得无与伦比,但是真实的艮岳其实恐怕未必就如这歌功颂德文字所写的那样被按计划建设得至美至善。需要指出的是,亲身感受内忧外患的当时百姓,对于皇帝不恤民情强行建造艮岳也应该是有怨恨的,除了发生在各地的劫“花石纲”,张淏的《艮岳记》中也有相关的间接记述:
越十年,金人犯阙,大雪盈尺,诏令民任便斫伐为薪;是曰百姓奔往,无虑十万人,台榭宫室,悉皆拆毁,官不能禁也。
由其中相关记述可知,本来在大敌当前、寒冷难当的时候,官方下令可以“任便斫伐为薪”的恐怕应该是指一般树木和不重要的房舍家具一类,但是当时汴京百姓首先想到的却是去把艮岳“台榭宫室,悉皆拆毁”,且其势“官不能禁也”。这似乎可以从侧面证实本文关于宋徽宗建造艮岳之时,其实早已并非“海内乂安,朝廷无事”。在此基础上,也可以从另一个侧面推论并想见,艮岳的建造确实不可能非常从容讲究,难以切实做到精益求精,即无法使它在艺术创作上成为一个真正精美绝伦的中国古典园林典范——本文下面一部分将对此展开较为深入具体的论述。
二、强化经营缺乏创新
关于艮岳的建造情况,张淏《艮岳记》有这样的描述:
时有朱勔者,取浙中珍异花木竹石以进,号曰“花石纲”,专置应奉局于平江,所费动以亿万计,调民搜岩剔薮,幽隐不置,一花一木,曾经黄封,护视稍不谨,则加之以罪,斫山辇石,虽江湖不测之渊,力不可致者,百计以出之至,名曰“神运”,舟楫相继,曰夜不绝,广济四指挥,尽以充挽士,犹不给。时东南监司郡守,二广市舶,率有应奉。又有不待旨,但进物至都计会宦者以献者。大率灵璧太湖诸石,二浙奇竹异花,登莱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异木之属,皆越海度江,凿城郭而至;后上亦知其扰,稍加禁戟,独许朱勔及蔡攸入贡,竭府库之积聚,萃天下之伎艺,凡六载而始成,亦呼为万岁山,奇花美木,珍禽异兽,莫不毕集,飞楼杰观,雄伟瑰丽,极于此矣。
在国家内忧外患的环境下,如此穷奢极侈的建设,主要依靠什么才能来维持其正常地进行?笔者认为主要在于这样两个方面:第一,不惜劳民伤财,第二,拼命强抢豪夺。因此,清华大学教授朱育帆在纪录片《园林》之《汴京艮岳梦》关于艮岳的建造说过这样一句话:“经过强化性的经营,不断将全国各地的好东西加入其中。”①见央视纪录片《园林》之《汴京艮岳梦》中清华大学教授朱育帆的访谈。该片总导演金明哲,总制片人周艳,制片人徐欢,中央电视台纪录频道于2015年6月20日首播。从朱教授这句说得比较委婉的话中,读者们其实可以想见这样的问题:对于精益求精的整体艺术创作而言,任何随意而来的“强化性经营”和几乎是无序的“不断加入”的做法,显然都不如一切按整体艺术设计而来那样是上策,其效果有时很可能适得其反。联想到当时严峻的边关形势,山雨欲来的国内乱象,如冠云峰、瑞云峰、八音石等绝顶奇石都没有按计划运到,想来艮岳的建造主要在于其垒石叠山的规模宏大,同时依靠强抢征集各地奇石异树、珍禽异兽来丰富景观营造,其建造过程难以像建造圆明园、避暑山庄和颐和园那样比较从容,故难以达到很高的艺术水平。中国第一位园林艺术理论家计成在其著作《园冶·选石》中曾经针对宋徽宗及艮岳说过这样的话:“古胜太湖,好事只知花石。”[1]翻译成现代汉语的意思就是:古人以太湖石为佳,但好事者只知花石之名。将计成的这句话,和蔡京、朱勔只要听说哪里有奇石就去搜刮而来,以“花石纲”送到汴京的历史事实结合起来,就很容易想见艮岳的这种建造情景:抢到什么就加入什么,难以有整体的精心设计;其次,所有垒石都是奇石,反而不具有很好的力学结构,也难以成就优秀的叠石佳作。这就像没有起码审美能力的人或者没有精心设计安排的着装,即使全身穿了名牌,也有可能一看就是个二百五。
部分对艮岳具有特别崇拜心理的人,都认为艮岳的文化艺术高度表现在:“后世的万千园林,其中都有它的身影。”②见央视纪录片《园林》之《汴京艮岳梦》解说词。其实差矣,至少并不尽然。比如很多人都特别强调艮岳在垒石叠山技艺方面的开创新,殊不知那种造园技艺在唐代早就司空见惯了。请看清华大学建筑系周维权教授《中国古典园林史》[2]中引述的如下材料(为了体现证据充分,本文适当多引一些,其中加下划线的部分,可以直接证实唐代用垒石叠山技艺来制作山水园林的普遍性):
《长安志》记琼山县主在太平坊的住宅“内有山池院,溪磴自然,林木葱郁,京城称之。”记剑南东川节度使冯宿在亲仁坊的住宅“南有山亭院。”(152页)
“山池院”、“山亭院”,即是唐代人对城市私园的普遍称谓。唐人诗歌对此也多有吟咏:
“攒石当轩倚,悬泉度牗飞。”杜审言《和韦承庆过义阳公主山池五首》之四“石自蓬山得,泉经太液来。”司空曙《题玉真观公主山池院》(以上均见153页)
宋之问《太平公主山池赋》对其山池院中叠石为山的形态变化、山体与水体,花木、建筑的配合成景,都有细致的描写:“其为状也,攒怪石而岑崟。其为异也,含清气而萧瑟。列海岸而争耸,分水亭而对出。其东则峰崖刻划,洞穴萦回。……图万里于积石,匿千岭于天台。……阳崖夺锦,阴壑生风。奇树抱石,新花灌丛。……其西则翠屏崭岩,山路诘曲。高阁翔云,丹崖吐绿。”(153-154页)
李华在《贺遂员外药园小山池记》:“庭除有砥砺之材,础礩之璞,立而象之衡巫;……一夫蹑轮而三江逼户,十指攒石而群山倚蹊。”(154页)
白居易《题岐王旧山池石壁》:“树深藤老竹回环,石壁重重锦翠斑。俗客看来犹解爱,忙人到此亦须闲。况当霁景凉风后,如在千岩万壑间。黄绮更归何处去?洛阳城内有商山。”(155页)
韦元旦《奉和幸安乐公主山庄应制》:“刻风蟠螭凌桂邸,穿池叠石写蓬壶。” (160页)
王建《薛十二池亭》:“斜竖小桥看岛势,远移山石作泉声。” (160页)①以上文字均引自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二版),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
唐代平泉山庄主人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记》记载园中所用之石有:“日观、震泽、巫岭、罗浮、桂水、严湍、庐阜、漏泽之石。”还明确其具体使用:“台岭、八公之怪石,巫峡之严湍,琅琊台之水石,布于清渠之侧,仙人迹、鹿迹之石,列于佛榻之前。”(160页)
周维权教授的以上有关唐人对当时造园情况的相关记述,无论是“攒石”“移石”“立石”“积石”还是“布石”“列石”,其实都与“叠石写蓬壶”之“叠石”完全相同,可见唐代私宅中的“山池院”和“山亭院”的建造,与王维“辋川别业”主要利用自然山水地貌置景不同,已经完全拥有垒石叠山营造山池园林的技艺,并且引领了当时的这种造园风气。因此,周维权教授关于“在(隋唐九成宫)泉眼附近发掘出土一些太湖石,可能当年这里还有园林假山的建置”[2]的判断,应该不无道理——即垒石叠山造园技艺至少应该开始于隋唐时代。经过有唐一代几百年的传承发展,这种造园技艺基本趋于成熟,这就是宋徽宗可以征召天下造园工匠建造规模宏大的、以垒石叠山为主要特色的艮岳的客观基础之所在。
另外,央视纪录片《园林》在《写在大地上的诗》这集中关于唐三彩假山的解说词,也正好与本文以上所列材料及本文的观点非常一致,有力地击破了该片在《汴京艮岳梦》中请部分专家学人讲述关于艮岳的观点。以下是其相关字幕内容:
唐三彩假山,它所代表的,就是我们将要寻找的唐代园林……唐代园林的假山已经不再是土山,而是尖三角形的石山。山下有水一池,山上有鸟有树。这种后世典型的园林元素,在唐代已经初具规模。我们很难在历史典籍中找到唐代园林的记载,然而在唐诗中却发现有大量的描述。
“唐代园林的假山已经不再是土山,而是尖三角形的石山。”这足以说明垒石叠山在唐代私宅园林建设中不仅已经初具规模,而且应该已经蔚然成风,不然就不会有那么多唐代的诗文会写到相关的园林建设内容。基于对中国古代园林发展史的这些基本了解可知,艮岳以人工建造山水园林的做法,其实与它的垒石叠山一样并无真正原创性可言。顺便说一下,在文人私宅园林开始大量涌现的唐代,李德裕《平泉山居草木记》记载园中所用之石就有:“日观、震泽、巫岭、罗浮、桂水、严湍、庐阜、漏泽之石。”可见广泛采用各地奇石造园,早已是唐代的风尚。此外,也许是唐代文人造园者对江南山水的偏爱或对江南造园艺术的推崇,所以会有白居易在诗歌中的这样描写:“洛下园林好自知,江南景物闇相随。……停杯一问苏州客,何似吴松江上时。”②白居易诗《池上小宴问程秀才》。这其实也就是为什么宋徽宗建造艮岳时,会“专置应奉局于平江(苏州)”的理由之所在。要之,叠石为山,理水置景的造园技艺在唐代已经有之并基本成熟,因此艮岳造园主要技艺在整体上看确实并没有创新之处,至多在人造景观规模和叠石品种数量方面都有所空前而已。
明清以来是中国造园的一个重要发展阶段,其中有大量经典作品被留存了下来。不管是皇家园林,还是私宅园林,主流做法还是更多从苏州聘请造园高手,也就是说,依然更多学习以苏州为主的江南造园艺术,期间几乎从未听说有以艮岳为“模山范水”的案例,③清华大学朱育帆教授曾经认为北京景山是明显效仿艮岳的,具体请见《关于北宋皇家苑囿艮岳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探讨》,《中国园林》,2007年第6期。其实,景山在北京城的中轴线上,主要是用挖护城河的泥土堆起来的,仅凭这两点,就可以知道该观点很难成立,至少值得商榷。可见艮岳示范后世的作用及效果其实几乎可以忽略不计。以计成《园冶》来看,其中谈到造园,有时强调要有“荆、关之绘也”;有时明确“不羡摩诘辋川,何数季伦金谷”,“五亩何拘,且效温公之独乐”(不赞赏规模模巨大豪华);注重“片山多致,寸石生情”,“略成小筑,足征大观也”(倡导以少取胜,与艮岳垒石叠山的做法完全不同)。[1]其唯一涉及宋徽宗及艮岳的就是前面所引的:“古胜太湖,好事只知花石。”很明显,这还是带有贬义口吻的。因此,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作为第一个对中国古代园林造园进行全面理论总结和技艺介绍的大家,为何从理论到技法都没有提及被今人誉为“后世的万千园林,其中都有它的身影”的艮岳?为何在其谈论“选石”时唯一间接提及宋徽宗及艮岳时,竟然还是从贬义角度而言的?想来它其实应该少有特别之处为真正的园林大家所瞩目与重视。
三、短命艮岳难成观止
极其短命的艮岳,给中国园林发展史留下的主要印象是缥缈的奢华,几乎没有原创性的造园技艺给后世造园提供学习借鉴的垂范效果,因此在中国古代造园史上不可能产生衣被后世的影响——这就是计成《园冶》没有提及它的主要原因之所在。本文这个观点,可以通过央视纪录片《园林》之《汴京艮岳梦》的拍摄情况来提供侧面的有力佐证。在专门以艮岳为专题的这一集纪录片中,正面涉及艮岳的内容非常少,少得可怜,乃至可以说几乎没有。笔者对纪录片《汴京艮岳梦》这一集的内容做过非常详细的“拉片”工作,其全部内容大致可以分成41个小片段。为了节省篇幅,在此将其前面15个小片段内容提供如下:
1.约2分钟片头之后是清明上河园里王小姐在招亲的演出;
2.清明上河园负责人周旭东谈该园的发展设想;
6.黄浦江边的画家夏小万在完成具有现代空间装置艺术特征的《桃花源》后,准备用在玻璃上绘画来造就举世无双的《宋代山水》这样一个作品;
4.杭州凤凰山管理处的邵群正在担心具有1049年历史的宋代梵天寺石经幢的保护;
5.画面以三屏的方式呈现同时介绍周旭东、夏小万和邵群三位的各自忙碌工作;
6.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正在上演大型水上实景演出《东京梦华》,其中演唱的竟然是唐朝李后主的《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
7.歌声延续,历史到了1100年,赵佶在画画,随后被告知要登基即位;
8.回到《东京梦华》演出现场,赵佶成为徽宗皇帝与民同乐,开始起君王之梦;
9.周旭东说开封有4台大型演出,压力很大,于是想办法去请好演员来提升表演质量;
10.在《东京梦华》演出情景中加入关于蓬莱、桃花源与园林关系的简要论说,讲述徽宗皇帝将把蓬莱和桃花源重新打造宋人眼里的人间仙境——艮岳;
11.分析赵佶《听琴图》中的真实历史人物关系,特别强调作为宰相的蔡京对徽宗皇帝说大宋国库殷实足以支持皇帝办任何事情以彰显其开辟盛世的“丰亨豫大”;
12.中国宋史研究会副会长程民生讲述赵佶当皇帝是一个历史错位;
13.颐和园景观,夏小万想用22层玻璃再现宋代山水,清华大学建筑学专家朱育帆说艮岳是绕不过的高度,于是两人在颐和园里继续深入探讨;
14.河南开封的街景和历史传说。介绍清明上河图的创作和徽宗为之题名并作为第一个收藏者,再讲述徽宗看到此画后又想起要建艮岳了,然后风水先生的话语又让艮岳的建设变成不得不做的事;
15.苏州画家叶放(该纪录片顾问)在寻找小型的太湖石制作艮岳微型景观……
在以上超过三分之一的纪录片内容中,没有正面涉及艮岳的内容,在以下还有的36个片段中,内容最多的是关于当今开封市大型游乐节目《清明上河园》台前幕后的故事,正面涉及艮岳的只有一、二处,那就是1122年春天,艮岳落成时,宋徽宗前去观看,其中画面内容是扮演宋徽宗的一行人来到一处园林模样的建筑(艮岳大门)之前,接下来马上呈现的是夏小万正在进行《宋代山水》的最后一道工序。于是,情景再现中来到艮岳的宋徽宗,看到的其实就是夏小万的《宋代山水》及其动画呈现。再接下去,用《御制艮岳记》主要文字极其简单而原则地介绍艮岳(同步画面上出现的还只是夏小万的《宋代山水》)。就这样,一直到该集结束,始终没给人一点关于艮岳大致模样的具象呈现(比如可以根据《御制艮岳记》描述制作部分数字成像画面),而只是说宋徽宗死了。
笔者如此不厌其烦地介绍该集的主要声像内容,为的是让读者更好地理解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纪录片创作者为什么没有、也没能正面地讲述并有所具体地呈现艮岳?第二,纪录片创作者在如此碎片化表述后,其实并没有能够进行很好的组合,或者说其实所有这些内容也根本无法对艮岳具体形象进行有效的重构。其原因何在?笔者以为,艮岳建成不久即遭拆毁,后来又为自然所湮没,后人不仅无法见到其实体,甚至也看不到遗迹,只能凭《御制艮岳记》展开想象,确实难以进行比较具象的呈现。纪录片中叶放先生关于艮岳的那个用石头制作成的清供小品,体量实在太小,既不具备“寿山艮岳”的特征,更没有相关水系的存在,而夏小万的作品,在纪录片中也始终只有若隐若现的玻璃画的平面表达。令人不解的是,该纪录片创作者聘请清华大学园林研究学者朱育帆教授进行了相关讲述,而朱教授于十多年在孟兆祯教授指导下,制作了“艮岳想象景观”并捐给北京古代建筑博物馆进行陈列展示,获得著名园林学家吴良镛、周维权教授等的好评,[3]但是纪录片创作者对此难得而极具直观效果的成果却完全忽略了。也许作者要说,这部纪录片重点谈的是关于园林文化思想与人们生活理念之间的关系,或者说主要关注的是渗透在古代园林里的文化思想和古人生活理念与我们今天选择可能生活方式之间的历史渊源及文化相关。那么本文笔者要说,正如作者在这一集最后所讲述的那样“关键是给谁看”,即《汴京艮岳梦》到底要让观众知道艮岳的什么?
正如再别开生面,还是要得其环中;宕开一笔,须及时言归正传才不会离题太远;再怎么高明的侧面描写,总也不能替代置身其境的“执手相看”。纪录片创作者和参与其间的很多专家学人其实都无法给观众以比较直观的艮岳(没有采用数字成像技术),是因为其实谁也无法相对具体直观地描摹艮岳的大致样态,这说明所谓“后世的万千园林,其中都有它的身影”,确实不过是想象之词而并没有很坐实的根据。这与很多中国古代园林研究者可以比较充分地论述哪个园林借鉴了哪个园林的研究成果相比,显然关于艮岳这方面的关注和研究都显得苍白无力,确实根本无法从中找到“它的身影”。当代对于艮岳具有专门研究的清华大学朱育帆教授早就说过:“艮岳的实际规模可能远非人们臆想中的那么大……。”[4]这无异是清醒而理智的学术认识。事实上,如果艮岳足够的大,不至于被破坏得那么快,因为其作为垒石叠山的基础部分将非常庞大,加之使用黏合材料的原因难以被转移到别处有效使用而留存下来,从而也就不可能在短时间内被完全湮没。
900年来,艮岳本身给中国园林留下的主要印象只是奢华的缥缈,一般认为其最具特色的垒石叠山造园技艺,也并不具有开创性。如果艮岳真的被建设得足够宏伟壮观结实,它应该不至于连一点遗址痕迹都没有,使得它事实上没有垂范后世之经典的实际效果。因此笔者认为,关于艮岳的关注和研究确实需要秉持事实求是的态度,除非有重要的新发现,不应该仅凭那些几乎虚无缥缈的东西就花费太大的力气将其捧到天上去,因为那既不是很好的学术态度,也确实没有多少传播价值。
[1]刘乾先.〈园林说〉译注[M].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8:223.
[2]周维权.中国古典园林史(第二版)[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148.
[3]潘琪燕.艮岳与艮岳想象景观[J].古建园林技术,2004(9).
[4]朱育帆.关于北宋皇家苑囿艮岳研究中若干问题的探讨[J].中国园林,2007(6).
J209
A
1008-9675(2017)06-0110-05
2017-09-18
倪祥保(1953-),男,江苏常熟人,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影视艺术与中国美学。
(责任编辑:吕少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