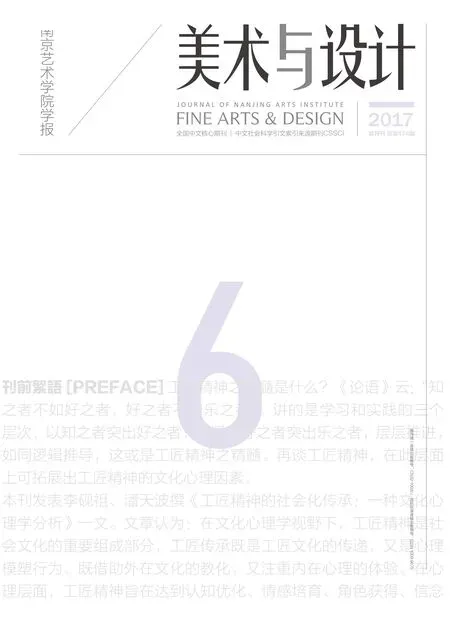八十年代的会议精神与美术创作转向
2017-02-17王志亮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王志亮(河北大学 艺术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八十年代的会议精神与美术创作转向
王志亮(河北大学 艺术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在1980年代的艺术发展过程中,不同会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时创作实践中的问题和要求,反过来,会议又促进了创作实践的发展和转型。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描绘群众形象的作品备受关注,由此产生了关于《父亲》一作的争论。反精神污染之后,题材决定论成为美术界急需解决的问题,由此引发了关于第六届全国美展的反思。1985年与1986年的两次油画讨论会,提出创作自由的要求,并且关注青年美术家,这在某种程度上进一步推动了80年代后半期美术创作的进一步发展。
十一届三中全会;题材决定论;创作自由
要说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美术史研究的独特魅力,其核心所在就是整一性。
在艺术市场还未形成的八十年代,从艺术体制的角度来看,这一时期美术发展的整一性表现为,持各种观点的艺术家、批评家、报刊杂志、展览空间和高校知识分子都被高度整合在一起,围绕一个话语核心推进创作实践。八十年代美术发展的整一性让我们看到,美术在社会整体结构中扮演的重要角色,而不像今天这般已经形成一个自治的领域。基于整一性的视角,本文以八十年代的几次重要会议为核心,讨论会议决议与美术创作观念之间的互动关系。
一、从工作重心转移到绘画中的群众形象
罗中立的作品《父亲》在四川青年美展中崭露头角,于1981年初刊登于《美术》杂志,并斩获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金奖。这样的殊荣自然让作品成为美术界甚至社会关注的焦点。自1980年至1982年,以《美术》杂志为媒介,美术界发生了一场围绕罗中立《父亲》的争论。在这场争论中,《父亲》成为一个时代的图像符号。这个符号背后是整个伤痕和乡土美术代表的创作转向。而创作转向背后,又是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的调整。我们或许可以反过来推论,国家政治和经济发展方向的调整,涉及到文化政策转向,从而直接影响了关于《父亲》的争论。
时任《美术》编辑主任何溶最早提出了《父亲》的重要意义,并将其所代表的四川青年美展反映出的现象称之为“美术创作的伟大转折”。何溶的文章显然已经明确注意到美术创作潮流与时代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的国家正处在一个新旧交替的伟大转折之中,为了促进这个伟大转折的发展进程,我们的美术创作已开始发挥它的积极作用。”[1]这里的“伟大转折”正是作者所论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更是指1978年底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简称十一届三中全会),会议结束后,公开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以下简称《公报》),这让我们得以讨论该次会议与《父亲》一作,甚至整个乡土和伤痕艺术的话语传播和影响关系。
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发布后,社会各界积极响应,并发表一系列学习报告。这一系列学习报告都将这次会议的整体精神总结为“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符合我们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2]因此,何溶在评价四川青年美展时的判断,恰是指三中全会后中国社会的整体转型。实际上,在何溶之前,美术界早已对此作出反应。在1978年华东六省一市三十周年美术展览草图观摩会中,华君武主持会议,与王朝闻、肖峰等针对《公报》涉及内容展开讨论。面对社会改革局势,这次座谈会是美术界最早对《公报》作出的反应。《公报》中明确提出了有关文艺作品的问题:“华国锋同志在会上着重强调了党中央和各级党委的领导。他提议:全国报刊宣传和文艺作品要多歌颂工农兵群众,多歌颂党和老一辈革命家,少宣传个人。”[3]针对这一点,座谈会参与者表示“由衷赞同”,认为“我们宣传工作应该来个根本性的转变,把创造历史的人民群众作为美术创作的主要歌颂对象,占主要位置。”[4]
1978年底美术界的座谈会,体现出后来判断艺术作品的某些标准,尤其是在全国性的展览中,其中,四川的伤痕绘画和乡土绘画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话语的某种体现。经过各地的座谈会后,艺术创作的标准被更加明确化。标准的关键是“歌颂工农兵群众”,破除个人神话。伤痕美术能够在全国范围内流行起来,重要原因正是符合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对文化大革命的纠偏决议,以致何溶看到这类作品后,判断美术的创作转折已经到来。而《父亲》一作的成名和争论显得更加复杂。《父亲》首次亮相四川青年美展时,题目还是《我的父亲》,后来更名为《父亲》,这其实更符合《公报》决议中“少宣传个人”的要求。更名后的《父亲》不再是某个具体人,而是成为中国农民的典型。后来有关《父亲》的争论,也即出现在对这一典型的争论中,争论的焦点恰是围绕对这一典型的批判与歌颂意义的不同理解。《公报》决议所定的基调为“歌颂”,而《父亲》则既是歌颂,同时又是批判,相比起伤痕绘画的青春忧伤和单向的批判,《父亲》激起了不同的理解。
围绕《父亲》展开的争论中,邵养德和邵大箴的观点最有代表性。他们争论的焦点其实正是围绕华国锋的意见展开,即如何歌颂人民群众。显然,邵养德的出发点依然停留在文革意识形态中,认为歌颂即是只能呈现好的一面,所以,《父亲》体现了农民“生理上的缺陷,畸形怪状。”[5]通过《美术》发表的评论看,对《父亲》的评价显然都倾向于邵大箴的看法:“《父亲》确实表现了我国当代农民的疾苦,但它远非只是客观地再现农民的苦楚,而是表现了在仍然是艰苦的劳动和生活条件下,老一代农民的勤劳、朴素和任劳任怨的优秀品质”[6]从某种程度上说,批判也是歌颂的一种形式。对于《父亲》的评价,集中反映出整个艺术批评和创作在80年代初期的新标准,这一标准与社会转型相一致。
二、反精神污染与题材决定论
1983年十二届二中全会中,邓小平讲话指出“理论、文艺工作中存在的混乱现象,强调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7]之后的1985年,有关第六届全国美展的多数评论指出艺术创作中的“题材决定论”问题。例如《美术》杂志1984年12月刊登了署名为“时真”,标题为《第六届全国美展油画研讨会在沈阳举行》的报道文章。文章提出了油画创作中存的问题,其中这样几项不断被后来的艺术会议提到:1、“题材决定论”的影响依然很大,有些作品仍然是所谓的“大题材”,架子大,板着面孔,使观众感到疏远。2、有些作品重视美术的教育功能而忽视美术的审美功能。3、形式风格过于单调和简单,油画形式的丰富性和技巧的特殊性,未能得到充分研究和发挥。[8]
1984年,第六届全国美展所反映出的题材决定论问题,虽与十二届二中全会发起的反精神污染运动关系密切,但不是因果关系,题材决定论在乡土和伤痕美术中早已存在,这是新中国美术的核心命题。什么是反精神污染,它又针对什么?在文艺创作中,精神污染被总结为:艺术作品表现自我,与时代保持距离,鼓吹抽象的人性论和抽象的人道主义,盲目崇拜西方现代派文艺。[9]这样的内容落实到1983年美协工作会议中,便成为:美术理论“过于夸大形式、自我和抽象在创作中的作用,助长了创作中脱离现实、脱离群众的倾向,实际上对党的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推陈出新的方针有所干扰。”[10]虽然,美协工作会议纪要显示,除了贯彻反精神污染外,不要把第六届全国美展搞成“冷冷清清、单调枯燥的局面”。但是,对精神污染的上述认定,基本上否定了现实主义之外其他艺术创作方式的价值。
美术界反对精神污染的目标很明确,距离会议最近的正是《美术》杂志讨论抽象艺术的一系列文章,再远一点我们会发现,1979年美术界关于袁运生壁画《泼水节》的争论。关于前一点,《美术》杂志编辑部以本刊评论员的名义发表《高举社会主义旗帜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并坦言:“我们刊物在近几年的工作中,也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缺点、错误,希望广大读者和美术家提出批评意见。”[11]
种种迹象表明,反精神污染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第六届全国美展的评价标准和作品形式。据统计,在获奖的两百零七件作品中,“描写重大政治题材和描绘社会主义建设成就题材的作品有七十余件,描写少数民族、乡土风情的六十余件,山水、花鸟、风景、古代人物和装饰画等作品六十余件。”[12]①有关第六届美展的具体分析,也可参考:陈醉,《从形式角度看第六届全国美展:兼谈中国美术向何处去之我见》《美术史论》,1985(03):4-14.其中,作者对油画题材做了详细的统计。获奖作品以现实主义为主,并且大部分作品体现出反精神污染的要求,没有“夸大”的形式美、自我表现和抽象艺术的作品。题材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作品的优劣。这样的题材决定论实际让我们再次回到了有关《父亲》的争论中。在不同读者对《父亲》展开的争论中,没有人质疑过罗中立的创作手法,因为《父亲》的超级写实主义本质是现实主义的某种极端表现形式。这场争论的焦点依然是题材,以及其涉及的意义问题。所以,一直到全国第六届美展中,美术批评和创作的标准相比文革时的更新,更多体现为题材内容的更新,而非创作手法。而1984年的第六届全国美展,实际是更新后的题材决定论极端化的一次展现。
三、政策纠偏与创作自由
题材决定论伴随反精神污染运动的开展而愈加严重,这一状况不仅立刻在美术家协会内部得到反思,而且在作家协会内部,也明确提出创作自由的新标准。受中共中央书记处委托,胡启立曾于1984年底的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发言,题为《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以下简称《祝词》)。《祝词》主要内容之一,就是相关文学创作的自由问题。在《祝词》中,胡启立直言党对文艺的领导存在一些缺点,并总结道:
第一,党对文艺的领导存在“左”的偏向,在相当长的时期,干涉太多,帽子太多,行政命令太多。第二,我们党派了一些干部到文艺部门和单位去,他们是好同志,但有的不大懂文艺,也影响了党同作家和文艺工作者的关系。第三,文艺工作者之间,作家之间……相互议论和指责太多,伤感情的东西太多。[13]
这样的反思意味着要从领导层面展开文艺政策的调整,如何调整?在笔者看来,这就是从题材决定论逐渐转向创作自由,即尊重艺术创作本身的艺术性:
因此,创作必须是自由的。这就是说,作家必须用自己的头脑来思维,有题材选择、主题和艺术表现方法的充分自由,有抒发自己感情、激情和自己的思想的充分自由,这样才能够写出真正有感染力的能够起教育作用的作品。[14]
这次《祝词》对于1983年开始的反精神污染避而不谈,在某种程度说明,持续至第六届全国美展的题材决定论,其实是文艺界对中央反精神污染问题的过度解读。《祝词》中提示出,艺术不仅要有创作自由,而且发表《祝词》的《文艺研究》杂志也以本刊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强调“评论也要自由”。[15]
紧接着作家协会的《祝词》之后,美术界也展开相关艺术创作自由的讨论。这一讨论分别体现在两次油画讨论会中,第一次讨论会是于1985年4月在安徽黄山举办的“油画艺术讨论会”,第二次讨论会是于1986年4月,由中国美协油画艺术委员会在北京举办的“全国油画艺术讨论会”。
《美术史论》杂志以《迎接油画艺术的春天——油画艺术讨论会纪要》为题(以下简称《纪要》),全文刊载了会议讨论的主要内容。何为“油画艺术的春天”呢?如果有春天,那冬天具体指何时呢?所谓“冬天”,正是胡启立在《祝词》中所谈的“左”的偏向,而黄山油画讨论会《纪要》中,更进一步指明了“左”的时间点。这个时间点恰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几年,具体即是1983年至1984年这段时间。《纪要》认为油画的“公式化、概念化和单一化现象,在近年的油画创作中曾一度抬头。”[16]根据《纪要》的反映,此次油画研讨会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便是“题材决定论”。本次会议可以说彻底理清了题材决定论的问题。一方面,认为题材决定论的根源在艺术与政治之间划了等号,只要表现政治内容的要求还在,问题就得不到解决。另一方面,如何克服题材决定论?不仅题材内容和形式风格要多样,就是创作方法也不能只有现实主义,应向多样化发展。与此同时,对艺术的认识和教育功能,都应通过审美功能来体现。[17]总之,创作自由成为改变题材决定论的核心问题,这一点在文学界和艺术界的体现具有一致性。
文学界和美术界有关创作自由的讨论很快在艺术创作中体现出来,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即是张群、孟禄丁创作的《在新时代——亚当夏娃的启示》。作品《在新时代》展出于1985年5月的“前进中的中国青年美术作品展”,作品采用超现实主义的方法,挪用了西方基督教故事和中国传统元素,表现青年对新时代的向往。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让所有观者耳目一新,而对于两位创作者而言,美术界对创作自由的肯定是促使该作品完成的主要推动力:“创作自由使我们振奋,驱使我们勇敢地对原有艺术模式和框框做出新的评判。”[19]1985年之后,青年艺术家成为实践创作自由的主要群体。
四、引入青年:1986年全国油画艺术讨论会
80年代常用的代际划分词语是老、中、青,似乎青年更是活力的象征。自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随着中央政策的不断调整和转变,美术界的创作也随之发生变化。从“多歌颂群众”到“反精神污染”,再到政策纠偏后的“创作自由”,青年创作群体成为整个美术界的关注焦点。在1985年之后的各类会议中,青年艺术家和批评家出现的频率逐渐提高,其中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当属1986年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油画艺术讨论会。
全国油画艺术讨论会于1986年4月14日至17日在京召开。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吴作人、副主席华君武及美协书记处有关同志出席会议并讲话。这次会议的最大特点在于邀请了不少各地青年艺术家参会,高名潞和朱青生两位青年批评家被邀请做了专题发言。也正是在这次发言中,朱青生宣读了《当代西方画坛隔岸观》,高名潞宣读了《’85美术运动》一文。在高名潞文章中,1985年和青年联系在了一起,并被称之为运动,后来文章在《文艺研究》发表时,改为“‘85青年美术之潮”。[20]
这次会议邀请的青年油画家包括舒群、张培力和李山等,他们当时已经在1985年的创作潮流中崭露头角。李山的发言体现出当时青年艺术家与整个美术界的关系:“来自上海的画家李山在发言中也谈到,他参加会议之前,一些朋友认为这是‘凶多吉少’,告诫他不要说话。经过几天的会议,他感到老同志心胸豁达、态度诚恳,对艺术真挚执着,过去的疑团得到了冰释,已经开始有了一个共同对话的基础。”[21]
青年艺术家李山所提及的轻松对话环境,一部分源自1985年的黄山油画讨论会的理论成果,另一部分源自刚刚不久在中国美术馆举办的“当代油画展”。1986年3月29日至4月20日,黄山油画讨论会的参与者自选作品参加“当代油画展”。这次展览呈现出多样化的艺术风格,如古典风格,唯美抒情,浪漫写实,象征写实,表现光线效果,田园风情等。[22]“当代油画展”已是中年油画家实践创作自由的最大努力,但是他们与1985年出现的青年思潮相比,显然更加学院化。青年艺术家备受关注,主要在于他们既是学院的一员,又在创作方法上不同于学院派。比如发生在1985年有关浙江美术学院毕业作品的讨论,耿建翌的作品《灯光下的两个人》因为有异于学院派的写实手法成为关注的焦点。①有关这次讨论,可参考《美术》,1985年第9期的系列文章。
总体来说,1985年以后,青年艺术家成为整个美术界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1986年的全国油画讨论会正视了这股不断涌现的创作新潮,为接下来艺术创作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
小 结
会议是话语交锋和传播的公共空间。在1980年代的艺术发展过程中,不同会议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当时创作实践的问题和要求,反过来,会议又会促进创作实践的发展和转型。本文考察的四次会议,恰恰体现出话语传播与艺术创作实践之间的互动关系。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艺术创作与国家政策、社会转型紧密相关,艺术家们一方面受限于政策,不断调整创作,另一方面,艺术家们的创作实践反之也推动了政策调整。总之,突破现实主义的唯一性,追求创作自由的思潮,贯穿于整个80年代艺术发展的全部过程。
[1]何溶.读四川青年美展及其他——再论美术创作的伟大转折[J].美术 ,1980,(12):5.
[2]黄汉江.阶级斗争与工作重点转移——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
会公报的笔记[J].实事求是,1979,(2):9-15;马富武,韩纪元.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与阶级斗争问题——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J].社会科学研究,1979,(1):38-42.
[3]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J].实事求是 ,1978,(4):9.
[4]夏硕琦.为伟大的转变创作美好的图画——华东六省一市三十周年美展草图观摩会代表座谈三中全会公报[J].美术,1979,(1):2.
[5]邵养德.创作·欣赏·评论——读《父亲》并与有关评论者商榷[J].美术 ,1981,(09):57.
[6]邵大箴.也谈《父亲》这幅画的评价[J].美术,1981,(11):15.
[7]清除精神污染是文学工作者的重要任务[J].文学评论 ,1984,(1):3.
[8]时真.第六届全国美展油画讨论会在沈阳举行[J].美术 ,1984,(12):64.
[9]唐达成.清除精神污染是文艺界的当务之急[J].瞭望 ,1983,(12):18-19.
[10]一九八三年全国美协工作会议纪要[J].美术,1984,(03):4-5.
[11]高举社会主义旗帜抵制和清除精神污染[J].美术 ,1983,(11):4.
[12]高名潞等:《八五美术运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73.
[13]胡启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J].美术史论 ,1985,(1):4-5.
[14]胡启立.在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上的祝词[J].美术史论 ,1985,(1):4-5.
[15]本刊评论员.评论也要自由[J].文艺研究,1985,(1):6.
[16]迎接油画艺术的春天——油画艺术讨论会纪要[J].美术史论 ,1985,(4):4.
[17]迎接油画艺术的春天——油画艺术讨论会纪要[J].美术史论 ,1985,(4):5.
[19]张群、孟禄丁.新时代的启示:“在新时代”创作谈[J].美术 ,1985,(7):47.
[20]高名潞.’85青年美术之潮[J].文艺研究,1986,(4):33-41
[21]全国油画艺术讨论会在京召开[J].美术,1986(6),34.
[22]高名潞.八五美术运动[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87-98.
J209
A
1008-9675(2017)06-0085-04
2017-07-26
王志亮(1984-), 男, 山东临朐人, 河北大学艺术学院教师, 研究方向: 西方现代美学、现当代艺术史。
①“整一性”这一概念最早由高名潞先生提出,并进行了相关解释。高名潞先生认为,与西方分裂的现代性不同,中国现代性的发展呈现出整一性的特征。涉及到艺术观念上,表现为“艺术、政治、人性、道德,甚至宗教是被整一性地思考的。”本文所说八十年美术史发展的整一性,不特指艺术观念,更是一种艺术体制的整一性判断。详见:高名潞,《另类方法,另类现代》,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6年,第5-15页。
(责任编辑:杨身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