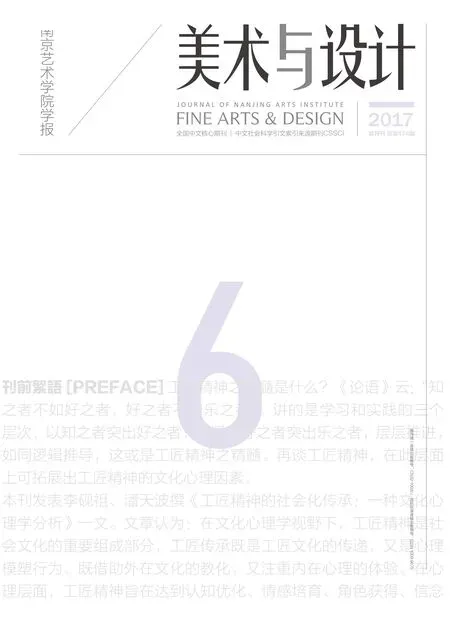董其昌文人画共同体及其绘画规范的构建
2017-02-17曹院生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上海200062
曹院生(华东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上海 200062)
董其昌文人画共同体及其绘画规范的构建
曹院生(华东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上海 200062)
晚明董其昌在政治理想屡屡折翅时,也像晚明其他的士大夫文人一样,将其经世抱负转变为对地方文化事业的发展。他和陈继儒等人一起构建文人画共同体,确立文人画规范新秩序,以实现松江地区文化的稳定发展,并通过共同体内的各种力量,包括士大夫文人话语权的力量,将文人画共同体和文人画规范推广到整个社会,而成为正统派主流绘画。
董其昌;文人画共同体;文人画规范;文人话语权
明末清初是中国绘画史上画派兴盛之际,此与明代士大夫文人喜好结社有关,更主要的原因是绘画发展到晚明原来为人所遵循的古典绘画规范发生了危机,不能继续发挥有效的指导作用,于是就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情境。如浙派后学、苏州画派余续、松江画派、金陵画派、娄东画派等,画派林立及相互攻击式的批评那是风行一时。下面我们将从社会学、文化权力学等多镜头下考察董其昌主导下的松江画派这个绘画共同体及其绘画观念的构建,以及它存在的历史意义。
一、文人画共同体和文人话语权
董其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艺术圈,在这个圈子里有其诗文书画等方面的好友,还有官场上的同僚,以及艺术市场上的朋友。
笔者根据任道斌编著的《董其昌年系》及其它资料对董其昌交游的人群进行了一个粗略的整理,大概有一百五十人左右。他们中的很多人经常围绕着“南北宗论”而展开讨论文人画理论,他们因为绘画观念相统一或相近而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小小的绘画共同体。笔者根据他们的艺术主张以及艺术交流的频率对这个共同体进行了一个圈内层级分类:核心层和非核心层。
核心层主要是由一些绘画主张相近,遵循同一绘画艺术规范进行艺术创作,且创作能力比较强、作品质量比较高以及作品数量比较多的人构成。这些人主要是董其昌、陈继儒、莫是龙、顾正谊、沈士充、宋旭、赵左等人,他们也是松江画派的领袖人物,是共享文人画理论的核心人群。这群人在文人画规范的指导下,创作出了许多典范之作,影响了一大群人加入这个圈子,繁荣了松江地区的书画艺术。更为重要的是,晚明松江画派与松江诗派、词派、几社等合力营造出了具有松江地域特色的地方意识。
非核心层与核心层共享同样的绘画规范,只是创作能力、作品质量及数量相对于核心成员而言次点、少点而已。如项元汴、姚允在、李流芳、项圣谟、冒襄、范允临、杨继朋、朱国盛、吴廷、孙叔达、吴治,以及一些为董其昌代笔的人,如珂雪、赵行之、叶君山、吴振等。这个层级的成员随着发展也会逐渐发展成为核心层成员,当然有一些人会退出这个共同体,也就是说,这是一个动态的圈层。
此外,还有游离于共同体圈外的一些人,他们是绘画共同体不断扩大的能量场,很多人将会从圈外进入共同体之内而成为圈内人员。他们当中有很多人也共享着这个绘画规范,如书法家如刑侗、米万钟等,他们偶尔也会作画;还有一些董其昌的同僚,他们收藏了很多书画作品,有时也会兴之所至;还有一些董其昌的文友,这些人在晚明都喜欢厕身于书画,聊以遣兴。这三类人的书法、诗文都不错,尤其是在董其昌大力宣扬文人画理论的影响下,提倡诗书画印一体的时候,他们个个跃跃欲试,借助于他们的诗文与书法的功力跻身于绘画之中。虽然他们缺乏造型能力训练,甚至很多时候存在着对董其昌文人画理论的曲解,但是董其昌并不放弃引导他们,反而和他们不断地进行艺术交流,共同分享文人画理论。他知道这些人随着绘画修养的不断提高将会成为这个圈子里的中坚力量,如后来的李流芳就是其中一个显著的例子。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一个绘画规范的确立应该与政治无关,但是董其昌文人画理论的构建却与其日常生活密不可分,尤其无法回避他的官宦生活的作用与影响。董其昌绘画所影响的一大批人中有许多官员,如张觐宸、袁宏道、唐文献、陶望龄、许国、焦竑、朱国桢、徐显臣、何三畏、冯梦桢、王肯堂、吴正志、朱国盛、许维新、王锡爵、范允临、陈禹谟、赵南星、叶向高、潘云翼、孟昭虞、李鲁生、朱延禧、冯从吾、冯铨、周宗建、阮大铖、朱大韶、左光斗、陈子龙、高弘图、周延儒等等。在这些官员中,董其昌都是他们中间一个非常懂得绘画,且画得非常好的画家,而且官位不小,在他们之中自然有一定的绘画话语权。他们也为董其昌的文人画理论的传播与推广产生了积极作用,董其昌自然不会放弃这样一股力量。
夏允彝为陈子龙作《岳起堂稿序》云:
唐宋之时,文章之贵贱操之在上,其权在贤公卿,其起也以多延奖,其合也或贽文以献,挟笔舌权而随其后,殆有如战国纵横士之为者。至国朝而操之在下,其权在能自立。其起也以同声相引重,其成也以悬书示人,而人莫之能非。[4]
上述情形由两个方面的原因造成:其一,科举制度的变更。唐宋科举有“诗赋”之科,明代则取而代之以“制义”之科,诗赋不再作为获取功名的工具,而成为个人才情表达的艺术形式,其独立审美价值反而更能彰显。自然而然,文章之贵贱由“操之在上”而转变为“操之在下”。当然,这也不是完全否定士大夫政治话语权的力量,只是说大潮流发生了变化;其二,文艺传播方式的拓宽。明代从事诗文创作的群体急剧扩大,诗酒倡和,结集出版,广为流传。文章的优劣判定自有公论,非贤公卿所能左右。在此情势下,文人们通过交流达成共识,形成群体意识而相互结盟成一个个小共同体。
董其昌正是认清了这个时代的变化,把握了这个时代的脉搏,他才懂得如何行之有效的构建他的绘画共同体,推广他的文人画理论。他不仅重视建设松江地区绘画群体意识,还努力将此地方群体意识推广到整个士大夫群体,并通过他们的话语权影响到整个社会。
此外,董其昌也在积极地推销自己,如他在自己的绘画作品中不断地钤上“青宫太保”“太史之章”“宫詹学士”“宗伯学士”“大宗伯印”“纂修两朝实录”“知制诰日讲官”等印,这些印章无不隐含着其话语权的宣示。这种钤印现象在晚明书画中绝无仅有,董其昌简直就是个奇葩。
不仅如此,天启元年(1622年),蛰伏二十多年的董其昌知道自己要出仕了,他给陈禹谟尚书书《神道碑》,落款是这样的:
赐进士第、通议大夫、礼部右侍郎、詹事府协理府事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奉旨纂修两朝实录、前知制诰起居经筵讲官董其昌撰并书。[5]
如果说这是一时兴起所书也情有可原,然而崇祯四年(1631年)董其昌又恰逢去北京赴任,他一高兴又狠狠地刷了一下存在感。他在《贺曹大中丞召对叙册》中款云:
赐进士出身、资善大夫、南京礼部尚书、前礼部左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詹事府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实录副总裁、经筵讲官、治生董其昌顿首并书。[6]
故伎重演无非是标榜他的社会地位,同时也是为其所倡导的文人画规范赋予政治话语权。虽然对于规范的建立而言这还是不可取的,让人忌讳的,但是对于规范的推广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所以通过董其昌这些日常生活中点点滴滴的行为方式,我们可以发现,他是一个有谋划的人,为了达到某种目的,有时甚至不择手段,或者说手段有点俗气。这才是真实的董其昌。
从社会学角度而言,根据共同体理论,共享同一规范的一群人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共同体。[7]
董其昌苦心经营的这个绘画圈子就是一个共同体,共同体内的所有成员共享着文人画理论。而且这个绘画共同体还是一个社会生态圈,它的发展有一种可供持续发展的正能量,这个能量就是董其昌一辈子精心打造的。滕尼斯说:
有一种优越的力量,它被用于下属的福利或者根据下属的意志实施,因此也为下属所首肯,我把这种力量称为威严或者权威。比如有3种威严:年龄的威严、强大的威严、智慧或者智力的威严,它们相互之间是不同的。[8]53
从上文所列举的一系列的共同体成员,且不说董其昌、陈继儒、顾正谊等文人士大夫所具有的一种优越的力量,就是那些受董其昌影响而游离于这个共同体边缘的士大夫人群,也具有年龄或者辈分的威严,以及智慧或者智力的威严。他们甚至会影响整个社会文人士大夫的对绘画艺术风尚的喜好,这无形中扩大了文人画规范下的共同体的壮大发展。也正因为以董其昌为首的绘画共同体集聚了三种力量于一身,所以当他振臂一呼,才逐渐地在其文人画理论的基础之上确立了文人画规范。旧的由“六法”和“六要”所确立的古典绘画规范霎时失去向心力,许多画家纷纷改宗,皈依到共享文人画规范的共同体中。
绘画共同体不排除地域共同体,如松江画派,娄东画派等,但更多的是因志同道合的友谊,大家相互结合在一起。当然这种志同道合的友谊还必须通过简便而频繁的交流来联结与维系时,绘画规范就像教徒心中的神一样,永恒地根植于共同体所有成员的灵魂之中,并在神的启发下,秉承神的意志进行绘画创作与交流。正如滕尼斯所说:
精神的友谊是一种看不见的地方,一座神秘的城市和一种神秘的大会,它仿佛由于一种艺术家的直觉,由于一种创造的意志而活灵活现。[8]55
可见,艺术家因直觉而结合在一起的精神友谊,都归于一种创造的意志。精神的友谊和艺术家的创造意志具有相同的内涵。志同道合的共同体成员之间的关系也许受本能、习惯的制约,但是它们更受艺术规范所统摄,具有心灵的性质,似乎是建立在自由选择的基础之上,从而表现出它复杂的社会性。所以,在文人画规范统摄下的文人画共同体再也不仅仅局限于松江画派中的那些群体人员,而是整个社会中的共享文人画规范的画家。说到这里,就再也不用去争执董其昌一会儿靠近东林党人,一会儿亲近阉党人的是是非非,其实这里面的许多人,如潘云翼、朱延禧、冯从吾、阮大铖、陈子龙等人,他们与董其昌拥有一种宗教式的艺术精神的友谊和艺术创造的意志。只不过他们这些人并不像陈继儒那样与董其昌之间达到一种至为纯洁的友谊罢了。由于受艺术规范的统摄,他们只是由董其昌所主导的文人画共同体的成员而已,而不是什么东林党,也不是什么阉党。当然,也不是说所有与董交往的人之间都具有这种品质,董其昌是文人画共同体的旗手,他们有些人也可能是看热闹的。
话到此处,也许有人还是会质疑董其昌文人画规范的确立涉嫌文人话语权的作用,即在不同规范之间做出选择时,文人话语权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果作为规范辩论的裁判员仅仅是社会政治人物而非共同体内的核心成员,那么这场辩论赛的结果即使是创新,也绝非名副其实的创新。真正的绘画创新,对于规范的选择将有赖于一群特殊的绘画共同体成员,他们在绘画的发展过程中,有如下三个品质:其一,他们关注解决规范中的各种复杂问题;其二,他们共享整个规范,但是研究的却是规范内的细节问题;第三,他们解决问题的标准、方式、手段及答案必须为共同体内核心成员所认可。而这三个品质董其昌等共同体核心成员都完全具备。所以在讨论这个问题时不必求全责备,更不能因为董其昌在这个共同体中借助于文人话语权推波助澜的行为,而否定这个共同体的存在,及其所共享的绘画规范在绘画史上的价值与意义。
二、确立文人绘画规范新秩序
那么,文人画共同体成员平时交流的艺术主张具体是一些什么内容,共享着一个什么样的绘画规范,以及如何确立一个新的绘画规范呢?
谁是“南北宗论”的提出者,一直以来没有定论。对此我们先简地单梳理一下。赵孟頫在提倡“复古”主张的时候,弘崇文人画格,并将其与院体画相对立,提出了自己的美学观点和理论见解,认为绘画除了有“古意”还要表现“士气”。后来何良俊在《四友斋画论》中认为画有雅俗之分,提出了“利家”“行家”的观念,基本上与赵孟頫所说的文人画与院体画相吻合,而“南北宗论”与上述观点何其相似,应该说是一脉相承。当然这里涉及以禅喻画的思维方式。年轻的董其昌就学于莫如忠时,曾得莫的指导研习禅学。他说:
仆于举子业本无深解,徒以曩时读书于莫中江先生家塾,先生数举《毘陵绪言》指示同学,颇有省入。少年盛气,不耐专习。荏苒十五年,业亦屡变。至岁丙戌,读《曹洞语录》偏正宾主互换伤触之旨,遂稍悟文章宗趣,因以师门议论与先辈手笔印之,无不合者。[9]192
可见,莫如忠是他的禅学启蒙老师。在莫如忠的启发下,董其昌“独好参曹洞禅,批阅《永明宗镜录》一百卷,大有奇悟”。1587年,莫如忠的儿子、董其昌的同窗莫是龙去世了,年仅五十岁。比董其昌年长十七岁的莫是龙就是其中“师门议论”者之一。所以这个悬案是大有争议的。不过“南北宗论”冠名权的纷争并不影响本文研究的继续,而且可以证明董其昌和莫是龙是这个绘画共同体中的核心人物。“南北宗论”是直接导致董其昌文人画理论的底本。
除了课堂上的交流以外,平时的雅集更是探讨文人画理论的好机会。万历五年(1577年),丁云鹏游学松江,用白描笔法作《罗汉图》,董其昌观后甚为叹服。
此罗汉娄水王弇山先生所藏,乃吾友丁南羽游云间时笔。当为丙子、丁丑年,如生力驹、顺风鸿,非复晚岁枯木禅也。诗文书画,少而工、老而淡。淡胜工,不工亦何能淡!东坡云:‘笔势峥嵘,文采绚烂,渐老渐熟,乃造平淡。实非平淡,绚烂之极也。’观此卷者,当以意求之。[10]706
据此可知,二十三岁的董其昌对于“淡”的理解已很深刻。虽然这个“淡”的观念来自苏轼,但当它应用到绘画中时,他提出自己的见解:“诗文书画,少而工、老而淡。淡胜工,不工亦何能淡”。此处董其昌将“工”与“淡”相对提出为孕育其文人画理论做好了充分的准备。由此可见,文人画理论的“雏形”都是来自于他日常生活中的艺术交流。丁云鹏白描《罗汉图》是在丙子、丁丑年间来游松江时在董其昌斋中所作,后来又在游松江时为顾正谊作了《五相观音图卷》。说明丁云鹏来松江游学时受到了松江画派成员的热情接待尤其是松江画派的老前辈顾正谊都将他请到了自己的正心所馆中做客,而这两次似乎董其昌都在场。董其昌在丁云鹏画上的题跋自然是他们雅集中艺术交流的主要内容。
后来董其昌还提出了“寄乐于画”的观点,他说:
画之道,所谓以宇宙在乎手者。眼前无非生机,故其人往往多寿。至如刻画细谨,为造物役者,乃能损寿,盖无生机也。黄子久、沈石田、文徵仲皆大耋,仇英短命,赵吴兴止六十余。仇与赵虽品格不同,皆习者之流。非以画为寄、以画为乐者也。寄乐于画,自黄公望始,开此门庭耳。[10]676
不错,这个“寄乐于画”观点也是来自苏东坡:
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11]
他对绘画的审美娱乐功能表达了自己的主张,反对绘画为皇家服务的教化功能。不过董其昌将绘画的风格学与画家的寿命混为一谈就有失偏颇,更何况赵孟頫活了六十九岁,而不像他所说的“赵吴兴止六十余”。虽然董其昌一心想颠覆赵孟頫在元代绘画史上的地位,但是他又无法回避赵孟頫在文人画发展中的意义。赵孟頫“以书入画”的主张最后直接成为董其昌文人画理论的核心。
士人作画,当以草隶奇字之法为之。树如屈铁,山如画沙。绝去甜俗蹊径,乃为士气。不尔,纵俨然及格,已落画师魔界,不复可救药矣。若能解脱绳束,便是透网鳞也。[10]674
董其昌倡导书法介入绘画,用书法的标准作为绘画的标准,使绘画中的线条像书法线条一样具有“锥画沙”“折股钗”“印印泥”的美感,以“绝去甜俗蹊径,脱去画工习气”。只不过这个概念的界定比赵孟頫、钱舜举的更加准确些,至少是从中国画的本体对其进行定义。为此笔者在拙著《规范与创新:探究另一种中国画史观的存在》中说:
董其昌以“淡”为宗,“寄乐于画”的文人画理论是寓建设于破坏之中。其“淡”来自书法性的笔墨,“寄画于乐”也是通过书法性的笔墨表现出来,所以他所确立的文人画规范就是以笔墨为中心,形象服务于笔墨,意境出于笔墨。从本体论而言,董其昌文人画规范以笔墨为中心,形象在绘画中失去了中心地位;从方法论而言,它提倡“以书入画”,将书法作为绘画的基础,全面介入绘画;从价值论而言,它以“淡”为宗,追求绘画的“自娱”和“寄乐于画”的审美功能。[12]
可见,文人画规范是对古典绘画规范的一个创新。在这两个规范中,形象、笔墨与意境的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古典绘画规范是以形象为中心,笔墨服务于形象,意境出于形象;而文人画规范是以笔墨为中心,形象服务于笔墨,意境出于笔墨。这种绘画规范的演进就是一次绘画革命性的创新,它为中国画构建了一个新秩序。
众所周知,确立一个新的绘画规范,建立一个新的绘画秩序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其中少不了为了这个规范建立而出现的“教材性”的学习典范或参考资料,以此推广这个理论,吸引更多的画家加入这个共同体。万历十九年(1591年),董其昌在《龙宿郊民图》中跋云:“辛卯请告还里,乃大搜吾乡四家泼墨之作”[13]27,到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董其昌终于从他的许多藏品中选择了一些作品,编辑了《唐宋元宝绘(计二十册)》。他跋册首云:
宋以前大家都不作小幅,小幅自南宋以后始盛。又僧巨然笔绝少丈余画卷,长卷亦惟院体诸人有之。此册皆北宋名迹,及吴兴赵文敏之笔。余于马夏、李唐,性所不好,故不入选佛场也。[14]
这个画册中第一幅是《王维雪溪图》,第三幅是《子昂自题西洞庭图》与《子昂自题东洞庭图》合版,第四幅是《米芾云山》,第七幅是《倪云林六君子图》,第八幅是《王蒙秋林书屋图》,第九幅是《曹知白吴淞山色》,第十九幅是《高彦敬山水》,第二十幅是《梅道人画》。“余于马夏、李唐,性所不好,故不入选佛场也”,可见这本画册的编辑充分反映了董其昌文人画理论的审美取向和艺术理想。是年春天他还将此册带去请汪砢玉、项又新和孔璋一起观赏,汪砢玉对此事如此描述:
此册在万历丁巳春仲,董太史玄宰携至吾地,余同项又新、孔彰过其舟中得阅。翌日太史挈雷仁甫、沈商丞至余家,更携黄子久画二十册与先子观,越宿始返之也。”[15]
董其昌经常到嘉兴和鉴藏好友一起观画,像这样携带其所编辑的画册出游是传播其绘画理论的最佳途径。
万历四十年(1612年),董其昌绘《仿宋元诸家山水册》,分别为仿董源、方从义、范宽、郭熙、马和之、吴镇、王蒙诸人笔意。他在第十帧款云:“壬子夏日避暑山庄,午睡初足,随手检阅宋元山水墨迹,略取其意,为此十帧。”[13]122虽说是随手检阅但是这十个人却都是文人画理论体系内的核心成员。不言而喻,通过董其昌“仿”“拟”之后的作品自然就是其文人画规范的典范,即遵循以笔墨为中心,形象服务于笔墨,意境出于笔墨的文人画规范而创作出的绘画典范。
此外,还有一本《明董其昌仿宋元人缩本画及跋册》(亦称《小中现大册》),此册由整整二十二幅山水画的缩图和董其昌所撰的题跋构成。据古原宏伸研究,此册是董其昌在73岁时请画家一次性绘制而成,然后将以往所作的札记作为题跋重新写在即时完成的摹本上而制成的。[16]董其昌在此册第一幅中款云:“谛玩之,其古雅简淡,有摩诘之韵,兼巨然之势,定是营丘也……”[13]55且不说此处董其昌对南宗山水一脉的表述,单说这本册子本身就是一本关于文人画规范的教材,是文人画中的典范。它的编辑与题跋都透露出了董其昌的艺术主张。
如果将《明董其昌仿宋元人缩本画及跋册》中的《临范宽〈溪山行旅图〉》与范宽《溪山行旅图》进行对照就会发现,范宽所创造出的严谨朴素的山水样式被董其昌程式化了,并不惜失去形象的真实性而简省其山水的细节、变化以及所有特殊景点的样式。为的是配合画家独特的笔墨语言情感,他将范宽笔下多元地质地貌简化成为性质较为统一,且视觉差异较小的物质。在强大的笔墨感情的驱使下,形象成为笔墨的附庸,也就是说,绘画以笔墨为中心,形象服务于笔墨,古典绘画规范被文人画规范所颠覆。
毋庸置疑,董其昌的品鉴与编辑的画册,以及他所主导下编撰的《明董其昌仿宋元人缩本画及跋册》对晚明文人画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也为其建立新的绘画秩序确立了典范,并进行了一个非常好的推广与完善。当然,这里面如李日华、项圣谟等人虽然推崇他,但并不一定照单全收,也包括吴门画派和浙派的余续。一个规范的创新不是一蹴而就的,一个共同体成员的改宗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观念的改变都需要一个过程。
三、大共同体本位下的文人画共同体
如果我们在研究的时候放弃道德绑架,客观地看待董其昌,只将他看做是晚明的一个普通官员,他的某些行为在当时的环境下都是可以理解的;如果我们淡化他的艺术作品的高华,他将作品送给达官贵人,包括阉党之类,从而斡旋于两党之间,即使是为了免于党祸,也是可以理解的。或许他周旋于两党之间是为了实现其政治理想也是有可能的,只是这种努力最后没有实现而已。遗憾的是,我们在研究董其昌的时候要么将他神圣化,要么将他妖魔化,这都是不客观的态度。董其昌在政治上确实没有什么建树,虽然他官至南京礼部尚书,正二品,但那只是一个职务而已。其实他是一个有政治理想的人,只是一直没有得到实现理想的机会。
天启元年,董其昌从江南返京,任太常寺少卿,掌管国子司业,开始他最后的政治生活,这时的他已经六十八岁。仰仗叶向高的提携与信任,他干得有声有色,两年间擢升为太常寺卿兼侍读学士。这一时期,他写了许多奏议,如《救荒弭盗议》:
凡天下所以患荒者,积蓄少也;积蓄少者,地有遗利,民有遗力也。凡天下所以患盗者,武备衰也;武备衰者,国多冗军,兵多冗食也。今有一举而可备荒,又可以弭盗,而又惟民饥盗起之时,可因其势而用之,则何策乎?曰:“抚流民而已。”夫流民固民也,进可以战,退可以耕,饥灾所驱,惟食是仰。当是时,使奸雄用之,则倡乱之构也;使国家拊之,则富强之资也,故处之得其术而已矣。[9]338-339
董其昌看清了当时的流民问题,主张妥善地安抚流民。流民也是民,进可以战,退可以耕。如被人利用就是祸乱,所以要妥善的处理。众所周知,后来的农民起义之所以波澜壮阔就是流民一哄而上的结果。
董其昌主张开采富藏以充军实。在当时一片反矿税声中,这是一个大胆的主张。他就直截了当地说辽东有不少产矿的地方,一旦落入敌手就等于是给了敌人的资源,所以他主张不用白不用。在论及边界市的问题,他极力推崇高拱、张居正的做法,赞扬他们敢于承担责任,实行六十多年来的互市给边境百姓带来了安宁,给国家增加了财政收入,京师得以安稳。
在其《神庙留中奏疏汇编》中,他系统地谈到了一系列的问题:其一,国用向题。这是晚明最突出的问题。明万历后期军费、宗藩、宫廷费用大增,财政危机严重。他主张广开源,重节流。其二,建都北京,赋仰东南。这个问题带来了漕运、白粮、布解、屯田、治河等一系列问题。他和许多有识之士大声疾呼恢复屯田,开垦西北。其三,宗藩问题也是晚明的一个严重问题。他是认为宗藩可以不拘一格选拔人才,主张于科举之外辅之以乡举里选,扩大录用人才的路子。其四,边防问题。他认为边防是一个整体,要相互依赖,相互支援,同时避免用不得其人、防不得其法;他主张以守为主,集中兵力,缩短战线,同时注重情报收集,屯田实军。
史学家邓之诚对《神庙留中奏疏汇编》中董其昌的按语评价如是说:
其笔断仿史赞之例,称臣以资献替,称职以辨是非,无先所见则阙之。当党争最激烈之时而能为持平之论,以明正义。兵事最详,吏户次之,要其所录皆有关系之作,慎所持择,又后之侈言档案者所当取法也。[17]
当然这是作为一个史学家对董其昌的高度评价,由此可见,董其昌高瞻远瞩的政治理念。
以上所论其实只是一个简单的概述,无非是想给董其昌一个立体的描述。对于董其昌这一精妙之论请参阅王守稼、缪振鹏的《画坛巨匠、云间劣绅》一文。
在此,还有一点不能忽略。晚明的董其昌对君权的高度集中问题有其独特的看法。他在《爱惜人才为社稷计(丁酉江西程)》中说:
古之说曰:“立天子以为天下也,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君以为国也,非立国以为君也。”官天下者,无论亦以周之十世也,而周公营洛曰:“使有德者易以兴焉,无德者易以亡焉。”深乎!深乎!藏天下于天下而不私者乎?迨德下衰,而天子者始掩天下而为一人之私利、一家之私业、一姓之私传,惟社稷之知而已矣。[9] 317-318
董其昌在晚明这个危急存亡之秋,大力提倡孟子“君轻民重”的思想并不简单。在封建专制体制之内倡导:“立天子以为天下也,非立天下以为天子也;立君以为国也,非立国以为君也”的思想,简直就是对衰落的明王朝致命的一击。实质上,这是民主主义思潮。也许晚明时期的董其昌受到了西方政治制度的影响。当然,利玛窦是传播民主种子的主要人员之一,董其昌应该与他有所接触。在晚明复杂又腐朽的政治环境中,董其昌可以称得上是民主思想的先行者。他想建立一个新的政治秩序,只是老天不借三分力。
据学者赵世瑜研究,晚明以来经济的发展,社会流动的频繁,实学之风的兴起,使得传统儒家士大夫将其未能实现的远大理想落实在稳定本社区的努力之中。在这种乡绅的凝聚主持之下,特别是在社会动荡的形势下,无论在乡里、村落还是家族,这样的“小共同体”具有相当的自我维系和调节能力。[19]如董其昌的同乡好友陈继儒,虽然身为隐士,但对于朝廷里的政事也颇为关心,对江南地方事务也持有议论,为松江之名流。当时松江士大夫就经常向其请教,咨询天下之大事。华亭钱龙赐被征召任阁臣时,临行前就曾问政于陈继儒。[20]不仅如此,陈继儒还“性喜奖掖士类,屦常满户外,片言酬应,莫不当意去”[21]。程子龙编纂的原刻本《皇明经世文编》的封面上就印有“方禹修陈眉公两先生鉴定”,也就是说博学多才的陈继儒为编辑此书鼎力襄助,表明了地方缙绅浓烈的“经世”意识。可见,晚明的地方缙绅虽然不愿意踏入仕途,但仍然心系国家之安危,持经世之思想。而我们在此关注的更多是董其昌、陈继儒等人所经营的绘画艺术“小共同体”,并将其扩大到整个社会。毋庸置疑,董其昌的这个文人画共同体是大共同体本位下的小共同体,这个文人画共同体继承与发展着松江地区的绘画及其地方意识,它成为晚明壮志难酬的士大夫文人的理想归属地。
于是,在其新政治秩序无法建立的时候,他在其苦心经营下的社交圈内实现了他重建艺术新秩序的理想。这就是董其昌聪明之处,他自下而上的构建他的“小共同体”,在推广的过程中,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建立广大而强有力的艺术统一战线,积极倡导他的艺术主张,颠覆以“六法”理论、“六要”理论所确立的古典绘画规范,创建文人画规范。
结 论
董其昌为官四十五年,赋闲在家二十八年,无论是在京城,还是在江南,或是在来来往往的路上,董其昌一直没有放弃仕途上的进取之心。虽然仕途三番五次遭遇挫折,打击沉重,但是他并没有失去信心,依然抱着建立新政治秩序的理想,提出了很多有建设性的策略。但是,残酷的现实屡屡使其政治理想折翅,无可奈何之下他也和其他士大夫文人一样寄情于诗文书画,利用自己特殊的社会身份,以及这个身份所带来的人脉与财力,收购了大量南宗绘画作品,利用雅集交流、编辑画册进行文人画理论的传播。同时还“盘活”自己各种社交圈子,构建他的文人画共同体。可以毫不隐讳地说,他利用自己的官员身份用心经营着自己的艺术理想;同时又利用书画交流让自己在风雨飘摇的晚明朝廷、血雨腥风的晚明官场中悠哉悠哉,甚至可以说是游刃有余地活着,最终成就了他构筑一个新时代、新的绘画秩序的梦想。虽然这个梦想并不属于政治范畴,却与政治脱不了干系。在这个文人画共同体中,所有的成员共享着文人画规范,这里没有党争,只有怀着艺术精神的友谊和在文人画规范下从事艺术创造的意志。董其昌与他很多的同僚们一样,他们难以真正实践自己经国济世的理想,因而将其经世抱负转变为对地方文化事业的关注。也正因为有此强烈的经世意识,所以像董其昌、陈继儒、袁宏道等人皆视地方文化事业为己任,广泛参与地方文化建设。他们重新构建一个小共同体,确立一个新秩序,以实现区域文化的稳定发展,充分发挥小共同体内的自我维系和调节的能力。董其昌的文人画共同体,袁宏道的“公安派”文学共同体等都是这个时期特定的产物。
[1][明]屠隆.画笺[G]//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三).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995.
[2][明]唐志契.绘事微言[G]//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四).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62.
[3][清]王原祁.雨窗漫笔[G]//卢辅圣主编.中国书画全书(八)[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3:710.
[4]夏允彝.岳起堂稿序[G]//陈忠裕公全集.嘉庆八年·山草堂刻本.
[5]孔广陶著.岳雪楼书画录:卷四,刻四卷本,1861:125-127.
[6]任道斌编著.董其昌系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270.
[7]埃齐奥·曼齐尼(EzioManzini).创事:社会创新与设计[J].孙志详、辛向阳,译.创意与设计,2017(3):4.
[8][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林荣远,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3.
[9]董其昌.容台集(上)(中国古代书画家诗文集丛书)[G].邵海清,点校.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
[10]董其昌.容台集(下)(中国古代书画家诗文集丛书)[G].邵海清,点校.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2.
[11][宋]苏轼.苏东坡全集[G].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4326.
[12]曹院生.规范与创新:探究另一种中国画史观的存在[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179.
[13]任道斌编著.董其昌系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27.
[14]书画汇考:卷三三.画三·历代画册[M].钦定四库全书本.
[15]汪珂玉.珊瑚:卷四三. [G]//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一八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809.
[16](日)古原宏伸.有关董其昌〈小中现大册〉两三个问题[G]//《朵云》编辑部.董其昌研究文集.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1998:595.
[17]王永昌主编.董其昌史料[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147.
[19]赵世瑜.社会动荡与地方士绅——以明末清初的山西阳城陈氏为例[J].清史研究[M].1999(2).
[20]叶梦珠.阅世篇:卷十.纪闻[M].
[21]明史:卷二九八 陈继儒传[M].
J203
A
1008-9675(2017)06-0049-06
2017-08-05
曹院生(1969-),男,江西鄱阳人,华东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美术史论。
(责任编辑:梁 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