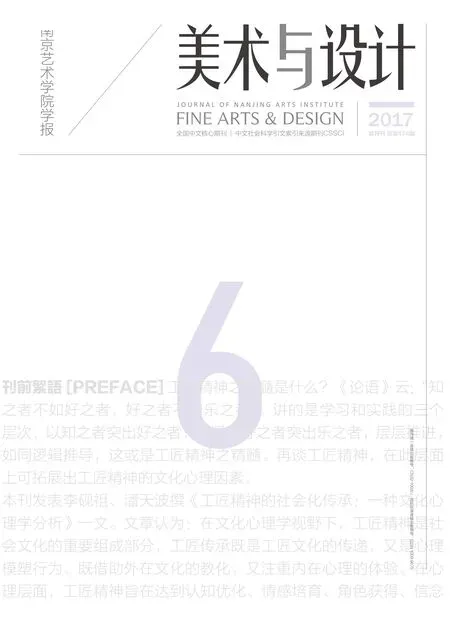工匠精神的社会化传承:一种文化心理学分析
2017-02-17李砚祖潘天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北京100084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江苏徐州221009
李砚祖 潘天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 北京 100084;江苏师范大学 传媒与影视学院,江苏 徐州221009)
工匠精神的社会化传承:一种文化心理学分析
李砚祖 潘天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中国 北京 100084;江苏师范大学 传媒与影视学院,江苏 徐州221009)
在文化心理学视野下,作为心理特质的工匠精神是社会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工匠精神传承既是对工匠文化的传递,又是持续社会化心理模塑行为。在此模塑过程中,我们既要借助外在文化的教化,又要注重内在心理的内化与体验。在心理机能层面,工匠精神社会化旨在达到认知优化、情感培育、角色获得、信念养成、价值认同等心理品格的整合与同化;在意识形态层面,工匠精神社会化主要依赖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社会传播、文化接受及批评等途径,以期完善自我人格结构及其价值观。工匠精神社会化传承不仅创生了有益的正向社会化的工匠文化,也产生了一种反向社会化的工匠文化。
工匠精神;社会化;传承路径;文化;心理
目前,由于国家议程的积极推动以及民众的持续关注,“工匠精神”作为一个曾经相对沉寂的文化范畴俨然呈现繁荣之势,并日趋成为学界较为活跃的研究对象。尽管人们试图从文化、艺术、制度、历史、时空等多个维度描述、阐释与反思工匠精神的诸多问题向度,愈发显示出人们对工匠精神传承与需要的呼声日渐高涨。但目前学界对此研究较少涉猎文化心理学视角下的工匠精神传承,问题的复杂性还在于工匠精神的传承既是一种工匠文化的传承,又是一种持续社会化心理活动行为。因此,在本质上,工匠精神的传承问题就是工匠文化的社会化问题,它又指向工匠精神的“外化”与“内化”这两个较为复杂的心理结构的文化塑造过程;在此过程中,又关联到工匠精神所包含的心理机能与意识形态在内的心理学内容向度。由此观之,工匠精神的传承问题有较宽的文化学研究视域及心理学阐释空间。抑或说,作为心理特质的工匠精神传承问题,文化学者有责任阐明它在心理学维度上的运行逻辑及其发生机理,以期工匠精神社会化传承的解读朝向文化心理学迈进。
一、基本概念及研究方法
在马克思主义人学视野下,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过渡是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途径,而“社会化”就是通过各种文化建构出来的一种终生持续性行为。因此,在本质上,工匠精神的社会化行为就是自然人通过社会文化构造,以期望获取工匠精神价值行为与思想规范,其目的主要来自人的社会存在、社会需要以及发展等方面的客观需求。换言之,工匠精神的社会化是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产物。在这个过程中,个体通过体验、学习与传承工匠精神,从而获取工匠的行为价值观、思想道德操守、职业行业规范、理想人格魅力等特质文化,并积极反作用于社会。
就广义文化概念而言,工匠文化包括工匠创物(物质表层)、工匠手作(行为浅层)、工匠制度(制度中层)和工匠精神(精神深层)等内容指向。其中,工匠精神是工匠文化理论的核心,它包括工匠心理与工匠意识形态两部分内容。在心理层面,工匠借助“专注”“持久”“严谨”“细腻”“精益求精”“坚守”“不急不躁”“精致”“敬业”等心理品质完成创物行为,这些工匠心理品质的聚集便构成了工匠精神文化。可见,工匠的心理活动直接产生与构造了工匠文化。在此,工匠特有的心理品质不仅能稳定自我的心理状态及其行为规范,还能提升工匠自我的价值取向与理想人格,进而进一步完善工匠自我以及他人的审美情趣和精神结构。在意识形态层面,工匠的价值观、思想、观点、观念、准则、规范、理想等聚合成工匠的意识形态聚合体,而诸多工匠的意识形态的聚合就形成一种具有现实性与独立性的工匠精神文化。简言之,精神文化是工匠行为的心理特质经验化表述;同时又是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出现,并通过社会化过程塑造出新的心理文化。工匠精神所蕴含的工匠行为、工匠心理和工匠文化三者之间的逻辑关系直接昭示出一种可能的被称之为“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出场。
文化心理学(Cultural Psychology)是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一种较为新兴与活跃的心理学分支学科,它“旨在寻求永在的镶嵌在意义和背景里的心理”[1],抑或说从文化视角理解行为的心理学意义取向,并将行为与心理在不同文化背景下的普遍性与特异性作为研究己任,尤其是关注文化对心理活动、行为表现的塑造与干预。作为研究对象的工匠精神被纳入文化心理学研究视野的合法性理由大致有三:一是“心理学是文化的一部分”[2],工匠精神是工匠的价值文化与心理特质的聚合体,它所呈现的心理与文化、主体与客体、对象与背景等均是文化心理学所关注的核心命题;二是“在社会心理理论中融入文化症候群”[3]有助于阐释社会心理与文化之间的某些关联性特征,工匠的心理活动与行为表现是通过特定文化建构起来的,进而形成一种工匠精神的价值观,工匠精神的社会化行为路径也就是通过工匠文化塑造与干预心理的选择与定位;三是“文化心理学是人类学与认知科学的一座桥梁。”[4]同时,文化心理学本身突破了传统科学心理学的文化盲区,尤其是超越传统实证研究方法日趋机械化的发展困境,并能在跨文化比较的视野下阐释心理与行为的各自异同性。据此,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拟将采用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方法透视工匠精神的社会化传承问题,力图阐明工匠精神的社会化传承路径及其核心指向,并兼及工匠精神社会化传承的文化意义,从而在文化与心理的整合视角探工匠精神社会化传承的心理学向度及其文化逻辑。
二、工匠精神的社会化传承路径:外化与内化
工匠精神是工匠文化系统中最为核心的内容。就文化传承而言,工匠精神的社会化过程就是面向人与社会的文化“控制”与心理“约束”的过程,从而寻求工匠精神的文化信仰与价值观,并进一步模塑与整合个体的价值观、行为操守、道德规范等行为方式和人格特质,以适应社会并积极作用于社会而创生新文化。简言之,工匠精神的社会化过程就是个体的心理及其行为的模塑过程。在此模塑过程中,既要借助外在文化的社会教化,又要注重内在心理的内化与体验,即工匠精神社会化传承包含“外化”与“内化”两种路径的选择与定位。
在外化(Externalization)路径层面,工匠精神社会化过程就是工匠文化的社会传播、传递与体现过程。在此过程中,工匠精神的社会化主要以家庭、社会、高校以及媒介等宏观文化环境为载体,并借助心理学展开工匠精神文化的持续传承与增长。因为在宏观层面,“心理学是激发和引导社会行为的主观过程,是文化的主观方面。所以,心理学与宏观文化因素必然是具有一致性的。”[5]这也是选择宏观的外在文化传承工匠精神的合法基础与理论支撑。
在工匠精神传承的外化路径选择上,营造工匠精神传承的社会文化环境极其重要,特别是家庭文化环境、学校文化环境以及社会文化环境的整合建构与积极培育。家庭是心理模塑的基础因素之一,是社会化互动的纽带与关节点,具有很强的限制性与实时性。[6]一般心理学研究表明,在学前期是心理发展的“非常期”,它处于社会化过程中的基础层;另外,儿童期也是早期文化心理形成以及社会化的“强化期”,它处于社会化过程中的加强期。由于个体的学前期与儿童期主要以家庭为主轴的实时性文化教育,它对于个体的社会化进程具有前期限制性作用,特别是在建构人的思想、价值以及调节个体的心理机能增长等层面具有显著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寓工匠精神于家庭文化教育以及营造具有工匠精神的家庭文化环境是工匠精神传承最为有力的基础路径。譬如培养儿童的手作行为欲望及其手作行为的步骤性、严谨性与秩序性就显得特别重要。应当着力培养儿童的感知、信念等心理机能,进而有效地调节儿童心理机能的成长与发展。这些心理机能的培养对于儿童进入“预期社会化”的青春期发展起到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与决定因素,因为儿童在家庭有了一定的精神文化体验与学习的基础,在他们步入学校环境之后,便拥有了模塑自我心理的原初动机与欲望,也期望通过个人行为感受到文化自我的存在价值。就是说,家庭文化因素是建构个体心理原发动力。另外,优化校园外在文化环境对于传承工匠精神也尤为重要,抑或说校园文化环境是着力培养“匠二代”工匠精神的有效空间场,也是协调文化与心理之间合理化发展的有效途径。当成群的接受工匠精神的“匠二代”走向社会,他们用自己的文化信仰、工匠性的价值观以及人格魅力又影响了周围人,从而在文化心理上发挥改造旧文化与创造新文化的榜样与示范。可见,“家庭——学校——社会”的工匠精神传承是一个复杂的有机整体,不可断然决裂与隔离地传承工匠精神,系统性与整体性的营造家庭、学校与社会的文化环境对于工匠精神的外化传承作用至关重要。只有通过在这个宏观场域内的社会化行为塑造以及心理机能的积极培育,并使得这些心理机能积极介入社会,进而实现工匠精神的有效社会化。
在文化心理学视野下,工匠精神的社会化传承更为具体和富于启发性的路径当数“文化产品”的开发与设计。西方学者Hammack,P.L.认为:“文化心理学的框架重点是大叙述(master narratives)与身份的个人叙事之间的关系。”[7]可见,文化心理学与工匠手作的文化产品在叙事结构框架上极其相似。在工匠创造层面,工匠手作产品就是工匠精神及其思想的外化的叙事产物。因为,“心理能引导着文化行为。”[8]同时,手作产品也是工匠个人价值观与外在社会文化语境之间契合的叙事产物。抑或说,工匠的文化产品不仅是个人叙事产品,还是借助社会大语境而创造出来的文化符号。工匠精神可视为社会文化的直接反映、体现与传达。作为工匠的文化产品既可呈现出社会文化因素对工匠精神传承的激发、支持和规定,又能揭示出社会文化因素建构工匠精神的动力原理。为此,文化产品在工匠精神社会化过程中的起到最为直接的模塑人的心理及其思想的作用,这给“文化产品”的生产提出了非常严格的社会行为规范与道德伦理要求。在这一点上,明代黄大成所著的《髹饰录》[9]有过精准的描述,他认为髹漆的行为规范与道德伦理在于“三法”“二戒”“四失”“三病”等维度,这些“规约”或“伦理”的要求是对工匠精神的最好表述与传达。具体地说,在文化产品设计层面,工匠行为要遵循“巧法造化”“质则人身”“文象阴阳”之法规;在文化产品形式装饰上,工匠得戒除“淫巧荡心”“行滥夺目”之滥饰;在行为观念上,工匠不可有“制度不中(不鬻市)”“工过不改(是为过)”“器成不省(不忠乎?)”“倦怠不力(不可雕)”之失范;在心理以及行为技巧上,工匠谨防“独巧不传”“巧趣不贯”“文采不适”之病理。黄氏对髹漆工匠行为与伦理规范的约定不仅显示“文化产品”是由工匠精神文化构造而成,还显示出文化产品符号所彰显的心理文化特质对于工匠精神的社会化传承具有潜在的推进作用。
从文化类型上看,文化包括有形的文化与无形的文化,产品是工匠文化传播的有形载体,也是工匠精神传达与增长的有效途径。文化产品是工匠文化与工匠心理相结合的特殊产物,既能反映工匠及其社会文化特征,也可反映工匠行为及其心理的偏向。因此,作为心理文化元素的工匠精神可以通过文化产品来集中体现、表达与传递。在理论上,工匠的文化产品既可以昭示文化间(Between-culture)性或文化内(Within-culture)的差异性, 又可以反映出跨文化(Cross-culture)的差异性或用来显示文化本身的特征以及反映人们的心理特点。[10]因此,文化产品不仅是工匠文化自身的行为结果的符号化产物,也是不同文化交叉相互作用而生成的结果。或者说,文化产品的设计与制造过程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社会化行为。可见,作为使用和消费的文化产品在传递与增长工匠精神,也不断地通过心理内化或社会化途径稳定成特定的文化价值观。由此观之,文化产品在工匠精神的社会化中肩负重要的使命。为此,文化产品的设计与制造在“劳动之美”“心灵之美”“艺术之美”“叙事之美”等文化心理的塑造上十分关键。抑或说,工匠创造的产品要体现自身是美的创造者、心灵的富足者、艺术的传承者和时代的叙事者。唯有如此,文化产品创造者才能为工匠精神的社会化提供文化基础与心理力量。
值得讨论的是,植入工匠精神于媒体传播,在文化媒体的教化下体验工匠精神的价值、信念与理想,也是工匠精神社会化路径的有效选择。因为,媒介的文化传播具有超强的文化构型与知识重组的能力。譬如工匠、传统文化、工匠精神等这些即将失落的社会文化词语,一旦社会媒体介入其中以“新闻化”或“叙述化”等集中出现在公众面前时,这些词语或现象立刻构形成为公共话题,并唤醒公众的普遍化知识认同以及赋予人们学习的权力,迫使该问题朝向有利于解决的方向迈进。近年来,“工匠精神”话语被国家政治议程提及后,社会媒体便急速传播相关文化,特别是新闻、报纸、客户端以及微信等媒体的广泛传播,这应当够唤醒了沉睡已久的“工匠精神”文化,并引起普通公众的高度关注以及学界的介入讨论。可以认为,传媒在知识唤醒与范式构型的能力上是巨大的,并影响历史事件及其现象的发展进程。当然,这个进程除了取决于社会对它所采取的何种传播立场及其叙事策略,还取决于传媒社会化路径的选择与定位。
在内化(Internalization)路径层面,工匠精神的社会化过程是工匠文化的自我内化过程,“同化”“顺应”“整合”等是工匠精神内化过程完成的基本心理机制。个体认知结构在接纳、过滤与整合外部工匠文化刺激而形成新的认知结构的同化过程,认知结构自身也在顺应中发生结构性变化。尽管大部分人的个性及其认知结构有基因进化决定了一部分,但社会化过程可以塑造它在特定的个性方向,通过行为或鼓励特定的文化信念和信仰态度,以及有选择性地提供社会化经验,对于个体的个性与认知结构的后天教化是必要的。因此,在个性与人格形成过程中,内化式的社会化途径极为重要。
工匠精神社会化传承的“内化”路径首先莫过于个体的持续性终生学习,进而达到“自我同一性”之目的。在心理学层面看,“自我同一性”水平来自于自我态度体系的完美程度。因此,工匠精神的社会化过程是要依赖个体持续化的学习过程,在学习工匠知识及其精神文化的过程中,不断地积累工匠知识与手作能力,并在心理上以价值观念的形式建构出相对稳定的认知结构及价值态度。对此,个人树立终生持续性的学习态度极为重要。因为个体的认知结构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变化的能力系统,只有在不断地学习中才能适应、支持与顺应社会的发展,从而才能解决新问题与创造新知识。只要个人在持续的工匠文化的学习过程中,就能不断地激化与发现个体的认知结构与外在工匠精神的矛盾性或差异性,从而在优势文化配置中不断优化主体的认知结构,进而形成工匠精神支配下的行为规范与道德准则。
同时,个体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在“文化适应”(Acculturation)中实现内化或同化,这也是行之有效的工匠精神社会化的传承路径。工匠精神的社会化具有很强的实践性与实时性,并具有丰富的社会延展性偏向。就工匠精神的社会化内容而言,它包括行为社会化、角色社会化、态度社会化、道德社会化、观念社会化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的社会化。因此,对于如此内容广泛的工匠精神社会化路径的选择与定位,必然要建基立广阔的社会实践领域,积极投身社会实践必然是工匠精神社会化路径的科学选择。在本质上,社会实践是社会化的终极途径,并在文化适应中实现人的社会化存在以及发展的客观需要。所谓“文化适应”,就是指“由个体组成的具有不同文化的两群体间,发生持续直接的文化接触,从而导致一方或双方原有文化模式发生变化的现象。”[11]作为工匠精神文化被社会实践的人们通过职业化行为活动,进而获得工匠精神的价值观、操守、规范等行为方式与人格特征后,个体就在这样的社会化过程中适应社会并积极作用于社会。根据Lee S K, Sobal J等在韩裔美国人的比较研究中提出了文化适应的整合(Integration)与同化(Assimilation)理论[12],社会文化就是一个职业化分工很细的实践活动现象,个体通过社会实践整合或同化适应文化发展的先进部分;相反则分离或边缘一些不适应文化发展的糟粕部分。进一步地说,在整合层面,社会实践个体既注重自我文化品格的“保护”与“矜持”,也试图冲破自我文化“接纳”与“认同”那些与自我文化相适用的新文化。在同化层面,当社会实践个体不愿意保持或意欲改变已有旧文化的时候,传统文化在新文化的改造与演进中就实现了一次进步与发展。因此,就工匠精神的社会化而言,它就是一次文化的整合或同化过程。或者说,它就是依赖职业实践介入工匠精神的文化适应,在内化自我人格思想以及价值观中实现工匠精神的社会化,尤其是在社会实践与行为规范中潜移默化地实现心理以及人格迈进理想化的文化适应区。
学会手作体验,以期富足心灵与“人格涵化”,也是必要的工匠精神社会化路径的内化选择。在本质上,工匠精神是一种手作精神,也是一种人文情怀。因此,工匠精神的内化过程必然建立于个体的手作基础之上,以期在亲在的行为活动中持有精神文化体验,并在渐进的行为模塑过程中寻求生活的意义,在“物我两忘”中达到身心合一,在一丝不苟的行为中追求产品的完美,进而富足与涵化自我人格。从文化视角看,手作文化在富足心灵上具有很强的优势特征:(1)手是心的最听话的“仆人”,心也是手最公正的“裁判”。手艺人的手与心是合一的,并在一丝不苟、不怕寂寞中实现人手的对话;(2)工匠的手作心理是在手作过程中建构“严谨”“细心”“严格”“持久”“慢作”“重复”“精致”等特质文化,工匠精神的内化只有依赖手作才能完美的进行;(3)工匠借助手的感知、动作、角色等指向调节心理功能以及心理表达,从而实现工匠的行为价值与理想目标。上述种种手作文化的心理优势特征为工匠精神的内化提供理论依据。
总而言之,工匠精神传承主要依赖“外化”与“内化”两种路径,实施工匠文化的社会化发展与演进,“外化”路径赋予了工匠精神社会化传承的文化外力,“内化”路径给予了工匠精神社会化传承的心理内力。
三、工匠精神社会化传承核心:心理机能与意识形态
从心理学层面看,工匠精神是存在内心的一种不可见的暗能量。由于工匠精神的社会化最终是指向个体行为规范的模塑,因此,“行为规范”是工匠精神社会化的核心指向,而行为规范又来自于个体的心理机能与意识形态的暗能量。因此,工匠精神社会化路径必然依赖心理机能与意识形态的核心内容建设。
在心理机能层面,工匠精神的社会化就是通过认知优化、情感培育、角色获得、信念养成、价值认同等实现高级心理品格的整体完形。在文化心理学层面,“心理发展是一个开放的,文化介导的过程(culturally mediated process)。”[13]因此,工匠精神文化的社会化传承对个体的心理发展起到“介导性”作用。
第一,认知优化。文化对认知以及思维方式的影响是心理学界的普遍共识,而作为文化形态的工匠精神对认知方式的干预、配置与优化同样存在。因此,从认知层面看,工匠精神的社会化构成是以认知优化为起点的。无论是社会环境文化营造对工匠精神社会化植入,还是通过产品美学传达工匠精神。认知优化是工匠精神获取的基础手段,也是工匠精神社会化的首要目的。
第二,情感培育。认知是产生情感的前提条件和决定因素,但仅有认知还无法持续地培育特定的情感,情感培育也是工匠精神社会化的必要途径,文化是建构与培育工匠精神及其行为的有效方法。工匠精神文化只有通过个体的行为方能体现自身存在的意义,进而在此基础上塑造特定的工匠文化心理与情感。
第三,角色获得。个体对工匠行为有了初步的认知与情感之后,便能站在工匠或他人的立场上考虑、体验与反思别人在社会化过程中的期望与态度,进而在心理上获得自身的社会角色。于是,在接受与内化工匠精神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影响他人的信仰、价值以及精神,并进一步地通过工匠精神的社会化进行角色调整或再社会化,从而产生较稳定的价值信念。
第四,信念养成。心理学研究认为,接受性信念是可以依赖控制性行为训练获得的。事实上,社会化就是一个控制与约束的行为过程。这就是说,工匠精神的信念养成是可以依赖社会化路径来实现的。根据工匠精神的文化特质分析,对其信念的养成主要在于工匠精神的生产性、公共性和社会性等三个基本维度。生产性信念指向工匠生产中所生成的“严谨”“乐观”“精益求精”等文化信念;公共性信念指向工匠产品的“大众性”“集体性”“公有性”等文化信念;社会性信念指向工匠文化是工匠与社会互相作用的结果,体现出工匠文化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这些工匠文化信念的养成不仅能提升个体的社会化价值信念,还能反哺社会并积极作用于社会文化创造。
第五,价值认同。个体通过认知优化、情感培育、角色获得、信念养成等环节的社会化规程之后,在心理观念上最终模塑成一种与他人共享、相互认可的价值,即价值认同。作为工匠精神的价值认同,主要是指向本体价值的认同。因为工匠精神在本质上是一种本体的人文价值。工匠精神社会化的核心就是对工匠精神的传递与内化,进而获得一种价值认同。因此,工匠精神的价值认同是考察工匠精神社会化路径有效性因素。
在意识形态层面,工匠精神的社会化主要依赖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社会传播、文化接受及批评等途径实现意识形态的完整建设。
第一,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工匠精神所蕴含的“价值观”“信仰”“理念”“思想”等意识形态是工匠精神社会化的重要内容,对其采取科学的理论化的总结与归纳是十分必要的。因为,工匠精神社会化的有效性关键在于这些意识形态的科学化与理论化。抑或说,这些工匠精神的意识形态是否适应社会实践,是否是与时俱进的意识形态,是否是科学地反映现实及其需要,是否具有普适性或符合时代的精神期待,这些都是工匠精神意识形态理论建构的内容,也是工匠精神社会化所要关注的理论形态要素。
第二,意识形态的社会传播。工匠精神的意识形态文化传播是工匠精神社会化的一种有效终端,即借助新闻、报纸、网络、客户端等媒介广泛传播工匠文化,宣扬工匠精神。因为,媒介传播具有文化构形与文化教育的实际功能,尤其是在可视化的新媒体传播中,工匠的意识形态传播更具有“植入”与“灌注”的效果。
第三,意识形态文化的接受与批评。任何文化的传播并非完全的正向接受与采纳,工匠精神文化的社会化同样也有接受与批判的问题向度。公众对文化的接受是有选择性的,也存在批判与自己价值观不一致的价值文化。因此,工匠精神的意识形态的理论建构与文化传播要注意与时俱进,特别是要贴近生活现实,更要注意理论的可视化以及适当的文本视觉转换,以求达到在可接受性中传播工匠精神。
四、余论:工匠精神社会化传承的文化意义
通过上述的分析发现,工匠精神的社会化传承是一种复杂的文化心理学现象,它关涉到外在社会文化的“外化”建设与“内化”营构,并在同化与整合中实现工匠精神的社会化传承;同时,也关涉到内在心理机能与意识形态的积极培育与建构,以期在内化与顺应中实现工匠精神的社会化传承。但就终极意义而言,工匠精神社会化传承的最终目标乃是培育、获得与创生新文化,这些新文化大致包括工匠精神的社会化文化与反向社会化文化。
在社会化层面,工匠精神的社会化传承不仅使得工匠文化得以延续与传播,还使得公众在学习与传承工匠文化的过程体验到了工匠精神,并在外化与内化的社会化传承路径中模塑自己的心理机能与意识形态,尤其是在角色获得、态度形成、道德规范、人格发展等方面,从而使个体获得丰富的工匠文化及其创造的动力,进而为创生新文化提供优秀的价值观、行为规范以及人格修养。
在反向社会化层面,工匠精神文化的获得又能借助同化与隔离等路径实现文化反哺,即公众在工匠精神社会化过程中汲取到的工匠精神文化营养之后,通过同化、顺化与整合等心理优化程序养成了优势工匠文化精神,再适应社会文化发展,并积极反哺社会文化创造。特别是在新媒体时代,伴随社会文化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反向社会化是文化传承模式“倒置”的一种特有现象,也是缓解社会文化的代际危机的有效手段与策略。
简言之,成功的工匠精神社会化传承不仅创生了有益于社会发展的社会化文化,也产生了有益于社会发展的反向社会化文化,它们在顺化与倒置中共同得益于社会朝向可持续化的健康发展之路迈进。
[1]R.A.Shweder.Cultural Psychology:What is it?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13.
[2]Ratner C. Cultural Psychology (General)[M]. Springer US, 2012.
[3]Harry C.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J].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2013, 2(1):127.
[4]Fryberg S A. Cultural Psychology as a Bridge between Anthropology and Cognitive Science [J]. Topics in Cognitive Science, 2012, 4(3):437.
[5](美)卡尔·拉特纳著,王波、丁紫瑄译.基于宏观文化心理学视角的心理能力研究[J].学术月刊,2014,12:51.
[6]Lee G R. Family, Socialization and Interaction Process[J]. Journal of Marriage & Family, 2000, 62(1).
[7]Hammack, P.L. Narrative and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identity.[J].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 Review,2008, 译,学术月刊,2014,12:51.
[8]Ratner C. Cultural psychology,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indigenous psychology. [J]. 2008:1.
[9]王世襄.髹饰录解说[M].北京:三联书店,2013:28-29.
[10]参见丰怡 等.文化产品研究——文化心理学的独特视角[J].心理科学进展,2013(2):329
[11]Salant T, Lauderdale D S. Measuring culture: a critical review of acculturation and health in Asian immigrant populations [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03,57(1):71-90.
[12]Lee S K, Sobal J, Frongillo E A. Comparison of Models of Acculturation the Case of Korean Americans[J]. Journal of Cross-Cultural Psychology, 2005,7(34):282-296.
[13]Miller J G. Cultural Psychology: Implications for Basic Psychological Theory [J]. Psychological Science, 1999,10(2):85.
J0-03
A
1008-9675(2017)06-0001-05
2017-09-06
李砚祖(1954-),男,江苏泰兴人,江苏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美术学教授,博士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设计历史与理论等。
潘天波(1969-),男,安徽无为人,江苏师范大学传媒与影视学院副教授,研究生导师,研究方向:工艺文化史。
( 责任编辑:夏燕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