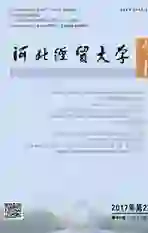领袖与学者在公平与效率理论演变中的互动性
2017-02-15苑秀丽
苑秀丽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认识经历过一系列复杂的认识演变过程,这一过程表现出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发展是领袖与学者共同推动的结果。在公平与效率的理论演变过程中,一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极大地发挥了正确领会中央精神、推动理论发展的作用。领袖和马克思主义学者之间是一种互动和互补的交互关系,他们共同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不断发展。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整体性;公平与效率;领袖与学者;互动性
中图分类号:F014.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2101(2017)02-0058-05
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创造性地提出、探索和完成了许多时代的新课题,它饱含着我们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广大学者们的思想结晶。其中,关于公平与效率的研究和认识的不断深化,鲜明地体现了领袖和学者在重大理论问题上互动、互补的交互关系。党中央对公平与效率的认识随着经济和社会发展而不断调整。我国一大批老中青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深入思考也推进了公平与效率问题的理论研究和政策探索。领袖和学者关于这一问题的认识随着改革进程的不断深入而更加科学丰满。
一、1978年至党的十四大:效率的前提性,公平的兼顾性
(一)对公平和效率有机结合的关注
改革开放使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迅速活跃起来,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率快速变革。此时,已经有学者开始关注到公平与效率有机结合的重要问题。1984年1月,杨圣明研究员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一书中就提出,中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更重视平等而轻视效率了,应当在不忽视平等的基础上,重视效率,扩大收入差距。同时,他认为,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强调效率,不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目的。中国的发展应当是从目前的比较平等,经历扩大差距、提高效率的阶段,达到真正的平等。“这种论断,根本不同于20世纪50年代库兹涅茨提出的所谓‘倒U字形假说。……与资本主义各国的情况不同,我国已经实现了生产资料社会主义公有制,通过对居民收入的有计划有步骤地调节,能够把效率和平等有机地结合起来,防止社会的两极分化,使我国最终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效率。”①可以看到,杨教授是较早提出要同时重视公平与效率、正确处理二者关系的经济学家。
(二)邓小平的“先富与共富”论提出
1984年10月,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要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和一部分人依靠勤奋劳动先富起来,并带动越来越多的人走向富裕。“先富与共富”、避免两极分化的提出影响很大。党的十三大报告提出,分配政策既要有利于善于经营的企业和诚实劳动的个人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又要防止贫富悬殊,坚持共同富裕的方向,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卫兴华教授认为,关于公平与效率的提法不存在孰重孰轻。提高效率的根本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的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要遵循分配公平原则。效率的提高要体现社会公平,防止贫富分化。分配公平有利于效率的提高。党的十三大关于公平与效率关系的提法,直接针对平均主义的弊端,平均主义既无公平也无效率。②
(三)效率的前提性从分配领域向经济社会领域放大
1992年党的十四大确立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并提出在分配制度上,兼顾效率与公平。对此,卫兴华教授认为,这与十三大报告相比,并无质的差别。合理拉开收入差距是效率与公平的连接点,我们党坚持既要促进效率,又要防止两极分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③我们党很长一段时期内在收入分配领域一直强调效率的前提性及公平的兼顾性。
然而,理论界的认识却是杂乱纷呈的。有学者提出“要用机会均等来代替传统的那种平等观”,应当“改变以往公平优先于效率的目标序列,把效率目标放在首位”,“效率目标与市场动力机制是为主,公平目标与社会稳定机制是为宾,无论如何不可喧宾夺主。这是由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决定的正确选择。”④这种观点得到一些人的赞同,这实际上导致了党中央关于“在促进效率提高的前提下体现社会公平”这个关于分配领域的指导被放大到了广泛的经济社会领域,导致将效率置于绝对优先的位置,片面地将效率视为社会发展的目的,导致现实社会公平状况令人堪忧。
(四)对“先富与共富”的混乱认识
收入的巨大变动及合理性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公众和经济学界的关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程恩富教授坚决反对在关于个人劳动收入的增减、关于个人福利收入的增减、关于价格和企业税后利润的变动对个人收入的影响的错误认识,提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使全体劳动者(至少是占百分之九十几的绝大多数劳动者)的生活水平都有程度不同的提高,这是社会主义生产目的所决定的,是共同富裕的目标,也是改革的初衷和归宿。⑤但是,一些人对党中央关于“先富”“后富”“共同富裕”“两极分化”的本意的理解越来越混乱。对效率的重视被一些人视为经济效益至上,社会现实表明,忽视公平导致在初次分配领域、再分配领域都引起了社会利益的矛盾与冲突。
二、党的十四大至党的十六大: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一)“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分配原则的形成
随着改革的推进,党中央着力实现效率与公平的结合。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提出个人收入分配要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一个重大的改变。卫兴华教授认为,在这里,“兼顾”的内涵已经明显不同。党的十四大所讲的“兼顾”是将效率与公平放在同等的地位,而这个新提法意味着分配公平在效率面前处于次要地位。⑥此后直到十六届三中全会,“效率优先、兼顧公平”的提法并没有改变。
(二)围绕“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争论
这一原则提出后,一方面得到了比较广泛的响应和有力的贯彻;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如何认识效率和公平的适用范围以及到底哪个优先。一些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坚决批驳了错误认识,提出应当正确领会党中央的思想。这一原则本来适用于分配领域,但却被一些人扩大了范围,与一些政策取向结合在一起,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在一些人那里,将效率作为发展的最终目的,颠倒了发展的目的与手段的辩证关系,“效率优先”被过度强化,社会各个领域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针对一些人认为公平同效率间的关系是一种此消彼长的交替关系,“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程恩富教授早在1996年就提出“正反同向交促互补变动论”,认为公平与效率具有正反同向的交促互补关系。他认为,“公平或平等不等于收入均等或收入平均。经济公平的内涵大大超过收入平均的概念。从经济活动的结果来界定收入分配是否公平,只是经济公平的涵义之一。结果公平至少也有财富分配和收入分配两个观察角度,财富分配的角度更为重要。况且,收入分配平均与收入分配公平属于不同层面的问题,不应混淆。包括阿瑟·奥肯和勒纳在内的国际学术界流行思潮,把经济公平和结果平等视为收入均等化或收入平均化,是明显含有严重逻辑错误的。”⑦顾钰民教授认为,市场经济体制内含着效率优先的机制。但市场经济运行本身缺乏实现公平的机制,不能解决公平分配的问题。协调好经济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关系的重点是解决好公平问题。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要求和追求的目标。⑧
从2002年起,很多学者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提法已经不能适应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应当改变。也有一些学者依然坚持这一原则。他们认为,市场经济中的问题,恰恰表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尚未得到充分贯彻。⑨学界的讨论并没有取得共识,但是,党的正式文件体现了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站在广大人民立场上建言献策的学者的观点。党的十六大报告提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刘国光先生反对一些人的曲解:“难道初次分配社会公平问题就不重要?垄断行业和非垄断行业的畸高畸低的个人收入,不是初次分配问题?有些部门、企业高管人员与普通职工的畸高畸低收入,不是初次分配问题?一些外资、内资工厂,把工人(特别是民工)工资压得那么低,而且多年不怎么涨,过量剥削剩余价值,不是初次分配的问题?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许多不合理、不合法、不规范的黑色收入和灰色收入,不是初次分配中产生的?初次分配秩序混乱,初次分配中的社会不公问题难道不需要重视、处理、解决?还要等到财税等再分配杠杆来调节,这在中国是远远不够的,是解决不了分配不公问题的。”⑩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文件关于在收入分配领域要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认识,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赞同,形而上学的观点割裂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后来,中共十六大报告不再有类似提法。党的十七大肯定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看法: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十八大的表述则更加明确: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可以看出,党中央肯定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的正确认识。
三、党的十六大以来,强调更加注重公平
很多人开始关注出现的新问题:收入差距过分扩大,贫富悬殊日益加剧,社会的公平正义正在遭遇严峻挑战。很多学者提出应当辩证地考虑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党中央也再三强调要解决“社会分配不公”的问题,并让人们看到了深化改革的实际行动。
(一)党中央引领确立“更加注重公平”原则
党的十六届三中、四中全会提出,要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力度,努力缓解收入分配差距扩大趋势,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加大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这反映了党中央贯彻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的决心。党中央关于公平与效率的提法的演变显示:“文件起草专家与高层领导在效率与公平关系的问题上,是有过理论认识上的推敲、反思和反复的”{11}。理论界关于公平与效率的讨论和争论引起了党中央的反思。
党中央对于没有正确理解和执行公平与效率原则导致的对社会公平的严重忽视进行了纠偏,坚决反对经济至上的发展,着力调节分配关系,增进社会公平,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党和政府开始在政策上和行动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党的十六大同时提出了“既要反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十六届六中全会进一步清晰: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要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有效调节过高收入,坚决取缔非法收入,促进共同富裕。从中可以看出党中央将社会公平放在突出位置,关怀弱势群体。党中央的这些科学而重要的思想为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指明了方向。
(二)关于公平与效率的激烈争论
一些学者提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必须把公正放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位置。”{12}刘国光先生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并产生了极大影响。他指出: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效率与公平关系的认识,符合当时的实际,是正确的。经济理论界阐述和宣传这一分配政策的精神也是正确的。但随着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不同利益开始影响经济理论界。有些人以“优先”和“兼顾”的差异,轻视、曲解社会公平和社会公正,这不符合改革的精神。{13}刘先生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提法,随着条件的变化,应当有所改变,将这种口号普遍化与历史事实不符。我们党的理论发展和现实的变化证实了刘国光先生的判断。
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任务,特别是从2005年党提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以后,理论界有关公平与效率关系问题的争论更加尖锐。如何理解和贯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效率优先”的原则还要不要坚持?一些研究者认为,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是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的进一步完善,是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和不足的弥补和改进。有人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不能改。在任何时候公平和效率都不能兼得,必然有先有后。在现阶段,收入差距扩大是好事。{14}有教授表示:财力无情,效率必須优先,公平只能注重,提出“至少在20年之内,‘公平都提不到优先的地位。”“只有效率才能促进公平,没有效率,没有财富,何谈财富的公平分配!”{15}这些说法遭到反对。刘国光先生提出,应当把“效率优先”这个提法,放到该讲的地方去讲。“现在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社会不公平造成许多矛盾紧张与社会不和谐现象,潜伏隐患,不时爆发。若继续把社会公平放在‘兼顾第二位,与我党构建和谐社会的宗旨不符。如果再拖下去,把公平放在‘兼顾的第二位,如何与‘社会主义国家的称号相匹配?”{16}刘国光先生认为,强调更加注重社会公平,才符合改革的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17}
有人将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不同意见视为是要改变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要改变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对于这种观点,有研究者坚决反对。有学者指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理论,在消除由于片面理解按劳分配理论而出现平均主义的实践倾向上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两极分化等现象也暴露了这一理论的缺陷;割裂了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把二者异化为非此即彼的对立物。国企产权改革中公平的严重缺失,广大国企职工权益严重丧失是不争的事实。{18}很多学者高度赞同党中央提出的“更加重视社会公平”。王伟光教授认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个一般原则。这个原则是要追求效率与公平的优化结合。改革开放发展到一定阶段,公平问题就突出了。平均主义是一种不公平、差距过大也是一种不公平,当前平均主义与差距过大同时存在,差距过大是突出问题。{19}针对有人担心,强调社会公平会回到传统体制固有的平均主义。刘国光先生指出,随着中国改革的发展,很少有人会愿意回到“大锅饭”的旧体制。“引发不满的是体制外的灰色收入、法制外的黑色收人以及体制内由法律不健全政策不完善造成的非规范收入。”{20}针对一些人抱着西方经济学理论不放,认为注重社会公平就会降低效率,就是走平均主义的回头路而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观点,卫兴华教授认为,这是把公平与平均主义混为一谈了。{21}
也有一些人持不同看法,认为公平是一个不能确定的标准,把公平作为分配的标准,是“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22},在分配上要用公平标准进行分配,只能实行平均分配。对此,卫兴华教授提出:分配的公平并不等于把公平作为分配标准,例如按劳分配依据的标准是劳动贡献,而不是公平。要把分配标准同衡量分配是否公平区别开来。{23}很多研究者指出,我国改革遇到的突出问题是不公平,这些问题若不及时解决可能会侵吞市场化改革带来的提高效率的成果。党中央提出要把改革成果惠及最广大人民,因此,改革也需要转到公平为先,才能构建和谐社会。{24}
(三)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时期,凸显公平正义的重要性
在党中央的关注下,社会公平问题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话题之一。收入差距拉大、分配高低悬殊等问题也成为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和下决心解决的问题。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新一届党中央明确提出改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增进人民福祉”。党的十八大报告多次提及“公平”,彰显了公平正义的执政新蓝图。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新的目标要求和“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共享”是公平正义的鲜明体现。共享发展理念是对效率和公平关系的一次理论升华。在“十三五”时期甚至更长的一段时期,共享发展理念应该是处理效率与公平关系的重要指针。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现如今,我们仍然需要做好两个层面的事情,一是持续不断地将“蛋糕”做大,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二是将不断做大的“蛋糕”分好,让人民群众充分享有改革的成果,具有更多的获得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特别需要保证社会公平正义,进一步保障和改善民生,实现全体人民共同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四、余论
回顾领袖与马克思主义学者在公平与效率理论演变中的互动性可以深切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深刻的领悟力和敏锐的透视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从理论到政策的思考和探讨推进了对二者关系的理解,是我们党实现对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科学合理定位的重要来源。正是他们的坚定探索,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与中国实践的紧密结合。坚定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是中国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决支持者和忠实执行者,是改革的首创者和杰出贡献者,现在他们继续朝着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努力。当前,关于公平与效率问题的争论还在继续。理论界应该深入理解和正确阐释党中央一再强调的“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思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
注释:
①《杨圣明文集》,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440—442页。
②③⑥{11}参见卫兴华:《放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需要——对党中央关于效率与公平的提法演变的解析》,《山西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学报》2007年第5期。
④周为民、卢中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通向繁荣的权衡》,《经济研究》1986年第2期。
⑤参见程恩富:《略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收入分配问题——与厉以宁同志商榷之二》,《世界经济文汇》1989年第3期。
⑦程恩富、王树迅:《经济发展中的公平与效率——“海派经济论坛”第二次研讨会论文节选》,《社会科学》1996年第8期。
⑧参见顾钰民、周龙根:《两种体制下的公平与效率》,《社会科学》1996年第8期。
⑨参见周为民:《对“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误解应当澄清》,《中国经济时报》2002年9月21日。
⑩刘国光:《把“效率优先”放到该讲的地方去》,《经济参考报》2005年10月15日。
{12}吴忠民:《“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提法再认识》,《天津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3}{20}参见刘国光:《进一步重视社会公平问题》,《经济学动态》2005年第4期。
{14}参见张问敏:《关于收入差距与工资体制改革問题的争论》,《经济研究参考》2005年第29期。
{15}周天勇:《效率优先不能动摇》,《中国企业报》2005 年12月15日。
{16}{17}刘国光:《收入分配不用再提“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中华魂》2006年第1期。
{18}参见程言君:《按劳分配制度体系走向完善的30 年——从效率优先到公平正义的权衡与抉择》,《现代经济探讨》2008年第8期。
{19}参见王伟光:《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更好地兼顾公平,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学习时报》2005年8月15日。
{21}参见卫兴华、张宇主编:《公平与效率的新选择》,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61页。
{22}何伟:《我们还没有搞清公平与分配的关系》,《北京日报》2005年12月12日。
{23}参见卫兴华:《应重视我国现阶段的分配公平问题》,《理论前沿》2006年第1期。
{24}参见洪银兴:《构建和谐社会要坚持统筹公平与效率的改革观》,《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5年第3期。
参考文献
[1]刘国光.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
[2]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重大的抉择[M].北京:华夏出版社,1987.
[3]卫兴华,张宇.公平与效率的新选择[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8.
[4]程恩富选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5]刘国光.重新审视社会公平问题[N].北京日报,2005-04-25.
[6]卫兴华.实现分配过程效率与公平的统一[N].光明日报,2006-09-11.
[7]卫兴华,侯为民.在科学发展观下坚持效率和公平的统一[J].经济学家,2008,(3).
责任编辑:艾 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