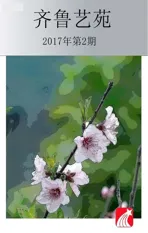试论《易传》中关于“神”的美学观点对后世“传神论”构建的影响
2017-02-14陈雅婧
陈雅婧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上海 200444)
试论《易传》中关于“神”的美学观点对后世“传神论”构建的影响
陈雅婧
(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上海 200444)
“神”是中国古代哲学的重要范畴,也是长期影响中国美学及艺术发展的基本概念和核心问题。早在《周易》一书的《易传》部分就有诸多关于“神”的理解,其中某些观念涵盖着一定的审美视角,成为后世“传神论”构建的雏形。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易传》中几种关于“神”的概念,及这些概念与“传神论”体系构建的联系,由此总结出其哲学性背后的美学含义,以及这种美学含义对后世中国艺术思想发展的重要影响。
《易传》;鬼神;神道;神妙;形神;传神论
一、引言
众所周知,《周易》一书是中国古代专门研究、占测宇宙万物变化规律的典籍,它由《易经》和《易传》两部分组成。《易经》内容包括六十四卦卦象、卦辞和爻辞,每卦六爻,六十四卦共三百八十四爻,传为周文王所作。《易传》内容是后人对《易经》部分作出的解释,传为孔子及其学徒所编,共七种十篇,分别是:《彖传》上下、《象传》上下、《系辞传》上下、《文言传》、《序卦传》、《说卦传》及《杂卦传》,又称《十翼》。
关于“神”的概念在《易经》部分并没有明确提出,而在《易传》部分却颇显集中。这可能是由于《易经》成书年代较早,且只是单纯的占事活动记录。而《易传》成书时以至春秋战国之后,当时的社会“百家争鸣”,学术思想极为活跃,且各家学说都爱从古籍经典中领会先贤之德,重读新解已是必由之路。所以不难想象,中国古代重要的哲学观念大多集中于此时成形问世。
当然,我们至今并无确切证据证明“神”这个概念是否最早出自于《周易》。但在《易传》中,很多关于“神”的理解,已初具哲学性及审美性内涵,对后世“传神论”绘画美学的构建与发展影响巨大。
二、《易传》中“神”的几种类型
在《易传》中谈“神”的地方很多,《乾卦·文言传》、《谦卦·彖传》、《观卦·彖传》、《丰卦·彖传》、《系辞传上下》及《说卦传》中都有不同程度地提到关于“神”的概念及理解,大致可分为四类:
第一类:鬼神
我们现代人所理解的“鬼神”通常只是单纯的神仙鬼怪论,是想象中有形有体的存在物。而《易传》中所提及的“鬼神”,除了含有某些宗教意味外,还指代自然界中某种无形存在物的运行规律。宋人程颐觉得是“造化之迹”,张载认为是阴阳“二气之良能”,朱熹说是“天地举全体而言,鬼神指其功用之迹,似有人所为者”[1](P434)。依他们的观点,天地间变化无常,神奇难测,却又有迹可寻,像似有人暗中主宰,却又不见踪影。这种看不见摸不着,但却可察觉到其踪迹的无形之物,在《易传》中就称之为“鬼神”。
如《乾卦·文言传》中记载:“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下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于人乎!况于鬼神乎!”[2](P166)这里的鬼神与天地、日月、四时一样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律而不能违逆,人虽看不见它的形,但能感觉到它的存在。
再如《谦卦·彖传》中记载:“谦亨。天道下济而光明,地道卑而上行。天道亏盈而益谦,地道变盈而流谦,鬼神害盈而福谦,人道恶盈而好谦。谦尊而光,卑而不可逾,君子之终也。”[3](P93)这里的“鬼神”与“天道”、“地道”、“人道”相似,都厌恶骄傲自满的人,而青睐谦虚隐忍的人,在宇宙间是一种无形的存在。
第二类:神道
关于“神道”,《观卦·彖传》中说:“大观在上,顺而巽,中正以观天下。观,盥而不荐,有孚顒若,下观而化也。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4](P94)在这里“神道”可能是一种精神或思想的法则,“观天之神道,而四时不忒,圣人以神道设教,而天下服矣”,即是,在瞻仰了天的精神法则后,四时就可以运行无差了,圣人以这种精神或思想法则来教化百姓,那么天下便会臣服。和今天所说的“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在《易传·系辞传上》中的“神无方而易无体”[5](P140)、“阴阳不测之谓神”[6](P142)、“显道神德行,是故可与酬酢,可与祐神矣”[7](P146)、“蓍之德圆而神”[8](P148)这些句子,“神”的含义可能与“神道”相类似,即精神或思想的法则没有具体的形状,很难预测。
第三类:神妙
在《易传》诸多关于“神”的理解中,有一种很接近后世美学概念中的“神妙”理论。《说卦传》中记载:“神也者,妙万物而为言者也。”[9](P171)自然造化之妙,没有一定的轨迹,变幻莫测,匪夷所思,无定在,而又无所不在。张乾元认为这里的“神”不是指脱离物质生活而独自存在的鬼神,而是指自然规律的神奇与巧妙。[10](P214)“妙”在中国古代美学中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范畴,老子曾指出:“玄而又玄,众妙之门”[11](P1),意指“道”的无限美妙,至精致微,至深至远,妙不可言。
“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过此以往,未之或知也。穷神知化,德之盛也。”[12](P155)这句话出自《周易·系辞传下》,其中“精义入神”中“神”的含义与也与“神妙”类似,也是指那种超乎想象的美好境界。而“精义”则指精微的道理,只有具备精益求精的进取精神才能达到出神入化的境界。
而《周易·系辞传下》中还有一句与“神妙”思想极为相关的话就是“子曰:‘知几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谄,下交不渎,其知几乎。几者,动之微,吉之先见者也,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13](P157)其中“知几其神”的“几”是指事物发展变化的苗头,“神”指超乎寻常,意思就是说能知道事物发展变化的苗头,学问超乎寻常。而学问都到了超乎寻常的境界了,岂不是“神妙”所在。
第四类:形神
在《周易·易传》中对后世绘画理论影响最为深远的,可谓“形神”之论了。也许此时的形神论与后来完整意义上的形神论体系并非完全一致,但初步的概念性思维已经形成。如《易传·系辞传上》中载:“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14](P150)“见乃谓之象,形乃谓之器,制而用之谓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谓之神。”[15](P148)在先秦哲学中很多时候“形”与“器”是紧密相连的,来解释一种自然界的有形存在,而“神”则与之相对,是一种无形的存在。两汉时期经过儒、释、道三家学说的整合,形神论已逐渐演变为一种人身体与精神之间的哲学矛盾。
其实上述四种解释,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可以相互渗透、互为补充。如:“子曰:‘知变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为乎!’”[16](P146)即,孔子认为知道变化之道的人,也就知道“神”的所作所为了。其实这里的“神”可有多种理解。宇宙是通过“神”在时间和空间上作用于万物的,无所不及,无所不漏,以此推测“神”的处世形态为没有固定居所的游离之物,即无处不在。这里的“神”有“鬼神”的性质,有“神道”的精神,“神妙”的美好,也有“形神”的立体存在感。先哲们试图从宏观上来体会天地变化的纵深力量,并以此说明“神”的影响力和穿透力无所不及。宇宙万物尊从天之命理,而人无法进行形式上的外在连接,只能用心去体会,用眼去观察。由于《易经》是研究“神”的精要义理,所以也无具体形式。“易,无思也,无为也,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非天下之至神,其孰能与于此?”[17](P147)古人观察事物的着眼点,通常以人为参考对象,先考察事物的形体相貌,然后是它区别于其他事物的功能属性。而“神”在此考察过程中,直接被省略掉了形的样貌局限和固有常态,所以无往不惧,博大精深。
三、《易传》对“传神论”构建的影响
“传神论”的提出始于东晋画家顾恺之,是一种专门针对人物画创作与审美的品评理论,之后延及绘画其它门类。《历代名画记》卷五载其所论:“人有长短,今既定远近以瞩其对,则不可改易阔促,错置高下也。凡生人亡有手揖眼视而前亡所对者,以形写神而空其实对,荃生之用乖,传神之趋失矣。空其实对则大失,对而不正则小失,不可不察也。一像之明昧,不若悟对之通神也。”[18](P110、111)整段话的意思大概是:在画一个举手作揖、眼睛向前看的人时,目光必须有焦点,如果“空其实对”,连形都不准,就更谈不上传神了,故曰“大失”。如果“对而不正”,那是构图安排不当,算是“小失”。所画的人物是否有光彩,不如对着对象物而心中有悟之通神,亦即“悟对通神”要高于“像之明昧”。由此可见“传神论”主要是针对人物画而言,尤其是对人物眼睛的刻画。于是顾恺之在《论画》中说:“点睛之节,上下、大小、浓薄,有一毫小失,则神气与之俱变矣。”[19](P110)他甚至将眼睛强调到绝对重要的地步,故《世说新语·巧艺》中又记其语:“四体妍媸本无关于妙处,传神写照正在阿堵中。”[20](P299)这些看法反映了绘画从绘形到写神的重大转变,以致形体之似降到次要地位,相应的眼睛成为了表现内在精神的重中之重,点睛荣升为绘画成败的关键。
“传神论”的形成与《易传》中关于“神”的几种理解颇具渊源,特别是“神妙论”与“形神论”。当时的人们受魏晋玄学影响很深,如汤用彤先生所言:“夫玄学者,谓玄远之学。学贵玄远,则略于具体事物而究心抽象原理。论天道则不拘于构成质料,而进探本体存在。论人事则轻忽有形之粗迹,而专期神理之妙用。”[21](P214)而对于宇宙神理的探讨,一直又是玄学最为热衷的课题。他们在吸收了儒、释、道三家中关于“神”的定义后,糅合成自家之言。其中也受到《易传》中“神”概念的影响。如玄学中认为“神妙”之境就是“得之于手而应之于心”,这与《易传·系辞下》中“精义入神”的定义颇为相似,也具熟能生巧的道理。而《易传》中关于“形”、 “神”间的讨论,对后世美学影响最为深远。
《易传》中认为“形”为自然界真实的存在,而“神”则为看不见摸不着的神秘之物。至两汉时期,“形”的定义已从广义的真实缩小到人的身体,“神”则指人的精神。如前后汉之交的桓谭在其《新论·形神》中,以烛火之喻来论形神的关系:“精神居形体,犹火之然烛矣;烛无,火亦不能独行于虚空。”[22](P7)东汉王充在其《论衡·论死篇》中也有类似的言论。可见,汉人对形神的认识是带有某种朴素的唯物主义辩证观点。至魏晋时期“形”与“神”已结成相对固定的概念,这与佛学的刺激也颇有关联。慧远《形尽神不灭》(问):“神虽妙物,故是阴阳之所化耳。既化而为生,又化而为死。既聚而为始,又散而为终。因兹而推,因知神形俱化,原无异统,精粗一气,始终同宅。宅全则气聚而有灵,宅毁则气散而照灭;散则反所受于天本,灭则复归于无物。”(答):“夫神者何耶?精极而为灵者也。精极则非卦象之所图……神也者,圆应无生,妙尽无名,感物而动,假数而行……推此而论,则知化以情感,神以化传,情为化之母,神为情之根,情有会物之道,神有冥移之功。”[23](P97)问者以神为精神,答以神为介于精神与人格化对象之间的东西,其含义延续扩展了汉人的观点。而善于清谈或辩论的魏晋名士们在空谈义理之外,常把“形神”理论引入文艺批评之中,特别是绘画理论,于是导致了“传神论”的问世。
四、结论
《易传》中关于“神”的理论,虽然只是远古哲人们零星的话语记载,且不成体系,年代真伪也难于考证。但在几千年的文明发展史中一直被视为经典,定有其可取之处。那种对于自然规律的敬畏,导致先哲开始探讨“神”的存在,当他们发现“神”与人类思维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时,又开始新一轮的探讨。于是“传神论”的出现成为了“神”理论的中心主干,它与《周易》有着极深的渊源,层层影响至发展成熟,可以说“传神论”的构建从《周易》开始就已起步。
[1]金景芳,吕绍刚.周易全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
[2][3][4][5][6][7][8][9][12][13][14][15][16][17](宋)朱熹.周易本义[M].苏勇校注.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
[10]张乾元.象外之意——周易意象学与中国书画美学[M].北京:中国书店出版社,2006.
[11](东周)老子.道德经[M].陈忠译评.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2004.
[18][19](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M].俞剑华校注.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4.
[20](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M].杨牧之等译.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21]汤用彤.汤用彤学术论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2](汉)桓谭.新论[M].吴则虞校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
[23]韦宾.汉魏六朝画论十讲[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刘德卿)
2016-10-21
陈雅婧,女,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在读博士生,研究方向:美术学。
10.3969/j.issn.1002-2236.2017.02.016
J20
A
1002-2236(2017)02-007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