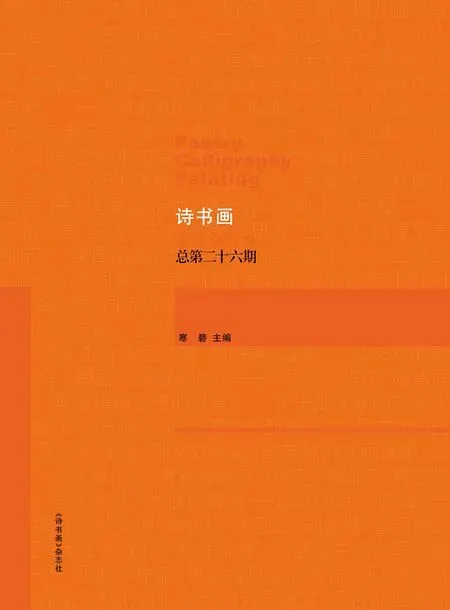隐秘的时间
——评邵文欢作品
2017-02-13陶寒辰
陶寒辰
邵文欢的作品往往出现在一个恰到好处的位置,因此我们很难用特定的艺术媒介去定义邵文欢的创作,也无法用“摄影”、“绘画”或更笼统的“综合艺术”概念去框定邵文欢的身份。媒介和身份问题不是邵文欢最关心的话题,他寻求的是通过媒介使用和身体碰撞,去获得艺术情感体验中的对位。当相机和摄影无法单独达成时,手和绘画由此介入创作,两者共谋形成了他作品的基础形式。
邵文欢一直在创作中尝试各种可能性的改变,并在变化之中留下持续性的线索。时间性是邵文欢的作品在符号性之外保留的关键线索之一。不同于录像和行为艺术自带的时间属性,摄影和绘画对于瞬间和静止的外部客观对象的具体描述,使得其中的时间性几乎无法自证。但邵文欢复杂而多层次的创作过程,以及把握材料并不断拆解和重新建立,使时间性贯穿在他的创作中。
邵文欢的时间性,首先来自他的三种不同而勾连的创作场域:相机(摄影)、暗房(负像)、画室(绘画)。摄影是邵文欢捕捉时间切片的过程。他反对概念先行,灵感发生于他对周围世界的探索,并伴随快门的按下而锁定。但他不会即刻消化获得的素材,时间在此成为最好的过滤器:也许几天,或许几年,这些素材会被重新审视。暗房是邵文欢最谨慎的实验室,也是他思考媒介关系最重要的场所。面对负像和感光乳剂,邵文欢进行过不同媒介的实验碰撞,为绘画阶段的创作预埋下意料之外的伏笔。曾经的绘画经验是邵文欢无法摆脱的情结,我们在他第三阶段的创作中可以很轻易发现其中的绘画性。但他也警惕于陷入媒介的控制,力求摆脱作品的形式和工具分析。因此,与其用绘画去概括邵文欢创作的第三阶段,不如称之为“用绘画对由摄影构成的基础画面的‘干扰’”来的精确。漫长的创作为邵文欢带来了更多的思考空间,我们也许可以看见那些始于灵感的开端,却不会知道止于时间沉淀的结局。
另一层时间性隐匿于邵文欢不同时期的作品,《不明》、《霉绿》、《暮生园》等对传统园林、树木、山石、风景等偏具象形式的展现,都营造了一种带有“中国性”的文脉联系。而在《国际旅游者》和《夜空中星尘的光》系列中,邵文欢表达了他对时间历史的两种反向认识:前者是艺术家对中国题材创作的自我突破,将个人意识具体到某个飘离和虚构的历史语境里;而后者把对宇宙、历史的宏大认知凝结到不可言说的个人历史观中。从不同作品在题材和语言上的演进、变化中,我们发现不变的是邵文欢试图隐埋的个人时间意识。而在邵文欢最近的创作中,时间的介入变得愈加直白。在大画幅近作《暖冬》中,邵文欢利用全景摄影技术,经历五个半小时的拍摄,将六百张照片拼合在一起。漫长的拍摄阶段,每一个细节都需艺术家去手动调整。六百个瞬间所蕴含的时间逻辑,赋予了作品丰富的可看性,也避免了“为拼合而拼合”的刻意。正如邵文欢自己所说的:“用眼睛去带动时间”,《暖冬》打破了摄影本身作为图片的单一时间性,让观看者在静止的画面前感受到动态而细腻的瞬间。
如果说《或在此-仿视频》、《囿苑蝶梦》等早期作品是邵文欢为了突破画面单一性而对技术介入的主动尝试,那么从《奥菲莉娅的河》开始一直到《穿过星尘的光》,以及二〇一七年主题为“界破”个展的近期创作,邵文欢用一种被动和偶发的方式突破了作品固定的边界:暗房阶段因为感光乳胶的意外崩塌,反而为他带来更多的画面层次;对画面进行“撕破”和“划痕”的处理,暗示了一种时间前和时间后的关系;从“失败之作”成为“可控之作”,邵文欢对材料和观念的把握也变得更加得心应手。邵文欢在探索中,不断明确了他的艺术态度,在警惕媒介对创作控制的同时,去“界破”艺术的“边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