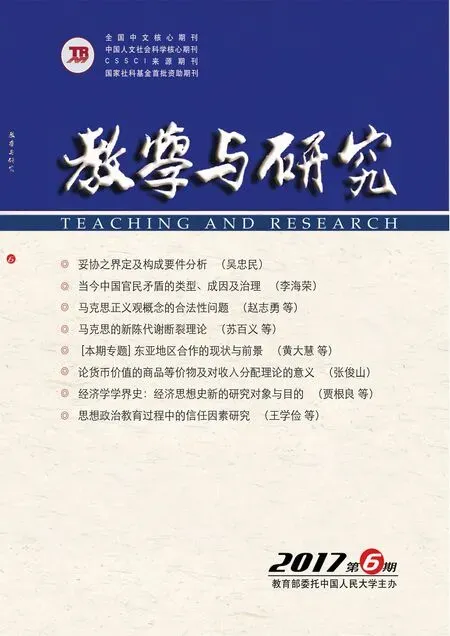东亚地区合作主导权与中日制度竞争*
2017-01-31黄大慧
黄大慧,孙 忆
东亚地区合作主导权与中日制度竞争*
黄大慧,孙 忆
中国;日本;美国;制度竞争;东亚合作主导权
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地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为赢得东亚地区合作主导权展开了激烈的制度竞争,两国对“10+3”、“10+6”等不同地区合作机制有着不同的利益倾向与选择。具体而言,中日两国实力差距越大,美国在东亚的制度性介入程度越深,中日两国关系可能相对越发紧张,彼此之间的制度竞争也将越激烈。在当前美国战略收缩的趋势下,中日两国需超越传统的地区主导权竞争逻辑,探求新的竞合路径以推动东亚地区未来一体化发展。
东亚地区合作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不断向前推进,多个地区合作机制的涌现引发了人们对东亚地区主义及其经济新秩序的广泛探讨。[1]与此同时,东亚地区事实上存在的多个制度相互竞争的格局也成为普遍关注的焦点。中国和日本是东亚地区最大的两个经济体,赢得制度竞争的胜利并获取东亚地区合作主导权对两国而言都有着重要意义。在日益明晰的“规则世界”中,中国与日本这两个东亚大国为何、如何展开制度竞争,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一、东亚合作主导权中的中日竞争
地区合作涉及规则的制定与资源的配置,这就往往体现出一种政治权力的色彩,因为权力占优的一方,即主导方,能够通过自身主导地位使地区合作进程更多地朝向自身意愿的方向发展,从而能获得更多的经济资源与议程便利,谋求并巩固自身利益。由此,大国间对地区合作主导权的争夺成为一种自然的现象。在东亚地区,崛起中的新兴大国中国和致力于“普通国家”化的日本,甚至包括全球霸主美国,它们为争夺地区合作主导权而展开的博弈甚至体现出了国家意志的较量。
(一)APEC与日本争夺东亚地区主导权的萌芽
对东亚地区主导权的争夺是在东亚地区主义的演变过程中逐渐凸显出来的。东亚地区主义的起源可追溯到1989年成立的超东亚范围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和1992年建立的次东亚范围的东盟自由贸易区(AFTA)。其中,日本在APEC的成立与发展进程中发挥了积极推动的作用。这一是因为当时的日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推动地区内贸易与投资深化发展,二是因为日本也意图通过地区经济融合实现本国产业转移和经济结构换代升级。可见,日本从最初阶段就意识到了要注重利用国际制度参与并推动地区经济合作。通过APEC这样的国际制度平台,日本可以逐渐发挥经济实力的影响力,使东亚成为由日本所控制或主导的经济圈,在美日欧资本主义经济三足鼎立格局中保持日本经济在全球范围内的竞争力;进而还可能将APEC发展为日本协商亚太安保问题的场所。
(二)“10+3”机制与中日制度竞争的发端
然而,日本对APEC的制度期待尚未如愿实现,1997年就爆发了严重的亚洲金融危机,但此次金融危机却成为东亚地区主义真正发轫的起点。1997年12月,东盟—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对话合作会议召开,建立起“10+3”系列峰会机制,以共同应对大规模金融危机带来的冲击与挑战,并摆脱对美国和IMF等国际金融机构的过度依赖。这似乎标志着东亚经济一体化合作迈出了实质性的一步,[2](P339-372)因为2000年5月各方在“10+3”框架下达成了《清迈倡议》(CMI),约定在一国出现流动性短缺或严重的国际收支失衡时可通过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请求提供援助,并且2010年3月,规模达1 200亿美元的东亚区域外汇储备库正式生效,其中中国和日本都是最大的出资国。尽管中日两国从储备库中能提取的外汇数量不超过其出资份额的一半,实际经济受益程度并不高,但中日两国寻求的是更长远的收益,如在亚洲货币合作中的主导权等。大国制度竞争的态势已显现端倪。
中国对“10+3”始终有着更强的倾向性,因为“10+3”事实上可帮助中国有效地实施以自身为核心的地区合作战略。一方面,“10+3”能使中国获得较大的经济好处,且“10+3”也更符合中国的周边战略要求,能使中国获得更大话语权;另一方面,“10+3”也得到韩国、东盟部分国家支持,合作决议相对更容易实现。[3]
日本曾是“10+3”的支持者,因为日本也意图凭借其经济大国的优势通过“10+3”掌握东亚地区合作主导权。然而,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使日本感到威胁,而 20世纪90年代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却使日本遭遇重挫;并且,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使得中国成功树立起负责任的大国威信和地区影响力,而日本在危机时贬值日元、从东亚撤资的行为却损害了日本的声望;另外,日本先后提出的倡议和举措,包括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倡议、“新宫泽构想”等,都未能成功地使日本提高日元及本国地位,也未能使日本成为亚洲领导者。[4](P86)[5](P117-120)因此,日本要借助其他的制度平台争取自身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优势地位,其中一项重大举措就是转而推动东亚峰会“10+6”机制的形成与发展。
(三)“10+6”机制与中日制度博弈的加剧
2005年12月,在东盟的推动下,首届东亚峰会(EAS)在马来西亚吉隆坡进行,东亚峰会由此启动。然而,在“10+6”东亚峰会的制度设计初期,中日两国就出现了分歧。东亚峰会最初构想,是要用更为正式的地区合作制度形式代替非正式的“10+3”领导人会议,进而推动建立东亚共同体。这是中国和马来西亚所主张的观点,即直接将“10+3”机制过渡为东亚峰会机制。[6](P110-142)但这却遭到了日本及印度尼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反对。日本认为,应以“10+3”加上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这3个东亚区域外国家来构建东亚共同体。双方发生分歧的原因及背景在于,中国意图以排除东亚区域外各国影响、使本国容易行使影响力的“10+3”为基础构筑东亚共同体;而日本则判断难以将兴起的中国的影响力抑制在“10+3”框架中,便提出要以加上与美日友好的、价值观一致的域外三国的“10+6”为基础构建东亚共同体,这其中有日本外交所固有的对美意识所发挥的作用。[7](P199)
日本倡导“10+6”机制还有一大重要原因,那就是因为“10+6”机制也是日本推进其经济伙伴协定(EPA)战略的重要环节,不仅主要的东亚国家都已被囊括在了“10+6”当中,而且“10+6”还能使日本顺利构筑起“东亚EPA”(即“扩大版的东亚共同体”)。[8]因此,日本并不愿意放弃通过“10+6”机制遏制中国、赢得合作主动权的机会。
最终,东亚峰会被定位为“10+3”成员国与域外国家进行对话的机制,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被列为东亚峰会机制成员国,这契合了日本的主张;而出于对中国立场的妥协,“10+3”继续运行而未被废止。由此可见,“10+6”与“10+3”成为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并行的两条渠道,分别代表了日本、中国在争夺东亚地区合作主导权时的路径选择偏好。
(四)中日关于地区合作机制的不同偏好与选择
不可否认,中国和日本也存在着实质性推进东亚地区合作的意愿与行为,这主要体现在中日韩三国领导人峰会机制的建立与演变上。自三国首脑于1999年11月的初次聚首以来,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在经贸合作、对外投资等功能性领域都有所深入,制度化程度也有所提高。然而,日本因领土问题、历史问题屡次破坏合作进程,政治猜忌与嫌隙给三国的地区合作带来严重干扰。日本既希望以中日韩为核心推动“东亚共同体”建设并抑制中日、韩日之间的民族主义冲突,又对中国的发展表现出忧虑与不安,力图将中国纳入并限制在以发达国家为主导的规则与秩序中,用多边制衡关系抑制中国地区影响力、追求日本国家利益。然而,客观上,日本无法阻遏中国的快速发展,且没有中国的配合与合作,日本的任何地区合作倡议都极有可能落空。
总体而言,中国和日本作为东亚地区主义领导地位的争夺者,无不意图通过推动自己所偏好的地区合作机制在地区制度竞争中胜出,以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中国为防止区外大国干扰东亚合作进程,更偏好“10+1”、“10+3”等机制;而日本为了运用区外大国制衡中国,更偏好东亚峰会等机制。[9]显然,中国和日本的偏好呈现出两种不同的朝向,也衍生出了相互竞争的地区主义理念:中国是内向型的,希望依靠东亚内部的国家力量推动东亚地区合作进程,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实力和愈发凸显的政治影响力赋予了其相应的资本,以使中国有能力在一定的东亚地区范围内协调与其他地区国家之间的关系,进而逐步获得实质上的东亚地区合作主导权;日本则是外向型的,在与中国制度竞争时的不自信心态以及相对较弱的经济实力,都促使日本更多地想要引入并借助域外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力量,以平衡中国对自身地位的冲击,进而获取东亚地区合作中的主导地位。
因此,中国和日本在东亚地区展开的关于地区合作主导权的制度竞争,很大程度上受到内外两方面的因素驱动。从地区内部来看,中日实力对比影响两国对彼此的国力认识,进而影响两国开展制度竞争的烈度。而且中日实力差距越大,两国开展的制度竞争将越激烈,实力较落后的一方意识到自己的竞争劣势,将更频繁地向自己偏好的机制投入更多资源,以避免进一步失利。从地区外部来看,美国依然在东亚地区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而日本作为美国的盟友将能借助美国的力量进行东亚制度竞争。由于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介入给日本提供了更多的竞争性制度选择和可依靠的制度力量,并且美国的介入程度越深,日本能获得的制度资源越多,其与中国开展制度竞争的对抗意味也将越强。
二、中日实力对比与两国地区影响力消长
国家需要充足的制度资源以参与制度竞争,而这是建立在国家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的基础之上的。从两个国家对比的视角来看,实力较强的一方显然比实力较弱一方有更大的经济优势获得制度竞争的胜利。并且,当两国实力差距拉大但又未及差距悬殊之时,两国之间的猜忌和不信任感就会有所增强,因为在两国实力几乎相当的情形下,两国有相似的概率赢得制度竞争;实力差距拉大后,弱势一方的急迫感和危机感愈发凸显,这将加剧两国间制度竞争的紧张态势。
从中日两国GDP之比的走势来看,20世纪中后期至21世纪头十年,日本始终在综合国力上强于中国,但中国改革开放后经济快速发展,2010年中国GDP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在此后短短5年间就高达日本GDP的2.5倍。
快速增强的经济实力使中国有更多的经济资源投入到地区制度建设当中。例如,2010年,在“10+3”框架下,中国出资384亿美元建立东亚区域外汇储备库,出资额与日本持平。在中国—东盟“10+1”框架下,双方不断深化互利互惠、合作共赢的经贸关系,中国也成为东盟最大贸易伙伴,双方于2010年全面建成中国—东盟自贸区;2013年10月,李克强总理还在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率先倡议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升级谈判,这也得到了东盟各国领导人的积极响应;2014年8月,在中国的努力推动下,中国—东盟经贸部长会议正式宣布启动升级谈判并于2015年11月签署了FTA升级《议定书》。自2012年以来,中国相继提出了一系列创新性的东亚战略倡议,积极推动地区合作制度化并致力于地区战略升级,具体表现除了包括深化与东盟的制度化联系以外,还体现在中国主导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等新地区合作制度上;由此,中国在实力上升过程中借助一些制度化的构想与举措,缓解东亚疑虑并深化地区利益与认同,力争在新一轮构建东亚乃至亚太秩序中发挥更强有力的塑造和引领作用。
中国的实力崛起及其在制度倡议中的主动态势加剧了日本的不安。并且,日本也意识到自己在东亚地区合作中开始面临来自东亚其他国家越来越大的压力,包括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压力、政治外交关系压力等,因此它不得不重新调整其国内经济,还包括一定程度上的外交政策,积极地使自己与东亚地区融为一体。[10](P132)除了利用意识形态、军事等手段遏制中国外,日本还试图选择并倡导对其更有利的地区合作制度,避免在制度竞争中落入被动境地。例如,当日本意识到中国牵头成立的联合专家组研究报告可能导致东亚合作沿着“10+3”的路径推进时,2006年日本也成立联合专家组,提出以“10+6”为基础的紧密经济伙伴协定(CEPEA)并倡议按此框架推动东亚贸易合作,建立大东亚版的OECD机构,使日本制定主要规则并发挥主导作用,并使得东亚合作亚太化。在东亚峰会扩容过程中,日本也努力促成美国加入东亚峰会,这是在东盟的默许下实现的。在强化与东盟国家的制度性联系时,日本借助粮食和农业合作拉拢东盟,实则与中国争夺主导权,其中包括:向亚洲开发银行注资并在东盟国家开展105个农业合作项目;支持“10+3紧急大米储备库”项目永久机制化进程并一定程度上主导“10+3”粮食安全务实合作等。[11]不仅如此,由于日本的“和平宪法”对日本对外政策目标和手段有所约束,日本不得不依赖经济援助这一有力手段争取各国支持、提高国际地位、争当政治大国。
目前,中日在经济合作领域仍呈现出对立竞争的态势。以国际发展援助领域为例,在援助内容上,中日发展援助都与基础设施建设及其投融资、国际产能合作有关,因此双方在扩大第三国市场份额时存在明显的竞争关系。在地缘范围上,中日的援助范围均涉及东亚、非洲、欧洲等地,覆盖范围有所重叠。在机制建设上,中日两国分别倡导的国际机构或机制存在明显的功能交叉与重合,如中国倡导建立的亚投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中非合作论坛”,日本占主导地位的亚洲开发银行、“日本国际协力机构”、“非洲发展会议”等,这是两者形成制度竞争态势的最明显表现。
中国和日本争相利用自身的经济实力赢取东亚地区伙伴对其自身的制度支持,但取得的成效却有差别。大部分东亚国家与中国关系更紧密,而与日本的关系则相对更紧张、更波动。一是因为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带来了经济效益外溢与红利扩散,这将给中国带来更广泛的制度支持;而日本因长期经济增长乏力,虽在科学技术、资金供给、教育人才等方面仍有优势,但已不复往日盛态,难以持久地推动地区经济增长,因而很难以足够的经济吸引力笼络其他东亚国家对其制度倡议的支持。二是因为中国在崛起过程中注意建立自身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在与东亚国家相处时不仅致力于维护国家间的和平共处,还承担起大国的地区责任并推动地区发展问题的解决,这获得了大多数东亚国家的支持;而日本所欠缺的亚洲认同使其很难以平等的伙伴身份与东亚各国开展真诚合作,并且日本对二战历史问题缺乏深刻反思的态度以及其多次挑衅的行为给东亚诸多国家带来更深的伤害,因此东亚国家很难对日本产生信任或完全支持日本的制度举措。
总体上看,中国经济实力超过日本并逐渐拉大,且在争取东亚地区伙伴的制度支持时似乎也比日本更占先机。于中国而言,这是进一步在东亚地区赢得制度竞争胜利并获得地区合作主导权的优势所在。但是于日本而言,经济实力的相对落后和地区制度伙伴的相对缺乏使日本感受到越来越强的制度竞争压力,抗衡中国的迫切性也愈发凸显。由于自身实力短期内难以重新超越中国,日本开始借助外力帮助自己争取东亚地区合作主导权。
三、美国因素与中日制度竞争新形态
在东亚地区的中日制度竞争中,美国始终是一个关键存在。重返东亚是美国防止其自身影响力衰落的重要举措,制衡中国在整合东亚经济中发挥的主导作用也成为其地区战略目标。这与日本的国家战略不谋而合,因而美国成为日本能借助和倚仗的外部力量。由此,美国在东亚经济中的介入也明显对中日制度竞争的态势产生影响。
(一)奥巴马政府“重返亚太”与中日间国际贸易制度博弈
美国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推行的“重返亚太”战略给中日制度竞争带来变数。首先,美国政府的介入主要体现在美国加快与东亚国家进行自由贸易协定(FTA)谈判上。早在2003年,美国就与新加坡签署了FTA;2012年,美国又与韩国签订了FTA。美国在区域层面借助FTA介入东亚地区整合的积极态势,加上2001年中国率先提出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2010年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最终建成的冲击,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坚定自身的FTA战略,并愈发加快了自身的东亚FTA网络建设。根据WTO的数据,当前日本已生效的FTA有15个,其中与东亚国家签署的FTA就达8个,不仅与东盟整体签署了FTA,日本还与新加坡、马来西亚、菲律宾、文莱、印度尼西亚、越南这些单个东盟国家签订了双边FTA。日本在双边层次上与东亚国家签订FTA的势头似乎超过中国*如果将东盟这一国家组织视为一个整体的话,那么目前中国已生效的东亚双边FTA只有中国—东盟FTA和中国—新加坡FTA,数量上不及日本的东亚双边FTA。但从FTA的质量与深度上,中国与东盟谈判并成功签署了“10+1”升级版FTA,这又是中国超越日本的地方。。日本和美国积极与东亚国家联系签订FTA,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在东亚地区构建起一个于其有利的FTA伙伴网络,因为FTA在增进签约国之间共同经济利益的基础上,还将向政治、安全等综合领域实现功能外溢。通过这种双边FTA的签订,日本也意图能获得更多来自东亚地区伙伴的政治支持,进而赢得对中国的制度之争。
此外,除了推进与东亚国家的双边FTA,日本也借助奥巴马政府在亚太地区推行的超大型FTA,即“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议”(TPP),力争掌握新一代更高标准的国际贸易规则制定权,并借加入TPP来增加其对外贸易谈判并维护自身地位的筹码。[12][13]尽管日本也自2012年起参与了“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的谈判,但日本的战略重心始终不在RCEP上。一是因为RCEP主要由东盟发起,中国凭借强大的经济实力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将其用作抗衡美国贸易制度压力的手段;二是因为,虽然RCEP也是追求更高水平的贸易规则,但RCEP以“东盟方式”进行规则谈判难以保证高标准规则的最终确立与实施。在东亚地区,日本显然选择了以美国为首的TPP作为贸易制度竞争的主要手段,而中国选择了RCEP。中日两国在两个规则制定模式截然不同的超大型FTA的框架下也展开了较为激烈的制度竞争。
(二)特朗普政府战略回缩与中日制度竞争新趋势
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台后,美国在东亚乃至亚太地区的存在发生大变化,即特朗普政府可能为重振美国国内经济而收缩美国在东亚、亚太地区承担的义务,这种变化将以另一种方式对中日之间的制度竞争产生影响。
一方面,美国的战略收缩趋势意味着特朗普政府的未来政策将以“美国优先”为核心,更多强调美国本土的经济利益而非海外经济利益;而中国作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在投资、制造业等经济领域与美国存在一定的竞争,特朗普上台后实施的经贸、产业等方面的政策可能将使中美经贸关系面临一定的挑战。受此影响,中国在亚太地区参与并开展制度竞争的经济与规则成本可能有所提高,因为中国面临国际贸易摩擦和制度性包围的可能性有增大的趋势。
另一方面,特朗普的当选出乎日本安倍政府的意料,为掌握日美同盟关系的未来走向,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采用一系列频繁首脑外交的方式确认美国对日本的继续支持,并试图让美国继续为日本在东亚地区抗衡中国提供助力与保障。2016年11月17日,在特朗普刚刚当选总统而尚未宣誓就职时,安倍就迫切地与特朗普举行了会面。而日本首相与美国新当选总统在就任前举行会谈是十分罕见的。由此也可见日本对美国对其支持立场、力度的高度重视甚至依赖。2017年2月10日,安倍在特朗普上台后再次急切访美,意图显示日美同盟关系之牢固。事实上,特朗普在安倍访美前还致信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示希望与中国发展建设性关系,意图在中国和日本之间展开平衡外交。由此可见,在美国对东亚及亚太地区的影响相对减弱的情况下,日本继续与中国开展制度竞争缺乏强有力的盟友保障,而日本当前的实力又不足以支撑其独自抗衡中国。因此短期来看,中日两国之间的制度竞争烈度可能会因美国的战略收缩而有所下降。
总体而言,日本的东亚合作很大程度上受到美国对东亚政策的直接影响,[14]它将中国视为制度竞争对手,强调必须使亚洲合作和日美同盟相互配合,才符合日本国家利益。[15]要成功争夺东亚地区合作主导权,国家要通过制度联系获得更多伙伴支持。因此,日本借助美国在东亚的介入,强化其与美国同盟体系的关系,由此抗衡中国。但中国也并没有坐以待毙,日益主动开放的中国FTA战略在双边层面上打造中国FTA伙伴网络,在区域层面上推动RCEP建设,这些都为中国化解伙伴压力、规则压力提供了解决方法。由此,中日两国在东亚地区开展的竞争态势也呈现出与以往不尽相同的特点,即除了传统的实力较量外,在形式上也更多地倾向于对超大型制度平台的借力,以实现自身的战略目标。
四、中日制度竞争的未来可能趋向
东亚地区内中日两国实力对比,以及域外力量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介入程度,是影响中日两国关系及双方制度竞争态势的两大重要因素。中日两国实力差距越大,美国在东亚的制度性介入程度越深,中日两国关系可能相对越发紧张,彼此之间的制度竞争也将越激烈。然而,由于中日之间的经济实力差距仍继续扩大,且美国传统性力量逐渐退出,这可能给中日制度竞争局面带来新变化。对中国和日本而言,似乎问题转变成:实力差距仍在扩大的两个地区经济大国是否还能各自凭借不同的国际制度平台开展竞争?是否出现在同一制度框架下继续开展竞争的可能?两国应该如何转变竞合关系?
对日本而言,面对地区形势新变化,尽快构建起针对中美两国的新经济外交战略迫在眉睫。首先,日本要调整过去偏重TPP的策略,重新审视RCEP在整合地区经贸关系及其在帮助国家获得地区主导权上的重要作用,警惕中国通过RCEP获得自由贸易规则主导权和地区主导权。然而,由于RCEP要照顾到区域内经济发展水平不高的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对农业等敏感议题也根据各国情况采取例外规定,规则制定过程中的弹性很可能无法满足规则质量的高标准,因而也很难满足日本意图在经济规则和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上达成“高质量的协议”的要求。因此,尽管当前美国退出了TPP,日本仍不愿放弃TPP,试图与另外的10个TPP成员国维持协定框架,把尽量不改变现有框架作为新协定的基本方针。日本决意引领“无美国版TPP”,通过TPP拉帮结伙,牵制中国。2017年4月19日,日本副首相兼财务大臣麻生太郎宣布将从5月开始讨论由不包括美国的11个国家促成TPP协定生效*参见2017年4月20日日本共同社、《读卖新闻》、《日本经济新闻》等主流媒体的相关报道。。尽管如此,日本仍然重视RCEP在地缘政治经济整合中的独特意义,不愿坐视中国利用RCEP的制度平台赢得国际经贸规则制定权并顺势掌控地区主导权,因此日本仍将对RCEP的走向表示高度关注。
其次,日本也未放弃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在经贸立场上依旧追随美国立场,将美国力量留在东亚并使其在地区主导权之争中继续对日本表示支持。日本于2016年11月底突然宣称准备取消中国“特惠关税制度”待遇,12月初进而决定继续不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这种立场表态在中日两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当下是极为反常的。但倘若联系美国战略收缩的可能性来看,在美国逐渐减弱与日本的在安全上同盟联系的情况下,日本的强硬表态或许是意味着日本将试图寻找在经济上重新构建并深化日美同盟联系的新渠道。换言之,日本原本预期特朗普上台后中美之间或将爆发大规模贸易战,因此在经济领域先行站队并表明其愿继续充当美国盟友的姿态和立场,试图凭借此举维持美国对日本在东亚地区合作中的继续支持与信任。
中国与日本关于东亚地区主导权的竞争不曾停止,美国因素在东亚地区的存在无疑显著对中日制度竞争的强度与烈度有着明显的影响。需要说明的是,当前美国在东亚地区的收缩或退出,只是在减少提供地区公共物品意义上的退出,而不是完全放弃对该地区的经济红利分享与战略掌控,也并不会坐视日本在与中国的制度竞争中处于下风。因此,尽管美国战略收缩在短期内可能会使得中日制度竞争的强度和烈度有一定程度上的缓解,但美国在东亚地区主导权竞争中的存在并不会就此消失,日本也还会继续设法将中国塑造成日美共同敌人,使美国成为其制衡中国的重要而坚实的后盾。
基于当前中国实力不断增长的现实,以及美国战略收缩的可能趋势,未来中日之间开展制度竞争的方式、烈度将再次出现重大转变,东亚地区合作主导权的最终归属悬而未决。诚然,理想状态下,中日两国在围绕东亚主导地位而展开的经济外交中,有可能超越传统的权力之争的逻辑,进而在更大的共同利益与合作的基础上,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与其他地区行为体携手推进亚太地区合作,但这固然道阻且长。在未来持续进行的地区主导权之争中,中国还需保持更加开放务实的心态,灵活应对日本及美国等国发起的制度攻势,在不断提升自身适应新规则能力的同时,争取更多制度伙伴国对自身崛起与发展的支持,从而避免在国际政治经济新规则、新秩序的形成过程中落于被动、不利的境地。
[1] 黄大慧,韩爱勇.东亚地区主义研究评析[J].外交评论,2011,(3).
[2] Douglas Webber.Two Funerals and a Wedding?: The Ups and Downs of Regionalism in East Asia and Asia-Pacific after the Asian Crisis[J].The Pacific Review, Vol.14, No.3, 2001.
[3] 王玉主.亚洲区域合作的路径竞争及中国的战略选择[J].当代亚太,2010,(4).
[4] 李炯喆.宮澤内閣とアジア [Z].長崎県立大学国際情報学部研究紀要,第14号,2013.
[5] [日]添谷芳秀,田所昌幸編.日本の東アジア構造[M].慶応義塾大学出版会,2004.
[6] Deepak Nair.Regionalism in the Asia Pacific / East Asia: A Frustrated Regionalism?[J].Contemporary Southeast Asia, Vol.31, No.1, April 2009.
[7] [日]西口清胜.现代东亚经济论:奇迹、危机、地区合作[M].刘晓民译.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1.
[8] 刘翔峰.日本EPA战略及“10+6”推进计划[J].当代亚太,2007,(5).
[9] 李巍.东亚经济地区主义的终结?——制度过剩与经济整合的困境[J].当代亚太,2011,(4).
[10] [日]宗像直子.政治如何赶上市场?寻找东亚的经济区域主义[A].[美]彼得·J·卡赞斯坦,[日]白石隆编.东亚大局势:日本的角色与东亚走势[C].王星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11] 崔海宁.东亚粮食安全合作困局与中国的角色[J].外交评论,2014,(1).
[12] Akio Egawa.TPP Participation Gives Japan a Bargaining Chip in Trade Negotiations[J].Bruegel ,November 2013.http://bruegel.org/2013/11/tpp-participation-gives-japan-a-bargaining-chip-in-trade-negotiations/.
[13] 王金波.日本区域合作战略调整与国家重新定位选择[J].国际经济合作,2015,(7).
[14] 高兰.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中国、日本、东盟[J].世界经济研究,2003,(11).
[15] 「日本の対中総合戦略」研究会最終報告書『日本の対中総合戦略—「戦略的パートナーとしての中 国」登場への期待と日本の方策—』[R].PHP総合研究所,2008 ,(6).http://research.php.co.jp/research/foreign_policy/policy/data/seisaku01_teigen34_03.pdf.
[责任编辑 刘蔚然]
The Leadership in East Asian Cooperation and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Huang Dahui, Sun Yi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Japan; US;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regional leadership in East Asia
As the biggest economies in East Asia, China and Japan compete with each other via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in order to win the regional leadership. Therefore, the two countries show different preferences when making choices among various regional cooperation institutions such as “10+3” and “10+6”. To be specific, Sino-Japan relation, as well as the institutional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Japan, would intensify as the strengths gap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widens, and the involvement of US in East Asia increases. However, with the tendency of strategic contraction of US, China and Japan should work beyond the traditional competitive logic, and also develop new paths to cooperate while still competing during the process of promoting integration in East Asia.
黄大慧,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孙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