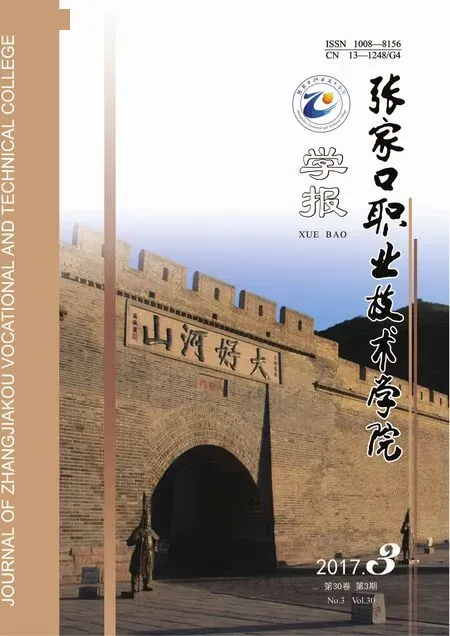《沁园春·瞬息浮生》与《梦亡妻》的对比研究
2017-01-28张晓宇
张晓宇
(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陕西 西安 710119)
《沁园春·瞬息浮生》与《梦亡妻》的对比研究
张晓宇
(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陕西 西安 710119)
在中西方诗歌史上,悼亡诗是一类不容忽视的重要的诗歌题材。中国清代词人纳兰性德所作的《沁园春· 瞬息浮生》与英国诗人约翰· 弥尔顿的《梦亡妻》作为中西方悼亡诗的代表之作,在思想主题上具有一致性,两位诗人都是因思成梦,由梦达情,用感人肺腑、诚挚哀婉的诗句寄托对亡妻深切的悲悼与思念。但由于中西方文化根源的差异,两首诗在具体内容、表现手法、感情倾向等诸多方面也存在着鲜明的差异。
悼亡诗;《沁园春·瞬息浮生》;《梦亡妻》;比较
在爱情中,死亡是最大的别离,将有情人永远拆散而毫无怜悯之心,不容反抗之力,被带走的人可怜薄命,而留下的人则要独自面对更大的悲痛与不幸,此后余生,伴随他的便是肝肠寸断的心碎与无边无尽的相思,而支撑着生者的动力,正是其积淀在内心深处的深情与痴心,只因人有生死而情无止境。
中国清代词人纳兰性德所作的《沁园春·瞬息浮生》和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的《梦亡妻》是两人在不同时空下创作的悼亡诗作,两首诗都以梦为题,由梦入情,通过描述在梦境中与亡妻相见的情景,用如泣如诉,深情哀婉的语言表达对爱人深切的怀念与追忆,将人性中最深刻最浓郁的感情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令人读之感伤悲叹,唏嘘不已。整体来看,两首诗在寄托对亡妻的深情思念以及表达沉痛悲哀的悼念之情上具有相通性,但由于中西方文化信仰等方面具有差异,两首诗中反映出的创作风格、意象选择、抒情方式、情感态度等也都具有不同之处,现来一一论述。
一、纳兰性德与《沁园春·瞬息浮生》
在中国文学史上,明末清初悼亡题材的作品日益增多,其中以纳兰性德的悼亡词尤为著名。词人纳兰性德的一生都带有传奇色彩,而在经历爱侣突然离世的沉重打击后,他原有的洒脱与豪迈都随着妻子的亡故而消逝了,最终形成了哀婉凄美的词风,其所作悼亡词一字一咽,含泪泣血,寄寓着对亡妻无尽的思念和刻骨的爱恋尤其令人称赏的是,他的悼亡词悲郁哀伤而不矫饰造作,悱恻缠绵而不刻意揉捏,字字句句皆是痛自肺腑,摧心剖肝的真实情意,朴实诚挚,悲不自禁。王国维有评:“纳兰性德以自然之眼观物,以自然之舌言情”,陈廷焯也认为:“容若词言中有物,几令人感激涕零。”当时盛传,“家家争唱饮水词,纳兰心事几人知”。
纳兰性德二十岁时,娶两广总督卢兴祖之女为妻。成婚后,二人夫妻恩爱,感情笃深,新婚生活美满更是激发他的诗词创作。但是这样幸福美满的生活仅仅持续了三年,卢氏因产后生病而亡,这给纳兰性德带来了难以承受的痛苦,并成为他心中永远的伤痛。卢氏去世三个月后的一天,词人在梦境中见到了心心念念的爱妻,梦中的卢氏淡妆素服,紧紧握着他的手,哽咽不止。词人惊醒后,虽已记不起卢氏所托之语,但却记得一向不善诗词的她,在梦中留下了两句诗:“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这样一个突如其来的梦,把本就没有痊愈的纳兰又往绝望悲凄之处狠推了一把。悲痛交加之下写出了这首《沁园春》。词中再一次回忆了他和卢氏琴瑟和谐的往日生活,也让他又一次深刻地体味了梦醒人去的孤独与悲凉之感:
“瞬息浮生,薄命如斯,低徊怎忘?记绣榻闲时,并吹红雨;雕阑曲处,同倚斜阳。梦好难留,诗残莫续,赢得更深哭一场。遗容在,只灵飙一转,未许端详。
重寻碧落茫茫,料短发,朝来定有霜。便人间天上,尘缘未断;春花秋月,触绪还伤。欲结绸缪,翻惊摇落,减尽荀衣昨日香。真无奈,倩声声邻笛,谱出回肠。”
浮生匆匆而过,瞬息即逝,人生本已短暂而妻子又红颜薄命,早早离自己而去,回思细数恩爱过往,怎么能不留恋依眷,又怎么能轻易忘却?记得当时寻常,共眠锦榻之上赏花,同倚雕栏依偎斜阳下。然而种种往事如今都化作一场难留的虚梦,梦醒之后面对未续完的残笺零句,只能更加刺痛回忆罢了,“更深哭一场”短短五字写尽了生者回忆过往、触景伤怀的痛彻心扉,足以见纳兰性情之深挚,笔力之重大。一阵朔风,爱人的音容俱逝,竟然已没有机会再细细端详。想要追随她而去,却一片茫茫找寻不得。从此天上人间,阴阳阻隔,然而在每一个曾经共同渡过的美好时刻,即便是春花与秋叶,都将触动未亡人的愁思。相思令人老,悲伤与憔悴早已使生者无复往日的风采。这时候,悠扬的笛声从临院传来,凄厉幽怨,一声声荡气回肠,让人愁怀萦绕。由此看来,“妇素未工诗”,又何以能在梦中吟唱出“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这样缠绵缱绻的诗句呢?想必这也定是纳兰代作,托付于梦境,发自于妻子之口而已。他多么期望两个人能像诗句中写的那样年年团圆,于是白日里急切而强烈的渴望入了梦来,从爱妻口中得到慰藉。词中藏而不露的难舍情深,已足令世人恻然动容。
此阕《沁园春》百字之间,词人情绪转换不停,上片述说由梦引起对往日夫妻相伴的回想与眷恋:梦遇亡人,爱人近在眼前却触不可及,想起往日两人亲密无间紧紧依偎,而今天人永隔,再无可能将对方端详,心如刀绞,悲痛断肠;下片写梦醒之后空余恨,茫然四顾,偌大世间再无爱侣,想随亡妻一同而去,却又知自己形容憔悴恐妻子伤心,况梦中都难相从,醒后更觉渺渺,徒有相思无尽,恍然间一时无我。“作者情绪轨迹至此慢慢划出平淡的弧线,在平淡中则涌动着持久而强劲的哀伤。”[1]一字一言都承载着词人内心汹涌难息的悲情与绝望。
二、约翰·弥尔顿与《梦亡妻》
《梦亡妻》是英国诗人约翰·弥尔顿的作品。弥尔顿是英国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巨人,并被评为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六大诗人之一,他的一生都在为资产阶级民主运动而奋斗,最终因积劳过度,导致双目失明。在1658年的某天,弥尔顿梦到了两年前死于难产的第二个妻子凯瑟琳。这个梦成为一个契机,令弥尔顿创作出在他个人作品中难得的温情真挚的爱情诗歌,也是英国诗史中最为著名最有影响的悼亡诗代表作。
1656年,弥尔顿与第二任妻子凯塞琳结婚,由于在此之前弥尔顿就已经完全失明,因此他一直都没有亲眼见过这位心爱的妻子。凯瑟琳性情温和善良,给弥尔顿带来极大的幸福与安慰,二人感情恩爱,生活美满。可惜好景不长,婚后15个月,他所依恋的凯塞琳不幸死于产褥热。爱人的离世给弥尔顿带来了沉重的打击,使他悲痛欲绝,久久难以释怀。两年后所作的这首诗便是描绘某一夜梦遇亡妻,醒后怅惘的情景:
“我仿佛看见了我那圣洁的亡妻,
好像从坟墓回来的阿尔雪斯蒂,
由约夫的伟大儿子送还她丈夫,
从死亡中被抢救出来,苍白而无力。
我的阿尔雪斯蒂已经洗净了产褥的污点,
按照古法规净化,保持无瑕的白璧;
因此,我也好像重新得到一度的光明,
毫无阻碍地、清楚地看见她在天堂里,
全身雪白的衣裳,跟她的心地一样纯洁,
她脸上罩着薄纱,但在我幻想的眼里,
她身上清晰地放射出爱、善和娇媚,
再也没有别的脸,比这叫人更加喜悦。
可是,啊!当她正要俯身抱我的时候,
我醒了,她逃走了,白昼又带回我的黑夜。”
诗一开始,诗人看见妻子又重新回到他的身边,百感交集的心情跃然纸上。现实中从未见过爱人的面容,因此在梦中她的样子依旧迷离恍惚,她向诗人走来,神秘的面容罩着轻纱,绰约渺渺、若即若离,但上帝仍是怜悯的,使诗人的眼睛暂时恢复光明,于是能在梦境里终于复原对妻子美好纯洁样貌的想象:她洗涤干净产褥的血污,全身穿着雪白的衣裳,如同她的心灵一样洁净无瑕。她就是光明与美丽的化身,犹如罩着光环的圣母一样,散发着爱与仁慈,善与温暖,这样一种摄人心魄的美给诗人带来了极大的愉悦与感动。正当她要俯身拥抱诗人的时候,梦境结束了。欢乐的情绪达到最高点的时候,“我醒了,她逃走了,白昼又带回我的黑夜。”有她在的黑夜也是光明快乐的白昼,而没有她陪伴的白昼才是真正漫长无边的黑夜。
诗人怀着失而复得的喜悦仔细端详了爱妻的面容和体态,想要用文字将这一次久别重逢真切的印刻下来。在诗中,对妻子形象的描写占据了大部分的篇幅,断肠柔情令人动容,超越生死的爱恋历久弥新。全诗只在最后笔锋一转,情感投放在诗人自己身上,‘我醒了’,于是妻子带来的一切美好和光明都烟消云散,触手可及的幸福戛然而止,仍旧回到了永恒的孤寂与暗夜中。值得一提的是,在诗人的梦境中,是妻子主动要俯身拥抱他,而不是自己去拥抱妻子,由此可见诗人的内心深处的脆弱,他渴望从爱人那里得到治愈的力量,梦中的重逢让诗人看到心爱之人已安睡在纯洁美好的天堂里,她的平和宁静也给自己带来一丝安慰。因而这首悼亡诗中也透出了一丝温暖积极的情调,为诗人的哀伤涂上了一层柔和的暖色水彩,给读者以哀而不伤,情致温和的感受。
三、诗歌比较
纳兰性德的《沁园春》与弥尔顿的《梦亡妻》都可以称是中西方悼亡诗中的佳作。两首诗都以梦境为切入口,描写了梦中与亡妻相见的情景,抒发了梦醒之后的惆怅与哀伤,表达了相思无尽的爱情主题,因此可以说两首诗具有某些相通之处。然而由于中西方不同宗教文化、思维方式、心理特征、表达风格等方面的渗透,两首诗在具体的诗歌内容、情感倾向、抒情方式、意象表达等角度也具有明显的差异。
(一)诗歌内容
两首诗虽然都是因诗人在梦中与亡妻重逢而有感而作,但相比较而言,《梦亡妻》倾向于记梦,而《沁园春》则更倾向于追梦。在《梦亡妻》中诗人不吝笔墨,深情地描写并赞美心爱的妻子,开篇便直奔主题,“我仿佛看见了我那圣洁的亡妻”,接着用了大量篇幅详细描述妻子的面容体态,让读者也能在他的诗中真切感受到其妻子的形象:一袭白色长袍,轻纱遮面,纯洁高雅,光芒四射,她的身上能够映衬出人间最美好的品格——仁爱、温纯、贤惠、善良,她像光明圣洁的女神一般,用仁慈怜爱的光辉温暖了她的丈夫也安慰了所有处于哀伤孤独中的人们。因此可以说,弥尔顿是有意要详细真实地记录一次梦境,并且在诗作中呈现出妻子纯洁善美近乎圣母的形象,描写细致,笔调柔和,同时也具有一定的梦幻色彩。
而在《沁园春》中,词人并没有使用过多笔墨描写妻子的容貌外形,连梦中相见的场景也近乎一笔带过,只在小序中提到“梦亡妇淡妆素服,执手哽咽,语多不复能记。但临别有云: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整体来看,词的上阕主要是在感慨和追忆,词人像是在自顾自地喃喃低语,感叹人生苦短命运无常,追念恩爱过往转眼成殇,词人以凝练细腻的笔触着重描绘了往日里夫妻二人亲密浪漫、相濡以沫的动人场景。这里不同于《梦亡妻》的是,纳兰词中的妻子虽然面容体态模糊,但她的形象是居家的平凡的,是更加生活化现实性的:她娇媚可爱,与爱侣一同闲卧绣榻;她诗意多情,能伴词人一同赏观落花;她温柔贤淑,与丈夫倚栏执手依偎斜阳下,一幕幕日常图景,当时只道是寻常,却不知是生活中最温馨幸福的沉静时光,《沁园春》中的妻子形象不是光芒万丈的女神,也不是神圣不可侵的圣母,她就是一个生活中的娴静温婉的女人,陪伴着自己的夫君,守护着自己的家庭,让人有亲切感和熟悉感。词的下阕整体是在抒发梦醒人悲的哀切与凄苦之情,诗人自述已脆弱到“春花秋月,触绪还伤。”可见纳兰之词中,着重表现由梦境引发出的无限悲情,更强调梦醒后的伤感,追怀时的痛苦。
(二)抒情方式
两首诗均为悼念亡妻,缅怀伴侣,诗歌的情感基调都是哀伤的,但比较之下,《梦亡妻》在抒发诗人梦中与梦醒后的情绪时更为直观,《沁园春》则更多的借助景物、环境来烘托诗人内心的苦闷忧愁,更为含蓄。在弥尔顿的诗中,无论是梦境中的温柔相见,还是醒后的孤独伤悲,诗人都以直抒胸臆、开口见心的方式来描述:诗歌开篇即写见到爱妻时满心的欣喜与激动,接着又不惜笔墨赞美妻子纯洁的样貌与心灵,经过前面十三行诗句的铺垫,欢乐的情绪达到最高点之时, 诗人突然在最后将前面辛苦构建起来的幸福感全部浇灭:“我醒了,她逃走了,白昼又带回我的黑夜。” 这是诗人倾其全力发出的一声哀叹。因此《梦亡妻》全诗都是诗人化泪为墨字字深情的告白,他的快乐与幸福真实可触,他的失落和悲哀也是直观而现的,正是诗人强烈而鲜明的表达才使诗歌具有极大的形象感和冲击力,让读者能够被带入其中,切身经历诗人感情的起伏落差,从而产生共鸣。
而在《沁园春》中,词人表达哀痛心情的手法则更显委婉含蓄。词中并无缠绵露骨的‘爱烈’‘情浓’字眼,唯一一句告白也是借托亡妻之口,淡朴之下却相思满溢,深厚绵远:“衔恨愿为天上月,年年犹得向郎圆。”不必言论情爱,长长久久的陪伴就弥足珍贵,也是夫妻二人最大的满足。在词中,纳兰性德也多是通过今昔对比,情景交融等手法来表现对亡妻的哀思与悲痛:从前“并吹红雨”、“同倚斜阳”而今“诗残莫续”、“未许端详”一场重逢却只能令人“赢得更深哭一场。”人间天上,再也寻不到她的身影,孤身一身留在世上,“春花秋月”、“声声邻笛”也怜悯‘我’的悲苦。因而可见,纳兰在词中虽未直接抒怀,却将剪不断的爱意幽思,道不尽的柔肠悲歌化于追忆与景物之中,把现实之事与幽冥之想揉并在一起,凄凄惨惨,悲悲切切,如断肠之曲,意蕴连绵,使人读来更觉字句之后难掩的深劲的悲哀,荡气回肠。
(三)意象选择
弥尔顿的《梦亡妻》追求一种梦幻的、古典的、神圣的美感,因而在诗歌中采用的多是想象性的意象,在引经据典时也带有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而《沁园春》则使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性意象,无论对梦境还是对现实的感叹都没有脱离现实。在《梦亡妻》中,诗人引用了希腊神话中的典故:“好像从坟墓回来的阿尔雪斯蒂,由约夫的伟大儿子送还她丈夫。”“阿尔雪斯蒂”是英雄阿德墨托斯的妻子,以忠贞著称。两人在阿波罗的帮助下结成眷属,十分相爱。后来阿德墨托斯被判定天亡,阿波罗又劝求命运女神,如有替死则可延年,其妻愿为替死。最终,英雄赫拉克勒斯在墓前与死神搏斗,将阿尔雪斯蒂从冥府带回了人间,还给了阿德墨托斯。弥尔顿用类比的方式描述他的妻子同神话人物一样,在天神的庇佑下又神奇地“从死亡中被抢救出来”,并且在梦中妻子是由远及近款款而来的,就如圣母下凡一般,因而全诗在一开始便通过典故烘托出了一种浪漫、想象的意境。此外,“我的阿尔雪斯蒂已经洗净了产褥的污点,按照古法规净化,保持无瑕的白璧”诗中还运用了希伯来法典中的“洗净礼”这一典故,爱妻不仅是从死神手中得以复生,也是生产之后的新生。按照古法洗净了人世的污秽与伤痛,净化为无瑕的白璧光彩夺目,纯洁神圣。诗中更有“光明”、“天堂”、“雪白的衣裳”、“罩着薄纱”、“爱、善和娇媚”等积极意象都体现出鲜明的宗教特征,在诗的最后,妻子正要拥抱诗人时,梦境突然结束,可见在诗人心中,妻子已经成为一个光环式的形象,不仅在肉体上是纯洁的,在精神上也是圣洁的,她在天堂散发着仁爱与善美的光辉,像圣母一样前来抚慰诗人的孤寂与哀伤,诗人对她带有崇仰与敬畏的感情。
而在《沁园春》中则包含更多的现实意象和生活色彩。在梦中相见时,妻子执手哽咽,嘱托哭诉,依旧是生活中亲密相近,体贴温良的爱人,并没有像《梦亡妻》中一样上升到神女的身份,她让词人亲切熟悉,而不包含崇拜的情感。在追忆过去时,词人描述的也是具体的生活片段,无论是过节赏花,还是倚栏观霞,这些琐碎生活化的意象都是现实中真实发生过的事,具有鲜明的现实性。因而将过往与现实进行对比,更加能烘托出词人物是人非的痛苦与凄凉。此外,在抒发梦醒后的感慨时,词人也是真实地再现了自己的身心状态,即使提到“重寻碧落茫茫”,也立刻想到现实情况是“料短发,朝来定有霜。”与苏轼《江城子》中“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有异曲同工之妙,终究还是从美好的幻想回归到残酷的现实中来。更有残诗、春花、秋月、邻笛等幽怨伤逝的现实景物意象为全诗渲染哀伤愁苦的气氛,寄托词人镂骨铭心、魂牵梦绕的追念之情。
(四)情感倾向
由上述可知,《梦亡妻》中以记梦的形式,将爱妻塑造为纯洁安详的圣母形象,在诗中表现出与爱妻重逢的喜悦心情,全诗多用积极意象来烘托光明温暖的意境,因此诗歌在反映诗人孤独迷茫的感情的同时,还流露出了一种平静、一份明朗和一线希望,让人读来哀而不伤;《沁园春》中则侧重追梦,在上阕将往日欢愉与残酷现实对照,下阕以悲凄景物衬托哀情,通篇冠以浓重的悲哀情绪和灰暗格调,哽噎难鸣、凄绝缠绵。
这与中西方的宗教文化有密切关联,体现出中西方生死观的差异性。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对于生死的谈论一直比较避讳,并将死亡看作一种不洁和不幸。“儒家学派对于生死的基本观点是‘未知生,焉知死?’‘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它强调的是人的生前,而非死后”[2],即认为人应当着重在生前努力,充实生活,而不必追问挂念死后的事,因为人的命数皆由天定而非人为能控制。一旦谈及死亡,人们都会流露出‘贪生’的愿望,是因为更渴望享受现世的幸福,而对死后的归属尚未可知,因此恐惧和排斥。当死亡的事实降临时,生者会难以接受,往往沉浸在痛苦孤独的悲伤境界里。而在西方,由于受到基督教教义的深刻影响,人们会把死亡视为某种新生或是苦难解脱,人死之后灵魂会升入天堂皈依天父,并以另一种方式继续生存,甚至得以永生,因此西方人对死亡的态度多是从容坦然的,对于逝世的亲人好友,生者也多是将悲痛与祈祷相结合,或者说是通过信仰的力量消解个人的哀痛,以相对来说更乐观更积极的心态面对现实。
综上,中西方不同的文化根源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也就具有明显不同的情感倾向。《沁园春》中着力描写亡妻生前与词人的恩爱情景,并以大量笔墨抒发对于生死离别的痛苦与伤感,传达出沉痛的哀悼之情,格调悲凄绝望,读之锥心泣血、催人心肝。同时它也代表了我国古代传统悼亡诗作的情感特点:强调追忆亡人生前的音容笑貌与生活情景,并倾向于将悲痛之情寄寓在凄凉的景物意象上,通过表现内心思想与客观世界的剧烈冲突来宣泄难以压抑的悲伤情绪。因此中国悼亡诗多通篇冠以浓重的悲哀色彩,感情悲切沉重、沉滞凄苦。而在《梦亡妻》中,诗人有意将爱妻塑造为在天堂中得到平和与安宁的天使般的形象,虽然她离开了人世间,但能在另一个世界得到了新生,仍然散发着爱与善,“可以看出诗人在内心深处祈求亡妻的灵魂得救成为圣徒的愿望,这一愿望在梦境中得到了实现,诗人因此感到莫大的释怀与安慰,”[3]可以说,全诗对梦境的描写都贯以一种喜悦幸福的情绪,最后在诗尾返回到现实的哀伤中,但总体上来说,诗歌的整体氛围是轻盈的,传达的感情也是悲中有慰、绝望中蕴育希望。正是宗教文化的启示,使得西方悼亡诗作相较而言更加超然旷达,把伤痛化作祈祷,把绝望转化为希望,把死亡看作新生的开端,从而在诗歌中表现出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情致相较于中国悼亡诗来说也更加温和、超脱。
结语
以上所述,分别从诗歌本身、主题内容、抒情方式、意象选择、感情倾向等方面探讨了两首诗各自的风格特点,对比其之间的差异。
《沁园春》一词写梦遇亡妻,并不是为写梦中之喜,而是为了抒发醒来之悲,它的总体基调是暗色,凄美伤感。纳兰性德用真挚深情、凄绝缠绵的诗句悼念爱妻,就如用尽心力创作了一曲柔肠悲歌,哽噎难鸣、欲哭无调,读来荡气回肠,久久悲伤。
《梦亡妻》则浸染在一种安详恬静的宗教气氛之中,它着力在写梦中相见的喜悦与欢乐,梦醒后虽怅惘孤寂,可因为有了梦中爱妻的鼓励与安抚,诗人对人生就仍会充满希望,全诗的总体基调则是亮色,悲中有慰,哀而不伤。诗人化悲痛为力量,在诗歌中传达出积极的态度导向,令世人相信生死不可抵挡,爱情同样。
[1]王喆.《梦亡妻》的情节与思想[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9(7):63.
[2]吴卫穷.从“未知生,焉知死”浅析孔子的生死观[J].学理论,2013(9):50.
[3]张丽娟,王旻.中国悼亡诗与西方挽歌诗之美学比较[J].Sino-US English Teaching ,2007(4):80.
AComparativeStudyof“InstantFloatingLife-totheTuneofQinyuanchun”and“OnHisDeceasedWife”
ZHANG Xiao-yu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119)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poetry, mourning poems is an important poetic subject that cannot be ignored. The "Instant Floating Life- to the tune of Qinyuanchun" by the Qing Dynasty poet Nalanxingde and the poet John Milton's "On his Deceased Wife" are regarded as the representative of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mourning poems. They are consistent with each other in terms of the ideological theme. The two poets began with dreams, and expressed their mourning and yearning through sincere and moving poetry. However, because of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there are also distinct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oems in their specific content, expression, emotional tendency and many other aspects.
mourning poems; Instant Floating Life-to the Tune of Qinyuanchun; On His Deceased Wife; comparison
I0-03
A
1008-8156(2017)03-0060-04
2017-06-11
2017-07-16
张晓宇(1993-),女,河北张家口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2016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语文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