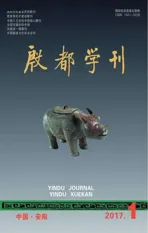杜甫中原情结探讨
2017-01-28谢其泉
谢其泉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1〕
杜甫中原情结探讨
谢其泉
(河南广播电视大学,河南 郑州 450001〕
“不敢忘本,不敢违仁”的诗圣杜甫在其诗歌中流露出其对中原故土的乡土“情结”,这是古代传统农耕文明中“叶落归根”思想的体现,亦是中原农耕文化影响诗人创作心态的一个剖面。本文结合诗人漫游经历及其诗歌创作探究杜甫的中原情结,并蠡测杜甫中原情结产生的原因有二:一是中原地区农耕文明的影响;二是诗人生活虽颠沛流离,但其内心始终充满“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使命感。
杜甫;乡土情节;中原;诗歌
杜甫于唐玄宗先天元年(712年)出生于河南巩县,在其“俱游梁宋”“归筑陆浑庄”以及“漂泊西南”等重要人生经历中对生养他的中原地区再三致意,不仅如此,在其他杜诗中亦流露出他对中原地区的乡土“情结”。
一
盛唐时期,士人颇重出游,这固然与当时安定繁荣的经济社会是分不开的,亦与当时士人阶层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息息相关。如李白、孟浩然等在游历期间留有脍炙人口的诗篇。杜甫也有着丰富的漫游经历,“吴越之行”开阔了眼界,“放荡齐赵”拓宽了心胸,与李白、高适的“俱游梁宋”是生逢知己,也成就了诗坛上的一段佳话。天宝三载,杜甫与李白在东都洛阳初次相遇,后来,李杜二人相约“俱游梁宋”,并在汶上邂逅高适。三人在梁宋两地游历,互有唱和,不亦乐乎。杜甫有《赠李白》诗:“二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李侯金闺彦,脱身事幽讨。亦有梁宋游,方期拾瑶草。”[1](P41-42)此诗作于天宝三载,李杜在东都的相逢,使杜甫对“东都”印象深刻。《新唐书·地理志》记载东都隋初设置,武德中期废,贞观六年称洛阳宫,显庆二年又称东都,武则天时期号神都,中宗李显复位,神龙元年复称东都,玄宗在位日久,或称东都,或称东京,“二年客东都”一句道出东都在隋唐之际存废的历史,显示出了诗人对中原风物的关注。
李、杜、高三人共游梁宋在杜甫看来也是人生之快事。《遣怀》就描写了他与高适、李白等人在此间游赏之事:“昔我游宋中,惟梁孝王都。名今陈留亚,剧则贝魏俱……忆与高李辈,论交入酒垆。两公壮藻思,得我色敷腴。气酣登吹台,怀古视平芜。芒砀云一去,雁鹜空相呼。”[1](P1747-1748)仇兆鳌在注疏此诗说:“此叙高、李同游之兴。三人相得,成千古文章知己。芒砀云去,汉高遗迹难寻也。《杜臆》云此可见其旷怀。”[1]同上可游之地到处有,同游知己无处寻,诗人间这种真诚地交往与切磋,同时对中原风物“芒砀山”、“吹台”等亦投以相应的关注。从杜甫在漫游创作中对诸多中原景观以及风物的关注,可以看出诗人对中原大地是充满感情的。后人在研读这些诗歌作品,或在观赏这些风物时,也会自然而然地联想起千百年前曾经饱含感情吟诵这些诗歌的诗圣。
漫游没有抛却乡土情思,在外漂泊反而加剧了对故园的依恋。安史之乱爆发,杜甫流离颠沛,无论是入蜀,还是沿江漂泊频遭冷遇。例如客居夔州时,《最能行》说“此乡之人气量窄,误竞南风疏北客。”[1](P1556)(仇兆鳌说此因人情淡薄,而致激励之语),“形胜有余风土恶[1](P1558)”(仇注《峡中览物》说此在峡而思乡也)。客居公安时,《久客》又云“羁旅知交态,淹留见俗情[1](P2344)。”流落异地方知世俗之情,漂泊他乡才能洞察世态炎凉,这种地域间人情之差异更加剧了杜甫对中原家乡的思念。[2](P83)
开元二十三、四年间(738年)至二十九年(741年),杜甫开始了第二次漫游。漫游齐鲁回到家乡后,在首阳山下(今洛阳市区东侧、偃师市西北二十五里)修筑新居号为陆浑庄。天宝七年(748年),宰相韦嗣立之孙韦济新任河南尹,慕杜甫诗名,多次去陆浑寻访。杜甫此时身在长安,于是作《奉寄河南韦尹丈人》诗感谢韦府尹探访:“甫故庐在偃师,承韦公频有访问,故有下句……尸乡徐土室,谁话祝鸡翁?”[1](P85)尸乡土室用的是刘向《列仙传·祝鸡翁》的典故,字面指他修葺于偃师的土庐,实希望得到韦济的汲引而步入仕途。乾元元年(758年)冬末,诗人从华州司功任回土庐小住探望亲友,二年春作《忆弟二首》可印证,其注云:“时归在河南陆浑庄。”[1](P617)大历年间杜甫流寓川湘,无力回乡故时常怀念故居,便托回东都的孟仓曹捎信给故人(《凭孟仓曹将书觅土娄旧庄》):“平居丧乱后,不到洛阳岑……十载江湖客,茫茫迟暮心。”[1](P2130)“洛阳岑”与“土娄旧庄”相映照,仇兆鳌用《杜臆》解尾联的“迟暮心”说“盖有首丘之思”。[1](P2130)“尸乡土室”、“河南陆浑庄”、“土娄旧庄”,都指一个地方,就是杜甫恋恋不舍的在中原的家园。[3]
盛世志四方,乱世思故园。杜甫中年时期,恰逢安史之乱爆发,大唐王朝迅速由盛转衰,杜甫也在乱世中颠沛流离,这时候对故园的思念在诗中表现的尤为明显。至德二年初(757年),唐军在回鹘军队的帮助下收复京师长安、重镇洛阳,杜甫千里跋涉,到长安追随肃宗,被任命为有清望京官之称的左拾遗,杜甫颇为振奋,可惜好景不长,很快又因为直言切谏惹怒肃宗,被贬为华州司功参军。在贬谪后他回到洛阳,探望遭遇战乱的故旧,第二年春,经新安、石壕返华州住所,这是他生涯中最后一次中原之行。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关注,对故土的深沉依恋,对亲友的至诚情感,使他对战乱之后的中原现实观察特别敏锐,忧家忧国的感情更加热切且溢于言表。
陆游曾吟“位卑未敢忘忧国”,杜甫忠贞耿直,且官小不畏忤龙颜。《新唐书·文艺传》载杜甫“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书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杂问。”[4](P5737)仅在他拜左拾遗短短一月任上,就由于抗疏救房琯,犯颜直谏而惹恼了肃宗获罪。一个人位高权重时,难免会有趋炎附势之徒争相结好,一旦失势,树倒猢狲散,由门庭若市迅速转为门可罗雀。房琯是偃师人,杜甫与之交于布衣,房琯为相时,杜甫也未飞黄腾达,而恰是在房琯兵败加之私匿董庭兰获罪时,杜甫仗义执言,冒着获罪危险替房琯辩护,除了谏臣耿介精神之外,应该还有一股浓浓的乡情渗透在里面。
郑虔,荥阳人,青年与杜甫就已是挚友。“伪授虔水部郎中……贼平,与张通、王维并囚宣阳里。”[3](P5766)所以杜甫认为他是冤枉的“白发千茎雪,丹心一寸灰。”[1](P422)最终朝廷还是判郑虔有罪,贬到台州。时为左拾遗杜甫便愤愤不平,朋友落难不躲不避,还为其辩护写诗《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郑公樗散鬓成丝,酒后常称老画师。万里伤心严谴日,百年垂死中兴时……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1](P515-516)郑虔遭贬,众人疏离,只有杜甫念念不忘,用血泪写成文字为之鸣冤,所以《杜诗镜诠》引卢德水评论此诗:“万转千回,清空一气,纯是泪点,都无墨痕”,[5](P173)顾宸感叹道:“古人不以成败论人,不以急难负友,其交谊真可泣鬼神”。[1](P517)
二
杜甫在创作中经常自觉不自觉地加入一些家乡元素,将故乡典故、人物,甚至方言俗语直接写入诗中。如乾元元年(758年)暮春作于长安的《得舍弟消息》中写道“风吹紫荆树,色与春庭暮。花落辞故枝,风回返无处。”这里的“紫荆树”用的是《续齐谐记》“紫荆传芳”的典故。民间流传河南府一带的豪门田氏家族有田广、田真、田庆兄弟三人,打算分散家财,当夜其庭院中的三棵紫荆树就枯萎了,田氏兄弟感慨万千,决定合家,而紫荆树也随即恢复往日繁荣。这个故事便发生在杜甫的家乡巩义,在巩义孝义镇广土山有块大石碑刻着“汉田真故里”五个大字,孝义大王沟西门上刻有“三田遗风”匾额,孝义和义沟岭上还有田真墓,这个被演绎成兄弟间重情重义的传说,至今仍在巩义广为流传。在这里,“紫荆树”是兄弟情义的象征,既表达了对兄弟天涯相隔的深切思念,也是杜甫对故乡萦绕不去的眷恋。
大历二年(767年)作于夔州的《送孟十二仓曹赴东京选》:“秋风楚竹冷,夜雪巩梅春。”[1](P2129)身在异国他乡的杜甫,深深感受到“楚竹”的寒冷,而能慰藉他的,只有家乡的梅花所预示的春天。《别唐十五诫因寄礼部贾侍郎》:“子负经济才,天门郁嵯峨。飘飘适东周,来往若崩波”。[1](P1444)司马贞《史记索隐》云:“西周,河南也。东周,巩也。”[6](P160)高诱注:“西周王城,今河南。东周成周,故洛阳之地。”[5](P160)这里的“东周”,指的正是唐东都河南府的巩洛故土。中原地区的地名、山、水如巩、东周、三川、河洛、嵩山、邙山、黄河、伊洛等字眼在杜诗大量出现不是单纯的地名,它们表达的是杜甫对中原故土浓烈的思念。
至德二载(757年) 闰八月,杜甫离开凤翔前往羌村,于途中作《晚行口号》:“三川不可到,归路晚山稠。落雁浮寒水,饥乌集戍楼。市朝今日异,丧乱几时休,远愧梁江总,还家尚黑头。”[1](P466)“口号”诗是随口吟成的诗歌短章,这首小诗前四句描写的是晚行途中所见之景:大军新败之余,路上行人少、戍卒稀,落雁饥乌,借景抒情,抒发身世之凄凉、思乡之浓情,最后四句借名南朝陈大臣、文学家江总流离在外十余年典故自喻,表达了目前虽遭流落之苦,还家有时的希冀。
天宝十四年(755年)冬作于长安的《后出塞五首》有:“坐见幽州骑,长驱河洛昏”。[1](P356)当时,安史叛军侵入大唐腹心河洛地区,连下长安、洛阳,作者用玄宗年间应募赴军到被迫脱逃的老兵之视角,深刻披露了天宝之变,安史叛乱的历史真相。《咏怀二首》作于大历四年(769年)春,自潭州(今长沙)至衡阳的舟中:“河洛化为血,公侯草间啼。”[1](P356)此诗是杜甫病逝前半年左右所作,词句间追述玄宗天宝年间因主昏臣佞,叛乱四起百姓流离失所的情景,写的是羁旅异地,有家难归,壮志难酬的仁人志士内心真实情感。
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自道:“王父某,名依艺,皇朝监察御史、洛州巩县令。”[1](P2696)结合杜文可知杜甫曾祖父(王父)杜依艺任巩县令开始定居洛州,依艺以降,杜氏一族诗中的故乡就囊括了唐代的河南府(属于河洛中心)的洛、洛下、洛州、洛阳、洛城、京洛等地。《北征》是至德二载(757年)秋所作,诗曰:“伊洛指掌收,西京不足拔。”[1](P489)是时,唐军虽勉力抗衡叛军却因房琯用人不当在陈涛斜附近一败再败,琯以宰相之尊被唐肃宗疏远罢为太子少师,杜甫因数次上疏辩护,触怒天子下三司问罪遭到贬官,被要求还鄜州(今陕西富县) 省家。这首五言古体长诗用140句700字的鸿篇巨制记录了杜甫被遣返鄜州探亲途中与到家后的亲身见闻,以描写遭安史之乱国家混乱、民生凋敝的情景为主,突出了对国家形势的关切,反映了当时人民群众早日打败叛军,过上平静生活的热烈情绪和殷切愿望,诗人心灵深处忧国忧民和牵挂故乡的情怀溢于纸表。
《闻官军收河南河北》,作于梓州(今四川三台)广德元年(763年)春,安史叛军首领史朝义兵败自杀,其手下大将李怀仙割其首级献给代宗,部属陆续反正降唐,失陷八年的幽冀名义上回归了朝廷。“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1](P1171)杜甫用涕泪满裳、漫卷诗书、放歌纵酒等迥异于常态的系列动作将初闻官军收复故乡,战乱平息刹那间的狂喜之态、欲歌欲哭之场景,写得惟妙惟肖活跃地显现在纸上,清代蒲起龙《读杜心解》说此诗“生平第一首快诗也。”[7](P628)
广德二年(764年)冬至稍后作的《至后》:“冬至至后日初长,远在剑南思洛阳。青袍白马有何意?金谷铜驼非故乡。”[1](P1449)此诗写身在剑南成都严武幕府,却思念家乡、亲友之情。当时杜甫应剑南节度使严武邀请担任检校工部员外郎、节度参谋(均属闲职、低品级官员),忙于应付幕府琐碎公文,“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之志不得伸,想离蜀回中原探访遭遇战乱的金谷园、铜驼街的愿望,一时又难以实现,只好借写诗咏怀,排遣苦闷。此诗为七律拗体,突出表达了诗人眷恋家园和怀念兄弟的真挚感情。
大历二年(767年)作于夔州的《熟食日示宗文宗武》:“松柏邙山路,风花白帝城。”[1](P1955)杜甫已近天命之年,此诗中痼疾缠身,衰老、贫病交加,恐时日无多,还乡祭扫祖不知何日的悲凉之情溢于言表。
杜甫不仅屡次提及出现关涉故乡的“元素”,还在一些诗句中直言对故乡的思念。乾元元年(758年)暮春作于长安的《送贾阁老出汝州》有“艰难归故里,去住损春心”,[1](P539)时杜甫任左拾遗。贾阁老,玄宗末年任中书舍人的贾至,遭肃宗近臣排挤,被贬汝州(今属河南)。为贾至写诗送行,不由使身在长安的杜甫思念故乡,肝肠寸断。
《观安西兵过赴关中待命二首》之二“奇兵不在众,万马救中原。”[1](P594)乾元元年(758年) 秋作于华州,杜甫见到怀州刺史、西北庭行营节度使李嗣业忠义智勇,所属军队军纪严明,深感中原家乡的人民脱离苦海有望,写诗以示鼓励。
《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之一:“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1](P837)乾元二年(759年) 十一月作于同谷县。诗人应邀携家带口投奔同谷县令,同谷令却因杜甫弃官职穷困潦倒避而不见。万般无奈杜甫带领家人在山谷中结庐以避风雪,血泪相和的长诗真实形象地记录了诗人一家困居同谷适逢隆冬,食不裹果腹,衣不蔽体,饥寒交迫的悲惨遭遇,因战乱而远离故园,对家乡对弟妹的刻骨思念。
乾元二年(759年) 十二月,到达成都作《成都府》:“但逢新人民,未卜见故乡。”[1](P874)写的是诗人带领全家经过艰苦的长途跋涉到达富庶繁华的成都的欣喜,反衬失陷于安史叛军的中原局面的令人心忧,思念遥远故乡之情更浓。
上元元年(760年)秋末,《蜀州送韩十四回乡》:“此别应须各努力,故乡犹恐未同归。”[1](P1004)表现了作者对朋友不舍的情感,盼望有一天能回到巩洛与他在故乡重逢。广德二年(764年)春的《泛江》:“故国流清渭,如今花正多。”[1](P1302)前半章极写宴饮之乐,后半章写长歌当哭,忧乱乡思的悲情。以乐景写哀情,来衬托诗人的因思乡之切而忧思愁苦的心情。
大历四年(769年) 春作于潭州的《清明二首》之二:“此身漂泊苦西东,右臂偏枯半耳聋。寂寂系舟双下泪,悠悠伏枕左书空。”[1](P2378)写诗人长年漂泊,寂寞病残,更思念家乡。
同年,杜甫买舟北归,不料羁旅久病入膏肓,自知病将不起,改由长沙赴岳阳,投奔流落当地的旧日僚友,作《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奉呈湖南亲友》“故国悲寒望,群云惨岁阴……书信中原阔,干戈北斗深。”[1](P2533-2538)奉呈湖南亲友,目的在于诗代讣托孤托葬。诗成不久,杜甫便病死在破船上,故仇兆鳌认为杜甫的绝笔诗。
由上可见,杜甫作于中年以及中年以后的诗,以诗史的方式记录了人生的窘迫与家国的风雨,在这种情况下,杜甫对故乡的认知也饱含着对家国的同情与热爱。同时,杜诗之“沉郁顿挫”风格也逐渐形成。毋庸讳言,杜诗中的中原“元素”在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过程中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关于杜诗中原情结对杜诗风格的影响,笔者拟另著文探讨。
三
杜甫中原情结的生成,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说,与以种植业为核心的农业民族对土地的高度依赖有关。韩成武《论杜甫的乡土情结》[2]认为土地对于传统的农耕民族来说有极为重要的意义。从周朝开始,便有了天子祭祀先农且躬耕田亩的象征性活动,这在当时具有极高的政治意义。天子分封土地建立藩国时举行隆重的仪式:用白色的茅草裹着社坛上的泥土交给被封者,寓意将权力授予被封的诸侯,就是所谓的“列土分茅”。统治者普遍认为土地是巩固政权的保障,是权力的象征,是国家兴亡、人民幸福的核心依托,农民有了土地种植就可以生存繁衍,失去土地就等于死亡。这种对于土地的高度依赖感,使得传统汉民族普遍具有安土重迁的情结。
杜甫的故乡河洛地区,正是以农耕经济、农耕文化为根基的儒家文化的发祥地。儒家“务本博学,经世致用”的思想理念[2]也深深地影响着杜甫。《秋行官张望督促东渚耗稻向毕》诗中提到“谷者命之本”,[1](P2006)《述古三首·其二》诗中指出“所务谷为本”,[1](P1235)认为土地是生产生活资料的来源,农业是保全生命和延续后代的根本,是人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战火绵延不熄,农田荒芜,他希望“化干戈为农具”,大声疾呼: “焉得铸甲作农器,一寸荒田牛得耕”[1](P1235)(《蚕谷行》)、“销兵铸农器,古今岁方宁”[1](P2043)(《奉酬薛十二丈判官》)。他关心天气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洗兵行》感叹关中大旱农民无法播种:“田家望望惜雨干,布谷处处催春种。”[1](P630)代宗初年两川冬旱无雪,四月喜雨降临作《大雨》“西蜀冬不雪,春农尚嗷嗷”。[1](P1097)字里行间无处不表现杜甫对农业生产的高度关注,正体现了农耕文化对他的深深影响。
其次,诗人内心始终充满“奉儒守官,未坠素业”的使命感。杜甫在《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志》里曾十分自豪的提到家族源远流长的历史:“远自周室,迄于圣代,传之以仁义礼智信,列之以公侯伯子男。”[1](P2696)杜氏一族,源于帝尧,始于杜康,盛于杜伯。杜甫的十三世祖杜预,作为朝廷柱石一代名将,战功卓著;作为经学大师,所撰《春秋左氏传集解》为十三经之一,为后世士子必读之经典,堪称 “立功立言立德”三不朽的典范。杜甫在《祭远祖当阳君文》对杜预进行了高度的颂扬,这是他自幼崇敬的“偶像”。杜甫的祖父杜审言,也是杜甫引以为豪的先人,他与李峤、崔融、苏味道并称“文章四友”,与沈佺期、宋之问互相唱和,揣摩诗律,对近体诗的确立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初唐诗坛有极高声誉。[8](P78-79)杜审言在政治上也颇得武则天赏识,累官修文馆直学士。这种诗书传家、礼义立世的优良家族传统,是杜甫内心的骄傲,同时也赋予了他神圣的使命。他在《进雕赋表》中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1](P2631)这样的家族使命感,让中原故土在他心中有了更为独特的意义,那不仅日夜思念的温暖家园,也是他精神的重要的支柱。
总的来说,杜甫在其诗歌中流露出的“中原情结”,反应了古代农耕文明对诗歌创作的一种渗透,这种影响在杜甫的身上体现的如此明显,而成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文学现象。同时这也是我们深入了解杜甫内心世界的一个重要视角,中原这片土地,是流淌在杜甫血脉里、纠缠在杜甫灵魂里的挥之不去的影子,它是这样的鲜明,这样的热切,这样的深厚,他已经是杜甫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1]本文所引杜甫诗文皆用[唐]杜甫著,[清]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2]韩成武: 论杜甫的乡土情结[J].河北学刊,2013,(3).
[3]霍松林: 杜甫与偃师[J].河东学刊,1999,(2).
[4][宋]欧阳修、宋祁: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5][清]杨伦笺注:杜诗镜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
[6][汉]司马迁撰,[宋]裴骃集解,[唐]司马贞索引,张守节正义: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7][清]蒲起龙:读杜心解[M].北京:中华书局,1977.
[责任编辑:舟舵]
2016-12-08
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青年项目“杜甫家园情结研究”(2016—QN—224)
谢其泉(1984-),男,河南商城人,河南广播电视大学人文学院教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文献研究。
I206
A
1001-0238(2017)01-0088-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