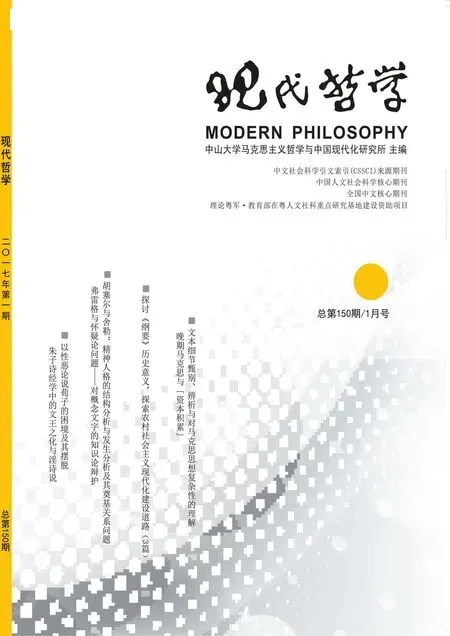朱子诗经学中的文王之化与淫诗说
2017-01-28黄少微
黄少微
朱子诗经学中的文王之化与淫诗说
黄少微
朱子以文王之化解说“二南”,又以淫诗说审视“郑卫之风”,其背后均通向圣人之学。具体而言,朱子通过“生有圣德”、后人追述称王、以“理”解“天”回应文王受命说等方式,在其诗经学体系中塑造了文王的圣人形象,并作为学之典范,且认为文王之化使“二南”之人均得性情之正。相较之下,未被文王之化的“郑卫”,旧俗未革,故多淫诗。朱子分别从作者定位、“止乎礼义”之义及雅郑邪正之辨等方面审视淫诗于学者之影响,其批驳之旨乃为使读者保持对淫诗的警省,从而得以端正性情,并通向圣人之学。
朱子诗经学;文王之化;淫诗说;圣人之学
文王之化与淫诗说是朱子诗经学中较有争论且突出的观点。在朱子看来,周、召二地因被文王之化,故均革其旧俗,其人亦得性情之正;“郑卫”之地未被文王之化,旧俗未改,多淫风,故多淫诗。然较《毛传》《郑笺》,毛郑并未如朱子般在解《诗》过程中着力彰显文王之化,也未在变风中突显淫诗于学者的影响。朱子为何努力彰显文王、批驳淫诗?这两个问题下文即一一辨析。
一、圣人:文王的形象建构
《诗经》里有关文王的记载,主要集中于 “二南”及《雅》《颂》诸篇。关于文王的论争,主要集中于文王在世时是否称王的问题,这既是许多经学家在改朝换代的政治生活中所须的问题,因它涉及王朝创立和存在的正当性与合理性,也是如何看待教化的正当性问题。《诗经》中“二雅”“二南”的记载均或显或隐与文王相关,在朱子的解释中,文王之位的突出和彰显颇费心力。
《诗集传·关雎》开篇:“周之文王,生有圣德,又得圣女姒氏以为之配。”*[宋]朱熹注、王华宝整理:《诗集传》,南京:凤凰出版社,2007年,第2页。“生有圣德”,是朱子对于周文王的定位与评价。周文王是圣王,自也是圣人。在程朱一脉里,圣人既是先觉者,更是无过之人,朱子称:“圣人生知安行,固无积累之渐,然其心未尝自谓已至此也。是其日用之间,必有独觉其进而人不及知者。”*[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55页。因此周文王自也是无过之人,那么,在朱子的解《诗》系统中,周文王在世时定不会称王,也不当称王(若周文王在世时称王,则为僭位,便不能称之为圣,程朱一脉又认为圣人无过),因而与文王相关的诸诗篇中,朱子不得不处处回护这一问题,煞费苦心。
《诗序》云:“《关雎》,后妃之德也。”《诗序辨说》(下简称《辨说》)曰:“后妃,文王之妃太姒也。天子之妃曰后。近世诸儒多辨文王未尝称王,则大姒亦未尝称后,《序》者盖追述之,亦未害也。”*[宋]朱熹:《诗序辨说》,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5页。“《序》者盖追述之”,将文王称王的问题化解为后人之追述,这是朱子的巧妙安排。既然文王称王是后世所追述,那么《大雅》言及文王的诸诗篇,其创作年代也当在文王之后。朱子确实也如此看待。如郑玄《诗谱》所列,《大雅·文王》篇是文王之诗(文王之时或与文王相关),而在《诗集传》,朱子首先标明:“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皆由于此,以戒成王。”*[宋]朱熹注、王华宝整理:《诗集传》,第204页。将《文王》定位为成王、周公时代的诗篇。或是朱子为确证文王王号为追述之观点的有效性,《诗集传·文王》篇又引《春秋传》“天王追命诸侯之词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宋]朱熹注、王华宝整理:《诗集传》,第204页。证之。依此,则《雅》《颂》中涉及周文王的诗篇的产生年代也均须重新确认,故朱子作两种努力:
其一,将《雅》《颂》诗篇的产生年代都推至文武之后。《诗集传序》言:“若夫《雅》、《颂》之篇,则皆成周之世,朝延效庙乐歌之辞。”*[宋]朱熹:《诗集传序》,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第351页。此处“成周之世”,指成王、周公时代,而非文、武时代。朱子多将《大雅》可能产生于文王时代的诸诗篇,定位为后人的追述,如《诗集传·大明》所注:“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诗。”《绵》亦云:“此亦周公戒成王之诗,追述太王始迁岐周以开王业,而文王因之以受天命也。”*[宋]朱熹注、王华宝整理:《诗集传》,第207、209页。其二,《雅》《颂》对“天子”的指代范围扩大,泛指周王。如《小雅·出车》,《序》云:“《出车》,劳还役也。”《辨说》曰:“同上诗。所谓天子,所谓王命,皆周王耳。”*所谓“同上诗”者,应指《采薇》的辨说。《采薇》篇,《序》云:“遣戍役也。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率遣戍役以守中国。”《辨说》云:“此未必文王之诗。‘以天子之命’者,衍说也。”参见[宋]朱熹:《诗序辨说》,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第382页。
因《文王》诸诗之文王称号都是后人所追述,那么对于《诗大序》两次提及的“先王”,朱子当另作解释。《诗大序》言:“先王以是经夫妇,成孝敬,厚人伦,美教化,移风俗。”朱子注曰:“先王,指文、武、周公、成王。”*[宋]朱熹:《诗序辨说》,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第343页。《诗大序》又言:“《鹊巢》、《驺虞》之德,诸侯之风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系之召公。”朱子又注:“先王,即文王也。旧说以为大王、王季,误矣。”*[宋]朱熹:《诗序辨说》,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第356页。“旧说”应指郑玄、孔颖达一派。此处,郑玄注:“先王,斥大王、王季。”*[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龚抗云等整理:《毛诗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23页。郑玄将“先王”指向大王、王季,周文王的祖父和父亲,既称自己祖父为王,则周文王在世时即已称王。朱子将“先王”指向文王本人,甚至周公、成王,则文王在世时并未称王。
这些都是朱子在重重维护文王在世未称王的努力。除了从后人追述和重解“先王”指称两方面澄清文王未称王的问题,朱子还亟须回应文王如何受命的大问题。朱子对这一回答来得更巧妙,其回应不仅将文王的圣德彰显囊括进自己的理学体系中,同时还从思想的根源上确立了文王的圣王形象。
《诗序》云:“《文王》,文王受命作周也。”《笺》曰:“受命,受天命而王天下,制立周邦。”《孔疏》:“此述文王为天子,故为受天命也。”*[汉]毛亨传、[汉]郑玄笺、[唐]孔颖达疏、龚抗云等整理:《毛诗正义》,第1114页。郑、孔二人明确指出,此处所言“命”指“天命”,则周文王乃受天命称王为天子。朱子显然不同意此说。因而,《辨说》辨之:
受命,受天命也。作周,造周室也。文王之德,上当天心,下为天下所归往,三分天下而有其二,则已受命而作周矣。武王继之,遂有天下,亦卒文王之功而已。然汉儒惑于谶纬,始有赤雀丹书之说,又谓文王因此遂称王而改元。殊不知所谓天之所以为天者,理而已矣;理之所在,众人之心而已矣;众人之心,是非向背,若出于一,而无一毫私意杂于其间,则是理之自然,而天之所以为天者不外是矣。今天下之心既以文王为归,则天命将安往哉!*[宋]朱熹:《诗序辨说》,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第391页。
朱子解“作周”为“造周室”,建造周之宫室,而非郑玄所解之“周邦”、邦国。“受命”,朱子无可奈何只能解为“天命”,但对于何为天命,朱子则从天理的角度来解说。以“理”释“天”,这是朱子的思想体系中固有的,并不足为奇。如他对《孟子·梁惠王》“以大事小者,乐天者也;以小事大者,畏天者也。乐天者保天下,畏天者保其国”所注:“天者,理而已矣。大之字小,小之事大,皆理之当然也。自然合理,故曰乐天。不敢违理,故曰畏天。包含徧覆,无不周徧,保天下之气象也。制节谨度,不敢纵逸,保一国之规模也。”*[宋]朱熹撰:《四书章句集注》,第215页。以“理”释“天”,以“天命”言“命”,则所谓“文王受命”也是天理之自然。至此,在“理”的光芒下,文王作为圣人的地位愈加神圣。
依此,朱子塑造文王圣王形象的基本路径也清晰可见。通过以“圣德”言“文王”,以后人的追述化解称王问题,重新界定“先王”之指称,又以“理”释“天”,将文王“受命”归结为“天理”之自然所归,而朱子也终于成功地在其诗经学体系中构建起文王的圣人形象。
二、文王之化:理的实现
朱子在“理”的系统下塑造了文王的圣人形象,文王受命终是天理所归。但此“天理”并非悬空之理,他的“理”须在格物层面来体认。文王为圣王,受命称王是天理所归,则此天理亦当在现实层面有其呈现。因而,作为能够表现文王为圣王,能彰显天理所归之正当性的最重要的一面,即是文王之化的突显。文王既是“生有圣德”,是先觉者,能够启发后觉之人;同时亦是学之典范,被其感化,亦能趋于成圣。由此,便不难理解周、召二南中,朱子着力彰显文王之化的苦心了。
《周南》11首诗的解释中,《桃夭》《兔罝》《汉广》《汝坟》《麟之趾》这5首明文论及文王之化。如《桃夭》注:“文王之化,自家而国,男女以正,婚姻以时。”《汝坟》注:“汝旁之国,亦先被文王之化者,故妇人喜其君子行役而归,因记其未归之时思望之情如此,而追赋之也。”*[宋]朱熹注、王华宝整理:《诗集传》,第6—8页。
《召南》14首诗,朱子则在《鹊巢》《采蘩》《草虫》《采蘋》《甘棠》《行露》《羔羊》《殷其雷》《摽有梅》《野有死麇》《何彼秾矣》《驺虞》等12首诗明确言及文王之化。如《鹊巢》篇,朱子从“正心修身齐家”谈论文王之化的作用:“南国诸侯被文王之化,能正心修身以齐其家,其女子亦被后妃之化,而有专静纯一之德。”*[宋]朱熹注、王华宝整理:《诗集传》,第10页。如《行露》篇,以“南国之人革其前日淫乱之俗”言文王之化,“南国之人,遵召伯之教,服文王之化,有以革其前日淫乱之俗。故女子有能以礼自守,而不为强暴所污者,自述己志,作此诗以绝其人”*[宋]朱熹注、王华宝整理:《诗集传》,第12页。。《召南》的终篇《驺虞》则在天下国家的背景中彰显文王之化的广博,“南国诸侯承文王之化,修身齐家以治其国,而其仁民之余恩,又有以及于庶类”*[宋]朱熹注、王华宝整理:《诗集传》,第16页。,认为在文王之化下,南国诸侯能够修身齐家治国,进而仁育民众,其余恩又惠庶类,则天地生物庶几都化被文王之化。
综观上述不厌繁琐的引用说明,在朱子所极力彰显的文王之化中,文王之化同时也是一个由内而外、自上而下的过程;而“二南”都因化被文王之化而得以为正,即使旧俗淫乱,也会在感被文王之化后得以革新,性情得以端正,其女子亦能以礼自守,如《行露》篇所解。朱子亦言:“惟《周南》、《召南》亲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而人皆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发于言者,乐而不过于淫,哀而不及于伤,是以二篇独为风诗之正经。”*[宋]朱熹:《诗集传序》,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第351页。
文王之化的解释贯穿“二南”的解释,也贯穿朱子对“二南”《诗序》的批驳。如《关雎》篇,朱子浓墨重彩辨说之:
……但其诗虽若专美太姒,而实以深见文王之德。《序》者徒见其词,而不察其意,遂一以后妃为主,而不复知有文王,是固已失之矣。至于化行国中,三分天下,亦皆以为后妃之所致,则是礼乐征伐皆出于妇人之手,而文王者徒拥虚器以为寄生之君也,其失甚矣。*[宋]朱熹:《诗序辨说》,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第355页。
《关雎》虽似只专美后妃,实以彰显文王之德化,这是朱子对文王地位的突显,又引曾氏之言提出“世皆知文王之所以兴,能得内助,而不知其所以然者,盖本于文王之躬化”*[宋]朱熹:《诗序辨说》,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第355页。。因家人身化文王之德,故文王才能由内而外行化成“二南”之业,“二南”之业实则亦由文王之化而来。
但《诗序》并未如此突显文王之化,而多贯之以“后妃之本”“后妃之志”“后妃之化”等表述,因而朱子在《辨说》屡为文王的突显申说。如《序》云:“《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妒忌,则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也。”朱子辨之:“《序》首句非是。其所谓‘男女以正,婚姻以时,国无鳏民’者得之。盖此以下诸诗,皆言文王风化之盛,由家及国之事。而《序》者失之,皆以为后妃之所致,既非所以正男女之位,而于此诗又专以为不妒忌不功,则其意愈狭,而说愈疏矣。”可见在朱子处,此类《序》之失只因专言后妃,而未明文王;而当《诗序》论及文王之化,朱子则肯定之。如《汉广》篇,《序》云:“《汉广》,德广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国,美化行乎江、汉之域,无思犯礼,求而不可得也。”朱子辨之:“此诗以篇内有‘汉之广矣’一句得名,而《序》者谬误,乃以‘德广所及’为言,失之远矣。然其下文复得诗意,而所谓文王之化者尤可以正前篇之误……”*上述引文均出自《诗序辨说》一文,参见[宋]朱熹:《诗序辨说》,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第358页。《汉广序》因言及“文王之道被于南国”,故朱子以之为得诗意,并认为其可正前篇(《桃夭》《兔罝》)之误。朱子彰显文王之化的努力,不仅表现在其对“二南”的解释中,也呈现在其对“二南”《诗序》的批判之中。
文王作为圣人,在程朱语脉中,圣人不仅是先觉者,可启发后觉者,同时也是学之典范,后觉者化其德而能端正性情。因而,朱子于“二南”中着力彰显文王之化,力辨《诗序》专言后妃之失,突显文王之主体性,这不仅是“天理”如何归之文王的回答,也是文王之为圣人在现实层面的体现。另外,“二南”均因被文王之化,故其地能革其淫乱之俗,以礼自守,其诗亦表现为端正恭敬,学者读之也可得性情之正,学以成圣。相较之下,“郑卫”之地未被文王之化,旧俗未除,其乐皆为淫声,因而,学者若不警戒之,则难以端正性情,甚至使善之本性为人欲所遮。
三、性情之正:淫诗说的背后指向
在朱子看来,《诗》有好坏邪正之分:“《易》有个阴阳,《诗》有个邪正,《书》有个治乱,皆是一直路径,可见别无峣崎。”*[宋]朱熹:《朱子语类》卷11,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14册,第345页。只有“正”的《诗》才能兴起善意,使得其性情之正;而“邪”的《诗》,则会令“自家心下如着枪”般警醒。如此看来,若对“邪”的《诗》无所辨别,又有何影响?由此角度切入朱子对淫诗——“邪”的《诗》之代表的批驳,亦可更好理解朱子之深意。
朱子对淫诗的批驳,主要集中于“郑卫”之风;朱子辨说淫诗,又主要从“思无邪”的定位出发,以“郑声淫”为中心展开“雅郑邪正”之辨。在诸多淫诗的批驳中,朱子对《鄘风·桑中》篇的批评较为集中而激烈,如《诗序辨说》中对于《诗序·桑中》的长达一千多字的辨说、文集中《读吕氏诗记桑中篇》等。因而,下文结合朱子对《桑中》篇的批评,重新审视朱子的淫诗说。
《诗序》云:“《桑中》,刺奔也。卫之公室淫乱,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窃妻妾,期于幽远,政散民流而不可止。”*[宋]朱熹:《诗序辨说》,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第364页。《诗序》认为,《鄘风·桑中》属刺诗,讽刺因卫国王室的淫乱而导致的政治散乱和人民流奔,其要旨在于表现对王室淫乱之讥刺。然而,朱子并不如此看待。
朱子言:“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宋]朱熹:《诗序辨说》,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第364页。朱子认为,《桑中》之旨并非“刺奔”,《桑中》是淫奔者所自作,这便把淫诗的作者确定为淫奔之人。淫诗的作者为谁?这是朱子审视淫诗首先面对的问题,因它直接涉及朱子如何看待淫诗之“美刺”问题。针对当时流行的一种观点,朱子否定之:“或者以为刺诗之体,固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辞,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于言外者,此类是也。岂必谯让质责,然后为刺也哉!此说不然。”*[宋]朱熹:《诗序辨说》,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第364—365页。“或者以为”,并非一定要表现为“谯让质责”才为“刺诗”,直述其事亦可呈现为“刺诗”。这里的“或者以为”也或为当时社会一种普遍流行的观点。此观点存有两个预设:其一,作“刺诗”之人与“刺诗”所刺之人不是同一个人,即淫诗的作者不是诗所要讽刺之人;其二,所刺之人对于自己所行之恶事有自觉性,能够反省自己的恶行。
朱子显然不同意此种看法,认为:
夫诗之为刺,固有不加一辞而意自见者,《清人》、《猗嗟》之属是已。然尝试习之,则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而词意之间犹有宾主之分也。岂有将欲刺人之恶,自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于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也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之人,安于为恶,其于此等之诗,计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无惭矣,又何待吾之铺陈而后始知其所为之如此,亦岂畏吾之闵惜而遂幡在遽有惩创之心邪!以是为刺,不唯无益,殆恐不免于鼓之舞之,而反以劝其恶也。*[宋]朱熹:《诗序辨说》,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第365页。
朱子分两层反驳“或者以为”的观点:第一,从诗篇表达的诗义来看,“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同时词意间仍有宾主之分,作诗之人自不会以讥刺的心态写所敬之“主”,因而,《序》说所刺之人与诗之作者应是同一人,即淫诗的作者为淫佚之人;第二,《诗序》所指的诗篇中所刺之人安于平日所行,没有反省之意识,因而对于记载自己之恶行的诗篇也不会有惩创之心。因此朱子认为将这类诗定位为刺诗,并不能起到“劝善”的目的,反而只会“劝恶”;也可见,朱子将淫诗定位为淫佚之人所自作,其背后还本着诗于学者可劝善惩恶的关怀,此也是朱子认可的诗之用。
郑卫之风多淫诗者所作,对于《诗大序》“故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及夫子所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之说,朱子也当重做解答。朱子认为所谓“止乎礼义”者,仅指《柏舟》《绿衣》《泉水》等部分诗篇,并非“三百篇”皆“止乎礼义”*[宋]朱熹:《诗序辨说》,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第365页。。“……然此言亦其大概有如此者,其放逸而不止乎礼义者,固已多矣。”*[宋]朱熹:《诗传纲领》,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1册,第345页。所谓“止乎礼义”也只是“大概有如此者”。由此,也并非“三百篇”皆能够“思无邪”了,“只是‘思无邪’一句好,不是一部《诗》皆‘思无邪’”*[宋]朱熹:《朱子语类》卷80,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17册,第2734页。。同时,“非以《桑中》之类亦以无邪之思作之也”,“思无邪”不是指作诗者都以“无邪之思”作诗,即“三百篇”之作者其思乃有邪有正。既然作者之思有邪有正,那么所谓的“思无邪”则主要针对读者而言。“孔子之称‘思无邪’也,以为《诗》三百篇劝善惩恶,虽其要归无不出于正,然未有若此言之约而尽者耳,非以作诗之人所思皆无邪也。”*[宋]朱熹:《读吕氏诗记桑中篇》,朱杰人主编:《朱子全书》第23册,第3371页。“三百篇”均对读者劝善惩恶,因而所谓“思无邪”,也只是指读诗之人要思无邪,从而使得读诗者能够“归于正”,这才是夫子提出“思无邪”最重要的目的。可见,朱子对于“思无邪”的重新界定,也在为《诗》对学者的劝善惩恶和端正性情的功用作辨说。一如《论语集注》所言:“凡《诗》之言,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第53页。
此外,朱子对“《诗》三百篇,皆雅乐也”及“凡百篇,孔子皆弦歌之”等古老说法也重作界定。“雅乐”,指大小“二雅”,它同“二南”及《颂》均可用于祭祀朝聘;而像《郑风》《邶风》《鄘风》及《卫风》等“郑卫”之乐,并非“雅乐”,而是“里巷狭邪之所歌”,不能用于宗庙朝廷之中。他又推测夫子存“郑卫之乐的缘由”,“夫子之于《郑》、《卫》,盖深绝其声于乐以为法,而严立其词于诗以为戒”。可见朱子区别“雅乐”与“郑乐”的标准之一,也应是夫子“郑声淫”之说。
“郑声淫”的提法来自《论语·阳货》:“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恶郑声之乱雅乐也,恶利口之覆邦家者。”“雅乐”是一种正乐,中正平和,符合礼法;“郑声之乱雅乐”,应指“郑声”扰乱此种中正平和之礼乐秩序。故而,在夫子的语境中,“郑声淫”之“淫”,并非指情欲上之淫乱,而是指其对礼乐的一种扰乱。如夫子言“《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此处的“淫”是过度的意思。因而,“郑声淫”应指“郑声”所表现的内容,超越了“郑声”所本有的礼法界限。
但朱子以道学家的道德感来界定“淫”,认为“郑声淫”指情欲之淫乱。这样,朱子对时人的“《三百篇》皆雅乐也”及“桑间、濮上之音”的论说便须重作界定。至于为何夫子仍存“郑卫之乐”,朱子认为这是夫子想以之“为法”,“如圣人固不语乱,而《春秋》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风俗事变之实,而垂监戒于后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
可见朱子审视淫诗,其旨在于申明《诗》对于学者劝善惩恶、端正性情的功用。淫诗,无疑属于《诗》之邪者,并不能启迪人之善心。学者只有以之为戒,时时自我提撕,以无邪之思读《诗》,才能通过读《诗》来端正性情。
由上所析,朱子着力彰显文王之化、辨驳淫诗之非的思想根据清晰可见。朱子解《诗》,文王乃作为圣人存在,不仅“生有圣德”,是先知先觉之圣人,也是无过之人,既是德化的象征,又是学之典范。“二南”因被其化,故均得其性情之正。“郑卫之地”未被其化,旧俗未改,其人亦未能端正性情,故其诗也多淫诗,学者只有警戒于此,才能通过学《诗》端正己之情性。因而,在朱子彰显文王之化、批驳淫诗的背后,始终贯穿着程朱一脉“圣人之学”的美好理想。圣人之心纯乎天理,可学而至,圣人与凡人其性本善,但凡人因受私欲之蔽性有不正,“学”可得其性情之正,复归于善,以至成圣。而《诗经》作为当时士人共同学习的经典之一,通过经典的重新解释,朱子在经典中为士人们重新树立起这一共同理念,这不仅凝聚起了士人共同体,同时亦为教化基层民众做好了铺垫。
(责任编辑 杨海文)
黄少微,广东汕头人,(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哲学系博士生。
B244.7
A
1000-7660(2017)01-015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