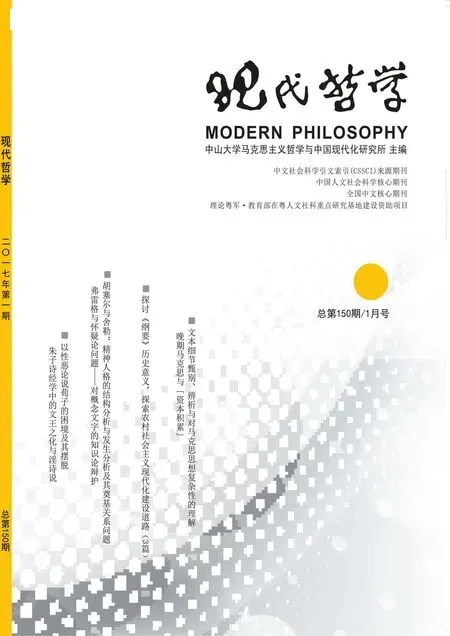胡塞尔与舍勒:精神人格的结构分析与发生分析及其奠基关系问题
2017-04-01倪梁康
倪梁康
胡塞尔与舍勒:精神人格的结构分析与发生分析及其奠基关系问题
倪梁康
从总体上看,胡塞尔的人格现象学思考和研究是沿着“人格(Person)”这个概念所具有的两个词义的方向展开的:其一,对与自然主义观念相对立的人格主义观点的探讨,以及对精神世界之构成的现象学描述,它涉及人格自我(das personale Ich)或精神自我(das geistige Ich)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亦即心灵与自然以及心灵与肉体的关系;其二,对与社会和共同体问题相对应的个体问题的探讨,以及通过同感(Einfühlung)对他人的构造问题,它涉及个人自我(das persönliche Ich)或个体主体性与社会主体性(die individuelle oder soziale Subjektivität)的关系问题亦即心灵与心灵的关系问题以及交互主体性问题。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两个含义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联系的问题,例如彼此的奠基关系问题,而只关注它们的相互蕴含关系。
胡塞尔;舍勒;精神人格;奠基问题;比较研究
一、引论:“人格(Person)”以及“人格现象学”的双重含义
在1931年初写给亚历山大·普凡德尔(Alexander Pfänder,1870-1941年)的信中,胡塞尔谈到他贯穿在其整个弗莱堡工作时期的“新的、极为广泛的研究”计划,其中首先便包括了“人格现象学与更高级次的人格性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r Person und der Personalitäten höherer Ordnung)*胡塞尔在这里接下来还提到的是:“文化现象学、人的周围世界一般的现象学;超越论的‘同感’现象学与超越论的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作为世界现象学的‘超越论感性学’,即纯粹经验世界的现象学,时间与个体化,作为被动性构造成就理论的联想现象学,逻各斯现象学、‘形而上学’的现象学问题域等等。”(书信II,180)——这里还需要留意一点:胡塞尔在这里所说的是“人格现象学”,而非“人格本体论”或“人格伦理学”。在梅勒的论文《胡塞尔的人格伦理学》中所讨论的主要是后两者。(参见[比利时]乌尔里希·梅勒:《胡塞尔的人格伦理学》,陈联营译,《中国现象学与哲学评论》第13辑,《现象学与神学》,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275—298页。),在这些新研究中产生的手稿,“数量已经增加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其间一再地产生出这样的担忧:在我这个年龄,我自己是否还能将这些托付给我的东西最终加以完成。激情的工作导致我一再地经受挫折并一再地陷入忧郁。最终留存下的是一种普遍的、压抑的基本情绪,是危险地坠落了的自身信任”。(书信II,180)这里的表述如实地反映出胡塞尔自弗莱堡就职(1916年)以来对自己在人格或人格性研究工作方面所持的总体的悲观与不满态度。由此便可以理解,直至1927年,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还写道:“胡塞尔关于‘人格性(Personalität)’的研究至今尚未印行。”但他在这里同时也指出:“问题提法的根本倾向早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这篇论文中就表现出来了(《逻各斯》I,1910年,第319页)。《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胡塞尔全集》IV)的第二部分更为深入地推进了这一研究。”(GA 20,47,Anm.1)当然,海德格尔在这里预告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卷,是在胡塞尔去世后才作为其遗稿而整理出版的。
这里所说的“人格”,其对应的德文是“Person”。这个词实际上具有两个基本的含义,因此有必要对它们进行分别讨论。*辛哈所做的关于胡塞尔“人格”概念的专论并未看到这个概念中的双重含义。参见Debabrata Sinha, “Der Begriff der Person in der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 in Zeitschrift für philosophische Forschung, Bd.18, H.4 (Oct.-Dec., 1964), S. 597-613.尽管无论是在胡塞尔那里,还是在舍勒那里,它们都不始终明显地以相互分离的形式出现,而更多是含糊、交织地包含在作为名词的“Person”中,然而它们在作为其派生的形容词和抽象化名词出现时则常常可以得到相对清晰的界定:
1.作为普遍精神生活的人格:它在胡塞尔那里基本上等于“精神的”,常以形容词“personal”的方式得到表明,也可以通过名词“Personalität”得到强调。这个意义上的“Person”问题是在与自然或自然世界相对应的语境中得到讨论的。它的抽象名词“Personalität”更应当被译作“人性”或“人格性”。*在此方向上的研究例如可以参见Thomas M. Seebohm, “Husserl on the Human Sciences in Ideen II”, in L. Embree and T. Nenon (eds.), Husserl’s Ideen, Springer: Dordrecht 2013, pp. 125-140.这也是在上引胡塞尔和海德格尔说法中谈及的“人格”或“人格性”。我们可以将它称作“第一人格问题”。这方面的阐述包含在胡塞尔在关于“自然与精神”问题下所做的所有思考中。*对此问题域的讨论可以参见胡塞尔的以下身前发表的和未发表的文稿与讲座稿:1、《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1910年,《全集》第25卷:《文章与讲演(1911-1921年)》);2、《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2卷(1913-1924年,《全集》第4卷)。3、“自然与精神”演讲(1919年夏季学期,《全集》第25卷:《文章与讲演(1911-1921年)》);4、《自然与精神》讲座(《全集资料编》第4卷:《自然与精神(1919年夏季学期讲座)》);5、《自然与精神。实事科学与规范科学。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1920/1924年夏季学期“伦理学引论”讲座附论,《全集》第37卷:《伦理学引论(1920/1924年夏季学期讲座)》;6、《自然与精神》讲座(《全集》第32卷:《自然与精神(1927年夏季学期讲座)》)。这些思考延续的时间如此之长,内容如此之丰富,以至于耿宁在为2001年出版的《自然与精神》(《胡塞尔全集》第32卷)所撰书评中可以说:“《胡塞尔全集》中的遗稿出版得越多,就越清楚地表明,胡塞尔哲学的主要问题与其说是为科学进行绝然性论证的问题(‘笛卡尔的动机’),远不如说是与自然科学相对的意识、主体性、人格、精神的科学和哲学的独立性问题。”*[瑞士]耿宁:《胡塞尔论“自然与精神”》,方向红译,[瑞士]耿宁:《心的现象》倪梁康编,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405页。这里提到的“人格”,主要是指第一意义上的人格概念。如果耿宁在这里作为“胡塞尔哲学主要问题”所列出的前者代表着“笛卡尔的动机”,那么后者应当就更多地代表着“黑格尔的动机”,或者也可以说代表着在黑格尔之前的“维柯的动机”,代表着在黑格尔之后的“狄尔泰的动机”。这两个动机贯穿在胡塞尔于纯粹意识现象学研究以及人格现象学研究中进行的横意向性的结构分析和纵意向性的发生分析之始终。
2.作为个体之个性的人格:它在胡塞尔那里是“普遍的”、“共同体的”的对应项,常常以形容词“persönlich”的方式得到表明,也可以通过名词“Persönlichkeit”得到强调。在此意义上的“Person”问题是在与共同生活与社会行为相对应的语境中得到讨论的。它的抽象名词“Persönlichkeit”更应当被译作“个性”或“个人性”。*在此方向上的研究例如可以参见J. G. Hart, The Person and the Common Life. Studies in a Husserlian Social Ethics, Dordrecht u.a., 1992.这个意义上的“人格”可以被称作“第二人格问题”。施特拉塞尔编辑出版的《笛卡尔式的沉思》第五沉思*[德]胡塞尔:《笛卡尔式的沉思与巴黎讲演》,《胡塞尔全集》第1卷,施特拉塞尔编,海牙: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1950年。、耿宁编辑出版的三卷本《交互主体性现象学》*[德]胡塞尔:《交互主体性现象学》第一部分:1905-1920年、第二部分:1921-1928年、第三部分:1929-1935年,[瑞士]耿宁编:《胡塞尔全集》第13、14、15卷,海牙: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1973年。、比梅尔编辑出版的《观念II》中的部分内容*[德]胡塞尔:《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2卷,《胡塞尔全集》第4卷,玛利·比梅尔编,海牙: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1952年。——这一卷的内容既涉及前一个意义上的人格,即精神生活意义上的“personales Ich”(Hua IV, 321),也涉及后一个意义上的人格,即个体自我意义上的“persönliches Ich”连同其“个人的特性或性格特征”(Hua IV, 249)。,以及舒曼编辑出版的“胡塞尔对埃迪·施泰因国家考试论文所做的摘录”*Vgl. “Husserls Exzerpt aus der Staatsexamensarbeit von Edith Stein”, edited by Karl Schuhmann, in Tijdschrift voor Filosofie, Nr. 53, 1991, S. 686-699.,主要是讨论这个问题的。
从总体上看,胡塞尔的人格现象学思考和研究也是沿着这两个词义的方向展开的:其一,对与自然主义观念相对立的人格主义观点的探讨,以及对精神世界之构成的现象学描述。它涉及人格自我(das personale Ich)或精神自我(das geistige Ich)与自然世界的关系,亦即心灵与自然以及心灵与肉体的关系。其二,对与社会和共同体问题相对应的个体问题的探讨,以及通过同感(Einfühlung)对他人的构造问题。它涉及个人自我(das personliche Ich)或个体主体性与社会主体性(die individuelle oder soziale Subjektivität)的关系问题,亦即心灵与心灵的关系问题以及交互主体性问题。我们暂且不去讨论这两个含义之间是否存在某种内在联系的问题,例如彼此的奠基关系问题,而只关注它们的相互蕴含关系。
无论如何,这两方面的思考都曾——如海德格尔所说——既包含在胡塞尔身前发表的《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的长文中,也包含在他身前未发表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卷中,而且两者尤其在《观念II》的第三篇中密切地、乃至不可区分地交织在一起。前一方向的思考更多将胡塞尔与狄尔泰联系在一起,后一方向的思考则更多将他与利普斯联系在一起。“人格”可以在此双重意义上被理解为“交互人格的精神生活(interpersonal spiritual life)”*T.M. Seebohm, “Husserl on the Human Sciences in Ideen II”, a.a.O., S. 129.,并在这两种相互交织为一的含义中受到胡塞尔的讨论和分析。
我们在此对胡塞尔与舍勒的人格现象学的讨论将会在这两个方向上伸展。*舍勒和胡塞尔在人格问题以及伦理学上的思想关联,也可参看[比利时]乌尔里杀·梅勒:《舍勒对胡塞尔弗莱堡伦理学的影响》,曾云译,《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这里题为“胡塞尔与舍勒:精神人格的结构分析与发生分析及其奠基关系问题”的第一部分将讨论胡塞尔和舍勒的第一个意义上的人格现象学,它也可以被称作“精神现象学”或“文化现象学”。随后在“胡塞尔与舍勒:交互人格经验的直接性与间接性问题”标题下进行的比较和讨论则是针对胡塞尔与舍勒在交互主体性或同感问题上的思考而发,这第二个意义上的“人格现象学”也可以被称作“交互主体性的现象学”或“同感现象学”。
二、从狄尔泰到胡塞尔和舍勒的人格问题研究
这里首先需要指出耿宁的一个看法:“仅就胡塞尔探讨交互主体性问题的那个最早时期(1905-1910年)而言,就已经必须指明一个全然不同的视角,他正是在这个视角下提出这个问题:对社会的精神世界的特殊经验问题以及在这个‘世界’所固有的动机引发关联中的历史问题。这是一个与其说是将胡塞尔与特奥多尔·利普斯、不如说是与威廉·狄尔泰联系起来的视角。”(Hua XIII,XXXII)
这个不仅为胡塞尔而且也是舍勒所接受的狄尔泰视角,就是我们在前一节中所说的“作为普遍精神生活的人格”之视角。海德格尔在1925年《时间概念历史导引》讲座的第13节“指明在现象学中对存在本身之意义问题和对人之存在问题的错失”中曾对这个人格主义视角做过较为细致的说明。他在这一节的a)、b)、e)三小节中专门讨论狄尔泰、胡塞尔和舍勒的人格理论或“人格主义心理学”。这些讨论可以被我们用作具有双重意义上的“引论”*海德格尔的这个双重意义上的引论的修订版后来被纳入其《存在与时间》的第10节:“此在分析与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之间的划界。”:一方面是因为海德格尔用它来引出他自己的“此在分析”的引论:人格理论在这里可以说是此在分析的前奏;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被用作人格现象学问题的一个历史的和系统的引论:我们在这里用它来引出胡塞尔和舍勒的人格描述与分析。
海德格尔用“人格主义心理学”的说法来命名和标示自狄尔泰开始的现象学人格问题研究趋向。这主要是指在上述在人格的双重词义中包含的第一个方向:精神科学的和人格主义的研究方向。海德格尔认为,狄尔泰的人格主义是对当时在心理学中盛行的自然主义的一种反叛。在此意义上,狄尔泰的“人格”,是“自然的对掷(Gegenwurf)”或“对自然的反作用(zurückwirken)”*M. Heidegger, Prolegomena zur Geschichte des Zeitbegriffs (Sommersemester 1925), GA 20, Klostermann: Frankfurt am Main 1994, S. 165.(以下凡引《海德格尔全集》,均仅在正文中给出该全集的简称“GA”、卷数和页码。)。他不仅区分自然与人格,也区分自然科学与精神科学,最后也区分自然科学及自然主义心理学的“说明”方法与精神科学及人格主义心理学的“描述”方法。
狄尔泰的这个立场当时在总体上被胡塞尔和舍勒所接受。严格说来,可以明显地看到这里有一个双向的相互作用存在:从胡塞尔和舍勒方面来看,他们在以现象学的方式实施狄尔泰的工作——开创一门与自然主义心理学相对立的“人格主义的”或“精神科学的”心理学*胡塞尔常常使用“人格心理学”概念,并将它用作“自然心理学”的对应概念或对掷概念(参见卡尔·舒曼:《胡塞尔年谱》,海牙: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1977年,第203、251、315页)。他还随之区分“自然主义的观点”与“人格主义的或实事科学的与精神科学的观点”以及“自然的经验”与“精神的经验”等等(手稿:A V 4408-112)。;而就狄尔泰方面而言,胡塞尔和舍勒的现象学也为他开启了一个新的领域,并且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一种以往被他称作对心理现象的“描述”和“分析”、而且如今已在现象学家那里得到出色实施的方法。因此海德格尔也指出:“狄尔泰是第一个理解了现象学诸意图的人。”(GA 20, 163)
狄尔泰将人(Mensch)理解为人格(Person),并开创了一门新的心理学。实际上它是一门人学,或如海德格尔所说,“一门关于人的科学,它对人进行第一性的把握,一如他作为人格、作为历史中行动的人格而生存的那样”(GA 20, 163)。在这里已经可以发现:人格在狄尔泰那里是一个历史的和发展的概念。黑格尔哲学以及真理观在狄尔泰这里留下了明显的作用痕迹,而且是双重的:它不仅表现在将人格与历史和发展的概念结合在一起,而且也将总体的概念纳入进来。人格在狄尔泰那里同时也是一个总体的概念:“在每个存在的瞬间,这个人格都在进行反作用,它是完整的人格,不仅仅是意愿的、感受的和观察的人格,而始终是同时以一切归一的方式在进行;人格的生命联系在每个处境中都是这样一种发展的人格。”(GA 20, 163)海德格尔所说的狄尔泰人格主义心理学,实际上就是这个意义上的历史哲学与生命哲学或精神科学的共同体。
海德格尔使用的这个意义上的“人格主义心理学”概念,应当主要来自舍勒。在狄尔泰和胡塞尔那里,“人格主义”一词较少出现,偶尔有之,也是以自然主义的对立概念的身份,较少带有完全积极的、实事性的内涵。这多半是因为思想史上的“人格主义”概念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对人格上帝的主张。这也正是舍勒人格主义伦理学或人格主义现象学的主张。*舍勒的代表作《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和质料的价值伦理学》第一版的副标题是“尤其关注伊曼努尔·康德的伦理学”,第二版之后的副标题则为“为一门伦理学人格主义奠基的新尝试”。舍勒对此曾做出说明:“笔者在这里所阐释的一个原理是:一切价值,也包括一切可能的实事价值(Sachwert),此外还有一切非人格的共同体和组织的价值,都隶属于人格价值;这个原理对笔者来说是如此重要,以至于他在书名中也把他的研究称作‘一种人格主义的新尝试’”。(参见M. Scheler, Gesammelte Werke, Bd. II, Francke Verlag: Bern und München, 1980, S. 14. 以下凡引《舍勒全集》,均仅在正文中给出该全集的简称“GW”、卷数和页码。)因此,它在舍勒那里具有一个积极的、奠基性的含义,如海德格尔所说,“就舍勒将人格视作行为的统一、即行为的意向性这一点而言,他说:人的本质是朝向某物的意向,或者如他所言,是超越的姿态本身。——人是一种永恒的超出-朝向,就像帕斯卡尔将人标示为上帝寻求者一样”。(GA 20, 181)
然而在海德格尔那里,“人格主义”更多是一个批判性的概念。对他来说,人格主义在舍勒的那里是“失败的尝试”(GA 20, 174)。海德格尔将精神哲学或意识哲学以及与此相关的人格主义都视作“对存在本身之意义问题和对人之存在问题的错失”*或者说“对存在本身的问题与意向者存在(Sein des Intentionalen)的问题的错失”。分别参见海德格尔:GA 20, S. 157, S. 179.,对此错失的“指明”和“理解”仅仅是他引出自己的存在问题的前奏:在提出自己对在“人格”问题研究上胡塞尔的纯粹性要求与舍勒的超越性前设的批评时,海德格尔已经站在了自己的立场上——存在论的立场。从这个立场出发,“所有由狄尔泰和柏格森规定下来的‘人格主义’流派,所有哲学人类学倾向”,都同狄尔泰和柏格森一道受制于他们的“问题域的限度”以及“概念性的限度”,而且,在海德格尔看来,“即使原则上更为透彻的现象学的人格阐释也不曾进入此在的存在问题这一维度”。*[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GA 2,第47页。这同时意味着,从海德格尔的这一立场出发,不仅人格主义和精神科学的思想取向被弃之不顾,而且“人格”概念本身最终也成为一个有问题的、有待克服的概念,*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明确地写道,“主体、心灵、意识、精神、人格”是一些可疑的名称,因为“使用这些名称的时候仿佛无须乎询问如此这般标明的存在者的存在。所以,如果我们避免使用这些名称,就像避免使用‘生命’与‘人’这类词来标识我们自己所是的那种存在者一样,那么这并非是一种术语上的倔犟(Eigenwilligkeit)。”(Heidegger, GA 2, S. 47.)人格问题研究实际上最终已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立足于基础存在论的此在分析。
事实上,我们在此也只是将海德格尔的批评当作引出我们这里所要讨论问题的前奏,以引出胡塞尔和舍勒的人格问题思想路径。因而在接下来的分析中,我们还是要回到毋宁说是在海德格尔那里“被错失”*这里可以参考波尔诺夫(O. F. Bollnow)在其经典研究著作《狄尔泰哲学引论》1967年第三版序言中对海德格尔的批评:“自《存在与时间》出版后,海德格尔的强劲扩展的影响一度将狄尔泰的影响挤到了台后。对于许多人来说,海德格尔的此在存在论似乎以一种澄清了的和彻底化的方式接受了在狄尔泰那里始终还处在某种不确定状态中的东西。因而狄尔泰看起来已经被新近的发展所超越。然而惟有对海德格尔的存在论所做的透彻批判分析才能表明,他的思考的彻底性是以对提问的强烈限制和窄化(Verengung)为代价的,而且要想继续富有成效地前行,就必须再度回到狄尔泰的更为开放的、尽管起初还显得不够决断的起点上去。”(波尔诺夫:《狄尔泰哲学引论》,斯图加特等地,1967年,第三版序言,第8页。)的人格问题研究上来。
三、胡塞尔与舍勒的人格结构现象学
在胡塞尔通过《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二卷所要表达的系统现象学研究的构想中,人格现象学属于现象学哲学的一部分,它与人格主义心理学的研究是平行的。在这里,人格现象学的问题首先必须为一个人格结构的问题,而后作为一个人格发生的问题出现。这也意味着,它首先是现象学的意识结构分析的课题,而后是现象学的意识发生分析的课题。在此意义上可以理解,胡塞尔为何将人格的关系视作“意向关系”*参见[德]胡塞尔:《手稿》(1928年圣灵降临节假期),AV7/110-116,转引自《胡塞尔年谱》,同上书,第334页。。人格一方面处在“它与实在事物的各种关系中”*T.M. Seebohm, “Husserl on the Human Sciences in Ideen II”, in L. Embree and T. Nenon (eds.), Husserl’s Ideen, Springer: Dordrecht 2013, S. 132: “The I as person, the egoic person, is given in this world in its relations to the real things as a representing, feeling, evaluating, striving, and acting person.”,而另一方面,“虽然人格是统一的同一极(Identitätspol),是对于诸性格以及诸如此类而言的基质(Substrat für Charakter und dergleichen),但所有这些都回溯到这个体验流之上”。*[德]胡塞尔:《手稿》AVI 15,转引自Debabrata Sinha, “Der Begriff der Person in der Phänomenologie Husserls”, in a.a.O., S. 598.在此双重意义上,就人格的结构而言,可以用胡塞尔在其《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中使用的“横意向性”*参见[德]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胡塞尔全集》第10卷,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129、483页。(以下凡引《胡塞尔全集》,均仅在正文中给出该全集的简称“Hua”、卷数和页码。)来表达这里的实事状况;而就人格的发生而言,则可以用胡塞尔在此使用的“纵意向性”(Hua X, 128,482)来表达这里的实事状况。这也与耿宁讨论过的“意识的共时统一或同时统一问题”以及与之相对的“意识的历时统一或演替统一问题”相呼应。*参见[瑞士]耿宁:《意识统一的两个原则:被体验状态以及诸体验的联系》,《心的现象——耿宁心性现象学研究文集》,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207页。
这里的“横意向性”所指的首先是贯穿在人格行为中的意识体验之意向活动与意向相关项的基本结构,尤其是意向活动对意向相关项的构造;其次它还进一步意味着在此结构和构造活动中包含的各种人格行为的奠基关系。它们与海德格尔所说的“意愿的、感受的和观察的人格”是基本一致的,但在排列顺序上存在差别。在胡塞尔那里恰恰相反,人格的行为动机顺序更应当如泽伯姆所说的那样是“表象的、感受的、评价的、欲求的和行动的人格”*T.M. Seebohm, “Husserl on the Human Sciences in Ideen II”, in L. Embree and T. Nenon (eds.), Husserl’s Ideen, a.a.O., S. 132.。这里对人格行为顺序排序涉及胡塞尔对它们之间存在的奠基关系的确定。梅勒指出“对于胡塞尔来说,在这些种类的行为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倒逆的奠基顺序:意愿行为奠基于感受行为之中,而它们两者又都奠基于理智行为之中”,他也将这些行为称之为“理论认知的、感受-评价的以及意愿和行动的”。*U. Melle, “Husserl’s personalist ethics”, in Husserl Studies, 2007, Nr. 23, S. 4, S. 14.如果我们划分得更细致些,那么在认知的或表象的行为中一方面还可以区分出感知的、回忆的、想象的、图像化的和符号化的行为以及奠基于其中的判断、表达等行为,在它们之间同样存在着一个不可倒逆的奠基顺序;另一方面是在感受行为中还可以区分出爱与恨的行为及同乐与同苦、羞愧与忿怒、喜欢与厌恶等情感活动,在它们之间并不必然存在类似在认知行为之间可以发现的明确奠基关系。
这里的所谓“奠基关系”,在胡塞尔的《逻辑研究》中便已得到说明:“一个行为的被奠基并不是指这个行为——无论在哪种意义上——建立在另一些行为之上,而是意味着,就其本质,即就其种类而言,被奠基的行为只有建立在奠基性种类的行为上才是可能的。”(Hua XIX, II/2, A650/B2178)梅勒所说的这种奠基顺序的不可逆性曾经被布伦塔诺定义为“单方面的可分离性”,即没有感受-评价行为和意愿行为,理智行为还是可以想象的;而没有意愿行为,感受-评价行为也还是可想象的;但反之则不成立。*参见U. Melle, “Husserl’s personalist ethics”, a.a.O., S. 4.这个奠基顺序也是为康德哲学所主张的,并且在布伦塔诺那里以“每一个行为或者是一个表象,或者以表象为基础”*[德]布伦塔诺:《出自经验立场的心理学》,汉堡:费利克斯·麦纳出版社,1973年,第1卷第2篇第1章第3节,第120页:“它们[心理现象]或者就是表象,或者建基于作为其基础的表象之上。”的方式而得到体现。胡塞尔继承了这个传统,在总体上将非客体化的行为视作必须奠基于客体化行为之中的行为。*对此还可以参见U. Melle, “Objektivierende und nicht-objektivierende Akte”, in Samuel Ijsseling (ed.), Husserl-Ausgabe und Husserl-Forschung, Phaenomenologica 115,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Boston/London, S. 35-49;倪梁康:《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的奠基关系问题——从唯识学和现象学的角度看识与智的关系》,《哲学研究》2008年第11期,第80—87页;倪梁康:《客体化行为与非客体化行为的奠基关系再论——从儒家心学与现象学的角度看“未发”与“已发”的关系》,《哲学研究》2012年第8期,第28—35页。
这个奠基顺序也可以在佛教唯识学这门有着漫长的跨民族、跨语言历史的东方意识哲学中找到应和与支持。世亲以来的唯识学将意识或“心”(citta)分为八种(阿赖耶、末那、前六识),它们意味着心的主体;而从属于它们的精神作用或心的现象则有五十一种(如惭、愧、忿、覆、悭、嫉、恼、害、恨、谄、诳、憍等),它们被称作“心所”(caitta)。从“心王-心所”的命名上已经可以看出,在它们之间也存在着一种不可逆的奠基关系。
但在舍勒的人格结构分析中,这个“意向的(intendierend)”向度被“感受的(fühlend)”向度所取代。这并不表明舍勒取消了胡塞尔“意向性”的视角。舍勒同样区分意向的和非意向的感受。舍勒的做法仅仅意味着,在他那里,感受的向度取代了意向的向度,成为其人格现象学或感受现象学(Gefühlsphänomenologie)的核心范畴。在这一点上,他在很大程度上与海德格尔处在同一战线上,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处在与胡塞尔相对立的战线中。*对此还可以参见倪梁康:《现象学背景中的意向性问题》,《学术月刊》2006年第6期,第47—50页。在《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一书“前言”中,舍勒曾介绍过他的思考和研究系统:除了当时即将出版的社会学和宗教哲学方向上的研究成果之外,他在这部代表作发表前就已经“在感受现象学的(gefühlsphänomenologisch)、道德批判的和伦理学运用方面”发表了一些研究成果(GW 2,4)。*[瑞典]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伯尔尼:弗兰克出版社,1980年;中文本,倪梁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4页。(以下引用舍勒时仅在正文中给出《舍勒全集》的卷数和页码,即中文本的边码)。事实上,与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相比,舍勒的现象学研究是以对感受的分析见长的,他对爱与恨、同情、羞耻、恭敬、屈辱、怨恨*舍勒对同情、羞耻、恭敬等情感心理的分析以及他提出的“伦常明察”的概念,意味着他已经对孟子所提到所有德性四端都做了感受现象学的讨论。等感受的描述分析已经成为感受现象学研究的经典,并且越来越强烈地影响着今天的情感问题讨论,无论这些讨论是以情感哲学或情感社会学的名义进行,还是以感受理论研究或情感历史研究的名义进行。*前一类的研究文献例如可以参见Christoph Demmerling/Hilge Landweer, Philosophie der Gefühle: Von Achtung bis Zorn, Verlag J.B. Metzler: Stuttgart 2007;Heiner Hastedt, Gefühle: Philosophische Bemerkungen, Reclam-Verlag: Stuttgart 2005。后一类的研究文献例如可以参见Agnes Heller, Theorie der Gefühle, VSA-Verlag: Hamburg 1981,该书的第一部分题为“感受的现象学(Phänomenologie der Gefühle)”,第二部分题为“感受的社会学”;此外还可以参见Jan Plamper, Geschichte und Gefühl: Grundlagen der Emotionsgeschichte, Siedler Verlag: München 2012, Ute Frevert (Autor), Bernhard Jussen (Herausgeber), Susanne Scholz (Herausgeber), Vergängliche Gefühle, Wallstein Verlag: Göttingen 2013, Eva Weber-Guskar, Die Klarheit der Gefühle:Was es heiβt, Emotionen zuverstehen, Walter de Gruyter: Berlin, 2009。值得注意的是,从自然科学角度讨论感受问题的文献可以被视作第三类,它们大都未没有顾及舍勒的研究。例如参见Martin Hartmann, Gefühle-Wie die Wissenschaften sie erklären, Campus Verlag: Frankfurt/New York 2005, Joseph LeDoux, The Emotional Brain. The Mysterious Underpinnings of Emotional Life, Simon and Schuster: New York, 1996.
但与今天大多数情感哲学的努力不同,舍勒并不只是进行一些孤立的感受现象学分析,反对在此意义上的片断、零碎的“连环画现象学(Bilderbuchphänomenologie)”*[瑞典]舍勒:《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质料的价值伦理学》,同上书,第11页。这个批评也可以被用来针对胡塞尔的“非历史的”的现象学(GW VII, 330)。海德格尔正是在此意义上——无论他在用词上是否受到过舍勒的影响——批评胡塞尔:“由于每个结构最终都必须在其自身上得到指明,现象学的研究方式首先获得了一种如人们所说的连环画现象学的特征或视角,即人们根据个别的结构去做出指明,这种结构也许对于一种体系哲学来说是非常有用的,但一种指明却只能是某种暂时的东西。”(GA 20, 120)海德格尔在这里说的“人们”,很可能就是指舍勒。,而是试图将它们纳入自己的价值感受现象学和人格主义伦理学的系统,指出它们之间的奠基关系。因此,他在进行具体的感受分析的同时也强调“对体系的意愿”的合理性,强调“实事本身构成一个体系的联系”(GW 2,3-4)。
在舍勒看来,现象学哲学所具有的“体系的特征”并不是其操作者自行编排的,而是由实事本身,即“心的秩序(Ordre du cur)”所决定的,因而是“哲学在任何奠基中、也包括在其现象学的奠基中所应有的特征”(GW 2,3)。但他所直观到的“心的秩序”似乎与胡塞尔所明察到的意识本质结构或“体验的数理模式(Mathesis der Erlebnisse)”*胡塞尔:《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海牙,1976年,页158。——以下引用胡塞尔文字时仅在正文中给出《胡塞尔全集》的卷数和页码(中文本的边码)。并不完全一致。概括地说,如果指向对象的表象行为在胡塞尔那里构成一切行为活动的基础,那么在舍勒那里,这个基础是由指向价值的感受行为所奠定的。*对此还可以参见倪梁康: “The Problem of the Phenomenology of Feelingin Husserl and Scheler”, in K.-Y. Lau and J.J. Drummond (eds.), Husserl’s Logical Investigations in the New Century: Western and Chinese Perspectives, Springer: Dordrecht 2007, pp. 67-82.张任之在其《质料先天与人格生成——对舍勒现象学的质料价值论的重构》(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年,第168及以后各页)一书的3.3.1“理性或情感:胡塞尔与舍勒现象学伦理学的建基”一节中对此也有更为详尽的讨论。这个意义上的意识分析在舍勒的《形式主义》书中得到特别的强调:“感受活动原初地指向一种特有的对象,这便是‘价值’。所以‘感受活动’才会是一种有意义的感受活动并且因此而是一种能够‘被充实’和‘不被充实’的事情。”他还特别注释说明,“因此,所有‘关于……的感受活动’(Fühlen von)也原则上是‘可理解的’”(GW 2,263)。从舍勒的论述来看,感受活动并不始终行使构造对象的功能。据此,舍勒意义上的“感受”具有比胡塞尔的“感受”概念宽泛得多的外延。它甚至把表象和判断的活动,即舍勒所说的“认知的功能”也包含在自身之中,例如对真假的判别等等。
这种价值感受活动在舍勒那里是同样具有直接的和根本的特征。在胡塞尔那里,把握对象的最原本的和最基础的活动在胡塞尔那里是感知(Wahrnehmen)或认之为真(Für-wahr-halten),而在舍勒这里,最原本的和最基础的活动是价值感知(Wertnehmen)或认之为有价(Für-wert-halten)。“价值感知”的概念是胡塞尔在其价值论和伦理学分析中根据“感知”概念而生造的一个语词。看起来他很早便使用这个极具特色的概念,但似乎始终只是在手稿中运用它。胡塞尔在其身前未发表的《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二卷中写道:“这个概念标示着一个从属于感受领域的、与感知(Wahrnehmung)相似的东西,后者意味着在意见(doxisch)领域中原初地(自身把握地)亲在于对象本身。” 所谓“价值认知”,是指对客体之“价值”的直接原本把握,就像“感知”是对客体自身的原本把握一样。在这个意义上,“价值认知”也可以被理解为“认之为有价”,而“感知”也可以被译作“认之为真”。胡塞尔在这里还说,“我还在几十年前便将价值认定这个表达用来说明”“最原初的价值构造”。*Hua III/2, 9.此外还可以参见Ms. A VI 8 1, 88a。但“价值认定”的概念在胡塞尔1908-1914年的早期《伦理学与价值论讲座》中只在附录中出现一次。参见同上书,编者引论第XXXVI页,以及正文第370页。而在1920年和1924年夏季学期的后期《伦理学引论》中则出现许多次,不仅在讲座正文中,也在相关的附录中。参见《伦理学引论》,Hua XXXVII (Dordrecht u.a. 2004) 72 ff., 86, 113, 120等。就此而论,虽然胡塞尔较早使用这个概念,但成为其主要的伦理学概念则是战后的事情。很可能是舍勒通过与胡塞尔的交谈而非通过阅读胡塞尔的著作才获悉并接受这个概念。它后来也为舍勒运用在其伦理学研究中。*参见W. Henckmann, Max Scheler, Verlag C.H.Beck: München 1998, S. 104.如果在胡塞尔那里可以说,任何行为要么是对象感知,要么以对象感知为基础,那么在舍勒这里就可以说,任何行为要么是价值感受,要么以价值感受为基础。
价值感受之所以可以成为一切行为的基础,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价值感知活动的意向相关项,亦即价值所决定的。在舍勒这里,高价值是低价值的基础,即前者为后者奠基。“价值越是延续,它们也就‘越高’,与此相同,它们在‘延展性’和可分性方面参与得越少,它们也就越高;其次还相同的是,它们通过其他价值‘被奠基得’越少,它们也就越高,再次还相同的是,与对它们之感受相联结的‘满足’越深,它们也就越高;最后还相同的是,对它们的感受在‘感受’与‘偏好’的特定本质载体设定上所具有的相对性越少,它们也就越高。”(GW II,107)
另一方面,这个价值感受的秩序也与价值感知的不同内涵种类的奠基秩序相关。就像在胡塞尔这里,想象材料(Phanstama, Phantasiegehalt)必定奠基于感觉材料(Sinnesdaten, Wahrnehmungsgehalt)之中一样,舍勒在这里也指出,“仍然决定着统一生物之统一兴趣方向的并不是觉知内涵(Perzeptionsgehalt),这种内涵必定已经被给予‘兴趣’,但决定着这个方向的却可以是觉知内涵的感情内涵(sensitiven Gehalt)”(GW 2,164)。这意味着,在舍勒这里同样存在着一种不可逆的奠基关系,但顺序与胡塞尔理解的恰恰相反:觉知内涵是奠基于感情内涵之中的。虽然,从胡塞尔的角度来看,这里的奠基关系也可以做发生意义上的“前客体化行为”与“客体化行为”的发生奠基关系来理解,类似于前面所述之胡塞尔的行为引动(Aktregung)与行为进行(Aktvollzug)之间的关系。
无论如何,舍勒在此基础上已经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说:“对于认识的所有历史进步而言都有效的是,这个认识的进步所把握的对象在被理智认识、分析和评判之前,首先必须被爱或恨。‘爱者(Liebhaber)’处处都先行于‘知者(Kenner)’。”(GW 5,81)而且这一点同样对哲学有效,因为“对于叫做哲学的这种特殊认识而言,本质必然的前提乃是一种道德态度。”(GW 5,78,83)这个观点,也成为舍勒的世界观哲学之主张的理论支撑,以及他强调实践理性优先于理论理性的根据,从而使他在一定程度上对立于胡塞尔的哲学作为严格科学的主张以及胡塞尔坚持的理论哲学作为第一哲学的理解。这也是海德格尔所说“胡塞尔与舍勒在问题的提法和处理方面、在世界观的倾向上大相径庭”(GA II,47)的原因所在。
舍勒认为,这是对伦理学的一种根本重建。在他看来,伦理学在其历史上“或者被构建为一门绝对先天的伦理学,而后是理性的伦理学,或者被构建为相对经验的和情感的伦理学”。思想史上只有几个思想家对这个成见进行了撼动,如奥古斯丁和帕斯卡尔,但他们也并未做出新的构建。他本人从根本上予以重建的乃是“一门绝对的并且情感的伦理学”。(GW 2,157)
由于对奠基次序的理解差异,胡塞尔与舍勒各自的人格现象学方案在这里似乎形成根本对立。*值得注意的是,耿宁在对儒家哲学中的阳明心学传统进行了长期研究之后似乎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在奠基次序的问题上开始持与舍勒新近的观点。他在2012年在中山大学举行的研讨会上曾说:“任何意识行为首先都是道德意识,而后才是认知意识。”在此问题上,他作为胡塞尔追随者似乎离舍勒比离胡塞尔更近。但我们在后面还要考察对这个说法的另一种可能解读。
四、胡塞尔与舍勒的人格发生现象学
1.笔者在这里所使用的“似乎”一词已经暗示,胡塞尔与舍勒在奠基次序问题上的分歧很可能不属于真正的对立,而只是由观察角度和解释方式的差异引起的理解与解释的偏差。在实事上他们所把握到的很可能是同一个东西。或许海德格尔已经注意到了这一点,因而他在上引文字中除了确认胡塞尔与舍勒的人格阐释之间差异的同时还指出他们之间的关键性的相同之处:“尽管胡塞尔与舍勒在问题的提法和处理方面、在世界观的倾向上大相径庭,但他们的人格阐释在否定方面却是一致的。它们都不再提‘人格存在’本身的问题。”(GA 2,47)这里提到的“人格存在”本身,是指胡塞尔和舍勒都不再把这种第一个意义上的“人格”看作是固定的对象、不变的本体、与客体相对立的主体,而是视作历史的、整体的、流动的精神生命活动。
这一点可以从人格发生现象学的角度来展开深入的考察。发生现象学的可能性是胡塞尔在《纯粹现象学与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1913年)完成后才开始系统思考的问题。*黑尔德曾指出:“写完《观念》I之后,胡塞尔越来越清楚地看到这样一个任务,即在个别的构造理论之间建立起系统的总体联系,这个联系应当可以解释,是什么将意向意识的所有视域结合为一个世界意识。”([德]克劳斯·黑尔德:《导言》,[德]胡塞尔:《生活世界现象学》,倪梁康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第32页。)但在1905/1906年的《内时间意识现象学讲座》中,胡塞尔实际上已经涉及“时间问题”与“发生问题”之间的关联。在此之后,胡塞尔不再将发生研究完全视作经验事实性的研究,而是开始考虑它作为本质研究的可能性,并且在大量研究手稿的基础上最终在1929年的《笛卡尔式的沉思》中讨论“普全发生的形式合规律性”。*对此问题的详细说明可以参见倪梁康:《纵意向性:时间、发生、历史——胡塞尔对它们之间内在关联的理解》,《哲学分析》2010年第2期,第60—78页。


胡塞尔本人只是在时间意识分析的讨论中使用了“纵意向性”的概念,用它来说明贯穿意识之流中,并在其流程中持续地与自己本身处在相合统一之中的意向性。“纵意向性”可以说是线性的意向性,它意味着“第一个原感觉在绝对的过渡中流动着地转变为它的滞留,这个滞留又转变为对此滞留的滞留,如此等等”,并且与点状的、即作为意识流横截面的“横意向性”一同组成“意识流的双重意向性”(Hua X,435,482)。但我们在这里可以像胡塞尔那样将“时间”理解为“所有本我论发生的普全形式”(Hua I,§ 37)。具体说来,每个意识行为,无论是表象的还是感受的,无论是表达的还是判断的,都在时间流的进程中从当下沉入到过去,并以潜意识的方式作用于新的当下意识行为。这就是胡塞尔所描述的状况:“经验作为个人的习性是一种在生活过程中以往自然经验执态行为的沉淀(Niederschlag)。它本质上是被这样一种方式所决定的,这种方式是指:个人性(Persönlichkeit)这种特别的个体性(Individualität)是如何通过本己的经验行为而受到在动机方面之引发的;这种方式同样是指:个体本身是如何以本己的赞同和拒绝的方式而受到陌生的和传习的经验的影响的。”(Hua XXV,48)当然,不仅每个意识行为都受到过去的意识行为及其沉淀的影响,并且它同时又会以类似的方式影响着将来的经验及其积淀。我们在后面将会看到,这种作为“习性现象学”讨论课题*关于胡塞尔的“习性现象学”,可以参见莫兰的研究:Dermot Morana, “Edmund Husserl’s Phenomenology of Habituality and Habitus”, in Journal of the British Society for Phenomenology, 42:1,2011, pp. 53-77.的意识经验状况与佛教唯识学中所说的“种(Bīja)熏(vāsanā)”观念是一致的。*对此问题可以参见杨惠南:《成唯识论中时间与种熏观念的研究》,氏著:《佛教思想新论》,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8年,第271—300页。
这里需要特别留意胡塞尔在人格发生问题上所做的三个方面的描述分析:
首先,在胡塞尔看来,人格是在发生中的统一。他指出:“本我(ego)并不将自己仅仅把握为流动的生活,而是把握为作为同一者体验着这个或那个、经历着这个和那个我思的自我。”(Hua I, 100)在这里和后面我们可以看到,人格在胡塞尔那里与本我(ego)以及其后期的、即《笛卡尔式的沉思》中的自我(Ich)概念是基本同义的。正是在此意义上,人格可以被理解为纵意向活动的意向相关项,或者说,“是诸体验的普全的、本质的相关性的相关项”*Shigeru Taguchi, Das Problem des ,Ur-Ich ‘bei Edmund Husserl -DieFrage nach der selbstverständ- lichen, Nähe ‘des Selbst, Phaenomenologlca 178, Springer: Dordrecht, 2006, S. 116.。但这个意向相关项是线性的而非点状的。即便是对当下自我的反思,也是由对彰显的当下本我(自我连同其当下体验)的感知以及对潜隐的过去本我(自我连同其过去体验)和将来本我(自我连同其未来体验)的回忆与期待所构成的。*这里已经涉及意识的根本结构“共现”问题。对此笔者在《现象学意识分析中的“共现”》(《鹅湖学志》2016年第6期)一文的第五节“流动的共现”中有较为详细的描述分析。这也可以说明,为什么胡塞尔早期将自我理解为空泛而无内容的极点(Hua XIX, A 335/B1357),因为他那时对自我的理解是点状的,而他后期将自我理解为“诸习性的基质”(Hua I, 100),因为这时他对自我的理解是线性的。
其次,这里的线性奠基关系在胡塞尔看来与点状的奠基关系一样,都是有规律可寻的,因为“由于自我作为恒久的自我特性之同一基质的自我从本己的主动发生中构造起自身,它在进一步的进展中也将自己构造成稳固的、恒久的人格自我”(Hua I,101),而且“借助于一种‘超越论发生’的合规律性,自我会随着它所发出的每一个新的对象意义的行为而获得一个新的恒久特性”(Hua I,100)。人格因此而获得某种可把握的习性意义和个性意义,亦即具有一种“超越论发生的合规律性”,他也被胡塞尔称作“动机引发的规律性”,它是“精神生活的基本规律性”(Hua IV,211),亦即人格发生的基本规律性。
最后,这种规律性与时间性有内在的关联。人格发生的规律性是纵意向性的规律性,亦即时间性的规律性。意识流的抽象时间形式与意识行为的具体发生内容在这里的融合为一,并以一种线性的奠基的方式规定着在其中形成并贯穿于其中的线性人格自我。对于胡塞尔来说,“无论在我的自我中以及本质上在一个本我一般中出现什么——在意向体验方面、在被构造的统一方面、在自我的习性方面——,它都具有其时间性,并且在这方面参与了普全时间性的形式系统,每个可想象的本我都自为地借助于这个系统而构造起自身”(Hua I, 108)。人格发生的纵意向奠基关系在这里获得时间性的维度。
这个意义上的“人格”不仅以彰显的方式生活在当下点上,而且以潜隐的方式同时地生活在纵贯的生命线中。如果我们在这里仍然坚持使用“人格存在本身”的概念,那么这里的“存在”所表明的更多是一个动词而非名词,因此我们也可以理解舍勒所说的“人格生成(Personwerden)”*就舍勒的“人格生成”的概念需要说明:从总体上看,舍勒的人格讨论主要集中在其生成和发生的维度,人格的共时统一或静态统一问题并不构成他的思考核心内容。而胡塞尔在其前、后期对人格的横、纵意向性分别则做出各有偏重的思考,因此可以各有偏重地思考意识(或人格)的共时统一或同时统一以及意识(或人格)的历时统一或演替统一问题。关于舍勒的人格生成问题,可以参见张任之:《质料先天与人格生成——对舍勒现象学的质料价值伦理学的重构》,同上书,第350及以后各页。。它在人格的第一意义上意味着精神生活,不仅是“我的自我”的精神生活,本质上也是“本我一般”的精神生活。
关于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联将是我们后面第二部分讨论的问题,即单个的人格与其他人格的关系问题。在这个部分中我们能够确定的是,胡塞尔通过对人格的发生现象学的探讨,勾勒了一条在普遍时间形式中从作为“诸习性基质”(Hua I, 100)的“人格自我”的精神生活到“作为人格生成的精神世界的文化”(Hua III/2, 597)的发生构造步骤。这也可以通过泽伯姆对胡塞尔《观念II》的解读所确定的在人格发生构造过程中的两个基本步骤而得到验证:首先是人格的心灵世界的发生构造,即“人格在其中以内省的方式发现自己,并且在同感中以表征的方式发现其他(诸)人格的那个世界”;其次是“更高阶次的共同体世界、精神世界,也包括其他的共同体”的发生构造,它们“在不同层次上具有不同的共同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一个文化的精神、一个宗教的精神,等等”。*T.M. Seebohm,“Husserl on the Human Sciences in Ideen II”, a.a.O., S. 134.这里所揭示的发生构造的步骤也就是本文开始时所引胡塞尔致普凡德尔信中所说的从“人格现象学”到“更高级次的人格性现象学”的进程,即从人格自我的意识体验现象学进入到人类精神生活和文化世界现象学的进程。
胡塞尔本人在《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中曾将这些发生构造的成就理解为世界观的培育和构造的能力,并且写道:“无须再进一步阐述,在这个特定的、尽管包含着杂多类型和价值等级的意义上的智慧或世界观不仅仅是单个的个性(Persönlichkeit)的成就,这种单个的个性本来就是一种抽象;这种智慧或世界观属于文化的共同体和时代,而就它所具有这些鲜明形式而论,如果我们不仅仅是谈论一个特定个体的教化和世界观,而是谈论这个时代的教化和世界观,那将会具有好的意义。这尤其适用于现在将要探讨的这些形式。”(Hua XXV,49)因此,对于胡塞尔来说,哲学本身不是世界观,但以世界观为探讨的对象,在此意义上,现象学是一种新的“世界观哲学,它在巨大的体系中为生活和世界的谜提供相对而言最完善的回答,即以最佳可能的方式来解决并令人满意地澄清那些不确定性,那些只能为经验、智慧、单纯的世界和生活观所不完善地加以克服的生活之理论、价值、实践的不确定性”(Hua XXV,50)。
从普全的时间形式,到交互人格的精神生活,再到由各种传统和习性构成的共同体的历史——文化传统的历史、民族精神的历史、宗教信仰的历史等等,这是一条贯穿在胡塞尔中、后期哲学思考中的红线,指示着他从时间现象学到发生现象学再到历史现象学的思想脉络。这是一条完全不同于结构性奠基的发生性奠基的思想脉络。*如果了解胡塞尔从早期时间分析,到中期的发生结构描述,再到后期的历史哲学思考的总体进程,舍勒就会修改他在1921年所做的“胡塞尔是非历史的”(GW 7, 330)的论断。当然,海德格尔也会收回他对胡塞尔人格研究的“再度回返……最终以笛卡尔为指南的”批评(GA 20,166)。
在这里,奠基性的东西不再是客体化行为的进行,而是非客体化的行为引动。
2.这个思想脉络同样可以在佛教唯识学的意识分析中找到对应的命题:正如唯识学在横意向性方向上有四分说和心王、心所说一样,它在纵意向性方向上还区分意识发生的三种能变(trividha-vijāna-parinama):作为初能变的阿赖耶、作为二能变的末那和作为三能变的前六识。在这三种能变之间存在着发生方面的不可逆的奠基关系。尽管玄奘的《成唯识论》中提到这三种能变各有四分,但依照唯识学经典的描述分析,除了三能变明显与现象学所说的客体化行为相对应之外,前两种能变更应当被视为非客体化的行为。也就是说,它们甚至不能称作通常意义上的“识(Vijnana)”*《解深密经》胜义谛相品第二。。这是因为:首先,阿赖耶的特征按《解深密经》的说法是“微细极微细,甚深极甚深,难通达极难通达”*佛教文献中常有“阿赖耶识(ālaya-vijāna)”和“末那识(manas-vijāna)”的说法。但严格说来,阿赖耶是“心”,末那是意,只有前六识才是“识”。,按《成唯识论》的说法也是“极微细故,难可了知”*玄奘:《成唯识论》卷二。,类似于心理学所说的“无意识”、“下意识”或“潜意识”,抑或是胡塞尔所说的“前自我(Vor-Ich)”,很难将它视为客体化行为;其次,末那识的特征被刻画为“由有末那,恒起我执”*玄奘:《成唯识论》卷四。,“四烦恼常俱,谓我痴、我见,并我慢、我爱,及余触等俱”*世亲:《唯识三十颂》第六颂。,类似于非对象性的、前反思的自我意识,它在前六识形成后通过反思才成为对象性的自我意识,具有类似胡塞尔所说的“原自我(Ur-Ich)”的功能,*“前自我”在胡塞尔那里被视作“最终的发生起源(letzter Ursprung der Gesesis)”,对立于作为“最终的效用起源(letzter Ursprung der Geltung)”的“原自我”。对此问题的讨论参见Nam-In Lee, Edmund Husserls Phänomenologie der Instinkte, Phaenomenologlca 128, Kluwer Academic Publishers: Dordrecht, 1993, S. 214 ff. 更为详细的论述还可以参见Shigeru Taguchi, Das Problem des ,Ur-Ich ‘bei Edmund Husserl, a.a.O., S. 116 ff.即是说,前者是纵意向性奠基关系中的最终奠基者,后者是横意向性奠基关系中的最终奠基者。因此,在“前自我”与“原自我”之间并不存在类似“阿赖耶识”和“末那识”之间的发生先后的奠基关系。但“原自我”与“末那识”之间仍有相似性,这是我们日后要深入讨论的课题。因而显然也难以归入客体化行为的一类。
此外,这里还值得注意胡塞尔在1934年6月的一份手稿中对“意向性的两个层次”区分:其一是“无自我的趋向、无自我的本欲”,其二是“自我的欲求的-追求的生活连同行为生活、连同以所有意志样式愿欲着的自我的生活”(Hua XXXIV, 470)。这两个层次可以用来刻画末那产生之前的非客体化、无自我或原自我-无自我的意识发生阶段,以及末那产生之后的客体化的、有自我的意识阶段。

唯识学也确定这个奠基关系的不可逆,因为“一切种子,皆本性有,不从熏生,由熏习力,但可增长”。*玄奘:《成唯识论》卷二。即是说,种子是熏习的可能性条件,但反之则不然。不过,熏习虽然不能产生种子,却可以使种子“由熏增长”*玄奘:《成唯识论》卷二。,并使得本来在种子中潜藏的内识发展成客体化的行为,即产生出主客体(我法)的分别。按唯识宗的说法:“我法分别,熏习力故。诸识生时,变似我法。此我法相,虽在内识,而由分别,似外境现。”*玄奘:《成唯识论》卷二。这意味着,先有非客体化的本性,而后通过细微的现行活动的熏习,产生出我-法分别的客体化行为,再通过这些认知和情感、意愿方面的客体化行为的现行活动,导致习性的形成,习性暂时或持久地附着于本性之上,并以此方式影响着本性。对于“种子生现行,现行熏种子”过程的思考,唯识学与胡塞尔在缘起-发生现象学方面的思考是基本一致的,只是在术语上有所不同:唯识学所说的“能变”或“生起”,在胡塞尔这里叫做“发生”;而胡塞尔更多会用“积淀”或“习性化”来表达唯识学借助“熏习”来说明的东西。
据此可以说,无论在佛教唯识学中,还是在胡塞尔的现象学中,发生问题都是人格研究(在唯识学那里是心、意、识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它们都确立一个从非客体化行为到客体化行为的发生奠基次序。*事实上,黑尔德用来阐释胡塞尔发生现象学的一段清楚、扼要的文化,在经过必要修正之后完全也适用于唯识学的阿赖耶缘起理论:“人类文化的所有对象都曾是通过原创立(Urstiftung)所具有的那种构成对象的成就而构造起自身的。随着每一次的原创立,意识便从此而赢得了一种一再地向新的对象回溯的权能性(Vermöglichkeit);这就意味着,对相关对象的经验逐渐成为习惯。这种‘习性化’(Habitualisierung),或者也可以说,这种‘积淀’(Sedimentierung)是一个被动的过程,即不是一个由我作为实行者而启动的过程。原创立的创造行为在这里通常会被遗忘。这种习惯逐渐成为一种亲熟性,即非课题地亲熟了这种对有关对象的经验的权能性。但这就意味着:通过对原创立的被动习性化,一个视域被构造起来,意识便持续地生活在这个视域中,它并不需要在原创立的主动性中一再地重新进行这个视域的原初形成。带着这个思想,构造理论获得了一个全新的维度。逐渐成为它的基本课题的是视域意识在其中得以形成和丰富的内部历史,它的‘发生’(Genesis)。”([德]黑尔德:《导言》,《生活世界现象学》,倪梁康译,第33页。)
3.这种发生奠基的维度在舍勒这里也可以找到,尽管它在术语上并未得到清楚的标明,而且舍勒对“发生”的理解在许多方面并不与胡塞尔的和唯识学的发生理解相一致。
在其早期著述中,无论是在早期发表的《超越论方法和心理学方法》中,还是已经写成并付印、但最终被舍勒抽回而最终未发表的《逻辑学》中,舍勒在阐述和批评心理学方法时都将实际的情感和认识活动的产生与积累更多理解为心理学意义上的“发生”,即经验性的和时间性的发生,并将这个意义上的发生研究的方法视作“发生的因果说明”。在此意义上,他或者批评传统的和当代的哲学考察都囿于包括“发生的因果说明”在内的许多狭隘的工作任务:“所有的哲学考察,即使它们自称为认识论、逻辑学、美学、形而上学,都会将自己的任务仅仅视作对特定的意识事实系列的确立、描述、分类以及对它们的发生做因果说明。若有人想要求哲学超出这些任务,那么最终的结果总是臆想一场。”(GW 1, 308)或者他也将“发生描述”划归给心理学研究:“确定目的设定的正确性,这是伦理学的事情而非逻辑学的事情。研究对象设定的正确性,这是逻辑学的事情而非伦理学的事情。研究作为心灵生活具体事实的思维活动和意愿活动,即描述目的表象及其发生以及心理再造进程,这是心理学的事情。”(GW 14, 31)带着这种对发生研究的理解,舍勒在其代表作《形式主义》书中明确否认这种通常意义上的因果发生的奠基:“显而易见,认识‘起源’的问题也完全独立于那些通过在客观时间中的实在主体而对特定的事物现实之认识的所有发生(Genese)。‘奠基’仅只存在于行为构造的秩序(Ordnung)之中,而不存在于行为的时间实在顺序(Abfolge)中。”(GW 2,91)
但是,舍勒仍然会在积极的意义上谈及“发生”,例如他曾指出在有价值的事物与纯粹事物和纯粹善业之间存在的被给予性顺序:“从发生(Genese)的起源性的立场来看,我们觉得情况毋宁说是这样的:在自然世界观中,实在对象‘首先’既非作为纯粹事物、也非作为纯粹善业而被给予,而是作为‘实事’(Sache),即作为就其是有价值的而言的(并且本质上是有用的)事物。但从这个中间点——可以说——出发,对纯粹事物与纯粹善业的总和(在持续地忽略一切事物本性的情况下)而后便得以开始。”(GW 2,44)这里所说的“起源性的发生”,很可能还是被舍勒理解为某种属于“构造的秩序”方面的奠基,即在被给予之物之间的结构奠基或有效性奠基。但在这里的确可以使用“发生奠基”的标示了,因为这种发生奠基显然不是指经验性的、时间性的、历史性的发生顺序,而是舍勒所说的“独立于所有经验发生的”(GW 2,143)起源奠基,或者说,在“观念的形态发生(Morphgenese)”(GW 11, 240)方面的奠基。
因此,在舍勒这里的确可以发现一种不同于与经验的、时间的发生以及相关心理学的发生研究的本质发生,它是“人类精神的所有主观起作用的先天结构的真实的和真正的发生”(GW 8,27)。这种发生的奠基次序不仅表现所谓实在对象先于纯粹事物和纯粹事业的被给予性方面,也表现在例如“一切价值,也包括一切可能的实事价值,此外还有一切非人格的共同体和组织的价值,都隶属于人格价值”(GW 2, 14)这个人格主义原理上。而且,由于各种价值始终处在与价值感受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中,因而发生奠基的法则既对各种作为意向相关项的价值之间的关系有效,也对各种作为意向活动的价值感受活动之间的关系有效,价值与价值感受在这里共同构成上述“人类精神的先天结构”的两个部分。*这里可以留意舍勒对“先天-后天”与“天生”和“习得”这两对概念的区分,后者“是因果发生的概念,因而在事关明察之种类的地方没有它们的位置”。(GW 2, 96)
舍勒强调这个精神结构不是单数,而是复数。单数的精神结构意味着一批“始终仅仅与一个精神结构和一个在时间和地点上受到限定的文化单位相应的作品之累积”(GW 8,27),它“被理解为设定绝对时间形态的动态生命过程的暂时凝结的构成物”(GW 11,240),并且在此意义上是固持的(konstant)、僵化的(erstarrte);而复数的精神结构意味着各种人类精神能力的发展和转变,因而它们是真正流动的、发生的结构,倘若“结构”这个表达在这里仍然合适的话。它实际上就是舍勒所强调的动态的精神生命过程,它作为“河流(Strom)”与“暂时凝结的构成物”或“始终被一个过去存在和一个将来存在所围绕流动的”意识瞬间的“横切面(Querschnitt)”形成对照(GW II,423)。在此意义上,舍勒谈及对精神生活的“静态的”和“动态的”定义、在比较社会学研究或文化社会学研究中的“静态的”和“动态的”理解,以及如此等等。这两个描述词在舍勒那里基本等同于我们这里所说的“结构的”和“发生的”。(参见GW VI,14;GW VII,94;GW VIII,23)
我们现在可以对前面曾引述过的舍勒对行为之间奠基关系的理解做一重审:“对于认识的所有历史进步而言都有效的是,这个认识的进步所把握的对象在被理智认识、分析和评判之前,首先必须被爱或恨。‘爱者’处处都先行于‘知者’。”(GW 5,81)此时我们应当可以发现:舍勒这里所强调的“首先”和“先行”实际上是对在动态或发生意义上的奠基关系的描述。*还有一个更直接的例子,舍勒在“爱与认识”(1916年)中曾批评历史上对“爱与认识”的一个异教错觉,即“在动态方面,爱不是先行于认识,而是追随着认识”(GW VI83)。他在此无疑是在“发生”的意义上使用“动态”一词。
至此已经可以看出,胡塞尔与舍勒各自对意识行为或精神活动(Tätigkeiten)中两种奠基关系的理解具有重大的一致性:他们都看到了结构的和发生的(或静态的和动态的)奠基的两种可能性,也承认后者相对于前者所具有的更为整全和更为重要的意义。这与佛教传统强调缘起胜于强调实相的做法相一致。胡塞尔与舍勒在此问题上的根本不同在于,前者将“普全发生的形式合规律性”看作意识发生的“纵意向性”,后者则将这种发生的奠基纳入以人格生成方式进行的精神生命活动之“心的生成秩序”或“心的发生逻辑”来考察。
在舍勒的人格主义理论中,这两种奠基关系(静态的和动态的)以人格存在和人格生成的方式表现出来:“生命是一个发生、一个过程。它只能以作用的-动态的方式被定义。任何静态的定义对它来说都是不充分的,而且从任何带有空间中的固定形式的构造物出发,它都是无法把握的。生命是一种只能从生成出发才能把握的存在。”(GW 11, 161-162)在这里,静态的生命存在与动态的生命生成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舍勒在前引文字中所提到的作为意识瞬间的“横切面(Querschnitt)”与作为意识整体的“河流(Strom)”之间的关系(GW 2,423)。这里应当留意这个“横切面”的说法。无独有偶,胡塞尔也曾在完全相同的意义上谈及意识分析中的“横切面”以及它与“整体”的关系:“出于本质理由而是一的东西,人们就无法将其撕扯开来。特殊的认识论问题和理性理论问题一般与理性这个首先是经验的权能标题相符合(只要它们产生于其超越论的纯化之中),它们只是意识与自我问题一般的横切面,而一个横切面只有在其整体得到研究时才可能完整地被理解。”(Hua XXV, 198)显然,舍勒用“[精神]生命是一种只能从生成出发才能把握的存在”与胡塞尔用“[意识]横切面只有在其整体得到研究时才可能完整地被理解”的相同说法所表达的是他们在人格研究中的相同明见或相同信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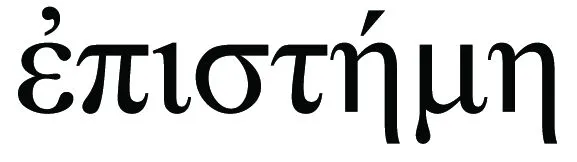
舍勒在这里所表达的对胡塞尔观点的双重(肯定的和否定的)态度涉及一个根本问题:如果哲学是科学,那么这种科学本身是世界观,还是独立于世界观之外?胡塞尔认为哲学独立于世界观之外,它以各种世界观的构成为自己思考和分析的对象,但本身不是世界观。这个观点也与胡塞尔早期对自然观点进行悬搁的要求以及后期以生活世界为课题的理论要求相一致。而舍勒则主张科学本身是一种世界观:自然科学是自然的世界观,哲学则是道德的世界观。因此,道德态度是哲学认识的必要前提,并且在本质上支配着(disponieren)哲学的认识(GW 5,78、89)。
这里的分歧的确如舍勒所说与二人在“语言使用”方面的差异有关,但它们更多还是在精神生活研究中因对两种不同视角的强调而形成的区别:动态的精神生活过程与静态的精神生活结构。只要胡塞尔与舍勒都将历史上的各种哲学流派和哲学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生活方式,那么哲学就与世界观一样属于精神生活,并且自身发生地、动态地奠基于各类情感、道德、习俗之中。但只要胡塞尔与舍勒都认为,可以通过现象学的反思和明察而在这个精神生活中把握到各种精神生活(表象、情感、意愿、态度、立场、信仰等)及其构造物(事物、价值、他人、社会、世界、观念、习俗、信念等)的基本类型与基本构成,以及把握到它们之间的静态奠基关系,那么哲学就不是世界观,而是一种对包括世界观在内的精神生活一般进行描述和分析的学说,并在二阶的意义上脱出了一阶的精神生活。
胡塞尔和舍勒都会赞同这个定义:哲学或现象学是一种起源于精神生活之中的一种对精神生活的本质自身认识。
五、结构的形而上学与发生的形而上学
如果我们在此回到笔者在前节开始时提出的假设上来,即胡塞尔与舍勒在奠基次序问题上的貌似分歧很可能并不属于真正的对立,而只是由观察角度和解释方式的差异引起的理解与解释的偏差,那么这个当初的假设现在基本上可以被视为一个事实认定了。应当说,胡塞尔与舍勒都已经注意到了这两种不同的奠基类型。虽然他们在各自的意识分析中对不同的奠基类型的指明和处理,但他们在总体上都没有完全偏执于一端,也没有试图用一端去取代另一端。他们二人实际上都站在一个现代哲学发展的交会点上:结构的现象学与发生的现象学的交会点,或者展开来说,逻辑哲学与历史哲学的交会点。这同时也意味着欧洲哲学中笛卡尔-康德动机与维柯-黑格尔动机的交会点。当然,他们之所以能够到达这个交会点,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是狄尔泰、纳托尔普等人的历史哲学和发生思想的引领。
而胡塞尔和舍勒关于静态与动态、结构与发生方面的奠基思想也已经发挥自己的影响。处在二人共同影响下的A.舒茨很早(1931年)便将这些思考转用于社会学研究的领域,并提出在社会学研究中带有本质特征的一项主要任务就在于,“在静态的和动态的分析中意向地阐释那些全都奠基在已完成的他我(alter ego)构造之中的较高层次的社会行为和社会构成物的杂多形式,并且因此而指明实证的社会科学的先天结构。”*A. Schütz, Alfred Schütz Werkausgabe, Bd. III, Philosophisch-phänomenologische Schriften 1, Zur Kritik der Phänomenologie Edmund Husserls, UVK Verlagsgesellschaft mbH: Konstanz, 2009, S. 76.
这两种奠基关系或两种现象学的思考后来在海德格尔那里通过“第一开端”和“另一开端”(GA 65,205)、“形而上学”和“存在历史的思考”(GA 65,1)等表述而得到阐释和界定。笔者也将它们称作“第一形而上学”(或曰“结构的形而上学”)与“另一形而上学”(或曰“发生的形而上学”)。但在海德格尔这里已经可以发现用发生的奠基取代结构的奠基、从而也用发生的形而上学取代结构的形而上学的趋向。海德格尔已经不再处于胡塞尔和舍勒曾在交会点上,而是踏上了两条道路中的一条。但我们只能在其他地方展开讨论这个问题。*对此可以参见笔者在《海德格尔思想中的黑格尔-狄尔泰动机》(《学术月刊》2014年第1期)以及《论海德格尔中期哲学的本体论与方法论——关于〈哲学论稿〉核心概念的中译及其思考》(《南京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二文中的相关论述。
在讨论了胡塞尔与舍勒在人格研究方面隐含的共同视角之后,这里有必要指出他们在此研究领域的各自不同的着眼点:舍勒讨论的问题,恰恰是胡塞尔不讨论的问题——人和神,或者说,人格与“一切人格的人格”(GW 7,86),又或者说,人与在他之中的永恒之物。*舍勒的人格研究的目光主要落在“人格”与“位格”的关系问题上。这两者在帕斯卡尔和舍勒这里都以“寻神者”的方式合而为一。海德格尔将舍勒的人格主义称之为“神形论(Theomorphismus)”(参见[德]海德格尔:GA 20,第181页);亨克曼则将它标示为“覆盖了(überformt)天主教的现象学哲学”(W.Henckmann, Max Scheler, a.a.O., S. 29)。前者在舍勒那里表现为哲学人类学,后者在他那里表现为人格主义的神学。而如果这两者成为哲学研究的首要课题,那么它们就会被胡塞尔称之为人类主义和形而上学。在胡塞尔这里,它们也会成为现象学哲学的对象,但不是首要的纯粹现象学课题。
多瑞恩·凯恩斯曾记录过他与晚年胡塞尔的一次交谈(1931年8月22日),在其中胡塞尔谈到舍勒,并形象地描述了舍勒的哲学思考与自己的哲学思考的区别:“本体论证明的现象学方式是从绝对的构造性意识中得出的结论……所有这些问题都要等到最后才能得到解决;但它们是如此引人入胜,以至于人们会试图一跃而起地(in Aufschwung, soarting)进入到形而上学之中——这是舍勒在刻画形而上学特征时使用的表达。然而在展翅飞翔之前我们要先练习爬行;只有在地上下足了苦功的人才能最终御风而行。”*凯恩斯:《与胡塞尔和芬克的交谈》,《现象学丛书》第66卷,海牙:马尔梯努斯·奈伊霍夫出版社,1976年,第23页(中译文参考了余洋的译本初稿)。这里所说的舍勒的“跃起(Aufschwung)”,应当与我们这里多次引用过的舍勒长文《论哲学的本质与哲学认识的道德条件》中第三节“道德跃起的分析”讨论的内容有关。舍勒在这里分两部分讨论了“A.跃起行为作为‘完整的人’的人格行为”以及“B.跃起的出发点和要素”。(GW 5,83-92)或许这里还有必要指出,舍勒在此使用的“跃起”概念,类似于海德格尔使用的“绽出(Ex-statik)”或“超越(Transzendenz)”(GA 15,384;GA 24,230)。由此可见,胡塞尔自己也认为他与舍勒的分歧仅在于如何循序渐进地展开工作。这里的进步次序固然很重要,因为它关系实事本身的奠基次序。但这个进步所朝向的共同目的地似乎已经被胡塞尔所默认。因此,我们也可以大致领会胡塞尔在同一谈话中所说:“超越论构造的问题与上帝如何创造了一个绝对世界并如何继续其创造的问题别无二致,这也是超越论的交互主体性创造世界的问题。”*凯恩斯:《与胡塞尔和芬克的交谈》,同上书,第22页。前引文中所谓“下足苦工”,大概就是指在超越论的交互主体性领域内的苦心孤诣与殚精竭虑。这是我们在下一章中所要面对的论题,它已经隐含在人格概念的语义之中。
(责任编辑 任 之)
倪梁康,(广州 510275)中山大学哲学系暨现象学研究所教授。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胡塞尔文集》中译”(12&ZD124)
B516.52
A
1000-7660(2017)01-0073-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