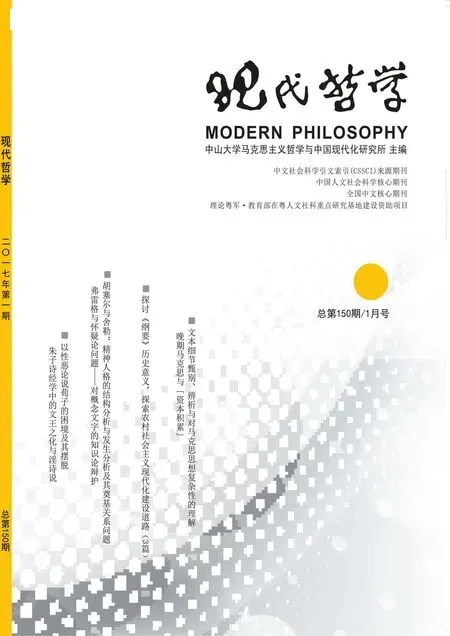描述与主体
——开掘《逻辑哲学论》中的“语用”意识
2017-01-28邹晓东
邹晓东
描述与主体
——开掘《逻辑哲学论》中的“语用”意识
邹晓东
《逻辑哲学论》预设唯独描述句有意义。准此,“主体”因无法充当被描述的客体,理应作为无意义的术语销声匿迹。秉承贝克莱思路,前期维特根斯坦对此心知肚明,却又“神秘”兮兮地主张“主体是世界的界限”。此与“唯独描述句有意义”原则扞格难容。究竟为何不能干脆放弃“主体”概念?站在语用角度看,语句的意义来自主体的使用。《逻辑哲学论》对“主体”概念的超常执着表明,怀揣“精确描述”之理想的前期维特根斯,坦已然触及到了某种带有全局性的“语用”意识。进一步的语用分析则表明:“绝对精确”的理想语言只属于全知者主体,现实中的描述句则总是在作者主体-读者主体默契的语言游戏中实时赋义。
描述句;主体;外在表达;内在心态;共鸣或默契;即时赋义
维特根斯坦在《逻辑哲学论》持“语言是图像”的观点*这一点从论题3、4.01、4.015、4.016等中的“图像”、“画像”、“描画”、“象形文字”等用词便可见一斑。另可参见韩林合《〈逻辑哲学论〉研究》(修订、完整版),二·二逻辑图像论、四·二命题的图像性质。本文所引《逻辑哲学论》译文,均取自韩林合:《〈逻辑哲学论〉研究》(修订、完整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该书第831—840页是“论题索引”,据此可以很方便地检索每个论题译文所在的页码,本文因而只提供维特根斯坦对论题的编号,而不再标注译文所在页码。此外,我还重点参考了D. F. Pears & B. F. McGuinness的英译本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Routledge & Kegan Paul Ltd, 1974),必要时本文也会征引这个译本。贺绍甲先生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译本(北京,1996年),即主要依据此英译本译出。,这意味着“唯独描述句有意义”。与此同时,《逻辑哲学论》明确意识到:正如眼睛无法看到自己,主体亦无法描述那正在从事描述活动的自己。准此,“主体”理应被作为无意义的术语被彻底清除。但《逻辑哲学论》却旋即“神秘”兮兮地主张“主体是世界的界限”。究竟什么原因使得该书无法彻底放弃“主体”概念呢?
《逻辑哲学论》中的“主体”,实即描述句的使用者,即造句者和解读者。该书对“主体”概念不惜代价的执着表明,前期维特根斯坦已经触及到了某种带有全局性的“语用”意识*黄敏针对论题3.262评论道:“这意味着只有在使用中我们才会有命题,从而,使得命题具有确定涵义的所有条件都属于使用……”见氏著《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文本疏义》,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99页。。本文基本任务是:从描述与主体的悖论性关系,引申出描述句的语用问题,进而结合后期维特根斯坦的思想遗产,考察描述句在实际使用中的赋义*用“意义”或“赋义”统称《逻辑哲学论》中的“涵义(sense,意义)”、“意指(meaning,所指,意味)”,也许会令一些维特根斯坦专家不满。这样做的依据是,论题3.3曰:“只有命题才有意义(sense);只有在一个命题的关联中一个名称才有所指(meaning)。”就此而言,“命题的涵义(sense,意义)”、“名称的意指(meaning,所指,意味)”,是内在关联而非相互孤立的。机制。
一、唯独描述句有意义,“主体”无法被描述
《逻辑哲学论》对于“描述句(有意义的命题)”有着严格的限定,分而言之即两个“必须”:1.作为基本元素,构成描述句的“名称”、构成被描述的事实/事态*《逻辑哲学论》在使用“事实”一词时,侧重于“事态是否现实存在”。也就是说,描述句完全可以描述现实中不存在的“事态”,这样的描述句在“事实”上为假,但此“假”毫不妨碍此描述句意义充足。本文不探讨描述句的真假问题,出于方便计采取“事实/事态”这种提法。的“对象”,必须一一对应;2.名称在描述句中的结合形式、对象在事实/事态中的结合形式,必须完全一致,即二者具有一致的“逻辑形式”*参考韩林合:《〈逻辑哲学论〉研究》(修订、完整版),三·四、四·二、四·五、五·一。。这个看似静态的限定,蕴含着操作(语言使用)上的指导。要想造出严格有意义的描述句,描述者必须充分分析被描述的事实/事态,将其分解为不可再分的最小元素(对象),并把握这些元素的结合形式(逻辑形式)。这种充分的分析,是描述者能够遵循“名称、对象一一对应”、“逻辑形式完全一致”原则造句的前提。
造句的过程,也是描述者在思想中再现相应事实/事态的过程,能动的思想是在名称、对象(以及两种结合形式)之间建立影射关系的中介。不难指出,这个作为中介的描述者或思想,是主体;而被分析、被再现的事实/事态,以及被构造的描述句,则是客体*值得一提的是,“对象(object)”本身即可译为“客体”。。
在西方哲学史上,“主客二分”导致了严峻的符合论困境*贝克莱这样追问:“不过凝聚的、有形的、被动的实体,纵然可以在心外存在,与我们所有的物体观念相符合,我们又如何能知道这一点呢?”参见[英]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一部第18节。“二分”的鸿沟禁止思想者越出“观念”谈论“是否符合存在”,“观念符合存在”这一“真知识”标准因而沦为无稽之谈。。为了消解这种困境,贝克莱在《人类知识原理》中自觉揭示并高举“存在就是被感知”*[英]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关文运译,第一部第4节。原理。这条“唯心主义”原理一经揭示,便以近乎无法反驳的逻辑约束力,规范着近现代西方哲学史的发展。按照这条原理,所谓的“存在”或“客观世界”,归根结底不过是谈论者自己的“观念”或“观念之全体”。作为主体的“谈论者自己”严格来讲似乎只能是一个个的“我”*在不考虑“主体间性”或“交互主体性”问题的情况下,“主体”即原子式的“我”。后期维特根斯坦对“私人语言”的反驳,意味着只有“交互主体”或“主体间性”才是现实存在着的“主体”,此当另文专论。。鉴于此,《逻辑哲学论》(论题5.64)遂将上述贝克莱思路命名为“唯我论”,论题5.641更是不无赞许地指出:“我是经由如下事实而出现于哲学之中的:‘世界是我的世界。’”“世界是我的世界”实乃贝克莱“存在就是被(我)感知”的翻版。
关于“感知者”主体,贝克莱写道:它又被称为“心灵”、“精神”、“灵魂”或“自我”,但无论如何,它“不表示我的任何观念,只表示完全和观念不同的另一种东西”*[英]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关文运译,第一部第2节。。但何谓“表示”呢?作为对“主体”的谈论,“表示完全和观念不同的另一种东西”不也是一种“观念”吗?如果这种谈论根本不是“观念”,则“主体”就根本无法被感知,按照“存在就是被感知”原理,这意味着“根本不存在主体”。这是内含于《人类知识原理》中的逻辑困境,《逻辑哲学论》作为贝克莱“唯我论”思路的继承者,同样深陷这种纠结。
我们通过分析两组论题,来呈现这种纠结:
论题1 世界是所有实际情况。
论题1.1 世界是事实而非物的总和。
论题2 实际情况,事实,是诸基本事态的存在。
论题2.06 诸基本事态的存在和不存在是实在。
论题2.063 全部的实在是世界。
通过混用“实际情况(all that is the case,所是的情况)”、“事态(state of affair)”、“事实(facts)”、“实在(reality)”这四个术语,上述论题致力于消解西方哲学中强调“‘第一性的性质’比‘第二性的性质’更实在(更是事实)”*可参见[英]贝克莱《人类知识原理》第一部第9节:“有些人把各种性质分为第一性的和第二性的两种……”的传统。附着在“事实(fact)”、“实在(reality)”术语上的“第一性的性质”意味,被“所是的情况(that is the case,实际情况)”、“事态(state of affairs)”的口语色彩大大冲淡。如此一来,作为“事实的总和”或“全部的实在”的“世界”,无非就是最宽泛意义上的“情况”或“事态”之全体。那么,“主体”是不是这“世界”的组成部分?
论题2.1曰:“我们为自己绘制事实的图像。”“绘制事实的图像”即“描述事实”,“可被描述性”是“事实”的基本特征。作为“主体”的“我们”,则是主动的描述者,而非被描述的客体。就此而言,“主体”不是“事实”(不具备“可被描述性”),因而不是“世界”的组成部分。
关于这一点,《逻辑哲学论》给出了一个形象的说法:
论题5.633 可以在世界中的什么地方看到形而上主体?你说:这里的情况与眼睛和视野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但是,实际上,你并没有看到眼睛。我们从视野中的任何东西都推导不出如下结论:它是被一个眼睛看到的。
此时此刻的真正“主体”,是那正在从事描述的描述者;任何被描述的“自己”,则无一例外都是受动的客体。被反思或被描述的“自己”,不是作为“主体”的自己,这在西方哲学史研究中被称为“主体倒退”问题*可参考谢文郁:《自由与生存:西方思想史上的自由观追踪》,张秀华、王天民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73—174页。。真正的主体既然无法作为客体被描述,那么,维特根斯坦为什么不干脆按照“唯独描述句有意义”原则,合乎逻辑地放弃“无意义”的“主体”概念?
二、神秘的“世界的界限”即“看待世界的眼光”
《逻辑哲学论》把“主体”重新界定为“世界的界限”(论题5.632、5.641),为了区别于“心理学事实”(参考论题4.1121),又称之为“哲学的我”、“形而上主体”(论题5.641)。什么意思呢?“世界的界限”也许可以理解为“盛装世界的容器”,此所谓“盛装”在贝克莱意义上即“感知”。而按照贝克莱的逻辑,作为“感知者”的“世界的界限”,是无法被描述的:
论题6.45 世界是一个有限的(limited)整体,这种感受是神秘的。
在唯独描述句有意义预设下,“神秘的”亦即“非描述性的=无意义的”。尽管“神秘的感受”提法带有拒绝诠释的倾向,但作为精心编织的表述,“主体是世界的界限”、“世界是一个有限的整体”等提法总归是有意义的。而一旦承认这种非描述性表述有意义,就等于打破了唯独描述句有意义的总则。
论题6.522 的确存在着不可言说的东西。它们显示自身,它们就是神秘的事项。
“神秘的事项”虽“不可言说(无法被描述)”,但却能“显示自身”。基于这种“显示”机制,可否发展出“非描述性的”另类语言呢?《逻辑哲学论》对此显得“口非心是”。论题7曰:“对于不可言说的东西,人们必须以沉默待之。”但在《逻辑哲学论》提出“主体是世界的界限”之类神秘兮兮的提法之际,它自己都无法恪守“沉默”的诫命。
写到最后,维特根斯坦不得不自己猛打自己的耳光:
论题6.54 我的命题以如下方式起着说明的作用:理解我的人,当他借助于这些命题——踩着它们——爬过它们之后,最终认识到它们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可以说,在登上梯子之后,他必须将梯子弃置一边。)
他必须放弃这些命题,然后他便正确地看待世界了。
作为苦心孤诣的哲学名著,《逻辑哲学论》当然是有意义的。“我的命题……没有任何意义”仅意味着,这些论题均非描述句。一本旨在高举“唯独描述句有意义”原则的著作,竟然通篇以非描述句写就——这究竟是什么逻辑?
论题6.54宣称:理解了《逻辑哲学论》的人,能够“正确地看待世界”。在唯独描述句有意义预设下,“正确地看待世界”即“以描述者的眼光看待世界”。考虑到把握“逻辑形式”是描述的基础,看出或领会逻辑形式之自我显示实为“描述者眼光”的本质。不过,按照本文上节的分析,作为“主体”的“眼光”是无法被描述的。但《逻辑哲学论》的旨趣,归根结底正在于向读者引荐一种作为生存视角的“描述者眼光”(难怪乎维特根斯坦会夫子自道说该书是一部“伦理学著作”*参考[奥]维特根斯坦:《致路德维希·冯·费克尔的信》,转引自[美]谢尔兹:《逻辑与罪》,黄敏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页。!),故对之不可能无所论述。迫不得已,它只好自相矛盾地宣布:本书论题虽然“起着说明的作用”,但却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以下两节,我们分别从造句、解读两个方面,进一步考察这种“描述者眼光”。
三、造句的主体:“思想-图像”与“指”的意向
《逻辑哲学论》在探讨语言命题(描述句)之前,先引入了“图像-思想”概念,例如:
论题2.1 我们为自己绘制事实的图像。
论题3 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
论题2.1中的“为自己”意味着,“绘制图像”属于描画者的认识或理解。这种作为认识理解的“图像”,被论题3称为“思想”。可见,《逻辑哲学论》中的“图像”,并非“物理图片”。离开“思想”活动,物理图片毫无意义可言。
物理性的“事实/事态”,原则上都“可被感官知觉”:
论题3.1 在命题中思想获得了可被感官知觉的表达。
描述句(命题)之所以具有“描述”功能,关键在于它是“思想”的“表达”。这种“表达”关系的成立,始终依赖描述者的“思想”活动:
论题3.11 我们使用感官可以知觉的命题符号(声音或书写符号)作为可能事态的投影。投影的方法是对命题-意义进行思维。
“对……进行思维(to think of)”,用的是“思想”的动词形式。在论题2.1511-2.1515中,维特根斯坦已经表示:作为“思想”的“图像”“触及到实在”,“像一把尺子一样被置于实在之上”,“只有刻度线的最外端的点才接触到所要度量的对象”。“我们使用……作为投影”之“我们”,严格来讲只能是动词性的“思想-图像”本身,这是描述关系赖以成立的动态中介。
再做一点补充说明。一个指称复合对象(其实是事实/事态)的名称,严格来讲并无准确指向。前期维特根斯坦认为这不是语言的理想状态,因而追求绝对精确的理想描述句。为此,描述句作者需将被描述的事实/事态分析到“简单对象”的层次。“简单对象”只可命名而无可描述(论题2.02-2.021、3.221、3.23),其“所是”即其在“逻辑形式”中占据的节点(参考论题2.0233)。换言之,指出一个“简单对象”,即领会相应的“逻辑形式”;对“指称”进行思维,就是对“逻辑形式”进行思维;反之亦然。
《逻辑哲学论》认为描述句(命题)自动“显示”*论题4.121的英译使用了两个词——“显示/show”、“展示/display”——二者在使用上,似无本质区别。其逻辑形式(论题4.121、4.1212),“投影的方法/对命题-意义进行思维”因而似乎无须多言。描述句(命题)由名称构成,论题3.203谓“名称指称对象”,3.22曰“名称在命题中代表对象”——“对命题-意义进行思维”必然涉及对“指称”进行思维(=对“逻辑形式”进行思维)。那么,这究竟是怎样一种“思维”?“指称”是一种进行中的动作,这个问题因而首先涉及到何谓理解一个动作?
举例来说:某人扔了一下石头。假设有多位摄影师,连续不断地从不同角度记录了此人扔石头的过程,那么,我如何借助这些记录,理解此人的“扔石头”动作呢?假如我仔细察看每一段视频,尽可能地记住此人在每个瞬间的身体形状,这样,我就算理解了这个“扔石头”的动作吗?仅仅由色彩、光、影组成的图片记忆,并不包含石头的沉甸甸感、身体的扭动感、扔的爆发感等等;在这些主观(主体性)感受,缺场的情况下,谈何对“扔石头”动作的理解?这里,本真意义上的“理解”,要求我以某种方式亲身体验一下类似的动作。
类似地,“指称”既然是一种动作,描述者在对它进行思维时,便必须亲自尝试“指向”动作。可以说,描述者造句时所选用的一个个名称,犹如一根根尖锐的手指,指向(“触及”)构成被描述事实/事态的一个个对象。而作为“思想”的“指称”,其实就是“指”的意向。
总之,描述句的作者,是凭着“指”的意向造句的*参考韩林合:《〈逻辑哲学论〉研究》(修订、完整版),第133页。。现在来看,论题6.54所谓的“正确地看待世界”的描述者眼光,其本质正是“指”的意向*值得一提的是,《逻辑哲学论》论题4.112强调:“哲学[‘使思想变得清楚’、‘命题的澄清’、‘思想的逻辑澄清’]不是任何理论,而是一种活动(activity)”。。既然如此,如何把握造句者试图藉描述句传达的“指”的意向,就成为解读一个描述句的关键所在。
四、解读的主体:“文盲、半文盲”与“全知者”
本节再来考察“描述句读者的眼光”,也即如何“解读一个描述句”。我们从“逻辑形式”(前已指出它与“指称”或“‘指’的意向”等价)的辨认问题谈起。
“逻辑形式”与“结构”概念接近,而剔除了“结构”的“质料”因素,可谓“纯粹的形式”。同一个“逻辑形式(纯粹的形式)”,可以内在于不同的“结构体”中。例如,写在纸上的乐谱和按照该乐谱演奏出来的音乐,一为墨迹结构体,一为声音结构体,但从乐理角度看二者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因为这种形式上的同构关系,我们说,乐谱描述了声调,声调演奏了乐谱。描述句和被描述者的关系与此类似。
但反过来看,描述句和被描述者虽然具有相同的“逻辑形式”,但它们毕竟是两个不同的事实/事态。“文盲、半文盲”现象最能凸显这种差别。一字不识的文盲,看到写在纸上的描述句段落,只能形成“白纸黑字的墨迹”印象。半文盲则边读边猜,他据此构想出来的“图像”,较之实情难免走样。可见,描述句逻辑形式之“显示”,受制于读者的主体性。
现实语言中的“名称”(如“鲁迅”、“阿Q”、“Green”等)通常并非“简单的对象”,它们本身具有特定“结构形式”。以这样的名称联缀成句,其固有的“结构形式”,不可避免会对读者辨认句子的“逻辑形式”构成干扰。*试看论题3.323中的例句:“Green is green”,“Green”和“green”字母拼写相同,易给初学者带来困惑。鉴于此,论题3.325提出了“逻辑语法”或“逻辑句法”的概念,试图诉诸完美的“语法”或“句法”规避上述混淆。问题在于,谁能准确无误地掌握这种“逻辑语法/逻辑句法(完美语法/完美句法)”,而成为理想描述句的理想读者呢?
造句者本人,似乎是第一人选。然而,造句者必须严格“不忘初心”,丝毫不差地保持着当初配置“两个必须”时的主观体验,即自己当初对“指称-逻辑形式”的思维。任何遗忘,都会导致“逻辑语法/逻辑句法”对他来说不再“透明”,因而使他沦为“文盲、半文盲”。考虑到“遗忘”的可能性,造句者本人的理想读者身份并非必然的。而换个角度看,其他读者也完全可以成为相应语句的理想读者,只要他充分通达了造句者当初的“主观体验”,即造句者造句时的“描述者眼光”。
维特根斯坦在1929年重返哲学领域之后写了一篇小文,题为《略论逻辑形式》。该文最后论及如何才能“制定出这样的规则”,认为“做到究极的分析”是使用理想语言的基本条件:
不过,在我们对有关的这些现象已实际做到究极的分析之前,还不可能制定出这样的规则。众所周知,我们尚未达到这个地步。*[奥]维特根斯坦:《维特根斯坦全集》第1卷,涂纪亮主编,陈启伟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74页。
“究极的分析”即从“复合事实/复合事态”到“基本事实/基本事态”与“简单对象”的分析。“对象”的“简单性”(不可再分、无可描述)是精确描述的前提,论题4.2211因而断言“必然存在着对象和基本事实”。在“究极的分析”基础上构造出来的描述句,在《逻辑哲学论》中被称为“完全分析了的命题”(论题3.2、3.201)。不过,《略论逻辑形式》最终却冷峻地直言:“我们尚未达到这个地步!”这意味着现实中的我们和绝对精确的理想描述句无缘。
“究极(完全)的分析”与“绝对精确的描述句”,归根结底只属于“全知者”主体。作为普通描述者,尽管我可以精心打理自己的描述句系统,努力做到同一个名称严格对应我所认识的同一个简单对象。但历史尚未终结,我的后续人生阅历将不断刷新我的相关认识,我原本以为简单的对象因此将显得不那么简单。新一轮的“使同一个名称严格对应我所认识的同一个简单对象”的“分析”工作遂重新提上议程,一系列更精确的描述句亦应运而生。除非使用者对过去、现在、未来之一切有了绝对精确的认识,否则出乎意料的新事实/新事态总会将“分析”的任务重新摆上桌面。而一个精确地认识了过去、现在、未来之一切的语言使用者,正是不折不扣的“全知者”。
遗憾的是,相对于全知者的“全知”,局限于特定历史时空的普通人类则是“文盲、半文盲”,根本没有能力恰如其分地玩转这套绝对精确的理想描述句系统。就此而言,即便存在“究极(完全)的分析”的理想语言,那也只能是全知者的“私人语言”或局限于全知者之间的“内部语言”。
五、“共鸣”或“默契”中的“即时赋义”
假设某作者已经造出一套绝对精确的描述句系统,假设他自己总能万无一失地正确使用其中的每一个句子,那么站在造福社会(使人类语言理想化)的角度,该作者如何推广这套理想语言?人类社会现有的日常语言精度不够,以之传授理想语言,自然无法取得理想的教学效果。理想语言尚未通行,径以之教学,闻者难免云里雾里。理想语言即便存在,终究还是无法推广困境。
后期维特根斯坦对此深有体会,《哲学研究》第一部分第85节云:
一条规则立在那里,就像一个路标。——路标不容我怀疑我该走的是哪条路吗?它是否指示出我走过路标之后该往哪个方向走?是沿着大路还是小径,抑或越野而行?但是哪里又写着我该在什么意义上跟从路标——是沿着箭头的方向还是(例如)沿着箭头的反方向?——但若不是一个路标,而是一串相互衔接的路标,或者地上用粉笔做的记号——难道它们只有一种解释吗?——以至于,我可以说,路标并没有留下任何怀疑的余地。或更恰当是说:它有时留下了,有时没留下。而这已不再是一个哲学命题,而是一个经验命题了。*[奥]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陈嘉映译,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6页。引用时参考G. E. M. Anscombe英译本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将“那么”改为“以至于”。
犹如“路标”“立在那里”的“规则”,即语法命题。正如“路标”在理解中可能出现歧义一样,语法命题的理解同样可能出现分歧。意识到并承认这一点,语言分析就不得不向日常语言与生活世界回归。“这已不再是一个哲学命题,而是一个经验命题了”意味着,《逻辑哲学论》通篇使用的另类语言(非描述句),无非就是日常语言在前期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中的临场发挥。
前期维特根斯坦虽然追求绝对精确的描述理想,但却并不认为理想语言(假如存在)的意义对所有人都当下自明。而作为公共语言,日常语言中的语词需要在使用者的共识中赋义,“指”的理解问题则是共识达成的关键。关于“指”,《逻辑哲学论》有如下说法:
论题3.263 诸初始符号的所指可以经由说明(Erläuterungen/elucidation)得到解释。所谓说明是指包含着这些初始符号的命题。因此,只有在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些符号的所指的情况下,我们才能理解这些说明。
韩林合认为,论题3.263中的“说明”,实即后期维特根斯坦所谓的“指物识字”或“实指定义”。言者说出诸如“这就是牡丹花”之类的“包含着初始符号的命题”,同时向听者做出“指示牡丹花”的动作。“说明或实指定义是语言和实在的最终的接触点,只是经过它们语言才最终与实在联系在一起了。”*参考韩林合:《〈逻辑哲学论〉研究》(修订、完整版),第140页;[奥]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第一部分第6小节。“指”,是描述的本质。
在现实交往中,作为外在表达的“指”,未必总能准确传达“指”的意向,反而可能导致这样或那样的误解。追加新的“指”,未必总能澄清误解,有时反而会弄巧成拙,连“你的这个理解误解了我的那个意思”都不知所云。现实中,基于“指”的语言游戏,究竟是怎么玩转的呢?
日常生活中有“情感共鸣”的提法,它涉及到情感的传达及理解问题——我怎样向对方传达我的情感,以及我怎样才算理解了对方的情感状态?交流中的双方尽可诉诸口头或书面语言表达各自的情感,乃至采用“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的肢体语言,但是,这些外在的表达并不直接等于内在的情感体验。特别地,机械地复述或模仿这些口头、书面或肢体语言,并不等于切身理解了对方所要表达的情感体验。显然,只有亲身体验到对方所经历的那种情感,我才算切身理解了对方的情感状态。“情感共鸣”提法强调的便是这种“感同身受”的关系。在感同身受的“共鸣”中,理解者本着自己的“相似情感”体验,理解被理解者的情感状态。这个观察还可进一步推广:一般来说,理解者只能本着自己的“相似心态”,理解被理解者的内在心态。此可谓一般意义上的“共鸣”*《逻辑哲学论》谓“命题显示其逻辑形式”(论题4.121、4.1212)。“显示其逻辑形式”与“指称对象”本质上是一回事,描述句本质上无异于人的手指。前期维特根斯坦所谓的“显示”,移植到日常语言分析中,即本文所谓的“共鸣”或“默契”。。
然而,理解者用以理解对方的“相似心态”,是否真的与对方所经历的内在心态相似?在现实生活中,情不自禁的恶意揣度、不知不觉的一厢情愿屡见不鲜,这些都是自以为相似而实际上并不相似的实例。但尽管如此,“共鸣”的基石地位仍然无法取消,因为在“共鸣”之外语言使用者根本找不到更客观的“相似心态”判定途径。道理很简单:看似“客观”的外在表达,究竟传递了怎样的“心态”体验,终究还是需要判定者在“共鸣”中加以把握。任何力求“客观”的心理学研究,归根结底仍然需要研究者在“共鸣”中,将被研究者的外在行为与特定心理体验挂钩。
实际上,“情不自禁的恶意揣度”、“不知不觉的一厢情愿”等,都是时过境迁之后的新判断。一方面,在事发当初,当事人本着鲜活的“共鸣”感信誓旦旦地认定了对方的心态。甚至,即便对方矢口否认他的认定,他还是有可能信誓旦旦地认为对方是顾虑特殊处境不敢实话实说等等,乃至自信“我们心照不宣达成了‘默契’”。另一方面,时过境迁之后,当初的听者即便否决了自己当初的判断,而对对方通过言语所欲传达的心态有了新的判断-理解,那么,这种否决与新判断-新理解也还是在“共鸣”或“默契”中达成的。长远来看,现实中的语言交流,无非就是一轮接一轮的“共鸣(默契)——打破——新共鸣(新默契)……”
小 结
《逻辑哲学论》中的“主体”即描述句的使用者(造句者、解读者),“语用”意识下的“赋义”问题是《逻辑哲学论》中未能充分展开的一道暗流。从“唯独描述句有意义”与“主体无法被描述”悖论入手,本文分析这条暗流指出:1.主体只能本着自己的相似内在心态,理解对方试图表达的内在心态;2.在语言使用的每一个当下,“共鸣感”或“默契感”是判定“相似心态”的唯一标识,离开当下的“共鸣感”或“默契感”,语言交流寸步难行;3.在情境与表达发生变化之际,原有的“共鸣感”或“默契感”会被打破,并被新的“共鸣感”或“默契感”取代,使用者对词句的赋义相应地发生变化。
《哲学研究》第一部分第19小节说:“想象一种语言就叫做想象一种生活样式。”《逻辑哲学论》论题4.002则谓,日常语言的规则“隐而未宣”且“极度复杂”。对于成年人来说,大多数日常语句的赋义过程似乎已经完结,每个句子通常都有大体不变的意义。但即便这样的句子,在变化了的生活情境中,亦每每被用得出人意料——试看当今互联网语言。读者若溺于旧情境中的“共鸣”或“默契”,则领会了微妙的新用法的使用者就会不断加以“指引”与“纠正”,直到他认为在对方那里已经产生了新的“默契”或“共鸣”,而指引者-纠正者的这种“认为”当然也是一种“默契”或“共鸣”。日常语言的规则之所以“隐而未宣”且“极度复杂”,正是因为它充满了在新的情境与新的使用方式中不时迸发“新共鸣”或“新默契”的可能性。对此有了冷静的觉察之后,原本执着于“绝对精确”之描述理想的维特根斯坦,便不得不进入充满变数的日常“生活”世界。
(责任编辑 任 之)
邹晓东,山东莱西人,哲学博士,(济南 250100)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暨中国诠释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马克思主义实践认识论的认知模态:一种新诠释”(16CZX006)
B151
A
1000-7660(2017)01-0118-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