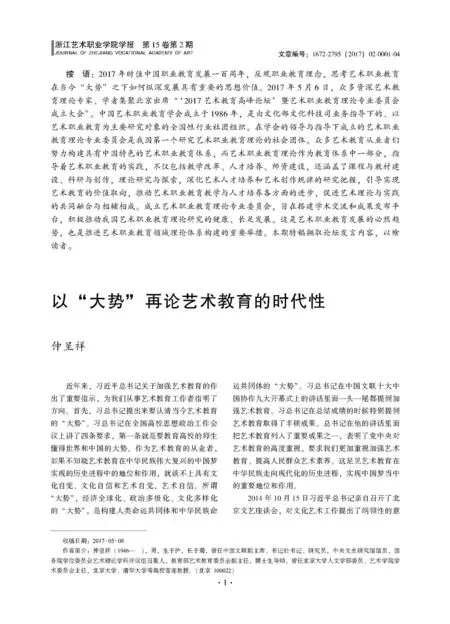科学把握高职教育本质 深度挖掘艺术职教内涵
2017-01-28许平
许 平
科学把握高职教育本质 深度挖掘艺术职教内涵
许 平
在职业教育百年发展的新机遇下思考艺术职业教育,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一直是从事设计教育的,其实对设计教育是属于艺术教育,还是属于职业教育,还是属于艺术职业教育,这归属问题本身就是蛮大的一个理论问题。但是我认为,也许它是艺术职业教育的一个另类,时至今日,也应当把它放在艺术教育的范畴里面来整理思考。
关于设计职业教育现状,第一个是目前我们国家设计教育发展的规模。根据最新中国美术学院中国艺术教育研究院的平台上2016版 “全国设计教育规模调查”的调研报告可知,目前我们国内各种高校中开设设计及相关专业教育的院校 (包括综合性大学、理工学校、高职高专学校、独立学院和单科艺术院校),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讲的 “设计高校”的总数已经达到2007所,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字。我们在2009年曾经和英国剑桥大学、英国设计委员会的 “世界各国设计竞争力排行榜”研究报告做过比较,根据他们公布的数字,中国的这个教育规模绝对是世界第一了。当时英国剑桥的调研是从全世界100多个设计比较发达的国家中挑选了42个,再从42个国家与地区里又选了前11个作详细的数据比对。这前11个设计最活跃的国家,同时也是设计教育最发达的国家。排在第一的是美国,每年设计专业毕业生是38000多人;排在第二的是韩国,每年33000多人;排在第三的是日本,每年28000多人;排在第四的是英国,每年16000多人。中国呢?2013年全国开设设计专业的高校招收的设计专业新生人数达到的554700多人,而2012年达到峰值时曾经是57万多人。根据中国的教育国情,入学人数几乎等同于毕业人数,因此可以理解为中国每年向社会投放的设计及相关专业人数至少为55万以上。而按每位入学新生在校学习年限基本为四年计算,则常年在校学习各种设计专业的学生人数将保持在200万以上。从这个规模来看,中国的设计教育规模已经绝对是全世界第一。当然,在2016年重新进行调研统计时,我们发现大势未变,但一些具体数字有所变化。
第一个数字是,在2012年达到峰值的时候,我国设计院校是1912所,到2013年时是1897所,已经出现一个小小的拐点,我们曾经认为它会继续下滑,但是没想到在2016年又回到了2000所以上,现在是2007所。这个变化是在教育部已经实现了部分学校的学科、专业调整、部分高校已经取消设计专业的情况下发生的,学校总数还在上升,并且达到2000所以上。但是,另外一个数字证实了一个发展的拐点开始出现——招生人数出现持续下滑。2016年设计专业新生入学的人数是54万多,比峰值的2012年57万下降了整整三万,就是说招收学生的势头已经开始有所减弱。也就是说,在办学单位对这一学科的投入仍然抱以较大期望和兴趣的同时,社会的响应程度已经开始下滑。对此,我们反倒认为是一个比较正常的,甚至还希望能够延续下去的趋势,因为不能再热,再热真要出问题。
第二个数字是,在这2007所院校的总体结构中发生了一个有趣的变化——高职院校的规模持续扩大。2016年的全国开设设计专业的高职高专院校数与招生数第一次全面超过了非高职类的普通高校。对此我们认为,这也是一件好事,或者说是一个转折点正在来临,值得期待。因为在我看来,高职教育对于设计这行业来讲,或许比普通本科教育有更明确的定位,社会针对性更强,承担的社会责任更重。反过来说,这种发展会 “倒逼”普通高等院校里的设计学科设计专业对自己提出反问,究竟设计学科应当是一个怎样的专业 “定位”,这已经是新形势之下必须要作出回答的现实问题了。前面已经说过,本科教育中的设计专业,到底它是应当属于艺术素质教育,还是属于专业能力教育,还是属于职业能力教育,究竟应当怎样给普通高校中的设计高等教育定位。由于对这些问题,没有做过理论上的梳理与探讨,就留下从宏观到微观、从政策到实践的许多问题,影响着各类学校对设计专业及学科的规划与引导。
目前职业教育界在筹备一件大事,就是即将要在2021年召开的,或者说2021年可能在中国上海召开的世界技能大会。前不久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向世界技能大会主席介绍中国的职业技能教育和宣传“工匠文化”、弘扬 “工匠精神”的热点,等等,以此表达中国政府的态度和对此事的关注。中国目前正在实行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以及 “中国制造2025”战略蓝图等,都离不开中国制造的能力基础,提高产业工人的生产技能已经是个非常现实的政治问题。中国政府希望通过世界技能大会,来促进大力宣扬的 “工匠精神”,能让中国制造力、经济竞争力有更多的黄金涵量,借此能力真正提高中国制造的尖端加工水平和创新实践能力,增强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和竞争力。这就是中国政府的态度和愿景。目前,各个方面已经在为准备2021年在上海举行世界技能大会作准备,以高职院校为主,全国已经组成41支国家队在进行培训,准备到时以高水平、高姿态参加世界性的职业能力角逐。其中既包含艺术项目、设计项目,也包含传统技术项目和许多新兴专业技术领域的项目,内容十分丰富。但目前主办国的竞争还有悬念,中国与瑞典都在竞办,待到尘埃落定。如果如愿,这将会是一个宣传职业技能的舆论热点,随着这个热点的到来,我们对于设计职业教育的思考,可能会变得更加现实且有针对性。
在这样的形势之下,我们应当怎样去理解职业教育,应当树立怎样的职业教育价值观,这个问题既基础,又根本;既老生常谈,又面临新的矛盾。但毫无疑问,它是我们要办好新时代的新高职教育的首要前提。
不知道各位有怎样的感觉,在很多的场合,谈到职业教育,总有一种低人一等的感觉,有种尚未回到正轨、甚至越走越偏的感觉。我也不知道在这样的场合适不合适说这样的话,我对目前教育部门有些决策不敢苟同,尤其是在部分高职院校实施所谓 “2+2” 教育模式。所谓 “2+2”,就是在高职院校的学生学习两年以后再送到名牌本科高校再学两年,然后变成本科名校培养出来的本科学生毕业,名曰 “打通”。我认为这是否定了高等职业教育本身完整性的短视的做法。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把高职教育变成了一个本科的预科教育,高职教育本身应有的完整过程和定位目标都被变相地取消了。这样一来,学生方面更不安心在高等职校学习,教学方面也更加没有心思把高职学科当成符合时代要求的高等教育。我觉得这种做法非常奇怪,与今天国家大量需要真正能在现场实现高质量生产和高水平管理的 “现场工程师”型的高级专门人才的目标要求大相径庭、适得其反,我不明白为什么还要大力推行。也许这件事在这里讨论并不合适。我只是在这里把问题提出来:到底什么是我们所需要的高等职业教育,什么是理想的设计职业教育?
关于职业教育,我有一个很个人化的、并不严谨的解释,称之为高职教育是塑造民族的良心之学。尽管这种说法很不学术很不规范,但我认为应当要从这样一个角度来理解职业教育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培训,它应当成为把职业能力送上现代轨道,成为一个面向未来的、真正打造社会生产能力、创造能力的树德立人的工程。我不敢说它是灵魂之学,因为我想文学是塑造民族的灵魂之学;我也不敢说它是脊梁之学,我想史学是塑造民族的脊梁之学。那么,我认为它是良心之学,因为它不是从伦理良知的层面进行理论说教,而是从日常生活、物质生产、衣食住行,日常生活的行为中,划定一种价值底线、奉献一种职业责任、践行一种职业准则的教育,是化天道于无形,融理性于万物、奉良知于日常、视手工若神谕的精神塑型教育。因为这种能力与责任会通过生产行业渗透到方方面面的社会产品与生活内容之中。所以它所贯彻的物质观、价值观、文化观、审美观又会通过日常生活的层面渗透到全社会的生活意识与价值判断中,最终形成全民族的日常之风、文明之风。这种作用是其它层次的教育所无法替代的。因此,我把它称作为塑造民族的良心之学。
为什么要讲高职教育应成一门 “良心之学”而不只是技能培训?我想举两所学校试作说明。第一所学校,是我的 “母校”。“我的大学”学历是在当时有幸所在的一个地方性的集体所有制单位 “南通工艺美术研究所”完成的,我似乎更愿意认为那里就是我的 “母校”,因为这个母校连接到一个更为早期的中国职业教育雏形,一个朴素、原始然而并不简单的职业教育民办机构——南通女红传习所。回顾中国职业教育史,南通女红传习所实际上是与 “中华职业教育社”同时代诞生的中国早期职业教育机构中的其中之一。我认为它是我的真正意义上的 “母校”或是 “祖母校”。“南通女红传习所”规模很小,但因晚清状元、民国初年中国的实业家、政治活动家、经济名人,同时也是一代教育家的张謇先生,让它的历史影响非同一般。黄炎培先生创立的 “中华职业教育社”有几个最主要的联合创始人,第一是蔡元培,第二是梁启超,第三就是这位张謇先生。中华职业教育社于1917年成立,而 “南通女红传习所”是1914年成立的,比中华职业教育社还要早3年。张謇先生与蔡元培先生一样,都是从清末科举考试制度中走出来的时代改革、新型的公共知识分子。他是清末最后几期状元之一,但他很快叛离了这样一个系统而拥抱共和革命。他曾经做过三朝重臣,曾经是晚清政府的重臣,曾经主政孙中山政府的实业部,后来又出任北洋政府的农工商部部长,但他最后的大作为,是从官场毅然退出,在家乡南通一手创建民族实业大生集团,是中国最早的现代实业创始人之一。
晚清有所谓四大巨商:张之洞,盛宣怀、郑观应和张謇。其中有官商、洋商和买办之分,而张謇则是真正的民商,是完全用民间资金自己筹办实业的民间资本经营者,也是难得的成功者。他在创建企业成功之后,又开创了一系列社会实业和公益事业,其中就包括开中国现代城市规划之先河的 “南通三镇”城市设计,为今天的苏北明星城市南通的现代化进展奠定了历史基础。同时,我觉得他一生还必须一提的重要贡献,就是开创了中国最早的职业教育,这就是他在1904年创立的南通师范学校女子师范学校,然后1914年创立了 “女红传习所”,一直延续到20世纪四十年代,对于南通的城市职业文明现代进程有深远的影响。新中国建国以后,女红传习所被撤销,五十年代时曾计划复建,但在恢复时,曾经讨论是继续沿袭 “女红传习所”还是叫 “工艺美术研究所”,后来按照当时的经济体制,改名叫工艺美术研究所,但研习宗旨与工艺精神一脉相承。女红传习所最后几代学员中,曾有不少继续进入研究所任职。到七十年代我进入工艺研究所工作时,还能见到当年女红传习所培养出来的工艺大师们,比如巫玉女士、陈锦女士、张元芳女士以及庄锦云女士等,她们在五十年代又带出来一批新中国的工艺师们,后来成为六七十年代工艺美术研究所的骨干。这几代人,都是我在这所 “大学”里的老师,我对她们如终报以深深的敬意。尤其是从女红传习所走来的一批老工艺家们,她们都是没有受过正规的洋式学堂教育,甚至没有读过几本书,甚至不认识几个字,但是一个个都温文而雅,彬彬有礼,艺术修养极高。她们有一位共同的师长,也是女红传习所的精神领袖,自然也是南通工艺美术研究的精神源头,这就是南通刺绣的代表人物、南通女红传习所领头人、中国近现代工艺史上最重要的刺绣工艺家之一的沈寿女士。沈寿女士与张謇先生的南通事业创建有极深的渊源。1916年是张謇先生亲自把她从天津邀请到南通去开创刺绣事业,然后主持女红传习所。在当时,沈寿女士不仅是一个很有名气的刺绣工艺家,还是一位勇敢的创新者。她出身贫寒,但能把自己的刺绣作品送进清宫后苑得到慈禧的欣赏,她的作品送到世界国际博览会并荣获金奖,她还东渡日本去考察现代艺术,在学习日本及西洋美术的同时将现代艺术观念与方法带回自己的刺绣之中。在当时多数中国妇女都还缠裹着小脚的时代,她已经以现代女性艺术家的姿态走出国门拥抱世界,这是一种超越时代的表现。她的一个重要历史贡献,就是晚年弥留之际跟张謇合作编写了近代中国工艺史上最完整的刺绣工艺教学文本 《雪宧绣谱》,她和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进行工艺总结的文献不一样,她把现代艺术修养的概念带进了 《雪宧绣谱》,成为其中最有特色的 “绣品”“绣德”“绣通”等篇章。当时的张謇代表中国最高层的精英文化,是对整个的中国历史经济文化有深刻思考的一个人,他竟然跟刺绣工艺家合作撰写这样一本刺绣工艺教材,这是精英文化与民间工艺文化的结合,我想这也应该是中国职业教育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一段佳话。其中成为特色的 “绣品”“绣德”绝对所言不虚,直到七十年代我们这一代人进入研究所时,所受到教育仍然如故,那种职业人格的修养是通过她们的言谈举止、专业判断以及对己对人的要求中体现出来的,其中很多都来自于当年女红传习所传下来的,所以到后来我也成为研究所副所长的时候,在我的脑子里面就是以沈寿当年的风采和一代代女红传习所学员们的作为和修养为楷模的。所以我认为她们是 “我的大学”,是这种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的职业学校给我的、终生受用并且刻骨铭心的感受。
第二个学校是完全不同的另一个故事。20世纪八十年代之后,我到南京艺术学院读研,后来到日本留学,回国之后仍然在南京艺术学院教学。在这过程里,我参与了一个叫做 “钢琴调律学校”的建设项目。这恰好又是另一个职业教育的范畴。当时,这个学校跟日本爱知县一个私立的钢琴调律专门学校合作办学。因为我从日本回来,这方面的人脉比较熟,所以参与这个学校前后所有的创建过程。虽然不是我的专业,但从中获得不少收益。
为什么当时要做 “钢琴调律学校”。因为在九十年代中期的时候,中国百姓的生活水平已经开始提高,家长们在孩子们身上家花钱培养学钢琴的风气开始形成。根据当时南京的一个市场调研结果显示:南京城市中钢琴的保有率已经超过两万台,这个数字在当时已经不是小数字,但是调律师只有两个。换句话说,一个调律师要面对一万台钢琴的维修和专业 “调音”的工作,市场极其巨大,所以当时钢琴调律业也是 “一将难求”。请到一个钢琴调律师进行 “调音”,就要付出很高的成本。
当时多数人的工资都还是在一个月六七十块钱左右的时候,而钢琴调律师就是一个小时二百块钱的水平,在当时相当于 “天价”。所以当时我们看好这个市场,就由南京艺术学院和日本爱知县这家调律学校合办 “中日合作钢琴调律学校”。整个过程非常顺利,日方也给予很大的投入。我记得日方主要负责来华工作的一位教书长叫做山口太,一个年龄不大的中年专家,工作勤恳,为人正直,给我印象很深。他是日方主要代表,负责这个学校的筹建和负责调度课程组织、教学资源并担任监督执行,也是钢琴调律师和教学专家。有一天工作结束的时候大家一起吃饭,互相举杯祝贺这个项目快成功了,这时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跟我讲一句话,让我印象极深,至今难忘。他跟我说,我真担心我们的教学效果能不能达到。这句话让我觉得奇怪,我就问,你是对我们的教学计划担心或是对师资水平有怀疑吗,还是觉得学生天资不够聪明。他说都不是,学生非常好,课程计划非常完美,老师非常尽职。我更奇怪了,那为什么呢?他回答说:我担心的是我们能不能说清楚钢琴调律这件事情。于是我说,这有什么说不清楚的吗?他说钢琴调律的技术教学没有问题,但是对这样的一个职业,我们能不能说清楚,我没把握。因为它是看不见的。这时我明白了,他担忧的是什么呢?因为钢琴调律有这样一个特殊的规律,就是调到最后,全在调律师一把扳头。它稍微扳一扳,可能就达到一个理想的音准,如果没有这一扳手,外行是听不出来,即使调出来是另外的音准,也只有调律师自己心里知道。据我所知,在日本的调律工作中,从钢琴厂出厂的钢琴要经过三道调律工序过程。第一道是机械式调律,就是这个用标准的机械工具将所有的零件按标准组装并达到一个科学的音准就行了;第二道工序是电子调律,即用精准的电子调音器,非常精密地把音准调整到极为精细的范围之内,这叫精调;最后,在完成出厂之前还有最后一遍校准,才算把所有的调律工序都完成,才可以达到出厂标准,这最后一道关,叫人工调律,只能由富有经验的高级人工调音。所谓“人工调律”说白了,就是把已经调到非常整齐的音律调乱,乱到它听起来是 “音乐”,而不只是 “乐声”的效果。这是对 “钢琴调律”的一种极高的职业理解,所以优秀的调律专家往往会在某位钢琴大师举行独奏音乐会的开幕之前被请做最后一道调律,将钢琴音准调到与当晚的音乐氛围与情绪最为适配的状态之后,钢琴演奏才能开始。调律师做完最后一个动作将钢琴盖盖上,里面的实际状态是谁都看不见,一般人也听不出来。但却体现着职业修养和职业伦理。他说我们能把这个事情跟学生说清楚吗?能把这个底线交到学生手里吗?就是这句话,我后来一直记着,我觉得这句话对我的影响已经不是钢琴调律的专业的问题了,而是我们所有的艺术专业里面可能都面临一个同样的、以什么样的艺术责任来对待自己的工作投入与专业品质的问题,永远都有一个不敢懈怠的底线。
另外还有一件事、一句话我同样记得很深,当然这是另一个范畴的问题了。我们这个学校办了三年,第一届学生毕业了,专业水平很好,非常抢手。整个学校管理井井有条,学校面貌非常好,于是申请升格为本科。因为这所中日合作调律学校当初申报时是三年的专科,报告提交上去后,省教委也认为这是中日合作学校中非常完美的一个典范,升级没什么问题,很快就批下来了,由我代表中方转告日方这个消息。当时我坐在日方校长办公室,印象非常深,那位校长一听这个消息当时就楞了。楞了半天才说,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做错了什么了吗?我说没有啊!就是因为做得非常好,这是一个鼓励。他说不对呀,我好好的一个专科学校,怎么把它弄到本科了呢?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就是说在他们的教育理念里面,本科和专科的界限非常明显,而且教育的价值与我们的理解刚好相反。本科是一般的国民教育,是给予受教育者以基本的国民精神塑造的教育,是最基本的公民品质塑造。而专科是真正的专业教育。所以一般的从业者都要经过真正的专科教育以后才能获得一个职业的资格去执业运营,专科学校的毕业证书往往也是职业能力的资格证书。所以,如果变为本科以后反而没有这个资格了,对他来讲就是处分。当时我就发现理解上完全错了,也很尴尬。只好努力说明这在中国完全是另一种理解,本科教学代表更高水平,只好这样蒙过去了。我想通过这个故事表明,在我们职业教育的系统定位和整个的体制设计是有问题的。尤其是把专科看做本科的预科教育或次一级的国民教育,是完全不合适的,它代表的是完全不同的教育内涵与能力培养目标,高职教育的宗旨与内涵都不应与本科教育混淆,甚至互相干扰。所谓的 “2+2”的的改革方法,可能会有方向性的失误,甚至会有对职业教育,尤其是对高职高专教育完整性和科学性的破坏。我不知道是不是还有其它的办法能够解开这个结。
另外我再想讲两本书。这两本书也是对我为什么说职业教育是一个 “良心之学”的解释的补充。一本书是意大利的作家叫普里莫·莱维,他是一位意大利作家,二战期间是曾被法西斯关押奥斯威辛集中营,后来被解救出来,成为专门描写二战期间被关押者心灵状态的作家,因而也被称为 “意大利的良心”。他一直以文学的身份、文学的方式完成对二战期间意大利民族的生存状态和心灵世界的反思。比如有人问他你为什么没有死,为什么没有选择反抗?他说或许我的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我要用我的笔反思,反思这个民族。他唤醒了人们对二战期间在集中营度过漫漫苦难岁月的许多普通人难以言表的心灵世界的关注。
其中有一段关于工匠的生存状态的描述非常典型,也很有启示。什么是工匠精神的内核?我觉得他那段描述对于我们了解 “工匠精神”是一个深刻的提醒。他在书中举例说到,当时集中营里,在他身边就有一批非常优秀的手工艺人,如钟表匠、机器匠、建筑匠、水泥匠、泥瓦匠等等,他和他们相处得应当是非常好的,有一件事情给他印象特别深,就是他们的是非立场是没有问题的,都非常憎恨纳粹,恨不得与这些法西斯作最后的搏斗,但是即使在这种状态下,在他们干手工艺活的时候他们仍会出于一种本能,或者一种深层的意志,把活干得非常好,好到他们自己满意为止,以至于当有人在提醒他们这个是给敌人在干活,不必要干这么好的时候,他们还要费很大的劲儿,才能把这个活做“坏”。这是一段非常特殊的描写,他没有再做任何的评论,就这样把它记录下来。而我想这一段描述超出了某种意识形态界限,其实是在提醒我们什么是普通的劳动者,他们的心目中职业意识或者所谓的 “工匠精神”还不仅仅如 “精致”“执着”那么简单,这似乎是一条深入到生命本真的一条底线、一种在任何时刻都不能轻易放弃的作为职业生命的标准。这种特殊形态下表现出来的 “工匠精神”,是值得我们反复思考的。
第二本书是当代美国社会学家理查德·桑内特写的 《匠人》,这也是一本讨论工匠精神的重要读物。从书中也可获得不少启示。第一个观点,就是今天讲的 “工匠精神”,可能更多地是从技艺的角度来谈的。但是在桑内特的 《匠人》里,他讲的几个方面,总结起来。我觉得对我们的启示非常大。
第一条,可以叫作 “一种为公共性产品的生产而自豪的职业意识”,这句话让我想起来我的老师张道一先生曾经给讲过的一位中国民间工艺家的例子。他说广东佛山有一位一辈子制作彩妆“狮头”的老艺人,他做得非常好,每年也不多做,逢年过节时就做几个狮头拿到市场去卖,价钱也不贵。人们很好奇,就问,既然你的手艺这么好,你为什么不多做点,或卖贵一点?他说,我做狮头不为别的,就为了让人知道我 “狮头老王”还在,就这么简单。为什么要说 “老王还在”?就是代表这个手艺还在。不是 “老王”,而是这个手艺、这个传统、这个文化、这种价值还在。这一点和桑内特笔下的 “职业自豪感”是一模一样的。
第二条,可以叫作 “一种分享隐而不宣的手工知识的职业乐趣”,他认为非常重要的是这种隐而不宣的知识分享的乐趣。这是我们所讲的工匠性之专业精神的重要来源。工匠他之所以被称作工匠,并不是说我仅仅是拿着工具在做活的工匠,而是一定有自己独到的观察、体悟和仿佛 “独门绝技”的心得,使它成为不同于他人的专门生产者,这种可以与他人分享绝非显而易见的专门知识的心态,是构成工匠精神状态的另一现实来源。传统的手工艺人讲究绝窍,但并不封锁这些绝窍,他以可以与人分享,或通过作品与人共有这种知识而倍感有趣,因而乐此不疲。这就成为他乐以追求卓越的一种强大的心理动力。
第三条,可以称为 “一种对于完整性的执着追求而内化为人格的的职业修养”。手工追求的完美性,最终体现为工匠对于自身精神修为的不懈追求。
综上所述,我认为这种公共性生产、隐秘性知识和完整性人格三个角度的追求,可以为我们思考时代的 “工匠精神”提供更为深入和广阔的视角,也是我们进一步思考职业教育内涵的新起点。
“工匠精神”在现在可能会有许许多多的讨论和解释,但我认为可以找到一把理解 “工匠精神”的关键性的钥匙,就是 “人在物质生产过程及其它生产过程中的 ‘主体性’”这个最基本的哲学概念。如果从这个角度切入的话,我们会找到它和当代工业生产体系、当代工业文化哲学的根本差别所在,从这个源头可以划清许多从 “工匠文明”与工业文明的分水,工匠精神与当代经济文化、政治哲学和社会发展批判的理论对应,包含着丰富的命题。
(责任编辑:李 宁)
1672⁃2795 (2017) 02⁃0009⁃06
2017-05-08
许平 (1953— ),男,江西彭泽人,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设计学成员,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学院高等艺术教育研究院副院长,艺术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艺术教育研究。(北京 100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