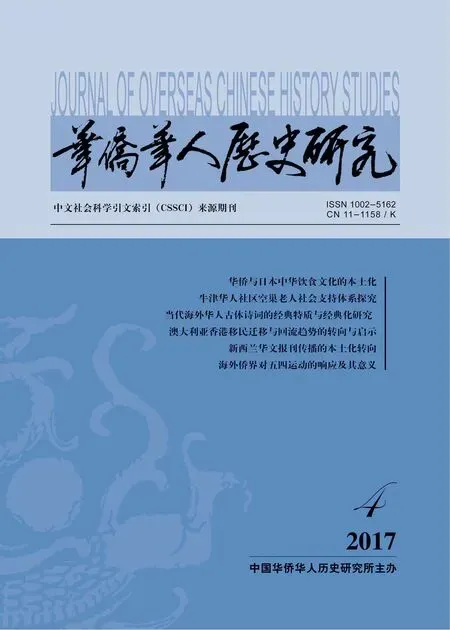吧国公堂华人丧葬管理研究*—以《塚地簿》为中心
2017-01-28沈燕清
沈燕清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史海探源
吧国公堂华人丧葬管理研究*—以《塚地簿》为中心
沈燕清
(厦门大学 东南亚研究中心,福建 厦门 361005)
印尼华人;荷属东印度;吧国公堂;丧葬管理;塚地簿A
论文利用吧国公堂《塚地簿》档案,回顾了吧城华人塚地的发展轨迹,分析了吧国华人丧葬管理机制和吧国公堂丧葬管理的特点,以及19世纪中期以后公堂丧葬管理面临的问题、管理职能的丧失。认为19世纪中期以前,面对数量不断增长的华人,统治力量尚薄弱的荷兰殖民政府给予华人社会一定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就体现在公堂对华人婚姻、丧葬、教育、宗教、社会福利等诸多事务的自主管理。公堂的管理为促进华人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及维护荷兰殖民统治做出重要贡献。但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荷兰殖民统治力量的增强,华人社会的自治权被削弱,加上华人社会新风气的兴起,公堂的管理举措难以与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相衔接,其管理职能的丧失是历史的必然。
丧葬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事死如事生,乃唐人之道也。”[1]海外华人同样重视丧葬,华人在移居国建立塚地已成为其移民文化的一个集体象征。[2]迄今为止,对海外华人丧葬问题的研究已有一些成果,如李明欢教授通过整理丹绒坟山档案中死者的来源地、年龄、性别、埋葬方式、塚地规模等信息,分析了吧城华人社会的历史变迁。[3]冯尔康教授梳理了澳洲、美国、新加坡等地当代华文报纸的讣告内容,以此分析中华文化在海外华人丧葬礼仪中的体现与演变。[4]张小欣以公堂丧葬管理为个案,分析了吧城华人社会自治方式及其面临的困境。[5]厦门大学薛灿通过对《南洋商报》(1951—1976年)刊载的讣告内容进行分析,探究新马华人的家庭形态与社会网络。[6]上述研究成果,多是通过华人丧葬史料来研究华人社会的演变或中华文化在海外的传承,并没有对华人丧葬问题本身进行深入探讨。
吧城又称“吧国”,是原荷属东印度首府巴达维亚的简称,即今雅加达。“吧国公堂”(以下简称“公堂”)即吧城华人评议会(The Chinese Council in Batavia),始创于1742年,是吧国华人处理华社各项事务的行政和司法机构。公堂设玛腰、甲必丹、雷珍兰、朱葛礁等华人官职,由荷兰殖民政权委任。二战后,公堂被解散并重新组合到各个寺庙基金会和义冢社团。[7]公堂在管理华人丧葬事务的过程中留下大量档案资料,即今存于荷兰莱顿大学汉学院的公馆系列档案之《塚地簿》。《塚地簿》共82卷,均为未刊档案,其中23卷为塚地丧葬登记,即《丹绒义塚》,其他59卷和几百个独立档案则包括塚地的购买登记及其他相关文件,其中中文档案有129册,时间跨度为1811—1954年,有些年份的档案丢失;马来文和荷兰文档案为5册,时间跨度为1930—1948年。《塚地簿》的记录相对完整和连续,对研究吧城华人丧葬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价值。本文尝试利用《塚地簿》档案分析荷印时期吧城华人丧葬管理的特点,并探讨公堂职能终结的原因,以期弥补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一、吧城华人塚地的建立与发展
(一 )华人义塚的建立
中国人移居印尼历史悠久,1619年荷兰人占领吧城后更利诱或劫持华船和华人前来。据载,当时前往东南亚的商船所载人数,“大约闽省居十之六七,粤省与江浙等省居十之三四”。[8]“1739年居住在吧城及大港唇(RaljBegah)两旁的华人有4,389人,……住在吧城郊区的华人有10,962人”,吧城遂成为闽南人的汇聚之地。[9]华人人口增长的趋势一直持续到20世纪中期。[10]
与华人移民增长相伴的是高死亡率。1780年出版的《吧达维亚学会文集》记载了1759—1778年吧城人口死亡统计情况,20年间共死亡74,254人,其中华人为15,379人,年均死亡769人,是同期欧洲人死亡人数的近6倍。[11]1883年11月,吧城西医曾提及华人多病乃至死亡的五个原因,“一、由各污秽什物臭气所致,遇有雨至,雨水停滞不留,因居人不以时清沟窦。二、华人村落居者过满。三、华人居宅彼此太密,至无间隙之地可通气纳凉。四、贾肆多蓄货物,有能以其臭气触人致病。五、华人居肆置货过满,其秽杂又不以时扫清或洗净,其第宅惟每年只扫洗一次。又遇死丧,停尸家内过久。”[12]《塚地簿》之《丹绒义塚》档案(档案号为61101-61123)也显示,1811—1896年的86年间共有55,385份死亡登记,年均为644份,其中大多为华人,华人死亡率之高由此可见一斑。
由于死者众多,丧葬用地成为华人社会的一大问题。最初,由于没有集中的墓地,华人去世后只能四处埋葬,再加上一些人讲究排场,把墓地修得过于高大,侵占了荷兰人的坟地,挖土留下的洼地积水后又脏又臭,从而招致他们的诸多不满。1650年,荷兰总督下令不准华人葬在东印度公司辖地,于是公堂雷珍兰郭训观同其兄长郭乔观等商议建立唐人义塚。“于是郭乔观为首,招募唐人请各量力捐金喜捨以建塚地,众人皆乐从,乃买东塚之地一所,用一人为土公①土公,闽南话,指专司尸体埋葬及塚地管理者。管理葬事,而唐人丧葬始无犯禁之苦,诚乃阴骘之善事也,当时土公名曰黄石公。”[13]自此,华人义塚开始建立了。
(二 )从义塚转变为华人公墓
1728年时,因东塚已满,公堂开始组织大家捐款购置新墓地。“甲大郭昂观与六雷议建塚地,令人劝谕诸唐人,各量力捐银,将项买勃昂山大菜园为义塚,甲大立颜经观长子颜銮观为土公。”[14]1742年公堂建立后,华人延续了捐银买塚地的做法,1745年购置了双柄园日本亭至妈蛲兰之地为义塚,设立土公三名。1762年又购置了牛郎沙里园地作为塚地。[15]几年后,这些塚地逐渐葬满。1778年3月,吧城当局谕令华人甲必丹、雷珍兰要“速寻别地以为葬坟之所,不得迟缓”。但直到1809年后,才又陆续购置了其他三个塚地,即丹绒塚地(1809年)、式里陂塚地(1828年)、惹致塚地(1854年),其中,丹绒地占地387亩,式里陂地占地218墓,惹致地占地130亩,三块塚地合计占地735亩。据估计,“丹绒、式里陂二处,约可再葬八年或十年之久,若添入惹致地,则更远矣。”[16]
1809年公堂购买丹绒塚地时,因为要划定荷兰人、华人和当地人的塚地界限,荷兰殖民政府向公堂提议:将本属华人塚地范围的把杀浮抵地区变更为荷兰人的塚地,为此,准许华人美色甘②荷兰语Weeskamer音译,指孤贫养济院,有华人美色甘和荷人美色甘之分。借给公堂7万文,用于购买丹绒塚地,全年利息6八仙。[17]公堂采纳了这一提议,并达成以下决议:
1. 由公堂在职甲必丹陈烨郎、首雷李东旺、武直迷吴祖绶等共同承担缴还70000文借款本息的责任,该款项不得拆分使用。
2. 批准甲必丹胡勃实③马来语Opsir音译,指有官阶的华人。推举甲必丹陈炳哥、雷珍兰林长生官、雷珍兰苏广哥,及首雷李东旺官等共同料理葬坟事项;又推举雷珍兰林长生官为茄实④荷兰语Kassier音译,指账房、会计。。
3. 批准甲必丹胡勃实所定葬坟规格及售价标准,即葬坟阔8脚距⑤马来语Kaki音译,长度单位。、长12脚距,是免费提供给贫困之人的塚地。如要获得更大规格的塚地,需另缴费用,其缴费标准是:阔12脚距、长24脚距,该缴纳200文。阔16脚距、长32脚距,该缴纳650文。阔20脚距、长40脚距,该缴纳1600文。阔24脚距、长48脚距,该缴纳3600文等。
4. 公堂每年缴还华人美色甘2000文,在70000文借款本息缴还完毕后,丹绒葬坟便成为“公众之地”等。[18]
自此,公堂不再号召众人“量力捐金喜捨”来购买塚地,而是通过出售塚地来偿还借款并购置新塚,这个做法成为解决华人丧葬用地的新模式。公堂除了为贫病人士提供少量免费的小规格塚地外,其他华人都能根据自身经济实力购置一定规格的塚地,这样一来,公益性质的义塚就转变为华人社会的公有墓园。
1828年,公堂再向华人美色甘借款5000盾,向荷兰美色甘借款1万盾,购买了吧城外西南郊式厘坡塚地。[19]1855年,向华人美色甘借2.5万盾购买了玛腰陈永元自置惹致作为储备塚地。[20]1890年,又以22万盾的价格买下玛腰李子凤名下的如南末、勃生、君领三处共五幅地皮,并从1892年起将这些地块“开作碎段,发售风水,为唐人葬地及寿域……,至其价项,仍依旧例。”[21]1897年又添置了烟埔以及红桥故等地。[22]不断购置的塚地基本满足了19世纪中后期吧城华人的葬地需求,同时公堂也逐步确立了华人丧葬事务的管理机制。
二、从《塚地簿》看吧城华人丧葬管理机制
在未刊的82卷《塚地簿》中,丧葬登记档案有23卷《丹绒义塚》,内容包括丹绒、式里陂、惹致、如南末、吃啷五处塚地的丧葬登记;其他59卷和几百个独立档案则记录塚地的购买登记(档案号为61201-61604),以及荫地簿、寿域规例、寿域单据簿、风水买地申报书、风水附单等相关文件(档案号为62101-64503),吧城华人丧葬的管理机制在《塚地簿》档案中得到充分体现。
(一 )丧葬信息登记
公堂对埋葬在塚地的死者进行详细的信息登记,如《丹绒义塚》记录了1811年1月到1896年10月超过5万名死者的基本信息,其中大多数是华人。不同年份的档案内容有所不同,19世纪初的档案记录主要包括登簿时间、死者的姓名①无法获知姓名的死者称为“唐人”“路边唐人”或“病厝人”等,夭折的婴儿称为“男孩”“女孩”等。即经办人。、年龄②1823年以后,死者的年龄才被记录下来,而由吧城慈善机构料理丧葬的死者则被标注为“不知岁”。即美色甘。、埋葬方式③1811—1872年的档案中记录了死者的埋葬方式,有员板(即厚板)、薄板、薄布、施棺或施板等。1858年以后,死者的出生地记录增多,一般有“唐生长”(出生和成长于中国)“吧生长”“暹客”(来自暹罗)“新客”“海屿新客”“旧客”“万丹客”“廖生长”“花旗人”“浪生长”“直葛”“北加浪”“井里汶生长”“垅生长”“唐旧客”“唐生长旧客”“新客唐生长”“唠务安人”“州府客”“番婆”“猫厘婆”“番猫厘婆”“山顶人”“新客南安由人”“把东客”“东势茄老旺生长”等情况。、塚地规格④1811—1872年的档案中记录了塚地规格。对死者职业或经济状况的记录比较零星,常见的有“贫人、“龟里”(即苦力)“水手”“小商”“做工人”等。等。如档案61107号之《丹绒义塚》(1823年1月—1823年12月31日)中记录:
癸⑤即,癸未年,此指1823年。1872年以后记录了死亡日期,通常死亡日期与登簿日期只相差几天,但有的间隔达两三个星期之久。8月26和⑥指荷历,即公历。对于死者的遗产及遗嘱状况,档案中分别以“有业”“无业”“有物”“无物”及“有做字”“无做字”等标注出来。9月30日拜贰⑦即星期二。,甲必丹来单,黄梓和故,年10,员板准葬,依例之处;甲必丹来单,陈莫官故,年24,员板准葬,依例之处;甲必丹来单,张牛官故,年20,薄板准葬,依例之处;甲必丹来单,黄天喜故,年34,薄板准葬,依例之处;甲必丹来单,蒋凤娘故,年9,员板准葬,依例之处。全月12距计葬二穴;全月8距计葬五十三穴;全月薄板计葬廿七穴;全月孩儿薄板计葬三穴,全月员板共葬五十五穴,全月薄板共葬三十穴。[23]
1836年以后的丧葬登记则添加了死者住址⑧无名氏或无住址的死者的地址记录为承办丧葬机构的地址,如“病厝”“美惜甘”等。和丧事经办人⑨有时经办人和死者之间的关系也被提及。如果是由慈善机构料理其后事的,则标注上慈善机构的名字,通常是“美色甘”或“病厝”。的名字,如档案61109号之《丹绒义塚》(1852年4月1日-1854年12月31日)中记录:
甲寅四月初二日和1854年4月28日拜五吉,郭碧故,不知岁,薄板,在病厝⑩荷兰语“Weeskamer”音译,指专理孤品的养济院、福利院。内,理事人①无法获知姓名的死者称为“唐人”“路边唐人”或“病厝人”等,夭折的婴儿称为“男孩”“女孩”等。即经办人。美惜甘②1823年以后,死者的年龄才被记录下来,而由吧城慈善机构料理丧葬的死者则被标注为“不知岁”。即美色甘。;陈双四故,不知岁,薄板,在病厝内,理事人美惜甘;许润故,不知岁,薄板,在病厝内,理事人美惜甘……。[24]
1852年以后一些死者的生平简介也被记录下来,包括其出生地③1811—1872年的档案中记录了死者的埋葬方式,有员板(即厚板)、薄板、薄布、施棺或施板等。1858年以后,死者的出生地记录增多,一般有“唐生长”(出生和成长于中国)“吧生长”“暹客”(来自暹罗)“新客”“海屿新客”“旧客”“万丹客”“廖生长”“花旗人”“浪生长”“直葛”“北加浪”“井里汶生长”“垅生长”“唐旧客”“唐生长旧客”“新客唐生长”“唠务安人”“州府客”“番婆”“猫厘婆”“番猫厘婆”“山顶人”“新客南安由人”“把东客”“东势茄老旺生长”等情况。、职业或经济状况④1811—1872年的档案中记录了塚地规格。对死者职业或经济状况的记录比较零星,常见的有“贫人、“龟里”(即苦力)“水手”“小商”“做工人”等。、死亡日期⑤即,癸未年,此指1823年。1872年以后记录了死亡日期,通常死亡日期与登簿日期只相差几天,但有的间隔达两三个星期之久。及是否有遗产或遗嘱等⑥指荷历,即公历。对于死者的遗产及遗嘱状况,档案中分别以“有业”“无业”“有物”“无物”及“有做字”“无做字”等标注出来。。如档案61114号之《丹绒义塚》(1872年8月1日至1878年3月30日)第81号记录为:
癸酉年正月初四日和1873年2月1日,拜六,唐生(长)、龟里张瑞祥,年26,正月廿七日故,贫人,(住)五角桥,理事人张亚翰。[25]
遗憾的是,《丹绒义塚》档案只截止到1896年10月,此后的丧葬登记情况不得而知。
(二 )塚地购买信息登记
现存《塚地簿》档案显示,19世纪公堂出售的塚地大部分位于丹绒(1812—1954年,其中一些年份的档案丢失)和式里陂(1850—1934年,其中一些年份的档案丢失),到19世纪70年代以后惹致(1878—1935年)及如南末(1892—1934年,其中一些年份的档案丢失)被提及,吃啷塚地的档案则出现在20世纪初期(1918—1934年)。
19世纪初期的塚地购买档案记录较为简略,包括以下内容:
购买日期:日期的记录按农历和荷历两种历法,日据时期日本历法“昭和”也曾被使用。
购买者姓名和将要使用塚地者的姓名:即此塚地是为了埋葬谁,通常购买者和塚地使用者之间的关系也被记录。
塚地的面积和价格等:和丧葬登记档案一样,销售塚地的面积在19世纪初到20世纪初都使用“脚距”来表示,而使用“冥达”(即“米”)来标注塚地面积的最早记录是在1923年。如档案61211号之《丹绒塚地》(风水买地)(1918年3月6日—1929年12月6日)记录到:
和1923年3月9日癸亥年正月二十二日拜五,苏善虎买过丹绒风水一穴,阔20冥达长10冥达,万律①管理塚地的华人官员。许庆宁查报,前至大路、后至旧坟,左至旧坟,右至旧坟,四至无碍,即收来艮35盾,付单为炤,昭和18年11月5日。[26]
19世纪初的档案并没有记录塚地具体售价,而是“须遵和1809年10月26日君厘书之例而行”。1830年以后塚地售价才被清楚地记录下来。②原档案中1823—1829年的记录丢失,对墓地售价的明确标注仅见于1830年以后的档案。如档案61207号之《丹绒塚地》(丹绒风水买地)(1830年1月7日至1845年11月27日)中记录:
壬辰三月初六日,和1832年4月6日拜五,叶义哥买过丹绒风水一穴,阔12脚距、长24脚距,欲葬伊岳父母谢宗官、罗辛娘仝为寿域,收来雷67.7盾。[27]
档案显示,19世纪中期塚地的售价标准为:
第一号阔24距,长48距,兑银1218.5盾;第二号阔20距,长40距,兑银541.6盾;第三号阔16距,长32距,兑银220盾;第四号阔12距,长24距,兑银67.7盾;
第五号阔8距,长16距,系捨施贫人及小孩,免还价。[28]
到了20世纪,由于《丹绒塚地》(丹绒风水买地)在1897—1918年之间的一些档案缺失,档案61211号之《丹绒塚地》(风水买地)(1918年3月6日至1929年12月6日)开始记录的塚地的售价标准为:12脚距、宽24脚距长35盾;16脚距宽、32脚距长110盾;12脚距宽、40脚距长250盾。[29]
《式里陂塚地》(式里陂塚风水买地)1891—1918年之间的档案也缺失。这一时期的惹致、如南末、吃啷塚地档案未缺失,而档案61502号之《如南末塚地》(二揽末风水买地)(1904年1月27日至1909年9月14日)中记录:
和1906年9月11日丁未八月初四日拜二,林玉娘买过如南末地风水一穴,阔12脚长24脚,要葬伊子刘启芳为双壙之坟,经万律邱思珍查报,前至旧坟,后至黄□娘之坟,左至旧坟,右至李启娘之坟,四至无碍,付字为炤,来艮35盾。[30]
据此推算,1906年前后塚地的售价标准发生变化,这或许与荷印殖民政府的货币改革有一定关系,此处不做赘述。此外,每一份塚地购买记录上都盖有吧国公堂的公章,通常盖在标注面积和价
格的地方,以防止日后纠纷,这也为此后公堂处理相关案件提供依据。
(三 )其他独立档案的补充
《塚地簿》中的几百个独立档案,包括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各塚地的总簿、风水买地申请书、风水附单、寿域单据簿、荫地簿等文件,它们多是对前两种档案的补充说明,可与塚地购买档案互相印证。如档案62103号之《丹绒、式里陂、吃啷、如南末、惹致寿域总簿》(1891年9月26日—1911年12月15日)中1893年第3号记录为:
和1893年3月14日和正月廿六日拜二,叶旁,年71,住班芝兰,默王俊山,门牌第1214号,买过二南末寿域一穴,阔12脚距、长24脚距,要荫自己双壙之坟,经公堂光媚沙里雷珍兰曾金莲查勘无碍,即收来艮67盾7方正,据万律邱枝头查报,前港、后空地、左陈清河寿域、右空地,四至无碍,付此为炤(补:和1894年11月19日公堂朱批准伊妻刘传娘先葬此域。和1903年3月2日,公堂朱李批叶旁合葬于此以成双壙之坟)。[31]
上述档案记录补充了默氏姓名、门牌号等前两种档案所忽略的信息。
此外,如档案63301号之《惹致风水买地申请书》(1902年4月24日至1902年5月12日)第11号记录为:
兹报刘水娘要买惹致地风水壹穴,阔壹拾贰脚、长贰拾四脚,要葬伊夫吴亚森为双圹之坟,前至田,后至许金池舍之坟,左至旧坟,右至旧坟,四至无碍,耑此奉公堂列位大人电照。[32]
可见,风水买地申请书要在正式购买塚地之前向公堂提出申请。
再如档案64205号之《式里陂风水附单》(1926年5月31日至1931年12月3日)第23号记录为:
和1884年5月15日甲申年四月二十二日拜四,陈顺章买过式里陂地风水一穴,阔12(脚距)长24(脚距),要葬伊妻张凤娘为双圹之坟,经委万律丘枝头查报,……四至明白无碍,即收来艮67.7盾,付单为炤,今因原单遗失,恳给副单一纸为据,即准陈顺章本身合葬此穴以成双圹之坟。[33]
该档案显示,公堂给出风水附单的原因是“原单遗失,恳给副单一纸为据”。可见,风水附单多是为前两种档案提供补遗、证明文件等。
再如档案62302号之《寿域单据簿》(1912年1月15日至1918年12月30日)第53号记录为:
大淡和1891年4月29日第3161号谕,兹杨锦文,年42岁,住晋郎安,默①指默氏,马来语Bek音译,指区长、街长。杨金英,第78号门牌,买过第叁拾号吃啷地寿域壹门,阔壹拾陆脚距、长叁拾贰脚距,要葬伊自己并伊妻陈金娘为叁圹之坟,此据,叩公堂光眉沙里甲必丹梁辉运查验无碍,即收来银贰佰贰拾盾,据万律查报,……四至无碍,付此为据。[34]
由此可见,寿域单据簿是塚地买卖完成后的一个凭据,也是对塚地购买档案的一个补充。
在其他独立档案中,最特殊的一种是荫地簿。所谓荫地,即免费塚地②1805年11月15日规定:政府给有功绩的华人蔗糖厂主人一块免费坟地,此应为免费荫地之始。见[荷]包乐史、[中]吴凤斌:《18世纪末巴达维亚唐人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41-42页。。公堂曾议定:“凡在公堂任事职员,不论久暂,已身辞尘,或妻室谢世,应即给予第一号风水一穴,盖以示优崇也。”[35]档案显示,能够获得荫地者包括妈腰、甲必丹、雷珍兰、默氏等,此外还包括公堂各级雇员,如秘书、账房先生、警卫和跑腿的,及塚地土公和华人寺庙主持,甚至还包括玛腰的保镖等,不同地位享有不同规格的塚地。如档案62201号之《丹绒、如南末吃啷式里陂、惹致荫地簿》(公堂特许坟地)(1891年6月8日—1934年12月24日)中记录:
和1919年6月13日已未年五月十六日拜五,现任雷珍兰陈进水因病身故,其女婿许达新恳乞荫地壹穴为葬岳父之所,公堂依例准给惹致第壹号风水壹穴,阔24长18,作四壙之坟,经委万律丘继兴查报,……四至无碍,付单为据,兹准伊岳祖母沈珠娘合葬此穴,以成之坟,付此为炤。[36]
(四)公堂丧葬管理机制
由以上分析可见,公堂是吧城华人丧葬管理的主体,土公负责塚地的日常维护与具体丧葬事宜;万律负责塚地的现场勘测;华人死亡登记、塚地购买、风水收入管理、荫地授予、塚地纠纷等事项都由公堂值月甲必丹、雷珍兰(华人称之为公勃低)及朱葛礁①荷兰语Secretaris音译,指公堂书记官。等直接管理,公堂针对不同事项制定了不同的法规。
一般而言,华人死亡后,其亲属必须到公堂进行死亡登记,同时到所在街区的默氏处开出相关证明,然后向公堂提交风水买地申请书,此后公勃低委托万律等对其欲购塚地的规格、四至等情况进行现场勘验,一切无碍后才准予买卖,公堂将售卖情况登记在案(即寿域簿),在缴清相关费用后公堂向购买者开具寿域单据簿,并将所得款项存入公堂柜项。该款项由公堂官员共同管理,公勃低及朱葛礁要开柜动用必须先请示公堂,每月月底还需将收支结册呈奉公堂查阅。[37]
为保证塚地收益,公堂对荫地及义塚的授予实行严格控制,如公堂曾规定“倘欲预先求荫寿域者,即应计核其任事有四年足额,方准给予,则又以昭珍重也。至原任致仕者,尤必照此查给耳。除本公堂外,各处职员,无论现任、致仕,应查核任事有四年足额,并查阅其案夺字名目,临时准给风水一穴。”[38]此外,公堂派万律逐年核查寿域簿与默氏单据是否相符,每五年核实一次塚地买主信息,如其不知所踪且无亲人可查寻,须注明在簿。公堂还每年派员与土公一起实地核查塚地安葬情况,防止有人预买塚地空置不用。[39]
值得一提的是,在上述塚地出售及相关独立档案中不时出现一些补注,其内容大致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塚地购买者要求更改其所购置塚地的方位;二是塚地购买者要求更改其所购塚地的使用者;三是被销售的塚地实际面积被发现小于标准规格,但买方同意接受和按标准支付款项;四是新的死者,通常是现有塚地埋葬者的家庭成员或亲戚,获准与之前的死者埋在一起。这些补注多在塚地购买登记的十几年乃至几十年后添加,有些则是在不同的年份里被添加了几次。[40]这些补注说明,公堂对塚地售后情况进行长期跟踪与管理,并在塚地纠纷出现时利用这些相关资料进行裁断。
可以说,公堂的丧葬管理在维护华人丧葬秩序、保持吧城社会稳定及传承中国传统丧葬文化等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三、吧国公堂丧葬管理特点分析
由于公堂是“一个华人精英分子管理华人社会内部事务的半自治机构”[41],这种半自治性质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其丧葬管理的特点,即它首先必须服从于荷兰殖民政府的统治利益,同时又具有一定的自主管理和获取收益的权利。
(一 )吧国公堂丧葬管理以服从殖民政府法令为前提
荷兰殖民政府颁布了一系列法令以规范华人的丧葬行为,如1755年8月规定,华人运柩回中国要按其遗产的多少付给武直迷②荷兰语Boedelmeester音译,管理遗产、孤贫福利之职,1690年立郭郡官为吧城首任华人武直迷,议定三年一任。50~100文钱;1778年3月规定,华人塚地宽度不能超过12脚距;1791年8月规定,甲必丹、雷珍兰及其亲属的塚地,宽不超过24脚距,长不得超过36脚距,高不超过8脚距,特别申请者可高到10至11脚距。其他华人塚地标准为宽8脚距,长12脚距,高不超过6脚距,违者罚500文;1797年7月规定,塚地规格超过规定者罚款500文,甲必丹、雷珍兰也要连带受罚500文;1800年规定,按照中国风俗习惯葬礼擎高灯者,需交500文;此外,还规定华人官员的塚地规格只能符合其职称所定,后代若过分装饰其塚地要付500文;等等。[42]
公堂成立后,殖民政府利用华人官员来加强华人丧葬管理,公堂也制定了一系列条规来响应政府的法令,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规范塚地买卖并监督塚地实际使用情况
19世纪初开始出售塚地后,公堂曾规定,“凡公堂塚山准兑大小寿域……如有男妇老幼要买寿域,可到公馆向朱葛礁询其规例……”。[43]到1891年4月10日公堂所定《寿域规例》又规定:
一、男妇老幼要买寿域,须亲带该辖默氏单据,开写姓名、年数、住居何村第几号厝、要葬何人,寿域买卖后不许更售别人。二、寿域单一张则墓牌一门,不许数单合作一门,要葬时仍须将单带到公堂另加批明,然后准葬。三、寿域买后须自立石为表识,刻姓名年月时日单中号头。四、寿域须公堂公媚沙里①荷兰语Commissaris音译,指专员、委员。壹员,或有事,故委值公馆朱葛礁率该塚地万律预勘该处,然后准买……。五、公堂别置寿域一簿,详誌买者姓名,务与单合,逐年万律查点,经否葬埋,务与簿符,五年一次召讯买主,如不知去向,又查无服亲,切须批明在簿。六、买主或身故葬在别域,准其服亲依序承用,若买主自愿将域付服亲收用,不得依序较论等。[44]
1932年2月,公堂又进行了一些补充,如向公堂购买塚地后,需要在塚地范围内树立界碑以示区别,否则如有误卖情况发生时,公堂不负赔偿责任;购买塚地时,先由公堂值月员查勘,或派秘书会同塚地土公查勘无误时才准许发售;公堂每年派委员或秘书偕同塚地土公调查卖出塚地是否已用于葬埋,以杜流弊;等等。[45]
2.防止丧葬仪式过度以维护荷兰殖民者的威权
徐吉军在《中国丧葬史》一书中曾提及,泉州“丧祭以俭薄为耻”;漳州“亲旧之葬,或设祖祭,数月营办,务求珍异,不计财费。丧家则盛筵席以待之,竞为丰侈”。[46]漳泉地区丧葬的奢靡风气自然也影响了以闽侨为主的吧城华社,并引起荷兰殖民者的不满,认为这是对他们威权地位的一种藐视。[47]为此,公堂也不断采取限制措施,以缓和荷华关系。
如1805年9月13日公堂规定,“唐平常人欲盛葬者,须完纳500盾以人病厝,完纳之人亦不敢僭越于甲大之仪,……若谓官阶品级,不论何美色甘条规申明,涓(捐)纳甲必丹葬仪须从现任雷职;涓(捐)纳雷珍兰葬仪,须从朱葛礁职,则等第明矣。至于庶人完纳500盾,原准其盛葬而已,固非可任其侵凌品级,辱玷衣冠。”“和1832年2月19日定一条规:凡甲必丹、雷珍兰、朱葛礁及完纳500盾者该用之仪。”[48]到1845年11月17日,公堂又定华人还银500盾出葬该用物件,防止华人丧葬排场过度。[49]1852年11月把杀旺地区华人郭容和“身故卜葬之时,要用浅丝绸伞,并带三条余,虽盛葬,卻无过犯。”但公堂的评议是:“若谓有钱便可滥用丝伞,将置缙绅于何地?”[50]公堂在防止华人丧葬仪式过度方面的态度可见一斑。
3.禁止华人归葬故乡以维护殖民政府财政收入
早在东印度公司时期,荷兰殖民者就对华人收取丧葬税,最初为0.5里尔②即Real,西班牙银币。,后增加到2里尔,1660年后改为3文钱。[51]此外,立墓碑需另缴费用,政府还要从死者遗产中抽取5%的税。为阻止乡土情结强烈的华人归葬故土而减少税收收入,1755年荷兰殖民政府规定华人要运柩回中国须按其遗产抽税。虽然如此,稍有经济能力的华人还是会缴纳费用归葬故土。为此,1805年政府又规定人死后停尸超过3个月的要付73文钱,若再增加停放时间,每月增收25文钱,甚至甲必丹的孩子死后停尸超过25天也要付100文钱。这些规定的目的也在于阻止华人筹措经费以归葬故土。[52]
公堂掌理华人丧葬事宜后也延袭这一政策。如1892年4月29日雷珍兰邱春昌请求公堂各官员联名上禀吧城督宪,以期另立一规例使华人能够将亲属骨骸畀归乡土。他说,“美色甘官都老例和1819年第64号第九条,准华人运棺回梓。其例第一号,纳银440盾;第二号,纳银220盾。……然必殷实者而后能支此数,若家无担石,必难措办,而死葬首丘①指故乡。之心,我华人不论贫富皆同。……如宪论谕准之后,一则存没均感于靡涯,二则病院胥受其沾润,三则葬地迁骸而可以复用,四则火船局因运骸归增者多,而利源益广。”而公堂官员对此的审议结果是,“为不从者多于从,故此事遂寝不行。”[53]
(二 )吧国公堂在华人丧葬管理中的自主权
在服从殖民政府法令的同时,公堂管理华人丧葬也拥有以下几个方面的自主权。
1.自主管理塚地出售及周围土地出租事务
档案显示,公堂能够制定塚地出售和塚地周围土地出租的相关条规。如1855年11月10日公堂拟定丹绒、式里陂塚地管理事务条规九款:
一、丹绒、式里陂兑风水事,自和1855年1月1日起,已委应值公勃低掌理,每月出入钫项若干须详复于公堂。二、每年终须造一册,登明全年出入钫项若干,缴上挨实嗹②荷兰语Resident音译,指驻扎官。查阅。三、公馆(即公堂)兑风水公勃低及朱③即朱葛礁。在数出单,铃(钤)印花押,然后送到妈腰鉴押。四、兑风水之项存在公馆,置一铁柜用锁三门,首位掌一、公勃低掌一、朱葛礁掌一,每月所收之项充入在柜,上下月相承。要出、要入钫项,须三人齐到方可。五、所存在柜之钫,倘挨实嗹不时检察,当遵命无违。六、凡塚务该用之费,务在嘧喳唠④马来语Bicara音译,指公庭、审判庭。内请明,方可开出。七、公堂经委公勃低料理塚事,若小可之费,可以先开,然后请命于公堂。八、丹绒、式里陂二地待君得⑤马来语Kontrak音译,指合同书。满,田园取息,当叫黎垄付人承税,谁最高价且安呾人最当者得之……。九、一暨塚务,须立一蛮律掌理坟域及开圹、造坟等事。[54]
1855年12月15日挨实嗹在此九款的基础上,又拟定了丹绒、式里陂君厘书⑥荷兰语Kennisgeving音译,指官方的通告、通知书、布告。稿十四条,其中规定:
遵公堂所命理事之人,乃值月公馆二员公勃低,及朱葛礁一位;二地取息,除兑风水外,每年须发叫黎垄,而要叫黎垄,可公堂自主发叫,二地公班衙番不得入于税入,须付掌塚蛮律整理坟域;凡一切整理坟域及春秋祭祀之费,可开柜内之项,又可开还掌塚蛮律辛金。该开若干,公堂自裁;公堂所命,凡钫项不可妄借于人,须有地头或厝宅为质,又当二妥人安呾,其利息凭公堂折衷轻重等,但每年终须结册呈上挨实嗹查阅。[55]
这说明殖民政府既尊重公堂塚地出售法规,又同时对公堂的相关收入进行监督。
对塚地周围土地出租的事务,公堂也自行拟定了管理条例。如1844年10月25日妈腰陈永元代表公堂与陈井订立关于承包丹绒、式里陂塚地之合同,如承包者需要两位担保人,享有出租地内的各项经济利益,如果承包者有违约情况,则要再寻承包人;承包者需要听从公堂的命令,还要听从殖民政府的法令等规定。[56]
可见,在塚地出售或周围土地出租上殖民政府具有最终的决定权,但公堂也有一定的自主权。
2.调解塚地纠纷,维护华人丧葬秩序
塚地公开售卖后,相关的纠纷层出不穷,主要存在塚地所有权争夺和塚地侵占等问题。由于实行了严格的丧葬登记和塚地买卖登记,公堂才能够对相关纠纷进行调解以维护华人丧葬秩序。
如1825年4月22日,华人妇女碧桃和张镭争夺丹绒一塚地的所有权,碧桃购买了一块塚地,但该塚地的购买登记簿中却是华人张法生(此人为碧桃女婿)的名字,公堂一时难以断定塚地归属。雷珍兰戴明基向公堂汇报说“卑职遂即唤到案内又名人数并邻居厨工等,为之一一推究,分明是碧桃嘱咐法生代买之业,虽单载张法生名字,法生已死,亦不得以此而疑之也。……又据厨工桑马逸云:‘当时营造风水,一切资用工费俱是碧桃支理。’……而邻人蔡惟亦云,此事伊所深知,方买之际,与既买之后,法生俱尝对伊相商,的是碧桃托法生代买之业。……卑职以为,有此二端信证,自可断归碧桃,毋庸遊移。”在该塚地纠纷案中,公堂根据塚地购买登记簿及相关证人证言最终将塚地判归碧桃,其判决合情合理,令人信服。[57]
此外,向贫病人士赠予舍施地也是公堂自主权的一个表现,虽然其所占比例不高,且逐年减少。
四、吧国公堂丧葬管理职能的丧失
19世纪中期以后,公堂的丧葬管理开始面临诸多问题。
首先,塚地销售及周围土地的出租使得塚地的公益性质丧失,其对华人的吸引力逐渐下降。19世纪中后期,塚地销售及周围土地的出租日益成为公堂重要的收入来源。1880年公堂出入柜项全年结册显示,当年总收入为13793.865盾,分别来自“兑风水条目”(即塚地出售)收入(共2640.2盾)及“收地税利息条目”收入(共11153.665盾),而在“收地税利息条目”中,除了1471.335盾来自公堂义学学费、借款利息及公堂房屋典当收入外,其余均来自上述五处塚地的土地出租收入。[58]这种与塚地相关的丰厚利润使公堂得以维持各项公共开支,与此同时塚地的公益性质也逐渐减淡,缩紧了免费塚地的发放。如1844年公堂条例还规定“凡捨施棺到塚,有单便可埋葬,……免还(指缴纳费用)其项(指钱款)”。[59]到1871年,则提出应由华人美色甘发棺木周济贫苦之人。[60]1881年2月,对擅自发放塚地给贫困人士的万律邱枝头,公堂做出令其赔偿塚地资费以补偿公堂之亏的决议。[61]此后1881年3月,公堂商议曰:“夫捨施地者,乃欲济贫乏,不施殷富。今皆准葬捨施地,然是时初定新例,或无弊端,久后必至于土公私相暗昧,而公堂亦不免减兑。故有力者,皆当买地,方为合理。”[62]可见,公堂在丧葬管理中的逐利性质越来越浓厚,塚地对华人社会的吸引力也必然下降。
其次,19世纪中期以后,由于城市化进程加速及其他族群社会活动的影响,吧城华人塚地不断受到侵占。1832年11月,近公班衙修路侵占了公堂土地。[63]1855年,荷印政府动议平毁牛郎沙里塚地,遭华人各界反对而未果。[64]1876年1月“因公班衙要用公堂地,在式里陂及惹致以为开港。就该割用二处之地,的西①荷兰语Taxatie音译,即检验、查验的意思。价银12180盾”。[65]1881年11月,因娼间②闽南话,指妓院。要移在牛郎沙里,公堂抗议曰,“所指之处,系番运律之厝,约离完劫寺一百步之远,且近于塚地。……我唐人妇女或有时谒墓,或清明祭祀,迫近娼间,殊为不便。……冀其择别地。”29日,荷印政府又买去惹致地一块;1907年,荷人缎亚七频里购买惹致地四亩;1908年12月18日,八戈然之地被火车路占用;1912年11月4日,副淡③指副驻扎官。催促公堂迁移红桥各坟墓等。[66]
再次,20世纪初吧城华人塚地被盗事件频发,这对重视风水的华人来说尤其难以接受,而警方治理不力让华人更为不满。1908年3月3日,华人向副淡申诉祖坟被偷掘,公堂议定出赏银抓捕盗墓者,但收效甚微。1909年4月21日,警察捕获了偷盗墓砖者,但副淡以此案无原告而予以释放。[67]再加上1900年吧城中华会馆建立后,提倡“革除陋习为先”,在婚丧教育等方面提出改革思路,改变了吧城华人的丧葬观念,[68]公堂的丧葬管理机制受到冲击,其丧葬管理职能逐渐丧失,直至二战后公堂被解散。
吧国公堂丧葬管理的整个历史过程,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吧城华人社会发展演变的一个缩影。19世纪中期以前,面对数量不断增长的华人,统治力量尚薄弱的荷兰殖民政府给予华人社会一定的自治权,这种自治权体现在公堂对华人婚姻、丧葬、教育、宗教、社会福利等诸多事务的自主管理。公堂的管理为促进华人社会的稳定发展及维护荷兰殖民统治做出重要贡献。但到19世纪中后期,随着荷兰殖民统治力量的增强,华人社会的自治权逐渐被削弱,加上华人社会新风气的兴起,“公堂的管理举措在延续上百年的时间中已难与发展变化的社会现实相衔接”[69],其管理职能的丧失是历史的必然。
[注释]
[1] [17][18]聂德宁、侯真平、吴凤斌等校注:《公案簿》(第7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198~200,198~200 页。
[2] Li Minghuan. Batavia’s Chinese Society in Transition: Indications of Tandjoeng Cemetery Archives(1811-1896),IIA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Workshop, “Chinese Archival Sources And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1775-1950)” , December 1999, Leiden ,the Netherlands, p1.
[3] 李明欢:《变迁中的吧城华人社会:十九世纪丹绒坟山档案资料的启示》,《亚洲文化》,2000年,总第24期。[4]卞利、胡中生主编:《民间文献与地域中国研究》,黄山书社,2010年,第79~94页。
[5] [69]张小欣:《荷属东印度华人社会的自治与困境——以18—19世纪吧城公堂丧葬管理为中心》,《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16年第4期。
[6] 薛灿:《映像在华文报刊讣告中的新马华人“家庭”与“社会”——1951—1976年〈南洋商报〉讣告研究初探》,厦门大学硕士论文,2008年。
[7]聂德宁:《吧城华人公馆档案文献及其研究现状》,《南洋问题研究》2006年第4期。
[8] 清世宗胤禛批,允禄、鄂尔泰等编:《朱批喻旨》,清雍正十年(1732年)至乾隆三年(1738年)武英殿刻,朱墨套印本,第46册。
[9]陈碧笙:《世界华侨华人简史》,厦门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97页。
[10] 见黄文鹰等著:《荷属东印度公司统治时期吧城华人人口分析》附录部分,厦门大学南洋研究院1981年,以及杨建成主编:《荷属东印度华人商人》,台湾中华学术院南洋研究所印行,1984年。
[11] [42][51][52][荷]包乐史、吴凤斌著:《18世纪末巴达维亚唐人社会》,厦门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76,41~42,41,41~43 页。
[12] [58][61][62][65]聂德宁、吴凤斌、[荷]包乐史校注:《公案簿》(第13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440,295~296,307,309~310,223~224页。
[13] [14]许云樵校注:《开吧历代史纪》(公堂藏抄本),《南洋学报》第九卷第一辑,新加坡南洋学会,1953年6月。
[15][16][荷]包乐史、聂德宁等校注:《公案簿》(第10辑),2010年,前言,第1~3页。
[19][荷]包乐史、刘勇等校注:《公案簿》(第6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2~63页。
[20] [37][54][55][64]吴凤斌、[荷]包乐史等校注:《公案簿》(第9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260,161~162,153~154,161~612,125 页。
[21] [22][28][35][38][66][67]吴凤斌、聂德宁、[荷]包乐史校注:《公案簿》(第14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 年,第 88,4~5,88,157~158,157~158,4~5,4~5 页。
[23]莱顿大学汉学院馆藏公馆档案第61107号之《丹绒义塚》(1823年1月至1823年12月31日)。
[24]莱顿大学汉学院馆藏公馆档案第61109号之《丹绒义塚》(1852年4月1日至1854年12月31日)。
[25]莱顿大学汉学院馆藏公馆档案第61114号之《丹绒义塚》(1872年8月1日至1878年3月30日)。
[26] [29]莱顿大学汉学院馆藏公馆档案第61211号之《丹绒塚地》(风水买地)(1918年3月6日至1929年12月6日)。
[27] 莱顿大学汉学院馆藏公馆档案第61207号之《丹绒塚地》(丹绒风水买地)(1830年1月7日至1845年11月27日)。
[30] 莱顿大学汉学院馆藏公馆档案第61502号之《如南末塚地》(二揽末风水买地)(1904年1月27日至1909年9月14日)。
[31] 莱顿大学汉学院馆藏公馆档案第62103号之《丹绒、式里陂、吃啷、如南末、惹致寿域总簿》(1891年9月26日—1911年12月15日)。
[32] 莱顿大学汉学院馆藏公馆档案第63301号之《惹致风水买地申请书》(1902年4月24日至1902年5月12日)。
[33]莱顿大学汉学院馆藏公馆档案第64205号之《式里陂风水附单》(1926年5月31日至1931年12月3日)。[34]莱顿大学汉学院馆藏公馆档案第62302号之《寿域单据簿》(1912年1月15日至1918年12月30日)。
[36] 莱顿大学汉学院馆藏公馆档案第62201号之《丹绒、如南末吃啷式里陂、惹致荫地簿》(公堂特许坟地)(1891年6月8日—1934年12月24日)。
[39] 莱顿大学汉学院馆藏公馆档案第62201号之《丹绒如南末吃啷式里陂惹致公堂特许坟地》(1891年6月8日至1934年12月24日)及第62306号之《寿域单据簿》(1931年5月1日至1954年1月18日)。
[40] Li Minghuan,Batavia’ s Chinese Society in Transition: Indications of Tandjoeng Cemetery Archives(1811—1896), IIAS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Asian Studies)Workshop, “Chinese Archival Sources And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1775—1950)” , December 1999, Leiden ,the Netherlands, p.8.
[41]聂德宁:《吧国公堂档案》,《历史档案》2000年第3期,第129页。
[43]莱顿大学汉学院馆藏公馆档案第12002号之《通息簿》(1885年7月16日至1904年8月23日)。
[44] 莱顿大学汉学院馆藏公馆档案第62201号之《丹绒 如南末吃啷式里陂惹致公堂特许坟地》(1891年6月8日至1934年12月24日)。
[45]莱顿大学汉学院馆藏档案号第62306之《寿域单据簿》(1931年5月1日至1954年1月18日)。
[46]徐吉军:《中国丧葬史》,江西高校出版社,1998年,第511页。
[47]吴凤斌、包乐史等校注:《公案簿》(第5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1~229页。
[48]聂德宁、侯真平等校注:《公案簿》(第3辑),厦大出版社,2004年,第117~118页。
[49][56]侯真平、聂德宁等校注:《公案簿》(第4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04~205,6~9页。
[50]侯真平、吴凤斌等校注:《公案簿》(第8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15~116页。
[53]吴凤斌、聂德宁、[荷]包乐史校注:《公案簿》(第14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123~124页。
[57]袁冰凌、(法)苏尔梦校注:《公案簿》(第2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3~194页。
[59]侯真平、聂德宁等校注:《公案簿》(第4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53~54页。
[60][荷]包乐史、聂德宁等校注:《公案簿》(第12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13 年,第354~355页。
[63]袁冰凌、(法)苏尔梦校注:《公案簿》(第2辑),厦门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32页。
[68]王爱平:《印度尼西亚孔教研究》,中国文史出版社,2010年,第66页。
The Funeral Management of the Gongtang(The Chinese Council in Batavia):——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Funeral Archives
SHEN Yan-qing
(Center for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Xiamen University, Xiamen 361005, China)
Indonesian Chinese; Dutch East Indies; the Gongtang in Batavia; funeral management; the Funeral Archives
Based on the Funeral Archives from Gongtang in Batavia, this paper reviews the historic trajectory of Chinese cemetery in Batavia, then analyzes the mechanism and characteristics of funeral management of Gongtang(The Chinese Council in Batavia). It also discusses the problems which the Gongtang funeral management faced with and its loss of such management function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paper concludes that, before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due to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immigrants,Dutch colonial government, which has relatively weak ruling power, had to give a certain level of autonomy to the Chinese society, and such autonomy was reflected in the Gongtang’s independent management on several affairs such as marriage, funeral, education, religion, social welfare, etc. The management of Gongtang has made an important contribution to the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society and maintenance of Dutch colonial ruling. However,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due to the increasing of the Dutch colonial ruling power,the autonomy of Chinese community has been weakened. Along with the rise of new social ethos in Chinese society, the Gongtang’s management was difficult to follow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social reality, the loss of its management functions is historically inevitable.
D634.334.2
A
1002-5162(2017)04-0051-12
2017-08-14;
2017-11-08
沈燕清(1975—),女,厦门大学东南亚研究中心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东南亚华侨华人史、国际移民问题研究。
*本文为2015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基于未刊公馆档案之印尼华人社会结构研究”(15BZS016)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责任编辑:李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