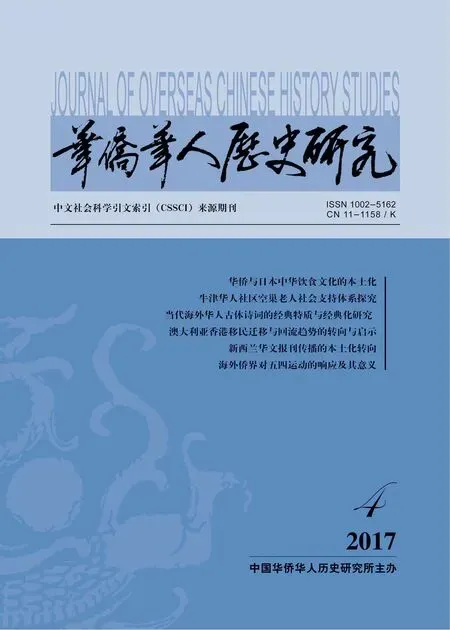新西兰华文报刊传播的本土化转向(1865—1970)*
2017-12-20曹小杰
曹小杰
(中山大学 传播与设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新西兰华文报刊传播的本土化转向(1865—1970)*
曹小杰
(中山大学 传播与设计学院,广东 广州 510006)
新西兰;华文报刊;华人移民;身份认同;本土化转向
论文对1865—1970年华文报刊在新西兰由外来报刊主导到本土报刊主导的传播扩散过程、新西兰华人身份认同及想象进行了初步梳理。认为新西兰早期本土华文报刊并不仅仅只有《民声报》,其华文报刊实践活动要丰富得多。因受到华人移民潮、新西兰移民政策及中国国内政治时局的影响,新西兰早期华文报刊传播存在明显的阶段转向特征。在1910年以前尤其是淘金热时期,基本以消费外来华文报刊为主;而1920—1970年随着华人政治社团的兴起,依附这些社团的本土报刊不断出现并在本地华人阅读市场中占据了主体地位;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视新西兰为家园以及以英文为母语的第二代华人的出现,华文报刊又逐渐走向了衰落。
一、新西兰华文报刊研究现状及存在问题
当前学界对早期海外华文报纸的研究多集中在东南亚、北美、日本、西欧等地区,对大洋洲地区的考察则主要集中在澳大利亚,诸如1894年在悉尼创刊《广益华报》的史实,已被一些新闻史学者关注。在与澳大利亚隔塔斯曼海相望的新西兰,其早期华文报刊实践情况在目前国内学界几乎仍是空白。事实上,新西兰作为19世纪中叶大洋洲第二大金矿所在地,从1865年首波有史可考的淘金矿工登陆南岛中部奥塔哥开始,大批华人就前往新西兰淘金并逐渐定居。[1]此后华文报刊传播活动也开始在该岛国登陆,从早期以流通来自中国及东南亚、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的华文报刊为主,到后来第一份华文报纸的创刊,新西兰本土华文报刊的传播历史严格来说并不晚于澳大利亚。
国内目前只有几篇文章专门讨论新西兰华文媒体,中国知网上相关论文不超过3篇且都是对现状的简单描述,其他文章散见于报纸杂志并且几乎都是非学术的简单见闻录。①具体可参见王瀚东、郭习松:《新西兰华文媒体现状考察》,《新闻前哨》2011年第8期;张明新:《如何改进对外传播—澳、新、马华文媒体考察之思考》,《对外大传播》2007年第6期。另外有为数不多的论文在研究海外华人报刊史时,间接谈到了新西兰的情况,但大部分有史实错误。比如有硕士论文谈到了早期新西兰华文报纸《民声报》,但作者想当然地将该报英译名称“The Man Sing Times”转译作“民醒报”,还误将《民声报》的创刊年份定在了1913年。②参见白祖偕:《海外华文传媒的问题及发展研究》,中南大学2007年硕士论文,第15~16页。将《民声报》报名错当“民醒报”不只这一篇文章,比如还有胡耀华:《新西兰华文传媒发展综述》,载《2005年世界华文传媒年鉴》,北京:世界华文传媒年鉴社,2005年。实际上如果了解第一期《民声报》报头有“中华民国十年”字样,则容易推算出该报是1921年创刊的(下文将有更多旁证)。
在目前可以搜集到的中文著作中,最早谈到新西兰华文报刊的是胡道静于1940年在世界书局出版的《报坛逸话》,在书内文章《大洋洲的华侨报纸》中,作者简单介绍了早期澳大利亚、新西兰及飞枝(今译“斐济”)等地的华文报纸实践。关于新西兰的部分,只有一段话:“雪梨(今译‘悉尼’)的报纸同时是在新西兰销行的。新西兰的华侨社会也曾企图自己办一个报纸,在一九二一年出版一个周刊,叫《民声报》,在惠灵吞(今译‘惠灵顿’)发行,但是缺乏支柱,出版不到两年就停刊了。此后这里不曾再出过中文刊物,而仰给于雪梨。”[2]
这段文字提供了一些史实,但更多地引出了疑问。一是《民声报》于1921年在新西兰惠灵顿创刊。但它是否是周刊?是在什么背景下创刊的?在该报之前及之后(以该文写作时间1938年至1939年间为参照)是否仍有其他华文报纸发行?二是澳大利亚尤其是悉尼的报纸在新西兰流通,但来自澳洲的报纸究竟有哪些?依托何种渠道流通?影响如何?
1989年出版的《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两位作者在谈到大洋洲国家的华文报刊时简单提及“新西兰最早的华文报《民声报》由中国国民党驻新西兰惠灵顿分部于1921年创办。该报鼓吹革命,赞助孙中山先生北伐”[3]。这里比胡道静明显往前推进了一点,将《民声报》与国民党的关系指出来了。但二者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具体关系?同样,将《民声报》定义为新西兰最早的华文报,依据何在?此外关于《民声报》的停刊时间,在1989年的这部专著中没有提及。胡道静的说法是“不到两年”即停刊,而根据后来程曼丽的说法则是“二战前停刊”。[4]不到两年也就是1923年前后,二战前就相当宽泛了,1937年以前都是二战前。那么,究竟谁的说法更准确呢?
总体而言,当前国内有关新西兰早期华文报纸的既有研究都是在研究大洋洲时以非常简短的文字一笔带过,甚至对相对受关注的《民声报》的讨论也存在许多基本史实层面的问题。极少论文查阅相关报刊原文。①目前仅找到一篇中文论文较多地接触到了《民声报》原文,但该文也仅仅分析了该报1921年的情况,对1922年没有涉及。参见张金超:《从新西兰〈民声报〉看国民党的海外宣传与筹款》,2015年1月19日,http://www.gdass.gov.cn/webmanage/Resource/attached/file/20150129/20150129181623_7675.pdf,2016年7月16日访问。如果说1921年的《民声报》是新西兰第一份华文报刊(这个结论本身需要讨论,参见下文),那么在19世纪下半叶中国本土及海外其他华人聚居区如火如荼创办华文报刊的大背景下,为什么新西兰要迟至1921年才创刊本土第一份华文报纸?究竟是什么因素限制了本土华文报刊的出现?在1949年以前,除《民声报》外,新西兰华人还有没有创办其他报刊?如果有的话,应该如何从海外华文报刊史角度给予合理评价?
以上种种问题在此前的研究中没有得到解答,主要原因可能是史料难找。过去五年间,凭借在新西兰攻读博士的便利,笔者利用业余时间在奥克兰市图书馆搜集了《民声报》、《中国大事周报》及《侨农月刊》绝大部分报刊原文资料并系统梳理了相关英文研究文献。新西兰本土英文学位论文目前已至少可查到7篇(其中硕士论文5篇、博士论文2篇),另外华人学者叶宋曼瑛、伍德明以及一些西方学者也写过相关论文。他们多数是从口述史、移民历史与政治、身份认同等角度来讨论的。其中有些与华文报刊相关的观点值得探讨,比如新西兰华人之间形成某种“虚拟共同体”(virtual community)是在20世纪上半叶第一次华文报刊办报高潮时形成的,还是在更早的时候就已经有了雏形?总的来说,目前这类英文文献基本未被国内新闻史学者所重视。②最近中国社会科学院创新工程重大项目《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研究》在整理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的过程中梳理了一些英文著作,参见张丽:《新西兰华侨华人史的英文著述研究》,《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2期。但专门从华文新闻史的角度做文献回溯的基本还没看到过。
本文基于历史资料及相关文献,将从三个方面回答前文提出的有关新西兰早期华文报刊传播史的问题。③需要事先说明的是,这里所讨论的新西兰早期华文报刊传播,并不只谈第一份华文报刊创办后的历史,还会涉及到对华文报刊创办之前外来华文报刊在新西兰的传播情况,正是报纸的跨国流动及延伸影响使得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指的“想象的共同体”雏形得以更早出现。首先是淘金热时期,外来华文报刊在新西兰的流通及可能影响,力图回答为什么新西兰迟至20世纪初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华文报刊。接下来探讨20世纪上半叶社团政治及其引发的第一波办报高潮,着重分析华人社团与华文报刊的关系(比如《民声报》与国民党的关系)。最后再分析二战后归化时期华文报刊的情况及启示。此外,论文尝试揭示新西兰早期华文报刊传播从外来报刊主导到本土报刊主导的阶段转向及其内在缘由。
二、淘金热与外来华文报刊在新西兰的流通
(一 )新西兰华人移民潮的政治经济背景
新西兰地处南太平洋,分南北两大岛外加一些小岛,国土面积26.8万平方公里(面积介于我国广西和云南之间)。岛上传统居民是毛利土著,17世纪欧洲航海者发现这片陆地时,毛利人已在这里生活了1000多年。欧洲人从18世纪末开始登陆新西兰,到1840年2月(正值中英鸦片战争前夕)英国王室与毛利人签署《怀唐伊条约》,标志着新西兰正式成为大不列颠帝国在大洋洲的第二大殖民地。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同为英帝国的附属,两地与远东地区其他英国殖民地如印度、中国香港等,在人口流动、资本、信息及货物往来的便捷和相互依赖,远洋货轮、电报业以及后来的民用飞机的发展,意味着新西兰早期华人移民史及此后的华文媒介实践活动,首先应该放在英国全球范围内殖民扩张的历史大背景中来理解。
19世纪淘金热的兴起刺激了劳动人口在世界范围的流动,这包括1848年开始的加州淘金热、1851年澳大利亚淘金热以及19世纪60年代的新西兰淘金热等。因为生存压力,大批中国南方农民尤其是粤闽两省农民选择背井离乡去海外淘金。这与清末中国人外流出现高峰的历史是相符的。据当时上海《神州日报》的不完全统计,1907年前后全世界华人总数已超过600万人,其中澳洲3.5万余人。[5]这份统计没有把新西兰的数据纳入进去,1906年新西兰华人总数大概为2500人。①参见新西兰1906年人口普查数据。而在其前面的半个世纪尤其是1874—1881年间,新西兰华人数量达到顶峰,超过5000人(参见图1)。大洋洲地区的华人淘金者起先主要集中在澳洲矿区,后来部分淘金者继续迁移到新西兰。随着新西兰矿区稳定开采后,陆续有直接从中国(绝大部分是广东)过来的矿工。早期华人来新西兰的主要目的是存到100镑就回中国,他们在新西兰期间以亲戚、宗族或者同乡关系为纽带生活在一起。②一方面在真正赚到钱之前大约五分之四的人即使想回去也无法回去,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人回去了又再次出来。参见James Ng, 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 How the Cantonese Goldseekers and Their Heirs Settled in New Zealand ( I ), p.85。

图1 新西兰华人总数变化及历史事件(1860—1960)
当然资本及殖民扩张一方面促使各种资源跨国跨地域流动,另一方面也会对这种流动产生抑制作用。华人数量在新西兰、澳洲等地迅速增长,引起了各殖民区当局的恐惧。澳洲早在19世纪中叶就开始了歧视华人及其他有色人种的政策,1901年更是修改移民法并正式确立“白澳政策”(半个世纪后才逐渐废除)。新西兰虽没有明文的“白新政策”,但限制政策实际上是存在的,如1881年开始向华工征收歧视性的入境人头税(直到1944年才正式废除)。③20世纪20年代新西兰移民政策进一步收紧,除了英国人能自由移民新西兰外(针对英国人的优待一直持续到70年代),俄国、意大利、日本及非洲人都面临限制入境的政策。2002年时任新西兰总理海伦·克拉克代表政府为历史上向华人收取入境人头税等歧视性政策道歉,随后于2004年为新成立的华人人头税历史遗产信托委员会(Chinese Poll Tax Heritage Trust)拨款500万新西兰元,用于对早期华人移民对新西兰贡献的研究等。据华人学者叶宋曼瑛对新西兰早期主流英文报纸的研究,被称为“苦力”的华人当时是各类讽刺漫画中的主角,华人的信仰和习俗均遭到嘲讽。[6]这些政策及整体社会气氛对华人移民新西兰有明显的抑制作用。事实上1870—1915年间新西兰华人总数一直在不断下降(参见图1)。此后华人数量极大地受到新西兰移民政策的影响。
(二 )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西兰外来华文报刊及其影响
虽然19世纪华文报刊在新西兰本土创办的空间及可能性都非常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外来华文报刊在新西兰流通没有市场。最早进入新西兰南岛奥塔戈与西海岸地区的华人淘金矿工主要来自广东珠三角地区,并以农民居多,他们只是把新西兰当作暂时赚钱的地方。这些淘金者多数没有接受过文化教育,不少人连名字都不会拼写,他们没有能力也没有动机去创办报刊(比如像国内精英同胞那样去经营报馆),也不太可能成为报纸的直接“读”者(而只能是“听”者,听其他识字的华人读报)。①针对南岛矿区华人淘金者传教的牧师亚历山大·丹曾经记录了他的中文老师收集写过字的纸片,然后在一些仪式性场合烧掉。但毫无疑问像这样“珍惜字纸”的华人在当时的矿工群体中是少之又少的。参见《新西兰长老会》(New Zealand Presbyterian)1883年9月1日的记载,转引自James Ng & Nigel Murphy, “Chinese”, in Penny Griffith, Ross Harvey and Keith Maslen (eds.), Book & Print in New Zealand:A Guide to Print Culture in Aotearoa,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1997。当时华人整体的文字素养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为什么1921年以前新西兰没有产生真正意义上的本土华文报刊。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对中国尤其是广东家乡新闻的消费需求。作为替代,许多在中国本土出版或在近邻澳大利亚出版的华文报刊,进入了新西兰并在华人社区流通。
因史料有限,无法判断当时是否还有其他中国本土出版的报刊在新西兰流通,但比较确切的是,1880—1900年,在新西兰流通的海外华文报刊至少包括香港创刊的日报《德臣西报》与《华字日报》,上海创办的月刊《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与《花图新报》,以及广州创刊的日报《广报》。②这些报刊名称在当时的《基督教史观》(Christian Outlook)、《新西兰长老会》等英文宗教刊物以及亚历山大·丹(Alexander Don)的私人日记中有较详细的记录。其中一些杂志的原物收藏在但尼丁华人长老会华文图书馆(1984年以后存于Hocken Library),转引自James Ng & Nigel Murphy, “Chinese” , in Penny Griffith, Ross Harvey and Keith Maslen (eds.), Book & Print in New Zealand: A Guide to Print Culture in Aotearoa。更多的华文报刊直接从澳洲进来,较有名气的是1894年9月由华商孙君臣与两名西方人G. A. Down和J. A. Philip在悉尼创刊的《广益华报》(Chinese Australian Herald)。[7]该周报1895年曾载文要求清政府协助解决和关心澳洲华人问题。[8]根据刘康杰的研究,《广益华报》主要服务于华社并且办报思路已经比较现代化,发行范围包括新西兰。[9]其他一些在澳洲创办的华文报刊,如1898年在悉尼创刊的《东华新报》(1902年改名《东华报》,初为亲保皇党立场后有所转向)号称是当时澳洲联邦、新西兰、太平洋群岛销量最广的华文报纸。另外根据胡道静《报坛逸话》的记录,1913年在悉尼创刊(但刘渭平认为是1912年创刊)的《民国报》以及1922年在悉尼创刊的《公报》,至少从它们各自的发刊声明中,是将读者范围延伸至澳洲联邦、新西兰以及太平洋群岛甚至东南亚及中国各地的。
19世纪华文报刊向海外流播是中国新闻史上一个比较重要的特征,它意味着某种类似文化意义上的“想象的共同体”是可能存在的。不同于卓南生对日本华文报刊的研究发现,即“在十九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沿海城市(主要是香港)出版的中文报刊传入日本,但翻刻时都经删削,改变了版式,有的报名全改了,和原件已面目全非。”[10]至少20世纪前在新西兰流通的华文报刊因为印刷技术的限制,基本上不存在翻刻的问题,流通的往往就是原版报纸。报纸的时效性虽因信息传播技术的限制而大打折扣,但并不妨碍这些“过时的报纸”成为远赴重洋华人的精神食粮。多数目不识丁的淘金者可以通过有限的具有识读能力的同伴来分享报纸上的消息。
值得说明的是,这个时期的华文报纸对当地普通华人移民的影响不应被拔高。在当时的新西兰,绝大部分普通华人所面临的生存压力、歧视遭遇以及各种日常生活层面的诉求,外来的华文报刊几乎无法扮演有效的承载渠道。③外来报刊无法成为申诉渠道,促使华人发展其他表达诉求的方式。比如惠灵顿国家档案记录了1878年华人向奥塔戈省议会的集体请愿书,指向金矿主Warden R. Beetham的不公平。请愿书由英文写就,但签名都是中文(或指印)。这大概意味着有通晓英文的华人精英在后面策划此事。反倒是当时本地的英文报刊,常常会报道与华人有关的新闻,当然这些信息大多数都是负面的,比如以中英双语发布在华人社区禁止鸦片和禁止赌博的内容,甚至以悬赏方式呼吁华人提供一些案件的线索信息。④参见《邓斯坦时报》(Dunstan Times)1882年1月27日以及《新西兰长老会》1888年12月1日的记载,转引自James Ng & Nigel Murphy, “Chinese” , in Penny Griffith, Ross Harvey and Keith Maslen (eds.), Book & Print in New Zealand: A Guide to Print Culture in Aotearoa。外来华文报刊信息流通的单向性尤其体现在来自澳大利亚保皇党或者革命党创办的刊物上,以至于它们未必真能够广泛动员到新西兰普通华人并影响到他们的政见与认同。新西兰本土诞生的华文报刊似乎更可能成为新西兰华人的真正发声渠道。
三、社团政治与新西兰华文报刊的初创高潮
(一 )国民党《民声报》创刊前后
在华人社团之前,西方的宗教社团曾经尝试过办报。1883年在南岛圆山金矿区曾出现过一份由传教士亚力山大·丹(Alexander Don, 1857—1934)创办的华文周报。丹是长老教会牧师,1879—1913年,向华人矿工传教,他不仅学习中文尤其是粤语,还曾数次到访广东并记录了大量有关当时华工的情况。①这些宝贵的资料如今主要保存在但尼丁市的霍肯图书馆以及诺克斯学院的休伊森图书馆(Hewitson Library Knox College)。诺克斯学院于1909年创办,由长老教会拥有并附属于奥塔哥大学。还有一些资料散落在私人收藏者手中。有关丹本人的传记介绍,参见Dictionary of New Zealand Biography, Volume 2, 1993。这份周报叫“Kam lei Tong I Po”,Kam lei Tong是丹在南岛里佛顿镇传教时租的房子名称,“I Po”则指“日报”。根据其记录,第一期报纸出版于1883年5月12日,是手写的大纸,可以像海报那样在宣教时贴在墙上。丹在创办这份报纸时,应该得到了他的粤语老师的帮助。他笔下最后一次提及此报是在1883年10月,当时华人抗议他提供的中法战争信息与他们自己从海外报纸或信函了解的信息不一样。②参见《新西兰长老会》(New Zealand Presbyterian)1883年9月1日的记载,转引自James Ng & Nigel Murphy, “Chinese” , in Penny Griffith, Ross Harvey and Keith Maslen (eds.), Book & Print in New Zealand: A Guide to Print Culture in Aotearoa。现在已无法找到这份周刊的原物(而只能通过丹本人碎片化的记录来推测),故无法分析该刊物的内容板块,停刊日期也无从知晓。虽然创刊者丹并不是专业的报人,出版过程也缺乏专业的印刷工具(只是手写)和信息采编团队,但从该报会涉及中法战争这样的时事新闻来看,它已经具有新闻纸的雏形,因此可算作是新西兰本土华文报刊的首次尝试。
随着淘金热潮退去,部分淘金矿工开始涉足蔬果种植及小商业如蔬果店、洗衣店、木匠、餐饮等,同时随着一些华商及有知识素养的华人移民新西兰,华人群体的文化素质构成在逐渐改变,这为新西兰华文报刊的创刊奠定了直接基础。另外一个相对更重要的大背景是中国国内风云变幻的社会政治形势,促使知识分子外流并在海外创建社团、创办刊物来发展队伍并宣传各自的政见,并与国内政治派系有着千丝万缕的或竞争或合作的关系。以1900—1915年为例,新西兰共有同盟会、致公堂等五家华人社团创立。其中华人联盟(Chinese Association)是由清政府驻新西兰领事黄荣良于1909年支持创办的,目的是消解其他政治社团的反政府行为。③1908年4月22日,清朝外务部奏准在新西兰设领事一人,历任领事依次为黄荣良(1908年5月—1911年5月,后转任驻澳大利亚总领事直到清朝覆灭)、夏廷献(1911年5月上任)以及周玺(1911年上任)。参见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福建师范大学历史系编:《清季中外使领年表》,中华书局,1985年,第83页。该社团的年刊于1911年在新西兰编制但在中国印制,算是新西兰20世纪的首份华文印刷物,其内容主要是该社团的宗旨(为清政府寻求支持)、活动和创办者名录等,翌年即随清政府覆灭而告终。[11]
相较而言,后来影响甚巨的国民党最初在新西兰华人中的支持率并不高,随着当时一批坚定支持孙中山的革命党人积极发展壮大革命力量,其影响力才逐渐扩大。1921年上半年,国民党新西兰分部在惠灵顿成立(隶属于澳大利亚悉尼支部),其核心成员包括执行部正部长黄培、副部长周炳林、书记赵平鸣及周方锦、总务科主任周仲麟、会计科主任黄同发、评议部正议长陈兆芳(详见《民声报》创刊号)。在该分部的支持下,1921年7月11日新西兰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份本土华文报刊《民声报》(Man Sing Times)在惠灵顿创刊,赵平鸣及周仲麟为编辑、陈兆芳为督印。④《民声报》1921年7月11日创刊号对此进行了详细记载。其中赵平鸣(又名国后,1884—1957),原是悉尼《民国报》两位主笔之一(另一主笔是伍鸿培)。因攻击袁世凯称帝,而不见容于倾向保皇党的中国驻澳洲总领事商,后者请求澳洲政府驱逐伍鸿培出境。赵平鸣随后也转赴新西兰。上述资料得到刘渭平的佐证,参见刘渭平:《澳洲华侨史》,星岛出版社,1989年,第103页。
该报定位为国民党机关报,每10天出一期,售价为每份6便士,年费(含邮资)岛内16先令、外埠18先令。首页彩印绘有青天白日旗、五色旗及新西兰在世界地图的位置,外加中英文报头及期数等信息(英文报头明显是根据粤语发音译来)。其他页的内容则都是手写后另外复印的,这是20世纪初新西兰华文报刊的共同特征,汉字印刷技术在1949年后才引入新西兰。据其声明,发行范围不仅包括新西兰与澳大利亚,还远至美洲、英属海峡殖民地、太平洋岛屿、中国香港、广州及其他地方。①转引自Manying Ip, “Chinese Media in New Zealand: Transnational Outpost or Unchecked Floodtide?” in Wanning Sun (ed.),Media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Community, 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 Routledge, 2006, pp.178-200。该报实际发行范围是否真有这么广目前已无法证实,极可能是出版者借用国民党当时海外组织网络而作的夸大描述。该报内容较专业,包括言论(编者按)、特载、要电、要闻、时评、杂记(卫生、道德、笑林、灯谜、文学小品等,相当于“副刊”)、街市行情(蔬果菜肴价格、交通、金融等)与广告(西方人及华人商铺信息)等,基本每页分上下两栏或上中下三栏,偶尔有手绘插图。绝大部分内容是关于中国时政的,极少涉及世界其他地方信息。有“本岛新闻”板块,但也多与中国局势有关。比如1922年10月的本岛新闻,有3篇分别报道惠灵顿、奥克兰、但尼丁等埠侨报的“双十”国庆活动,唯有1篇隐晦批判盗贼猖獗以及警匪沆瀣一气。该报1922年10月21日出版第2卷9~10期合刊,内容配置如常,没有停刊告示。唯有一则以“本报营业部”名义发出启事催缴报费“俾资周转”,暗示存在经营问题。此后停止印发,直到1923年有过短暂的复刊但很快又停刊。《民声报》在1921—1922年间共连续出版40期,目前保存完好者仅32期(1921年与1922年各16期),各期页数在15~39页之间(平均每期29.5页),广告平均占9页。②需要指出的是,目前相关研究文献一致认为《民声报》仅出版了31期,这是有误的。根据笔者的统计,1921年连续出版了16期,这可以从连续的期号看出来,而1922年总共连续出过24期,除开最后两期是合刊的以及目前没法找到的第18、20-25期外,两年总共存世32期。另外因篇幅所限,有关《民声报》以及下文将提到的《中国大事周报》及《侨农月刊》的详细内容研究,笔者将另文探讨,本文仅对其基本情况略作简述。
国民党奥克兰分部于1930年也尝试出版过一份叫《民铎月刊》(Min Hok Times)的报纸,但仅出版一期即告停刊。[12]这个阶段新西兰本土华文报刊的出现,主要是社团政治的产物,尤其是国民党的报刊活动不仅起到了联络海外国民党成员的作用,也在一定程度上将新西兰华人卷入中国时局和政治斗争中去。但真正将南太平洋的普通华人与遥远的中国联系起来的主要是抗日战争期间所创办的华文报刊。
(二 )报刊动员与纽西兰华侨联合会的办报活动
1937年“七七事变”后,成立不久的纽西兰华侨联合会(New Zealand Chinese Association,后为华联总会)旋即筹划《中国大事周报》(New Zealand Chinese Weekly News),首期于8月20日在惠灵顿面世,周仲麟任编辑,督印及抄写者经常变换。该周刊持续出版至1946年7月31日停刊,共出440期(目前保存完好428期,平均每期29页)。③李海蓉博士论文认为该报创刊是在1937年9月,准确来说是在当年8月20日创刊,8月份出版了两期。另外她论文中所认为的该报共发行379期也并不准确。具体见Hairong Li, A Virtual Chinatown The Diasporic Mediasphere of Chinese Migrants in New Zealand,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2009。该刊向全新西兰发行,据估计每期发行大约三至四百份,13自第二期始售价为每份一先令。全刊手写并复印出版,主要内容包括中国战事情况、呼吁新西兰华侨捐款捐物及其他支持中国抗战活动(华商每星期要求捐款10先令,工人每星期每镑工资定捐2先令),几乎没有任何商业广告。大部分内容来自国内电报,部分内容译自英文报纸(包括《惠灵顿早报》、英国《泰晤士报》、苏联《真理报》等),偶有当地华人来稿。办报收入(仅付笔纸墨开支,报人均属义务劳动)及所有捐款都归入救国抗日捐金,捐款者的名字以“芳名录”方式印在每期报纸上。《中国大事周报》毫无疑问与国民党关系密切,报名即由时任国民政府驻惠灵顿总领事馆总领事汪丰题写,④汪丰于1935年2月19日至1939年5月17日任中华民国驻惠灵顿领事,1939年5月17日至1949年任总领事,参见刘国铭:《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军政职官人物志》,春秋出版社,1989年,第689页。每期首页必登出孙中山先生的《总理遗嘱》,在抗日战争期间针对新西兰华人社区的救国动员中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纽西兰华侨联合会的奥克兰分支机构于1938年11月也创办了一份战时刊物,即《屋伦侨声》(Q-Sing Times),①因为笔者手头暂无该报原文,本段有关《屋伦侨声》的内容分析如无特别说明均主要参考了李海蓉博士论文的相关分析,具体见Hairong Li, A Virtual Chinatown The Diasporic Mediasphere of Chinese Migrants in New Zealand,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2009, pp.30-33。但笔者尽量寻找其他佐证材料并对其博士论文中的错误进行订正,具体参见本段下一条注释。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停刊。②参见新西兰国家图书馆电子档案的相关介绍:http://natlib.govt.nz/records/22246331?search%5Bpath%5D=items&search%5Btext%5D=q-sing+times,2016年7月21日访问。李海蓉博士论文第30页认为《屋伦侨声》于1930年11月创刊,应该是作者的笔误。《屋伦侨声》最初只有中文报名(“屋伦”是早期华人对北岛城市“奥克兰”的译称),1939年5月应新西兰政府的要求才以Q-Sing Times英文登记注册。此后中英文双语出版,手写后再复印,每两星期出一期,每页略小于今天的A4纸,头版通常是手绘的战争人物如政客或士兵。内容包括编者按、中国和本地华社新闻、广告(与《民声报》类似同样包括华人和西方人商铺广告)以及一份叫“声光”的文学副刊。《屋伦侨声》在使用“我国”、“我政府”时都分别指当时的中国及国民党政府,表现出对中国国内政府的亲近与对新西兰政府的距离感。这与《民声报》是类似的。《屋伦侨声》的经费来源主要可能是捐款、广告收入和订阅费,但部分研究者暗示它可能还有来自中国国民党政府驻新西兰领事的资助,或者直接由国民党赞助。该报主要发行于奥克兰,但在新西兰其他地方甚至澳大利亚、南太平洋岛国都有流通。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的华文本土化报刊基本上是以社团为核心的,既包括中国政府创办的社团也包括拨款支持的社团,可谓政治社团的报刊时代。不论是《民声报》还是后来的两份刊物,在内容上都以中国新闻为主。尤其是纽西兰华侨联合会创办的两份刊物对中国国内战事以及援战动员的报道,在某种意义上有助于将分散各地的华人整合成一个“共同体”。[14]当然这个阶段所形成的“共同体”与外来华文报刊所形成的“共同体”存在着明显区别。首先,本阶段的“共同体”意识并不全是依赖华文报刊所形成,也同样依赖报刊背后的华人社团及中国国内政治时局,后者的作用也许更为本质。其次,虽然这个阶段的华文报刊依旧表现出较明显对中国的亲近与对新西兰的距离感,但是华人与新西兰社会的关系已经在发生微妙的变化,华文报刊刊登西方人商铺广告恰从侧面体现出华人已与本地社会形成了一定的融合。这种融合趋势在二战之后表现得更为明显。
四、归化时期的华文报刊:《侨农月刊》及其他
(一 )《侨农月刊》的出现和风格转向
二战结束后,1947年弗雷泽领导的工党政府允许新西兰华人的妻儿以难民身份进入新西兰。③皮特·弗雷泽(Peter Fraser,1884—1950),于1940—1949年间任新西兰总理,赢得当时绝大多数华人的尊敬,认为他是非常人性化的总理。弗雷泽甚至出席了1942年惠灵顿华人举行的“双十”国庆活动。同时,随着中国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不少华人移民开始把新西兰当作定居地。华文报刊的出版逐渐走向低潮,仅有部分社团出版发行内部刊物以及一些小范围流通的政治性刊物。如亲国民党派别(当时新西兰华人社团多数持亲国民党立场)先后创办《中国呼声》、《新西兰华文月刊》(The New Zealand Chinese Monthly Special,1950年创办)、《快报》(Kui Pao,1952年创办),以支持台湾当局。而亲共产党派别的新西兰华人文化协会(New Zealand Chinese Cultural Society)也创办了一份新闻月刊来消解国民党阵营刊物的影响,其中包括一些时事通讯特刊如1958年的《五一特刊》(May Day Special),以促使新西兰侨民保持与新中国的关系。[15]与该时期其他出版物不同的是,这些特刊是由中文打字机打字并影印的。
一些关注现实生活的报刊也得到出版,最有代表性的是由新西兰华侨农业会(Dominion Federation of New Zealand Chinese Commercial Growers)①该机构是为了响应弗雷泽工党政府号召而于1943年1月15日成立的,工党希望可以为当时太平洋的美军提供粮食补给,为此弗雷泽政府出资300镑,呼吁该组织把华人种植者联合起来并促使信息共享。参见Charles Sedgwick,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1982, pp.413-414。在1949年7月1日出版的《侨农月刊》(New Zealand Chinese Growers’ Monthly Journal)。该刊出版发行达23年之久,一直到1972年8月1日停刊,共出版237期,②李海蓉博士论文第34页认为该报共发行165期,这并不准确。算是新西兰早期华人移民出版刊物中历时最久的。严格来说该刊在1967年以前基本算是月刊,1968—1970年间是双月刊,此后一直到停刊则是三个月出一期。在发刊词中,《侨农月刊》原本是作为社团内部刊物来出版(1942年农业会雏形阶段就已经出版),后考虑到“本会所负之任务极其重大”(当时从事农业相关工作的华人已占华人总数的一半多),而从年刊扩大为月刊并正式成为华侨农业会的机关刊物,以“增加各地侨农间之联系,促进农会之会务,灌输有关于助长农事业生产之技术知识,鼓吹提高侨农生活水准及阐扬我国之文化等”(见该刊1949年7月1日内容)。先后由华侨农业会秘书陈中岳(见1949年8月1日第15版内容)、石松主持编辑工作,后改组为社长负责制,另设督印、经理、编辑、采访、会计、广告、排印等部门(见1961年10月1日第1版),编辑团队就基本再没有什么变化。印刷方面开始时是钢笔写印后改为铅字排印,自1949年9月“开始改用电版颜色印刷”,大小像今天的A2纸张,两面印刷,各期印刷页数在4~38页范围内变动,平均下来每期出版10.5页。该刊用传统中文书写,采自上而下自右而左的排版方式,并以“民国纪年”发行,报头同样也是汪丰题写。因是“非卖品”而以会费、广告、捐助等维持运营,由“纽西兰华农印务出版有限公司”负责发行,面向侨农免费邮发,每期发行约700份。其中广告费用根据面积大小(分整版、半版、四分之一版)和时间长短(分整年、半年、一月)依次不等,全年整版为65镑,一个月四分之一版为2镑。这份刊物行业性、针对性强,除了华人广告外也吸引了许多西方人的商铺广告,尤其包括保险、银行、农用洒水工具、拖拉机、农作物杀虫与施肥、种子售卖等。
根据早期文章内容来看,该刊物虽在政治立场上离国民党及台湾政权近些,但对中共解放上海、南京等城的消息报道还算中肯持平。刊物定位在农业话题上,但很快就成了社区传声筒,是新西兰有史以来第一份主要关注本地新闻和故事的华文刊物。内容方面本来打算“在香港聘任专员访采国内时事新闻”(见1949年9月1日第10版),但自1960年7月30日开始因新西兰政府推行融合政策的缘故,“一律减除登载有政治色彩之新闻”(1960年6月30日第6版),本刊重归“侨农”定位,只登载新西兰本土与农业有关的新闻,刊物变得更为融合新西兰本地社区。1972年8月因“字房搬迁,编辑工作人员转业”而停刊,但直接原因是经费问题(见该刊1972年8月1日第五版中英文停刊启事),尤其是该刊读者市场有限,凭借广告收入(自创刊以来广告费用就没有变过)及华侨农业会的经费支持仍入不敷出。该刊后期刊数的缩水大概也暗示着编辑人员及运营经费的紧张。
(二 )多元刊物的出现与新西兰华人的进一步归化
此外,活跃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刊物多数是些小范围的时事通讯,以中英文双语出版(英语已经逐渐成为当时第二代华人的母语)。比如惠灵顿地区教会的双语时事通讯《华人圣公会》(Chinese Anglican,创刊于20世纪60年代),奥克兰地区的时事通讯《奥克兰华文厅》(Auckland Chinese Hall,创刊于1961年),还有体育出版物如《惠灵顿华人运动与文化中心时事通讯》(Wellington Chinese Sports and Cultural Center Newsletter,1974年创刊)。另外四邑会馆(Seyip Association,四邑指新会、台山、开平、恩平)出版了月刊《四邑青年》(Seyip Youth),该刊物的出版并不晚于1949年。③参见《侨农月刊》1949年8月1日第三版时任副领事刘东维写的文章《祝新西兰华农月刊》,该文中提及“《中国呼声》和《四邑青年》是纽西兰侨胞们宣扬祖国文化和中外知识两块仅有的园地”。该会馆还于1970年参与出版了美食书《新西兰筷子》(Kiwi Chopsticks)去推广中国饮食文化,从而为“后来中餐馆和外卖店的流行铺了道路”[16]。
总的来说,1950年以后新西兰华文报刊实践带有明显的归化时期的特征,正如新西兰华侨农业会及其机关刊物《侨农月刊》所反映出来的,虽然在有关中国问题上仍持亲国民党的政治立场,但其政治色彩已经相当淡化,而是更多地与新西兰本土发生密切联系。事实上以华侨农业会组织本身与弗雷泽工党政府的关系可以看出来,这是新西兰历史上第一个被政府认可的华人社团组织,此前的华人社团莫不是由中国领事馆所加持。[17]而《侨农月刊》作为一份农业专门刊物,能够持续出版20余年实属不易,其编辑方针不断调整以促使内容(包括广告)不断亲近本土,不仅为新西兰侨农提供了一块精神园地,也不断促使侨农融入本土社会。另外双语刊物的出现也是对新西兰移民政策潜在影响的回应,许多华人后代接受的是英文教育,尽管当时也有些免费中文学校来试图培育新一代华人说中文,但整体上会读华文报刊的读者群在逐渐萎缩。确切来说,《侨农月刊》的停刊基本上标志了华文报刊传播在新西兰走向了全面衰落。新西兰本土华文报刊实践的重新兴起有赖1987年后新一波华人移民的到来。
五、结语
因受到华人移民潮、新西兰移民政策及中国国内政治时局的影响,新西兰早期华文报刊传播存在明显的阶段转向特征。在1910年以前尤其是淘金热时期基本以消费外来华文报刊为主;而1920—1970年间随着华人政治社团的兴起,依附这些社团的本土报刊不断出现并在本地华人阅读市场中占据了主体地位;①值得说明的是,淘金热退去之后外来华文报刊在新西兰的流通过程实际上一直没有中断过。哪怕新西兰本土开始出版华文报刊杂志之后,仍有诸如《海外》、《中美周报》、《生活》等刊物进入新西兰并在华人群体中流通。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视新西兰为家园以及以英文为母语的第二代华人的出现,华文报刊又逐渐走向了衰落。华文报刊传播的阶段特征呼应了叶宋曼瑛等学者关于早期新西兰华人在身份认同方面从“侨居者”到“定居者”的转向,②早期华工并未把新西兰当作家乡,是明显的侨居者(sojourners)而非定居者(settlers),当时新西兰政府对华人入籍也有非常严格的限制。参见Manying Ip, “Chinese Media in New Zealand: Transnational Outpost or Unchecked Floodtide?” in Wanning Sun (ed.), Media and the Chinese Diaspora: Community, Communications and Commerce, Routledge, 2006, pp.178-200。侨居阶段主要消费外来报刊,而定居阶段则以创办与消费本土报刊为主。
同时,本文比较系统地梳理了1865—1970年间在新西兰传播的外来华文报刊与本土华文报刊,也对目前学界关于这些报纸的谬误进行了比较细致的纠正。正如本文所述,新西兰早期本土华文报刊并不仅仅只有《民声报》,其华文报刊实践活动要丰富得多,此后不仅先后创办过《中国大事周报》、《屋伦侨声》、《侨农月刊》等比较有影响力的刊物,还发行过其他大大小小的出版物。这种梳理为研究早期海外华文报刊史提供了一个较为清晰的新西兰个案。
不过正如新闻史学研究的耆老方汉奇先生所言,海外华文媒体“……历史跨度近两百年,因此资料搜集整理非常困难,第一手资料搜集整理更加困难”,还是一个“未曾穷尽也不可能穷尽的研究课题”。[18]本文对新西兰早期华文报刊传播的梳理仅算抛砖引玉,远远没有达到充分挖掘这段尘封历史的目的。尤其是诸如早期华文报刊内容分析、二战后至今新西兰华文媒体实践、与西方媒体在内容上的互动等议题仍需继续努力探究。
[注释]
[1] James Ng, 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 How the Cantonese Goldseekers and Their Heirs Settled in New Zealand (I),Otago: Otago Heritage Books, 1993, p.7.
[2] 胡道静:《报坛逸话》,世界书局,1940年,第22~23页。
[3] 方积根、胡文英:《海外华文报刊的历史与现状》,新华出版社,1989年,第258~259页。
[4] 程曼丽:《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92页。
[5] 方汉奇:《〈清史·报刊表〉中的海外华文报刊》,《国际新闻界》2005年第5期。
[6] Manying Ip & Nigel Murphy, Aliens at My Table: Asians as New Zealanders See Them, New Zealand: Penguin, 2005.
[7] 刘渭平:《澳洲华侨史》,星岛出版社,1989年,第99~102页。
[8] 李安山:《详人所略的策略与史料史识的结合—评黄贤强博士的〈海外华人的抗争:对美抵制运动史实与史料〉》,《华侨华人历史研究》2007年第3期。
[9] 刘康杰:《澳洲华文报纸的发展历程研究》,《新闻与传播研究》2013年第9期。
[10] 宁树藩:《撩开中国近代报史的面纱—喜读卓南生的〈中国近代报业发展史(1815-1874)〉》,《新闻大学》1999年春季刊。
[11] [12][15]James Ng & Nigel Murphy, “Chinese” , in Penny Griffith, Ross Harvey and Keith Maslen (eds.), Book &Print in New Zealand: A Guide to Print Culture in Aotearoa, Wellington: Victor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13] Jiangqiang Huo, A Study of Chinese Print Media in New Zealand: History, Culture and Professionalism, MA thesis,The University of Auckland, 1999.
[14] Charles Sedgwick,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1982.
[16] James Ng, Windows on A Chinese Past: How the Cantonese Goldseekers and Their Heirs Settled in New Zealand(III), Otago: Otago Heritage Books, 1993, pp.391-392.
[17] Charles Sedgwick, The Politics of Survival: A Social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New Zealand, PhD thesis, The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1982, p.414.
[18] 方汉奇:《海外华文媒体研究的新思路》,《新闻与写作》2009年第10期;程曼丽:《海外华文传媒研究》,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3页。
The Domestication of Chinese Newspapers in New Zealand (1865—1970)
CAO Xiao-jie
(School of Communication and Design, Sun Yat-sen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006, China)
New Zealand; Chinese newspapers; Chinese migrants; identity recognition; domestication
This paper preliminarily lists the disseminating process of Chinese newspapers during the transition from the dominant of the overseas newspapers to the dominant of the local newspapers in New Zealand from 1865 to 1970 and its influence onto the identity interpretation and recognition of Chinese migrants in New Zealand. The paper finds that “The Man Sing Times” was not the only Chinese newspaper published in New Zealand in the early days; actually, much more Chinese newspapers were printed and circulated during that time.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Chinese migration wave, the immigration policy in New Zealand and the political situations in China, there was an obviously feature of the gradual transition of the disseminating process of early Chinese newspapers in New Zealand. Before 1910, especially during the Gold Rush period, Chinese migrants mainly consumed overseas newspapers. From 1920 to 1970,accompany with the rise of local Chinese political organizations, local Chinese newspapers which attached to these organizations started to emerge and dominated the local Chinese reading market. However,there is an increasing number of Chinese migrants who treat New Zealand as their new homeland and the appearance of the second Chinese generation who take English as their mother tongue, it makes local Chinese newspapers encountered a gradual decline in popularity.
D634.361.2
A
1002-5162(2017)04-0040-11
2017-06-22;
2017-08-18
曹小杰(1985—),男,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新西兰媒介史、媒介社会学、互联网文化研究。
*本文为2017年度中央高校基本业务经费项目“文化史视域下的新西兰华人移民与华文报刊研究”(17WKPY03)之成果。
[责任编辑:胡修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