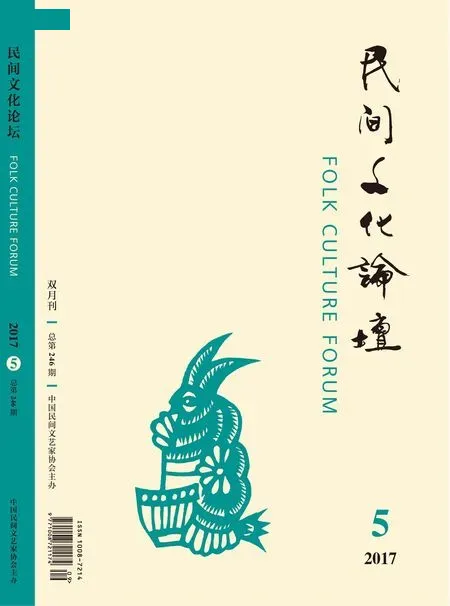“神话主义”的应用与“中国民俗学派”的建设
2017-01-28施爱东
施爱东
前沿话题神话主义与朝向当下的神话学
“神话主义”的应用与“中国民俗学派”的建设
施爱东
杨利慧教授所定义的新“神话主义”,是指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现代文化产业和数字化传播技术的广泛影响而产生的,对传统神话的挪用和重新建构。神话主义虽然摆脱了旧社区的生活语境,但是,它有助于将我们的研究视野引向更广阔的现代神话传承语境。所以说,神话主义是以当代文化为视角、为目的、为旨归的研究,是一个时代性的前沿学术概念,也是钟敬文先生所倡导的“中国民俗学派”的探索性成果。
神话主义;民俗学;中国民俗学派
杨利慧教授关于“神话主义”的建构已有多年,日臻成熟。几年前大概是在刘魁立老师召开的“亚细亚民间叙事文学学会”年会上,第一次听到杨利慧关于“神话主义”的理论构想,我当时就表示非常喜欢,并且建议说,论文应该尽快正式发表,方便同行引证。今天看到这本《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以遗产旅游和电子媒介的考察为中心》,借此机会,我想再展开谈谈自己对于神话主义,以及对于实践钟敬文先生“建立中国民俗学派”①钟敬文:《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9年。的一些想法。
我对自己的定位是个典型的现实主义者,吕微说我是科学主义,我也欣然接受,还有人给我贴上别的一些标签,比如实用主义、技术主义、操作主义,我都不反对。每次面对新概念、新计划,或者新理论,我的第一反应永远是“有用吗”“可行吗”“谁来执行”“会产生什么效果”?
神话主义有用吗?
神话研究,或者说我们的民间文学研究,都是人文科学的一部分。人文科学最根本的目的,就是不断完善我们对于世界的理解方式,以此解决困扰人类的种种问题。那么,神话主义是否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社会人的精神世界及其活动规律呢?我倾向于是有助于。
传统的神话研究或者执着于源流考镜,或者执着于土著语境。对于神话在当代社会中,尤其是在文化商品化、民俗旅游化、传播数字化进程中的传承、变异及其意义,鲜有充分的关注和细致的研究,而神话主义正是为了弥补这一缺憾应运而生的。
杨利慧所定义的新“神话主义”,是指二十世纪后半叶以来,由于现代文化产业和数字化传播技术的广泛影响而产生的,对传统神话的挪用和重新建构,神话被从其原本生存的社区日常生活的传统语境移入新的开放性语境中,为不同的受众而展示,并被赋予了新的功能和意义①杨利慧等:《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以遗产旅游和电子媒介的考察为中心》,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2017年7月,第6页。。
吕微和王娟均认同马林诺夫斯基功能主义神话学的观点,认为“神话是神圣性的信仰叙事”,神话与传统仪式、神圣性之间有不可分割的关系,而悬置了神圣性的神话主义只能是一种外在于“神话”的文化现象。但是,电子技术、数字传播、全球经济已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知识渠道和生活方式,如果继续执着于这样一种传统的神话观的理解模式,当代文化生活中的神话传承和发展变化就被“神圣性”的大墙挡在了既有的神话学学术框架之外,神话研究与当代文化生活的距离也将越拉越远。
而杨利慧的神话主义恰恰是为了“探究神话传统在当代社会中,特别是由于文化产业和电子媒介技术的广泛影响而产生的对神话的挪用和重新建构,使学者的目光从以往的社区日常生活语境扩展到在各种公共社会文化空间中被展示和重述的神话,并把该现象自觉地纳入学术研究的范畴之中,从理论上加以具体、深入的研究,从而使神话学这门一直擅长于‘向后看’的学问也能直面身边生动鲜活的社会事实,在‘向后看’的同时也能‘朝当下看’,进而在完整的历史脉络中把握神话的生活力”②杨利慧等:《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以遗产旅游和电子媒介的考察为中心》,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2017年7月,第11页。。
杨利慧在对神话主义理论资源的追溯中说到,神话主义是对民俗主义的借鉴和发展,是国际学术对话的深化。神话主义既指涉一种新兴的文化现象,也是一种价值视角。它有利于拓宽神话研究的学术视野,将神话研究从原始思维、溯源研究中解放出来,直面当下文化现实,从而打通神话研究的古今隔阂。
从语境与功能的角度来看,神话主义摆脱了旧社区的生活语境,它有助于将我们的研究视野引向更广阔的现代神话传承语境,如网络社交平台、虚拟社区、电影电视、网络游戏、旅游服务、市场开发、民族政治等领域。当我们把视角转向这些新的神话语境,神话的意义和功能也会呈现出新的面貌,这有助于加强神话学与大众文化、数字传播、文化产业等学科领域的对话。
从学术政治的角度看,神话主义恰恰是对习近平倡导的“要按照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关怀人类、面向未来的思路,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③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news.cn/,2016-05-18。的具体响应。
神话主义可行吗?
为了回应神话主义建构的可行性问题,杨利慧带领她的学生们做出了六个案例分析。这六个案例大致可以分成两个版块,每个版块各三例。一个版块是通过不同地域、不同民族、不同神话类型的个案,描述遗产旅游语境中神话主义的具体表现及其变异性特点,对旅游文化给神话传统所造成的冲击和影响进行了分析。另一个版块则聚焦于神话主义在影视和网络传播中的表现、在新媒体视界中所呈现的新形态,以及神话主义与传统神话形态的关联、神话主义在网络群体中的互动形式等。
传统的神话研究关注文献、图像、文物、仪式、日常生活中的神话,但很少关注遗产旅游语境下官方主导、企业策划、导游讲述的神话。事实上通过导游的讲述和传播,遗产旅游语境下的神话讲述与神话景观已经成为一种影响巨大的文化现象、它们与旧语境中的神话传统之间有着怎样的继承关系、它们的存在是否会对原有的神话传统形成冲击、各自有什么特点,这些都是值得我们关注的。杨利慧和她的学生分别在河北省涉县娲皇宫景区、云南省元阳县箐口村、湖南省泸溪县辛女村进行了田野调查,细致地探讨了神话主义的发生、发展及其影响,其前期成果发表之后,引起了民间文学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其中的部分论文还被《文化研究》等报刊复印资料全文转载。
数字传播通道繁复,数量巨大,对于我们这些中老年民间文化工作者来说,可谓“海客谈瀛洲,烟涛微茫信难求”,于是许多学者干脆选择放弃、无视,甚至以“没有学术价值”作为逃遁、回避的理由。但是不可否认,电子传媒和数字传播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文化大势,刻意回避只会让我们的民间文化研究更加脱离社会现实,坐失与时俱进的学术良机。
令人欣慰的是,网络文化对于80后、90后的年轻学者来说并不陌生,他们中的部分活跃分子,学有余力尚能浸淫其中、乐在其中,问题在于如何引导他们将那些日常生活和娱乐中貌似无用的知识积累转化为有用的学术资源。在这一点上,据我所知,杨利慧、田兆元、孙正国是做得最好的老师,比如田兆元指导张海岚撰写的《制造节日:“双十一”如何成功收编“光棍节”》就曾给我非常深刻的印象。杨利慧以神话主义的前沿学术理念,指导学生大胆探索;祝鹏程的《“神话段子”:互联网中的传统重构》;包媛媛的《中国神话在电子游戏中的运用与表现——以国产单机游戏<古剑奇谭:琴心剑魄今何在>为例》;陈汝静的《影视媒介中的神话主义——以<远古的传说><天地传奇><哪吒传奇>等为个案》就是其中的试验成果。
杨利慧的引领和示范无疑是卓有成效的,许多年轻学者受此启发,发挥各自的阐释想象,生产出了更多的学术成果。比如吴新锋“以神话主义的理念为基本视角,以西王母神话的当代呈现为中心,讨论神话主义与当代西王母神话研究的可能性路向,以此讨论神话主义的理论贡献,并通过引入心灵、秩序、记忆等概念丰富神话主义的讨论。”①吴新锋:《心灵与秩序:“神话主义”与当代西王母神话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高健则进一步将神话主义拓展到现代出版业中的“书面神话”领域,认为:“书面神话彰显了神话的民族性,神话由原来的内部传承关系转变为外部传播关系,通过汇编等文本制作手段,神话的叙事性也被进一步增强。在现当代社会语境中,神话主义的现象越来越普遍,从神话到神话主义应当被看作是神话生命的延续,而神话学研究也应适当地聚焦在认同、调适、修辞、权力等问题上。”②高健:《书面神话与神话主义——1949年以来云南少数民族神话书面文本研究》,《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6期。
谁来执行神话主义?
既然神话主义可行,那么谁来执行呢?也就是说,谁会借用神话主义的眼光看待问题、使用神话主义的工具分析问题?学生!或者比我们年轻一辈的青年学者。
我们永远不要指望上一辈的学者会认真阅读你的著作,接受你的理论,更不要指望他们会应用你的理论来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他们中间如果有谁像乌丙安先生那样,间或向更年轻的一辈推介你的理论,或者在某些场合表示对你的欣赏,那已经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了。我在许多场合说过,乌先生有一颗年轻的心,他常常笑称自己是“80后”,我想,乐于接受新事物、新观念、新理论,或许是乌先生保持年轻的最高秘诀。我乐于借助这篇文章,顺带表达我对乌先生的由衷敬意。那么,同辈学人会接受你的理论吗?也许会,但很难。学者的思维定式在40岁以前已经形成,其理论框架已经基本固定,要想让他接受一种新的理论,尤其是学术地位跟自己半斤八两的同行的新理论,那是非常困难的。就算他接受了,愿意向更多的学者推介,也不等于他会应用你的理论来看待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我因为做学术史,加上经常写年度学术综述,常常翻阅同行的论文,印象比较深的,最常引证同辈学者论文的民俗学者主要有吕微、户晓辉、张士闪三位。借助这篇笔谈,顺便再表达一下我对三位学者的敬意。
之所以要表达敬意,是因为大部分学者都做不到这一点。我曾经在一些公开场合指名批评过某些学者的古怪学术心态。同样的学术观点,国内学者早就说过,他们却视而不见,非要去引证一些别人不便查证的国外某出版物上的某些非著名西方学者的佶屈聱牙的平庸的片言只语,好像不如此就不足以证明他学贯中西、旁征博引。甚至我还从不同渠道听说,有个别知名学者居然要求自己的学生,除了钟敬文先生的著作和自己的著作,其他国内同行的著作都不用读、不许引。这真是天方夜谭,我甚至宁愿相信这只是一种学术传说,或者学术玩笑。
我始终认为,关注和引用同行,尤其是同辈或晚辈同行学者的优秀学术成果,不仅是学术上的精进和深入,也是一种相互尊重的学术美德。当然,关注既包括推介和引证,也包括批评。最令人遗憾的其实是对同行成果的漠视乃至无视,彼此漠视的结果,一定是共同湮没。我们每个人都在写论文,每个人都在读“经典”,却不关注同辈同行的学术成果,于是,大量的重复劳动和“同义创新”就变得不可避免。
民俗学界在译介国外同行的学术成果时,往往也偏向于译介“过去的经典”。我们从译者手中接过的,总是慢了半拍的“海外学术”。东南大学外国语学院陆薇薇教授曾经和我讨论学术成果的译介问题,我建议说:“希望你能密切跟进、消化日本中青年民俗学者最前沿、最优秀的学术成果,将它介绍给中国民俗学界,推动中国民俗学的国际交流与发展。不要像有些学者,老盯着别人的旧货市场,译介一些过时的东西。”那些过时的经典有用吗?当然有用,世上没有没用的知识。可是,这些经典在国外本已过时,我们好不容易学了来,你有兴趣向前追,人家没兴趣回头看,跟不上别人的步伐,国际对话就建立不起来。所以说,无论是面对国际同行还是国内同行,我们最该关注的,都应该是学界同行的当代成果、前沿学术。只有彼此关注对方的兴奋点和前沿思考,才能有效地点燃学术对话。
习近平同志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在国际上的声音还比较小,还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境地。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①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新华网,http://www.news.cn,2016-05-18。这段话说得非常精当。学术话语的生产,不仅要“说得出”,还要“传得开”。打造概念当然是第一位的,引导讨论也是必不可少的。如果大家都只顾着各自低头“创新”,不讨论、不呼应学界同人的学术话语,新概念再多又有什么用呢?充其量只是鱼目混珠的杂货堆,所谓“建立中国民俗学派”就永远只能是一句空话。试想,如果连我们自己都不尊重、不重视学界同人的学术创造,不相互支持、引用,有可能让国际同行认识你、理解你、重视你吗?
在这一点上,我特别赞赏吕微、户晓辉、高丙中、王杰文等几位同行互相呼应、反复讨论、不断精进的学术精神,他们的学术对话和互动已经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共鸣场”,产生了巨大的学术能量,在学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户晓辉提出的“未来民俗学”概念虽然时间不长,但影响不小,这个“标识性概念”连带着概念背后的学理和主张,已经为许多民俗学者所理解。所谓“学派”的形成,不就是一个个“共鸣场”所发出的同声共气的学术声音吗?
在神话主义的学术领域,目前跟进讨论的全都是比我们年轻一辈的民俗学者,这种站在前人肩膀上继续攀登的学术风气是我们所乐于看到的。无论跟进、补充、修正还是批评,参与讨论本身就是扩大学术影响的有效途径。仅仅“说得出”并不能自然构成一个学派,只有通过充分的对话和讨论,让那些有意义的学术话语“传得开”,使之成为共同知识,才能在这些共同知识的基础上建立“中国民俗学派”。
神话主义会产生什么效果?
这里所说的“效果”,既包括社会效果,也包括学术效果,还包括其他可能引发的不良“后果”。那么,神话主义可能会引发什么不良“后果”吗?当然会。
神话主义现象与社区文化传统的分离、语境的转换、对神圣性的悬置,都有可能导致神话“异质性”现象的发生,对于神话的“本真性”和“原生态”无疑是一种冲击。认同了神话主义的合理性、合法性,也就意味着丧失了守卫神话“神圣性”的伦理威力,拆除了保障神话“纯洁性”的防火墙,这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神话传统的加速腐蚀和式微。
可是我们知道,任何知识都具有不完善性和非终极性,它必须在不断变化的社会条件下受到持续的修正。价值观念也一样,随着社会的变革,对事物认识的深化和反复,我们会不断修正自己对于事物的印象和成见。神话主义赋予当代神话的变异性传承以合法性、正当性,恰恰有助于我们开启一种新的理解模式,打破“本真性”的思维局限,从“真”与“伪”的僵化思维中跳脱出来,进一步深化我们对于神话作为一种变异性民间文化的认识。
一旦打破传统观念的思维窠臼,许多习以为常的文化现象就会呈现不一样的精神面貌。比如,受到西方文明观的影响,我们一直以“不喧哗不吵闹”作为文明观戏的一条标准。有“当代坤生第一人”之誉的王佩瑜却说到一件事:“戏中的核心唱腔,是我和我的几位老师精心打磨出来的,我们打磨这些唱腔为什么呀?就是要让观众叫好呀!”可是,她却多次遭遇文明观众的沉默观戏,“唱得那么好,没有人鼓掌”①蔡木兰:《王珮瑜:京剧的叫好是一种文化》,澎湃思想,http://www.thepaper.cn,2017-08-20。,王佩瑜觉得很伤心,她渴望得到观众的叫好鼓励,她认为没有互动的表演是不中国、不完整的。经过王珮瑜的重新阐释,“京剧的叫好是一种文化”得到观众和读者的一致认可。“观戏叫好”到底是一种文化还是一种恶俗?的确需要我们换一种价值视角进行重新阐释。从民俗学的角度来说,理查德•鲍曼的“表演理论”就可以为此提供一个好的分析视角。
同样,脱离了传统社区生活的原有语境,被改编过的神话还能算神话吗?执着于本真性和原生态的神话学者一定会给出否定的回答。可是,神话主义却可以提供另一种分析视角,给出不一样的回答。祝鹏程通过网络“神话段子”的神话主义分析认为,神话段子是当代网民神话观的特殊表现形式,体现了网民自我表达的诉求。神话段子的创编经历了去语境化与再语境化的过程,重构了神话传统。神话段子既延续了经典神话的部分功能,也生产了新的功能;既使神话题材趋于雷同,又丰富了神话的表现形式①祝鹏程:《“神话段子”:互联网中的传统重构》,《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经过祝鹏程的阐释,神话段子得以从“恶搞”的标签中摆脱尴尬,在神话大家庭中找到一张座位。王志清通过对稷山蒲剧《农祖后稷》的考察,也对神话主义给出了正名:“神话主义在稷山地区的蒲剧《农祖后稷》中呈现出‘移位的神话母题’与‘凸显的地域名称’两个特质,嵌入性地思考蒲剧《农祖后稷》的知识生产过程,可以发现当地不同利益主体的‘组织叙述’活动促生了后稷神话的‘第二次生命’,《农祖后稷》营造了戏剧领域内后稷神话特有的艺术光晕,昭示了远古神话生生不息传承的生命力。”②王志清:《蒲剧展演情境中的“神话主义”——以山西稷山的<农祖后稷>为研究对象》,《贵州民族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
所谓“第二次生命”,是杨利慧借鉴芬兰民俗学家劳里•杭柯《民俗过程中的文化身份和研究伦理》而提出的概念。劳里将“民俗过程”划分为22个阶段,认为前12阶段是民俗的第一次生命,后10个阶段是民俗的第二次生命:“它意味着民俗从档案馆的深处或者其他某些隐蔽之地的死而复生。曾经从民俗过程中割裂出来并被搁置起来的材料又产生了影响力。它将在通常都远离其最初环境的一个新的语境和环境中被表演。”③劳里•杭柯著,户晓辉译:《民俗过程中的文化身份和研究伦理》,《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第4期。杨利慧将这一观念创造性地融入了对神话生命过程的认识,指出神话主义是神话的第二次生命:“神话被从其原本生存的社区日常生活的语境中挪移出去并被整合运用,为广大公共社会文化空间中的一般大众而展现。”④杨利慧等:《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以遗产旅游和电子媒介的考察为中心》,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2017年7月,第17页。
不过,与劳里•杭柯梳理“民俗过程”的单向进路不同,杨利慧认为神话第一、第二次生命的划分不应被视作一种单向的过程,在新语境中被挪用和重构的神话,也可能返回社区生活,成为社区内部表达自我认同、增进社区交流的表达性手段。
最重要的是,杨利慧课题团队的研究指出:神话主义并不是物质变革、技术革命的产物,也不是古老神话在当下时空中的简单再现,“相反,神话主义是由当下中国的社会形势、意识形态、文化策略以及市场经济等因素共同作用而产生的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一种以过去为资源的当下文化生产模式’”⑤杨利慧等:《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以遗产旅游和电子媒介的考察为中心》,国家社科基金结项成果,2017年7月,第17页。。也就是说,神话主义自始至终是以“当代文化”为视角、为目的、为旨归的研究。
一句话,神话主义是一个时代性的前沿学术概念,是国际对话语境中“中国民俗学派”的具体实践和有机组成。
编者按
神话主义是近两三年来国内民俗学和神话学界讨论的热点话题之一。今年7月3日,值此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结项之际,该概念的主要阐释者和倡导者杨利慧教授邀请部分在京学者,于北京师范大学召开了一个小型的“当代中国的神话主义”研讨会。会上大家就神话主义研究产生的学术史背景及其当代意义、未来的拓展潜力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等,展开了深入讨论。会后学者们又针对会议聚焦的一些重点问题,撰写了观点明确、彼此多有交锋的论文。这些论文从不同角度触及了相关研究的核心,对于丰富已有的神话主义研究、进一步推进民俗学和神话学学科实现“朝向当下”的转向具有重要意义。
K890
A
1008-7214(2017)05-0005-06
施爱东,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冯 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