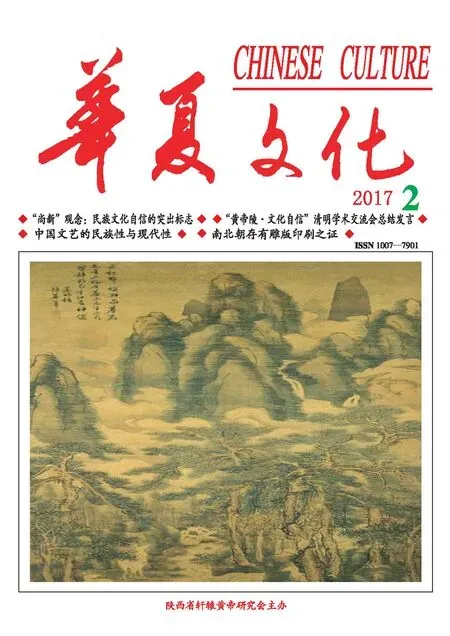宋人“道学”与“理学”名称考辨
2017-01-27□梁山
□ 梁 山
宋人“道学”与“理学”名称考辨
□ 梁 山
对于宋朝产生的儒学新形态,历来称谓繁多:道学、理学、宋学、新儒学等等。每一种称谓都反映着不同时代的人对于自身现状的独特认知。“道学”和“理学”是宋人自言之语,其中透露着他们对于自身学术与理想的认识;“道学”与“理学”概念之间的差异,也彰显着宋人思想与政治的真实处境;元明清三朝沿用“道学”与“理学”的概念,但其背后所表现出的思想差异更为复杂;用“宋学”来指称宋代学术,这是清人在考据之学的学术理路上做的概念划分;用新儒学来指称宋代儒学新形态,则是近代以来中国学人借鉴西人对于宋代儒学的新认识。每种称谓都有其独立发展的过程,在这期间,它们或许前后相继或许革新。本文旨在探究宋人使用“道学”与“理学”的历史情境以及隐藏在其后的宋人思想的变迁。
一、“道学”辨析
冯友兰先生很早就关注到,学界对于宋代“道学”与“理学”概念认知的混淆。他曾说:“在北宋时,‘道学’这个名称就有了,最晚在南宋已经流行。‘理学’这个名称出现比较晚,大概出现在南宋。自从清朝以来,道学和理学这两个名称是互相通用的。”(冯友兰:《通论道学》,《中国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但基于“名从主人”的原则,冯友兰认为还是要用“道学”这个名称来指称宋代儒学兴起的新思潮。王茂先生在《‘道学’、‘理学’称名考辨》一文中认为:“北宋的‘道学’与南宋不同,它要宽泛得多,其含意也不确定。以朱熹为代表的南宋道学,又与北宋诸家有同有异……‘理学’当是南宋人所谓‘性理之学’、‘义理之学’的简括。”姜广辉先生在《宋代道学定名缘起》一文中指出:“北宋儒者首先用‘道学’称其学并有文献为见证的,当推王开祖。但他的学术思想与二程所创立的‘道学’实有重大区别。”其文虽概述了北宋道学定名的过程,但并未分析最终定名“道学”的原因。以上所述文献,虽然指出了“道学”与“理学”的相同点与不同点,但并未从两宋三百年历史的整体视角来考察“道学”与“理学”演变的整个过程,也并未详细论述其背后所体现的思想变迁。
“道学”一名最早使用而为宋人所认可的是王开祖。他说:“孟子以来,道学不明,我欲述尧舜之道,论文武之治,杜淫邪之路,辟皇极之门。”(金沛霖主编《四库全书子部精要》)南宋学者陈谦在《儒志编附录》中说:“当庆历、皇祐间,宋兴未百年,经术道微,伊洛先生未作,景山独能研精覃思,发明经蕴,倡鸣‘道学’二字……后四十余年,伊洛儒宗始出。”庆历年间兴起的古文运动以“文以载道”著称,王开祖所言之“道学”当是指追求三代大道的学问。宋仁宗嘉祐年间,张载曾说:“嘉祐初,见洛阳程伯淳、正叔昆弟于京师,共语道学之要。”(《横渠先生行状》)此事乃吕大临在熙宁十年张载去世时,为其所写行状时的回忆,可见“道学”一词最迟在熙宁年间已为士人所共知。在程颐看来,其兄程颢乃得道统之真传:“既而门人朋友为文,以叙其事迹,述其道学者甚众。其所以推尊称美之意,人各用其所知,盖不同也。而以孟子之后,传圣人之道者,一人而已。”(《二程集·明道先生门人朋友叙述序》)并且早在熙宁年间,司马光就曾赞誉邵雍是“道学”权威:“某陕人,先生卫人,今同居洛,即乡人也。有如先生道学之尊,当以年德为贵,官职不足道也。”(《邵氏闻见录》卷十八)此时“道学”一词已成为当世之人所共识,虽在具体践履“道学”的内容上或有差异,但人们所认同的政治追求的目标就是三代之道。
然而,“道学”一词的指称并不仅仅限于儒家的三代之道。任渊在给陈师道《送王元均贬衡州兼寄元龙二首》中“石头路滑行能速”一句作注说:“师云,什么处去?对云,石头去。师云,石头路滑。石头谓南岳希迁和尚所居也。用衡山故事言其道学之胜。”此言“道学”自是针对佛教而言。任渊生活在两宋之际的乱世,可见当时“道学”是人所共称的,但关于这个“道”到底是属于佛还是儒,人们还有着不同的认识。编于南宋末年的《五灯会元》卷十九中也曾言:“时张无尽寓荆南,以道学自居,少见推许。师舣舟谒之,剧谈华严旨要。曰:‘华严现量境界,理事全真,初无假法,所以即一而万,了万为一,一复一,万复万,浩然莫穷。’”这里的“道学”很明显是指华严宗。查阅宋代的佛教史料,可以发现在佛教僧侣范围内,“道学”一词的使用一直存在。此外,不单单是儒释,“道学”也被用来指称道教之学。宋徽宗笃信道教,“建宝籙于京城,创神霄宫于天下,置道学,改寺院。”(《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南宋道士陈葆光所作《三洞群仙录》说:“盘古真人,天地之精。自号元始天王。《道学传》:黄帝,少典之子,姓公孙,号常鸿氏,一号归蔵氏。”此一“道学”便是道教之学的意涵。
纵观整个北宋的思想史,有两个很重要的特征:其一,儒释道三教融合很显著,虽然有儒家之“道学”、道家之“道学”和佛教之“道学”的区别,但是三家在各自的思想体系中都认同最高的价值是“道”,故而他们都争相自称为“道学”。其二,儒家内部思想多元。虽然儒者普遍认同只有讲明“道学”才能重建秩序和收拾人心,但他们对于“性与天道”的诠释进路与摄取重心,其实各有差异。以王安石为代表的变法派以“外王”之法求三代之“道”,然变法最终失败,北宋也亡于金人之手。宋室南渡后,曾经居住在洛阳的元祐党人及其门生也纷纷南迁。在国破家亡之际,他们痛定思痛,反思北宋灭亡的原因,由此也拉开了思想转型的历史过程。
二程的再传学生胡安国,靖康时居于南方。宋室南迁后,为中书舍人兼侍讲。他曾说:“本朝自嘉祐以来,西都有邵雍、程颢及弟颐,关中有张载。此四人者,皆道学德行名于当世。”(《河南程氏遗书》附录胡安国奏状)这里体现出胡安国对于道学传承的认识,此处的“道学”似乎有了固定的指称对象,道统叙事也似呼之欲出。胡安国之子,同为湖湘学派创始人的胡宏也曾说过:“道学须用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然后力行则不差耳。”(《胡宏集·与孙正儒书》)此处“道学”的具体内涵进一步明晰,他们二人皆传续二程之道。至于此道是否唯一,儒释道三家之道何以相类,胡安国之侄胡寅在《零陵郡学策问》中说:“问:道果一乎?而《易》有天道、地道、人道,于其中又有阴阳、刚柔、仁义之异名,而非一也。果二乎?孔子、孟子皆曰‘道一而已’。何也?果不异乎?……先圣后圣,其揆一也;三子不同,其趋一也。”
正是经由胡安国这样的程门弟子,二程之学在两宋之际逐渐由伊洛而播迁至南方。随着洛学的薪火相传,程门弟子在政坛上占据了重要地位,他们渐渐掌握了话语权。于是,在他们口里“道学”也逐渐有了专指的对象、具体的内涵,那就是二程先生及其学问。朱熹是二程的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他在《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之失其传而作也。”朱熹有意识地建立“道学”传承的谱系,子思是曾子之后,“道学”的传承人。作为二程老师的周敦颐,更是被朱熹抬高到孟子之后复传“道学”的人。他在《韶州州学濂溪先生祠记》中说:“宋兴,九疑之下、舂陵之墟,有濂溪先生者作,然后天理明而道学之传复续。”朱熹有意识地以二程为宗,加以筛检,作《伊洛渊源录》以叙道统。随着朱熹在学问上的日渐增进,他多次与当世学者论辩,更增加了门人弟子对于“道学”这一称谓的认同感,其对手也为区别自身与朱熹一派的差别,不再使用“道学”来指称自身。于是“道学”逐渐丧失其普遍意义的内涵,变成了程朱一系的专有。
综上所述,“道学”一词的内涵在北宋末至南宋初发生了改变,由泛指回到圣人之道的学问,变成了洛学的代名词。南宋史学家李心传于宁宗嘉泰二年写作《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其卷六载有《道学兴废》一文。他所认同的“道学”已经完全是二程到朱熹的学问了。宋理宗嘉熙年间,李心传还著有《道命录》一书。其中所提出的“道学”,已经是被理宗所推崇的程朱之学。因此“道学”在由“圣人之道”转变为由官方所钦定时,已经使得原本“道学”的范围愈发狭隘化了。
二、“理学”辨析
“理学”一词出现在南宋孝宗淳熙到光宗绍熙之际,公开使用于宁宗嘉定年间,流行于理宗之时,盛行于元、明、清,沿用至今。二程把超越的“理”作为宇宙自然结构的理解原则、政治运作的根本规范和道德伦理的人性本原。在穷理方法上,程颢“主静”,强调“正心诚意”;程颐“主敬”,强调“格物致知”。但随着思考讨论的深入,无论是在程门弟子内部,还是在当世其他儒者那里,关于“理”、“气”、“心”、“性”、“命”等范畴的思考都有了分歧。中国思想史上著名的“鹅湖之会”,便是一场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的争锋。查阅文献,已知最早提到“理学”一词的正是与朱熹有对立观点的陆九渊,其在《与李省幹》文中说:“秦、汉以来,学绝道丧,世不复有师……惟本朝理学,远过汉唐,始复有师道。”意在区别自己不同于朱熹对其当世学术的认识,并彰显自身的学问不是专指程朱一脉的学术。陆九渊认为“心”即是“理”,穷“理”只需“发明本心”,而朱熹却认为只有“格物”才能穷“理”。正是因为陆氏兄弟及其门人不认同以“道学”自居的朱熹,他们便以“理学”来指称自身。宁宗时发生的庆元党禁使得“道学”一词污名化,朱熹一派的士人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嘉定更化时,朱熹后学的很多人都得到了平反,但在他们中却渐渐出现用“理学”一名来表称程朱之学者。
嘉定十三年,楼观复为周敦颐议谥,议曰:“理学之说,隐然于唐虞三代之躬行,闿端于孔门洙泗之设教,推广于子思孟轲之讲明,驳杂于汉唐诸儒之论议,而复恢于我宋濂溪先生周公。”(李心传编《道命录》卷九)在这里“道学”被“理学”所替换。关于这一时期“理学”一名兴起的原因,真德秀的学生刘克庄的一段话或许能够带给我们启发。他在《季父易藳》一文中说:“本朝数学,有华山陈氏、河南邵氏。今邵氏之书虽存,通者极少。理学有伊川程氏、新安朱氏,举世诵习,众说几废。”刘克庄将邵雍之学称为“数学”,而将程朱之学称之为“理学”。由此可见,因程朱之学的关键在于讲求“天理”,故而称之为“理学”;邵雍之学的核心在于“象数”,故而称之为“数学”。学宗朱熹的黄震说:“本朝之治,远追唐虞,以理学为之根柢也。义理之学独盛本朝,以程先生为之宗师也。”黄震将“理学”定义为义理之学,并且认为二程才是“理学”的开创者。他也曾说:“臣尝窃谓理学至本朝而后大明,至先皇帝而后心契。”(《黄氏日钞》卷六十九)黄震接续道统叙述,“朱子发明程氏之言,理学至伊洛而大明,理学至考亭而愈著,一门伯仲,自相发明。”认为朱熹之学接续道统,称为“理学”。
至于宁宗时期,“理学”一名为何能够取代“道学”一名,成为程朱之学的新称谓。史料所限,尚未找到明确的说法,然大致有以下几个原因:其一,“道学”的称呼在北宋时就为儒士所普遍认同。从二程到朱熹,学术体系日渐成熟,要与别派作一区分。程朱之学,最为核心的在于体认“理”,故需名以副其实。其二,释老两家同样以“道学”自居,程朱之“道学”因此屡为反对者所攻击,这对于争夺儒家正统极为不利。其三,南宋庆元间屡禁“道学”,“道学”一名在政治上已经有所贬抑。
三、结语
纵观整个宋代,“道学”一词的内涵逐渐窄化。北宋时“道学”一词泛指以期达至大道的学问,其包括更为全面和广泛性的意涵,为广大的儒者、道士和释者所共享。两宋之际,随着旨在“外王”以求治道的失败,士人的思想普遍有了“内圣”的倾向。南宋初,随着程门弟子的大力弘扬,“道学”逐渐成了洛学的代称。后朱熹继起,“道学”专指由二程到朱子的学问。由宁宗时的“庆元党禁”到理宗时的“端平更化”,程朱之学由在野逐渐走向朝堂。“理学”最初由陆九渊提出,嘉定更化后,朱子后学渐采用“理学”一词来指称程朱以来的道统。元、明、清三朝,程朱之学大盛,论著浩如烟海。明清以来,士人以“理学”为一个具有学术蕴涵的概念,而“道学”更多出现于历史考订的叙述中。
(作者:陕西省西安市西北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所硕士研究生,邮编7100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