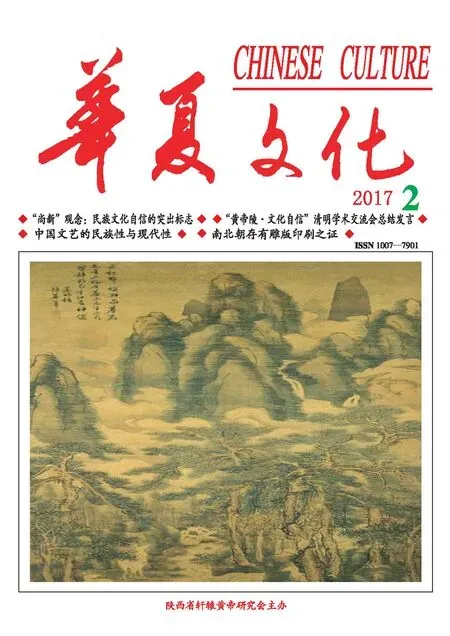清明节与寒食节的纠葛
2017-01-27梁丽红
□ 梁丽红
清明节与寒食节的纠葛
□ 梁丽红
国务院于2006年5月20日正式公布《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清明节便名列其中,其重要的文化价值可见一斑。但不管是与人交谈,还是课堂教学,我发现为数不少的人以今天的民俗为准,认定清明节就是寒食节,甚至把二者的来历都当成是一样的,谬之甚远。
一、 清明与寒食的起源
清明,夏历二十四节气之一,其由来已久,《逸周书·时训》就有记载:“春分之日玄鸟至……清明之日萍始生……。”一般在农历三月初一前后(公历4月4-6日),《历书》云:“春分后十五日,斗指丁,为清明,时万物皆洁齐而清明,盖时当气清景明,万物皆显,因此得名。”《岁时百问》亦云:“万物生长此时,皆清洁而明净,故谓之清明。”据上可知,“清明”一名源起于物候变化,是对自然界景致贴切的描绘。也有学者认为“清明”源于“清明风”,《国语》中记载,一年中共有“八风”,东南风叫清明风,属巽,即“阳气上升,万物齐巽”(雨竹《漫话清明节与寒食节》,《神州》2012年第10期)。不论哪种说法,我们都有理由相信清明初始仅仅是一个农业节气,用于区分时序,指导农事,与节日毫不相干。今天所流行的许多谚语:“清明前后,种瓜种豆”、“清明忙种麦,谷雨种大田”等亦可资佐证。
寒食,顾名思义,吃冷食,又称为“禁烟节”。关于寒食节的起源目前尚无定论,主要有以下五种说法:周代禁火说、古代改火说、纪念介子推说、山戎习俗说、求雨说,后两种说法立论薄弱,支持者少;前三种说法争论激烈,支持者众。细细梳理现有论述,可以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主张周代禁火说与古代改火说的多为历史学家;主张纪念介子推说的多为民俗学家。这主要是由于二者的研究方法不同,历史学家用史料说话,理性阐述,而民俗学家则从民众的情感出发,感性解读。面对学术界炽热的争论到底该何去何从?
查阅史料可知,关于介子推的记载最早见于《左传》僖公廿四年,但云“遂隐而死”,并非焚死。此后的《吕氏春秋·介立》、《史记·晋世家》也未见焚死的记载。《庄子·盗跖》中首次出现了“抱木而燔死”的说法,到了西汉时期,刘向的《新序·节士》详细地描绘了介子推被焚死的过程,之后此说不断被延续和丰富。据此,裘锡圭先生说:“这显然是为了解释寒食的起源而编造出来的。”确实,从关于介子推记载的演变可以看出,其故事并非完全真实的,而是层累地造成的,但能否因此就否认寒食的起源与介子推故事的密切关系呢?答案是否定的。正如七夕节的起源一样,不能因为否认牛郎织女故事的真实性,就否认七夕节起源于此。一般说来,节日产生的途径有两种:一种是自上而下的,通过政令规定某月某日是某某节日;一种是自下而上的,由部分民众自发组织产生,后蔓延至更广阔的地域,最终得到朝廷或政府的认可。查阅史料可知,周举、曹操、石勒、孝文帝等统治者均先后禁断过寒食,故可推测寒食节当属于自下而上兴起的,故而才会一再被朝廷禁止。作为民众自发组织产生的节日,感性自然多于理性,普通民众决不会去查阅史料辨别介子推的故事是真是假,只会依据个人喜好进行传播,甚至加入一些个人的意识。对此,张勃说:“介子推传说,作为民众对于社会过程的阐释和解读,是民众主体在其心理作用下,在一定的历史社会背景之中进行的,是在集体无意识和个体有意识的互动中加工和创作的结果。与此同时,它的传承和播布也是一个或多个时代、区域、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不断筛选优化的结果,其中融汇了一个地域或民族共同的心理素质、审美意识、道德观念和政治理想。”(张勃《寒食节起源新论》,《西北民族研究》2004年第3期)民众创造一种方式对一个符合自己价值观的英雄进行纪念是极有可能的。另,据史料记载,早期寒食之地基本局限于以太原郡为中心的并州地区,而介子推是晋国人,传说其被焚死在介休,二者空间上吻合。如果是因为改火或者禁火而寒食,为何关于寒食的早期记载未见于其他地区?这难以讲通。再次,关于介子推的传说成熟于西汉,而现存关于寒食的最早记载也出现于西汉。桓谭《新论·离事》记载:“太原郡民,以隆冬不火食五日,虽有疾病缓急,犹不敢犯,为介子推故也。”二者时间上也契合。综上所述,寒食节的起源必与纪念介子推有关,史书记载具体日期的不同及时间长短的差异只能说明寒食节形成的初期还不具稳定性,时常发生变动。
二、 清明与寒食的融合
一个是节气,用于区分时序,指导农事;一个是节日,用于纪念先贤,表达哀思,它们是如何相互融合,以至于今人极易将其混为一谈的呢?据杨琳先生考证,唐朝以前清明基本还仅仅是作为节气存在的,“没有形成节日的规模和气氛,没有形成全民遵从的礼俗和持续不断的传统,因而还不能称为节日。”(杨琳《清明节考源》,《寻根》1996年第2期)而寒食自西汉时期出现伊始,也仅局限于以太原郡为中心的并州地区,其典型的民俗事象便是禁烟、吃冷食,抑或在某些地区还有祭祀介子推的习俗,《后汉书·周举传》记载“乃作吊书以置子推之庙”。随着魏晋南北朝时期人口的大迁徙,寒食节开始得到广泛的传播,祭祀介子推慢慢演变为祭祀先人,至唐朝时期,唐玄宗的一道圣旨将寒食上坟祭祖定为“恒式”。《通典》卷五十二记载:“开元二十年四月,制曰:‘寒食上墓,礼经无文,近代相传,浸以成俗,士庶有不合庙享,何以用展孝思?宜许上墓同拜扫。礼于茔南门外,奠祭馔讫,泣辞。食余馔任于他处,不得作乐。仍编入五礼,永为恒式。’”甚至还为此全国放假,《唐会要》卷八十二记载:“二十四年二月十一日敕:‘寒食清明,四日为假’。至大历十三年二月十五日敕:‘自今已后,寒食通清明休假五日’。至贞元六年三月九日敕:‘寒食清明,宜准元日节,前后各给三日。’”这一举动更推动了寒食祭祖的扩大化,于是乎,到了寒食人人上坟,家家祭祖,蔚成风气。但由于在禁烟的寒食节上坟祭祖,无法焚烧纸钱,不少人担心“三日无火烧纸钱,纸钱那得到黄泉?”(王建《寒食行》)于是,民众越来越倾向于在可以用火且与寒食时间相近的清明上坟祭祖,焚烧纸钱,清明便与寒食有了最初的交融。唐诗中常见对寒食民俗事象的描述,如“寒食家家出古城,老人看屋少年行”、“丘墟郭门外,寒食谁家哭?”虽也有称清明的,如“寂寞清明日,萧条司马家”,但此时寒食的称谓还处于主导地位,“到后世,禁火寒食的习俗因纪念对象与人们的现实生活及思想情感关系甚浅而日渐淡漠,清明祭祖则因符合民情物望而喧宾夺主,延续至今。”(杨琳《清明节考源》,《寻根》1996年第2期)寒食节将扫墓、祭祖等节日习俗让渡给清明后,又随着禁烟、吃冷食等陋俗的淡化,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而清明则从农时节气蜕变为一个肃穆的节日。另外,清明出游踏青的习俗则是继承了上巳节的传统,因此,清明具有双重性。
综上,清明本为一个农业节气,由于时间与寒食节相近,到唐朝时开始逐渐侵占寒食节的扫墓、饮食等节日习俗,后来随着寒食节的式微,清明一跃成为一个重要的节日。寒食节则起源于介子推的传说,早期主要在并州地区流行,后辐射至更远的地区,其主要习俗是禁烟、吃冷食,至唐朝时才增加了上坟祭祖的习俗,但此习俗不久便被清明侵占,至宋代以后,随着禁烟习俗的淡化,寒食节也慢慢被清明节取代,故而今人多只知清明,而不知寒食。历史是动态的,在绵延的历史长河中,不论政治、经济,还是文化、习俗都不是一成不变的,今天我们所看到的、所实践的,都是其不断演变的结果。
(作者:广东省广州市华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邮编510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