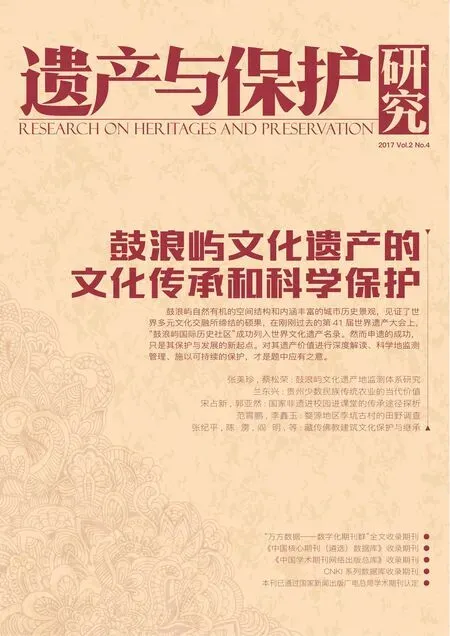山西东汾阳村赵盾故里忠义文化调查与探析
2017-01-27孙英芳毕啸南
孙英芳,毕啸南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北京 100875)
山西东汾阳村赵盾故里忠义文化调查与探析
孙英芳,毕啸南
(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北京 100875)
社会转型期文化习俗与生活方式的嬗变与重构系列专题(Ⅳ)
山西东汾阳村一带长期以来流传“赵氏孤儿”传说和赵盾故里故事,并伴随着祭祖、庙会、戏剧演出等民俗活动,形成了极具地方特色的忠义文化传统,深刻地影响着当地的村际关系和村落民风。这种忠义文化传统的传承,有其内在和外在因素的影响,在当代重建过程中,依托历史遗迹,地方知识分子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同时需要当地村民和地方政府的共同努力。
赵盾故里和赵氏孤儿传说;忠义;文化传统;重建
山西省襄汾县赵康镇东汾阳村一带在史前尧舜禹时期是政治中心区域,深受夏文化影响。春秋时期晋国曾一度在距离东汾阳村2 km外的赵康镇晋城村定都近百年,东汾阳是紧邻都城的政治中心区域,也是晋国颇有势力的以赵盾为代表的赵氏家族所在地,至今赵氏后人仍居住在这里。为了解东汾阳村落经过长期历史发展形成的忠义文化传统,2016年8月29日至9月2日,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萧放教授带领调查小组,以博士生孙英芳、硕士生廖珮帆为小组成员,对东汾阳村展开了调查。
1 东汾阳村概况
东汾阳村在山西省襄汾县城西南20 km处,离汾城镇大约3 km,隶属于赵康镇。村子现有100多户居民,823人,以赵姓为主,约占全村人口的90%,所以东汾阳可以看作赵姓的单姓村落。村子中间一条公路,是襄汾至新绛、侯马的重要交通线。东汾阳一带自然条件良好,土地肥沃,适合谷子、玉米等农作物生长,长期以来,村民在生计方式上以农耕为主。明清时期晋商活跃,东汾阳村也有人在外经商,现在仍有不少村民在外经商或打工。整体来看,东汾阳村落经济状况较好,村民生活较为富裕。
东汾阳也是一个家族性的村落,赵姓村民在东汾阳村同属一个家族。村落历史悠久,春秋时期,晋国曾一度定都赵康镇晋城村,称故绛,也称古晋城。早在1965年,“赵康古城遗址”就被公布为山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今尚存古绛都遗址。晋城村距离东汾阳大约2 km,所以东汾阳是晋国都城附近的重要地方,处于春秋时代晋国政治核心区域。东汾阳北有习礼村,据说是当年大臣、使者觐见晋国国君前学习礼仪的地方。而晋国显赫的赵氏家族就住在今天东汾阳村附近,并在这里繁衍发展下来,所以东汾阳是一个赵姓家族世代居住的家族性村落。赵氏家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由于人口繁衍增多,不断向四周扩张,在东汾阳周围形成不少与赵氏家族有关的村落,如赵康村、赵豹村、赵雄村、大赵村、小赵村、南赵村、北赵村,虽然现在这些村落已经发展为杂姓村,但赵姓村民依然占据很大比例。调查中发现,东汾阳村民对赵氏历史较为了解,对赵氏祖先的显赫充满了自豪感,家族的归属意识明确。
2 东汾阳村落忠义文化传统的民间传承与发展现状
东汾阳村文化最具有鲜明特色的是家族文化中的忠义文化传统。东汾阳一带流传赵盾故事和赵氏孤儿传说,但故事和传说的核心并不是宣传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因果报应思想,而是赞扬赵盾对国家的忠诚和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人的忠义精神。这种忠义文化的传承在当代东汾阳村有以下几种明显的表现形态。
2.1 故事讲述
“赵氏孤儿”的传说是东汾阳一带妇孺皆知的故事,讲的是春秋时期晋国程婴、公孙杵臼、韩厥等人为保护赵氏孤儿与屠岸贾斗争的故事。这个故事在东汾阳一带早已流传久远,究竟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已经很难考证。访谈中,村民都说是听老辈人讲的,因为是祖先的故事,所以就代代流传下来了。这个今天被我们称之为“传说”的故事,在东汾阳村民的心里却是真真切切的家族历史,是他们对祖先的认知,对宗族历史上重大事件刻苦铭心的记忆。不仅在东汾阳,在东汾阳一带其他赵氏后人的村落里,以及汾城、新绛的不少村子,人们对这个故事都深信不疑。在今天的汾城境内还有不少村落和赵氏孤儿的故事有关。比如在东汾阳西北大约7 km的程公村,原名程婴村,是程婴故里,至今有程公衣冠冢。程公村西有三公村,是公孙杵臼祠堂和墓地所在地。之所以叫“三公村”,相传公孙杵臼、程婴、韩厥3人为保孤儿议事于此。在三公村西不远处,在姑射山脚下有太常村,俗名“没娃沟”,据传当时屠岸贾怀疑赵氏孤儿藏于山沟人家,为了斩草除根,就将与赵氏孤儿年纪相近者尽杀掉,因此山沟成为“没娃沟”。后来百姓为了祈求太平常在,取名太常村。太常村外山上有“藏孤洞”和“安儿坡”,相传是当年程婴藏孤儿的地方。
不论这个故事是虚拟还是事实,在已过2 000多年后的现代化生活里,当地村民依然执着地认为他们讲述的是真实的祖先历史,他们朴实的方言中带着几分激动,让这个遥远王朝的政治事件增添了令人扼腕的慷慨和悲壮。在民间的口头传承里,保留了如此生动鲜活的历史记忆,真是让人感到震撼。在学术界,民间口头传承往往因其难以确切考证而遭到质疑,但谁又能证实这样的历史不是真实的呢?
从文献上看,目前所见最早记载春秋时期赵氏家族历史的是《春秋》一书。《春秋》关于赵氏家族主要有4条记载:①(宣公元年)“ 晋赵盾帅师救陈。冬,晋赵穿帅师侵崇[1]532。”②(宣公二年)“秋九月乙丑,晋赵盾弑其君夷皋[1]536。”③(宣公六年)“春,晋赵盾、卫孙免侵陈[1]558。”④(成公八年)“晋杀其大夫赵同、赵括[1]691。”虽然《春秋》的作者对赵氏家族有一定的批判态度,但也反映了赵氏家族在晋国的崛起和显要地位。春秋中后期是社会急剧变革的时期,随着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和经济的明显变化,诸侯国内部的一些贵族势力崛起,并开始向国君争夺权力,晋国的赵氏家族就是其中的一支。公元前607年,赵盾的族弟赵穿弑晋灵公后,赵盾派赵穿从周京迎来晋灵公的叔叔姬黑臀,让他即位,这就是成公。成公即位后赐赵氏为公族大夫,赵氏家族在晋国成为地位最高的公族。
《左传》中更加详细地记载了赵氏家族的历史。《左传》宣公二年、宣公八年、成公四年、成公五年、成公八年等都有关于赵氏家族的记载,主要内容有几个方面:一是关于赵氏“弑君”的事件。文公六年(公元前621),赵衰之子赵盾被立为晋国正卿。晋襄公卒,为立嗣问题赵盾与狐射姑争执,狐射姑被驱逐,可见赵氏势力之大[1]444-445。宣公二年(公元前607),晋灵公要杀赵盾,赵盾出逃,族弟赵穿在桃园杀了晋灵公。赵盾派赵穿到成周迎晋国公子姬黑臀并立为国君。晋成公即位,赐赵氏为公族大夫。赵盾去世后其子赵朔承父位,佐下军[1]539-543。二是关于赵氏家族灭亡和赵氏孤儿的记载。成公四年(公元前587),赵朔死后,其妻赵庄姬与赵婴(赵盾四弟) 私通受到同母兄弟赵同、赵括的反对,并于成公五年春(公元前586)把赵婴放逐到齐国[1]674-675。赵庄姬因此怨恨赵同、赵括,向晋景公诬陷赵同、赵括作乱,晋国讨伐赵同、赵括,赵族被消灭。赵武跟随庄姬寄住在晋景公宫里,后来韩厥对晋景公说起赵衰、赵盾、赵朔对国家的忠诚和功劳,于是立赵武为赵氏后祀,归还赵氏田地,赵氏家族复兴,后三家分晋,赵氏建国。可以看出,《左传》中记载的赵氏孤儿的故事和后来民间流传的赵氏孤儿故事并不一样。
到《史记》中,赵氏孤儿故事在司马迁笔下具有了戏剧性和传奇性。《史记·赵世家》中记载了奸臣屠岸贾带领诸将攻赵氏于下宫,灭其族,程婴、公孙杵臼大义救孤儿,赵武复兴赵族的故事[2]。《史记》的记载就是后来民间广为流传的赵氏孤儿故事文本。由于《史记》所载赵氏孤儿故事与《左传》中有较大出入,学界常常认为司马迁《史记》中所载故事的传说性大于历史真实性,即它不是真实的历史而是文学性虚构。《史记》的记载也成了后来各种赵氏孤儿文学作品的底本。元代纪君祥以《史记》记载为蓝本,创作杂剧《赵氏孤儿》,随着戏曲的反复演出和文学的传播功能,赵氏孤儿的故事在国内广为流传,并由法国传教士马约瑟翻译成《中国孤儿》,成为第一部传入欧洲的戏剧,远播海外。
从赵氏孤儿故事的文本看到,赵氏孤儿故事在漫长的历史中似乎发生了转变,但转变的不应该是历史事实本身,而是记录者对历史事件本身的认知、情感和态度。学界毫不犹豫地认为《史记》所载赵氏孤儿故事是虚构,并没有给予赵氏孤儿故事的真假成为历史疑案的机会。但田野调查中发现的口承历史与《史记》的记载却是契合的,让人不禁浮想联翩。东汾阳一带赵氏后人数量巨大,在慎终追远的中国文化传统里,人们对自己祖先持以最大的敬重,又怎会对自己祖先的历史进行集体的虚构创造?东汾阳赵氏族人关于祖先事件的记忆究竟从哪里来?如果故事是虚构的,那又如何变成东汾阳一带赵氏族人心目中的历史真实,并伴随着年复一年的民俗行为传递下来?司马迁的记载又从哪里来?作为公认的具有理性精神的史官,为什么要虚构一个历史故事传给后人?人们在相信《史记》中其他历史事件的记载时为什么又偏偏质疑这个事件的真实性?诸多的问题纠结于脑海之中虽难以解决,但田野带来的思考对于重新认识赵氏孤儿故事无疑是有意义的。
但无论如何,由于赵氏孤儿的故事它具有伦理道德的丰富内涵,包含着对社会人生的审视和判断,因而它不仅是东汾阳一带赵氏家族的故事,它的原型特征也表现了民族早期记忆和集体意识,因而也是中华民族整个族群的文化记忆。赵氏孤儿悲壮故事的背后,显示着深沉而执着的文化信仰,那就是忠义的精神。这种不寻常的动人的力量,能够引起整个中华民族族群的共同的情绪反应,因而使它广为流传,成了久传不衰的经典故事。
2.2 民俗活动
赵盾的故事和赵氏孤儿的传说作为东汾阳人的祖先记忆,在今天他们的生活中依然影响深刻,在民俗活动中表现突出。
(1)祭祖和庙会。东汾阳村和赵雄村在每年清明节时会在赵盾墓地举行祭祖活动。据当地风俗,清明上坟祭祖多在清明前三天内或清明节当天。祭祖时,东汾阳村和赵雄村的赵姓村民联合起来一起上坟,在上午八点左右,带上酒、菜(4个凉菜)、馒头、纸钱、鞭炮等祭品,到西汾阳村的赵盾墓地上进行集体祭奠。祭奠中在坟前摆上祭品,众族人按行辈排列,上香,磕头、放鞭炮、烧纸钱。这样的祭祖活动流传了多少年,村民大都说不清楚,他们只说是祖上留下来的,年年如此。此外,在每年的农历二月十五,在赵盾墓地和赵大夫庙所在的西汾阳村会举行赵大夫庙会,这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庙会,解放前通常由东汾阳村、西汾阳村、赵雄村等几个村子联合举办。近十几年来,东汾阳村、西汾阳村、赵雄村都各自举办庙会,但均与赵大夫庙会有密切关系。东汾阳村的庙会在每年阴历二月十二举行,庙会举办前会举行祭祖仪式,农历二月十二当天早晨要去赵盾墓地进行祭祀,祭祀礼仪如清明一般。中午12点以前,也要在村中赵大夫故里碑刻或赵大夫塑像前举行祭奠仪式,然后方才开戏。东汾阳庙会上要唱戏,其中重要的一场戏是《赵氏孤儿》。庙会一般举办3天,虽然现代社会中它已是热闹的商品贸易性质的庙会,但这个庙会却是因为赵盾祭祀延续下来的。
(2)蒲剧《赵氏孤儿》。山西戏曲源远流长,元明清时期极为兴盛,尤其是蒲剧,在晋南临汾一带很流行。这是个十分古老的剧种,在数百年前的山西晋南地区已经流行开来,唱腔时而婉转,如泣如诉,时而慷慨激扬,撼动人心,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在东汾阳一带,蒲剧是最受民众欢迎的剧种,岁时节日的庙会中常有蒲剧演出,村民在重要的人生仪礼场合也会请蒲剧班子来唱戏。而蒲剧中最为民众熟悉的剧目是《赵氏孤儿》,演述的就是赵氏孤儿的故事。在庙会和当地人婚丧嫁娶的人生仪礼活动中,凡是演戏的,《赵氏孤儿》作为经典剧目,也是出现频率最高的。比如东汾阳村至今有“过36岁”的民俗活动,即每年村里年龄到36岁的男子会联合起来,共同捐资为村里挂红灯笼、办庙会唱戏。为了组织好每年的这个活动,村里36岁的男子会选其中几个人作为理事,共同协商负责相关各种事宜,通过这样的活动,既增进了村民之间的融洽关系,增强村民的集体归属感,也让村里同龄人之间多了联系和交往,增强了他们对村里事务的责任意识。在每年“过36岁”的唱戏活动中,《赵氏孤儿》都是东汾阳必选的剧目。就在这年复一年的听戏中,一遍遍讲述着那个遥远的历史故事,村民以一种复杂难以言说的情感来回溯宗族灭亡的沉痛记忆,忠诚、悲壮、仇恨、志向交织在一起。这是他们对祖先的记忆,也是对自我的认知,在脑海中对忠诚大义的反复强调和巩固,从而唤起对家族这种文化精神不断传承的历史责任感。民众朴实的语言中没有宏大的词汇,但千百年来却默默地执着地记忆这个故事,正是这种精神,让忠义的文化传统延续下来。
2.3 村际关系
在东汾阳村调查,发现东汾阳村和周围村落的村际关系具有鲜明的地方历史文化特点。如前面村落概述中所言,东汾阳村是赵姓的单姓家族村落,东汾阳周围的赵雄、赵豹、赵康、大赵、小赵、南赵、北赵都曾是与赵氏有关的家族性村落,这些村子的赵姓村民都尊奉以赵盾为代表的赵氏祖先,有着几乎一样的人生仪礼、岁时节日活动和日常生活习俗。调查中东汾阳村赵根管老人讲到一个有趣的细节,说赵姓村落过去不养狗,原因是他们的祖先赵盾曾被恶狗攻击过。这个故事在《左传》中有详细记载,晋灵公为杀赵盾,养獒攻击赵盾,幸亏武士提弥明拼了性命保护赵盾,使其得以逃脱。东汾阳一带有个戏叫《狗咬赵盾》,演述的就是这个故事。由于他们具有共同的祖先信仰和家族认同,这几个赵姓村落的村际关系长期以来比较和谐,村际之间通婚现象很多,因此姻亲关系普遍。在经济、文化方面交往也频繁,因此赵姓村落之间联系较多。在访谈中,村民也反映这几个村落熟人多,人际关系和谐,矛盾问题较少。所以,当地赵姓村落虽然不止一个,但由于其文化上的相近性,它们实质上形成了一个文化共同体,依托着共同的家族历史和祖先信仰,形成了超越了当下行政村落划分的文化联村组织。
除了赵姓村落,东汾阳村与西边1 km左右的西汾阳村以及隶属汾城镇的程公村、三公村、太常村、习礼村、尉村、西中黄村、北中黄村等的交往都比较多,村际关系较为和谐。这些村落都是赵盾故事和赵氏孤儿传说流传的中心区域。比如,西汾阳村当地人叫做“坟茔”,因为那里是赵盾墓所在地。程公村据说也曾是单姓家族村落,村民为程婴后人,近代以来的人口流动,使目前程公村的程姓村民已经很少。据赵根管老人讲,程婴死后,赵氏家族为了感激程婴的忠义,把他安葬在赵盾墓旁,至今在赵盾墓的西边能见到程婴墓。赵氏家族在每次上坟祭奠祖先赵盾时候,都要祭奠程婴。程公村程氏后人为了祭奠方便,就在村南为程婴修建了衣冠冢,可以就近祭祀。(关于程婴墓,当地有不同的说法,此为之一。)总之,围绕着赵盾故事和赵氏孤儿传说,相关村落之间的关系在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就格外紧密些。
有意思的是,与此恰恰相反,东汾阳村与永固村的关系就不太好。当地人说,永固村是屠岸贾的家族所在地。屠岸贾灭了赵氏家族,和赵氏埋下了深仇大恨。后来赵氏复仇,也灭了屠岸贾家族,屠家人为了求生,纷纷改作他姓,今天永固村的原姓为屠岸贾后人。有了这样的历史关系,东汾阳一带的赵氏家族与永固村便几乎不来往,调查组在访谈中听东汾阳村民就说,很久以前老祖先留下来的规矩,赵姓和永固的原姓是不能通婚的。访谈中发现,除了不联姻,赵姓和原姓之间的其他往来也很少,在东汾阳一带常演的蒲剧《赵氏孤儿》,在永固村是从来不演的。我们看到,一个2 000多年前的遥远历史事件,却鲜明地映射在当代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让人不得不感慨历史和文化传统对村际关系的深刻影响。人生不过百年,历史却能穿越尘埃,通过人们的口头记忆代代渗透,显示着无与伦比的张力。
2.4 历史遗迹
虽然东汾阳人对赵盾的故事和赵氏孤儿的传说深信不疑,但口传的历史和故事总是给外人虚幻的不真实感,只有依靠实物的历史,才更有真实的存在感。在东汾阳村,现存的一些历史遗迹给了东汾阳村民极大的自信,让他们更加理直气壮地坚信自己祖先的历史。调查中看到,目前东汾阳村现存的历史遗迹主要有以下几处。
(1)赵盾墓和赵氏坟冢。赵盾墓在东汾阳西南1 km的西汾阳村。在广阔的庄稼地里,一个高大的坟冢格外显眼,坟前有一个高大的石碑,为乾隆年间刻立,上写着“晋大夫赵宣子之墓”,字迹清晰遒劲,碑额雕刻精美。碑阴有文,因时间久远,字迹湮没不清。墓地的历史已经难以考证,东汾阳一带的村民说这个坟很久远了,世世代代都存在着,他们坚信这就是他们祖先赵盾的墓地。据《宋史》记载,宋仁宗时曾派人到绛,看到两墓,于是封侯立庙。如果宋代见到的两墓即今所见的墓地,那赵盾墓确实历史久远了。此外,在赵雄村有“下宫之难”中赵氏家族被杀的360口人的墓地,共有九冢,今存其半,其中一坟冢名“七星冢”,坟冢高大,上有7棵古柏。
(2)赵盾故里碑。赵盾故里碑今天安放在村里新建的“忠义文化广场”门口马路对面。上面建有小亭,亭下立着这块石碑。据东汾阳前村主任赵根管老人讲,这个碑有专家考证是唐代的,上面写着“晋上大夫赵宣子故里”,字体清晰。访谈中,赵根管老人讲述了此碑的坎坷经历,说此碑以前一直在村里安放着,就在今天碑刻的位置,文革“破四旧”时,有人要破坏此碑,赵根管老人和村里几个人商量,觉得这是老祖先的东西,破坏了太可惜,于是连夜用平板车把碑拉到村西的地里埋了起来,才免遭破坏。2003年赵祖鼎老人和赵根管老人要重新发掘村子历史文化,想起了这块碑,赶紧找村民把这块碑挖了出来,尚且完好,后来从县里申请了经费,在原址建亭安放此碑。
(3)赵盾故里城门。据东汾阳村委赵天明书记讲,东汾阳村在民国前为城堡式村落,分东城和西城,四周都有高大的城墙,四方都有城门出入。日本侵华时,对东汾阳村狂轰乱炸,村民房屋和城墙消失殆尽。今天能看到的唯一的城门是西城的东门,为清代所建,原为二层,上层已被炸毁,现在仅剩下残缺的下层。城门洞为青砖砌成,保存完好,行人尚可通行。城门上有石匾额,上写“赵宣子故里”。
此外,赵根管老人还翻出多年前拍摄的赵府旧照片,说赵盾故居原来在今天村西头,一直保留有旧宅院,不知何时始建,“破四旧”时候要拆毁这个宅院,赵根管老人请求拍个照片,于是留下了一张难得的照片,而赵府旧宅已经被拆毁,如今是一片平坦的庄稼地。
2.5 地方民风
调查组在东汾阳调查中感受到,忠义的文化传统在当代民众生活中依然存在着,它像是一股暗流潜移默化地渗入到村民一点一滴的生活里,融入当地人的血脉之中,最终幻化成一个个淳朴的笑容和一句句淡然且充满自豪感的简单语言,带着一种从历史而来的不漏声色的凛然之气,清晰却难以言表。访谈中,村民普遍认为,当地民风忠厚朴实,村里打架斗殴、不孝敬老人的现象很少,我们也发现确如村民所言。村委赵书记说,虽然近几年人们经济生活水平提高了,人们对经济利益的追求愿望明显增强,但民风整体上仍然较好。忠义文化在民众生活里不需要惊天动地的大事和让世人瞩目的丰功伟绩,只要忠厚仁爱,持家和睦,有道德,守礼仪,又何尝不是忠义精神呢?
值得分析的是,忠义的家族文化传统能这样传承下来,形成具有地方性的民风特色,有其内在和外在的因素。首先,东汾阳一带村民作为赵盾后人,有着浓重的祖先崇拜观念。尤其是当自己的祖先有着辉煌显赫的历史功绩或受人推崇的文化精神时,后人通过祖先可以获得骄傲的力量和生存的自信,这种祖先崇拜的观念就更为强烈。春秋战国时期赵氏家族的显赫和赵盾、程婴等人的忠义精神让东汾阳村民感到骄傲,他们在一遍遍的故事讲述中流露出对祖先的敬仰和重视。此外,“赵氏孤儿”故事中包含的赵氏家族的毁灭和复兴作为家族历史发展中的重大事件,也值得赵氏族人代代传承,因为这种祖先观念,在家族的发展过程中具有现实的意义。通过不断的重复记忆,赵氏族人巩固了对祖先认知、强化了对祖先认同,具有凝聚宗族力量的作用。
其次是人们对忠义之善的普遍追求。忠义精神作为善的一种,是善在国家、政治层面上的典型表现。中国古代所推崇的忠义精神往往关联着重要的历史人物和一时代之国家政治,在忠义故事的悲壮背后,更多的是个人命运、家族荣辱和国家兴衰,由于对社会发展有较大影响,因此更加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推崇。善的定义和人们对善追求的内在人性根源作为复杂的哲学命题,虽然学界争议了几千年也未有明确的判断和共识,但从古到今千百年来人们对善普遍的追求和向往却是不争的历史事实。不论善是出于人的本能,如休谟所说,善是“使人发生慈爱情感的那种倾向,就使一个人在人生一切部门中都成为令人愉快的、有益于人的;并且给他那些本来可以有害于社会的所有其他性质以一个正确的方向”[3]。抑或是善是一种对他物的认知或自我认知,如康德所说的,善是令人喜欢的东西,“是被尊敬的、被赞成的东西,也就是在里面被他认可了一种客观价值的东西”[4]。善都被认为是好的,是对人有益的,它所包含的精神内涵是有利于社会发展的。
对忠义精神的追求和推崇是历代社会普遍的价值观念。在赵氏孤儿的故事中,围绕托孤、救孤、抚孤、复孤,将程婴、公孙杵臼、韩厥几位义士舍生取义、勇于献身的精神揭示得淋漓尽致。其中韩厥是为救孤而献身的第一位义士。当他发现赵孤后,没有报告屠岸贾,而是放走程婴和孤儿,引颈自刎。公孙杵臼故意背上背叛亲友的恶名,为救孤毫不犹豫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程婴是赵氏孤儿故事中最悲壮的一位英雄,他知恩图报,为报答赵盾父子的知遇之恩,临危救孤,并交出自己的亲生孩子换得孤儿平安,此后他忍辱负重,背负着卖孤求荣的骂名,含辛茹苦地抚养孤儿。他强颜欢笑侍奉屠岸贾,使屠岸贾收赵孤为义子,为赵孤最终的复仇和家族复兴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赵氏孤儿故事中所表现的这种知恩图报、舍生取义的气节人格,传达出“忠、孝、仁、义、礼、智、信”等道德观念或伦理精神,正适合广大民众对善的价值追求。
再次,政府的提倡强化了人们的忠义观念。如上所述,忠义精神是和人性内在特质相连的文化观念,对人和社会是有益的,在中国古代,“忠”主要表现为对国君的忠诚,它有利于形成国家政治的凝聚力,维护国君的权威和国家的安定团结,迎合了统治阶级的政治需要,因此也受到历代统治者的提倡。赵氏孤儿故事所表达的忠君爱国的民族情怀正契合了历代统治者所提倡和鼓励的忠义观念,因而受到统治者的褒扬和封赐。《宋史》记载,宋代曾对赵盾封侯立庙,并诏封程婴为成信侯,公孙杵臼为忠智侯,命绛州立庙,名“祚德”,岁时致祭。崇宁三年(公元1104),宋徽宗又封韩厥为义成侯,祚德庙遂称“祚德三侯庙”。宋高宗绍兴十六年(公元1146),又加封程婴为忠节成信侯,公孙杵臼为通勇忠智侯,韩厥为忠定义成侯,并于绍兴二十二年(公元1152)在杭州建祚德庙。宋理宗淳祐二年(公元1242)又封程婴为忠济王,公孙杵臼为忠祐王,韩厥为忠利王,三侯升为王爵,以表其忠节[5]。统治者的提倡,给了普通民众极大的信仰力量,让这种精神成为整个社会广泛的价值追求。这样,统治者即使出于功利性目的来提倡忠义精神,也与民众普遍的人性追求形成契合,因而使崇尚忠义精神成为社会普遍的共识,成为支配人们行为的准则和评判人们德行的标准。
3 赵盾故里忠义文化精神的当代重建
3.1 忠义文化的中断、消解与当代恢复
以“赵氏孤儿”故事为典型代表的忠义文化精神,在东汾阳一带通过故事讲述、祖先祭祀、民间信仰等种种形式历经千年不断传承,但到近五六十年的一段时间里也受到了沉重打击,甚至一度中断。调查组在调查中发现,东汾阳村原来保存的大量古建、遗物,包括民居、城墙、祠堂、寺庙、家谱、碑刻等,几乎都是在40—70年代被毁坏的,原先的很多民俗传统也是在这段时间内消失的。发生这样剧烈的文化变迁有两种主要原因:一是人为的强制干预;二是社会变迁带来文化的自然消解和增长。在20世纪40—70年代,东汾阳一带忠义文化的中断主要是由于人为的强制干预。调查组访谈东汾阳村民得知,在村子中间原有赵氏祠堂,为四合院建筑,有高大的门楼,主要祭祀赵氏祖先赵盾,过去赵氏在每年二月十二、清明节、新年时都要去祠堂进行祭祀活动,大跃进时期,祠堂成了生产队库房。后来祠堂被拆,1968年又新盖了库房。新中国成立后,东汾阳祭祖活动一度停止,后来到七八十年代渐渐恢复,但参与活动的赵氏后人较少,已经不再是赵氏集体举行大规模祭祀了。受到政治的影响,东汾阳一带与赵氏祖先祭祀相关的不少民俗活动也渐渐淡化,在民众日常生活中大量消失。除了祠堂外,村中原来还有不少庙宇,如赵盾庙(当地人称“大庙”,主祭赵盾)、关帝庙、菩萨庙、三官庙、药王庙等,在抗日战争期间和“破四旧”中都被毁弃了。东汾阳原来藏有赵氏家谱,“文革”中烧掉,今已不存。
到20世纪80年以后,伴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和市场化等现代化力量的强大作用,中国村落社会发生了激烈而深刻的变化,传统村落社会的特点逐渐消解,村落文化传统也进入了解构和重建的阶段。这个过程,对于山西襄汾一带来说,虽然来得迟些,但调查中也听村民普遍反映,近些年农村社会变化很大,传统的文化活动在不断消失。另一方面,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国文化旅游热的兴起和山西政府对文化资源的逐渐重视,襄汾县地方政府也逐渐开始发掘地方文化资源。响应政府号召,赵康镇也开始梳理东汾阳一代的忠义文化故事。十几年来,东汾阳在村落忠义文化建设方面,有了一定的发展,比较突出的主要有两个方面。
3.1.1 地方知识分子的积极参与
2000年以后,在东汾阳一带进行赵盾故里历史考证和“赵氏孤儿”故事梳理过程中,有两位关键的地方知识分子:一位是赵祖鼎老人;一位是赵根管老人。两位老人都是东汾阳村的赵氏后人,从小耳濡目染,听了不少关于祖先的传说,对家乡文化耳熟能详。
赵祖鼎老人是汾西灌溉管理局退休干部,生在西安,祖籍在东汾阳村,小时候回老家听家人说祖先故事,很感兴趣,后来在山西水利干部学院学习,毕业后到汾西灌溉管理局、襄汾县农机局等单位上班,长期住在襄汾,1994年退休后,开始关注家乡文化。赵根管老人曾做东汾阳村干部48年,任村委会主任等职务,从2002年开始,赵祖鼎和时任村委会主任的赵根管一起致力于东汾阳赵盾故里文化的发掘整理,并为申报“赵氏孤儿”传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积极奔走。2002年,赵祖鼎和当年埋藏石碑的赵根管老人及村民一起,把石碑找到,并从县里申请经费,建亭重新立碑;赵祖鼎老人为了给“赵氏孤儿”传说找到历史依据,翻阅大量历史古籍和地方志文献,并与安徽程氏多次联系交往,找到《程氏家谱》,印证东汾阳为赵盾故里。赵根管老人在村里反复讲赵盾故事和赵氏孤儿传说,唤起村民因政治影响下文化中断而带来的模糊记忆。随着国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鼓励地方积极申报非遗项目,赵祖鼎和赵根管也为申报东汾阳一带“赵氏孤儿”传说非遗项目准备了大量材料,2009年被此传说被列入山西省非遗目录。在此过程中,襄汾县和赵康镇政府也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和支持,使得东汾阳赵盾故里故事和“赵氏孤儿”传说重新受到人们关注,“忠义文化”成为赵康镇的文化名片。
3.1.2 村落忠义文化景观的建设
近些年,东汾阳村在忠义文化精神的恢复和建设中,逐渐恢复和新建一些文化景观,如忠义文化广场、忠义亭、忠义文化墙、庙宇等。2010年,在县政府的财政支持下,东汾阳村在村小学原址上建设了“忠义文化广场”。忠义文化广场占地面积有500 m2,有大门和围墙,呈现院落形态。大门上有“忠义文化广场”几个大字,围墙内侧有关于“赵氏孤儿”故事的壁画,广场中心是赵盾的人物雕塑,旁边建有亭子和一些碑刻。忠义亭在忠义文化广场马路对面,亭上额题大字“一代忠良”,亭柱有对联“浩气弥乾坤晋国一根撑天柱,忠义贯日月华夏千秋系地维。”亭内安放“晋上大夫赵宣子故里”碑,亭后有照壁,上有赵祖鼎老人撰写的《治国安邦、彪炳千秋》之文来宣传东汾阳的忠义文化。在东汾阳后巷民居墙壁上,有规则地绘有几十幅忠义文化宣传画,具体内容是关于赵盾故事和赵氏孤儿传说的。在村里原三官庙之处,2000年新建三官小庙,庙内墙壁上有三官画像,画像下摆放桌案和香炉,以适应民众民俗生活的需要。
3.2 关于东汾阳赵盾故里忠义文化重建的思考
如上所述,调查小组调查中发现,东汾阳一带的忠义文化精神在民众的口头传承和日常生活中一直存在,但由于时代的变迁,政治的影响,这种文化精神或隐或显。在走过了20世纪40—70年代传统文化的低迷之后,近些年来优秀的忠义文化传统在东汾阳一带逐渐复兴。可以预测的是,由于这里的忠义文化传统具有良好的根基,在当代社会政府鼓励、经济支持、传统文化复兴的大背景下,东汾阳一带忠义文化的复兴势在必然。具体分析来说,这种传统文化复兴需要内在和外在的各种条件,但以下几个关键的因素格外重要。
3.2.1 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
文化传统的形成需要民众长期的社会生活实践,是一个民众集体漫长历史发展中经过无数次取舍后的文化选择。经历历史洗练之后这种文化选择,一定是有利于家族发展和国家稳定的,能够为世代民众提供精神支持。东汾阳一带的忠义文化传统,正是这样的一种文化选择,并通过世代故事讲述、祖先祭祀、民俗活动等种种社会实践来巩固、强化这样的文化选择,从而让这种文化传统和精神信仰成为人们遵循的生活信条,渗入到当地民众的血脉之中,构成一种地方文化基因。文化传统的强大力量在于它能渗透到民众心灵的深处和生活的方方面面,即使经历残酷打击,在短时期内会可能失落,但文化基因在,它就不会完全消失,它在人们的日常生活和精神风貌中依然能够体现出来,一旦有了适合的社会环境,它便又焕发生机、蓬勃发展。所以,一脉相承的文化传统是文化复兴的前提和基本条件,也是文化复兴中关键的核心要素。
3.2.2 当代人的努力
文化的发展离不开人的主观努力和行为实践。东汾阳一带忠义文化的复兴发展,有3类人都是必不可少的。首先是村民的忠义文化精神,伴随着祖先崇拜的忠义文化信仰,让东汾阳一带的赵氏族人走过了几千年,已成为赵氏族人集体的文化标志。调查中发现,当代的东汾阳村民虽然没有传统社会那么丰富的民俗活动,但对祖先的敬重、对忠义文化精神的推崇依然强烈。访谈中也了解到,近几年随着村民经济的宽裕、生活水平的提高,村民在日常生活中自发恢复了一些民俗活动。比如近些年村落挂灯笼的传统重新恢复,每到正月里生了孩子或新娶媳妇的人家都给祠堂里挂灯笼;2000年三官小庙建成以后,村民在做“36岁”活动中也要给小庙里和村中主要道路上挂灯笼。
在村落文化发展过程中,地方知识分子发挥着十分关键的作用,他们有较多的文化知识,和村外的联系较多,对国家政策、社会变化比较熟悉,他们能够密切关注国家的政策动向,积极争取政府的建设支持,积极寻求村落的文化发展。在近些年东汾阳忠义文化建设中,赵祖鼎老人和赵根管老人就是典型的代表。若没有他们的付出和努力,村落文化要为外界所了解,势必需要更长的时间。从他们身上可以看到文化信仰的力量。正是这些地方知识分子的努力,让地方政府更加重视当地文化,让外界逐渐了解当地文化,从而为村落文化的当代发展带来了机遇。
另外,在当代村落文化的发展中,地方政府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不仅是国家文化政策的贯彻者,也是村落文化发展中最强大的经济支撑者。当代村落的文化发展往往要得到地方政府的重视,并从地方政府部门申请建设经费,来推进村落文化的建设,因此,村落文化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政策和经济支持。访谈中我们得知,东汾阳忠义文化的复兴和当时任赵康镇党委书记的杨建庭有很大关系。他重视赵康镇文化建设,鼓励地方知识分子挖掘整理忠义文化,努力打造赵康镇忠义文化名牌,不仅让东汾阳一带的村民对自身世代流传的文化更加自信,也扩大了东汾阳一带的赵盾故里文化的影响,让更多人了解这里。后杨建庭做襄汾县宣传部部长后,继续紧抓文化建设,2013年组建襄汾县三晋文化研究会,又重组蒲剧团,鼓励戏曲演出,这些都有助于东汾阳一带忠义文化的传播。
3.2.3 文化空间或景观实物的建设
文化精神属于意识范畴,它本身无象无形,只有依托一定的物质存在才能够体现出来,因此在文化发展中,空间或景观实物的建设非常重要,尤其是在村落文化发展中,依靠口承的文化传统在传承方式上本身有其弱点,村民往往会依托文化空间或景观实物来强化历史记忆,如祠堂、墓地、庙宇等。这些空间和景观在村民生活和村落文化中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是地方文化精神的象征物,包含着能够唤起村民的历史记忆。因此在村落文化的发展建设中,文化空间和景观实物的建设是非常必要的。
4 结束语
短暂的东汾阳调查,给笔者以深切的感受,像是历史的厚重画卷,以鲜明的忠义主题在面前层层铺展开来。从夏文化到赵氏孤儿到关公信仰,那些可歌可泣的故事和惊天地、泣鬼神的作为经历了历史沉淀之后,隐藏在民众心灵深处,形塑成一种地方风气和民众性格,并默默化作民众日常生活中的一个个细节,从他们的一言一行、一颦一笑中流露出来。一个地方的文化传统不仅是历史和过去,也是现在和未来。在东汾阳,我们看到了这种一脉相承的忠义文化传统,它穿越历史,顽强地延续,对当代民众的社会生活依然影响深刻。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文化复兴和重建的今天,村民、地方知识分子和地方政府已经做了一定的工作,但要弘扬这种优秀的文化传统,还需要更多的努力。总之,东汾阳的文化传统、历史发展和当代建设为我们思考中国传统村落的文化发展和当代精神重建提供了一个典型的案例,值得我们进行深入的分析和研究。
[1]杜预.春秋经传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14:2150-2153.
[3]休谟.人性论[M].关文运,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147.
[4]康德.判断力批判[M].邓晓芒,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46
[5]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2560-2561.
The 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Loyalty and Righteousness Culture In the hometown of Zhao Dun
SUN Yingfang, BI Xiaonan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Social Institute,Beijing 100875,China)
The legend of "the Orphan of Chao" and the story of Zhao Dun has long been circulated in Dong Fenyang village area in Shanxi, China. Be accompanied by ancestor worship,temple fair, theatrical performance and other folk activities, the loyalty and righteousness culture here has formed a very local characteristics, and which for a long time, influenced the village relations and village customs in depth. This loyalty culture tradition inherits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internal and external factors. In the process of reconstruction, relying on historical sites, local intellectuals played a special role, also needs the joint efforts of the local villagers and local government.
hometown of Zhao Dun and the orphan of Zhao; loyalty and righteousness;culture tradition; reconstruction
G122
A
孙英芳(1981-),女,讲师,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历史民俗学。E- mail:sunyingfang2011@163.com.毕啸南(1988-),男,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传媒艺术、跨文化传播。E- mail:bixiaonanjn@126.com.
本文系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阶段性成果之一(2015MZD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