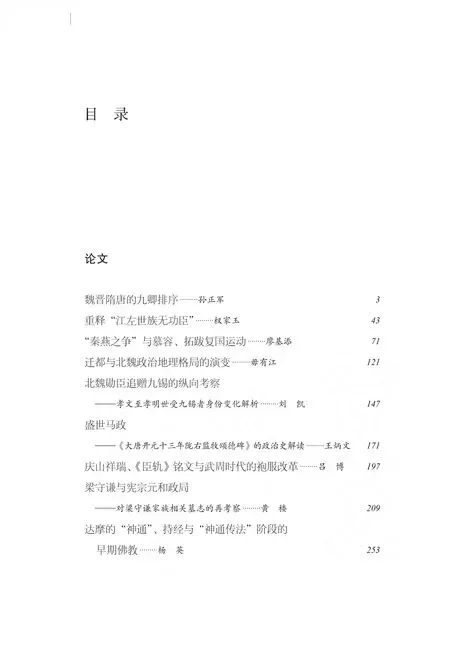唐宋变革与北美士族研究*——从麦希维克的中古社会阶层流动谈起
2017-01-27
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诞生伊始便肩负着实践与知识的双重使命,实践导向对知识构筑有强大的干扰力量,在知识领域获得客观性的意图受到了“测不准原理”的干预。[1]刘东:《中国研究领域的“测不准原理”》,载氏著:《我们的学术生态——被污染与被损害的》,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71—172 页。这一点在美国的士族研究领域也有相当的体现。士族研究相较于其他史学领域有着独特的魅力,面对相同的史料,不同的研究者会在自己的知识建构体系中将它们解读成不同的史学信息,这一点是它区别于传统考据史学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士族研究本来就存在目标模糊的特点,这种模糊感在差异化的中西学术话语催化下,更是显得暧昧含混。士族研究领域有很多重要问题长期以来就是中外学者争论不休的公案,比如士族的称谓,这是中国学者的用法,而美国学者用精英、乡绅、贵族。不同称呼背后包含着不同的性质界定。又如唐代士族门阀的社会地位如何、唐前期是否仍然是贵族社会、士族身份的变迁等,这些分歧与研究视角、方法的不同有关联,亦与中西学术话语的介入有千丝万缕的关系。
中国史研究对于海外汉学成果的引介一直以来都有很好的传统,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相比之下,对美国“中国学”的介绍又较为简单。[1]何寅、许光华:《国外汉学史》,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侯且岸:《当代美国的显学——美国现代中国学研究》,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张国刚:《德国的汉学研究》,中华书局1994年版;李学勤:《国际汉学著作提要》,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莫东寅:《汉学发达史》,上海书店1989年版;张静河:《瑞典汉学史》,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美国中国学的研究大多数集中在两宋以及明清时期,对魏晋南北朝、隋唐的研究就显得较为稀疏。[2]王晴佳:《美国的中国学研究评述》,《历史研究》1993年第6 期;高华:《三十年来美国“中国学”的研究趋向》,《社科信息》1988年第1 期;〔美〕杜尼尔:《美国八十年代的中国学研究》,王明泽译,《历史文献研究》第2 辑,第396—406 页;张国刚:《剑桥大学中国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3 期;张铠:《美国中国史研究专业队伍的形成及其史学成就》,《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7 期;张铠:《国际学术思潮与美国的中国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1995年第2 期;朱政惠:《美国学者对中国学研究的回顾与反思》,《江海学刊》2011年第3 期;〔美〕霍尔:《美国对中国史研究三十年回顾》,俞兴龙译,郭子畿校,载李范文主编:《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8—636 页。加之多年以前受语言的限制,这种距离感越发明显,我们对欧美唐史研究的认识长期以来都处于一种雾里看花的尴尬局面。这些年新兴翻译力量突起,一系列经典的汉学著作被引介至中国本土。[3]这些年海外汉学的翻译工作发展迅速,仅就中古士族研究而言,若干重要书籍在近几年相继翻译出版。〔美〕伊沛霞:《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范兆飞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美〕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范兆飞等译,中西书局2016年版;〔美〕谭凯:《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胡耀飞、谢宇荣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就中古士族研究成果而言,海外汉学的翻译过程非常缓慢,三十多年前,伊沛霞(Patricia Ebrey)、姜士彬(David Johnson)的著作就已经名满欧美,但直到近年其中译本才姗姗来迟。这些多年以前的旧著的价值与意义,在粗览之下很容易被当下的研究成果所遮蔽,但是经过抽丝剥茧的细绎,寻得惊喜亦非难事。由于伊沛霞、姜士彬等学者成果杰出,使我们的目光过多地聚集在他们身上,从而忽视了与之同时代的其他学者。因此,重绎与之同时的其他作品在这个问题上的得与失,还原美国士族研究在当时所遇到的困难与转折,给予学术史层面的价值与意义是有必要的。
《寡头社会抑或流动社会:早期中古中国大族研究》(Oligarchy or Social Mobility? A Study of the Great Clan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一文是麦希维克(Dušanka Dušana Miščević)于1992年申请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论文,该文提出了与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不同的学术观点。[1]Dušanka Dušana Miščević, Oligarchy or Social Mobility? A Study of the Great Clan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Ph.D.Columbia University, 1992.该文后发表于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ol.65, 1993。该文的博论可参见由University Microfilms International (UMI)所制作的影印本,博士论文近900 页,附录部分占全书篇幅的一半左右,《远东博物馆馆刊》对博论中的相关内容、表格有删削。本文在讨论时,以发表在《远东博物馆馆刊》上的版本为主,兼用博论,以期展现西方学者在这个问题上的探索过程。姜士彬认为中古社会是典型的寡头统治,士族表现了顽强的生命力,而麦希维克认为魏晋南北朝社会流动性很强,不存在所谓的寡头政治。本文亦欲借助该文,对20世纪末美国中国学研究进行重新审读与思考,梳理它们在士族领域的研究特点,重估它们在学术史上的地位,挖掘值得当下研究借鉴的智慧和经验。
一
一个历史研究议题的消失并不全是由于已经获得了妥善的回应与解决,而是新学术浪潮的席卷登陆。唐宋变革论在时下的境况便是如此,正如张广达先生在《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一文中所说那样:“今天,关于唐宋变革之后的中国是进入了近世还是依然停留在中世的意见分歧依然存在,但是,时过境迁,中外学者已经打不起精神,提不起兴致再做时代性质的争论。”[1]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载《唐研究》第11 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后载氏著:《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3 页。当下流行的新史学以及学术内卷化、边缘崛起、中心陷落的学术浪潮成为主流[2]参见张国刚:《二十世纪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历史研究》2001年第2 期;曹文柱、李传军:《二十世纪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历史研究》2002年第5 期;范兆飞:《中古地域集团学说的运用及流变——以关陇集团理论的影响为线索》,《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 期。,唐宋变革的或证明、或证伪、或修订工作早就难以博取学术关注。但是吊诡的是,时至今日,对于唐宋变革这个议题我们又不得不时常拿出来讨论。[3]仅简单罗列一下21世纪以来关于“唐宋变革”的研究,张其凡:《关于“唐宋变革期”学说的介绍与思考》,《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 期;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第2 期;李华瑞:《20世纪中日“唐宋变革”观研究述评》,《史学理论研究》2003年第4 期;葛金芳:《唐宋变革期研究》,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载氏著:《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第57—133 页;张国刚:《“唐宋变革”与中国历史分期问题》,《史学集刊》2006年第1 期;柳立言:《何谓“唐宋变革”》,《中华文史论丛》2006年第1 期;张国刚:《论唐宋变革的时代特征》,《江汉论坛》2006年第3 期;陆扬:《陆扬谈唐宋变革》,《东方早报》2016年5月29日。这背后暴露了我们现在所处的一种尴尬的困境:一方面我们已经疲于应对历史分期所产生的各种难题,对于与唐宋变革有关的各种论调显得麻木漠然;另一方面又提不出新的研究范式,在关涉理论构筑时又不得不加以重谈。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欧美学界对于唐宋变革这样一个理论框架的珍视,时至今日仍然保有相当的热情。张广达在《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中同样也说道:“实际上,在今天,海外研究唐宋元明清的学者很少不是以唐宋变革为预设而进行研究工作的。”[1]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载氏著:《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第61 页。19世纪初内藤湖南提出“唐宋变革”,并在日本国内引发大规模的学术研究讨论潮流,然而直至1954年,宫川尚志“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一文提出“内藤假说”,才把这一理论叙述模式带入美国。[2]Miyakawa Hisayuki, An Outline of the Naitō Hypothesis and Its Effects on Japanese Studies of China, Far Eastern Quarterly, Vol.14, No.4, 1995, pp.533-552.关于宫川尚志对美国史学界的影响,参见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载氏著:《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第108—109 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内藤学说开始在美国史学界泛滥开来。[3]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载氏著:《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第60 页。张广达等学者将美国史学界对日本唐宋变革的回应归功于宋史研究,以刘子健(James T.C.Liu)《宋代中国的变化:创新抑或翻新》、《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以及郝若贝(Robert M.Hartwell)《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社会转型》一系列著作的问世为代表。[4]张广达:《内藤湖南的唐宋变革说及其影响》,载氏著:《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第108 页。李贵:《中唐至北宋的典范选择与诗歌因革》,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1 页。James T.C.Liu, Peter J.Golas eds., Change in Sung China: Innovation or Renovation?Lexington, Mass.刘子健著作的中译本参见〔美〕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赵冬梅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 页。Robert M.Hartwell,Demographic, Political and Social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750-1550,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42(2), 1982, pp.365-442.郝若贝著作的中译本参见〔美〕郝若贝:《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转型》,易素梅等译,载〔美〕伊沛霞、姚平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75—246 页。必须承认,美国史学界对于唐宋变革系统的修订完成于研究宋史的郝若贝与韩明士之手,但是最初对于唐宋变革的试探性论证工作几乎是在唐史、宋史研究领域同时进行的。
最早讨论唐代统治阶层性质的作品当属杜希德(Denis Twitchett)于1973年在《唐代的概观》里所撰写的《从敦煌文书看唐代的统治阶层》一文。杜希德在文中介绍了该文的研究背景:“历史分期这类大问题,现在已被人视作某种信仰的申述,……我试图探究的,只是整体社会变动下一个环节——中国统治阶层的结构与成份的急剧变动。”不仅如此,他还承认对唐代统治阶层的探讨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明清社会流动研究的影响。[1]Denis Twitchett,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ang Ruling Class, Perspectives on the T’ang, ed.by Arthur F.Wright and Denis Twichett,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该文有两个中译本,〔美〕杜希德:《从敦煌文书看唐代统治阶级的构成》,叶妙娜译,《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 期。本文以何冠环译本为主,参见杜希德:《从敦煌文书看唐代统治阶层的成份》,何冠环译,载〔美〕芮沃寿等:《唐史论文选集》,陶晋生等译,第87、89 页。这两点概括了西方学者在探讨唐代社会阶层及其流动性问题时的两个基本出发点,一是受到了历史分期问题的影响,二是受到了社会流动理论的影响。姜士彬对于唐代统治阶层的探讨也正是要回应唐代的性质问题,正如他在《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引言中所写的那样:“在研究伊始,笔者就尝试验证或驳斥一个被广泛认同的观点:即中国中古时期的统治阶层是世袭贵族。”[2]〔美〕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第1 页。而对于与该书紧密相关的另外一篇论文《世家大族的没落——唐末宋初的赵郡李氏》,姜士彬也直言:“这篇论文对宋史学者影响甚大。正如我的兴趣曾经集中于中古统治阶层的本质一样,宋史学人也希望洞悉宋代统治阶层的性质。”[3]〔美〕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第2 页。南北朝领域讨论社会流动问题以葛涤风(Dennis Graffin)、霍姆格伦(Jennifer Holmgren)、麦希维克的研究为代表,他们认为南北朝并不存在能够世代占据上层官僚社会的阶层。[4]范兆飞:《北美士族研究传统的演变——以姜士彬和伊沛霞研究的异同为线索》,该文于2016年在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沙龙第53 期(2016年10月15日)、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2016年11月28日)进行过报告,发表于《文史哲》2017年第3 期。欧美汉学家与中国学者存在一个较为明显的差异,前者的研究广角相当开阔,横跨多个朝代,从汉延伸至唐,甚及明与清,而后者则聚焦于某个特定的历史时期进行周而复始的深耕细作。中国学者“对于前后历史时期通贯的整体把握能力不足,唐史学者与宋史学者各自为战、欠缺沟通”[1]邓小南、荣新江:《“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序”》,载《唐研究》第11 卷,第2 页。,了解这种研究习性,对于梳理学术史是非常必要的。欧美学者在宋史领域研究这些问题时,常常会将思路与结论向上延伸至唐、至魏晋南北朝,因而,他们研究魏晋隋唐的相关问题可以从宋史的延长线上加以捋顺。对于社会流动问题几乎在唐、宋、明清各个时段均有探讨,我们先来看看这个问题在两宋以及明清史领域的探讨。
杜希德讲社会流动对唐史研究的影响正是指何炳棣(Ping-Ti Ho)《明清社会史论》中对明清社会流动的探讨。[2]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62.中译本参见〔美〕何炳棣:《明清社会史论》,徐泓译,联经出版社2016年版。何炳棣的研究掀起了社会流动性的大争论,有学者将这一争论的论点分为三个派别:以潘光旦、费孝通、柯睿格(Edward Kracke)、何炳棣为代表的流动派,以韩明士(Robert P.Hymes)、郝若贝、艾尔曼(Benjamin A.Elman)为代表的非流动派,以贾志扬(John W.Chaffee)等为代表的中间派。[3]郑若玲:《〈清代朱卷集成〉的社会学研究价值——以社会流动的考察为例》,载《科举与科举文献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下)》,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版,第6—7 页。这样的划分无疑较为清晰地展现了各自的立场,但是由于缺乏学术史的梳理,没有将社会流动的研究热潮置于合适的学术史线索中,因此遮蔽了这个问题背后的史学目的与意义。关于社会流动的探讨非常之多,不能被简单地装在一个框架当中。从美国的宋史领域来看,他们最早开始对社会流动进行探讨。在“唐宋假说”引入美国之前,柯睿格、何炳棣就已经开始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他们的研究思路与从19世纪末社会分层理论中衍生而来的精英理论相关。[1]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柯睿格考察了宋代科举制与社会流动的关系,他以登科录为蓝本,计算了进士的上下流动,认为宋代的官僚社会具有很大的流动性。[2]Edward Kracke, Family Vs.Merit in Chines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under the Empire,Religion, Family and Individual in the Chinese Examination System,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X, No.2, 1947.但是对于宋代社会流动性的探讨却没有像魏晋隋唐史一样陷入反复争论的泥沼,这一点得益于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的区域发展理论在宋史研究领域的灵活应用。郝若贝在社会流动研究基础上对施坚雅经济空间理论的演绎帮助他构建了美国唐宋变革的新范式,他“突破了此理论只运用于地域经济研究的局限,而扩展到了社会与政治史领域。这也成为了郝若贝理论的起点。在此基础上,郝若贝提出了一个贯穿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唐宋变革论框架”[3]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施坚雅区域地方史研究及其对美国中国学的影响,参见陈君静:《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中国地方史研究》,《中国史研究动态》2003年第2 期。,用施坚雅的经济空间理论来解释中国不同区域发展的动力。[4]刘方:《唐宋变革与宋代审美文化转型》,学林出版社2009年版,第36 页。郝若贝对于区域地理的关注一开始也是注意区域的同一性,《十一世纪中国铁、钢市场、技术与商业发展》、《帝制中国的经济圈变动:中国北方的煤和钢,750—1350》这两个区域地理的著作便是这类思想的衍生品。但他坦言在受到施坚雅的启发后,他才开始将区域地理之间的关联与发展。Robert M.Hartwell, Markets, Technology, and the Structure of Enterprise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leventh-century Chinese Iron and Steel Industry,The 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Vol.26, 1996, pp.29-58; Robert M.Hartwell, A Cycle of Economic Change in Imperial China: Coal and Iron in Northeast China, 750-1350, 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10, 1967, pp.102-159.〔美〕郝若贝:《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转型》,载〔美〕伊沛霞、姚平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第175—246 页。郝若贝跳出了社会是否流动的怪圈,从社会流动入手,结合区域地方史的视角,打开了新的局面,提出了不同于日本唐宋变革论的新思路;1985年贾志扬《宋代科举》一书对于流动派与非流动派的观点进行了调和;1986年韩明士《官宦与绅士:两宋江西抚州的精英》的发表将这一理论框架全面加以阐释。[1]〔美〕郝若贝:《750—1550年间中国的人口、政治及社会转型》,载〔美〕伊沛霞、姚平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第175—246 页。John W.Chaffee, The Thorny Gates of Learning in Sung China: A Social History of Examinations,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中译本参见〔美〕贾志扬:《宋代科举》,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5年版。Robert P.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pp.34-48.之后美国宋史领域关于社会流动的探讨也就随之停止。这场争论以非流动派建立起全新的唐宋叙述模式而宣告结束。
唐宋变革论对于美国中国学最为直接的影响是将宋代视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历史时期,特别重视对于宋代科举与社会流动、精英与士绅的地方化及身份的转型的研究。[2]葛兆光:《思想史研究课堂讲录续编》,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2年版,第32页;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第25 页。日本的唐宋变革论传入美国后,唐史和宋史领域就向两个不同方向开进,唐史研究往往可以在宋史的延长线上加以考察,正如包弼德(Peter K.Bol)所说:“为了寻找北宋精英文化的来源,我上溯到唐代后期的历史,……当我开始理解唐代后期与北宋的文化创造如何与唐代门阀文化的消失联系在一起的时候,对于究竟是什么因素使新儒家运动与众不同,我也逐渐能理解了。”[3]〔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刘宁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 页。唐宋文化的差异需要从唐后期的门阀文化中寻找答案,唐宋士人由国家官僚精英如何向地方文人精英的转变也是在唐宋史的延长线上加以考虑的:“为什么作为世家大族的士在隋唐以前的那些王朝衰落之后能维系下来,却不能度过唐朝?为什么士在北宋早期,作为有学养的文官官僚这样的国家精英再度出现?为什么在有宋一代,士变成作为地方精英的文人。”[1]〔美〕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第35 页。从宋史研究领域展开的唐宋变革的论证修订是从士的身份转型的路径上取得成果的,与此同时,以姜士彬为代表的美国士族研究开始从讨论魏晋南北朝隋唐统治阶层的性质入手来回应唐宋变革,姜士彬认为唐代确实存在一个贵族阶层,他们长期以来把持着唐代的统治权力。考察中古时期统治阶层的性质成为这一时期研究的热点,以葛涤风、霍姆格伦为代表的学者提出了与姜士彬相反的意见。
与宋史领域对唐宋变革的回应不同,美国魏晋隋唐史研究领域对于这个问题的探讨从一开始便陷入了怪圈,他们反复在一个问题上绕圈子,做着重复性辩证,即魏晋南北朝隋唐统治阶层是否封闭,他们是否为贵族政治或者寡头政治,还是一个有着相对流动性的阶层。而新近出版谭凯(Nicolas Tackett)的《中古中国贵族的崩溃》一书也是在韩明士精英理论关照下所书写的佳作[2]王晶:《重绘中古士族的衰亡史——以The Destruction of the Medieval Chinese Aristocracy为中心》,《中华文史论丛》2015年第2 期。,宋史研究方法和理论对唐史的补给借用,才得以使美国在唐代士族研究方面打开新的局面。美国对唐宋变革论的修订完成于宋史研究者之手,但何以这一研究会在宋史方面开花结果,而非南北朝隋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领域社会流动理论的探讨陷入原地徘徊的原因究竟何在?
二
美国关于中古社会统治阶层性质的研究以姜士彬、麦希维克、葛涤风、霍姆格伦为代表。[1]范兆飞:《北美士族研究传统的演变——以姜士彬和伊沛霞研究的异同为线索》,《文史哲》2017年第3 期。麦希维克的著作虽然篇幅较长,但在书写论证方面留下了明显的程式化印记,每章的行文结构整齐一致,这使得读者即便面对庞大的阅读量也能理解与驾驭。在导言部分,作者对于西方学术界关于中古贵族制的研究情况进行了基本的概述与评价,并对自己的研究方法、思路以及史料进行了阐述。她认为西方学术话语对于中国史的研究是一种巨大的障碍,学者们对于中古中国的统治阶层这个特殊群体在理解认识上存在着差异,这导致了他们在研究过程中会使用不同的英语词汇来加以描摹。[2]这一点在《远东博物馆馆刊》中发表时被删除,此点可以参阅麦希维克博论的UMI 影印本,第8 页。艾伯华(Wolfram Eberhard)使用“gentry”一词来强调其与土地的紧密联系,以及在此基础上发展而来的教育与官宦,但是在论述“gentry”是如何进入贵族圈时,艾伯华并没有给出强有力的解释;伊沛霞用“aristocracy”以说明其身份的获得主要来自于声望(prestige)而非权力与财富;姜士彬则重视其社会身份地位,故而使用了“oligarchy”。[3]参见麦希维克博论的UMI 影印本,第8 页。而作者麦希维克更倾向于使用“中古大姓”(great medieval clans),她认为这些研究最主要的遗憾是没有将研究建立在某个具体的家族基础上,毛汉光忽视了晋以前的史料,姜士彬完全倚靠唐代的史料,并将结论回溯后应用于唐以前的社会。[4]Dušanka Dušana Miščević, Oligarchy or Social Mobility? A Study of the Great Clan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ol.65, 1993, p.11.作者还对书中所使用的材料进行了解释:她在美国、日本与中国台湾的图书馆搜集了已经出版或未出版的墓志1069 方,却并没有将它们应用在本书的研究工作中,拓跋时期的墓志太多以至于无法用于研究所有氏族,而东晋南朝的墓志又太少以至于可以忽视,《世说新语》类的笔记小说对于本书的研究帮助不大,故而作者以正史为其最主要的史料来源。[1]参见麦希维克博论的UMI 影印本,第12 页。
在第二章“早期中古大族”中,作者对《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上溯至汉代的世系表示了高度的怀疑,对正史史料中出现的人物进行了大规模的统计工作。她对由汉至隋在正史中出现的延续至少一个朝代或者多个朝代的氏族进行了分类列表,绘制了延续两朝、三朝、四朝、五朝氏族的数量,发现氏族数量随着时间的推移呈减弱趋势。比如由汉延续至三国的氏族有32 个,由三国至西晋的有43个,由刘宋至陈有8 个,由三国至南齐的氏族只有1 个。而能够延续五朝的氏族则非常稀少,从后汉延续到南齐的氏族数量为0,从西晋延续至陈的氏族有4 个,从后汉延续至东魏北齐的氏族只有3 个。第三章和第四章是全书篇幅最重的部分。作者所注目的问题是氏族能否通过获得中正官为本家族攫取官宦资源,为此她依三国至西魏北周的朝代更替顺序把中正官数量、来源,一品文官家族及其来源,一品武官家族及其来源,中正官与一品文武官兼有家族分别绘制图表,共56 幅。由此得出的结论是中正官在提升本家族官宦实力方面并无显著作用,而且那些同时拥有中正官与一品官的家族并不是来自于“旧族”(established clan),中正官在地方上的影响力并不能确保家族成员获得高位,地方影响力也难以转变为国家官僚权力。在第四章,作者对于三国至西魏北周时期获得贵族勋爵的氏族进行了统计,分列出他们的郡望、勋爵、品位,统计结果表明很少有氏族能够历经数朝之后仍然保有他们的贵族勋爵,南方的上层统治阶级总是被称为贵族,但是实际上真正拥有贵族勋爵数朝之久的只有极少数的几个北方氏族。第五章讨论了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皇后的来源,指出如果将皇后是否来自高门作为衡量社会流动的标准,那么魏、蜀、吴以及拓跋魏时期的社会流动性是非常大的,这个结论也与第三章、第四章的结论一致。从东汉至隋,有28 个高门大族产生了至少一个皇后,但是持续数朝仍然能将本族女性推为皇后的氏族却少之又少,琅琊王氏虽历经五朝都有皇后产生,但这只是少数,不能作为中古社会的典型形态。在第六章,作者对于每章的论点进行了总结,并对葛涤风做出回应,重申不应该把唐代的史学结论直接应用至魏晋南北朝。附录部分作者认为在运用《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来研究魏晋南北朝的氏族时需要特别注意,因此她以115 个氏族为中心绘制了海量图表,每个氏族均包含有一个世系图、一个官位表以及一个勋位表。[1]这一部分在发表时有删节,原文可参麦希维克博论的UMI 影印本,第505—899 页。
麦希维克认为中正与家族官位高低并无直接关联,旧官僚精英的中正数量与他们在朝中的高位呈负相关,拥有中正官的家族并不能借助这一优势提高本宗的高官数量,九品官人法在维系中古门阀制度中的地位和作用有可能被高估了。她的这一结论与现有的认知不同,乌廷玉的研究就表明:“在两晋南北朝三百余年间,各朝总共有中正官327 人,由士族门阀出身者255 人,占总数75.3%,可见当时选拔评定全国官员之权,基本上是由士族门阀掌握。”[2]乌廷玉:《两晋南北朝士族门阀的特征》,《史学集刊》1995年第1 期。从家族网络圈的角度来看,中正与地方其他家族可以结成社会乡里网络,网络关系使不同家族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密,网络内部成员相互提携亦可以维系社会地位。麦希维克只是注意到了中正与本家族之间的关系,而忽略了中古门阀大族之间互为依赖的网络圈的意义。诚然,中正官或许无法直接举荐本宗成员,但是与其他士族之间通过各种社会关系,比如婚姻、乡里、门生、故吏等形成交游圈却是中古士族间成长的基本生态网络,互为奥援之事亦非鲜见。关于乡里网络的研究,在欧美学者中似乎还未曾引起关注,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中国中古研究领域的一个新课题。
姜士彬认为中古政治权力由部分寡头所统治,他们长期以来占据着国家权力结构的顶端。而麦希维克则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社会的流动性相当之大,不存在一个所谓的“寡头”集团。麦希维克提出了与姜士彬结论完全相反的另外一种意见,但值得注意的是她所选取的研究对象、方法与前者截然不同。姜士彬在讨论寡头政治之前,先划定了大族的界线,大族是“被界定为姓望氏族谱所包括的那些氏族”[1]〔美〕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第116 页。。而麦希维克则是将所有五品以上的官僚进行了追踪式的调查比对,研究样本、手段、方法的差异对于结论有很大影响。杜希德指出:“对唐代社会流动及相关问题有兴趣的史家,他们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一类问题上,即是官僚们个人的社会背景与其成就的相互关系。”判断某个体的社会背景,一是借助某些只能由贵族胜任的官职来判断是否系出名门,二是看其入仕途径,科举出身则是寒门,恩荫入仕则是世家。[2]〔美〕杜希德:《从敦煌文书看唐代统治阶层的成份》,第111 页。杜希德、姜士彬、麦希维克这三人的判断准则完全不同。麦希维克并没有正面地讨论姜士彬研究的不足之处,而是另立研究样本。这一点在某种程度上弱化了她的论证力度。不对研究样本进行差异性描述,那么就失去了对话与讨论的平台。麦希维克注意的是很少有大型家族能够从魏晋一直延续至唐,对于大族在中古时期的持续时间表现出了很高的关注度,只能连续二世、三世的自然不算为贵族,能够持续两朝、三朝的也算不得贵族。麦希维克的研究回答了中古社会的统治阶层不是一个寡头社会,但是却并没有给出一个正面的积极答案。此外,作者在文献的征引方面也很值得中国学者反思。对于新近引介中文世界的《哈佛中国史》系列丛书,葛兆光在书系文献材料的征引方面表达了中国学者的疑惑:“以中古史为例,虽然陈寅恪、郭沫若、唐长孺、王仲荦、韩国磐等人的著作时有引述,但是,显然对近年以来中国学者的新研究了解相当不足。”[1]葛兆光:《侧看成峰》,《东方早报》2016年9月25日。从这本1992年的博士论文来看,这种“了解相当不足”的情况似乎早已经如此。作者征引的中文著作有陈寅恪、毛汉光、王伊同、杨筠如四人,在对魏晋南北朝中正官进行研究时,没有征引任何中国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一点就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该书的研究水准。然而,从中国学者的立场来看,如何更积极地推动本国学术走向世界舞台,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美国学者对于中国史的研究往往受到了西方学术话语的干扰。学者们在定义士族时,意见分歧较多,但无非在官宦、婚姻、文化这三个维度展开持久的拉锯式争论。官宦这个方面还被分化为几品官、勋位、家族几世为官这三个更为精微的细部,“寡头”一词,姜士彬有定义说明:“指称一小撮家族,这些家族的代表世世代代在中央政府最高级官员中占据绝大多数。……笔者在本书中使用的这个词汇,正是出于这个意义:它指的是一个小型的统治集团,不是世袭的贵族阶层;而是寻求其他方式来维持其统治权力,并将局外人排除在等级序列之外。”[2]〔美〕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第3—4 页。而“寡头”等词汇从西方固有学术语境中生发而来,在引入中国中古史研究领域伊始就不可避免地携带了西方史学价值的因素。姜士彬指出“寡头”一词可以追溯至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是西方政治哲学中的固有词汇,有特定的意义表达,“用来描述那种令人反感的少数人掌握政权的统治方式”,历史学家在使用这个词时,剥离了其中所蕴含的贬义。[1]〔美〕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第3—4 页。姜士彬对于贵族的界定乃是那些书于士族谱牒中的人物。[2]〔美〕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第2—3 页。中国史学界对于士族界定的认识实际上是清晰的。张国刚对魏晋隋唐士族身份的变迁洞若观火,他的解释相当透彻,他说:
把门第与士大夫脱钩是新做法,但把礼法文化的承担者与士大夫挂钩是南北朝的老规矩,把官爵与士大夫挂钩则是旧瓶装新酒的亦新亦老的规矩。士大夫或者士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只是指门阀士族,并不指官员,南朝中书舍人王宏应该属于文官,但并不是士大夫。可见士族与官爵不构成必然联系,只是那个时候的士族都有官爵,才构成了二者的相关性。唐太宗强调官爵对于士族的意义,是针对南北朝的旧士族失去官爵之后的情况而发的,所以是旧瓶(士族门阀都有官爵)装新酒(新王朝的显贵)。于是士大夫概念的内涵就在逐渐演变,到宋代就是泛指士人做官者,其独特的门阀内涵已经完全消失了。[3]张国刚:《论“唐宋变革”的时代特征》,《江汉论坛》2006年第3 期。
也就是说,士族一直以来都是礼法的承担者,与官爵并不完全挂钩,南北朝时的士族就与官爵不完全关联,唐朝时才将士族与官爵挂钩等同。官爵之于士族既非充分也非必要条件,而文化才是士族的充要条件。但是其中让人产生混乱的是,文化、礼法不可量化,在实际的论证操作过程中很难进行相关分析,官爵品级之数量特点却很容易进行等量计价。如果仅将官爵作为衡量的标准,而忽视文化方面的考量,那么所得出的结论就一定有失偏颇。麦希维克的研究正是仅仅关注了贵族的官僚性这一点,而对士族在文化、礼法上的地位没有做合适的评价。
对于贵族的界定存在着一个历史标准与学术标准,历史标准当然是指历史层面的实际情况,而学术标准则是指史学层面。对于士族之定义,张国刚的相关论述实际上就已经非常清楚了,但问题在于文化不可量化,研究难度较大,而官宦虽并非士族之必要条件,却很容易进行史料方面的裁剪与推论,换言之,在研究贵族的实际操作中,我们必须把他们简化成一个可以用历史文献加以把握和描述的对象,从史料层面将贵族这个概念进行约算处理,将他们等价为可以书写、计量的文献。李约翰批评伊沛霞虽然重视了士族的文化,但是她对官僚的重视并不比姜士彬少[1]〔美〕李约翰:《英美关于中国中世纪贵族制研究的成果与课题》,《中国史研究动态》1984年第7 期。,这并非是研究者有意地将文化这一特征忽视,而是在实际的研究操作层面难以加以把握的缘故。中国学者从文化层面对士族社会的变迁加以把握,比如,张国刚对于儒家礼法从门阀士族向其他社会阶层的转移进行了探讨,揭示了士族衰落过程中礼法下移的历史现象。[2]张国刚:《中古士族文化的下移与唐宋之际的社会演变》,《中华文史论丛》2014年第1 期;《汉唐“家法”观念的演变》,《史学月刊》2005年第5 期。而这一点正是美国学者所没有尝试的。
还有一些美国学者回避了社会学研究理论的关照,从其他角度对中古时期的统治阶层进行了探讨,比如葛涤风等。葛涤风在麦希维克的文中被多次提及,故而在这里对其《中国南方大族》一文加以简要介绍是有必要的。葛涤风开篇便将内藤湖南“中古中国是一个贵族社会”这个观点作为讨论的靶心摆出,并对日本唐宋变革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和热情。他认为由于文献史料的特点,我们无法对中古精英的整体构造进行还原,但是通过几个主要家族的集中式分析却可以帮助理解中古社会的特点。故而葛涤风以琅琊王氏、太原王氏、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为例,对南方大族进行了论述,文章的结论表明东晋上层精英迅速消失,且没有生长出新的精英阶层,有些东晋家族虽然重新出现在唐朝,但这绝非家族复兴的端倪,而是北魏贵族对自我身份的标榜与追附。[1]Dennis Grafflin, The Great Family in Medieval South China,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41, No.1(Jun., 1981), pp.65-74.美国学者对于社会流动性的探讨还注重从制度角度进行论证,比如丁爱博(Albert E.Dien)就从制度方面论证北朝的社会性质,他说现代学者经常使用“贵族”、“大族”这样的词汇,这使得我们在研究过程中非常重视血统、谱系以及家族身份地位,但是从原始史料来看,关于如何区分社会阶层和家族地位的材料是非常稀少的,唯一对此有明确规定的是北魏孝文帝在495年所颁布的法令。[2]Albert E.Dien, Elite Lineages and the T’o-pa Accomodation: A Study of the Edict of 495,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19, No.1(Feb., 1976), p.61.这个法令,艾伯华、姜士彬认为是拓跋为了获得汉人贵族的支持,争取传统士族的合作,以确保拓跋统治地位。但丁爱博对此予以否定,他认为这一法令非但不利于汉族士人,而且还要将他们在制度上进行限制,以防止汉族士人大量地涌入权力高层,故而,这个法令所要建立的目标体制是精英社会,而非贵族制。[3]Albert E.Dien, Elite Lineages and the T’o-pa Accomodation: A Study of the Edict of 495,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Vol.19, No.1(Feb., 1976), pp.78-79.
这些研究结论虽然与麦希维克的观点互为支持,方法却截然不同。它虽然鲜少受到社会阶层流动理论研究的影响,但也难以摆脱西方学术传统框架的束缚,习惯于使用精英这样的概念。精英这个概念是从19世纪社会学研究社会分层理论中衍生出来的,对精英理论阐释最为深刻的当属意大利社会学家帕累托,中古官僚贵族的流动性就是与之有关。[1]罗祎楠:《模式及其变迁——史学史视野中的唐宋变革问题》,《中国文化研究》2003年夏之卷。对于精英,帕累托并没有给出非常明确的定义,只是说“精英是指最强有力、最生气勃勃和最精明能干的人,而无论好人还是坏人”[2]〔意〕帕累托:《精英的兴衰》,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3 页。。美国学者在做唐宋统治阶层研究时常使用的精英一词,他们也未曾做出严谨的解释。从文本语境来看,他们所使用的“精英”一词很宽泛,指上层社会统治者,至于如何从官宦、乡里社会、土地、文化等方面加以精确地对应,则是缺乏学术考量的。美国学者自己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伊沛霞认为“精英”与“士”相比,前者主要是指个体,而后者多指集团,她还对“士”这个概念进行了梳理,提出西方学者不能从西方学术知识体系中寻找资源来对应中国的统治阶层,而应该试图接受“士”这个概念。但是她在分析了传统史学研究者与现代学者对于“士”这个概念的理解之后,又认为“士”是一个边界模糊的社会阶层。[3]Patricia Ebrey, Toward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Later Han Upper Class, 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Edited by Albert E.Dien, California,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关于该文的介绍可以参见丁爱博在该书中的序言,该序言有中译本,参见〔美〕丁爱博:《〈中国中世纪早期的国家与社会〉导言》,张琳译,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4 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82—194 页。至于门阀社会鼎盛期魏晋南北朝隋唐士族的衍生形态则没能给予相应的关注。“寡头”一词在中文世界使用的普及面并不广泛,我们更多地使用门阀政治、士族政治。让人玩味的是,美国学者在研究中古统治阶层时,鲜少使用中文史籍中所出现并为中国学者所认可的“士族”一词,他们更多地用贵族、乡绅、寡头等表述;他们所理解的士,麦希维克将它定义为学者、乡绅、官僚、军人、武人。[1]Dušanka Dušana Miščević, Oligarchy or Social Mobility? A Study of the Great Clan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ol.65, 1993, pp.55, 199.作者对于中古社会阶层也有分类,多次提到established clans[2]Dušanka Dušana Miščević, Oligarchy or Social Mobility? A Study of the Great Clan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ol.65, 1993, pp.161, 164,212, 245.,其指在曹魏之前就有已经有直系先祖拥有官爵的氏族。[3]原文是the clans that are considered “established” in this table are those that can be successfully traced back to direct ancestor who held office under the dynasty preceding the Arbiter appointment。Dušanka Dušana Miščević, Oligarchy or Social Mobility? A Study of the Great Clans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Vol.65, 1993, p.162。美国学者对于史籍中经常出现的“士”表现出了很大的困惑,他们认为“士”在不同的语境中会有不同的解释,它可能是“上层阶级”的普通用语,不具有法律意义。因此,在研究过程中对于如何理解“士”这个概念,他们往往选择“搁置不译”,还试图将“士”这个词与没有英译的词汇junker(容克)、samurai(武士)、bourgeoisie(资产阶级)联系起来。[4]〔美〕姜士彬:《中古中国的寡头政治》,第9、23 页。美国学者没有对“士”的语境文本进行分析,在西方学术话语中又找不到与之相契合的词汇,被迫使用一个在中古史籍中极为鲜见的“寡头”,使得中西学术话语存在着明显的扞格。这给中古士族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困惑,看似我们的研究目标也即“中古社会统治阶层”,但是实际上中国与美国学者所关注的这个阶层又难以等同,美国学者难以从西方知识结构中抽取一个恰当的对象加以对应,只能用相近的概念来类比,这无疑使得他们与真实历史之间越发疏远。
三
在美国史学界讨论魏晋南北朝隋唐统治阶层的流动性时,与之相辉映,大洋彼岸的中国也注意到了士族阶层内部的流动性。中国学者所关注的社会流动,“主要关注点在于个人、家族或特定群体在社会等级、社会分层体系中的流动,特别是导致他们所隶属的社会阶层发生变化的运动”[1]邓小南、荣新江:《“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究”专号“序”》,载《唐研究》第11 卷,第2 页。宁欣、张天虹:《汉唐时期中央官学的演变与社会流动》,《河北学刊》2003年第23 卷第4 期。韩昇:《科举制与唐代社会阶层的变迁》,《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4 期。金滢坤:《中晚唐五代科举与社会阶层的变迁》,载氏著:《唐五代科举的世界》,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58—302 页。陈灵海:《唐代籍没制与社会流动——兼论中古社会阶层的“扁平化”动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1 期。范兆飞:《中古太原士族群体的流动与秩序》,《中国社会科学报》2014年12月17日第A06 版。。唐长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一文是关于这个问题的重要著作。[2]唐长孺:《士族的形成和升降》,载氏著:《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63 页。唐长孺的这篇文章并没有单列发表,于1983年出版时被收录进来,该文内未引用相关论文,故而将时间下限定为1983年。陈寅恪、祝总斌、田余庆在研究东晋门阀政治时,分析了“次等士族”这类阶层,田余庆认为文化是士族的必要条件,士族门户下降无法选择优等的婚宦关系,致使他们无从维持门户之文化,而不学无文的武将因婚宦而依附于士族,就是次等士族。[3]由于陈寅恪、祝总斌没有对“次等士族”的内涵加以解释,故而田余庆对于自己“次等士族”的概念与他们的“原意是否符合,那就很难说了”(参见田余庆:《论东晋门阀政治》,《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2 期)。毛汉光也使用了类似的词汇“次级士族”,就是陈寅恪所说拥有地方势力的“中层社会阶层”。[4]毛汉光:《中古官僚选制与士族权力的转变》,载中国唐代学会编:《唐代研究论集》第1 辑,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90 页。除此之外,近年来,有学者从士籍谱系出发,挖掘绵长谱系内部的断裂之处来阐述士族内部的更替。[1]仇鹿鸣:《“攀附先世”与“伪冒士籍”——以渤海高氏为中心的研究》,《历史研究》2008年第2 期;尹波涛:《北魏时期杨播家族建构祖先谱系过程初探——以墓志为中心》,《中国史研究》2013年第4 期。中国学者虽然对社会流动的认识有分歧,然而在社会性质的认识上并没有疑义,这一点与美国的中国学研究明显不同。美国学者对于魏晋隋唐社会流动性的探讨是意图回应日本学者倡导的唐宋变革,也源于对于中国社会平等与开放的关注。[2]罗祎楠:《社会流动理论与历史研究——以美国宋代社会史的讨论为例》,载《唐宋时期的社会流动与社会秩序研讨会论文集》,2004年。而中国学者对于社会流动性的探讨并不是为了对唐宋变革做出回应。
1934年,周一良《日本内藤湖南先生在中国史上的贡献》一文就对唐宋变革进行了介绍和引进,但是在当时学界并未引起广泛关注,80年代以后,日本的唐宋变革论才开始进入中国学者的视野。[3]张邦炜:《“唐宋变革”论与宋代社会史研究》,载李华瑞主编:《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天津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10 页。20世纪隋唐五代社会流动问题的专门性探讨并不丰富,这个议题往往是附属于以下三个问题的讨论中:农民战争中所涉及的社会身份的变化;贱民等级问题中所涉及的人的地位升降;地主、农民阶级问题中所涉及的社会流动。[4]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00—801 页。关于士族身份与地位的变化亦形成了四类观点:唐代士族仍然有很强的势力;唐代士族已经势微,但其社会影响力仍不可小觑;唐代士庶合流,没有魏晋南北朝时期那样的门阀士族,只存在具有士族血统的人;庶族与士族不能准确地概括唐代统治阶层的特点,皇家地主、官僚地主、庶民地主、僧侣地主是唐代主要的特权阶层。[5]胡戟等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第803—805 页。这些观点渐渐从对立走向了相互融合、借鉴,近些年来,中国学者对于唐代士族的认识越发清晰,多数学者认为唐代是一个贵族社会,只不过其权力结构已经开始瓦解,他们的身份及其赖以存在的社会政治经济体制正走向崩溃。
中国史学界在士族研究领域的分歧事实上是相对澄澈的。本文开头曾提到,学科理论以及背后的政治关怀对学术的客观性存有干扰,针对这一点,也有学者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葛兆光就认为:“正是这种民族主义甚至是帝国主义的政治背景,恰恰激活了学术领域的研究兴趣,而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取向,又逐渐变成一种重新理解中国的普遍观念。”[1]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44 页。而中国史学界在中古士族领域正是遭受着理论的双重困扰:一方面,我们受到了西方、日本学术理论的影响,他们的介入混淆了我们自身的学术脉络;另一方面,我们又没有形成独立的学术理论和话语体系,导致学术研究缺乏活力与拓展空间。这正是中国士族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日本唐宋变革说的提出给史学界带来了全新的研究视角,在日本国内形成了京都学派与东京学派两大阵营。美国唐—北宋—南宋历史观的形成是对宋史领域认识取得突破后的成果,这个理论框架已经开始向唐史研究辐射,表现出了顽强而鲜活的生命力。中国史学界是先有了对唐宋时期所发生的巨大变化的认识,然后再开始探讨社会流动的。但让人唏嘘的是,中国对于唐宋变革的研究逐渐走向工具化、低俗化[2]陆扬:《唐宋变革论究竟是怎么回事》,澎湃新闻2016年5月29日。,相形之下,这样差强人意的理论自觉性对于我们当今史学不得不说是一种警示。美国中国学从士族政治、精英理论的角度出发,从中找到了可以替代唐宋变革的新范式;中国的唐宋变革在唐史研究的众多领域虽也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在士族研究领域却没有能够产生与唐宋变革相提并论的理论,这是研究中古士族史的学者应该反思的问题。
20世纪,汉学经历了一次大的转变,它从欧洲转向美国,从一门专业性极强的冷学问锐变为跨越学科界线的热学问,从人文学科的领地一直扩张到社会科学。[1]陈珏:《杜希德与20世纪欧美汉学“典范大转移”》,《古今论衡》2009年第20 期。汉学曾以古典文化为主,重视校勘考据,著名的汉学家有马伯乐(M.Henri Maspero)、葛兰言(Marcel Granet)、伯希和(Paul Pelliot)、沙畹(Edouard Chavannes),他们恪守文献学的基本方法。在经历了典范转移之后,美国中国学研究则更多地关注20世纪中国的一系列理论与实践问题,擅长从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方法中汲取营养,拓宽历史研究的视野。[2]周武:《西方世界中国研究的典范转移》,《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年7月6日第013 版。这次转移带给中国学者在士族研究领域最大的震撼便是来自于社会学的个案研究方法与手段。中国学者从欧美学者借鉴的个案研究法,目前看来是得到了广泛的认可与学术应用,但是从其所取得的成果来看,并不如预期。除了个案研究法外,社会流动理论也是这一时期美国中国学所流行的研究思路与路径。对于中国学者而言,它远不如个案研究法一样受到广泛追捧,但对于美国学者来说,却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研究范式。当社会学的研究方法被引至历史学领域,固然会带来新的学术生长点,但也不可避免地带来混乱。这正是社会学定量研究在士族研究领域的运用中所产生的负面效果。
对于同一个问题,不同的研究范式与研究思路在着眼点、方法等方面存在不同是正常的:“尽管各个体系往往在相互证伪,它们的内部结构却相对完满自足。”[3]刘东:《理论与心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6 页。但是在唐史、宋史领域,社会流动的探讨却远没有达到这样的学术自立。关于社会流动性的探讨就像“二律背反”一样存在,当我们选取不同的研究对象和计量方法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黄宽重在研究宋代家族兴衰与社会流动时指出:“设定一个宽广的标准,以一个地区作较长时期的观察,可能看到一个地区长期被某些家族垄断的现象,但如果从个案的方式做细致的研究,而且从家庭内部的变化去看,结论或许又有所不同。”[1]黄宽重:《宋代的家族与社会》,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6年版,第262 页。魏晋南北朝隋唐史对社会流动性的研究现状也可以简单地加以比附,如此,霍姆格伦从个案入手,对北燕冯氏的个案式透析也得出了北朝社会不同于南朝,其社会流动性较大的结论。[2]Jennifer Holmgren, Social Mobility in the Northern Dynasties: a Case Study of the Feng of Northern Yen, Monumenta Serica, Vol.35(1981-1983), pp.19-23.从整体入手,一般会得出社会流动性不强的结论,而从细节入手,又很容易指向对立面。
这是社会流动探讨引入历史学所带来的一个混乱,但是给史学工作者带来的错愕远不止如此。面对社会流动这个问题,往往增添一个新的参数或者影响因子便会改变最后的研究结论。以清代的社会流动为例,何炳棣便指出,社会流动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更新系统,当对具体家族做个案式分析时,便会发现家族内部的流动是非常普遍的,如曾祖父时家族拥有很高的官位,但后来家道中落,直至己身时才重新获得了曾祖父的官位,这一过程在数据统计时是无法加以表现的。[3]Ping-Ti Ho, 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 Aspects of Social Mobility, 1368-1911,pp.92-125.韩明士还指出,除了直系父祖外,母系及其他家庭成员也应当被计入影响家族社会流动的因素当中,故而他的研究工作表明,家族相互联姻因素的代入大大降低了统计结果中流动性的程度。[4]Robert P.Hymes, Statesmen and Gentlemen: The Elite of Fu-chou, Chiang-His, in Northern and Southern Su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34-48.研究者对于流动与非流动这两派的观点进行对比,发现采用全国性的、大规模的史料往往得出的是中华帝国后期有流动性的结论,而局部的、区域性的史实,则会对此提出质疑。[5]沈登苗:《关于科举社会流动讨论中的几个问题(概述)》,载《文化的薪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201—202 页。姜士彬从敦煌姓氏文书入手来考察唐代的社会流动性。敦煌姓氏文书能够整体地展现姓氏的兴衰沉浮,却不涉及姓氏背后家族的具体世系,姜士彬借此得出了社会流动相对稳定的结论。而麦希维克绘制了大规模的氏族世系图表,从每个家族具体的升降沉浮中做统计说明,得出的是魏晋南北朝社会流动性较强的结论。如此,不同性质的材料对于结论的确存在着非常明显的影响。
社会流动的探讨从明清史蔓延至宋史,又转入魏晋南北朝以及唐史,这个问题的争论看似无处不在,却又似毫无进展与突破,若不对其中的学术分歧进行深入的净化,那么再多的探讨只能造成抱薪救火般的混乱。社会流动研究中出现的这些矛盾和怪圈,不得不从研究方法、研究手段上来寻求原因。这些问题正是在借鉴社会学研究主题、研究方法过程中所滋生的顽疾。历史学从社会学中汲取营养时,也必须同时思考社会学在引入历史学过程中所产生的负面效应:社会学与历史学应该保持一定的距离。诚然,在多学科融合发展的新学科建设背景下,这样的说法显得有点鲁莽,但是在士族研究领域滥用社会学的主题与方法给我们所造成的秩序混乱,却不得不让我们有这样的自觉与警醒。社会学方法在真实不妄的历史面前应该保持足够的谦卑,而历史学者使用社会学方法来从事研究工作时更应该保持应有的恭敬。
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对于这种分歧便有着自己的见解。丁爱博在编撰《中国中世纪早期的国家与社会》一书时认为,六朝史的研究不仅史料较为稀少,而且呈现出各种不同的研究取向,因此这一领域的研究与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所描述的“前范型时期”有很大的相似性,“它以围绕着合理方法、问题及其解决标准而展开的频繁而深刻的争论为特征,虽然这些与其说是用以达成共识,毋宁说是用以界定学派”,魏晋南北朝的统治阶层是否为贵族的讨论已然呈现了阵营对垒的局面,而面对这样的形势,美国学者认为“历史学家的职责在于促进一场迟早都要到来又不可避免且必须的争鸣,以废弃他的或她的研究成果”。[1]丁爱博:《〈中国中世纪早期的国家与社会〉导言》,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4 辑,第182—194 页。本文在引用时译文略有改动,原文可参看Albert E.Dien, Introduction, State and Society in Early Medieval China, Edited by Albert E.Dien, pp.28-29。美国的中国学研究也认识到了其内部的分歧与争端,但他们对待这场学术辩论所持有的是一种消极态度,无意于澄清各自学术的弊端,似乎构建两种平分秋色的对峙意见才是一种学术理想国。仅就当时的学术水平而言,我们尚能推卸历史学者的些许责任,但时至今日,这一研究分歧在宋史领域获得突破性进展,中国史学界又经历着与美国唐史研究同样的学术纷争,如果不对这些研究分歧加以厘清与辨别,则确有失责之嫌。
中古士族研究所产生的诸多分歧主要来自两方面的干扰:一是海外汉学中固有的实践偏好对于探讨真实历史的干扰;二是社会学主题、方法植入历史学土壤时所产生的排斥反应。这两点造成了中国中古士族研究领域中呈胶着状的持久论战。细绎我们自身的学术理路,不难发现,吾国学术对于中古士族研究确实有着相当清晰的认识与理解,意见分歧的实质是学术理论层面与学术书写、操作层面之间的矛盾。通过梳理美国士族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亦不难发现,他们对于社会学方法有着近乎天然的亲近感与熟悉感,在唐史研究领域运用社会学主题、方法发生阻塞时,在宋史领域又能很快打开突破口,形成可以与日本“唐宋变革”相埒的大历史观。如果说认清自身优势与特点是一种学术自觉,建立历史学理论是一种学术自立,那么,这两方面正是我们史学界目前亟待建设、发展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