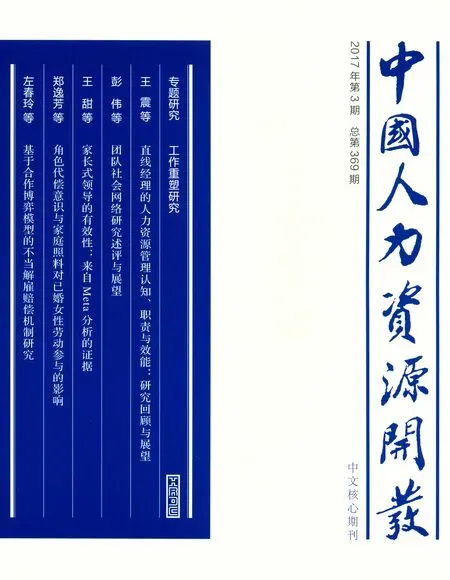个别劳动关系法治化治理研究
2017-01-26江峰
● 江峰
内容摘要个别劳动关系法治化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存在法律规制价值取向不明确,个别劳动关系的法律界定不清晰,典型劳动关系割裂与非典型劳动关系放纵等问题。在《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修订过程中,个别劳动关系法治化治理需要进一步明确价值导向,实行劳动者分层保护和用人单位分类适用,重构劳动合同期限制度,完善非全日制用工法律,并将共享经济下互联网平台用工纳入劳动法律规制。
关 键 词个别劳动关系 法治化 治理
个别劳动关系法治化治理研究
● 江峰
内容摘要个别劳动关系法治化治理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存在法律规制价值取向不明确,个别劳动关系的法律界定不清晰,典型劳动关系割裂与非典型劳动关系放纵等问题。在《劳动合同法》等法律的修订过程中,个别劳动关系法治化治理需要进一步明确价值导向,实行劳动者分层保护和用人单位分类适用,重构劳动合同期限制度,完善非全日制用工法律,并将共享经济下互联网平台用工纳入劳动法律规制。
关 键 词个别劳动关系 法治化 治理
当前,我国正处于经济社会转型时期,劳动关系的主体及其利益诉求多元化,劳动关系矛盾进入凸显期和多发期,劳动争议案件居高不下,集体停工和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任务艰巨繁重。基于这一背景,中共中央、国务院适时印发《关于构建和谐劳动关系的意见》,提出要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个别劳动关系作为劳动关系最直接、最本质和最一般的构成形态,是劳动关系系统的基础构成。以《劳动合同法》修订为契机,加强个别劳动关系法治化治理的对策措施研究,有利于整体实现劳动关系法治化,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一、个别劳动关系法治化治理历史进程及经验
(一)个别劳动关系法治化治理的历史进程
个别劳动关系法治化进程是伴随我国劳动立法的历史进阶逐步演化推进的,立法规制个别劳动关系经历了萌芽、起步、停滞和恢复发展历史时期,与我国劳动力市场化和法治化是密不可分的。
个别劳动关系法律规制萌芽阶段。1949年11月至1950年11月,我国颁布了调整劳资关系三大文件:即《关于劳资关系暂行处理办法》、《关于私营工商业企业劳资双方订立集体合同的暂行办法》和《关于劳动争议解决程序的暂行规定》,这些规定实现了对私人资本的利用、限制和改造,促进了“发展生产,劳资两利”的实现。
个别劳动关系法律规制初始阶段。即第一个五年计划到文革时期(1953-1977),在这一阶段,通过社会主义改造,中国进入指令性计划经济时期。劳动立法方面,1952年8月,政务院发布《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1954年7月,政务院公布《国营企业内部劳动规则纲要》,1956年国务院公布《工厂安全卫生规程》,这一时期的劳动立法具有公法性质,“公法一元化”,“行政一元化”,形成了“一元法律结构”。1966年至1976年,受文革影响,劳动立法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个别劳动关系法律规制的恢复阶段。1976年10月以后,我国的劳动立法进入恢复发展发展阶段。用工管理方面的立法包括:《企业职工奖惩条例》(1982年)、《关于招工考核、择优录用的暂行规定》(1983年)等。劳动人事部1982年制定了《关于积极试行劳动合同制的通知》,开始探索劳动合同用工制度。这一时期,还进行了工资分配制度的改革,完善退休养老制度,制定了《关于工人退休退职的暂行办法》。
个别劳动关系法治化治理的发展阶段。这一时期,劳动立法主要围绕劳动制度改革进行。一是在国营企业推行劳动合同制度,1986年7月至1988年间,国务院先后发布《国营企业实行劳动合同制暂行规定》、《国营企业招用工人暂行规定》、《国营企业辞退违纪职工暂行规定》。二是恢复劳动争议处理制度,1987年7月31日,国务院颁布《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1993年国务院发布《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条例》,由此恢复了自1956年起中断了的劳动争议处理制度。
个别劳动关系法律规制法治化治理新阶段。1994年7月5日,经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标志中国劳动关系法治化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填补了我国劳动基本法的空白,为健全市场经济体制,实现劳动力配置市场化创造了改革条件。2007年6月29日,全国人大会常委员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从劳动合同的订立、履行和变更、解除和终止等多个方面,完善了劳动合同制度,明确了劳动合同双方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标志着我国个别劳动关系法律规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二)历史经验
个别劳动关系法治化治理始终坚持“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为宗旨,体现立法宗旨的“单向性”。《劳动法》将“为了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确立为立法宗旨,并通过确立基本劳动标准和劳动关系规则,以及劳动监察、争议处理和社会保险等制度,全面规范企业用工行为,倡导正确的用工理念,为劳动者依法维权提供了强有力的依据和保障。《劳动合同法》继续坚持了单保护的原则,以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为宗旨、以劳资力量平衡为中心、以劳资共同发展为目的,从而推动劳动关系的公平公正,促进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维护市场经济的基本秩序。
个别劳动关系法治化治理始终坚持“健全市场经济体制”为担当,体现劳动资源配置的“市场化”。《劳动法》打破了企业的所有制界限,确立了劳动力资源市场配置的原则,建立了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规则,为建立统一、公平的劳动力市场提供了基本原则和法制规则。《劳动合同法》则进一步确立了市场化的劳动用工体制,确定了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市场化管理原则,建立了通过劳动合同和调整劳动关系的法律制度,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制度活力。
个别劳动关系法治化治理始终坚持“市场经济就是法治经济”的基本方向,体现劳动关系法律规制“法治化”。《劳动法》通过明确劳动关系双方主体的权利义务,规范了劳动关系的建立、变更、终止、解除行为,建立了劳动关系监督和劳动争议处理的机制体制,设计了社会保险制度的构架,为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关系的依法运行提供了遵循,总体上解决了劳动关系无法可依问题。如今,以《劳动法》为基本法、以《劳动合同法》《就业促进法》《社会保险法》等多层级劳动法律法规为补充的劳动法律体系,已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林嘉,2016)。
二、个别劳动关系法治化治理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加速转型,新行业、新业态快速发展,劳资关系上出现了一系列的新变化,如劳动力总体过剩与结构性短缺,劳动力市场曾长期呈现的“强资本、弱劳动”的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企业用工管理和劳动者的劳动形态发生深刻变化,劳动关系主体多元化与形态弹性化等。此外,随着互联网等新经济的蓬勃发展,非全日制用工、劳务派遣、劳务外包、互联网平台用工等一些非规则用工形式大量出现。这些非规则用工大多未纳入劳动法律调整,特别是互联网企业的用工管理和劳动者的劳动形态发生了深刻变化,企业用工碎片化、工作场所虚拟化,直接冲击着传统劳动关系,也对我国劳动法律体系的发展和完善,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实现个别劳动关系法治化提出了新的要求,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个别劳动关系的法律界定不清晰
泛劳动关系与去劳动关系并存。由于新行业、新业态快速发展,企业用工管理和劳动者的劳动形态深刻变化,个别劳动关系多元化趋势向复杂化演进,泛劳动关系与去劳动关系纠缠不清。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11月30日发布《第八次全国法院民事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首次提出“防止认定劳动关系泛化”。从裁判口径上看,数以亿计的建设工地农民工劳动关系被归入了“泛化”之列。同时,随着互联网等新经济的蓬勃发展,共享经济等新经济业态的发展,诸如网约车等网络平台用工形式大量出现,这些非规则用工大多未纳入劳动法律调整,业务主管部门匆匆进行的“去劳动关系”定调,更让这部分劳动者游离于劳动关系与劳动关系之外,这种既泛劳动关系又去劳动关系,反映了理论和实务上对劳动关系的界定模糊不清的现状。
劳动关系人事化与人事关系劳动化。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还存在一个独立于劳动关系之外的人事关系。而事实上,人事关系中聘用合同本质上属于劳动合同,本可以纳入劳动法律的规制的范畴。但是,事业单位作为政府举办的从事专业性公共服务的机构,具有优先性质。即与一般劳动关系仅直接涉及双方利益不同,事业单位人员聘用还直接关系到公共利益,并遵循公益优先原则(李建忠,2014)。正因为《劳动合同法》所规定的劳动者利益的优先性与事业单位应遵循的公共利益的优先性,在法律关系调整原则上存在根本的差异,衍生了中国部分“劳动关系人事化”特殊国情。但是,事业单位人事关系和人事管理进行专门规定的法律法规体系并不健全,政策治理成为普遍现现象的同时,人事关系治理无法可依的问题显得越来越窘迫,由此出现了《劳动合同法》第九十六条所规范的特别条款,在法律适用上又不得不将“人事关系劳动化”。
(二)个别劳动关系法律规制价值取向不明确
追求安全还是追求灵活。前财政部长楼继伟2015年以来,先后多次对《劳动合同法》提出了批评,认为其降低了劳动力市场的流动性和灵活性,关于劳动合同法是否影响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讨论也变得更为激烈。劳动立法如果过于刚性,给予企业和劳动者的弹性的空间过小,是可能对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造成影响。因此,个别劳动关系法律规制如何适应社会的变化,满足劳动力市场需求,又不影响劳动者职业安全稳定,都是在下一步修改中所需要讨论的重点问题。
追求效率还是追求公平。科斯定理假设了两种情形:“在零交易成本的条件下, 法律规定无关紧要 , 因为人们可以在没有交易成本的条件下就如何取得划分和组合各种权利进行谈判,其结果总是能够使产值增加。”但是“如果存在交易成本,有效率的结果就不可能在任一法律规则下发生,合意的法律规则是使交易成本的效应减至最低的规则(科斯,2009)。”个别劳动关系法律规制,涉及到的立法、执法以及司法活动, 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交易主体的成本与收益。如何平衡公平与效率两者之间的关系,成为法律规制应当考量的重要课题。
保护劳动还是保护资本。这是劳动合同立法规制个别劳动关系的需要解决的价值理念问题,也称为“单保护”还是“双保护”的论争。劳动合同立法的价值取向是保护劳动还是保护资本,或者说是单纯地追求利润的增长以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还是通过倾斜保护劳动者权益,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之秩序,这确实属于一个利益博弈和政策选择的过程。倾斜保护原则是劳动法的重要理念和基本原则,立法规制个别劳动关系,建立法治化的劳动力市场,就必须针对劳动者之弱势进行立法匡扶,以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和平衡。
(三)典型劳动关系割裂与非典型劳动关系法律规制放纵
个别劳动关系又被分类为典型劳动关系与非典型劳动关系,也称标准劳动关系与非标准劳动关系。在个别劳动关系领域法律规制方面,显然还需要正视和关注两种极端的现象。那就是灵活的更灵活,不灵活的更加不灵活,典型劳动关系被割裂和非典型劳动关系被放纵的倾向并存。比如垄断行业所谓的正规用工,市场化程度现在依然很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固定工”模式并没有根本改观,割裂于现代劳动力市场,割裂于现代劳动法体制下的薪酬福利制度,不灵活的更加不灵活,体制内的劳动资源不仅没有激活,更有被凝固的趋势。另一方面,《劳动合同法》对非全日制用工虽然做了规定,但是该法对非全日制劳动者的保护明显不足,接近放任的程度。比如用工可以不订立书面劳动合同,可以不支付经济补偿,也可以不缴纳社会保险。这些规定不符合非典型用工发展的需要,也不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灵活的更加灵活,灵活泛滥,甚至过度灵活的倾向日益加剧。
三、个别劳动关系法治化治理的建议
推动个别劳动关系法治化治理,构建和谐劳动关系,首先要解决法律规制个别劳动关系的基本理念问题,坚持以保护劳动合法权益为宗旨,灵活与安全并重。在具体举措上,坚持劳动者分层与用人单位分类相结合,完善劳动合同期限制度和非全日制用工,依法将互联网平台用工纳入劳动法律规范。
(一)明确个别劳动关系法治化治理的价值导向
灵活与安全并重。个别劳动关系法律规制无疑要维护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但是这种灵活性的实现是以劳动力市场存在安全保障为前提的,正如有学者所说“劳动力市场如果有了安全保障,那么灵活性就不再是有争论的话题”。劳动力市场的安全保障是市场主体具有选择自由的前提,但这种选择自由不仅是理论上的行为自由,更是实质上的,即劳动者不会为了生存而被迫做出选择。同时,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不能够损害劳动力市场的健康和可持续发展,需要兼顾就业稳定性和劳动者职业安全。
坚持劳动立法宗旨。在保护劳动还是保护资本的问题上,继续强调保护劳动者这一基本立场,这是劳动合同立法规制个别劳动关系的需要解决的价值理念问题,也称为“单保护”还是“双保护”的论争。劳动合同立法的价值取向是保护劳动还是保护资本,或者说是单纯地追求利润的增长以推动经济持续快速发展,还是通过倾斜保护劳动者权益,达到维护社会稳定之秩序,这确实属于一个利益博弈和政策选择的过程。倾斜保护原则是劳动法的重要理念和基本原则,立法规制个别劳动关系,建立法治化的劳动力市场,就必须针对劳动者之弱势进行立法匡扶,以实现实质意义上的平等和衡平。
劳资自治与国家强制相结合。劳动立法作为社会法的有机组成部分,以解决劳动问题、保护劳动者利益为己任。要实现这一立法宗旨,恰如其分的国家强制意志体现成为必需。这是由劳动合同双方主体的特殊性所决定的,虽然用人单位与劳动者在形式上平等,但实质上无法达到平等的谈判地位。在我国,集体谈判力量弱且不具有普遍性,劳动者的利益几乎都要由个别劳动合同来规定,而大部分个体劳动者的谈判能力很有限。因此,个别劳动关系法律规制,应该是国家强制与劳资自治相结合的特别法。
(二)劳动者分层保护与用人单位分类适用
关于劳动者分层保护的问题,现有立法并非完全无视,比如高薪劳动者的经济补偿“双限”制度,公益性岗位适用法律部分排除方面的制度设计,就是在劳动者分层保护方面作出的有益尝试。但是,实务中反映出来的问题,认为这还远远不够。在不同岗位、不同职业劳动者构成日益复杂的情况下,需要有一种更加明确或者细微的区分,比如,不能将企业高管一视同仁纳入对普通劳动者的同等保护体系,因为“企业高管往往兼备法律知识、企业运营策略和管理经验,在求职中具有很强的谈判能力,即使离职之后也很容易谋到高位,有比较高的自由度来支配自己每天的工作时间,具有灵活性和机动性。其薪酬结构也不同于普通劳动者,多为年薪或者另加风险收入,已经不仅仅属于谋生的报酬,不具有特殊保护的必要” (贺安杰,2016)。高管的排除适用似乎比较容易达成共识,但是问题是如何界定高管的身份?依职位还是依收入?在具体法条的适用上是整体排除还是部分排除适用?这些都是需要在修法过程中进行具体的论证和探讨。
关于用人单位分类适用,劳动合同法没有对市场经济中的不同规模不同类型的用人单位加以区分对待,近乎是一刀切地完全适用法律中的所有条款,确实在实践中产生了很多新的问题。从企业规模来看,大型企业生产经营形式相对固定,内部管理更加规范,承担责任的能力更强,各方面都具备执行劳动合同法的条件;而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规模较小,用工方式比较灵活,内部缺乏规范的规章制度,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存在比较大困难。基于这些理由,应该考虑对不同类型的企业进行分类适用劳动合同法,实施差别化适用。但是,小微企业的界定标准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其劳动者又恰恰是劳动者中最弱势的群体之一,如果将这些人整体排除在劳动合同法的的适用范围之外,与劳动合同法的精神和使命不符。所以在劳动合同法总的适用范围上并不排除小微企业,而只是在劳动规章制度的制定程序、劳动合同解除的工会告知程序、裁员规定的适用等具体规定中,可以予以例外规定,比如设立20人以下企业的简易程序。需要平衡的是,这种差异性适用,是否会给其他用人单位和差别化适用法律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带来新的不公?以及到底如何区分分类适用的用人单位类型,法律适用到何种程度等等,都有待做进一步的探讨。
(三)重构劳动合同期限制度
现行劳动合同法确定了“以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原则,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例外”的劳动合同期限规则,这种规则之下固定期限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所适用的解雇条件是完全一样的。这与“以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为常态、解雇保护制度仅适用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国际通行模式刚好相反,形成了独特的中国大陆模式。这种模式的初衷在于要解决“现实生活中劳动合同短期化的问题非常突出,损害劳动者的权益,不利于建立稳定的劳动关系”(钱叶芳,2016)。但是这种“对劳动关系的稳定作用被僵化为对劳动关系的锁定作用”(上海市劳动保障局课题组,2005)的制度设计,无疑也引发了近十年间对于签订固定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博弈,以及实践中用人单位对于无固定期限合同的规避行为。这种立法者煞费苦心,却因劳动合同期限规则没有理顺,在推进较长期限的劳动合同的努力中出现了法律理解和适用上的混乱。
推动劳动合同制度立法完善,加强个别劳动关系法律规制,应当正视这种立法以及理解适用上的种种博弈困局,探讨在合同期限制度设计上与国际惯例接轨,确立“以不定期劳动合同为常态,以定期劳动合同为例外”合同期限一般原则,重新审视签订固定期限劳动合同与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要素式条件,探索建立与不同期限劳动合同相匹配,解雇条件和保护水平与合同期限类型相适应的立体化分类解雇保护制度。但是,现行法律通过制度设计强推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努力,并没有在实践中得以较好的实现。因此,立法规制合同期限制度,还应当从成本和收益的角度对用人单位在合同期限选择上进行必要的鼓励和诱导,比如适当放松对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解雇限制,将用人单位的单方解除权限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既能够有效保护劳动者,又能够为用人单位所接纳。有如,建立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财政奖励机制,对于首次就业签订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的情形,可以在就业资金补助、社保费率优惠、税收减免等方面依法依规给予一定程度的奖励性回馈。
(四)完善非全日制用工法律规制,探讨共享经济下互联网平台用工入法
非全日制用工劳动关系已经从传统的劳动者与单一用人单位(雇用者)之间的一重劳动关系,演变为劳动者与多个用人单位之间的多重劳动关系。在这些新兴劳动形态普遍化发展的背后,预示着一个劳动关系非典型化的发展趋势。但是,劳动合同法仅有的5条规范,一是对于非全日制用工对界定过窄,每日不超过4个小时,每周不超过24个小时的时间标准则束缚了用工灵活,宜参照主要市场经济国家部分工时工作的通常界定,把少于周标准工作时间的用工统一纳入非全日制进行规范。二是要提高非全日制劳动基准,对于非全日制劳动者的工资福利、社会保险、劳动条件、合同管理以及解雇上应与全日制用工基本等同。防止、减少、解决非典型劳动关系中侵害劳动者权益的事件。
互联网对于劳资关系结构和力量的改变,要求国家立法和管理层面要进行相应的调整。这种调整非常重要的一点,是基于互联网并未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目前最基本的雇佣关系形态和雇佣关系的性质的基本判断,共享经济下互联网平台用工等新兴就业形态并不具备劳动法外豁免等特权,探讨互联网平台用工等灵活就业形式“入法”,实现劳动法律规制从“正规就业友好型”向“就业友好型”的转变,从“劳动关系”规制向“劳动的关系”规制转变具有重要意义。从立法上纳入并认可灵活就业形式,赋予其合法地位,有利于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有利于从业劳动者合法权益保护。但是,对于互联网新兴用工形式,是否执行标准劳动关系之下的劳动基准,显然值得探讨和研究。法律规制需要考虑如何从互联网灵活就业形式从属关系比较弱的基本特征,在立法体例和指导思想上打破劳动关系与劳动基准、社会保险的捆绑关系,放宽劳动关系范围,设定与标准劳动关系不同的工资、工时基准,以此推动和增强相关基准的适用性和灵活性,同时也为就业劳动者提供必要的收入安全和劳动安全保障。
1.曹艳春:《劳动合同法修改应坚持六项原则》,载《上海法治报》,2016年11月30日B6版。
2.贺安杰:《关于修改《劳动合同法》的几点建议》,载《中国劳动》,2016年09期,第7-10页。
3.李建忠:《〈事业单位人事管理条例〉重点热点问题解读》,载《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14年第10期,第55-58页。
4.钱叶芳:《〈劳动合同法〉修改之争及修法建议》,载《法学》,2016年第5期,第51-64页。
5.林嘉:《劳动法的原理体系与问题》,法律出版社,2016年版。
6.科斯:《企业、市场与法律》,上海三联书店,2009年版。
■ 责编/ 孟泉 Tel: 010-88383907 E-mail: mengquan1982@gmail.com
Research on the Legalization Governance of Individual Labor Relations
Jiang Feng
(School of Labor and Human Resource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The rule of law of individual labor relation has made some achievements.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such as the legal definition of individual labor relations is not clear, the application to the typical labor relations and atypical labor relations is not standard and so on. In the process of revision of "labor contract law" and other laws, it’s necessary to further clarify the value orientation of labor protection and hierarchical employer classifcation for reconstruction of labor contract system, to perfect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part-time employment,and to share the Internet platform under the legal regulation of labor into the labor economy.
Individual Labor Relations; Legalization; Governance
江 峰,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