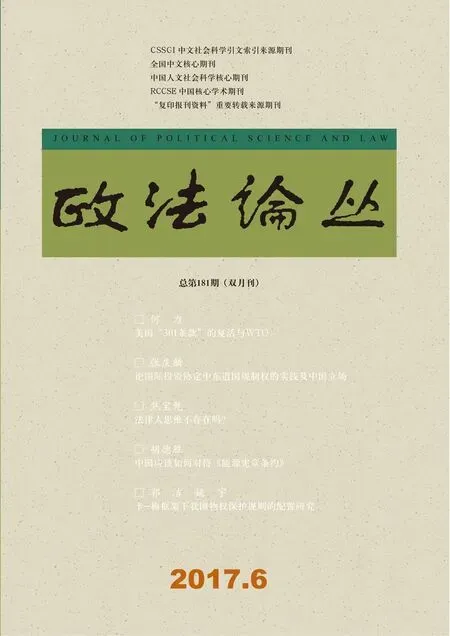中国应该如何对待《能源宪章条约》*
2017-01-26胡德胜
胡德胜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中国应该如何对待《能源宪章条约》*
胡德胜
(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陕西 西安 710049)
《能源宪章条约》体系是推动国际能源合作的重要国际法律工具。它存在着适用活动范围“能源部门的经济活动”缺乏边界,以及强制争端解决机制的核心国际仲裁机制缺乏公正保障的重大法律缺陷。这两项缺陷所导致的风险会由于地缘政治、缔约方之间或者投资者与作为东道方的缔约方之间的价值理念差异、仲裁机构(员)枉法等因素而变得更为扩大或者严重。中国不应该参加现行《能源宪章条约》,但是应该在审慎检视自己相关能源法律制度与其兼容性的基础上,推动其修改工作,而后决定是参加它还是继续作为观察员国。
能源宪章条约 适用活动范围 强制争端解决机制 地缘政治 价值理念
2015年5月20日至2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国家能源局局长努尔·白克力率团出席在海牙举行的国际能源宪章部长级会议,并代表中国签署了《国际能源宪章》。这是中国显示其积极参与国际能源合作①、努力提升其话语权和国际规则制定能力的一个重大事件。尽管国内学者此前就1991年《欧洲能源宪章》、1994年《能源宪章条约》以及中国是否应该参加这一条约有所研究,但是此后发声的学者却几乎都力主中国尽快参加现行《能源宪章条约》,并在其修改进程中增强中国的话语权和影响力。认真分析已有研究②,绝大多数缺乏对中国加入《能源宪章条约》利弊的全面、深入和理性分析,既没有立足应有的视角或者高度,也缺乏必要的审慎和推演。本文旨在以问题意识针对“中国应该尽快加入《能源宪章条约》”这一论断进行分析,通过“发现问题→提出问题→如何行动”的路径,就中国应该如何对待《能源宪章条约》这一问题进行研究,略述浅见。
一、中国参加现行《能源宪章条约》的风险:是否被严重淡化
(一)《能源宪章条约》的适用活动范围:明确还是模糊
人们通常认为,《能源宪章条约》致力于加强和推动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国家与企业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在能源部门③诸多环节和方面多层次、多维度的对话和合作,并为此提供一个具有法律拘束力的法律框架。仅从文字的表述上看,该条约的适用活动范围无疑是明确的,即,其第1条第5项界定的“能源部门的经济活动”:“任何一项涉及能源原材料和产品的勘探、萃取、精炼、生产、储存、陆路运输、输送、配送、贸易、营销或者销售的经济活动,或者任何一项涉及向多处房屋供暖的经济活动,但是附件NI中所包括的除外”。④与之有关的界定还有,如附件T《关于能源效率及相关环境影响的能源宪章协议书》第2条第4项。该项这样界定“能源周期(Energy Cycle)”:“整个能源链,包括各种形式能源的寻找、勘探、生产、转换、存储、运输、配送和消费活动,废弃物的处理与处置活动,以及这些活动的停止、中断或者结束,最小化它们有害环境影响的活动”。⑤
那么,条约第1条第5项规定的这一适用活动范围是否明确呢?从逻辑的角度审视,它并不十分明确。因为这基本上是概括性的表述,属于内涵上的界定,而且“concerning”、“related to”这类词语的使用更进一步决定了这一点。因而,需要列举式的外延界定作为补充。于是,便有了“关于第1条第5项的理解”,用7类活动予以举例说明“能源部门的经济活动”。⑥而且不难发现的是,“能源周期”的上述界定更进一步扩大了条约的适用活动范围。如果再加上某类经济活动的范围过大或者不明确,那么,该条约的适用活动范围将几乎是没有范围限制的。这里以投资活动为例进行讨论。根据该条约第1条第6项的规定,该条约适用于的投资是指“与能源部门的任何一项经济活动有联系的任何一项投资,或者一个缔约方在其区域内划定为投资或者投资级别的并且已经通知条约秘书处的‘宪章效率项目’”。而且,该项将投资宽泛地定义为“投资者直接或者间接拥有或者控制的各种资产”,并在列举了范围广泛的6类投资后规定“已投资资产形式的改变不影响它们作为投资的特性”。
可能会有学者认为,以投资活动这一个方面就断定条约的所有方面的适用范围都存在问题,似乎有以偏概全之嫌。然而,一方面,经济学常识告诉人们,投资是经济活动的开端和基础;(法律)逻辑上讲,如果将能源投资的范围界定宽泛而缺乏边界,其他方面的争端都可以“包装”为投资争端;另一方面,投资的定义问题也经常是国际投资仲裁实践中的关键争议问题之一。因此,非常明显的是,《能源宪章条约》的适用活动范围“能源部门的经济活动”缺乏边界,从法律技术上的视角可以视为似乎没有限制。不仅西方学者关于《能源宪章条约》项下争端解决机制所面临挑战的实证研究可以证明这一点[1],而且,下文提及的常设仲裁法院临时仲裁庭就尤科斯三个间接股东诉俄罗斯损害赔偿仲裁案所作出的裁决也可以充分证明这一点。完全可以说,投资的界定问题是影响《能源宪章条约》适用活动范围的关键性问题。
(二)《能源宪章条约》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能否确保公平
《能源宪章条约》将其所涉及的争端分为投资者与缔约方之间的争端以及缔约方之间的争端两大类。“多元化的争端解决机制”被认为是它“最引人注目的条约安排”[2]和基石[3]。但是,其强制争端解决机制能否确保公平,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严重疑存。
1.《能源宪章条约》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能源宪章条约》规定了分别适用于投资者与缔约方之间的以及缔约方之间的两大类强制争端解决机制。
关于投资者与缔约方之间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该条约第26条规定,如果这类争端在任何一方要求解决之日起3个月内未能解决的,投资者有权选择将争端提交以下机构之一进行解决:提交给涉及争端的缔约方(东道方)法院或者行政机构;根据任何可用的、先前同意的争端解决程序;根据条约的规定将争端提交仲裁。除可以做出保留的个别事项外,任何缔约方都必须无条件地同意将其与投资者之间的争端提交国际仲裁。投资者可以选择以下仲裁机构和程序中的任何之一进行仲裁(第26、27条):1)解决投资争端国际中心(ICSID)及其仲裁规则;如果投资者的母国和东道国之一为ICSID的缔约国时,应当根据ICSID的附加便利规则进行仲裁。2)根据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UNCITRAL)仲裁规则指定的独任仲裁员或成立的临时仲裁庭,并适用该仲裁规则进行仲裁。3)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及其仲裁规则。上述任何仲裁机构的仲裁裁决都是终局的,对双方均具有法律拘束力。⑦需要指出的是,《能源宪章条约》项下争端中的投资者有权向位于荷兰海牙的常设仲裁法院提出请求,请求其根据UNCITRAL仲裁规则指定独任仲裁员或成立临时仲裁庭,并适用该仲裁规则进行仲裁。
缔约方之间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又分为一般争端和特殊争端两类强制争端解决机制。在第26条规定的一般争端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项下,缔约方之间如果通过外交途径未能解决争端的,任何一方都有权将争端提交特设的仲裁机构。仲裁机构应当适用UNCITRAL仲裁规则,并根据《能源宪章条约》和国际法中可适用的原则和规则进行裁决。
对于特殊争端中的能源过境争端和贸易争端,《能源宪章条约》规定了强制争端解决机制;对于与环境和竞争有关的两类特殊能源争端,则没有规定强制争端解决机制。关于能源过境强制争端解决机制,第7条第7款规定,发生能源过境争端的缔约方未能自行解决它们之间争端的,任何一方都有权将争端提交给能源宪章大会(下称“宪章大会”)秘书长。秘书长向有关各方通报该争端,并在30日内与争端各方协商后任命一位调解人。该调解人应当有相关方面的经验,并且不是争端任何一方的公民或在争端任何一方没有固定居所。调解人应当努力促使争端各方达成协议。争端各方未能在90日内达成协议的,调解人应当对争端的解决办法或程序提出建议。此外,调解人还应当就有关能源过境的关税及其他条款和条件,做出临时性安排,直到争端解决为止;对于这种临时性安排,争端各方应当确保其管辖或者控制下的有关实体予以遵守。
关于能源贸易争端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能源宪章条约》规定了两种情形。1)争端双方都是世贸组织成员的,它们之间贸易争端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按照世贸组织的相关规定进行。2)争端一方或者双方不是世贸组织成员的,如果双方未能在60日内协商解决的或者不同意通过调解、斡旋、仲裁或其他方法解决的,任何一方都可以向秘书处申请成立一个专家小组。秘书处在收到申请的45日内组建专家小组。专家小组需要在其成立后的180日内完成全部程序,并提交一份包括事实陈述、争议观点概要、专家小组意见和结论在内的最终报告。最终报告在得到宪章大会缔约方简单多数支持后有效。如果缔约一方在一段合理的时间内没有遵守宪章大会采纳的最终报告,受损一方可以向不遵守一方递交书面申请,就有关补偿问题进行协商。如果双方未能在30日内达成一致,受损一方有权以书面形式请求宪章大会中止履行第5条或第29条中规定的它对不遵守一方的义务。如果不遵守一方就义务履行中止的程度向秘书长提交书面反对意见,可以由专门成立的仲裁小组对该反对意见进行仲裁。仲裁小组应当在成立后60日内提交书面决定。仲裁小组的决定自宪章大会通过之日起30日后成为最终决定并具有法律约束力,届时受损一方有权以适当的程度中止履行义务。
2.对《能源宪章条约》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的分析。进行文义分析,不难发现:第一,尽管《能源宪章条约》要求争端各方首先通过协商、斡旋等非司法裁决方式解决争端,但是它大都规定了以强制争端解决机制作为最后的程序;第二,它总体上推行的是多元化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允许缔约方保留的范围很小;第三,从法律技术上讲,缔约方之间的争端以及它所规定的不适用强制争端解决机制的与环境和竞争有关的两类特殊能源争端,是可能(通过“包装”性操作)转化为投资者与缔约方之间的争端的,从而适用强制争端解决机制;第四,国际仲裁是最主要的争端解决途径,而且仲裁规则必须是ICSID仲裁规则、UNCITRAL仲裁规则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三者中的一个。但存在的问题是:《能源宪章条约》规定的可选国际仲裁规则能否确保公平,特别是在仲裁程序和仲裁结果确有错误的情况下?国际仲裁的主流理论和一般做法是: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当事人各方均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必须无条件遵守和执行。但是,现代国际仲裁实践表明,仲裁裁决在程序和结果上发生错误的情况屡见不鲜,而且从根据《ICSID公约》第52条规定启动的仲裁裁决撤销程序结果来看,仲裁裁决在程序和结果上发生错误的比例并不低。
首先,最近两三年中有名的错误仲裁程序和结果错误事例可以证明这一点。事例一是中国和菲律宾之间的南海争端仲裁案。该案中,菲律宾关于成立仲裁庭对南海争端作出裁决的非法请求就是向常设仲裁法院提出的,而该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菲律宾的非法请求成立了非法的临时仲裁庭。在仲裁程序上,非法的临时仲裁庭置中国合法的关于管辖权或者管辖范围的抗辩于不顾,认可菲律宾“包装”的仲裁请求、裁决自己有权管辖。在仲裁结果上,非法的临时仲裁庭罔顾事实和法律,于2016年7月12日认定太平岛是“礁”、裁决菲律宾胜诉。事例二是尤科斯(OAO Yukos Oil Company)原来的三个间接股东⑧2005年2月诉俄罗斯的损害赔偿仲裁案是由该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能源宪章条约》的规定而成立的临时仲裁庭进行审理的。临时仲裁庭驳回了俄罗斯关于仲裁庭没有管辖权和/或争端不可受理性的3次抗辩。⑨临时仲裁庭于2014年7月18日裁决俄罗斯赔偿三位原告损失约500亿美元并承担原告承担或者支出的仲裁费用和律师等费用。⑩
其次,ICSID于2016年5月发布的《提交给ICSID行政理事会的关于仲裁裁决撤销问题的更新背景文件》中的统计数字可以证明这一点。根据该文件,截至2016年4月15日,ICSID共审结投资争端仲裁案件334起,登记撤销仲裁裁决申请90起,审结撤销仲裁裁决申请案件72起;审结的72起案件中,因未交纳费用而导致的撤销申请案件中途终止的数量6起,因申请人申请和未在规定时间内采取行动而导致的撤销申请案件中途终止的数量14起,驳回撤销申请案件的数量37起,撤销部分裁决案件的数量10起,撤销全部裁决案件的数量5起。[4]根据美国学者毕晓普和阿根廷学者马奇利对2012年以前案件[5]以及笔者对此后案件的初步观察:因未交纳费用而导致结案的6起撤销申请案件,主要是仲裁程序和裁决(基本)正确而申请人采取拖延策略的案件;因申请人申请而导致结案的6起撤销申请案件中途终止,主要是仲裁程序或者裁决结果确有错误而当事人达成和解的案件,因申请人未在规定时间内采取行动而导致结案的8起撤销申请案件中途终止,也主要是仲裁程序和裁决(基本)正确而申请人采取拖延策略的案件。可以发现:在审结的72起撤销仲裁裁决申请案件中,除去14起仲裁程序和裁决(基本)正确而申请人采取拖延策略的案件,撤销部分和全部裁决案件的数量达15起,占申请人实际上认为仲裁程序或者裁决结果确有错误的案件数量(58起)的25.86%;如果将主要是仲裁程序或者裁决结果确有错误而当事人达成和解的6起案件也视为撤销部分和全部裁决案件,比例则高达36.2%。
然而不容忽视的是,在《能源宪章条约》规定的可选国际仲裁规则中,除了《ICSID公约》第52条规定了针对仲裁程序和结果的救济手段之外,UNCITRAL仲裁规则和瑞典斯德哥尔摩商会仲裁院仲裁规则都没有就此作出规定。这样,一方面,在国际仲裁程序通常由私人投资者启动的情况下,作为争端对方的国家往往失去了选择国际仲裁机构和国际仲裁规则的权利,对作为争端一方的国家来说并不公平,特别是在涉及国家重大利益的情况下更为明显。另一方面,在仲裁程序或者裁决结果确有错误的情况下,由于缺乏救济程序,难以确保公平,特别是在涉及作为争端一方的国家重大利益的情况下。因此,作为《能源宪章条约》强制争端解决机制的核心国际仲裁机制不能确保公平;而这一点对于作为争端一方的国家来说又非常重要。
(三)参加现行《能源宪章条约》风险的进一步讨论
一个国家参加一项国际条约,期望获得据之行事而能够实现的预期法律后果应该成为参加该项条约的直接目的或者重要考量之一;而这对其他缔约方来说也才是公正的。所谓“约定必须遵守”才能体现其应有的正义价值。现行《能源宪章条约》规定和机制下的缺陷,决定了参加它具有相当大的风险。
首先,前述现行《能源宪章条约》在适用活动范围“能源部门的经济活动”方面缺乏边界、过于宽泛,乃至具有几乎没有范围限制的嫌疑,以及强制争端解决机制的核心国际仲裁机制不能确保公平这两大缺陷本身,就是参加它的重大风险。其次,如果它是一项框架性条约,而且没有规定强制争端解决机制或者允许缔约方在合理的范围内做出保留或者选择的话,那么,缔约方是可以对该条约所调整事宜或者行为的法律预期作出相对确定性的预判的。然而,《能源宪章条约》并不是一项框架性条约,不仅规定了强制争端解决机制,而且只允许缔约方就个别事项作出保留。所以,即使仅从法律上讲,缔约方是难以对该条约所调整事宜或者行为的法律预期作出相对确定性的预判的,存在着法律上的重大风险。最后,法律上的风险往往会由于其他风险因素的存在或者变化而变得更为扩大或者严重。其他因素主要有地缘政治、缔约方之间的或者投资者与作为东道方的缔约方之间的价值理念差异、仲裁机构或(员)因贪赃贪财或者受政治及本国利益而枉法。它们所导致的法律上风险的扩大或者严重,将在下一部分讨论。
二、中国参加现行《能源宪章条约》:是否应该
现代国际社会由政治之国家所组成,这是一个客观现实。包括国际条约在内的国际法是国家间政治和经济力量(暂时)平衡的结果,并会因政治和经济因素(特别是政治因素)而不时变化。国际关系学的创始人之一查尔斯·曼宁认为:国际关系理论需要处理国家主权、国际社会和国际法之间的关系,只有将它们一同使用才能理解国际关系问题的本质;国际法虽然应该是国际社会成员相互遵守的行为准则,但却不能是超越国家主权之上的法律。[6]如果国际政治因素发生重大变化,必然会对相关国际法以及相关国家或者国际法主体是否采取法律行动产生重要乃至决定性的影响。一个主权国家参加一项国际条约,意味着它放弃了一定范围内的或者一定程度上的主权或者主权权利;特别是在强制争端解决机制下,是让某种形式的第三方来行使该国所放弃的相关主权或者主权权利,乃至决定该国在某些方面的命运。因此,决定是否参加一项国际条约,一国需要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地对该项条约进行审慎的检视。对于是否应该参加《能源宪章条约》这一涉及国际能源法这门交叉学科的重大问题来说,更应该如此。“因为能源问题不仅涉及到能源工业本身,对于经济安全、社会分配、环境保护乃至国际关系都有着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利害关系,需要以跨学科的视角来研究”。[7]检视不能、也不应该仅仅是法律层面的,还必须立足本国国情、本国的潜在竞争国乃至敌对国、地缘政治等因素考虑国家安全这一生死存亡的根本问题,分析本国能够履行条约项下国际义务的条件、能力和可行性,并避免食言而肥、有损国际诚信的情况发生。在此,我们从预期结果确定性、地缘政治、价值理念以及仲裁机构(员)枉法这四个方面予以检视,讨论中国是否应该参加现行《能源宪章条约》。
(一)预期结果确定性方面
正常情形下,一个国家之所以缔结或者参加一项国际条约,是因为它想在不会严重损害其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获得各方履约所产生预期结果给它带来的利益。首先,如果一个主权国家大范围或者在不明确的范围内放弃其主权或者主权权利,一方面,政治和法律上就难以成其为主权国家;这是欧盟不少成员国(特别是西欧国家)的一些民众感觉本国没有或者缺乏主权的原因,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英国的脱离欧盟的公投结果。另一方面,该国可能也时常会受制于一些国家(特别是政治上、经济上不友好的国家),乃至将命运交由他人。其次,一国在决定是否成为某项国际条约的缔约国时,往往会考虑其缔约国身份所引起的或者产生的对涉外援助和投资、贸易以及国内政治支持等方面的可预期结果。[8]
国际实践告诉我们:第一,对于一个国家,特别是中国和俄罗斯这样的大国,因国际合作需要而暂时于一定程度上限制或放弃部分主权或者主权权利的,应当设定一个合理的期限(原则上最长不超过30年)并规定可以提前终止的情形,从而避免国家根本性利益遭受实质上的重大损害[9];否则,不参加有关国际条约才是可取的。第二,政治因素有时能够决定可以证明的法律事实的存在与否以及性质,国际法庭对于此类争端可能会、也确实已经作出并不公正或者并不适宜的裁判。[10]国际法院裁判的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之间的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项目案,常设仲裁法院建立的临时仲裁庭根据《能源宪章条约》所裁决的尤科斯原来三个间接股东诉俄罗斯损害赔偿案,我国参加《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及南海仲裁案裁决,其中的教训都需要我国有国家责任感的学者认真思考、负责任的官员注意吸取。就现行《能源宪章条约》而言,前已讨论,其适用活动范围和强制争端解决机制具有过分的宽泛性。如果中国贸然加入,将承担难以预测的巨大风险(如前所述),且这种过分宽泛性在法律上将给中国作为缔约方的行为预期后果带来很大的不确定性。
(二)地缘政治方面
西方学者的研究表明,一方面,来自地方的、国家的、区域的、国家间的和全球性的各个层面的政治压力,导致能源政策具有与其他领域不同的多维性和不可分割性[11];另一方面,地缘政治已经严重影响包括争端解决机制在内的《能源宪章条约》诸多法律机制的运转,导致其在一定程度上失灵,有时甚至严重失灵[12]。“大国的能源政策法律必然体现国际政治及国际政治关系”。[13]例如,俄罗斯的对外能源政策受追求地缘政治影响的政治目标的驱动而不仅仅是经济利益的驱动。[14]美国学者乌纳哈撒韦在其2005年的一项研究成果中认为,关于国家针对条约决策的理论,应该基于政治学和法学两个学科。[8]因此,在决定如何对待《能源宪章条约》时,必须考虑地缘政治因素的影响。分析《能源宪章条约》的现有缔约方,其主体和主导国家是以欧盟成员国为主的国家,日本也是缔约方之一。欧盟和北约两者的成员国基本重合,欧盟及其成员国地缘政治上受美国左右既是势所必然,也是客观现实。如果美国要求欧盟及其成员国采取对中国不利的法律行动,后者基本上会站在美国一方而非中国一方。已经发生的许多事例可以证明这一论断。例如,欧盟受美国左右于2014年开始制裁俄罗斯至今。再如,欧盟受美国之邀先后在世贸组织强制争端解决机制下对中国提起了三起类似的自然资源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件,即,中国铝土、焦炭、萤石、镁、锰、矽铁、矽化碳、黄磷和锌九种原材料产品出口限制措施一案(下称“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中国稀土、钨、钼相关产品出口一案(下称“稀土等产品出口案”),以及中国石墨、钴、铬、氧化镁、锑、铟等十一种原材料产品出口关税等限制措施一案(下称“石墨等产品出口案”)。前两起案件的裁决报告已分别于2012年2月22日、2014年8月29日通过,中国均在实质上败诉;第三起则是在2016年7月19日提起,在本文定稿时尚未结案。
(三)价值理念方面
欧盟和美国之间有着包括市场经济理念在内的共同(普世)价值观,而不是与中国之间。[15]中国必须承认自己与欧盟所奉行和推行的共同(普世)价值观之间存在着很大差异的客观现实。因此,在价值理念发生冲突时,欧盟及其成员国尊重和推行的必然是自己的、很多时候也是与美国共同的价值理念,而不是中国的;也是必然采取偏向或者遵从美国意愿的行动的。例如,在是否承认中国具有完全市场经济地位这一问题上,欧盟唯美国马首是瞻,至今也不承认中国具有完全市场经济地位。2016年5月12日,欧洲议会在一次投票中以546票赞同、28票反对的、实属罕见情形的压倒性多数通过了一项决议,认为中国仍不具备获得市场经济地位的资格,反对承认中国自动获得世贸组织下的市场经济地位。不仅如此,欧盟还准备在中国根据世贸组织规定于2016年年底取得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后,在法律上采取变相措施否定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当然,也必须看到的是,中国确实匮乏对市场经济有着全面和深刻理解的学者和官员,一定程度上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学者误国、官员败国”的现象。例如,美国和欧盟在2016年7月先后提起中国石墨等产品出口案后,一位来自某一部委研究机构的学者还在《人民日报(海外版)》上撰文,错误地认为中国的涉案做法符合市场经济规律、符合世贸组织规则。[16]而中国政府则在原材料出口限制措施案和稀土等产品出口案相继败诉后,除了消极地取消了相关限制措施外,不知所措。
(四)仲裁机构(员)枉法
现行《能源宪章条约》项下强制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仲裁类程序,存在着仲裁机构或者仲裁员因贪赃、贪财或者受政治及本国利益而枉法的重大可能性,而且由于一裁终局的法律效力让遭受不法仲裁程序和结果损害的国家缺乏有力的法律上的救济渠道。常设仲裁法院所成立临时仲裁庭作出的菲律宾所提南海争端案裁决以及尤科斯原来三个间接股东诉俄罗斯损害赔偿案裁决就是活生生的有力证明。或许,俄罗斯幸运的是,根据俄罗斯对尤科斯公司原来三个间接股东的起诉,荷兰的海牙地区法院认为仲裁庭没有管辖权,于2016年4月20日作出判决,撤销了常设仲裁法院临时仲裁庭关于俄罗斯赔偿后者约500亿美元的仲裁裁决。海牙地区法院认定临时仲裁庭没有管辖权的理由是:仲裁庭关于《能源宪章条约》第44条“生效”和第45条“临时适用”的解释,以及对《俄罗斯联邦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中涉及俄罗斯参加国际条约的决定权的规定,都存在错误或者曲解;《能源宪章条约》并没有对俄罗斯生效,临时适用条款对俄罗斯也不应当适用。但是,有关争议仍然没有划上句号;一是因为这三个间接股东可能向海牙上诉法院提起上诉,二是因为《能源宪章条约》秘书处的文件曾经解释一国国民成立的离岸公司对于该国而言也具有外国投资者的法律地位。而且,面对10多年来的以小讹大的法律纠纷,俄罗斯不得不花费本来不应该花费的巨大人力、物力、财力和精力,予以谨慎应对。
综上所述,现行《能源宪章条约》法律上适用活动范围过分宽泛性和强制争端解决机制缺乏公正保障的缺陷而导致的预期结果严重不确定性,及其与地缘政治、中国与其他缔约方(主要是欧盟及其成员国、日本)之间的或者作为东道方与投资者之间的价值理念差异、仲裁机构或(员)因贪赃贪财或者受政治及本国利益而枉法因素的叠加,将不可避免地给中国带来巨大的乃至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损害国家主权或者主权权利的风险。因此,中国不宜、也不应该参加现行《能源宪章条约》。
三、中国不参加现行《能源宪章条约》:应该如何行动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立场和观点来看,基于市场经济规律“这只看不见的手”而推动的经济某(些)领域的全球化,一直带动或者助推着政治、法律、文化、科技等领域或其某(些)部分的全球化。当代,以国际化表征的全球化已经发展到了质的程度;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既是一种趋势,在许多领域或者其某(些)部分也是一项现实。能源部门也是如此;能源市场经济行为的国际性日益增强、全球互动性影响不断增长,需要各国采取一定的行动维护国际能源市场或者对国际能源市场具有重大影响的某(些)国内能源市场的相对稳定。
受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社会发展规律的决定,世界范围内能源部门的法律需要一定程度的统一或者协调,出现了能源法律的全球化。能源法律的全球化,一方面表现为能源法律在国际或者区域层面的统一范围不断扩大,其体现是国际能源或者相关条约的增加;另一方面表现在,在目前条件下尚不能或者难以统一的能源法律领域,国家之间加强了协调,尽量避免或者减少国内能源法律之间适用上的冲突。
中国能源的客观现状和发展战略,决定了中国必须、也需要与《能源宪章条约》体系进行合作。首先,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能源生产国、消费国和进口国之一,也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无论愿意与否,都需要、也不得不融入能源部门的全球化之中。其次,中国能源革命战略的进行和完成需要国际合作的助推和支撑,能源合作是落实“一带一路”倡议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对于国际能源秩序的变革和国际能源新秩序的建立,国际法发挥着一定的促进、规范和保障作用。[17]中国能源产业的转型在国际与国内市场经济转型的压力下逐步开始[18];其发展也需要在国际合作的促进下发展。因此,不应该参加现行《能源宪章条约》并不是说中国就必须放弃该条约体系机制并与之一刀两断、分道扬镳;明智的决策应该是在审慎检视中国相关能源法律制度与现行《能源宪章条约》兼容性的基础上,推动对现行《能源宪章条约》的修改工作,如果修改后的《能源宪章条约》合适就参加它,如果不合适则继续作为观察员国与该条约体系进行合作。
(一)检视中国相关能源法律制度与现行《能源宪章条约》的兼容性
国际条约的履行,特别是经济贸易投资类国际条约的实施,需要缔约国国内法律执行机制的有效配合;也就是说,一个缔约国所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需要与其国内法具有兼容性。国外学者的研究表明,一国涉及某项国际条约的国内法律执行机制,是该国决定是否成为该项条约缔约国的关键影响因素。[8]检视中国相关能源法律制度与现行《能源宪章条约》的兼容性,应该是中国作出参加与否决策的必要程序。笔者认为,检视至少需要认真而有效地做好如下六个方面的工作:一是厘清现行《能源宪章条约》及其相关法律文件中每一条款的含义、实施情况以及相关讨论(特别是争议和已经发生的争端事例);二是发现现行《能源宪章条约》存在的缺陷或者问题;三是研究中国相关能源法律制度与现行《能源宪章条约》每一条款的兼容性;四是检视不兼容之处是由于中国相关能源法律制度的不合理原因还是由于现行《能源宪章条约》的不合理原因所导致;五是,如果不兼容是由于中国制度的不合理原因所导致,则应该讨论修改中国相关制度的可能性、方案及修改程度;六是,如果不兼容是由于现行《能源宪章条约》的原因所导致,则应该讨论修改现行《能源宪章条约》的可能性以及相应方案。
厘清每一条款的含义,需要从如下四个方面进行:它的形成过程、字面语义或者含义;宪章条约相关议定书和秘书处对它的解释;学者关于它的讨论和解释;以及,已经发生争端案件的,相关当事人(特别是缔约方),特别是宪章条约秘书处、调解人、专家小组、仲裁小组以及仲裁或其他裁决机构所作出的解释。而且,需要对每一条款是否具有确定性以及确定性的程度作出判断。
(二)推动对现行《能源宪章条约》的修改
基于对中国相关能源法律制度与现行《能源宪章条约》兼容性的认真而有效检视,推动对后者的修改工作可以分为两大步骤。第一步,列出对现行《能源宪章条约》需要进行修改、删除或者增加的条款,详细陈述理由,作为推动对它进行修改的中国方案。第二步,根据现行《能源宪章条约》体系的运转程序,提出修改它的中国方案,并参与到有关谈判和磋商过程和程序之中。修改方案和谈判中特别需要注意的方面是,克服现行《能源宪章条约》适用活动范围过于宽泛和强制争端解决机制缺乏公正保障这两项重大法律缺陷以及受地缘政治、价值理念和仲裁机构(员)枉法因素影响较大的问题。
(三)修改后的《能源宪章条约》:参加或不参加的后续行动
关于如何对待修改后的《能源宪章条约》,至少需要分两种情形作出不同决策。第一,如果修改后的《能源宪章条约》的规定在总体上或者其关键条款能够与中国现行或者修改后的相关能源制度相兼容的,中国可以考虑参加修改后的条约,并在参加后积极开展条约项下的国际能源合作。第二,如果修改后的《能源宪章条约》的规定在总体上或者关键条款不能与中国现行或者修改后的相关能源制度相兼容的,中国则不应该考虑参加修改后的条约,但是应该通过多种渠道(如作为观察员国参加活动)继续与该修改后的条约机制保持密切联系、开展合作。
(四)克服适用活动范围过于宽泛以及强制争端解决机制缺乏公正保障的框架建议
无论是解决现行《能源宪章条约》适用活动范围过于宽泛的缺陷,还是解决其现行强制争端解决机制缺乏公正保障的弊端,都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而且需要将这两个问题结合起来予以考虑解决。笔者提出的框架性建议:一是尽可能缩小并明确条约的适用活动范围,不将适用活动范围问题留给争端解决机构来解释或者解决。例如,将投资限定为直接投资,使作为东道国的缔约方能够增加对各方行为预期后果的确定性,尽量消除或者大幅度降低不友好或者敌对的国家或者组织对某一(些)缔约方实施阴谋的可能性;二是在宪章大会下建立类似于世贸组织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三是对于目前所有适用强制争端解决机制的争端,赋予缔约方选择前述类似于世贸组织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的权利,适用一种“专家小组起草初裁报告、征询争端各方意见、完成初裁报告→宪章大会决议”的程序,而且这种选择具有相对于其他选择的优先地位。换句话说,在争端一方选择其他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时,争端另一方有权否决而选择该类似于世贸组织的强制争端解决机制。这样可以避免出现类似于尤科斯原来三个间接股东诉俄罗斯损害赔偿案被常设仲裁法院和海牙地区法院两个不同的司法裁判机构基于相同的事实、适用同样的现行《能源宪章条约》却得出不同结论的荒谬现象,从而提高条约体系的确定性、权威性和可信性。
四、结语
“能源是生活之要、生产之基”;能源政策法律需要服务于国家安全、保障民生、生态环境以及经济健康这四项具有根本性的广泛的国家目标或者政策,尽管它们之间时有冲突。[19]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和能源体制革命四位一体的中国能源革命进程,在全球化的当代国际社会,离不开国际能源合作的助推和支撑。《能源宪章条约》倡导者的西欧国家在利用市场经济机制推动能源变革方面有着二百多年的丰富经验;源起于欧洲煤钢共同体,历经欧洲经济共同体、欧洲原子能共同体、欧洲共同体而产生的欧盟,有着包括能源部门在内的国际合作方面的丰富经验。作为正在力争圆满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中国来说,这些丰富的经验无疑是一笔可资借鉴和利用的巨大财富,特别是从经济和法律的角度来看。但是,国际关系特别是国际政治关系的发展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是经济还是法律领域的国际合作,都往往受到国际政治的强大而直接的影响。单纯地用法律视角考察、分析和研究国际问题以及提出解决方案都是有害的。能源部门也概莫能外。
一国负责任的政府决定该国是否应该缔结或者参加一项事关或者影响该国国家安全重要事项的国际条约,应该是一项基于科学研究的理性决策活动,学者和决策者都需要认真严谨地而不是沽名钓誉地对待和处理。“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战国策·赵策一》)中国先是贸然于1996年递交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批准书、10年后发现问题严重后又提交保留声明以致在南海有关领土主权和主权权利争端中处于国际法上不利地位的教训,不宜重演。因此,在是否应该参加《能源宪章条约》这一重大问题上,中国需要高质量地实施一项以能源事务问题为中心的,涉及国际法和中国法、(国际)经济、国际(地缘)政治以及管理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研究的基础是对现行《能源宪章条约》的每一条款及其整体性审慎地进行全方位、多层次和宽领域的检视,详细考察中国相关能源法律规定与条约现有规定或者修改后规定的兼容性。仅凭现行《能源宪章条约》存在着的适用活动范围缺乏边界和强制争端解决机制缺乏公正保障这两项重大法律缺陷,及其与地缘政治、价值理念差异、仲裁机构(员)枉法裁判因素叠加而不可避免地给中国带来的主权或者主权权利方面的巨大风险,中国就不应该参加现行《能源宪章条约》。但是,国际能源合作的需要,要求中国积极推动和有效参与《能源宪章条约》的修改工作,并在其修改后参加与否都在修改后的《能源宪章条约》体系机制下或者根据一般国际法积极开展后续的国际能源合作活动,与其他国家或者地区共同努力维护国际能源秩序的相对稳定,力求国际能源安全,践行生态文明理念,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注释:
① 对“国际能源合作”一词,人们通常有许多不同的理解或者界定;有模糊的,也有(相对)清晰的;有狭义的,中义的和广义的。模糊的定义,如“国际能源合作是指能源资源国与能源消费国以及能源中转国之间进行的能源交往”。(参见岳树梅:《中国参与国际能源合作的法律机制创新研究》,《河北法学》2009,4)。一般情况下,除非在“能源”前面加限定词或者通过其他方式予以限定,人们所说的“国际能源合作”通常涉及所有的能源活动领域或者环节。狭义的国际能源合作将主体仅限于主权国家,是指能源资源国与能源消费国之间、能源中转国之间以及能源资源国和/或能源消费国与能源中转国之间进行的能源合作活动。中义的国际能源合作将主体限于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或者某种形式的合作机制,是指国家之间、政府间国际组织或者某种形式的合作机制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进行的能源合作活动。广义的国际能源合作,其主体不仅包括主权国家、政府间国际组织或者某种形式的合作机制,而且包括企业和其他组织乃至个人,通常包括:1)国家之间、政府间国际组织或者某种形式的合作机制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它们与外国企业和其他组织之间进行的能源合作活动;和/或,2)企业或者其他组织所实施的跨越国境的能源合作活动。如无特别说明或者相反表示,本文在广义上使用“国际能源合作”一词。
② 2017年8月1日,笔者以“能源宪章”先后作为篇名和关键词在中国知网中文数据总库中进行模糊和精确检索,分别获得69篇和6篇文献。其中,两者之间有4篇重复,该69篇中有1篇无关文献。因此,有效文献数量为70篇。
③ 也有许多文献将“Energy Sector”翻译为“能源领域”。鉴于《能源宪章条约》使用的是“Energy Sector”而不是“Energy Field”,为了避免法律(术语)上的混淆,本文以“能源部门”作为“Energy Sector”的对应中文术语。此外,还有“Energy Industry”(能源产业)这一与“Energy Sector”意思相近、范围宽泛的术语。
④ 英文原文是:“Economic Activity in the Energy Sector” means an economic activity concerning the exploration, extraction, refining, production, storage, land transport, transmission, distribution, trade, marketing, or sale of Energy Materials and Products except those included in Annex NI, or concerning the distribution of heat to multiple premises。
⑤ 英文原文是:“Energy Cycle” means the entire energy chain, including activities related to prospecting for, exploration, production, conversion, storage, transport, distribution and consumption of the various forms of energy, and the treatment and disposal of wastes, as well as the decommissioning, cessation or closure of these activities, minimising harmful Environmental Impacts。
⑥ 这7类活动是:“(i)石油、天然气、煤炭和铀等的寻找、勘探和开采;(ii)发电设施(包括以风能和其他可再生能源作为动力的)的建设和运行;(iii)能源原材料料和产品的陆上运输、配送、储存和供应(例如,通过输电和配电电网、管道或专用铁路线等方式)以及为此目的设施建设(包括石油、天然气和煤浆管道等的铺设);(iv)移除和处置能源相关设施(例如,发电站)产生的废物(包括核电站产生的放射性废物);(v)能源相关设施(包括石油钻塔、炼油厂和发电厂)的退役;(vi)能源原材料和产品的营销、销售和贸易(例如,汽油的零售);以及(vii)与上述活动相关的研究、咨询、规划、管理和设计活动,包括那些旨在提高能源效率的此类活动。”(Final Act of the European Energy Charter Conference, Understanding 2.)
⑦ 但是,如果仲裁地法中作出了相反的强制性规定的,则在一方依仲裁地法提出反对程序的情况下,仲裁裁决不会自动产生终局的法律效力。例如,下文提及的尤科斯原来三个间接股东诉俄罗斯损害赔偿案,常设仲裁法院根据《能源宪章条约》的规定而成立的临时仲裁庭所作出的裁决,就因俄罗斯根据仲裁地法在海牙地区法院的起诉而没有自动产生终局的法律效力。
⑧ 这三个间接股东是胡勒公司(Hulley Enterprises Ltd.,1997年成立于塞浦路斯),尤科斯环球公司(Yukos Universal Ltd.,1997年成立于英属曼岛(Isle of Man),全资持有胡勒公司)以及石油老兵公司(Veteran Petroleum Ltd.,2001年成立于塞浦路斯,系尤科斯公司设立的养老基金)。
⑨ 俄罗斯的主要抗辩包括:(1)仲裁庭对案件所涉争端没有管辖权。理由是《能源宪章条约》对俄罗斯没有生效,其临时适用条款对俄罗斯也不发生效力。(2)退一步讲,即使仲裁庭有管辖权,案件所涉争端也不具有可受理性。主要理由包括案件争端涉及条约第21条的税收条款、第26条第3款b项i目的缔约方没有无条件同意条款、三个原告都是离岸公司并非俄罗斯的外国投资者因而不受《能源宪章条约》的保护,以及存在“不干净之手”和“非法和恶意行为”等。
⑩ 关于常设仲裁法院所设的由相同仲裁员所组成的三个仲裁庭就这三起案件所作出的三份最终仲裁裁决情况,分别请见常设仲裁法院案件号为AA226(Hulley)、AA227(YUL)和AA228 (VPL)的裁决书。Hulley Enterprises Limited v. Russian Federation, Interim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Russian Federation Russian Federation, PCA Case No. AA 226; Yukos Universal Limited v. Russian Federation, Interim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Russian Federation Russian Federation, PCA Case No. AA 227; Veteran Petroleum Limited v. Russian Federation, Interim Award on Jurisdiction and Admissibility, Russian Federation Russian Federation, PCA Case No. AA 228.
[1] Iuliana-Gabriela Iacob, Ramona-Elisabeta Cirlig.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 and settlement of disputes-current challenges [J]. Juridical Tribune, 2016, 1.
[2] 蒋新. 能源宪章条约之争端解决机制探析[J]. 求索,2012,7.
[3] 白中红. 《能源宪章条约》的争端解决机制研究[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1,3.
[4] ICSID. Updated Background Paper on Annulment for the Administrative Council of ICSID [R]. Washington D.C.: ICSID, 2016.
[5] R. Doak Bishop, Silvia M. Marchili. Annulment under the ICSID Conven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6] Suganami H. C. A. W. Manning and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J].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2001, 1.
[7] 马俊驹,龚向前. 论能源法的变革[J]. 中国法学,2007,3.
[8] Oona A.Hathaway. Between Power and Principle: An Integrated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 [J].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005, 2.
[9] 胡德胜.我国开发境内恒河流域的国际水法问题[J].青海社会科学, 2016,3.
[10] 胡德胜. 国际法庭在跨界水资源争端解决中的作用——以盖巴斯科夫-拉基玛洛项目案为例[J]. 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2.
[11] Steve Wood. Europe's Energy Politics [J].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European Studies, 2010,3.
[12] Arthur Rocco.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s Failure? The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Energy Security: within the European Union and beyond its Borders [J]. Eurolimes. 2013,15.
[13] 胡德胜. 大国能源政策的国际政治特性刍议[J]. 国际石油经济, 2014,10.
[14] Marek Hannibal. The power of energy politics [J]. European View, 2014,1.
[15] 外媒称多数美国及欧洲人互认拥有相同价值观(2012-09-17) [EB/OL]. http://www.chinanews.com/gj/2012/09-17/4189069.shtml, 2017-09-16.
[16] 梅新育. 美欧挑起贸易争端注定竹篮打水[N]. 人民日报海外版,2016-07-21(01).
[17] 杨泽伟.国际能源秩序的变革:国际法的作用与中国的角色定位[J].东方法学,2013,4.
[18] 肖国兴.能源发展转型与《能源法》的制度抉择[J].法学,2011,12.
[19] 胡德胜.论我国能源监管的架构——混合经济的视角[J].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2014,4.
HowShouldChinaDealwithTheEnergyCharterTreaty
HuDe-sheng
(Law School of Xi’an Jiaotong University, Xi’an Shaanxi 710049)
The Energy Charter Treaty system is one of important international legal instrument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energy cooperation. However, it has two major legal defects,i.e., a too wide scope of activities applied to (i.e., “Economic Activities in the Energy Sector”) without a definite delimitation, and insufficient assurance to a just result from all of its mandatory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s with international arbitration mechanism as core. The risks caused by them often expanse and/or become more serious due to existence of factors and/or elements of geopolitics, differences in value concept between contracting parties and/or an investor and a contracting party, arbitration institutions’ and arbitrators’ bending law. China therefore should not participate in it. However, China should, based on reviewing the compatibility between the treaty and China’s relevant energy legal system in a thorough and prudent way,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and amendment of the current Energy Charter Treaty; and if the amended one suitable, China should become its contracting party; if not, China should not do otherwise and continue to cooperate as an observer.
Energy Charter Treaty; mandatory dispute settlement mechanism; scope of activities applied to; geopolitics; value concept
1002—6274(2017)06—078—10
DF467
A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能源革命与法律制度创新研究”(15ZDB179)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胡德胜(1965-),男,河南卫辉人,哲学博士,西安交通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丝绸之路国际法与比较法研究所副所长,研究方向为国际法和比较法、环境资源和能源政策法律。致谢:作者曾在2016年8月中国能源法研究会年会作同题报告介绍主要观点,与杨泽伟教授和张利宾律师的讨论对完善本文有所帮助。
(责任编辑:唐艳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