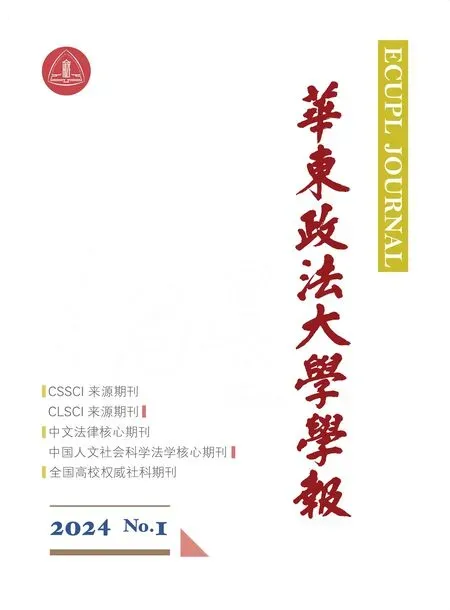“《大宪章》连续性神话”的知识考古
2024-04-10王栋
王 栋
目 次
一、1215 年《大宪章》:现代人的《大宪章》
二、1215 年《大宪章》在中世纪:被1225 年《大宪章》遮蔽
三、连续性神话的核心证据:“伪”1215 年《大宪章》
四、爱德华·柯克完善了“《大宪章》连续性神话”
五、神话未受挑战:《大宪章》正本在18 世纪的确证
六、修正版神话:辉格解释中的“《大宪章》连续性神话”
七、“《大宪章》连续性神话”的想象与真实
《大宪章》是历史最为长久的宪法性文件,一直以来被视为现代宪治和法治的渊源。但与此相伴,各个时代都有人斥责这种观点是神话。1659 年,律师威廉·科尔在小册子中称《大宪章》仅仅是男爵免于国王意志的自保,没有免除民众对男爵负有的义务。〔1〕See Arthur Lyon Cross, “An Unpopular Seventeenth-Century View of Magna Carta”, 29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4,74-76 (1923).1783 年,约翰·里夫斯的《英国法律史》批评了《大宪章》的混乱。1839 年宪章运动者罗伯特·欧文在狱中写作,称《大宪章》未考虑民众利益。〔2〕See Carl F.Brand, “An Early Nineteenth Century View of Magna Carta”, 32 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793, 793-794(1927).1904 年,甄克思在《〈大宪章〉的神话》一文中系统批评了《大宪章》神话,认为《大宪章》实质上是维护男爵利益,阻碍了法律改革和国家司法管辖权的形成。〔3〕See Edward Jenks, “The Myth of Magna Carta”, 4 Independent Review 260, 260-268 (1904).1947 年,美国学者马克斯·雷丁也认为将现代政治自由追溯到《大宪章》是过时的范式。〔4〕See Max Radin, “The Myth of Magna Carta”, 60 Harvard Law Review 1060, 1060-1063 (1947).1957 年,波考克的《古代宪法与封建法》进一步确认了《大宪章》的负面角色,认为《大宪章》是“古代宪法的神话”。〔5〕See J.G.A.Pocock, The Ancient Constitution and the Feudal Law: A Study of English Historical Thought in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4, 36, 56-57.
2015 年是《大宪章》问世800 周年,学者继续讨论《大宪章》神话问题。安东尼·阿利奇和伊戈尔·嘉吉合著了《〈大宪章〉揭秘》一书,致力于揭示《大宪章》的中世纪意义及此后的意义变迁。〔6〕See Anthony Arlidge & Igor Judge, Magna Carta Uncovered, Hart Publishing, 2014, p.2.史家彼得·科斯反思当下主义(présentisme)中的《大宪章》神话,揭示和拒斥神话与扭曲。〔7〕See Peter Coss, “Presentism and the ‘Myth’of Magna Carta”, 234 Past & Present 227, 227-235 (2017).有关当下主义的系统讨论,参见[法]弗朗索瓦·阿赫托戈:《历史性的体制:当下主义与时间经验》,黄艳红译,中信出版社2020 年版,第viii-xxxiii 页。美国法学家理查德·赫姆霍尔兹则更为综合,他在《重访〈大宪章〉神话》一文中,一方面承认1215 年没有陪审团审判和议会;另一方面试图从传统法理学的角度解释《大宪章》,阐释《大宪章》与现代世界的联系。〔8〕See Richard H.Helmholz, “The Myth of Magna Carta Revisited”, 94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1475, 1475-1493 (2016).
上述《大宪章》神话研究关注《大宪章》的起源与性质。相较于支持者认为《大宪章》是现代法治的起源;〔9〕See William Stubbs,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In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vol.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 p.532; David Carpenter, Magna Carta, Penguin Classics, 2015, p.460.批评者认为这是一种不符合历史却被确信的神圣叙事,《大宪章》是封建性的。故“《大宪章》神话”也可以称为“《大宪章》起源神话”或“《大宪章》现代性神话”。我国学者也参与了“《大宪章》起源神话”论争。整体上,我国法学界和政治学界更为强调《大宪章》的现代性,认为《大宪章》是现代法治的起源。〔10〕参见李红海:《他山之玉,何以攻石——论大宪章对中国的镜鉴意义》,载《比较法研究》2015 年第6 期,第174-183 页。历史学界更强调《大宪章》的封建性,认为其展现了丰富的权力意旨、强制性以及不平等性。〔11〕参见孟广林:《封建契约与中世纪英国王权》,载《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10 期,第141-154 页。此种论争之产生,既有史实之因由,也有立场与偏好不同。
本文无意讨论“《大宪章》起源神话”,而是聚焦学界少有讨论的《大宪章》连续性问题。《大宪章》有1215 年、1216 年、1217 年和1225 年四个版本,现代人所称的《大宪章》一般是指1215 年《大宪章》。长久以来,国内研究者极少关注《大宪章》的版本变迁。近来有研究者对版本问题进行了分析,但未深入展现《大宪章》的实质断裂。〔12〕参见王栋:《〈大宪章〉文本考:版本、正本、副本及译本》,载《法律科学(西北政法大学学报)》2020 年第3 期,第21-31 页。事实上,《大宪章》的修订和传播都产生了重要断裂。如研究者关注1215 年《大宪章》第12 章,认为该章确立了“税收法定”原则,〔13〕参见顾銮斋:《与英国史家论英国中古税制中的授予问题》,载《世界历史》2011 年第1 期,第128-137 页。但1216 年、1217 年和1225 年版本都删除了该章内容,在中世纪基本不为人所知。由此,学者需要重新评估《大宪章》在“税收法定”确立中的角色。
外国学者当然关注《大宪章》文本。如威廉·麦克奇尼的《大宪章:约翰王〈大宪章〉评论及其历史简介》一书曾梳理了1215 年《大宪章》的四份正本,〔14〕See William Sharp McKechnie, Magna Carta: Commentary on the Great Charter of King John, with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James Maclehose and Sons Pulishers to the University, 1914, pp.164-170.詹姆斯·霍尔特的《大宪章》也曾考察《未知特许状》《男爵法案》与《大宪章》的相互关系。〔15〕See Walter Ullmann, “Magna Carta by James Holt”, 53 The Catholic Historical Review 262, 262-264 (1967).事实上,随着1215 年《大宪章》正本的发现和校对,学者围绕1215 年《大宪章》正本之优劣产生诸多争论。1215 年《大宪章》现存4 份正本,即科顿第一份《大宪章》(亦称坎特伯雷《大宪章》)、科顿第二份《大宪章》、林肯《大宪章》以及索尔兹伯里《大宪章》,一般称为Ci、Cii、L、S。18 世纪布莱克斯通认为Ci 版本更好,19 世纪初档案委员会选择了L 版本。20 世纪初麦克奇尼认为L 版本修订少是因为后出,权威性弱,所以他选择了Cii 版本。〔16〕See William Sharp McKechnie, Magna Carta: Commentary on the Great Charter of King John, with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James Maclehose and Sons Pulishers to the University, 1914, pp.164-170, 185.
之后学者的争论仍在继续。其中比较重要的是约翰·福克斯在1924 年和亚瑟·柯林斯在1948年对四个正本优劣的讨论。〔17〕See John C.Fox, “The Originals of the Great Charter of 1215”, 39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321, 321-336 (1924); A.J.Collins, “The Documents of the Great Charter of 1215”, 34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233, 233-279(1948).不过这种争论被维维安·加尔布雷斯1948 年的文章所消解,他认为并不存在唯一权威的正本,相反它们具有相同的权威性。这一观点在五六十年代被克里斯托弗·切尼、威尔弗雷德·沃伦以及戈弗雷·戴维斯等人接受,并为霍尔特所继承。〔18〕See James Holt, Magna Cart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373-374.之后的学者不再讨论四正本何者更权威,而是各自选择版本,如戴维斯和霍尔特选择了Cii 版本,而大卫·卡朋特则选择了L 版本。〔19〕See G.R.C.Davis, Magna Carta,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 Limited, 1977, pp.23-33; James Holt, Magna Cart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378-397; David Carpenter, Magna Carta, Penguin Classics, 2015, pp.36-69.值得注意的是,自布莱克斯通采用数字分章后,卡朋特第一次在著作中标注了《大宪章》正本自带的章节划分,这为研究者重新梳理《大宪章》提供了启发。
总体上,正本的选择体现出学者的不同偏好。S 正本字体和内容与其他正本差异相对较大,理所当然不是第一选择。Ci 正本无法识读只留版画,自布莱克斯通之后难为学者所用。Cii 版本为斯塔布斯、麦克奇尼和霍尔特系统研究,成为《大宪章》的核心文本。在此学术背景下,卡朋特深入研究林肯《大宪章》提供了新路径。克莱尔·布里和朱利安·哈里森主编的《〈大宪章〉:法律、自由和遗产》对相关正本进行了简介。〔20〕See Claire Breay & Julian Harrison eds., Magna Carta: Law, Liberty, Legacy, The British Library, 2015, p.5.尼古拉斯·文森特的《〈大宪章〉:起源与遗产》收录了已有的《大宪章》正本,包括2014 年才被发现的桑威奇《大宪章》正本,总体上颇具创见。〔21〕See Nicholas Vincent, Magna Carta: Origins and Legacy, The Bodleian Library, 2015, pp.204-256.概言之,这些专著对《大宪章》文本的研究各有侧重,但或者无意于作整体性的介绍,或者失之于简。
学术研究是人们观察世界、理解世界和产生知识的科学方式,不同学科赋予人们不同审读视域、研究理路和解释框架,知识考古是研究方法的一种。福柯所谓的知识考古既指向知识的结构(知识型),也指向知识作为权力技术的实践和功能。福柯指出话语具有偶然性、不连续性和物质性。知识考古关注话语本身,试图重新分析和激活局部知识或次要知识。〔22〕知识(scientia)本意是“知道的事”。在福柯看来,知识既不受制于人的意志或理性,又不是对“客观现实”的真理性认识。知识是话语隐秘争夺后的产物。刘北成:《福柯的思想肖像》,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 年版,第154-155,238 页;Michel Foucault,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translated by A.M.Sheridan Smith, Routledge, 2002, pp.221-223.本文试图对“《大宪章》连续性神话”进行知识考古,发掘《大宪章》文本和话语的偶然性、不连续性和物质性,展现《大宪章》发展中的重要断裂,并为重估《大宪章》的影响作准备。
一、1215 年《大宪章》:现代人的《大宪章》
首先,需要明确1215 年《大宪章》具有政府文件性质。《大宪章》之名直到1218 年才出现,1215年《大宪章》只是约翰颁布的一份特许状(或称为宪章)。〔23〕“carta”(charter)在中文世界有“特许状”和“宪章”两种对译,大体上特许状是中世纪文件的特征,宪章是近代的理解。本文依据语境使用两种对译,当然“大宪章”的对译是固定的。中世纪英国的文秘署分发三种文件,分别是特许状、开封函令以及密封函令,特许状是最重要的文件,一般用于永久性授予土地或权利。《大宪章》是特许状,源于其结尾:“由我们亲手给予,在温莎和斯坦斯之间,名为兰尼米德的草地上,于我们统治的第17 年的6 月15 日。”(Data per manum nostram in prato quod vocatur Ronimed inter Windlesoram et Stanes, quinto decimo die junii, anno regni nostri decimo septimo.)〔24〕三个常见的拉丁语—英文对照译本,参考G.R.C.Davis, Magna Carta, British Museum Publication Limited, 1977, pp.23-33; James Holt, Magna Cart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378-397; David Carpenter, Magna Carta, Penguin Classics, 2015, pp.36-69.“亲手给予”(data per manum)是王室特许状的程式用语,用以表明何时、何地由何人给予最后文本以法律效力。其中特许状的日期条款是理查一世时引入的。虽然特许状本质上是国王授权,但特许状记载的授予者多为御前大臣或其他文秘署官员,偶尔才是国王亲自给出。如在1215 年上半年(6 月15 日之前)御前大臣理查德·马什和他的副手拉尔夫·德·内维尔分别在10 个不同的地点给予了特许状。《大宪章》是约翰在1215 年唯一亲手给予的特许状。《大宪章》的另一个特殊之处是建议者不是作为证人出现在特许状末尾,而是出现在序言中。
特许状一般分为正本(engrossment)和副本(copy)。正本是一份权威的原始文件,区别于后来的副本。正本有法律效力,而副本没有。一般而言,正本有两个特征,一个是由文书正式写就(engross),因而成为一份正式合法的记录;〔25〕See Nicholas Vincent, Magna Carta: Origins and Legacy, The Bodleian Library, 2015, pp.187-198.另一个是加盖国玺。学界通过上述两个标准,确定了1215 年《大宪章》有四份正本。其一,《大宪章》由专业文书正式写就。就正本字体而言,Ci、Cii 和L 三份正本基本是一致的,是飘逸流畅的草写体(cursive),而S 版本的字体是书本体(bookish)。卡朋特从字体判断,认为前三份《大宪章》是约翰王文秘署书写文书时的典型字体,最后一份大概是外来教士帮助书写的。〔26〕See David Carpenter, Magna Carta, Penguin Classics, 2015, pp.11-12, 373-379.2015 年的“《大宪章》研究项目”比较了主教文书与《大宪章》的字迹,认为Ci、Cii 是文秘署写作的,而L 和S 正本是教会文书书写的。《大宪章》写在羊皮纸上,使用鞣酸铁墨水(iron gall ink),正本的羊皮纸和墨水品质都很高,也体现了《大宪章》的重要性。其二,《大宪章》加盖了国玺,这也是“亲手给予”的证明。
二、1215 年《大宪章》在中世纪:被1225 年《大宪章》遮蔽
不同于现代习惯,约翰王1215 年特许状在中世纪未被称为《大宪章》,而是被叫作“《兰尼米德特许状》”。“大宪章”一名直到1218 年2 月才出现,指的是亨利三世于1217 年制定的“长特许状”。亨利三世于1216 年颁布特许状(即1216 年《大宪章》),1217 年亨利三世颁行了特许状的修订版(即1217 年《大宪章》),并将之前特许状中涉及王室森林区管理的条文单独制定为《森林区特许状》。为了执行1217 年的两个特许状(即1217 年《大宪章》和1217 年《森林区特许状》),1218 年2 月,亨利三世命令郡长将两份特许状颁行全国并贯彻执行。颁布命令的令状中产生了“大宪章”一词。“大宪章”一名直到爱德华一世时期才完全确立,但指向的是亨利三世1225 年颁布的《大宪章》。
故此,约翰王1215 年特许状(即1215 年《大宪章》)在13 世纪一般被称为“兰尼米德特许状”(the charter of Runnymede)、“兰尼米德条例”(the provisions of Runnymede)、“兰尼米德的约翰王特许状”或者“兰尼米德”。也因此《兰尼米德特许状》会和1225 年《大宪章》一起登记在制定法汇编以及契据册(cartulary)中。〔27〕See David Carpenter, Magna Carta, Penguin Classics, 2015, pp.6-7, 433-434.摄政威廉·马歇尔当然记得1215 年特许状与1216 年特许状之间的联系。1217 年2 月马歇尔将1216 年《大宪章》副本送达爱尔兰,附随的函令中记载“我们和我们的父亲授予的特权”,显然记得亨利三世1216 年特许状与1215 年约翰王特许状的联系。〔28〕See James Holt, Magna Cart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28.但是之后这种连续性日趋减弱并逐渐被遗忘。
《兰尼米德特许状》与《大宪章》的并立很早就已形成。1231 年牛津郡的一个陪审团认为郡长巡回治安法庭(sheriあ’s tourns)规定在《兰尼米德特许状》中,尽管该内容首次出现是在1217 年《大宪章》中。〔29〕See James Holt, Magna Cart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328.当然在非常偶然的例子中,约翰王特许状也会被称为《大宪章》。在1290 年的莫蒂默诉托尼案(Mortimer v.Tony)中,莫蒂默引用的就是“来自兰尼米德的约翰王的《大宪章》”(magna carta Johannis Regis de Ronemede)的第56 章。他据此主张赫里福德郡的法官对涉及威尔士边区的案件没有管辖权。〔30〕See John Baker, The Reinvention of Magna Carta, 1216-161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4.汤普森也记录了该案,不过记录的是1291 年。See Faith Thompson, The First Century of Magna Carta: Why It Persisted as a Document, Russell & Russell, 1976,p.65.
《兰尼米德特许状》并非制定法,也没有出现在《制定法卷宗》中,因此几乎无人见到其文本。到17 世纪初,爱德华·柯克爵士仍未见过《兰尼米德特许状》正本。在中世纪文献中,《兰尼米德特许状》也很少被讨论。它一般被视作和平条约,而非制定法。15 世纪早期,律师会馆讲稿中的“标准评注”(Glossa Ordinaria)仍强调《兰尼米德特许状》只是条约。〔31〕See John Baker ed., Selected Readings and Commentaries on Magna Carta 1400-1604, Selden Society, 2015, p.xxxix.《兰尼米德特许状》因此既未见诸《诉讼卷宗》和《年鉴》,也为律师群体所忽略。不过仍偶尔有人援引,如1506 年理查德·海斯凯茨(Richard Hesketh)在格雷律师会馆的演讲中讨论森林区法律问题,认为森林区侵害规定在“约翰王的《兰尼米德特许状》”(le chartre de Runne Mead)中。〔32〕See John Baker ed., Selected Readings and Commentaries on Magna Carta 1400-1604, Seldon Society, 2015, p.362.
因此在法律人群体中,1215 年约翰王特许状与《大宪章》(即1225 年《大宪章》)极少混淆。约翰·贝克考证了大量会馆讲稿,只发现两位16 世纪的讲诵师(reader)错误地认为,约翰王特许状成为后来制定法中的《大宪章》。一位错误地认为,1215 年《大宪章》被爱德华一世确认为《大宪章》;另一位错误地认为,1215 年《大宪章》在马尔伯勒被确认为制定法。二人显然混淆了1215 年《大宪章》和1225 年《大宪章》,爱德华一世和马尔伯勒确认的《大宪章》都是1225 年《大宪章》。这两位讲诵师应并未见过1215 年《大宪章》。〔33〕See John Baker, The Reinvention of Magna Carta, 1216-161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3.
在没有印刷术的时代,许多《大宪章》抄本混合了不同版本的《大宪章》,故此1215 年《大宪章》常会被“误引”。鲍德温·马利特1512 年的演讲提到了《大宪章》中的“如果任何自由人无遗嘱死亡”(si quis liber homo intestatus decesserit)内容。该句实际上只存在于1215 年《大宪章》第27 章中,从未进入制定法汇编,但马利特却认为该句是制定法。〔34〕See John Baker ed., Selected Readings and Commentaries on Magna Carta 1400-1604, Seldon Society, 2015, p.210.因此,应当推测马利特没有读过1215 年《大宪章》正本,而是读了杂糅1215 年《大宪章》字句的1225 年《大宪章》手稿。
总体上,直到16 世纪中叶,《大宪章》指的仍是1225 年《大宪章》,是法律人关注的制定法。而1215 年《大宪章》只是一份和平条约,其文本少为人见,也几乎未被法律人研究。在“《大宪章》连续性神话”中,1215 年《大宪章》通过1225 年《大宪章》在中世纪产生了全面持续的影响。但实际上,这种1215 年《大宪章》的持续性被严重高估了。其一,1215 年《大宪章》与1225 年《大宪章》缺乏连续性,1215 年《大宪章》作为《兰尼米德特许状》是与《大宪章》并立的。其二,1215 年《大宪章》的影响被高估了。1215 年《大宪章》第12 章并没有保留在1225 年《大宪章》中,学者难以证明该章对中世纪后期(尤其是14 世纪之后)的“税收法定”的切实影响。1215 年《大宪章》的第61 章也是同样情形,该章也没有保留在1225 年《大宪章》中,“25 名男爵委员会”可能未对中古英国政治产生结构性影响。
三、连续性神话的核心证据:“伪”1215 年《大宪章》
自13 世纪中叶,《大宪章》就被普遍认为是亨利三世1225 年颁布的《大宪章》,不存在约翰王《大宪章》。尽管律师会馆的讲诵师一般会注意到《大宪章》起初是由约翰王授予的,不过他们也会立即解释直到亨利三世时期该《大宪章》才成为制定法。约翰·贝克认为,这些讲诵师大概是从编年史家那里知晓了“约翰王特许状”,但并没有看到原件,一般不知晓“约翰王特许状”与1225 年《大宪章》的不同。〔35〕See John Baker, The Reinvention of Magna Carta, 1216-161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4.值得注意的是,现代研究者常常低估了都铎时期对“约翰王特许状”的了解。威廉·弗利特伍德在16 世纪50 年代的著作就记录了约翰王及其特许状的故事,认为即使对历史一无所知的人也知晓该故事。
“约翰王特许状”在13 世纪初流传甚广,但之后流传日趋减衰。根据“《大宪章》项目”的统计,1215 年《大宪章》有34 份副本以及2 份法语译本。34 份副本中1 份来自《财政署红皮书》,3 份在伦敦的《习惯书》(Liber Custumarum)中,20 份在大小修道院中或者在大教堂契据保管处和编年史中,7份在制定法书籍中。最后7 份中的2 份以《兰尼米德特许状》开头,不过内容分别是1225 年《大宪章》文本,以及1225 年《大宪章》和1217 年《大宪章》的混编本。〔36〕See David J.Seipp, “Magna Carta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Over-Mighty Subjects, Under-Mighty Kings, and a Turn Away from Trial by Jury”, 25 William and Mary Bill of Rights Journal 665, 668-669 (2016).“约翰王特许状”被认为是普通和平条约,相关副本并未引起中世纪人的注意。又因为中世纪手抄本内容往往各异,当时人习惯于接受这种差异,故未对“约翰王特许状”和《大宪章》进行系统比较。
1571 年,温多弗的罗杰编辑的“约翰王特许状”(下文亦称“‘伪’1215 年《大宪章》”)印刷出版,这深刻形塑了17 世纪学者对《大宪章》的理解。温多弗的罗杰(死于1236 年)来自白金汉郡,是奥尔本斯修道院的教士,也是13 世纪著名的编年史学家。〔37〕刘城:《西方中世纪编年史的代表作:〈历史之花朵〉》,载《光明日报》2019 年3 月18 日,第14 版。罗杰认为1215 年《大宪章》和1225 年《大宪章》内容相同。〔38〕See David Carpenter, Magna Carta, Penguin Classics, 2015, p.424.罗杰最著名的编年史是《温多弗的罗杰之书,名为历史之花,始自盎格鲁国王亨利二世第一年1154 年》(Rogeri de Wendover liber qui dicitur Flores Historiarum ab anno domini MCLIV annoque Henrici Anglorum Regis Secundi Primo)一书。该书汇编多份材料,如同采撷鲜花,故被称为《历史之花》(Flores Historiarum)。〔39〕See Roger of Wendover, Liber Qui Dicitur Flores Historiarum AB Anno Domini MCLIV Annoque Henrici Anglorum Regis Secundi Primo, vol.2, edited by Henry G.Hewlet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2, pp.119-134.不过《历史之花》中1214年之前的内容来自奥尔本斯修道院的修士约翰·德·塞拉(John de Cella,死于1214 年),该人也被称为瓦林福德的约翰(John of Wallingford)。《历史之花》流传甚广,这本书虽然记载了亨利三世在13 世纪50 年代对《大宪章》的确认,但并没有明确提及约翰王《大宪章》,也没有提供《大宪章》的文本。〔40〕See David Carpenter, Magna Carta, Penguin Classics, 2015, p.7.
1236 年罗杰去世,奥尔本斯修道院的修士马修·帕里斯接替罗杰修撰编年史。马修·帕里斯写作了《大编年史》(Chronica Majora)一书,1235 年之前的内容主要采用了罗杰的材料。《大编年史》采用了罗杰编撰的1215 年、1217 年和1225 年《大宪章》混合而成的文本,并称其为“授予男爵共同特权的约翰王特许状”(Carta regis Johannis de communibus libertatibus baronibus concessis)。〔41〕See Mathew Paris, Matthaei Parisiensis, Monachi Sancti Albani Chronica Majora, edited by H.R.Luard, vol.2, Longman &Co., etc., 1874, pp.589-606.该“约翰王特许状”由三个版本的《大宪章》杂糅而成:第一部分是1215 年《大宪章》的序言和第一章,其后的内容是1217 年和1225 年《大宪章》中的部分章节;第二部分是1217 年《森林区特许状》和1225 年《森林区特许状》的混合本,这也被误归于约翰王;最后一部分是1215 年《大宪章》的担保章节(不过内容有所不同)。〔42〕See James Holt, “The St.Albans Chroniclers and Magna Carta”, 14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67, 67-68(1964).“伪”1215 年《大宪章》大约经历了温多弗和帕里斯两人的修订。首先,温多弗版本《大宪章》是在1225 年之后不久整理的,以约翰之名发布,混合了1215 年、1217 年和1225 年特许状。同时温多弗还编造了一份约翰授予的《森林区特许状》。之后帕里斯虽然获得了1215 年《大宪章》的真实抄本,但并未意识到上述文本的问题,而是进一步修正,形成了上述杂糅的“约翰《大宪章》”。帕里斯进而将1225 年《大宪章》称为“亨利三世宣誓维护的约翰王《大宪章》”。王栋:《〈大宪章〉的多重历史书写及其重构:以约翰王形象为中心》,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21 年第6 期,第83-84 页。因为中世纪手稿传播有限,该“约翰王特许状”并没有太大的影响。
伊丽莎白一世时期,坎特伯雷大主教马修·帕克(于1559—1575 年任职)起意建设图书馆并收集了大量中世纪手稿,以反对教皇权威,维护伊丽莎白一世的宗教改革。帕克发现国务大臣威廉·塞西尔收藏的《大编年史》有反教皇倾向,〔43〕See John Baker, The Reinvention of Magna Carta, 1216-161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270.不过特纳错误地认为手稿全部来自塞西尔,实际上塞西尔的手稿止于1208 年。便着力推动手稿在1571 年出版。〔44〕See Ralph V.Turner, Magna Carta: Through the Ages, Pearson Education, 2003, p.139.《大编年史》风靡近60年,影响深远,其记载的“约翰王特许状”也广为传播。16 世纪末到18 世纪中期,当时人一般认为该“约翰王特许状”就是约翰1215 年颁布的特许状,并在文本比较中进一步确认1225 年《大宪章》来自该“约翰王特许状”。该“约翰王特许状”因此也开始被称为“《大宪章》”。该“伪”1215 年《大宪章》被迅速接受,风靡近60 年,成为“《大宪章》连续性神话”的核心证据。
概言之,罗杰和帕里斯先后汇编了“约翰王特许状”,并记载在《大编年史》中,不过该文本在中世纪影响有限。17 世纪下半叶,该“伪”1215 年《大宪章》印刷出版,广泛传播,逐渐被认为与1225 年《大宪章》相同,并被确认为“1215 年《大宪章》”的权威文本。“伪”1215 年《大宪章》成为“《大宪章》连续性神话”的核心证据。1225 年《大宪章》因此被理解为是1215 年《大宪章》的承继,1215 年《大宪章》的重要性和历史影响也由是被夸大。对于该“伪”1215 年《大宪章》,相较于之前研究者(如菲茨·汤普森、霍尔特、沃伦和拉尔夫·特纳)对编年史家的批评,〔45〕See Faith Thompson, Magna Carta: Its Role in 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1300-1629, A Division of Farrar, Straus& Giroux, 1978, pp.1-5; James Holt, “The St Albans Chroniclers and Magna Carta”, 14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 67,69 (1964); W.L.Warren, King John, Eyre Methuen, 1978, pp.23-31; John Gillingham, “The Anonymous of Béthune, King John and Magna Carta”, in Janet S.Loengard ed., Magna Carta and the England of King John, The Boydell Press, 2015, p.27.当代学者(如苏珊·雷诺兹)开始更能理解编年史家面临众多抄本的困境。毕竟该“伪”1215 年《大宪章》并不比同时代很多制定法汇编中的文本差,甚至不比财政署的官方文件差。对制定法汇编者和编年史家来说,最重要的不是字句不差丝毫,而是主旨准确。〔46〕See Susan Reynolds, “Magna Carta 1297 and the Legal Use of Literacy”, 62 Historical Research 233, 241(1989).
只有在上述背景下,才能明白16、17 世纪的学者、政治家以及民众对《大宪章》的新理解。在中世纪,法律人一般认为《大宪章》就是1225 年《大宪章》,而“约翰王特许状”是《兰尼米德特许状》,不存在约翰王《大宪章》。但是随着1571 年帕里斯《大编年史》的出版,罗杰和帕里斯混合的“伪”1215年《大宪章》成为《大宪章》的重要来源。又因为“伪”1215 年《大宪章》本身混合了1217 年《大宪章》和1225 年《大宪章》,所以当时人认为1225 年《大宪章》继受了约翰王《大宪章》的主要内容。因此,16 世纪末期,原有的《兰尼米德特许状》被改称为约翰《大宪章》,将亨利三世1225 年《大宪章》追溯到约翰王1215 年《大宪章》。〔47〕虽然1629 年科顿发现了1215 年《大宪章》正本,但鉴于当时文本众多,缺乏研究,“伪”1215 年《大宪章》长久以来未受到有效挑战。
四、爱德华·柯克完善了“《大宪章》连续性神话”
16 世纪晚期,《兰尼米德特许状》已经被确立“《大宪章》”,并与1225 年《大宪章》紧密联系在一起。爱德华·柯克的研究和解释进一步完善了“《大宪章》连续性神话”。柯克早在1628 年出版的《英国法要义》(第一卷)中就注意到了某个法令中的“《大宪章》制定法”(statute of Magna Carta),认为这是约翰《大宪章》。〔48〕See John Baker, The Reinvention of Magna Carta, 1216-161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532.贝克指出柯克此处的日期不正确,这实际上是亨利三世最后时期的事情。他在《英国法要义》(第二卷)中进一步认为:“约翰王在其统治的第17 年曾批准过类似的特许状,后者也被称为《大宪章》(Magna Carta),在亨利三世《大宪章》(Great Charter)之前的一份档案中记录了。”〔49〕Edward Coke, The Se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Sir Edward Coke, vol.2, edited by Steve Sheppard, Liberty Fund, 2003,p.160.柯克此处添加的引注就是马修·帕里斯的著作。显然柯克接受了帕里斯的记载,认为“伪”1215 年《大宪章》就是“1215 年《大宪章》”,1225 年《大宪章》缘起于该“1215 年《大宪章》”,并与后者类似。柯克认为,“它(1225 年《大宪章》)大部分是英格兰基本法主要基础的宣告,剩余部分则弥补了普通法中的一些不足。”〔50〕Edward Coke, The Se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Sir Edward Coke, vol.2, edited by Steve Sheppard, Liberty Fund, 2003,pp.159-161.这是柯克对《大宪章》最为根本的观点,即乔治·加内特所称的“法律延续性现存最早的书面化身”。〔51〕George Garnett, “‘The Ould Fields’: Law and History in the Prefaces to Sir Edward Coke’s Reports”, 34 The Journal of Legal History 245, 283 (2013).
柯克进而在《英国法要义》中具体比较了“伪”1215 年《大宪章》和1225 年《大宪章》,申明了两者在形式和内容上的联系。在内容上,柯克证明1225 年《大宪章》和《森林区特许状》的序言和内容出现在1215 年《大宪章》中,其中最主要的部分是古代法律和王国习惯。在形式上,柯克强调1225年《大宪章》和1215 年《大宪章》一样,用“我们已让与”(concessimus)这种复数形式,而之前的国王采用第一人称单数形式。〔52〕See Edward Coke, The Se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Sir Edward Coke, vol.2, edited by Steve Sheppard, Liberty Fund,2003, pp.165-166.柯克还指出1225 年《大宪章》吸收了1215 年《大宪章》的教训:因为约翰王假装自己被强迫来撤销1215 年《大宪章》,所以1225 年《大宪章》添加了“Our Meer and Free Will”(我们纯粹自由的意志),〔53〕拉丁文原文为spontanea et bona voluntate nostra,意为“自由地和出于我们的善意的”。See James Holt, Magna Cart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420.以躲避约翰王的诡计。显然,柯克对于《大宪章》制定的历史有较为深入的了解。〔54〕See C.R.Cheney & W.H.Semple eds., Selected Letters of Pope Innocent III Concerning England, Thomas Nelson and Sons,1953, pp.212-216.
柯克最关键的影响是,复活了1215 年《大宪章》的第12 章。该章事实上在1215 之后的《大宪章》中删除了。柯克基于“伪”1215 年《大宪章》,认为爱德华一世时期的《大宪章》范本遗漏了“非经王国的共同建议,不得在我们的王国内征收免服兵役税和协助金”一句,该句实际上应在1225 年《大宪章》第8 章之后。柯克进而通过对1225 年《大宪章》第30 章的解释,以及《不经同意不得征收任意税法》(De tallagio non concedendo)的佐证,阐明1225 年《大宪章》第8 章遗漏的规定是“共同同意批准的补助金或关税”,即“为了公共利益通过议会权威批准的”税收。通过此种考辨和解释,柯克复活了1215年《大宪章》第12 章,将被删掉的第12 章补充进1225 年《大宪章》,进而确证了议会的征税权,即未经议会同意不得征税。〔55〕See Edward Coke, The Selected Writings and Speeches of Sir Edward Coke, vol.2, edited by Steve Sheppard, Liberty Fund,2003, pp.189, 235-237.曾经在13 世纪产生巨大影响的1215 年《大宪章》第12 章,通过帕里斯的混编文本以及柯克的考证解释,重新进入17 世纪的宪制论争中,确认了议会的征税权。通过柯克的解释,1215 年《大宪章》第12 章重新进入法律和历史,“《大宪章》连续性神话”更为融贯,成为“税收法定”和“议会征税”的宪法证明。
“《大宪章》连续性神话”杂糅了神话和真实。其中的事实是:中世纪存在《兰尼米德特许状》和1225 年《大宪章》两份性质不同的文件。《兰尼米德特许状》被认为是和平条约,较少传播。1225 年《大宪章》作为制定法被多次确认,既是13 世纪政治史和宪法史的核心文件;也是制定法卷宗的开篇法律,为中世纪法律人群体研习。只有1225 年《大宪章》,没有所谓的“1215 年《大宪章》”。其中的神话是:1571 年之后,“伪”1215 年《大宪章》被认为是1215 年特许状的权威文本且与1225 年《大宪章》基本相同,并被称为“1215 年《大宪章》”。经过柯克的考证和解释,认为被删掉的“伪”1215 年《大宪章》的内容保留在1225 年《大宪章》中。柯克进而坚称,“伪”1215 年《大宪章》确立了税收法定和议会主权的原则,并通过1225 年《大宪章》从中世纪延续到16、17 世纪。17 世纪的政治家因而认为,“1215 年《大宪章》”是中世纪英国的基本法,维护了议会主权,限制了专制王权,构建了英国宪制。
五、神话未受挑战:《大宪章》正本在18 世纪的确证
在17 世纪的政治论争、司法实践和学术著作中,柯克从未使用过1215 年《大宪章》正本,用的是“伪”1215 年《大宪章》。同时,柯克使用的1225 年《大宪章》文本也并非亨利三世1225 年授予的《大宪章》正本,而是1297 年爱德华一世确认的1225 年《大宪章》,尽管1297 年确认的文本在内容上略有差异。〔56〕See James Holt, Magna Cart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47.这种文本误用促进了“《大宪章》连续性神话”的形成,但并不能由此推断柯克是有意制造神话。实际上,在柯克的时代,总体而言没有人比他更审慎。这是时代性的知识限度,如检察总长罗伯特·希斯爵士也混淆了1215 年和1225 年《大宪章》,受其影响,约翰·塞尔登的早期作品也分不清两者。〔57〕See John Baker, The Reinvention of Magna Carta, 1216-161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p.9.
《大宪章》正本是逐渐发现的。1629 年,罗伯特·科顿爵士(1570—1631 年)从出庭律师汉弗莱·威姆斯(Humphrey Wyems)处获得了一份1215 年《大宪章》正本,即Cii 正本。该正本就是大英图书馆的藏品“Cotton MS Augustus ii.106”,研究者对其来历所知不多。〔58〕See Nicholas Vincent, Magna Carta: Origins and Legacy, The Bodleian Library, 2015, pp.206-207.1630 年5 月10 日,爱德华·迪林爵士送给罗伯特·科顿爵士另一份1215 年《大宪章》正本,即Ci 正本。〔59〕See Nicholas Vincent, Magna Carta: Origins and Legacy, The Bodleian Library, 2015, pp.206-207.虽然现存Ci 正本的文字已经不可辨识,且国玺印章已经只剩下黑乎乎的一团了。〔60〕See Nicholas Vincent, Magna Carta: Origins and Legacy, The Bodleian Library, 2015, pp.206-207.但1733 年的版画证明了Ci 版本曾悬挂有国玺。〔61〕1733 年约翰·派因(1690—1756 年)以Ci 版本为基础制作了一幅精美的版画,主体内容是25 名男爵的徽章围绕着《大宪章》原文,下部吊着不规则的红色(而非现在的黑色)国玺印章。就加盖国玺而言,Ci 是最典型的特许状,不过这不能表明其优于其他正本。
1215 年《大宪章》正本自1629 年发现之后就日益流传。17 世纪的考古者不停地发现不同年份的《大宪章》,但并不能有效地区分这些版本的不同之处。〔62〕See William Sharp McKechnie, Magna Carta: Commentary on the Great Charter of King John, with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James Maclehose and Sons Pulishers to the University, 1914, pp.176-177.托马斯·赖默(Thomas Rymer)在1704年出版的《条约》(Foedera)一书仍未区分。该书有林肯《大宪章》的版画,但并未提及1215 年《大宪章》四份正本的存在,相反还把1217 年才有的《森林区特许状》汇编到1215 年,该《森林区特许状》甚至还有彼时已去世的约翰(1216 年去世)的完整授权。〔63〕See Thomas Rymer, Foedera, Conventiones, Literae et cujuscunque Generis Acta Publica, vol.1, London, 1816, pp.131-133.1721 年,大卫·威尔金斯出版了斯佩尔曼的著作《盎格鲁撒克逊法》(Leges Anglo-Saxonicae),书中有上述正本,奠定了布莱克斯通深入研究的基础。
布莱克斯通在1759 年出版的《〈大宪章〉和〈森林区特许状〉》一书才真正弄清了《大宪章》的不同版本。〔64〕See William Blackstone, The Great Charter and Charter of the Forest, Clarendon Press, 1759, pp.xxxv, lxix.《〈大宪章〉和〈森林区特许状〉》包含了14 份中世纪文件,从1215 年的《男爵法案》一直到1300 年的《确认特许状》(Carta confirmationis)。不过布莱克斯通只知道1215 年《大宪章》的Ci 和Cii 本,并不知道L 版本的存在,去索尔兹伯里大教堂也没找到S 正本。〔65〕See William Sharp McKechnie, Magna Carta: Commentary on the Great Charter of King John, with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James Maclehose and Sons Pulishers to the University, 1914, pp.167-168.此外,他还知道四份没有国玺的副本,分别见于格罗切斯特修道院、大英博物馆(No.746)、《财政署红皮书》和《拾遗》(Spicilegium)中。最终,布莱克斯通以派因的版画Ci 为基础,交叉对比《财政署红皮书》中的抄本,出版了1215 年《大宪章》第一个精准版本。诚如学者所言:“布莱克斯通事实上第一个清晰地区别了约翰王原始《大宪章》与其后大量重新发布和修订的相同文件。”〔66〕Wilfrid Prest, “Blackstone’s Magna Carta”, 94 North Carolina Law Review 1495, 1497 (2016).
布莱克斯通对当代章节划分也有重要影响。布莱克斯通将1215 年《大宪章》分为61 章,并标上数字,此种方式延续至今。不过他的章节划分更多的是寻求《大宪章》与《男爵法案》章节的对应,〔67〕参见王栋:《〈大宪章〉制定考:从男爵方案到国家特许状》,载《古代文明》2021 年第1 期,第57-63 页。忽略了《大宪章》正本本身的划分。〔68〕当代学者将《大宪章》分为63 章,即把第61 章分为第61 章、第62 章和第63 章。中世纪抄本多以另起一行,同时彩写首字母或分段符,来标明新章节。在亨廷顿/彼得伯勒抄本系列中的一份抄本中,曾有标号的尝试,不过只进行了一部分。See David Carpenter, Magna Carta, Penguin Classics, 2015, pp.22-23.该数字分章虽与1215 年《大宪章》自带的大写字母分章不同,但却为后世沿用,深刻影响了后世对《大宪章》的研究和认识。布莱克斯通还依据自己的1215 年《大宪章》的编号,对1216 年《大宪章》(42 章)和1217 年《大宪章》(47 章)重新进行了编号。此三个版本的《大宪章》编号一直延续到现在。但因为1225 年《大宪章》在16 世纪早期已经编号(37 章)出版,且采用的是13、14 世纪文本中的编号,布莱克斯通直接采用了该中世纪编号。〔69〕See Claire Breay & Julian Harrison eds., Magna Carta: Law, Liberty, Legacy, The British Library, 2015, pp.168-169.
布莱克斯通将1215 年《大宪章》重置于现代世界,他编撰的《大宪章》版本畅行了半个世纪。值得注意的是,尽管1215 年《大宪章》正本的发现有助于学者比较《大宪章》不同版本之区别,对“《大宪章》连续性神话”构成了潜在挑战;但不同于柯克,布莱克斯通虽然撰写了导论,却没有作出任何评注。事实上,布莱克斯通与柯克观点相近,都认为《大宪章》是最古老的宪法。《大宪章》连续性神话非但未受到实质挑战,相反还继续延续。
布莱克斯通之后,《大宪章》的评注和研究也有所推进。1766 年,戴恩斯·巴灵顿的《评论:从〈大宪章〉到詹姆斯一世二十一年的制定法》对《大宪章》进行了评注,不过主要追随柯克的观点。1772 年,爱尔兰人弗朗西斯·沙利文(Francis S.Sullivan,1715—1766 年)出版了《封建法历史专论:附〈大宪章〉评注》,主要讨论《大宪章》中仍有法律效力的条文,省略了对封建土地保有的讨论。在1783—1784 年,约翰·里弗斯出版了《英国法律史》,顺带提及了《大宪章》,对《大宪章》的真实意图颇有洞察。〔70〕See William Sharp McKechnie, Magna Carta: Commentary on the Great Charter of King John, with an Historical Introduction,James Maclehose and Sons Pulishers to the University, 1914, pp.178-181.总体上,虽然1215 年《大宪章》已经发现,内容区别于1225 年《大宪章》,但柯克对《大宪章》的解释仍是18 世纪对《大宪章》的主流理解,“《大宪章》连续性神话”仍然稳固。
六、修正版神话:辉格解释中的“《大宪章》连续性神话”
19 世纪现代学科兴起,档案研究快速推进,“《大宪章》连续性神话”遭受了新挑战。1810 年,档案委员编辑出版了《王国制定法大全》,书中第一部分是“特权特许状/自由宪章”(Charters of Liberty),涉及亨利一世到爱德华一世时期的诸多特许状。不同于布莱克斯通,档案委员会认为L 正本书写流畅完整,保存完善,决定以此为底本出版《大宪章》。委员会同时参考了Ci 版本和Cii 版本,并附上了L 版本的影印本。L 版本虽然也没有国玺印章,但是在页面底部有三个呈三角形的小孔,卡朋特认为这暗示了其上曾经有印章。该版本背后有两个大写的“LINCOLNIA”(林肯),字体与正文一致,表明其目的地就是林肯大教堂。其他相关证据还有该版本背后有大教堂档案的书架标记(shelf marks),以及林肯大教堂14 世纪的登记册中有一份1215 年《大宪章》的副本。林肯主教休·德·威尔斯(Hugh de Welles)出现在《大宪章》制定现场。L 本应为林肯大教堂所制并一直保存此处。整体来看,该版本布局饱满,字体飘逸灵动,修改最少,写满了最后一行。卡朋特的新版《大宪章》拉丁文本也是本自L 正本。〔71〕See Nicholas Vincent, Magna Carta: Origins and Legacy, The Bodleian Library, 2015, pp.201-211.
S 版本当时恰好找不到了,所以对《王国制定法大全》中的《大宪章》没有影响。〔72〕See Nicholas Vincent, Magna Carta: Origins and Legacy, The Bodleian Library, 2015, pp.212-213.虽然17 世纪的研究者已经知晓S 版本的存在,但是档案委员会1806 年在索尔兹伯里大教堂没发现该正本,到1814 年该正本才又被发现。该版本同样没有国玺印章,但是底部的两条裂缝被看作是印章存在过的痕迹。一般认为迪勒姆的伊莱亚斯与S 本直接相关。伊莱亚斯是坎特伯雷大主教兰顿的管家,长袖善舞,参与了1215 年国王和男爵的谈判。伊莱亚斯还修建了索尔兹伯里大教堂。索尔兹伯里大教堂官方采用了艾弗·罗兰兹的说法,认为《大宪章》正本原件有13 份,其所藏的《大宪章》是发给老塞勒姆(Old Sarum)的旧教堂的,待索尔兹伯里大教堂新建后移入,并保管至今。概而论之,索尔兹伯里《大宪章》是影响最小的《大宪章》正本。《王国制定法大全》的另一贡献是同时出版了1215 年《大宪章》和1225 年《大宪章》,以及后续的相关法令。〔73〕See Alexander Luders ed., The Statutes of the Realm, Dawsons of Pall Mall, 1810, pp.5-28.
到19 世纪20 年代,1215 年《大宪章》的四份正本都已经发现。总体上,现代研究者从三个方面证明了1215 年《大宪章》四份正本的真实性:“第一,它们都以13 世纪早期的字体书写。第二,所有文件的基本内容都与主教函令证书中发现的内容相同。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所有文件都有加盖国玺的证据。”〔74〕不过《大宪章》作为特许状并非都符合标准程序。一般特许状在“亲手给予”条款之前都是证人名单,1225 年《大宪章》就是如此。但1215 年《大宪章》使用的措辞是“以上诸人和许多其他人证明”(Testibus supradictis et multis aliis)。See David Carpenter, Magna Carta, Penguin Classics, 2015, pp.11-12.这些正本为严肃的学术研究奠定了基础,但“《大宪章》连续性神话”并未遭受挑战。1829 年理查德·汤姆森出版了一个评注,但该评注主要接受了柯克的解释,并没有进行认真的历史研究与辨析。〔75〕See R.Thomson, Historical Essay on the Magna Charta of King John, Printed for John Major, Fleet Street and Robert Jennings,Poultry, 1829, pp.274, 425.
现代学术意义上的《大宪章》文本研究始于斯塔布斯。1868 年斯塔布斯修订出版了《约翰王大宪章》(Magna Carta regis Johanis)一书,并于1870 年出版了《英国早期宪法史宪章及实例选:从最初到爱德华一世》(以下简称《宪章精选》,Select Charters)。斯塔布斯认为Cii 正本更优,称约翰《大宪章》为《自由大宪章》(Great Charter of Liberties),并将亨利三世的三份宪章/特许状按年份顺序依次称为《亨利三世第一宪章》《亨利三世第二宪章》和《亨利三世第三宪章》。〔76〕See William Stubbs ed., Select Charters and Other Illustrations of English Constitutional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Reign of Edward the First, Clarendon Press, 1960, pp.291-303, 335-339, 340-344, 349-351.
颇有意味的是,在斯塔布斯的学术脉络中,1225 年《大宪章》只是“亨利三世第三宪章”,而“约翰王特许状”才是“自由大宪章”。中世纪的《兰尼米德特许状》如今却独占《大宪章》之名。斯塔布斯是文献识读和编校的大师,《宪章精选》成为《大宪章》诸版本的权威印刷本。《宪章精选》直到20 世纪60 年代仍是牛津大学研究生课程的核心文本。著名学者约翰·乔立夫、约翰·普雷斯特维奇、霍尔特以及卡朋特都曾受教于牛津大学,自然也学习了《宪章精选》。〔77〕See Nicholas Vincent, “Magna Carta and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A Review Article”, 130 The 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 646, 654 (2015).1215 年《大宪章》成为特指的“《大宪章》”,亨利三世《大宪章》只是不重要的修订版,两者在中世纪的地位被重构。此外,斯塔布斯没有对担保章节进行分章,所以《大宪章》一共是60 章。
《大宪章》名实变迁背后更为宏阔的背景是19 世纪辉格史学对“《大宪章》连续性神话”的重构。亨利·哈兰是辉格史学的开创者,强调宪法和普通法对民众自由、权利和财产的保护。《大宪章》承继了撒克逊民主,以司法保护自由人的自由与财产。《大宪章》是英国的实在法和基本法,赋予英国人民自由灵魂,构建了英国自由的基础。〔78〕See Henry Hallam, View of the State of Europe during the Middle Ages, vol.2, W.J.Widdleton, Publisher, 1872, pp.307-314.在哈兰的辉格解释中,历史细节没有那么重要,重要的是盎格鲁民主传统在宪法中的发展,《大宪章》则是典型文本。哈兰对《大宪章》的解释代表了19 世纪上半叶的共识,托马斯·麦考莱称《大宪章》中的男爵是辉格党人。〔79〕See J.W.Burrow, A Liberal Descent: Victorian Historians and the English Past,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 p.18.修正版的“《大宪章》连续性神话”以1215 年《大宪章》为核心,与英国民主、法治和宪制密切关联。
但是,在《大宪章》地位问题上,辉格史学内部也有差异。1872 年,爱德华·弗里曼出版了《英格兰宪法的生长》一书,强调盎格鲁自由传统以及英国古代宪法的连续性。弗里曼强调忏悔者爱德华宪章和《亨利一世宪章》都是古代宪法,而《大宪章》只是对古代宪法的确认,只是承认而非扩大了民众权利。在弗里曼的研究中,“《大宪章》连续性神话”仍然成立,但《大宪章》的核心地位失去了,《大宪章》既没有创造性,也没有对后世的改变。〔80〕See Edward A.Freeman, The Growth of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Macmillan and Co., 1872, pp.vi, 1-9, 66, 73, 86, 88, 106.
辉格史学的集大成者斯塔布斯进一步修正了“《大宪章》连续性神话”。斯塔布斯在《英格兰宪法史》(1874—1878 年)中强调英国宪法史受到了民族性、外部历史以及政治制度的综合影响,是日耳曼自由传统的发展。英国宪法根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之后为诺曼人加强,统一于《大宪章》中。斯塔布斯承继了柯克的观点,认为《大宪章》最核心的内容是确立国民大会的征税职能以及继承金和协助金的法定征收。国民大会具有立法和征税权力,是国家代议制的核心,整合了中央和地方行政制度。同侪审判退居次席,只是古老条顿法的重申。〔81〕See William Stubbs,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In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vol.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pp.337-338, 518-572.另参见王栋:《〈大宪章〉渊源:罗马法还是蛮族习惯法》,载《经济社会史评论》2021 年第2 期,第4-20 页。
斯塔布斯不仅修正了“《大宪章》连续性神话”,更申明《大宪章》是最伟大的形成性(formative)文件,称颂“整个英国宪法史不过是《大宪章》的评注而已。”〔82〕William Stubbs, The Constitutional History of England: In its Origin and Development, vol.1,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1, p.532.在斯塔布斯的辉格叙事中,“《大宪章》连续性神话”被修正,构成“《大宪章》起源神话”的组成部分,进而成为英国历史的核心。辉格解释及其核心内容的“《大宪章》起源神话”一直持续到60 年代。对于辉格解释,肯尼迪·麦克法兰指出:“大部分中世纪晚期宪法史的根源矛盾在于其假设国王和贵族的利益是对立的,而且这种对立是无法避免的。这种假设在我看来是错误的。”〔83〕K.B.McFarlane, The Nobility of Later Medieval England, Clarendon Press, 1973, p.120.尽管麦克法兰成功挑战了辉格解释,但他并未讨论《大宪章》神话。事实上是霍尔特将《大宪章》置于12、13 世纪的历史语境中,批评柯克和斯塔布斯创造了“《大宪章》起源神话”,强调《大宪章》的封建性。〔84〕See James Holt, Magna Cart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33-34.但是,研究者对“《大宪章》连续性神话”仍缺乏足够认识和深入讨论。〔85〕一个初步的讨论参见王栋:《建构大宪章的现代性:学科分立视野下的19 世纪大宪章研究》,载《杭州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2 期,第105-114 页;王栋:《神话与现代之间:〈大宪章〉在20 世纪初的两种叙事》,载《中山大学法律评论》第14 卷第2 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版,第239-253 页;王栋:《法治叙事的确立:二战后的〈大宪章〉研究》,载《政治思想史》2018 年第3 期,第171-195 页。
七、“《大宪章》连续性神话”的想象与真实
《大宪章》在历史中的角色纷纭变化,既曾引领政治变革,发展完善普通法,成为被长久尊崇的政治符号;也曾归于沉寂。与之相伴随的是对《大宪章》的多重理解。这些理解因研究路径差异建构出不同解释模式,形成了想象与真实相互交织的层累的知识积淀。当代研究者只有理解“《大宪章》连续性神话”,才能理解英国宪制转型和法治发展的复杂性。
概言之,约翰王1215 年6 月15 日颁行了特许状,即现代人所称的《大宪章》。但是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到16 世纪中叶)的人不称其为《大宪章》,而是《兰尼米德特许状》。《兰尼米德特许状》被认为是和平条约,相关文本在中世纪少为人知。同时,1216 年、1217 年和1225 年《大宪章》相继修订产生,《大宪章》之名也逐步确立。1225 年《大宪章》既是13 世纪政治史和宪法史的核心,也是中世纪普通法的开篇文本,一直为法律人研习。在中世纪,只有亨利三世《大宪章》(即1225 年《大宪章》),没有所谓的“1215 年《大宪章》”。
1225 年到1259 年,罗杰和帕里斯先后汇编了“约翰王特许状”。该文本含1215 年、1217 年、1225年《大宪章》以及1217 年、1225 年《森林区特许状》,并被命名为“约翰王特许状”。1571 年帕里斯的《大编年史》出版,“伪”1215 年《大宪章》被认为是1215 年特许状的权威文本,内容与1225 年《大宪章》基本相同,并被称为“1215 年《大宪章》”。经过柯克的考证和解释,1225 年《大宪章》中删掉的1215年《大宪章》的内容也被认为保留在1225 年《大宪章》中。柯克进而坚称,“伪”1215 年《大宪章》确立了税收法定和议会主权的原则,并通过1225 年《大宪章》从中世纪延续到16、17 世纪。17 世纪的政治家因而认为1215 年《大宪章》是中世纪英国的基本法,维护了议会主权,限制了专制王权,构建了英国宪制。“《大宪章》连续性神话”更为融贯,成为“税收法定”和“议会征税”的宪法性证明。
1629 年,英国人发现了1215 年《大宪章》正本,但是《大宪章》正本的内容长久以来并未确定。直到1759 年,布莱克斯通才在《〈大宪章〉和〈森林区特许状〉》一书中真正明确了1215 年《大宪章》的内容。但布莱克斯通与柯克观点相近,认为《大宪章》是最古老的宪法。“《大宪章》连续性神话”非但未受到实质挑战,相反还继续延续。同时1215 年《大宪章》取代1225 年《大宪章》,成为19 世纪法律体系和学术研究的主体。19 世纪随着档案研究的推进,辉格史家进一步修正了“《大宪章》连续性神话”,强调《大宪章》的盎格鲁自由渊源。斯塔布斯在《英格兰宪法史》中彻底完善了“《大宪章》连续性神话”,使之与“《大宪章》起源神话”一起成为辉格史学的核心。英国宪制根源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之后为诺曼人加强,统一于《大宪章》中,整个英国宪法史不过是《大宪章》的评注而已。
20 世纪下半叶,麦克法兰和霍尔特批判了辉格解释,但批判的主要是“《大宪章》起源神话”。“《大宪章》连续性神话”仍待学界深入论述,事实上,这是一个被模糊承认但未被言明的神话。通过知识考古,我们可以发现“《大宪章》连续性神话”作为知识的偶然性、物质性和不连续性。
第一,《大宪章》文本的流传具有不小的历史偶然性。在中世纪,“1215 年《大宪章》”并不存在,长久以来传播的是1225 年《大宪章》。如同大卫·赛普所讲的“如果最初的1215 年文本被14、15 世纪的律师如同我们今日这样知晓和崇敬,英格兰可能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宪法史”。〔86〕David J.Seipp, “Magna Carta in the Late Middle Ages: Over-Mighty Subjects, Under-Mighty Kings, and a Turn Away from Trial by Jury”, 25 William and Mary Bill of Rights Journal 665, 668 (2016).
第二,“《大宪章》连续性神话”具有明显的物质性。事实上,正是印刷术的出现和《大编年史》手稿1571 年的出版,才使得“伪”1215 年《大宪章》广为传播。该“伪”1215 年《大宪章》被误认为是权威文本,为“《大宪章》连续性神话”提供了核心证据。
第三,“《大宪章》连续性神话”具有不连续性。神话提供了一种简明叙事,即1215 年《大宪章》的制定与现代宪制的兴起。但实际上历史主体存在并立与变化:即13 世纪初的1215 年《大宪章》,中世纪到18 世纪的1225 年《大宪章》,16 世纪70 年代到18 世纪中叶的“伪”1215 年《大宪章》,19 世纪至今的1215 年《大宪章》。这些主体的并立、变化与更替展现了“《大宪章》连续性神话”的不连续性。
对《大宪章》的知识考古不仅展现了“《大宪章》连续性神话”的偶然性、物质性和不连续性,也对当代宪法史、法律史和政治史的确定性和连续性提出了挑战,如需要重新审视《大宪章》与“税收法定”“王在法下”和“程序正当”的关系。本研究无意否定《大宪章》在历史中的某种连续性,本文批评的是那种忽略偶然性和物质性的平滑叙事。事实上,当代学者都在努力重构某种历史连续性。如新宪法史派的克莉丝汀·卡朋特和爱德华·鲍威尔试图以财产权重构英国宪法史,〔87〕See Christine Carpenter, Locality and Polity: A Study of Warwickshire Landed Society, 1401-149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Christine Carpenter, The Wars of the Roses: Politics and the Constitution in England, c.1437-1509,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Edward Powell, Kingship, Law and Society: Criminal Justice in the Reign of Henry V, Clarendon Press, 1989.国内学界也有相对持续的反思和讨论。参见李栋:《试析英国的封建制度及其宪政之生》,载《环球法律评论》2011 年第4 期,第59-70 页;王栋:《中古英国宪制的整体图景》,载《古代文明》2022 年第2 期,第49-64 页;于明:《“不可追忆时代”的用途与滥用——英国“古代宪法”理论的再检讨》,载《学术月刊》2019 年第5 期,第89-101 页。法律史大家贝克以“重新发明”来解释法律制度的连续性。〔88〕See John Baker, The Reinvention of Magna Carta, 1216-1616,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另参见王栋:《法律人的〈大宪章〉史:读〈重新发明大宪章〉》,载《中山大学法律评论》第19 卷第1 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 年版,第274-284 页;泮伟江:《“偏执”的普通法心智与英格兰宪政的奥秘》,载《政法论坛》2013 年第4 期,第180-186 页;李红海:《当代英国宪政思潮中的普通法宪政主义》,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5 年第1 期,第129-136 页。纵观现代学术史,19 世纪以来的《大宪章》研究产生了诸多变化,但所有的《大宪章》学理模式,都与学者的学科、身份和研究路径有关。前辈学者在《大宪章》研究中付出了诸多心力,既受到时代、学科和研究路径的影响,也有自己的独创性。对他们诸多的学术定论作一批判与借鉴有机结合的解构,进而对《大宪章》的文本真义与社会影响建构出更为接近历史的诠释模式,对学术界来说无疑是一项颇具挑战性的重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