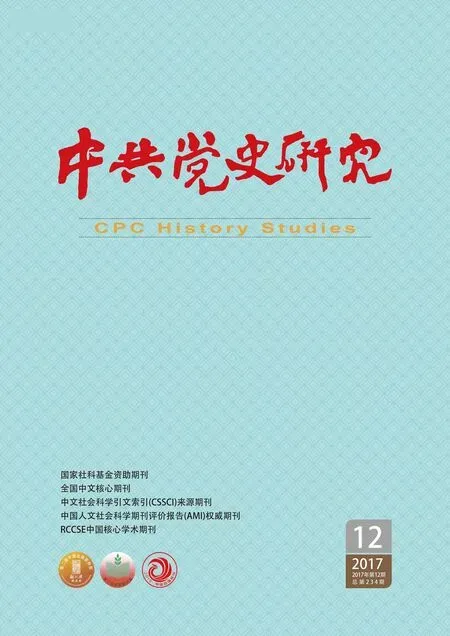去留之际:美国新教在华传教士对国共内战的因应*
2017-01-25陈铃
陈 铃
从19世纪30年代到抗战前夕,美国新教传教士在华活动已历时百余年之久。大批美国在华传教士不仅传播基督教信仰,且办理了众多教会学校、医院、慈善机构,同时又通过经济力量和人事制度长期主导中国基督教的发展。
* 本文是2015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美国基督新教在华传教士退出中国大陆研究”(15YJC770005)的阶段性成果。
他们的传教利益遍布中国各地,业已成为美国在华软实力的重要象征。抗战期间,美国新教在华传教事业虽遭受重创,但于战后迅速恢复。与此同时,战后国共矛盾日益显现,双方边打边谈,最终内战全面爆发,美国传教士所期望的和平稳定的社会政治环境不复存在。这就迫使美国传教士必须就国共内战适时作出应对。首先,国共内战涉及传教士的生命财产安全问题。据统计,美国新教主要宗派*美国新教主要宗派有北长老会、南长老会、卫理公会、信义会、公理会、北浸礼会、南浸信会等。派至中国的传教士人数,在1947年底尚有1000多人*New York: Foreign Mission Conference of N.A, Far Eastern Joint Office, China Committee, 1947-1951, Film S37, China-75, December 29, 1949, p.1.(以下引用该档案时使用略称China。)。其次,随着战争的扩大和深入,美国在华传教士对内战究竟持何种政治态度,对华传教的战略方针又作何调整,才最为符合自身的传教利益?再者,美国传教士来华的主要使命和目的就是传播基督教信仰,这与共产党的唯物主义理念相违背。因此,内战期间中共如何对待美国在华传教士,既是一个外侨问题,又是一个宗教问题。目前国内外学界就此议题的相关研究尚不多见*相关研究参见Nancy Bernkopf Tucker, “An Unlikely Peace: American Missionaries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1948-1950”, The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Vol.45.No.1(Feb., 1976) ;Paul A.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1890-1952, New York: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7;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姚民权、罗伟虹:《中国基督教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0年。,本文主要利用中英文史料,试作一较为全面深入的论述。
一、从“支持”国民党到等待观望
自30年代开始,因为国民党与美国传教士关系较为融洽,而且包括蒋介石夫妇在内的诸多国民政府高层人士都是基督徒,所以面对国共之争,美国传教士的主流态度是支持国民党。1945年3月来到重庆并在此驻留两个月之久的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the 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Council)又称世界基督教协进会,它的前身是成立于1910年的爱丁堡续行委办会,1921年方改用现名,它和全世界各国教会都有联系。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和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之间渊源颇深。在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的前身爱丁堡续行委办会于1912年举行全体会议时,美国人穆德(穆德在1921年至1942年期间长期担任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的会长,之后仍然担任名誉会长)被推选来远东进行活动,在中国召开一次全国大会。于是在1913年,穆德主持召开全国基督教大会,会议成立了一个全国基督教中心机构“中华续行委办会”,由诚静怡任总干事。1922年5月,中华续行委办会改组为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美国干事德惠廉当时就已看到,虽然重庆国民政府领导人民抗日有功,实际上却一直在走下坡路,相反中共的实力和声望与日俱增,同时国共相持的背后还涉及美英与苏联在远东的利益争端,这都增加了战后中国局势的不确定性。他预感到国共内战不可避免,所以呼吁加强团结。*J.W.Decker:《中国团结的重要关头》,《天风》第19期,1945年10月12日。但德惠廉所称的团结实质上是希望中国政令早日统一,国民党能真正统一中国。他对国民党的责备也是希望其能迅速进行自我改革,以增强政府合法性。1946年8月,美在华传教士的头面人物司徒雷登也撰文表达了他对中国局势的最新看法。他认为,国民党虽然腐败,但它毕竟模仿了美国式的民主,对美国而言是“可亲可近”的。在他看来,蒋介石是当时中国“唯一值得信赖和胜任挑战的领袖”,再加上马歇尔将军代表美国政府对中国的积极协助,中国可以实现“联合政府”的主张。*John Leighton Stuart, “Chinese Public Opinion”, The Public Opinion Quarterly, Vol.10, No.3 (Autumn, 1946), pp.445-446.是年7月,司徒雷登正式出任美国驻华大使。7月22日出版的美国《时代》杂志认为“这意味着中国统一的另一个新希望”*“Foreign Relationship: So Happy”, Time, Jul.22, 1946.。如果说德惠廉和司徒雷登的相关表述稍显含蓄的话,那么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联董”)*中国基督教大学联合董事会(“联董”)正式成立于1945年6月,是推动基督教高等教育合作运动的联合机构,其前身是1932年于美国纽约成立的中国基督教大学校董联合会。1951年,因政治原因,“联董”中断了对中国大陆的服务。1955年改组为“亚洲基督教高等教育联合董事会”(the United Board for Christian Higher Education in Asia,简称“亚联董”),工作重心转移到中国大陆以外的东亚和东南亚。中美重新建交后的1980年,“亚联董”恢复对华服务活动,直至今日。具体参见肖会平:《合作与共进:基督教高等教育合作组织对华活动研究(1922—1951)》,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92—142页。总干事樊都生的讲话则显得锋芒逼人。樊都生的另一重要身份是纽约协和神学院院长,因此他的讲话在中美基督教界甚至政界都具有相当影响力。1946年夏季,樊都生来中国并和许多中美领袖会谈,其中最主要的是马歇尔特使和司徒雷登大使。他明确表示马歇尔的调处只能起到暂时休战的作用,双方最终必有生死决斗。美国应支持国民党打赢内战,不然中国将被拉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樊都生:《中国之危机》,《天风》第42期,1946年10月12日。
德惠廉、司徒雷登和樊都生这三位在中美基督教界乃至政界颇具影响力的传教士,都意识到当时的中共已今非昔比,但又恐惧共产主义革命的到来,担忧中共胜利后中国会倒向苏联。他们也十分清楚国民党内部存在的各种严重问题,却仍将解决当时中国紧张状况的希望寄托在其身上。因此,他们一方面督促国民党抓紧进行政治上的自我改良,另一方面又支持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经济军事援助。他们这种带头的言行,已逾越了宗教和政治之间本应有的界限,加剧了中国局势的紧张,同时给美国在华传教事业造成负面效应。
司徒雷登接任美国驻华大使,在某种程度上开启了“传教士外交”的时代。作为基督教民主主义者,他积极协助马歇尔调停国共冲突,同时希望国民党能切实进行政治改良。他利用自己在中国基督教界广泛的人脉关系,试图通过基督教来影响政治。1946年7月13日,深受美国教会影响的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委派会长梁小初等三人,去南京访问尚在进行和谈的中共代表、民主党派人士及国民党政府代表等,表达了基督徒对和平的愿望。访问期间,司徒雷登力劝基督教人士应发表一篇合乎时代要求的宣言,但三人当时没有同意。司徒雷登随后介绍三人访问马歇尔,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口吻一致,认为中国应该有一个“改良政府”,民主人士应该参加这个政府。*参见姚民权:《上海基督教史(1843—1949)》,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上海市基督教教会委员会,1994年,第226—227页;崔宪详:《控诉美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协进会侵略中国的阴谋》,《天风》第11卷第19期,1951年6月9日。但是,到了8月10日,马歇尔和司徒雷登就发表联合声明,说战争日益扩大,且有席卷全国之势,国共双方所谈判的问题似无获得解决的可能*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第120—121页。。1947年7月4日,国民政府公布《戡乱总动员令》。同月,在司徒雷登的支持下,中国基督徒领袖代表团与宋美龄、蒋介石会面*参见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来华新教传教士评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83页。。中国基督徒领袖建议政府不能因为战争而牺牲人民的利益,对付共产主义最好的武器是建立给予人民更好生活、更多自由、更多公正的社会秩序*China-19, August 7, 1947, p.2.。然而会谈没有取得任何实质性成效。宋美龄和蒋介石在会见代表团时都在为国民党的决策开脱责任,并要求基督徒站在自己这边。代表团成员的“良苦用心”丝毫未打动“剿共”态度坚决的蒋介石。相反,蒋介石还责怪他们为何不像天主教那样表态支持政府。*China-19, August 7, 1947, p.4.事实说明,司徒雷登和中国基督教领袖尝试的改良主义道路已走入“死胡同”。
从军事上看,1947年是国共内战关键性的一年。为打破国民党军队对山东和陕北的进攻,中共中央大胆决策,将主要战场由山东转到中原,将战略重心由内线移至外线。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出击外线的行动,标志着全国战局的重大变化。*参见汪朝光:《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61—267页。与此对应的是,1947年下半年,在国共双方战事激烈的华北、华中地区,受炮火波及的美国传教士开始增多。同年底,许多美国传教士放弃了在河南或鄂北的传教站,坐着火车、卡车或骡车,当然更多的是徒步,涌入武昌城中避难。*“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Report”, Time, Jan.19, 1948.其中,来自河南郾城(亦有可能是漯河*安息日会的报告中曾提到:“河南漯河医院所有器材被劫一空,医院大厦也被付诸一炬。但同工都平安。”汪和仁:《华中联差会报告》,《末世牧声》第28卷第4期,1948年4月。)安息日会的传教士在圣诞节前夕就开始撤离。正常情况下,他们坐火车南下汉口只需一天。但是,这一次在老传教士汪和仁(Merritt C.Warren)的带领下,这支由6名美国人和28名中国人组成的逃难队伍却整整在路上花了3个星期。他们一路上不时遭遇国共两党军队的拉锯战。至于坚持留在原地的传教士,他们和解放军有了近距离的接触。同年12月,华东野战军占领河南许昌。美国信义会在许昌的教堂被中共军队临时征用,改作马厩。虽然当地的差会工作因战事受阻,但传教士认为中共军队对他们还算友好。当中共军队的1名士兵在教会屋子里的地板上随地吐痰时,他的长官批评他,表示人家美国人可没这个坏习惯,要向他们学习。*“International: Missionary Report”, Time, Jan.19, 1948.翌年1月15日,美国国务院宣称:“由于华中共军威胁地区排外情绪滋长,现已命令该处美国教士尽速撤退。”与此同时,美国信义会负责人也立即向军政当局接洽,希望协助战区的外籍传教士急速撤退。该请求得到同意后,信义会的飞机“圣保罗”号担负起运输责任,先后将在郑州老河口等地集中的传教士六七十人撤退至武汉。一批信义会传教士描述了他们如何从开封退至郑州:国共两军战火猛烈,他们也无法辨出谁是国民党军队,谁是中共军队,只有在烽火中祈祷。从开封到郑州坐火车约有75里路,一路上国民党军队白天出来,中共军队晚上出现,他们好不容易才到达郑州。*《宗教的世纪》,《天风》第5卷第4期,1948年1月24日。可见,这一时期豫、鄂一带的美国传教士受战事的影响非常大。
面对如此严重的危机,美国在华差会的态度至关重要。1948年1月15日,在沪的美北长老会差会干事华莲文(E.E.Walline)致信北平传教士梅尔文(W.C.Merwin),专门谈及此敏感问题。由信中可知,司徒雷登曾建议在西安东部和长江以北地区尚有传教士活动的差会将其所属的“非必需”传教士(即老弱传教士或传教士家属)先行转移至相对容易撤离的地点,以防事态进一步恶化。对于司徒雷登的建议,上海各差会的判断却认为其性质只是预警式的,不过美国传教士可以前去北平、天津和青岛这些大城市,以便在真正紧急情形下有办法对相关人员集中撤离。华莲文谈到,司徒雷登要求上海各美国差会团体推举一位代表直接与其联系,以便差会能获得最新情报,于是被推选为代表。因此,他能及时将收到的任何建议告知梅尔文。但他又特别叮嘱梅尔文,任何发自司徒雷登的情报都须列为机密,因为没有必要一开始就让其他传教士或中国基督徒高度紧张。*China-29, January 28, 1948, p.1.华莲文信中透露的内容表明,战事虽给美国传教士带来生命财产方面的威胁,但美国在华差会并没有听从司徒雷登的建议,也不想让教会内部因此慌乱不安,而是选择低调处理、继续观望。
二、中共中央对传教士的最新政策方针
从1947年底到1948年,国共内战胜利的天平明显向中共一方倾斜。解放军迅速南移,势如破竹,不仅占领了广大的农村和一批县城、市镇,而且开始占领一批中等甚至大的城市。在新解放区,中共军队遇到大量外国侨民,其中就包括当时外侨中的特殊群体——传教士。在这种新的形势下,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关于如何处理在华传教士问题的最新政策方针。*中共对传教士提出的新方针政策,实际上是中共中央为适应形势发展要求而提出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有机组成部分。1947年12月25日至28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米脂县杨家沟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报告,系统阐明了中共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此后,中共中央特别注意革命的政策和策略。中共长期以农村根据地和武装斗争为工作中心,干部也多来自于农村,对城市工作的复杂性和重要性缺乏认识和实践,故在占领城市初期曾发生过违反政策和纪律的错误,因此中共中央相当注意纠正城市工作中的“左”倾偏向。参见汪朝光:《中国命运的决战(1945—1949)》,第337—341页。
1948年2月7日,中共中央下发《中央关于对待在华外国人的政策的指示》,明确要求军队不得没收和破坏外人设立的教堂及其办理的各项产业*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36页。。对于传教士,该指示则要求各级政府及解放军采取友好态度,同时也要求警惕传教士当中存在某些帝国主义分子,注意其进行特务破坏活动。犯罪的传教士须治罪或驱逐出境,但不必封闭教堂,可许其另派人来主持,以免外国人民误会解放地区政府是在排斥宗教。*《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7册,第38页。3月4日,周恩来就如何认真执行2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对待外侨的指示一事,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各中央局、前委电:对于在我解放区犯罪的外侨,要敢于依法检查、拘捕、审讯和判决,“使帝国主义反动分子对我有所戒惧”。但要正确掌握政策,“凡有关外交行动和外交政策的决定,必须报告中央并得中央批准后,方可实行。一切违反中央外交政策及处理外侨方针的行动必须禁止”。*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第764页。4月12日,中共中央东北局发出《关于处理外国教会的临时办法的决定》,也作了类似指示与要求*参见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49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第296页。。11月,中共中央专门发出《关于宗教信仰政策及处理教会问题的指示》,再度告诫各地:“我党对中外教会采取信教、传教自由政策(只要遵守法令,不加干涉),系根据现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而来,即苏联社会主义国家宗教信仰仍然存在。须知天主教、基督教之存在是有其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纵然封建落后,甚至反动,但并非一下能消灭的。如果采取毕其功于一役的办法,借土改或间谍案的机会,将教堂没收消灭,必犯冒险主义的错误。”*转引自杨奎松:《新中国成立初期清除美国文化影响的经过》,《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第10期,第24页。1949年1月19日,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央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也明确规定:外国传教士已在解放区的可继续居住并执行业务,新来者暂不批准*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8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2年,第46页。。4月27日,毛泽东就解放军第35军进占南京后擅入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住宅一事,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总前委刘伯承、张际春、李达电:“三十五军到南京第二天(二十五日)擅自派兵侵入司徒雷登住宅一事,必须立即引起注意,否则可能出大乱子。其经过情形速即查明电告,以凭核办。”*《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489页。5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入城部队遵守城市纪律的指示。其中第三条规定要保护外侨不加侮辱,一切有关外侨事务均由最高机关办理,没有命令不得进入外侨住宅,不准住外侨的房屋或教堂、学校,也不得对外侨与外侨住宅施行室内检查与人身搜查。*《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下卷,第501页。
在解放军从胜利走向胜利,及至推翻南京国民政府的这一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格外注意外侨事务,能根据前线实际情形迅速作出指示,及时纠正部队中存在的一些错误倾向,而且愈到后面举措愈加慎重。这样做,既有利于严肃军纪、树立部队外在良好形象,也有利于稳定外侨情绪,避免引发外交冲突及可能的帝国主义军事干涉。中共中央从外交层面出发,将传教士视为外侨的重要部分,同样采取保护原则,奉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不过,保护不等于认同,在各指示中基督教仍被视为一种外来宗教,传教士被认为也是与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国家有密切联系的。
从这一时期美国传教士与中共各地方军政机构的接触来看,传教士确实是受到保护的。根据1948年10月30日的教会内部简报称,美国公理会设于山西汾阳、太谷两地的传教站已在中共治下五月之久。当地的四位女传教士报告称两家医院运转正常,早在7月中共军队就下了不准干扰教会的命令,这些命令目前也被严格执行。*China-36, November 10, 1948, p.2.1948年10月河南郑州(或开封)*信中地点被有意隐去,但根据其描述的内容及循理会的传道区域等综合分析,可以得出是郑州或开封。解放后,北美循理会的一位传教士也被告知共产党会保护当地的宗教信仰自由,他可以自行传道;教会办学校、医院及组织救济的钱虽来自美国,但都是有益的;他们不喜欢美国,因为它帮助国民党打内仗,但这并非表示就反对他这位美国传教士*China-50(原件没有标注日期), p.2.。1948年12月1日,中共军队进入徐州城。当夜11时,美国南长老会传教士彭永恩(Frank A.Brown)*彭永恩,1910年作为美南长老会传教士来华,自1911年起就在徐州传道。所在的教会与中共军队首次接触。当时有数名解放军士兵曾到教会医院调查是否有三个美国人在里面,得到答复后立即离开,去其他外国人住的地方作同样的调查。直至翌年2月彭永恩离开徐州,教会工作未受干涉,医院也照常工作。*《宗教的世纪》,《天风》第7卷第9期,1949年3月5日。1949年2月12日,苏皖区基督教乡村事业协会总干事葛思巍(O.J.Goulter)在信中报告了安徽滁县刚解放时的情形。他说,驻军负责人保证“宗教自由”,军队在他们房子前面贴着“此处不准驻军”“不准移动东西”等字样。葛思巍说他碰见的许多长官和士兵态度都很客气,但他们对美国政府以军事援助国民政府表示愤慨。*葛思巍:《解放区来鸿》,《天风》第7卷第10期,1949年3月12日。1949年四五月间,宁沪相继解放。在上海上学的一位美国小女孩在给南京的传教士父亲史迈士的电报中写道:除了期末考试,这里一切安好。*Margaret Garrett Smythe(史迈士夫人,南京基督会鼓楼医院医药传教士), Cyrus H.Peake& Arthur L.Rosenbaum, ed., China Missionaries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microform], originally published as the Oral History program of Claremont Graduate School,香港中文大学崇基图书馆藏,FMS 699,p.60.当然随着中共军队占领中心城市的增多,北平、天津、济南、上海等地的外侨管理科亦陆续建立,传教士受到的管制也趋于正规和严格。1949年5月武汉解放后,汉口的差会医生罗根·鲁兹(Logan Roots,美国圣公会鄂湘教区前主教吴德施之子)因没有按照规定向公安局登记,就到武昌给文华中学的康明德(Robert A.Kemp)治病而被拘留。尽管事后传教士曾向公安机关承认错误,但公安机关认为他破坏法律就必须得到应有的惩罚。参见Mrs.Netta Powell Allen, China Missionaries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microform], pp.63-65.
从1948年7月至1949年5月,美国传教士眼中的中共军队纪律严明,大致能做到维护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在那位美国小女孩的眼中,中共军队入城更像是个欢庆的节日,让她的心飞出了教室。尽管上述多地的传教士从解放军官兵处亲耳听到,中共反对帮国民党打内战的美国政府,但中共的公开宣传并没有将美传教士简单地等同于美帝国主义者。这无疑会增强传教士继续留在中国的信心,让他们对新政权多一些憧憬。
三、传教士对国民党态度的重大转变
随着国民党的溃败和中共的节节胜利,美国传教士对国民党的态度发生了重大变化。经过多年的交往,美国基督新教和国民党政权之间已发生密切的联系,大部分美国传教士对国民党或者说对蒋介石夫妇具有一种特殊的感情。但是,美国新教在华传教事业毕竟在这片土地上立基百年,“福音”传播的对象在过去和将来也都是面向这片土地上的中国人。故在此攸关之际,许多传教士尽管内心挣扎矛盾,但并不表示对形势缺乏清醒的认识。
1948年初,美圣公会传教士艾伦夫妇重返汉口。当时,他们感到中共进军的势头已不可阻挡,但心里还是有点想不通。在农历春节期间,艾伦夫妇造访了一位中国主教及其妻子。艾伦的丈夫说:“你知道,我现在见到的最悲伤的一件事就是政府故意在自杀。”言下之意是指国民政府已腐败透顶,不知道采取什么有效办法来阻止中共。中国主教则说:“你说得对。照这样下去,不出两年,就是共产党的天下。”听到这话,艾伦夫妇大吃一惊,他们对此显然没有思想准备。为此,他们还和这位中国主教继续商榷,但主教说:“我认定共产党能取得天下。”其实,艾伦夫妇所指的国民党的“腐败”是指许多国民党上层的将军或高官只图自己的私利,故意将蒋介石隔在一个小角落,以致蒋很难施展他个人的权威,并且不知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Mrs.Netta Powell Allen, China Missionaries oral history collection [microform],pp.59-60.可见,艾伦夫妇虽然认为国民政府已无可救药,但也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心情,对蒋还是比较欣赏和同情的。艾伦夫妇的这种心态,在当时的美国传教士群体中并不少见。
到了1948年10月,司徒雷登向美国国务院请示:“吾人是否可以建议蒋委员长退休,让位于李宗仁,或其它较有希望组成一非共产共和政府与较能有效与共匪作战之政治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1949年卷),第325页。该请示表明司徒雷登对蒋介石已失去信心。就在当月,司徒雷登到苏州参加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第五届总议会。司徒雷登在演讲中一边宣扬基督教与民主的关系,一边慨叹他和与会人士一样,对目前的时局感到悲观。*司徒雷登:《基督教与民主》,《公报》第21卷第2期,1949年2月。中午餐毕退到内室休息时,燕大校友、杭州市青年会总干事王揆生问司徒雷登关于国内战事进展的情况。他黯然说道:“国民党政府腐败无能,中央军肯定抵挡不住共产军的进攻,最后胜负,只是时间问题!”接着他又含糊其辞地说:“希望李宗仁能有办法收拾残局,与共产党隔江而治,在政治效果上比赛成绩。我很主张宋子文、张群等人能到华南、西南各处,另创一个新局面。实在不行,只有退到台湾。”*王揆生:《回忆司徒雷登》,《上海文史资料存稿汇编》第2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第466页。司徒雷登的这番言论,与其发给美国国务院的请示含义相似。有所不同的是,这番话是在中国教会内部讲的,折射出来的意味已全然不复有1946年夏那种积极乐观的态度。想必在座的教会人士听闻之后,也心中有数。
另外一位美国在华传教士的代表人物是毕范宇,他的观点也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毕范宇和国民党之间交情匪浅。他与蒋介石夫妇有长久的私谊,经常以牧师身份为夫妇二人主持礼拜。抗战爆发后,毕范宇积极支持蒋介石抵御日本,为国民政府奔走呼吁。宋美龄还不时请毕范宇代为斟酌蒋介石向公众演讲时所需的《圣经》章节。*Chiow, Samuel Hsueh-hsin, Religious education and reform in Chinese missions: The life and work of Francis Wilson Price (1895-1974), Ph.D.dissertation, Saint Louis University, 1988, pp.263-264.可是,毕范宇也意识到当时中国人民渴望和平的情绪越来越普遍。国民党政府称这是中共宣传的结果,但实际上是因为在国民党政府的统治下人民的生活正变得举步维艰。国民党政府埋怨民众是短视的失败主义者,民众则指责国民政府无视人民疾苦。毕范宇还看到有许多人是典型的“骑墙派”,正在观望胜利的天平究竟会倾向哪方。这一派里,有为“中间道路”呼吁的自由主义者,也有只会考虑自身利益的投机分子。接着,毕范宇在文章中明确说到,他自己已经和各地的中国基督教同工谈过,大家的共识是教会过去已历经许多“风雨”,这一次应该也能扛过去。全国性的教会或机构团体的总部,除了个别之外,都决定坚守原地。即使国民政府将来要迁至华南或其他地方,大部分的教会大学、中学和医院也计划照常开放。*Frank W.Price, “Bitter Dilemma in China”, The Christian Century, December 15, 1948, pp.1366-1367.毕范宇的分析说明当时的普通民众对国民政府已经失去了信任,一些所谓的精英分子也不再真心支持国民党。他透露出中国教会的抉择,表明国民党已经被教会的大多数所抛弃。教会虽对中共有疑虑,但又希望能在新时代生存下来。
1949年初,曾在山西太谷工作的美国公理会传教士石子毅,则对国民党和中共作了深刻到位的比较分析。石子毅认为,国际因素固然在国共内战中有重要影响,但这主要仍是一场内战,更准确地说是中国过去革命的延续。这场内战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争取“民心所向”,或者说是“中国进入20世纪工业化世界所需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即究竟是中共还是国民党的思想理论体系,才有资格在将来带领中国步入工业化社会。石子毅认为“中共的成功不是单凭武力的结果,而是某种程度上恰恰继承了国民党过去未能完成的历史使命”,“民主、自由、社会理想主义、宪政、土地改革、民族主义、进步”这些理念正是国民党过去能取得人民拥护、站稳脚跟的原因。但是这些理念至今无法实现,故中国的理想主义者已经彻底“失望与倦怠”。对于许多人来说,中共是将来唯一有希望继续推动中国最基本改革的政党。他还表示国共内战这场革命无可避免,只有中共有能力将中国整合成一个国家。*Robbins Strong, “The Future of the Church in China”, The Christian Century, April 13, 1949, pp.462-463.
从1948年初到1949年初,这段时期局势变化迅速,国民党败象正日益显露。艾伦夫妇、司徒雷登、毕范宇和石子毅这些美国教会人士虽然在个人地位、政治立场、知识视野上有所差别,但他们的观察和思考都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事实:国民党已难成气候,中共的胜利毋庸置疑。他们还从多种角度总结这一成一败背后的复杂原因。进一步而言,传教士该支持谁、该抛弃谁,已一目了然。可以这样说,在传教事业的现实利益面前,大多数传教士愿意接受国民党的失败,迎接新政权的到来。
四、传教政策的正式调整
1948年末至1949年初,正是在华的各美国差会最为焦虑不安、手忙脚乱的时期。外在原因当然是三大决战对传教工作的不利影响及内心的震撼,内在原因则是差会的在华传教政策已到了必须调整的危急时刻。在北美国外宣教事业协会中国委员会*北美国外宣教事业协会(the Foreign Missions Conference of North America)是负责派出来华传教士的教会联合机构,主要由美国教会主导,加拿大教会只占其中一小部分。早在1925年,该新教机构就支持4492位传教士来华服务,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所有在华新教传教士总数的58%,亦相当于北美派驻海外传教士总人数的33%。1928年,虽然当时不景气的经济形势迫使许多传教士返回美国,但该机构仍然在中国花费约6,567,056美金,占其总预算的20%。二战结束后,北美在华宣教事业恢复较好之际,该机构又支持2246位传教士来华工作,占在华新教传教士总数的62%,其总预算的23%,即8455404美金投向了中国。1950年,北美国外宣教事业协会和“美国基督教联合委员会”(the Feder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 in America,成立于1908年)一起改组加入新成立的“全美基督教协进会”(Nation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 in the U.S.A)。北美国外宣教事业协会随后改为全美基督教协进会下的国外差会部,英文是the Division of Foreign Missions 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the Churches of Christ in the U.S.A。同时,它与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的关系,也变成为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一个机构。 “亚东委员会”(the Committee on East Asia)是北美国外宣教事业协会的下设机构,成员则由北美各海外宣道部代表组成。该委员会拥有独立的财政预算和干事编制,在推动战后中国基督教运动方面可谓不遗余力,起到领导作用。负责亚东委员会运作的干事,一般由熟知中国传教事务的前传教士担任。“亚东委员会”当时不仅为中国,也为韩国和日本的宣教工作提供意见。1947年2月前后,它改名为“中国委员会”(the China Committee),以便集中处理中国教会事务。的协调下,美国国内的各差会总部代表频频开会磋商,决定差会及传教士到底要不要离华。
1948年10月下旬,美国政府通知其在华北的美国公民,如果他们想寄送大号行李,须即刻去做;如果准备离开,最后期限是12月1日。在此之前,运输条件是允许的。英法两国领事也各向其本国公民传达了类似警告。事实上,这些便是撤离通知。11月10日《中国通讯》上,中国委员会在致各差会海外宣道部中国秘书的信中也明确表明,因为东北易手,各宣道部对下一步采取何种政策须作新的考虑。在此情形下,此信要求各海外宣道部必须回答下面的问题:(1)传教士需要撤离吗?(2)是否所有的传教士都要撤离?(3)如果他们撤离,那么准备去哪里?(4)要是在解放区工作,又该采取什么政策?*China-36, November 10, 1948, p.1.
11月16日,关于“中国局势”的会议在中国委员会处所召开。出席的代表有卫理公会、卫理公会女部、基督教青年会、信义会、美北浸礼会等在华主要差会总部的代表,以及中国委员会干事寇润岚。与会代表就目前中国局势发表意见,并相互通报了各自宣道部对此的反应。会议讨论得出以下决定:(1)就目前来看,基督教在解放区工作的机会比五六个月之前更有希望;(2)传教士撤退的计划应该和中国基督徒的负责机构充分磋商;(3)宣道部会给予那些撤离的传教士道德和物质上的支持,同时鼓励并全力帮助愿意留下来的传教士;(4)应该优先撤离那些年老体弱或是带有小孩的传教士;(5)重点应放在撤退传教士的重新布置上面,要么到中国其他地区,要么转赴日本等国家,而非简单地返回美国了事;(6)全盘考虑撤离传教士的问题,应该认识到因传教士国籍的不同,中共对他们的态度和处置也可能随之不同;(7)决定实行预付款制度,即美国方面会提前给中国的传教士或基督徒一部分款项,以便他们能及时购买必需的食物。*China-37, November 17, 1948, pp.2-3.
为探明美国政府对在华传教士去留问题的真实态度,由德惠廉、葛惠良及寇润岚组成的代表团又于12月3日前往华盛顿与美国国务院举行了一天的会议。代表团的这三位成员,以前都曾在中国传教多年,故他们处理此类问题颇有经验。美国国务院告知代表团:首先,虽然政府建议在华美国公民撤离,但只要有充分的理由仍然可以留下来,很显然在中国传教是此类理由之一;其次,政府在资金问题上不能保证能否输入解放区,但如果将资金或物资寄给尚在解放区的美国人,政府对此不会采取禁运措施;最后,关于赴华传教士的护照签发问题,虽然政府目前不准备签发前往中国任何地区的护照,但如果涉及传教士,只要没有随同亲属,同时确有“令人信服”的返回中国的理由,经过审核后就可能取得前往中国的护照。*China-40, December 10, 1948, p.1.美国政府对传教事业的支持,无疑增强了各差会总部在决定传教士去留问题上的底气。
12月13日,中国委员会又一次召集“中国局势”讨论会。会上仍然讨论了一些政策方面的事宜,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如何安排退回到美国的传教士问题。大家认为长期保留这些传教士以期望他日重返中国是不明智的,但一致同意各宣道部要把那些年轻的或经验丰富的传教士保留半年或更长的时间,因为半年后情况就会变得较为有利。会上还提出可否先派一队传教士到“中国的外围地区”,即先让他们在泰国、菲律宾、马来亚等地暂住下来,然后择机返回中国。此外,委员会讨论了物资贮存问题。卫理公会海外宣道部计划扩大其在华差会司库在资金使用上的权限,如果司库认为现在是一个采购物资的良机,那么其可从年度预算里先行支取6个月的资金。*通常情况下,司库可以自行动用1个月的资金,见China-42, December 15, 1948, pp.1-2.12月20日,中国委员会再次召集“中国局势”讨论会。会上透露的信息是,大部分在华差会和基督教机构的总部目前仍将继续留在上海,但是专门处理资金往来的办公室将迁至香港。*China-43, December 22, 1948, pp.2-3.
至此,在中国委员会的居中协调和美国政府的支持下,美国国内各差会总部下一步的中国宣教政策已经成熟。从挽留回国的传教士、人员重新部署至中国周边地区,以及在华差会和基督教机构的总部留沪这些措施来看,无不包含着其想让美差会继续在华工作这一核心愿望。但另一方面,将处理资金的办公室转往香港等部分措施又具有一定的防范意味。
与此同时,在华的各美国差会开始落实上述政策。公理会在华北(主要是北平、天津)的传教士分四种情况行动:第一种是乘坐信义会的飞机前往福州,那里有公理会的传教事业;第二种主要是老弱妇孺返回美国;第三种属于本来也想回国,但临时决定转赴菲律宾宣教;第四种是继续留在北平和天津。至于美国北长老会,根据11月19日差会上海总部的电报,所有在长江以北的传教士都安然无恙,只有江苏海州的财产遭民众抢劫和焚毁。差会上海总部建议危险区的传教士转来上海,另外也建议近期准备来华的传教士暂时不要出发。*China-38, November 24, 1948, p.2.至12月20日,北长老会海外宣道部同意其差会上海总部在香港租赁一幢房屋,作为退路*China-43, December 22, 1948, p.1.。根据12月13日的报告,安息日会的5个传教士家庭返回美国,其中的3个家庭来自北平和青岛,两个家庭来自上海。7个传教士家庭以及1名单身女传教士仍在上海,其中有人决心不惧任何艰难。华中的两个传教士家庭被派往台湾,另外有五六个家庭重新部署在华南地区。同时,约有10个家庭和一些年轻同工在香港岛以及九龙地区学习语言。*China-42, December 15, 1948, p.1.截至12月20日,美北浸礼会撤出中国的传教士有6名赴菲律宾,另有两名去了日本,只有两名快退休的传教士返回美国。此外,3名仍继续留在沪江大学,直到学期结束。还有3名在宁波,这是华东地区仅有不在上海的传教士。*China-43, December 22, 1948, p.1.卫理公会的大部分传教士留在了中国。据12月28日的报告,卫理公会有15名传教士在北平和天津,1名在济南,2名在青岛,没有一人从华西或福建撤出。华中和华东边远地区的传教士暂时撤往上海。差会(the Division of Foreign Missions)81%的传教士仍留在中国,女部(the Woman’s Division)的比例更是高达89%。*China-45, December 28, 1948, p.1.
以上几个美国差会的安排具有以下特点:其一,这些差会都将继续留在中国,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应该说,这一时期中共保护教会、维护宗教信仰自由的工作,给差会增添了不少期望。其二,在危急时刻,这些差会不得不重新调整传教力量。许多传教士从华北、华中地区转移至华东、华南、西南,甚至香港、东南亚等地。在华传教人数也有所减少,许多年老体弱或带有孩童的传教士离开了中国大陆,留下的基本上是骨干。另外,一些重要机构也迁至香港。其三,这种安排固然是因为躲避风险或是出于对中共的疑虑,但更主要的目的在于保存实力,期待形势转好就能返回原地,所以大部分撤出中国大陆的美国传教士都迁至中国周边地区。
1949年1月,就在平津战役即将收尾的时刻,北美国外宣教事业协会又召开为期4天的大会,来自美国61个基督新教教派的145名传教士代表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代表们几乎一致认为,传教士应继续留在中共所控制的区域。无论发生什么,差会董事会仍会想方设法鼓励传教士坚持留下来,即使他们可能会被禁止在教堂讲道或是在学校教书。北美国外宣教事业协会中国委员会的葛惠良表示,虽然一些保守差会的董事会发出质疑声,但他们相信基督教能在那里站稳脚跟,为此很乐意做一些尝试。*Religion: New China Hands? Time, Monday, Jan.17, 1949.4月5日,渡江战役开始前夕,国际基督教宣教协会负责人穆德从菲律宾赴韩国,中途突然在上海停留20个小时。他先召集中华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和各差会在沪传教士了解局势,后由协进会召集中外教会领袖72人,讨论如何应付中共领导的新政权,穆德向他们传达了“美国教会决不抛弃中国教会”*姚民权:《上海基督教史(1843—1949)》,上海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上海市基督教教会委员会,1994年,第230页。的重要信息。可见,在中国革命即将全面胜利的情形下,美国教会仍然坚定地试图继续维持其在华传教事业。
五、余 论
美国差会及传教士作出上述抉择,是深思熟虑的结果。每在历史转折关头,美国传教士出于维护自身在华传教利益的考虑,总是能适时调整传教政策。这当中最根本的一条,就是选择与最能保证中国稳定的政治力量合作。从晚清政府到北洋政府,再到国民政府,历次政权的更迭并没有让美国新教在华传教力量衰亡,其影响力反而不断增强。因此,面对国共内战所带来的危机,他们在审时度势后作出了非常现实的决定。但这并不代表他们就订到了留在新中国的“座位票”。首先,美国新教的入华与发展是近代西力东渐在宗教层面的体现,归根结底离不开武力和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以往美国传教士和中国政府之间的所谓交好,实际是有中国政府承认其传教特权这一前提。中共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政党,向来以反对帝国主义、争取国家独立为使命,所以要让中共今后永久承认美国新教在华传教利益,可能性本就不大。而且在当时国际冷战的背景下,国共内战造成基督教的“政治化”,使宗教与意识形态竞争挂钩。美国传教士对中共一直抱有的疑虑以及差会在重新部署传教力量之时的“两手”做法都证明了这一点。再加上美国传教士长期掌控中国教会,使中国基督教逐渐“美国化”,缺乏独立自主性。这些状况都是中共所不能容忍的。以上因素相互叠加,增加了美国差会及传教士能否留下来的不确定性。
中美两国关系的恶化让美国传教士留在中国的前景更为黯淡。1949年7月1日,毛泽东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正式宣布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中共倒向苏联不仅是国家政治上的大事,对美国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的前途命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8月2日,司徒雷登黯然离宁返美。8月5日,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发表《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在8月30日对白皮书所作的第五篇评论《“友谊”,还是侵略?》一文里,毛泽东毫不客气地指出美帝国主义比较其他帝国主义国家,更加注重对中国的精神侵略。基督教的教育、慈善和文化事业与美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之间被画上等号,司徒雷登则被看作是这些侵略事业的主要代理人之一*《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506页。。
1950年5月,周恩来在北京连续三次邀集吴耀宗、刘良模、涂羽卿、崔宪详等基督教领袖参加有关基督教问题的座谈会。周恩来在谈话中强调基督教受帝国主义利用是历史事实,要求宗教界人士参加反帝爱国运动,和帝国主义割断联系*参见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80—186页。。三次谈话的最大成果是直接催生了名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三自革新”宣言。7月28日,这份宣言正式公布。这是中国基督教会按照周恩来的讲话精神,所作出的一项政治表态。为了争取尽可能广泛的中国基督徒表态支持这份宣言,吴耀宗、刘良模等人还发起了“三自革新”宣言签名运动。中共中央对这份宣言以及签名运动的进展予以密切关注,并作出实际支持。9月23日,《人民日报》全文发表了“三自革新”宣言,并用3个版面刊登了全部1527人的签名者名单,还在第一版发表了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从社论来看,矛头所对准的主要是美差会及传教士。紧接着10月份抗美援朝运动全面展开。美国政府为从经济上扼制中国,于12月16日发表关于管制中国在美资产及对中国实施禁运的新闻公报。中共中央立即着手制定政策予以反击。12月28日,政务院发布在中国管制清查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公私存款的命令。*参见《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109页。1951年1月12日,周恩来就去年12月28日发布的关于管制清查美国财产、冻结美国公私存款的命令,作出解释:这是“指美国的财产,美人的经济企业和美人的存款,其他接受美国津贴的学校、教会、医院等则不应视为美国所有,因此它们的存款不应冻结,仍准动用”。周恩来的这个解释说明,当时的中央政府考虑到中国教会在经济上的现实压力,在存款使用方面给予了适当照顾,体现出政策的灵活性。12月29日,周恩来在主持政务院第六十五次政务会议时指出:过去我们曾设想,要把美帝国主义的残余势力从中国完全肃清,还需要三四年的时间。但最近美国宣布冻结我国在其境内的财产,这就给了我们一个很有利的机会,我们可以提早把美帝国主义在我国的残余势力肃清出去。会议通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的决定》等文件。*《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第109—110页。12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题为《肃清美帝在中国的经济和文化侵略势力》的社论*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50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6年,第995页。。
为有效执行政务院的决定,1951年1月9日,中共中央又下达“关于设立宗教问题委员会及宗教事务处的指示”,决定在党内和政府中设立专门处理宗教事务的部门*参见《中央关于设立宗教问题委员会及宗教事务处的指示》,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编:《统一战线工作》第4期,1951年,第75—76页。。3月15日至19日,第一次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在京召开。会议的目的是建立政府对宗教事务的行政领导机构,研究推进天主教、基督教反帝爱国运动。*参见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51年卷),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第182—183页。4月16日至21日,由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宗教事务处召集的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全国基督教团体会议在北京举行,与会的中国基督徒领袖纷纷起来控诉美帝利用宗教进行侵略的罪行。而在会议期间的4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要求美国差会“停止在中国的活动,并撤出中国国境”,中国基督教的传教工作“应该完全由中国教士来担负”。*《彻底割断基督教与美帝国主义的联系》,《天风》第11卷第17、18合期,1951年5月8日。7月24日,政务院正式公布《对于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处理办法》。其中第二条规定,在教会及团体中工作的美国人员应按下列原则处理:“(一)有反人民政府言行者应予撤职,其犯有罪行者,报请政府依法惩办;(二)自愿离开者准其返国;(三)无反动言行而教会及团体认为有需要留下并愿供给其生活者,可以续留,但不得担任教会及团体的行政职务。”第四条则规定:“外国差会如自愿将其在中国的财产(不包括土地)捐赠给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经政府审核批准后,中国基督教教会及团体得接受其全部或一部,但此项捐赠不得附有任何条件。”*《对于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处理办法》,《公报》第23卷第8期,1951年8月1日。
至此,美国差会及传教士彻底退出中国已
成定局。早在4月7日,曾是在华传教士的加拿大友人文幼章(James G.Endicott)就发表评论:1951年将是西方传教士从中国总撤退的一年。虽然这已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撤退,但1951年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次,它宣告“外国”的差会已经到了末日。*文幼章:《西方传教士在中国的失败》,《天风》第11卷第13期,1951年4月7日。文幼章讲这番话时,大概还有150名至200名美国新教传教士留在中国*China-106, April 12, 1951, p.3.。至1952年4月,只剩下40名左右的美籍传教士未能成功取得出境许可*参见邢福增:《基督教在中国的失败?——中国共产运动与基督教史论》,道风书社(香港),2008年,第240页。。美国差会及传教士最终离华标志着历经百年之久的美国新教在华传教事业的终结,中国基督教从此走上爱国爱教、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