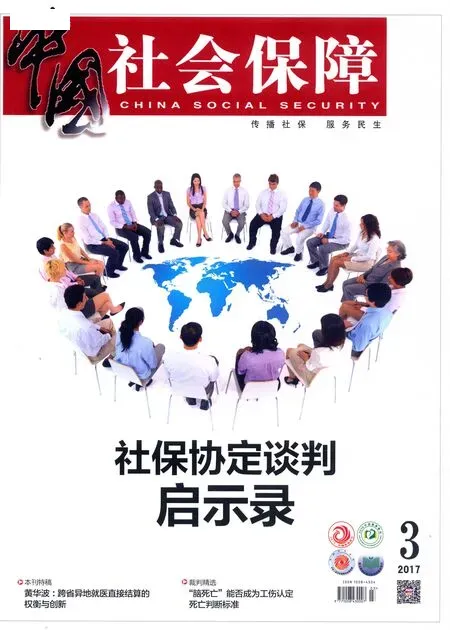“脑死亡”能否成为工伤认定死亡判断标准
2017-01-24向春华
■文/向春华
“脑死亡”能否成为工伤认定死亡判断标准
■文/向春华
核心提示:原告主张以“脑死亡”作为劳动者死亡判断标准,并据此主张劳动者属于“在48小时内经抢救无效死亡”应视同工伤,没有法律依据,不应支持。
基本案情
李某的丈夫马某系朝阳公司职工。2015年2月12日18时许,马某在工作期间突发疾病,朝阳公司安排人送其回家。家人于同日23时6分送其至市二院抢救,入院诊断为:脑出血、脑干出血、右侧基底节区出血并破入脑室、脑疝、糖尿病、肺部感染。次日,医院发出病危通知书。2月16日4时2分马某死亡。死亡记录载明入院时情况:患者因“言语不清,视物模糊半天,昏迷1小时余”入院;神志不清,深昏迷状态,对疼痛刺激无明显反应,GCS评3分,全身皮肤可见散发出血点,左侧前臂内侧可见豆粒大小出血斑;双瞳孔等大等圆,直径5.0mm,光反射消失;角膜反射消失,自主呼吸消失,两肺呼吸音粗,可闻及少量湿性罗音;心率74次/分,律齐,未闻及病理性杂音,双侧腱反射、腹壁反射消失,提睾反射微弱,双侧霍夫曼氏征、巴氏征未引出;APACHEII评36分,病死率94.9%。头颅CT示:脑出血并破入脑室(桥脑出血?),右侧基底节区及右侧顶叶高密度灶,考虑出血。住院经过及抢救经过:入科后立即予呼吸机辅助通气,维持全身组织器官血氧供应,予以止血。脱水降低颅内压,抗自山基、营养神经、改善细胞代谢等脑保护措施,控制血压,抑酸、化痰、抗感染,保护重要脏器功能,防治相关并发症,纠正水盐酸碱紊乱,维持内环境稳定等综合措施,后患者内环境较前呈一过性改善。患者系脑干出血,基底节区出血破入脑室,合并血液系统疾病,全身多脏器功能衰竭,无自主呼吸,血压需多种升压药物大剂量泵入维持,少尿,内环境紊乱,血流动力学极不稳定,患者处于疾病终未状态。患者13日凌晨2:00左右渐出现心率下降(最低至52次/分),伴有血压下降(大剂量多巴胺,去甲肾上腺素、垂体后叶素、间羟胺作用下血压最低至52/30mmHg),立即予盐酸肾上腺素运用、纠酸、葡萄糖酸钙运用拮抗高钾对心肌细胞损害作用、纠正电解质紊乱等综合措施,患者病情无改善,心率、血压逐渐下降,血氧饱和度测不出,至2015年2月16日4:02心电监护示心电图呈直线,患者心跳停止,抢救无效,临床死亡。死亡原因:脑出血。
2015年4月1日,李某就马某死亡向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并提交了工伤认定申请表等有关材料。人社局受理调查后于2015年5月7日依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于同日将该决定书送达当事人。李某不服遂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审判
一审法院认为,李某及朝阳公司对人社局认定的马某突发疾病、救治及死亡经过无异议,人社局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马某死亡超过了48小时,人社局据此认定马某不符合该情形而不予认定其为视同工伤,适用法律正确。李某关于“马某入院后处于疾病终末状态属于脑死亡,仅仅是上呼吸机等维持生命,并无实质性抢救治疗”等,因死亡时间应以医院的死亡记录载明的时间计算,李某的主张无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李某主张马某疾病与其职业有关的观点,按照《职业病防治法》和《职业病诊断与鉴定管理办法》的规定,应当在被诊断、鉴定为职业病后,根据《工伤认定办法》第四条第一款的规定,提出工伤认定申请。因马某是否属于职业病未经诊断或鉴定,故对该观点不予采纳。人社局受理李某的工伤认定申请后在60日内作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并告知了当事人有申请复议和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符合《工伤保险条例》有关程序规定。判决驳回李某的诉讼请求。
李某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称,《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本意在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没有法律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作出对劳动者有利的解释,“48小时”不应当机械、刻板的理解和运用,应当结合患者的病情和具体抢救措施综合认定。本案中,患者入院就转入重症医学科,并被确定为“处于疾病终末状态”,医院的抢救措施也仅仅是上呼吸机维持呼吸,患者死亡仅仅是时间长短的问题。综上,请求二审法院从《工伤保险条例》立法本意出发,结合本案具体情况,依法保护劳动者合法权益,请求依法改判,撤销被上诉人作出的不予认定工伤决定书,责令被上诉人重新作出工伤认定。
被上诉人市人社局答辩意见同一审答辩意见。
一审第三人朝阳公司意见同一审中发表的意见。
李某在一审举证期限内提供了其他法院支持“脑死亡”的行政判决书,证明依据脑死亡标准认定工伤在司法实践中已经有相关案例。
二审法院查明的案件主要事实与一审判决相同。
二审法院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第十五条明确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岗位,突发疾病死亡或者在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视同工伤。本案中马某在朝阳公司突发疾病,从医院出具的记录看,马某于2015年2月12日23时入院治疗,于2015年2月16日4时死亡,经抢救无效死亡超过48小时,不符合《工伤保险条例》视同工伤的规定。上诉人主张马某入院后不久就处于脑死亡状态应当认定为视同工伤,上诉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马某是在突发疾病后48小时内死亡。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依法不能成立,不予采纳。综上,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2016)苏07行终158号]
评析
█ 一、工伤认定司法实践中的“脑死亡”案例
在工伤认定中有个别案例采纳“脑死亡说”。例如在“盘璇诉长沙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工伤认定案”中,法院认为,关于死亡标准,我国并无法律上的明确规定,医学学术上存在“心肺死亡”和“脑死亡”的不同观点,《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本意在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没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情况下,应当作出对劳动者有利的解释。故“48小时之内经抢救无效死亡的”,应当按照脑死亡的标准予以解释,并据此撤销了社会保险行政部门不予认定工伤的决定。该案二审法院认为,该案中医院出具的《住院病人病情证明书》证明的“脑死亡”的时间认定及标准,与通行的《死亡证明书》证明的“心肺死亡”的时间及标准不一致,且在该案中两者相差较大,前者在“48小时”内,后者远超过“48小时”,但从保护工亡劳动者合法权益的立法目的而言,也并无不可。因为,“48小时”之内“脑死亡”仅靠呼吸机维持生命者,是放弃治疗还是继续抢救?如放弃治疗,明显有违人道,但是能够认定工伤;若继续抢救,一旦抢救无效,则无法认定工伤。所以,该案中,采纳“脑死亡”标准,于情于理于法更符合实际。从本案关键证据的证明力大小,死亡标准的人性化考量,结合工伤认定的立法原则,上诉人不予认定工伤不妥。原审法院撤销上诉人不予认定工伤决定,应予维持。
该判决理由背离了司法实践的一般标准,未深入分析死亡判定标准的学理与实践标准,未准确理解《工伤保险条例》的立法目的。正如前述马某死亡案一、二审法院所认为的,关于“脑死亡”的主张无法律依据,上诉人未提供充分证据证明马某是在突发疾病后48小时内死亡,亦即其主张马某入院后不久就处于脑死亡状态不符合法定的死亡判定标准。
█ 二、对死亡的判定标准无立法的明确规定,但这绝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可以随意采纳某种判定标准
目前,我国立法上确实未对何谓死亡即死亡的判定标准作出明确规定,但是这绝不意味着司法机关可以自行其是、随意确定死亡标准。死亡标准不仅对个人及利害关系人影响重大,甚至能决定其他公民的生与死,对于法律的正义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均具有重要意义。
就我国司法实践看,在大量涉及公民死亡判定标准的刑事和民事案件中,司法机关并无争议。由此亦表明在工伤认定中,司法机关采纳另一套死亡判定标准是极其不正当的。
█ 三、刑法和民法中采用“心跳停止说”(综合标准说)并无争议
“心跳停止说”又称“综合标准说”,是我国刑法中判定死亡的通用标准。脑死亡的认定标准还具有不明确性,有的人虽然被医院宣告脑死亡,后来却恢复了健康,因此在通常情况下,我国目前仍宜采取综合标准说,即自发呼吸停止、心脏跳动停止、瞳孔反射机能停止(张明楷: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6:847)。我国实践中仍以心脏停止跳动为生命终结的标志,任何人的生命权利在出生后和死亡前都受到刑法保护,不因对象的条件不同而有所区别(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461)。
死亡标准对于确定行为的性质和罪行轻重具有重要影响。如果以“脑死亡”作为标准确定受害人已经死亡,那么行为人实施“伤害”尸体的行为仅构成毁坏尸体罪,刑事责任相对较轻;而在同一事实中,如果采用“心跳停止说”确定受伤害人尚未死亡,则行为人杀害受害人则构成故意杀人罪,可能要被判处死刑。因此在刑事案件中死亡判定标准是确定的。
在民事案件中,我国司法实践关于死亡的时间原则上以心脏鼓动停止(呼吸断绝)时间为判断基准,唯自尸体摘取器官施行移植手术,其死亡得依脑死判定之(王泽鉴:民法总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1)。在我国,一般是以心跳和呼吸均告停止为自然人的生理死亡时间(申卫星,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69)。
作为例外,《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进行活体器官移植时,采用“脑死亡”标准,故不应将脑死亡者作为杀人罪的对象。
█ 四、个别案件采用“脑死亡说”违背法治原则
在工伤认定行政案件中采纳“脑死亡说”必然引发司法实践和社会实践的混乱和冲突,会引发诸多无法调和的社会冲突,违背基本的社会认知。
例如,对上述支持“脑死亡”的判决案例,对于同一死亡人员,医疗机构出具了《住院病人病情证明书》和《死亡证明书》,前者述及“脑死亡”的时间,后者则确定了“死亡时间”。很显然,医疗机构认为,“脑死亡”时间和“死亡时间”并非同一概念——亦即“脑死亡”并非死亡的确定标准,只有“心跳停止”时间才是“死亡时间”,死亡判定标准仍然是“心跳停止”。对于死亡的判断标准和死亡的准确时间,法官比医生更权威吗?法官显然不可以代替医生作出判定。
基于医疗机构的死亡判定意见,可以确定,公安、民政等其他政府部门及其他社会主体均会以“心跳停止”时间作为案涉公民的死亡时间。那么如果有死者近亲属或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该公民的户籍注销时间等提起诉讼,同一法院、同一法官也会以“脑死亡”为由撤销公安机关以及其他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吗?更进一步说,该法院在其他所有的涉及公民死亡案件中,均采纳“脑死亡”判定标准吗?几乎可以肯定,该法院不会这么做。这就意味着一个人被法院判决死亡了两次!这是何其荒谬!不同法院,特别是同一法院、同一法官,在判断自然人是否死亡时,采用不同标准、得出不同结论,是极其不当的。
法治的基本要求是“同样事实,同样处置”,违背这一原则必然侵害和践踏法治。对于死亡如此重要的事实,不管立法有没有明确规定,死亡均应秉持同一处断标准,否则是对法治原则的违背,是对正义和公正的背离。
█ 五、认为《工伤保险条例》立法本意在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并依此对法律条款进行解释,违背法律解释论和法律原理
在支持“脑死亡说”的案件中,司法机关的主要理由是,《工伤保险条例》立法本意在于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因此在立法未作明确规定时,应按对劳动者有利的方式处置。
首先,这一立法目的的概括不符合法律目的理论。法院的这一解释方式被称为目的解释,但是,法院对目的解释的适用违背目的解释方法及其理论。任何法律均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即便《刑法》《公司法》亦如此。难道我们可以说《刑法》《公司法》对于涉及公民权益问题未作明确规定的,就可以按照有利于公民的原则作解释吗?民法不存在这样的解释方法。目的解释,不能用法律的一般价值作为具体规范的立法目的。
其次,在其他任何部门法的法律适用的目的解释中,均无如此宽泛地适用法的一般目的的。目的解释有其一般的范式和理论,在各部门法中是通用的。在工伤保险法律适用的目的解释中,必须符合目的解释方法的基本要求。
再次,在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时,以保护个人权益(实际是利益而非权利)为出发点,致侵害法治、损害法律的平等、公平与正义,这本身就是非正义的,它虽然使个案中个人利益得以最大化,却是以牺牲多数人、更为长久的权益为代价的,即便从功利主义考量,也是不足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