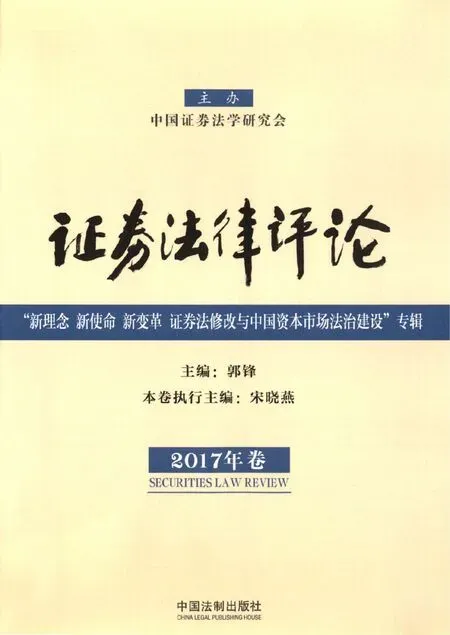跨境证券交易的冲突法逻辑与法律适用规则的完善
2017-01-24王克玉
王克玉
跨境证券交易的冲突法逻辑与法律适用规则的完善
王克玉*
国际商事交易从传统的物权交易、融资性贸易,再到证券跨境交易,均需要与之匹配的法律适用规则。资产的权利化和权利的证券化对传统的法律适用规则提出了挑战,债权法律适用规则与物权法律适用规则的简单组合不能适用现实的需要。实践表明意思自治这一法律适用原则,正在成为跨境金融性商事交易的首选原则,但对于新型经济体和转型过程中的资本市场秩序的冲击和影响亦应充分评估,我国的证券法律适用规则在借鉴意思自治时应予适度改造与完善。
跨境交易 证券权利 法律适用
一、内国法律适用规则应对跨境商事交易的不足
以物权单证化、资产证券化发展起来的融资性金融工具,包括公司股份、债券、基金份额等投资证券的买卖等,正成为现代国际商事交易的重要内容。在制度层面上,无论是从实体法的缔造还是冲突法规则的演变,正在塑造着现代国际商事法律制度的变革。
“商品是天生的平等派”,商事交易法律天生是“国际的”。然而,从国际商法的历史轨迹看,从其萌芽到中世纪商事法规则逐渐发展起来的“国际性”特征,却随着16、17世纪主权观念的强化,直至19世纪后期的“国内化”,经过了一段衰弱的历程。例如,以欧洲大陆国家为代表的将跨国商事活动纳入民族国家成文法的管辖之下的立法模式,使得国际商事交易关系一度依赖国际私法规则指引的国内法予以调整。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现代国际商事活动的触角,从传统的国际贸易、海商、运输、票据、代理、借贷等商事活动,伸向了国际保险、国际投融资、国际支付、知识产权、工程承包、破产、信托、保理、证券等领域,除了商品和服务的交易活动外,资本经营活动,例如投资、收购、证券发行、产权交易、企业控制等,成为国际商事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国际商事交易活动空前发展。法律适用领域中的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在统一实体法为代表的现代商人法规制之外,传统的商事法律适用规则正经受着现实挑战。
对于调整国际性的交易,以萨维尼为代表的“法律关系本座”说,尽管具有了“双边性”“国际性”“客观、适当”等优点,但其内在的逻辑仍然是基于内国法上对“本座”的建立和发现,国际商事交易的法律关系其实仍未摆脱“国内化”认知和规制的思维。同样,旨在摒弃单一“本座”缺陷的“重力中心说”“最密切联系说”等法律选择方法,仍没有摆脱以国内法定位国际商事交易的局限性。尽管国际私法规则在促进国际商事交往乃至构筑“国际民商事新秩序”方面的作用不可低估,但在现有的法律选择模式下,让国际商事交易走出国内法上的掣肘,摆脱一国的“民族性”“地域性”和国内法上的秩序安排和这种秩序安排背后的“权力意志”的限制,是徒劳的。
因为,一国国际私法上的法律选择规则,其本质是对国际民商事活动从国内法出发分配立法管辖权。这种安排的后果,要么是适用外国的国内法,要么是适用内国的国内法。尽管二者偶尔有所“调和”,但这种基于国内法的对国际秩序的安排,再辅以公共秩序保留制度,更多的情形是国际商事交易关系最终由内国法院适用了内国的法律。
诚然,在当今以主权国家为主体的国际社会,跨国商事交易不可能摆脱主权国家的属人和属地管辖。一国不管出于单边立场或者多变立场,通过特定的国际私法规则,将某种国际商事活动纳入本国的立法管辖权的思路,即使作为国际商事规则的“剩余角色”出现,〔1〕See Jan H.Dalhuisen,International Commercial,Financial and Trade Law,Third edition,Hart Publishing Oxford and Portaland,Oregon 2007,P175.但仍不失为固守本国特殊利益的重要措施。但是无论如何,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交易活动以及商人创新所带来的金融产品的交易,国内法上的立法管辖安排,以及由此所指向的准据法,将无法平等看待相关当事人的权益,亦无从保障商事交易的公正、安全和效率的价值。据此,内国的国际私法规则的改造和改良已成为必然。
二、金融类产品贸易对传统法律适用规则的冲击
(一)传统的物权交易
以货币换取动产物权权益是传统国际商事交易的主要目的,对此,传统的国际私法规则给出的解决方法是寻找物的所在地法,这无论是从“法律关系本座”抑或是从“最重要联系”考量出发,一度确立了一般性贸易中的物权权益的冲突法规则。
但是,这一准则在应对跨国转移或运输中的物品时,因所在地无法确定而茫然失措。问题还在于,即使货物本身有时没有跨境转移,但当作为同一合同交易项下的货物分处不同的国家时,对于货物的物权性利益,不论是否附有条件,抑或是作为担保物权的权益,单一的物之所在地法亦无所适从。
(二)过渡中的融资性贸易
当国际贸易与融资性需求紧密联系时,其通常表现是融资买卖和附条件的买卖。例如,保留所有权即为一种融资买卖或附条件的买卖。在现代融资交易的框架下,保留所有权的交易与分期付款的买卖、融资租赁、投资证券的回购,应收账款的买卖等融资买卖关系,并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在保留所有权的买卖关系中,无论是卖方还是买方分别在受制于合同设定的付款条件,从而分别对该资产拥有相应的物权性权益。同理,融资租赁中的出租人与承租人,分别对租赁财产拥有的物权性利益也是显而易见的。再如,在应收账款保理业务中,应收账款的转让,很多情况下是建立在保理人能够收取应收账款的条件之上。如果这个条件不能满足,应收账款的权益将回归至融资人一方。
上述融资性买卖的共同特征,均是对基础资产的所有权进行有条件的转移,甚至对同一所有权事项进行了“分割”。在这个交易中,融资与贸易成为交易关系并行的两个内容,物权类权益与金融类权益同时需要得到保障,法律适用规则不应只限于对物权类权益的保护,单一的“物之所在地”不可能再充当着权益分散状态下的连结点。
(三)物权单证的交易
不仅如此,当物权性权利形态发生变化时,物权法上的实体性规则和冲突法规则就需要进一步调整。例如,以可转让票据和物权单证为例,它们分别代表着一定的金钱债权和物权请求权。对于这些已经“单证化”的资产,伴随着权利的让与和转移的实际,一种的国际的、跨国的所有权观念(transnational concept of property rights)在实践领域逐渐发展起来。〔1〕“跨国所有权”以及类似的“国际所有权”概念,是新近许多学者在国际贸易、国际融资、跨国投资领域论述的重要话题之一。其内容涉及动产与不动产、有形资产与无形资产的买卖、投资、担保,甚至关涉国家的征收和征用。其核心在于保障跨国财产权人的正当权益。本文限于篇幅和主题无从详述。仅凭提单或票据的交付,受让人便获得一种独立的所有权地位。在当事人持有或占有这些票据或单证的情形下,便会得到特殊法律规则的保障,即谁持有单证谁便拥有单证下是物权或债权。这种独立的财产权权益的保障制度,已经开始超越内国的法律适用规则。
(四)资产证券化后——证券的交易
在资产证券化的概念下,可予证券化的资产不仅仅是物权类资产,而且还包括债权、知识产权类资产,当然最基础的是股权、企业控制权等权益资产。由此所形成的另一形态的财产权——证券权益就更为特殊。其特殊性首先表现为,即使在基础资产没有跨境,但证券的发行、交易、存放和持有却可以跨界进行,由此,相关的法律适用规则必须重新设计。
随着资产证券化的深入和证券交易规则的完善,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以来,股票、债券以及其他投资证券在持有和转让的方式上发生了两个重大变化:第一,传统的证券转移交付朝向非流动性或者说无纸化方向发展;第二,持有证券的方式从投资人占有权利证书转由投资人通过中介机构提供的账户登记间接持有证券。〔2〕Christophe Bernasconi,Harry C.Sigman,The Hague Conven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ertain Rights in Respect of Securities held with an Intermediary,10 Unif.L.Rev.n.s.p120,2005.对此,需要考虑的是,作为非流动性和无纸化的证券,该如何判定证券权益的归类并进而确定其法律适用规范,第三,如果需要使用证券所在地的法律,那么“所在地”应如何确定?
对于第一个问题,客观上,证券本身的特质亦决定了证券无法按照有形和无形、动产和不动的分类方法进行归类。但事实上,各国对于涉外的或者跨境的证券类权益,有的将之划入“物”的范围,视其为无形财产;也有国家把证券归入债的范围,作为债权对待。对于证券的法律适用规范,大致可分为四种情形:第一,把证券视为债权,证券法律适用与其他债权法律适用合并规定,例如《波兰国际私法》《奥地利国际私法》《匈牙利国际私法》等;第二,将证券视作财产权,同物权、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划为一类,如《法国民法典国际私法法规》(第二草案)则把股票的法律适用、股票转让人与持有人之间、持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法律适用,与物权、知识产权的法律适用合并规定;第三,把证券的法律适用与公司事项结合起来,例如,《瑞士国际私法法》第10章“公司”中规定了因发行股票和债券而产生的请求的法律适用,美国《第二次冲突法重述》也把股票的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规定置于“商业公司”项下,另外,由于没有传统的概念法学和逻辑法学的“包袱”,1994年《统一商法典》在其第5章直接设定了投资类证券的专门规则,并将证券权利从财产权(物权)的体系内分离出来,直接设定独立的“证券权”(security entitlement),投资者作为证券权人,对券商等中间人不再拥有证券追及的权利,仅对与其有直接合同关系的中间人享有“证券权”;第四,除上述情形外,还有的国家规定证券适用发行人的属人法,例如上述《匈牙利国际私法》第25条规定,如果证券涉及社员权利,证券权利和义务的产生、转移、消灭和生效适用属人法。
可见,传统的国际私法对于证券权利的法律适用规范的不同情形,进一步说明了证券权利属性的复杂程度和法律规制统一的艰难。作为折中的做法,许多国家勉强使用并围绕着由“证券所在地”这一传统物权连结点,〔1〕例如,《波兰国际私法》第25条规定:“在交易所所为的法律行为之债,依交易所所在地法,但当事人已选择准据法者不在此限。”《匈牙利国际私法》第27条规定:“通过证券交易所订立的合同,适用证券交易所所在地法。”《罗马尼亚国际私法》第55条规定:“不记名有价证券转让时的转让条件及效力适用证券所在地法律,此种法律同样适用于证券的后继所有人之间及其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法国国际私法法规》(第二草案)第246条规定:“股票转让人与持有人之间的关系,及持有人与第三人之间的关系适用不记名证券所在地法或者适用指示证券支付地法。”《韩国国际私法》(2001年修正)第21条规定:“涉及无记名证券的权利的取得、丧失和变更适用作为其原因的行为或事实完成当时该无记名证券所在地的法律。”由其指引应适用的法律——不论是将证券权益归于债权、物权、人身性权利、抑或是公司权利事项。
对于第二个问题,在证券直接持有模式下,国际私法对于“证券所在地”的确定,一般区分记名证券和不记名证券。对于不记名证券,取决于代表证券的权利证书的所在地法律,而对于登记的证券来说,证券所在地往往被理解为发行人的所在地或者是证券登记簿的所在地。〔2〕Christophe Bernasconi,Harry C.Sigman,The Hague Conven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ertain Rights in Respect of Securities held with an Intermediary,10 Unif.L.Rev.n.s.p121,2005.然而在现代证券交易的无纸化和间接持有模式下,确定证券的所在地是一项十分困难的事情,证券所在地这一连结点已不再像过去那样具有可确定性,从而使传统的“所在地”这一连结点的适用在跨国间接持有的证券领域陷入困境。
同时,与证券属性的分歧相比,对于登记在券商名下的投资者的证券,其权利属性的分歧就更为明显。在许多国家,证券投资者对于登记在券商账户中的证券权益,作为一种财产性(物权)权利;也有国家认为投资者对中间人享有的是一项合同权利,后者负有向前者交付或转移特定种类和数量证券的义务;还有国家主张,投资者相对于被他人间接持有的证券的权利,被当作信托法律关系下的受益人的权利,属于信托权利、信用证券账户、对可替代物的共同财产权,抑或是名义上的集合证券、担保权利、某种一揽子财产权、合同权利或者其他权利等等,不一而足。〔1〕Christophe Bernasconi,Harry C.Sigman,The Hague Convention on the law Applicable to Certain Rights in Respect of Securities held with an Intermediary,10 Unif.L.Rev.n.s.p130,2005.跨境融资和跨境证券交易,急需国际社会对此领域的权益属性予以界定并就其法律适用规则予以调整。
三、证券权利交易中法律适用规则的改进
(一)信托法律适用规则对于金融性权益适用法律的启示
如果对现代国际金融商事交易的发展加以审视,尤其是对比两大法系对于该领域的调整和规制,我们便不难发现一种新型的所有权制度正逐渐呈现出这样一个发展脉络:如果说现代国际商法作为现代媒介正将金融产品的物权性内容引入国际社会,尤其到了一个传统上成文法体系无法容纳的阶段的话,那么,在这方面,普通法国家的衡平法原则提供了一种更实用、和更灵活的示范。
在信托领域尤其如此。在衡平法支撑的信托领域,普通法国家创造性地赋予了受托人对于信托财产普通法上的所有权,和受益人对于受托财产的衡平法上的所有权制度,此谓信托法上的双重所有权制度。而事实上,普通法国家的衡平法制度,正发展成为国际间商事交易的保障性规则,并对崇尚统一所有权体系的大陆法系国家来说,也发生着一定的影响力。例如,对于附条件的或临时性的保留所有权的买卖中,大陆法系国家在其国际商事领域的实践中都给予一定程度的认可。对于更为复杂高级的所有权制度,例如浮动抵押、期货的转让,回购、融资租赁等作为附条件的所有权制度,也予以接受。
如果我们深入信托制度的本身,再来审视这种所有权安排的话,不难发现,信托关系法律适用规则的逻辑起点,恰恰是基于合同的安排体制。正因如此,在现代商事尤其是金融交易领域,尤其在信托或类似信托的产品结构中,附条件的和临时的所有权法律制度,将呈现出在一种更加开放的、合同化的所有权安排的基础上,通过更为简要的所有权证书转移机制,和对善意购买人和财产持有人的侧重保护机制。这种机制在物权的确定性方面,更有利于善意受让人、善意参与人以及第三人权益的保护。而且,在附条件的买卖和融资性贸易领域,以及浮动抵押领域,对第三人的正当权益的保护已成为国际社会一致性的性需求。〔1〕See Jan H.Dalhuisen,Dalhuise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Financial and Trade Law,Third edition,Hart Publishing Oxford and Portaland,Oregon 2007,P145.
正如学者指出,在物权权益的问题上,保护的重点将会转移到对实际占有人的保护上,而不是停留在所有权的抽象理念和推定占有上。〔2〕See Jan H.Dalhuisen,Dalhuisen on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Financial and Trade Law,Third edition,Hart Publishing Oxford and Portaland,Oregon 2007,P145.这种保护在本质最终通过对侵犯物权利益的行为进行制约来实现,然而制度的起点,却是源自合同上的一种权利安排。正因如此,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信托法律适用及其承认公约》,首选的法律适用规则便是当事人意思自治,再辅之以特定连结点基础上的最密切联系原则的指引,加上对域外信托产品下的特殊性物权利益予以承认,很好地解决了诸如“所有权分割”和“所在地”难以确定的问题,为金融产品的国际交易的法律适用提供了制度借鉴。
(二)跨境证券交易中法律适用的国际模式
跨境证券交易和持有的无纸化和电子化,一方面改变着人们对证券属性的判断和对证券权利内容的重新设定,但另一方面,意思自治原则与多重法律选择范式的组合,正在成为国际社会的倾向性实践。在这方面,2002年12月13日海牙国际私法会议通过的《关于间接持有证券的某些权利的法律适用公约》(下称《证券法律适用公约》)就是一个例证。
为了适用跨国证券交易的需要,尤其是解决间接持有证券交易法律权益的不确定性问题,《证券法律适用公约》首先规定由当事人在账户协议中约定的特定国家的法律来调整跨境证券交易和持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当然,公约规定只有中间人于账户协议签订时在该准据法所属国设有营业所,上述约定才是有效的,意即当事人选择的用于调整其跨境证券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必须是券商营业所所在国家的证券法。在此基础上,公约进一步规定,如果根据没有选择定准据法或者无从确定应适用法律的,但在书面账户协议中明确和清晰地表明该账户协议是由券商的某一办事机构签订的,则该办事机构所在国的证券法即为准据法。如果仍然无法确定准据法,那么就以书面账户协议签订时或(若无书面账户协议)证券账户开立时券商成立地法作准。最后,若准据法仍不能确定,则以书面账户协议签订时或证券账户开立时相关中间人的营业地法或(在有多个营业地时)主营业地法为准据法。
根据上述,《证券法律适用公约》在法律适用规范的设定上采取了意思自治原则和PRIMA(Place of the Relevant Intermediary Approach)原则相结合的原则,即允许双方当事人在一定的范围内选择法律,并将法律选择限于那些通过分支机构与中间人有实际联系的国家的法律,从而保证了当事人所选法律与证券持有活动的实际关联性,并对跨境证券交易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确定提供了一个尺度,帮助相关当事人对于权利的行使和义务的承担有了稳定的预期,这种法律的预先确定性对于保障当事人的正当权益和金融市场的平稳运行至关重要,并将进一步推动证券跨境交易的发展。
四、对我国跨境证券交易冲突法规则的检讨
(一)现行立法的技术问题
对于国际商事和金融法律秩序来说,规则的完善和进步将促成国际商事惯例,或者经由国家间的同意而上升为统一的实体法。如果不是这样,那么只能依赖国内法上的进步和完善。国内法的完善其实包含证券实体法与证券冲突法两个方面的内容。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从国家的证券实体法上的差异无从消除的情况下,国内法上的冲突法规则便承担起指引“适当”准据法的义务,这无论是基于国内金融秩序的稳定还是保障正常的国际商事交往,都是必要的。
在这方面,从海牙公约等国际社会的立法模式看,遵循国际商事交易的“国际性”,尊重“商品天生的平等性”和“商人的创造性”,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法律应成为法律适用的首要原则。毕竟,任何具有所有权属性的金融产品,包括证券权益的交易,往往是通过合同的方式进行。当然,也必须受制于国际商事领域中的一些根本性原则的规制:例如“保护善意购买人”原则,保障国际商事交易的确定性和安全性原则,以及保护内国的公共秩序与公共利益原则。在此基础上的任何法律适用规则,当与上述实体性法律原则相吻合,这些法律原则既是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法律的制度前提和保障。如果说,现代金融产品交易对传统物权法律适用规范的提出什么样的改造要求的话,把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作为该领域的首要原则,便是其中之一。
从这个角度,对我国现行国际私法立法有什么检讨的话,现行《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第39条关于有价证券的法律适用规则倒是一个显著的话题。从现实情况看,我国国内证券的发行和交易已基本实现了无纸化,证券的发行和交易通过中央证券电子交易系统来完成,任何证券的交易都只需在账面上作相应的记载即可完成。在证券持有模式上,我国目前采用的是直接持有和间接持有相结合的“双轨制”模式。对于境外投资者投资境内外资股(B股市场),境外投资者通过QFII投资我国国内证券市场,以及我国境内投资者通过QDII投资境外证券市场的,包括“沪港通”以及正在筹备的“深港通”,均采用证券间接持有和交易模式。随着“一带一路”战略推进,我国与沿线国家的证券资本市场的合作以及国际化的推进,跨境投资类权益和证券交易愈发普遍。然而,现行《法律适用法》第39条规定的有价证券适用有价证券“权利实现地”法律,以及其他与该有价证券“有最密切联系”的法律机制,并不能有效解决“所在地”不确定性的问题,即现行立法在技术上,并没有给出一个确定的连结点,这无论对于交易的当事人的合理预期,抑或是对于裁判者的自由裁量而言,无法确定一个明确的尺度。此外,现行立法对于国际社会首选的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也没有做出应有的回应。
(二)“意思自治”能否指向“进步的”准据法?
接下来的问题是,意思自治能否指向“进步的”准据法?不可否认,在特定的民商事领域,相对超前的或完善冲突法规则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实体法的不足。例如在产品责任等涉及消费者权益的领域,可以通过借助完善的冲突法规则指引到相对健全的产品责任法制完善的法域,从而实现对消费者的充分的保护和救济。但是,金融消费者领域尤其是证券资本市场的消费者和中小投资者而言,在证券资本市场法制不完善、监管缺位、越位的情况下,企图借助冲突法规则对金融消费者的保护无异于本末倒置。因为证券资本市场法制具有其系统性与特殊性,金融证券交易关系的法律适用规则是整个证券资本市场法制的一个部分,而无法独立于这个整体性的法制系统。
例如,中国资本市场法治正经历改革和转型,证券发行注册制改革等重大制度正在论证过程,证券资本市秩序、监管制度和投资者保护制度等尚需进一步完善。以投资者司法保护机制为例,目前证券市场上的司法救济还仅限于虚假陈述和有限的内幕交易情形,而且规定了行政处罚、刑事制裁等前置程序。证券的民事赔偿责任制度、包括损失的确定机制、举证责任规则都不完善,证券集团诉讼制度尚未确立和完善,证券仲裁也没有发展起来。相较而言,在发达的资本市场上,基于最低联系原则和效果原则上的长臂管辖权机制,以及完备的司法救济机制,在司法层面可以较好地实现对投资者和交易者合法权益的保护,有效维护本国的证券资本市场法制秩序。在中国法院不能有效实施司法管辖、立法上尚没有完善跨境司法管辖规则、以及当事人鉴于中国司法保护水平现状而选择外国管辖的可能性等境况下,跨境证券交易中的意思自治选法规则,可能会更多地导致外国法的适用,从而使我国的国内法上的治理与管辖目标落空。
在设定证券法律适用制度的过程中,却无法回避冲突法背后的实体法利益。所以在证券发行交易实体法、证券诉讼法等救济法制以及证券监管法不完备的情况下,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法律适用规则的需求,并不迫切。从某个角度,《证券法律适用公约》本身无益于提升监管水平和投资者利益的实体性保护,它仅仅是满足证券交易中的法律的适用问题,本质上属于私法性条约,而中国目前的资本市场和证券市场尚未确立有效、高效的监管机制,证券市场最急需改进和完善的则是监管体制和监管效果。
至少从资本市场法制建设的发展历程看,跨境证券交易和持有中的意思自治法律选择规则,其后果是将目前应属于国内法管辖的事项,交由当事人的选择的法律或中介机构的所在地的法律调整。从制度竞争的角度,当事人选择的法律当然是成熟资本市场的法律,因此这就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资本市场法制可能无从得以进入国际金融证券的调整领域。至于机构所在地连结点,较之发达国家的证券中介机构、投资银行,发展中国家的金融服务尚被视为幼稚行业,证券中介机构的竞争力无法与发达国家的中介机构匹配,因此在最终适用的准据法上,仍将是发达国家的中间机构的所在地和成立地以及主营业地的法律。
综合上述,对于我国证券跨境交易的法律适用规则的完善,首先应着眼于完善证券发行、交易、监管和投资者保护等实体性证券法律制度。其次,借鉴当事人意思自治选择法律的方法。第三,在赋予当事人选择准据法的同时,对于跨境证券交易、持有的法律适用规则,区分交易、持有、担保、处分等不同法律关系,辅助设置多个可予确定的选择型连结点,因为在完备的资本市场法制环境下,固然可以使用整体性法律选择方法,但是对资本市场法制尚未完备的情况下,与其对应的只能是分割式的法律选择模式。第四,基于我国证券市场的监管利益、投资者利益以及社会公共利益的限制性因素,规定在特定情况下只适用中国的法律。此谓完善我国跨境证券交易法律适用规则的适当路径。
*王克玉,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法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