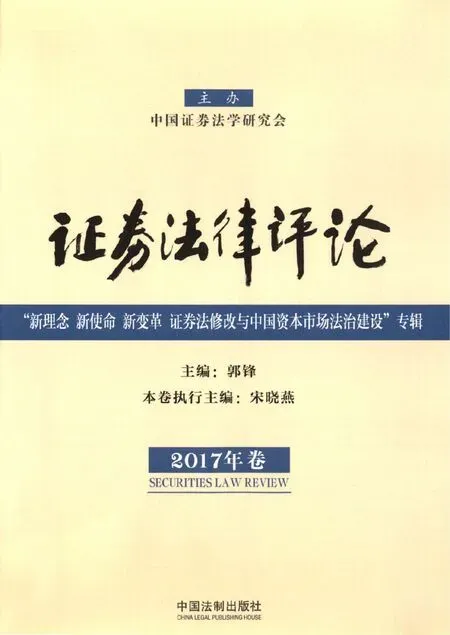证券法大宗持股权益变动法律责任研究
——以非合意并购为视角
2017-01-24钟洪明
钟洪明
证券法大宗持股权益变动法律责任研究
——以非合意并购为视角
钟洪明*
大宗持股权益变动制度旨在提高证券市场透明度和保护中小投资者合法权益,但在我国证券市场实践中尤其是非合意并购中,投资者屡屡违反该制度确立的公开义务和停止买卖义务,目标公司则利用相关立法漏洞采取各种限制股东权利的反收购措施。对权益变动规则和义务之违反成为证券市场的顽疾,其中首要原因在于我国现行收购制度愈发难以满足现行市场环境下各方主体的规则需求。为此,需要深入研究和反思现行大宗持股权益变动及其法律责任立法存在的问题。在此基础上,建议利用证券法修订契机,借鉴境外立法经验,尽快弥补相关法律漏洞,强化大宗持股主体的义务和责任。同时,进一步加强证券监管执法,形成监管合力,共同实现资本市场的澄明和健康发展。
大宗持股 信息披露 停止买卖 法律责任 证券法修订
在我国证券市场股权分置改革完成以后,上市公司的股票基本实现全流通,公司股权结构逐步向相对集中、分散或相对分散演变。同时,随着证券市场机构投资者的培育和发展,专业机构投资者不断发展壮大且“股东积极主义”明显抬头。〔1〕参见卢文道、方俊:“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之争的最新态势与监管路径研究”,载《证券法苑》(2014)第十三卷。在诸多因素的叠加共振下,证券市场的“举牌”与非合意并购(hostile takeover)日益剧增。〔1〕敌意收购又被称为恶意收购或者非合意并购。由于恶意收购之称存在合法性负面评价之嫌疑,为避免理解歧义,本文主要采用非合意并购的表述。在此过程中,投资者通过二级市场逐步买入目标公司股份,当其持股达到一定比例时即成为公司重要股东,依法应履行信息披露及相关义务,是为大宗持股权益变动(以下简称权益变动)制度。然而在我国,作为该制度核心且被视为资本市场生命线之一部分的披露规则,却屡屡成为被轻松突破的“马其诺防线”:投资者无视规则超比例买卖股份,目标公司不顾合法性争议肆意采取反收购措施,并俨然成了市场顽疾之一。严重者,还引发目标公司股价大幅波动、公司治理陷入僵局乃至侵害中小投资者利益等不良后果,导致资本市场一度“乱象丛生”。
上述情况的出现,虽有利益冲突的客观原因所致,但是毋庸置疑,现有权益变动及收购等法律制度不能适应证券市场发展变化的要求,各方主体的规则需求和现行制度供给之间的张力与日俱增,一些规则不够清晰、明确和合理导致了监管与执法实践上的困惑乃至窒碍难行。〔2〕参见张子学:“完善我国大额持股披露制度的若干问题”,载《证券法苑》(2011)第五卷,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目前,我国正致力于建设一个“融资功能完备、基础制度扎实、市场监管有效、投资者合法权益得到充分保护”的资本市场。以此为指导,本文以大宗持股权益变动法律责任为视角,对权益变动及所涉制度的适用和改革进行探讨,希冀为其立法完善和法律适用提供些许建议。
一、我国证券权益变动制度的立法构造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明确提出,大额股份持有情况的透明是投资者的一项基本权利。〔3〕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Principles ofCorporate Governance51(2004).而作为一项旨在提高市场透明度、促进市场效率、优化公司治理、防范操纵市场与内幕交易、保护公众投资者利益的制度安排,大宗持股信息公开制度已经为全球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所采用。〔4〕参见张子学:“完善我国大额持股披露制度的若干问题”,载《证券法苑》(2011)第五卷,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总结而言,大宗持股信息披露(Blockholder Disclosure)是指投资者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上市公司股份或者其他上市权益证券达到法定比例时,或者此后其持有量发生法定比例的增减变化时,依法披露权益持有情况的制度,具体可分为拥有或控制股份达到法定比例时的持股信息披露和其后增减股份达到法定比例时的持股变动信息披露。
(一)我国证券权益变动立法体例之流变
在我国,大宗持股权益变动制度的引入可溯源至1993年《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根据其第47条的规定,任何法人直接或者间接持有一个上市公司发行在外的普通股达到5%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3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证券交易场所和证监会作出书面报告并公告……持有一个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普通股后,其持有该种股票的增减变化每达到该种股票发行在外总额的2%时,应当自该事实发生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向该公司、证券交易场所和证监会作出书面报告并公告;在依照前两款规定作出报告并公告之日起2个工作日内和作出报告前,不得再行直接或者间接买入或者卖出该种股票。
上述制度后来为1995年《证券法》及2002年《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和《上市公司股东持股变动信息披露管理办法》所吸收并改造。2005年《证券法》修订时,在基本沿袭原有规定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补充完善,而证监会2006年亦对《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进行了相应修订,经其后多次修订后,共同奠定了现行权益变动规则的主要框架体系。〔1〕此外,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业务规则亦有关于收购及股份权益变动的内容,其对市场参与者具有直接约束力。
综上,在证券法律法规层面上,我国权益变动始终与收购统一规定于上市公司收购制度章节中。在部门规章层面,则经历了2002年对收购和持股变动分别制定规章到2006年合二为一的过程,并形成目前将权益变动附属于上市公司收购制度的状况。从实践来看,这一立法体例削弱了权益变动制度的独立价值,在认识上和执行中引发了混乱。〔2〕参见张子学:“完善我国大额持股披露制度的若干问题”,载《证券法苑》(2011)第五卷,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
(二)我国证券权益变动义务的基本界定
目前,我国证券权益变动规则主要见于《证券法》(2014年)第56条和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14年,以下简称《收购办法》)第二章等。综合其规定,证券市场大宗持股主体负有信息披露及停止买卖两大义务:信息披露义务是指投资者及一致行动人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持有上市公司已经发行股份总数的5%时,以及其后其所持上市公司已发行的股份比例每增加或者减少5%时,向证券监督管理机构、证券交易所书面报告、通知目标公司并进行公告的义务。停止买卖义务是指披露义务人在披露期限内以及其他法定期限内,不得再行买卖该上市公司的股票。对于信息披露规定,学界通常又称之为“公开规则”;而对于停止买卖规定,又谓之“慢走规则”。
与境外立法相比,我国权益变动制度的最大差异在于慢走规则。有观点认为,证券法慢走规则系我国独创,其确立与彼时股权分置及证券信息传递等原因相关,目前是否有必要继续保留值得讨论。〔1〕参见吴建忠:“上市公司权益披露规则与慢走规则法律适用”,载《证券市场导报》2013年第1期。另有学者将其称为“异化的预警式披露”,认为其加重了不以获得控制权为目的的收购方进行收购的成本与披露的负担,不利于不以获得控制权为目的的收购或出售活动。〔2〕参见郑彧:“上市公司收购法律制度的商法解读”,载《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就立法宗旨而言,证券法慢走规则的确立是为了防止信息披露时的内容和投资者控制股份的变动情况有出入,对社会公众造成错误诱导,损害他们的利益。〔3〕参见周正庆、李飞、桂敏杰主编:《新证券法条文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221~222页。尽管慢走规则有其历史乃至现实合理性,笔者仍赞同对其进行重新评估并在立法上作出取舍。现阶段则应重点考虑如何准确执行该规则,因为实践中超比例买卖股份行为几无例外地同时违反公开和慢走规则,对于这种信息披露与交易行为相互交织的违法行为如何监管及追责,是执法和司法实践中不容回避的重要问题。
此外,需要指出,我国证券权益变动规则区分了通过证券交易所的证券交易和其他权益变动方式。《证券法》第56条和《收购办法》第13条规定的交易方式是指通过证券交易所进行的交易,包括通过竞价交易系统或者大宗交易系统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行为。〔4〕参见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执行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具体事项的通知》(上证公字[2009]3号)及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严格执行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等有关规定的通知 》(2005年12月2日)。鉴于通过协议转让、行政划转、执行法院裁定、遗赠等方式引致的大宗股权变动往往需要一次性完成,要求其遵守慢走规则既不切实际亦无法操作。鉴于此,《收购办法》(第14、15条等)增加了通过协议转让及其他方式导致权益变动的规则,弥补了证券法相关规定的不足。
(三)证券权益变动违法行为之典型形态
大宗持股主体异于普通持股主体而负有特殊的义务,违反者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对权益变动违法行为进行类型化界定,有利于准确适用法律和追究违法者的法律责任。根据我国法律法规规定及证券市场实践,大宗持股主体常发之违法违规行为可列举如下:
1.内幕交易及短线交易。上市公司的股权较为分散,持股5%以上的股东就会成为公司的大股东,并由于其持股数量较大而控制公司,并可能直接控制公司营运,易于接触公司重要信息,故《证券法》将其规定为内幕信息的知情人。〔1〕参见周正庆、李飞、桂敏杰主编:《新证券法条文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123页。由此,大宗持股主体作为内幕知情人应当遵守《证券法》第76条关于“在内幕信息公开前,不得买卖该公司的证券,或者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的规定。同时,还应遵守第47条关于短线交易禁止之规定。否则,前述主体的行为可能构成内幕交易、短线交易。
2.信息披露违法。权益变动中的首要义务是向监管机构进行报告、通知上市公司并进行公告,同时根据信息披露一般要求保证披露信息的真实、准确、完整。实践中,绝大部分超比例买卖股份之行为人信息披露违法体现在不按照规定报送有关报告并及时作出披露。但事实上,境内外立法对于大额持股披露违法规定中,都同时包含报送的报告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且对于两类披露违法行为规定的法律责任基本相同。此外,如果构成收购而收购人不按法律规定公告、发出收购要约、报送收购报告书等,同样构成违反证券法律法规的行为。
3.限制期内交易股票。《证券法》56条规定,投资者在持股或者增减持股份达到法定比例时的限制期限内不得买卖上市公司的股票,在监管实践中常被界定为限制期内交易股票。如前所述,实践中权益变动违法行为往往同时违反信息披露和停止买卖两方面的义务。如在中国证监会最近作出处罚的阎克伟信息披露违法及限制期内交易股票案中,阎克伟控制使用两个账户连续交易“易世达”股票,至2016年1月29日合计持有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6.33%,但在首次超过5%时既未履行报告和披露义务,也未停止买入。〔2〕参见http://www.csrc.gov.cn/pub/fujian/fjjxzcf/201701/t20170117_309623.htm,2017年2月15日最后访问。
以上仅对较为常见及根据法律规定较为可能出现的权益变动违法行为之典型形态作出概括式列举,事实上在法律适用过程中出现法条竞合或者聚合的情况甚为常见,由此要求执法者或者裁判者准确区分各类违法行为和适用相关法律,以保证立法旨意顺利实现。
二、证券权益变动法律责任之界定及其主要争议
根据我国证券法律法规的规定,大宗持股主体负有信息披露及在限制期限内禁止交易的义务,违者应承担相应法律责任。然而,由于法律规定的模糊性或者不尽科学,导致对上述任一违法行为的定性及责任界定均存在理解争议,而对于二者相互交织的违法行为如何适用法律则存在更大的认识分歧。
(一)限制期内交易与内幕交易责任的承担
根据《证券法》之规定,持有公司股份5%以上的投资者不得进行内幕交易等禁止交易行为,否则将根据该法第76条、第195条、第202条和第233条承担相应的民事和行政责任,构成犯罪者还将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与此同时,《证券法》第76条第2款对内幕交易的例外情形作出规定:持有或者与他人共同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收购上市公司的股份,本法另有规定的适用其规定。有观点认为,此为豁免违规增减持股票行为构成内幕交易的规定,而更多学者则对此论持反对意见。〔1〕参见李振涛:“我国上市公司大额持股变动的法律责任探析”,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1期;陈洁:“违规大规模增减持股票行为的定性及惩处机制的完善”,载《法学》2016年第9期。
本文认为,上述规定是在平衡内幕交易防控和便利上市公司收购双重价值后所作立法,不能简单理解为对大宗持股主体所有交易行为构成内幕交易的豁免。相反,持股5%以上主体只有在遵守《证券法》第47条不得进行短线交易、第76条第1款不得在内幕信息公开前泄露该信息或者建议他人买卖该证券、第56条依法披露及限制期内停止买卖等规定的基础上,在有关收购方案公告前买卖目标公司的股票,方可能具有合法性。否则,其交易行为仍可能构成内幕交易。
(二)信息披露违法责任及疑似法条竞合
大宗持股主体违反报告和公告义务,在无特别规定前提下适用证券法信息披露违法之法律责任规定自不待言。然而,证券法对相关信息披露法律责任存在多个规定,由此引起了法条适用的竞合。
《证券法》第193条第1、2款规定,对违反规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30万元以上60万元以下的罚款。根据第213条的规定,收购人未按照规定履行收购的公告等义务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10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的罚款;在改正前,收购人对其收购或者与他人共同收购的股份不得行使表决权。而《收购办法》第75条对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信息披露及其他相关义务的行为规定相同的法律后果,即由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采取监管措施以及改正前限制表决权。由此,出现了违反第56条信息披露规定时应如何准确适用法律的问题。
从证券执法实践来看,对于超比例买卖股份违反披露义务的行为,基本援引第193条进行处罚。〔1〕参见上海新梅案件中国证监会宁波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王斌忠)》([2015]1号)以及易世达股东超比例增持股票案件中中国证监会福建监管局《行政处罚决定书(阎克伟)》。对于何以统一适用第193条之规定,目前仍缺乏相关法律或执法解释。有论者认为,第56条规定于《证券法》“上市公司的收购”中而第213条针对收购未履行法定义务规定法律责任,故违反第56条适用第213条的规定应无疑义;监管部门适用第193条的规定出于从重处罚所考虑,因为其规定的罚款幅度更高。〔2〕参见李振涛:“我国上市公司大额持股变动的法律责任探析”,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1期。本文认为,从第213条规定来看,其明显指向收购人在上市公司收购(狭义)也即取得或者巩固公司控制权过程中的违法情形,〔3〕关于收购之界定,可参见马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监管制度解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627页。另有学者指出,把所有持股5%以上的投资者均视为收购人既不符合立法本意也不符合市场实践。另有学者指出,把所有持股5%以上的投资者均视为收购人既不符合立法本意也不符合市场实践,参见陈洁:“违规大规模增减持股票行为的定性及惩处机制的完善”,载《法学》2016年第9期。因此监管机构对于尚不构成控制权变更的权益披露违法行为适用第193条的规定更加符合立法本意。
(三)权益变动违法责令改正及其实现
责令改正是指有关主管机关责成违法行为人自行改正错误行为、消除违法后果,它不是一种行政处罚。〔4〕参见周正庆、李飞、桂敏杰主编:《新证券法条文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35~536页。《证券法》第193、213条等关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中规定了责令改正,第213条还规定在改正前收购人对收购的股份不得行使表决权。《收购办法》第75条规定,收购及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违反披露及相关义务的,中国证监会责令改正且在改正前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得对其持有或者实际支配的股份行使表决权。综上,责令改正实现与否直接影响投资者的股东权益,可谓事关重大。
在超比例买卖股份案件中,对于信息披露违法行为通过补充披露实现责令改正并无太大争议,但对于与限制期内交易同时交织的行为如何责令改正成为实践中的一大难题。如对违反《证券法》第56条的行为根据第193条责令改正,仅限于对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改正,而不包括对限制期内交易的改正;即使根据第213条责令改正,仍无对限制期内交易责令改正的责任内容。由此,《证券法》对违反第56条规定在限制期内交易之法律责任未作规定,构成明显法律漏洞。《收购办法》虽然规定对违反披露及相关义务的行为责令改正,但对于限制期内交易的改正如何执行并无具体规定,笔者认为其主要原因在于:在缺乏上位法的情况下部门规章不宜另行创设,以防止于法无据或者对上位法的“越位”。
由于如上法律漏洞的存在,实践中对于违反《证券法》第56条行为的责令改正往往通过补充披露而实现。如在上海新梅案件中,一审法院认为:责令改正的事项应由证券监管机构依法作出决定,是否全面履行改正义务应由作出上述决定的机构审查认定。宁波证监局作出处罚决定责令被告改正违法行为、给予警告并处以50万元的罚款,而被告缴纳了罚款,并补充披露了相关权益变动报告书。迄今为止,相关证券监管部门未进一步责令被告改正其违法行为,或要求其进一步补充信息披露,故原告提出的被告改正行为尚未完成的诉称意见缺乏相应的事实及法律依据。〔1〕参见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5)沪一中民六(商)初字第66号民事判决书。此外,在易世达案件中福建证监局决定的责令改正内容为:责令阎克伟改正,在收到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3日内对超比例持股情况进行报告和公告。本文认为,监管机构和司法机关对于违反《证券法》第56条的行为根据第193条责令改正在现行法律法规下并无不妥,以完成补充披露和未被进一步责令改正的标准来认定责令改正业已实现亦具有较为充分的事实和法律基础。令人遗憾的是,相关执法和裁判结果均明显遗漏了对限制期内交易行为的责令改正。由于上述问题之主要成因在于法律规定付诸阙如,未来应通过立法完善以作根本解决。
还需指出,在阎克伟超比例买入易世达股票案件中,监管机构认为投资者的行为同时违反了《证券法》第35条的规定从而适用第204条进行处罚。〔2〕第35条规定:依法发行的股票、公司债券及其他证券,法律对其转让期限有限制性规定的,在限定的期限内不得买卖。第204条规定的法律后果包括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买卖证券等值以下的罚款。本文认为上述法律适用值得商榷,因为从立法旨意来看上述条文主要针对存在禁售期证券之交易而规定,〔3〕如IPO限售股、董监高所持股份、收购人所持被收购公司的限售股等。与第56条所指停止买卖之限制存在较大差异。〔4〕在上海新梅案件中宁波证监局并未援引《证券法》第35、204条进行处罚。而且,即使按照第204条进行处罚,监管机构对于如何责令改正也无明确指向。因此,通过上述法律适用填补违反第56条继续交易缺乏责任规定之立法漏洞,并无足够说服力。笔者认为更为妥适的方法是,适用第202条之规定并确定责令改正的内容为责令依法处理非法持有的证券,〔5〕参见李振涛:“我国上市公司大额持股变动的法律责任探析”,载《法律适用》2016年第1期。理由在于:持股5%以上主体唯有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条件下在收购方案公开前买卖目标公司证券才不构成内幕交易,如违反第56条等规定继续交易的,仍应纳入第76条第1款之规制范围而构成内幕交易,并引发第202条规定之适用。
(四)对违法主体持股限制表决权的适用与认定
上市公司收购的目的在于获得或者巩固对公司的控制权,如果收购了一定股份却未获得相应的表决权,则将导致收购目的落空。鉴于此,为促使投资者严格遵守法律规定,对收购人违法收购的股权限制表决权为诸多国家和地区所采纳。在我国,对于限制股东权利相关规定的理解和采用存在不少争议。
1.关于表决权限制的主要规定
根据《证券法》第213条之规定,在收购违法行为改正前,收购人对其收购或者共同收购的股份不得行使表决权。《收购办法》第75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存在违法行为被责令改正的,在改正前不得对其持有或者实际支配的股份行使表决权。两相比较可知,《收购办法》的规定更加明确和具体:首先,在主体方面,法律规定为收购人而《收购办法》规定为上市公司的收购及相关股份权益变动活动中的信息披露义务人;其次,《收购办法》明确义务主体在违法行为改正完成前对持有或实际支配的股份不得行使表决权,也即其持有的全部股份被限制行使表决权。反之,《证券法》第213条的表述读不出限制全部股份的意思。〔1〕马骁:《上市公司并购重组监管制度解析》,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页。总体而言,《收购办法》第75条对于《证券法》213条的规定作了扩充性解释。
针对《收购办法》第75条,各界较为一致的看法是其扩大了证券法上表决权限制范围,将因与上位法冲突而无效。〔2〕陈洁:“违规大规模增减持股票行为的定性及惩处机制的完善”,载《法学》2016年第9期。笔者赞同应严格按照证券法规定对超比例买卖股份的投资者进行表决权限制,同时建议反思导致上述规定出现效力瑕疵的深层原因:《证券法》未严格区分一般权益变动和收购,第56、193条均缺乏表决权限制的规定,而第213条主要针对上市公司收购违法行为作出规定,导致执法部门难以根据上述规定对第56条违反者限制表决权。在此情况下,《收购办法》旨在弥补证券法相关规定不足时,极易陷入上位法不足或者与之冲突的困境。鉴于此,建议在证券法修订中分别对权益变动和收购违法行为完善法律责任规定,在此之前可对《收购办法》先行修订。
2.限制股东权利之反收购措施的效力认定
近年来大量上市公司将限制敌意收购人股东权利作为反收购措施置入公司章程,其中不乏“偷梁换柱”“越俎代庖”等情况,其效力判断成为执法和司法实践中的又一重大问题。〔1〕如涉及诉讼的案例包括上海新梅股东新盛公司诉开南公司等证券欺诈责任纠纷案、宝万之争中万科工会诉钜盛华等损害股东利益责任纠纷案、京基集团诉康达尔董事会决议无效案、国风集团诉胡氏兄弟违规购买西藏旅游股份案等。总起而言,非合意并购中利用权益变动等规则限制股东权利的常见情形包括:第一,降低权益变动披露义务的标准,如伊利股份2016年5月9日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公司章程修正案将大宗持股比例降低至3%。第二,目标公司自行判断举牌或收购行为的合法性并作出权利限制。如康达尔董事会于2015年11月26日作出决议,认定京基集团等构成恶意收购并限制其表决权、股票处分权、收益权以及继续购买股票交易权。第三,扩大限制权利的范围。如在山大华特、伊利股份等公司章程中,对于其定义的恶意收购者规定不得享有公司董事、监事的提名权,董事会有权拒绝其行使除领取股利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在西藏旅游案件中,拉萨市中级人民法院裁定公司举牌方在案件判决生效前禁止行使股东权利,包括投票权、提案权、参加股东大会的权利、召集和主持股东大会的权利。
笔者认为,尽管举牌方超比例买卖股份具有违法性,但是股东权利是一种基本的民事权利,根据我国相关法律规定,非依法律或者行政法规规定的条件和程序,不得随意限制和剥夺,而表决权是股东权的重要组成部分。鉴于此,对于上述各种限制股东权利情形可作如下判断:第一,降低大宗持股比例标准属于对法律法规的“偷梁换柱”行为,不符合《证券法》第56条的规定,不当加重了股东的法定义务,不应具有拘束力。第二,权益变动和收购行为的合法性判断以及责令改正等监管和处罚措施的作出和认定,应当由证券监管机构或者司法裁判机构依法进行。因此,类似康达尔这种自行认定股东构成恶意收购并对其股东权利限制的行为不具法律效力。〔2〕2016年6月14日,深圳市福田法院判决康达尔董事会作出限制京基集团股东权利的董事会决议因违反法律规定而无效。第三,证券法和收购办法等明确规定在满足条件时仅限制违法人收购股份的表决权。为此,超出法律规章规定的主体、股份数额和具体股权内容的任何限制均不具有法律效力,对相关股东领取股利以外的其他股东权利如提案权进行单方限制的作法于法无据。此外,根据前述理解,不宜对收购主体所持全部股份限制表决权。
三、境外市场大宗持股披露立法与实践及其启示
在境外市场,持股预警信息披露属于股东透明度的强制披露规则范畴,历来为政策前沿问题,引起学界高度关注,且长期以来相关国家和地区均致力于制定实施有效的大额持股披露规则。〔1〕See Dirk Zetzsche,Challenging Wolf Packs:Thoughtson Efficient Enforcementof Shareholder Transparency Rules,CBC-RPSNo.0044/09.2010,available at:http://ssrn.com/abstract=1425599.目前,这一制度在美国、英国、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地区等立法中均有明确规定。
(一)美国和英国
美国对于大宗持股信息披露的主要规定为《证券交易法》第13(d)条及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据此制定的规则和附件。根据其规定,投资者在取得5%的公司股权时,需在10日内向SEC披露其持股情况及目的,此后每增加1%的持股需及时补充修正原来的披露。此外,持有少于20%的股份且不寻求获得或影响发行人控制权的消极投资人,可以提交附件13G进行简单报告。〔2〕参见[美]路易斯·罗思、乔尔·塞里格曼:《美国证券监管法基础》,张路等译,法律出版社2005年版,第445~445页。由于不存在宽限期限内停止买卖的规定,收购方往往在此期间内继续买入目标公司股票,以致于在披露时可能远超5%的持股比例。此外,无论SEC的执法还是美国法院的司法裁判,对于违反13(d)规定的行为均采取较为宽松的处理态度,一般只要求更正披露。美国对于大宗持股信息披露采取放松管制的进路,主要原因在于其并购法律对于公开收购股份的行为采取中性立场,既非鼓励亦非吓阻,并力求公平对待收购人与目标公司。〔3〕参见赖英照:《证券交易法解析》(简明版),台北自版2016年3月,第134页。
在英国,大额持股披露制度主要由金融服务局(FSA)根据《2006年公司法》制定之《披露与透明度规则》所规定。根据上述规则,获得目标公司3%以上金融商品的,英国以外的公司必须在4日内、英国公司在2日内进行报告,此后持股比例变动达到1%的增减也须履行报告义务。比较而言,英国对大额持股的披露要求明显比美国甚至其他国家严格。但是,关于英国对于持股预警信息披露违反者如何处罚的规定和实践并不清楚。〔4〕John C.Coffee&Darius Palia,The Impactof Hedge Fund Activism:Evidenceand Implications,Columbia Law and EconomicsWorking Paper No.459.2014,available at http://ssrn.com/abstract=2496515.
(二)日本与韩国
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区分公开收购和大量持有股票等状况的信息披露。根据其第27条之23、25规定,持有上市股票及相关有价证券的比例超过5%时,应当在成为大量持有者之日起5日内提交报告书,每增加或减少1%以上的应提交变更报告书。〔1〕参见朱大明译:《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105页。违反报告义务或者报告书重要事项有虚假记载的,将被处以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500万日元以下罚金或者两者并罚;如果报告书形式不完备或有虚假记载,内阁总理大臣可以命令提交订正报告书,处1年以下有期徒刑或100万日元以下罚金或者两者并罚。〔2〕参见庄玉友:《日本金融商品交易法信息披露制度研究》,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54~155页。
韩国《资本市场法》亦明确区分公开收购和大量持有股份等状况的报告。根据该法第147条之规定,大量持有(即5%以上)人应自大量持有之日起5日内向金融委员会和交易所报告,持股合计变动超过1%以及重要事项发生变更的均应履行上述报告义务。第150条规定了对违反大量持股报告义务的规制措施:对于超过表决权发行股份总数5%的违反份额,在总统令规定的期间内不得行使表决权,金融委员会可以责令其在6个月内处分该违反份额;如果持有股份是为了影响发行人经营权的报告人,自其应该报告的事由发生之日起,至报告日以后的5日为止,不得追加取得该发行人的股份等或者行使该持有股份等的表决权;如果追加取得股份亦不得行使表决权,且金融委员会可以责令其在6个月内处分该追加取得部分。此外,该法第445条还规定,对于不进行报告者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单处1亿韩元以下的罚金。〔3〕参见董新义译:《韩国资本市场法》,知识产权出版社2011年版,第116~117、347、353页。
从日韩立法来看,明确区分收购披露和权益披露规则及法律责任,对于违反者的处罚“呈现逐渐趋严之势,甚至从民事权利层面的违规者持股表决权限制向刑事制裁方向发展,”〔4〕傅穹:“敌意收购的法律变革:资本挟持治理?”,载清华大学商法研究中心:《公司再造:法治与实践》,21世纪商法论坛第十六届国际学术研讨会2016年10月。对此趋势的确不可不察。
(三)台湾地区
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43条之1第1项规定了在集中市场或店头市场取得公开发行公司的股份逾10%的申报义务,对于违反者第175条第1项第2款规定处新台币24万元以上240万元以下的罚金。2015年7月“企业并购法”修订时于第27条规定:为并购目的,取得任何一公开发行公司已发行股份总额超过10%之股份者,应于取得后10日内,向证券主管机关申报其并购目的及证券主管机关所规定应申报之事项;申报事项如有变动时,应随时补正之;违反前项规定取得公开发行公司已发行有表决权之股份者,其超过部分无表决权。该规定的立法理由在于加重违反揭露规定之处罚,以收成效。〔1〕参见刘连煜:《新证券交易法实例研习》,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6年增订十四版,第179页。
综上,台湾地区对于持股申报制度的立法趋势是强化义务,在“证券交易法”规定罚款制裁基础上,为强化投资人履行申报义务又修法增加对违反者剥夺表决权的处罚且规则清晰易行,颇值借鉴和参考。
四、完善我国权益变动法律责任制度之构想与建议
综合如上分析,本文建议我国利用证券法修订契机,筑牢证券市场制度篱笆,完善权益变动及其法律责任制度,并进一步强化监管执法。在此过程中,既要学习借鉴境外市场相关经验,更要密切结合本土实践,以实现制度与证券市场实际的最大契合性。
(一)立法理念和立法体例再反思
从境外大量持股信息披露制度看,美国采取放松管制的进路,韩日和我国台湾地区则实施日趋严格的立法和司法。应予指出,美国模式与其董事会中心主义、商业判断规则和集体诉讼等制度构成整体性的均衡系统,单独移植借鉴某一制度极易出现失灵。我国证券市场处于新兴加转轨阶段,信息披露是证券市场的薄弱环节,既是肘腋之患亦为心腹大患。鉴于此,完善我国证券权益变动制度应当强化主体义务并对违反者施以严格法律责任。就此而言,日韩及我国台湾地区立法模式更值得借鉴。
我国证券法未对权益变动与收购作实质区分而统一立法,《收购办法》虽意在区别不同规制内容,但终因上位法的阙如而难克竟全功。诚如有学者所指出,取得股份达一定比例有可能是发动收购之先兆,但其间并无绝对必然之关系,〔2〕曾宛如:《证券交易法原理》,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2年六版,第159页。大额持股与收购确有本质不同理应对其区别规制。为此,建议借鉴日韩立法,在证券法修订中通过不同章节对二者作出明确区分。事实上,2002年我国证券监管部门曾区分收购和持股变动分别制定规章,这一实践无疑是我们完善权益变动立法体例的重要本土经验。
(二)完善具体制度之构想
根据强化义务和严格责任之理念,我国证券立法宜尽快弥补有关法律漏洞,实现权益变动法律责任的明晰与多元化,充分发挥法律法规的威慑及吓阻功能。
1.权益变动临界点及变动幅度。在我国,一直存在将持股信息披露临界点由5%提高到10%的呼声。〔1〕参见李东方:“上市公司收购监管制度完善研究——兼评‘《证券法》修订草案’第五章”,载《政法论坛》2015年第6期。从境外相关立法来看,美国经历了从10%到5%的嬗变,而迄今除台湾地区外主要境外市场都采取5%的标准。大陆首次确立5%的比例以来沿用至今并未出现明显窒碍,同时上市公司股权结构逐步趋于分散,因此建议维持现行5%的权益变动临界点规定。此外,为强化权益变动义务并适应证券市场股权结构发展趋势,建议参酌境外立法,将持股变动披露比例由现行的5%调整为1%。〔2〕尽管台湾地区持股申报起点为持股10%,但其持股变动申报比例为1%。
2.完善责令改正的法律规定。目前对于违反《证券法》第56条的违规举牌行为适用第193条处罚为合理选择,但是由于后者仅针对信息披露违法规定法律责任,缺乏对限制期内交易行为的责任内容。因此,如果未来立法不专门针对权益披露规定责任条款,应通过完善第193条弥补立法漏洞:明确对于违反第56条的行为适用本规定,且对于限制期内交易行为责令改正。关于责令改正的内容,建议借鉴韩国立法并比照我国《证券法》第202条的规定,明定为责令依法处理行为人非法买卖部分的证券。
3.限制表决权内容之完善。根据强化权益变动义务之理念,本文赞同对大宗持股主体违规买卖部分的股份限制表决权,由此需要《证券法》作出补充完善:一方面,第193条增加对于限制期内交易行为责令改正的同时,规定在改正前持股主体不得行使表决权;另一方面,明确规定仅限制违法增持部分的表决权。〔3〕笔者认为,对于超比例减持股份的情形如何限制表决权亦应作相应考虑,否则立法有失周延。此外,在证券法修订之前,《收购办法》可先行作相应修订。
4.刑事责任之完善。证券法规定的法律责任包括民事、行政和刑事责任,在立法技术上对于民事和刑事责任仅作原则性规定和个别补充性规定而主要规定行政法律责任。〔4〕参见周正庆、李飞、桂敏杰主编:《新证券法条文解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522页。但事实上,我国刑法并未专门针对大宗持股权益变动违法行为作出规定,至于对其是否适用违规披露、不披露重要信息罪等规定有待明确。鉴于此,建议通过立法完善或者法律解释,明确大宗持股违法行为的刑事责任。
(三)强化证券执法之建言
近年来,我国证券监管机构确立了依法全面从严监管理念,加大了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打击和查处力度,自律监管机构亦充分发挥其一线监管职能,一大批超比例买卖股份等违法行为被立案或处理。但是,由于法律法规的缺陷以及执法资源有限等原因,在部分案例中也出现了监管缺位或者效率不足的情况。〔1〕如实践中出现了大量可能涉嫌违法违规的反收购章程条款,但尚未发现证监会根据法律及《收购办法》第50条等规定进行责令改正的案例。而且,无论法禁如何严苛,证券市场权益变动、收购与反收购中各种违法违规行为以及争议问题仍会层出不穷。
对此,本文同意部分争议应当通过争斗股东等市场主体协商解决,但由于上市公司股权之争具有较强的外部化效应和市场影响,〔2〕参见卢文道、方俊:“我国上市公司控制权之争的最新态势与监管路径研究”,载《证券法苑》(2014)第十三卷,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对于协商不成以及久拖不决不利于目标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问题,证券监管机构应当及时亮剑,依法作出监管或者处罚措施以定分止争,并不断提升执法效率。同时,建议自律监管机构充分利用限制交易等监管措施或纪律处分,发挥监管合力,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钟洪明,西南政法大学与四川省社会科学院联合培养博士后工作站研究人员,四川省社科院法学所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