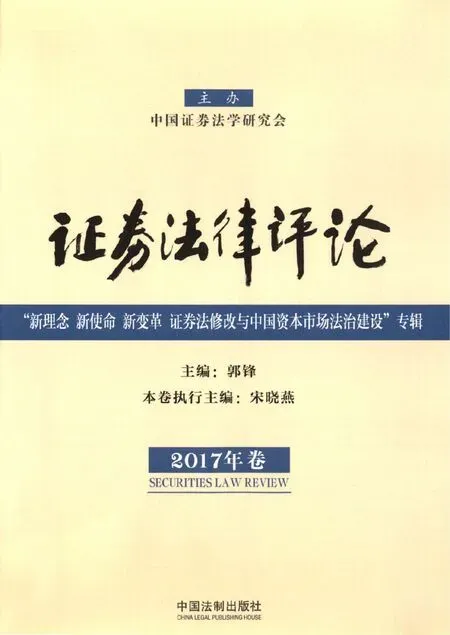操纵证券市场的不法所得与损害赔偿计算
2017-01-24张玮心
张玮心
操纵证券市场的不法所得与损害赔偿计算
张玮心*
我国有实证研究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关于操纵市场的规则标准化程度低和剩余立法权分配不明,操纵者往往通过人头账户进行大量股票的买卖交易,而证监会对于此种操纵市场的行为很难及时侦查执法。又目前在操纵者的违法所得计算与证券民事赔偿制度的建设未臻完备下,建议应以投资人的实际损失作为操纵者赔偿数额的计算标准。惟投资人的损害金额与操纵股价行为之间,仍必须证明具有因果关系,否则将非可归责于债务人事由之变动状况全数计入亦难谓合理。毕竟损害赔偿之目的在于填补债权人所生之损害,其应回复者,并非原来状态,而系应有状态。本文爰此引介台湾地区方面对于裁判证券损害赔偿的计算方式,冀供参考。
证券交易 公开募集 证券交易 交易价格 散布不实信息
一、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
为因应社会快速发展可能衍生的各类金融犯罪,其中藉由操纵证券市场获取暴利的行为,不惜造成股票价格剧烈波动、偏离其原始真实价格,严重者还可能引发非理性的市场崩盘。而两岸在维护证券市场公平机制的目标大体上一致,除禁止各种不法“操纵股价”的手段行为外,并明定有民事损害赔偿责任、以及提高刑事责任的处罚。惟因行为人的操纵手段变化多端,证监会多数时候不易掌握查办,加上股票的不法利得相当诱人,至今证券市场仍无法杜绝此类型的投机行为。此所指操纵证券市场、企图影响股票价格的方法,包括:故意违约不交割股票、拉抬某特定股票价格(拉尾盘)、恶意散布不实流言等。尤其《证券法》第77条和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5条所列之操纵证券市场行为,渠等行为的构成要件,并不以“获利”为前提,纵使行为人未获得预期的利益、或甚至赔本之情形,只要明确意图符合各款要件,即属违反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规定,应负刑事及民事责任。
揆诸两岸相关法规,《证券法》第77条明文禁止任何人以下列手段操纵证券市场:(一)单独或者通过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二)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三)在自己实际控制的账户之间进行证券交易,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者证券交易量;(四)以其他手段操纵证券市场。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行为人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上述的禁止规定则详列于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5条第1项,对于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有价证券,不得有下列各款之行为:(一)在集中交易市场委托买卖或申报买卖,业经成交而不履行交割,足以影响市场秩序;(二)(删除);(三)意图抬高或压低集中交易市场某种有价证券之交易价格,与他人通谋,以约定价格于自己出售,或购买有价证券时,使约定人同时为购买或出售之相对行为。(四)意图抬高或压低集中交易市场某种有价证券之交易价格,自行或以他人名义,对该有价证券,连续以高价买入或以低价卖出,而有影响市场价格或市场秩序之虞。(五)意图造成集中交易市场某种有价证券交易活络之表象,自行或以他人名义,连续委托买卖或申报买卖而相对成交。(六)意图影响集中交易市场有价证券交易价格,而散布流言或不实资料。(七)直接或间接从事其他影响集中交易市场有价证券交易价格之操纵行为。前项规定,于证券商营业处所买卖有价证券准用之。违反前二项规定者,对于善意买入或卖出有价证券之人所受之损害,应负赔偿责任。
尽管规范明确,两岸的证券法均未就操纵股价行为之“不法所得”定义,导致犯罪所得之范围、损害赔偿数额之多寡,究要如何计算,成了当今司法实务不容忽视的问题。换言之,由于相关法律条文及立法理由均未明文,导致法院在裁判案件时所采标准不一,且案件再经上诉、发回等程序,耗费不少诉讼资源。果尔,对于操纵股价行为暨其不法所得的认定,未来应有建立一个类型化、明确化制度的必要性,以确保证券市场的自由价格与合法投资人的权益。
查台湾地区各审级法院计算违反证券交易法的犯罪所得方法,可以发现主要三种计算方法:关联所得法、实际所得法、拟制所得法。采关联所得法的判决,如台开案〔1〕“台湾最高法院2007年台上字第7644号判决书”。、千兴案〔2〕“台湾高等法院2010年金上诉字第56号判决书”。;采实际所得法,如明基公司案〔3〕“台湾最高法院2012年台上字第3534号判决书”。、日月光公开收购环隆电器案〔4〕“台湾台北地方法院2012年金诉字第59号判决书”。、劲永公司案〔5〕“台湾高等法院2010年重金上更一字第2号判决书”。、复盛公司案〔6〕“台湾台北地方法院2011年金诉字第7号判决书”。、绿点公司案〔7〕“台湾最高法院2013年台上字第1420号判决书”。;采拟制所得法,如力特光电公司案〔8〕“台湾最高法院2007年台上字第7644号判决书”。、 宏巨公司案〔9〕“台湾高等法院2012年重金上更四字第6号判决书”。、 台湾日光灯案〔10〕“台湾高等法院2011年金上诉字第40号判决书”。。
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71条第2项曾于2004年4月25日修正,关于不法所得计算方式虽仅于立法理由说明列举内线交易、不法炒作两种犯罪类型为计算不法所得之方式,然前揭立法理由说明为文义解释,系为使法院适用时不致产生疑义,而列举其中二种犯罪类型计算方式,并未将其他如非常规交易、特别背信等犯罪类型不法所得之计算方式排除,即并未将“犯罪所得应以差额计算方法之概念”排斥其他如非常规交易、特别背信等犯罪类型不法所得计算之适用。再“损害”与“犯罪所得”为不同之概念,同法第171条第3项规定就特别背信罪以“公司遭受损害达新台币五百万元”为不法构成要件之一,同法条第二项以行为人犯罪所得达新台币一亿元以上金额为刑度加重之要件,一为构成要件之一,另一为刑度加重要件。举例,在元大投信公司案中,检察总长提起非常上诉,质疑法院如何计算出被告杜丽庄、马志玲等使元大投信公司遭受共新台币四亿四千四百八十万三千二百五十二元的损害?亦即,法院如何得出被告受有等额之款项及利益部分,并认定被告对该公司造成之“损害”同等其“犯罪所得”。
最高法院审理后说明,上开案件中被告二人乃发行有价证券公司之董事,因意图为自己之利益,而为违背其职务之行为,致公司遭受损害达五百万元,又其犯罪所得达一亿元以上罪刑,均系共同违犯证券交易法之背信罪;此与被告另违反证券交易法第155条第1项第5款规定(意图造成集中交易市场某种有价证券交易活络之表象,自行或以他人名义,连续委托买卖或申报买卖而相对成交),个案事实并非相同〔11〕“台湾最高法院2011年台上字第562号判决书”。。是前揭实务见解有关计算犯罪所得的方式,虽未全然一致,仍未违2004年修正“证券交易法”第171条第2项规定立法理由之原则。
具体而言,判断行为人是否有影响或操纵市场以抬高或压低某种有价证券价格之主观意图,除考虑行为人之属性、交易动机、交易前后之状况、交易型态、交易占有率以及是否违反投资效率等客观情形因素外,行为人之高买、低卖行为,是否意在创造错误或使人误信之交易热络表象、诱使投资大众跟进买卖或图谋不法利益,固亦为重要之判断因素,但究非本条成罪与否之主观构成要件要素。盖行为人高买、低卖行为之目的不一,诱使投资大众跟进买卖以图谋不法利益固为多数炒作者之主要动机;然基于其他各种特定目的,例如为避免供担保之有价证券价格滑落致遭断头,或为缔造公司经营荣景以招徕投资,或为顺利取得银行资金奥援,而维持特定有价证券于一定价格之护盘行为,同系以人为操纵方式维持价格于不坠,具有抬高价格之实质效果,致集中交易市场行情有发生异常变动而影响市场秩序之危险。此虽与“拉高倒货”“杀低进货”之炒作目的有异,行为人在主观上不一定有“坑杀”(指损害利益而言)其他投资人之意图,但破坏决定价格之市场自由机制,则无二致,亦属前述规定所禁止之高买证券违法炒作行为〔1〕“台湾最高法院2016年台上字第2173号判决书”。。
职是之故,证券流通的价格,系由利伯维尔场内的供给与需求而决定,任何人皆不得以不法手段去操纵供给与需求之假象,进而影响供需法则下证券的自然交易价格。否则,明定证券信息的公开揭露便失其意义,同时也会使投资人陷于错误判断。再者,放任操纵市场的行为,无疑让证券投机份子以为可以掌控证券价格,从而破坏了证券市场的公平交易秩序。又证券法的立法目的,在于确保证券市场之公平、公正,且能设法为投资人提供一个足以信赖且健全的投资环境。于兹,以下就证券市场内的操纵行为,从实务应用面兼学理的观点深入探究。
二、各类操纵手段的分析
归纳两岸证券市场常见的不法操纵行为有:违约不交割、相对委托、连续买卖、冲洗买卖、散布流言与不实数据、其他概括条款手段。以下援引违反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禁止操纵行为的实务案例,并解析其构成要件:
(一)违约不交割
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5条第1项第1款规定:不得在集中交易市场委托买卖或申报买卖,业经成交而不履行交割,足以影响市场秩序。学理与实务主流看法认为,违约不交割的构成要件包括〔2〕赖英照:《证券交易法解析》简明版,2013年,第273页。:投资人委托证券商买卖证券,但明知自己资力不足,却仍故意下单买进;投资人明知持有之证券数量不足,却仍故意下单卖出。由于本款条文的立法目的在以防止恶意投资人不履行交割义务,故构成本罪必须投资人主观上具备了违约不交割之故意。反之,若行为人因突发事件或其他非出于主观上恶意的原因者,则不构成此罪〔1〕赖英照:《证券交易法解析》简明版,2013年,第274页。。
不过,也有少数说者主张除上开构成要件外,应据以考虑投资人违约不交割之数额是否已达“足以影响市场秩序”的情形,才能以刑法相绳;倘若投资人仅有少量交易,纵使故意不履行买卖义务,而未影响市场交易秩序者,仅须就民事处理即可。其理由认为违约不交割本质上就是“债务不履行”,故应择先以民事解决〔2〕林小刊:“论操纵股价犯罪所得之计算”,载“司法新声”第120期,2016年,第71页。。惟多数意见说者普遍不表赞同,其理由指出故意违约不交割的本质已具备“扭曲证券市场”的能力,盖因每一个个人的少量交易在多数人的情形下就会形成大量,因此支持即便单纯的不交割都应负刑事责任〔3〕赖英照:《证券交易法解析》简明版,2013年,第276页。,方能收吓阻之成效。
(二)相对委托
次论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5条第1项第3款规定(同法同条第2款已删除):禁止意图抬高或压低集中交易市场某种有价证券之交易价格,与他人通谋,以约定价格于自己出售,或购买有价证券时,使约定人同时为购买或出售之相对行为。此种行为,又谓“相对委托”,系指行为人必有二人,才有交易价格“通谋”的可能。至于,上开条文中所指“约定价格”或“同时”,并不以完全相同为必要,亦无庸先具备“买卖成立”为前提要件,只要行为人在可能成交之时间或价格区间内下单,即满足“相对行为”。
简言之,“相对委托”的构成要件中是否应包含“锁定价格”之条件,学理上与实务界见解不同。多数学者认为只要行为人具备操控证券价格之意图已足;实务论者则认为,既然法条已明定“意图‘抬高’或‘压低’有价证券之交易价格”,则必有促成价格变动之意图,而非包含“锁定价格”之意图〔4〕林小刊:“论操纵股价犯罪所得之计算”,载“司法新声”第120期,2016年,第72页。,至于买卖有否成立也非前提要件。
(三)连续买卖
“连续买卖”的禁止,参照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5条第1项第4款,“意图抬高或压低集中交易市场某种有价证券之交易价格,自行或以他人名义,对该有价证券,连续以高价买入或以低价卖出,而有影响市场价格或市场秩序之虞”。指投资人以自己或他人之名义,对特定的股票,有“两次以上”高价买入或低价卖出之连续行为。此行为的认定不易,毕竟证券市场本得自由买卖,究竟投资还是故意炒作,实务上的判断标准严格,认为必须满足“在一段期间内,逐日以高于委托当时之揭示价、接近当日涨停参考价格或以当日涨停参考价之价格委托买进(低价则相反)”才能构成连续以“高价买入”或“低价卖出”的要件〔1〕“台湾最高法院2005年台上字第2171号判决书”。。倘若投资人多次的买入行为,未超过成交日当天得市场行情,又没“逐日增加”价格买入者,或投资人几次当中有一次低于或等于委托当时之揭示价,便不符合。
学理上则持不同意见认为,所谓“高价买入”或“低价卖出”要求的仅在于行为人主观上“不惜以高价买入或低价卖出”之买卖行为,而非对于买卖之价格有任何限制,盖因连续买卖行为,很可能牵动股价之涨幅剧烈,从而,行为人仍须具备“引诱或误导他人买卖股票之意图”,方能论以刑事责任〔2〕王志诚:“连续交易之认定基准及实务争议”,载《月旦民商法杂志》2005年第19期。。
(四)冲洗买卖
“冲洗买卖”乃学说上用语,参见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5条第1项第5款规定:不得“意图造成集中交易市场某种有价证券交易活络之表象,自行或以他人名义,连续委托买卖或申报买卖而相对成交。”指行为人在不同证券商开立账户,就同一证券、以相同价格,在同日时段内委托证券商卖出,并由另一家证券商买入,造成特定股票交易的活络假象,而该股票之所有人为同一人。检视本款禁止行为的构成要件,行为人必须有:1.至少“两次”以上连续买卖行为;2.行为人主观上具备“故意造成市场交易热络”之不法意图。
有学者长期观察指出,其实各种操纵证券市场的行为,基本上都会产生“交易市场某种有价证券交易活络之表象”,于是建议此项要件应适用所有禁止的操纵行为〔3〕陈俊仁:“论证券交易法操纵行为禁止之理论基础与规范缺失—以冲洗买卖观察”,载《月旦民商法杂志》2005年第19期。。
(五)散布不实讯息
散布不实讯息,明定于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依本法第155条第1项第6款:行为人如有“意图影响集中交易市场有价证券交易价格,而散布流言或不实资料”者,指任何人公然散布不正确或未经查证、且具有重要性而足以影响一般投资大众判断之错误讯息,俗称散布假消息〔1〕参见台湾大法官释字第145号、第617号解释。,去对市场进行操纵影响的行为。本条款的构成要件,必须行为人主观上具有“影响集中交易市场有价证券交易价格”之意图,反之,若行为人仅仅是因道听途说、或来自个人的猜测意见、或为其他目的而散布者,均不成立本罪。
比较美国证券交易法之操纵行为实质上乃证券诈欺之一种,故针对“散布不实消息”之操纵行为来说,其构成要件必须:1.行为人主观上具备“有引诱他人买卖有价证券”之意图,以及2.客观上确实实现了“散布重大不实或误导之信息”〔2〕SeeU.S.Securities Act,§ 9(a)(4).。而大陆方面亦将此类行为列入诈欺的范畴,另外规定于大陆《证券法》第79条第1项第6款:利用传播媒介或者通过其他方式提供、传播虚假或者误导投资者的信息。其限缩了行为人的身份,即在禁止证券公司及其从业人员从事下列损害客户利益的欺诈行为。反观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在本条款上却是少了引诱买卖的意图要件,可谓立法上的缺失。
(六)概括条款
又唯恐操纵行为的列举规定不足,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5条第1项特别增订了第7款的概括条款:“直接或间接从事其他影响集中交易市场有价证券交易价格之操纵行为”者。值得注意的是,概括条款与其它各款规定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辅相成之作用〔3〕庄永丞:“论证券价格操纵行为之规范理论基础——从行为人散布流言或不实数据之操纵行为开展”,载《东吴法律学报》2005年第20卷第1期。。惟“直接或间接影响”有价证券交易价格之操纵行为,究指何义?加上欠缺行为人的主观要件,似有条文定义不明确之虞。因此,有学者主张本款规定违反了刑法条文的明确性原则,建议宜应删除〔4〕刘连煜:“冲洗买卖行为之合法性”,载《月旦法学教室》2002年试刊号。。实务上意见则认为,上开五款之操纵行为纵能对号满足,仍应考虑有否“概括条款”之其他行为,而得再论“概括条款”之罪;反之,若行为人基于概括之犯意,行为单一,则仅成立一罪而从重处罚。至于行为人只存在上开五款任一列举之操纵行为,自当无庸再考虑“概括条款”〔5〕赖英照:《证券交易法解析》简明版,2013年,第259页。。
三、民事损害赔偿金额之计算
关于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5条第3项损害金额之计算,系以赔偿权利人的损害为计算基础;至于其计算方式,虽法无明文,但国内实务对于证券市场操纵行为之损害赔偿案例,多采取“净损差额法〔1〕“台湾最高法院2016年台上字第1336号判决书”。”或“毛损差额法”两种。
(一)净损差额法
“净损差额法”原则上与美国实务上针对证券诈欺、信息不实等行为,所采取损害赔偿的计算方法雷同,均认为行为人仅需赔偿因证券诈欺因素所造成之损失,即证券之真实价值与“买价或卖价”之间的差额,至于其余部分系因诈欺以外的因素所造成,行为人不负赔偿责任。参照升贸公司案,该公司股价因上诉人不法操纵行为,致于2009年7月6日至同年5月24日之操纵期间内,由每股55.5元上涨至73.5元。台湾地区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中心主张:授权人(多名投资人)本得以较低之真实价格买入升贸公司股票,却因上诉人不法操纵股价,致需支出经不法操纵后上涨之较高价格始得购入股票时,授权人之损害即已发生;且其所受损害,即为授权人以升贸公司股票非真实即经操纵上涨之股价,与渠等本得以真实股价购入股票间之价差,此即因买进成本被垫高所造成之损失。
简言之,采取“净损差额法”计算投资人所受损害,不法行为人所需赔偿者,乃证券之“真实价值”与“买价或卖价”之间的差额,业如前述。而所谓真实价格,系指若无诈欺因素的影响,股票所应有的价值;也就是把诈欺因素的影响响,从股价抽离,还原它本来的价值。惟投资人依证券交易法第155条第3项规定求偿,关于股票之真实价格应如何认定,法亦无明文。对真实价格究应如何认定,两造常各执一词。而法院的论理大致:
1.关于内线交易侵权行为损害计算方法,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57-1条第1项明定:该公司之董事、监察人、经理人及依公司法规定受指定代表行使职务之自然人、或持有该公司之股份超过百分之十之股东、或基于职业或控制关系获悉消息之人,于实际知悉发行股票公司有重大影响其股票价格之消息时,在该消息明确后,未公开前或公开后十八小时内,不得对该公司之上市或在证券商营业处所买卖之股票或其他具有股权性质之有价证券,自行或以他人名义买入或卖出。又对于当日善意从事相反买卖之人买入或卖出该证券之价格,与消息公开后10个营业日收盘平均价格之差额,负损害赔偿责任;然审酌于操纵股价之案例,多数于操纵期间并不会因检调机关侦查而经媒体揭露,被操纵公司更不可能主动揭露此不法情事;是于不法操纵行为结束后,先前操纵行为对于股价所生影响如未经实时揭露,将持续一段期间;此与内线交易重大消息公开后,于短期即约揭露后10个营业日期间,股价即会于交易市场反映之特性显然不同,且无“更正不实消息”之问题。从而,考虑于操纵市场类型之合理股价于操纵行为结束后未能及实时回复之特性,而操纵行为开始前之股价,则全未受到操纵行为影响之情为可采取。
2.按股票投资人通常以发行公司经营绩效、公司资产负债、财务业务状况、行业景气及其他相关因素作为投资股票之依归,人为操纵股价行为乃股票利伯维尔场所不许,股票投资人推定信赖利伯维尔场之机制而有交易因果关系,但投资人仍须证明其损害及金额与上揭人为操纵股价行为间,具有损害因果关系,否则,不啻将此项债务人赔偿责任,转化为填补债权人交易损失之投资保险,尚非事理之平。毕竟,损害赔偿之目的在于填补债权人所生之损害,其应回复者,并非原来状态,而系应有状态,自应将非可归责于债务人事由之变动状况考虑在内〔1〕“台湾最高法院2016年台上字第2215号判决书”。。如以本件授权人于操纵期间买入升贸公司股票之价格,除包括因上诉人不法操作行为所垫高之金额外,实未能排除于操纵行为期间,升贸公司股票因其他市场、政治或社会等因素所造成之涨跌结果;此等非因上诉人操纵行为所造成之股票涨跌之损益,与上诉人既无关联,自不应责由上诉人负担。又影响股价涨跌之各项因素甚多,固难以一一区辨。惟审酌升贸公司股票于操纵行为发生前及操纵行为期间,其公司基本面、资金面及政经走势并无大幅变动,亦无因突发之金融、社会或政治事件致股市剧烈波动之情形。则关于升贸公司就非因上诉人不法操纵行为、而系本于其他基本面、资金面及政经、社会面所造成股价涨跌走势之影响,应可以操纵期间内与升贸公司同类股平均涨跌幅据以认定,并作为前揭单纯以操纵行为开始前10个交易日平均收盘价计算所得金额调整之依据,俾将非因上诉人操纵行为所造成之涨跌损益予以排除,以求取投资人于操纵行为期间购买升贸公司股票之真实价格。
所以,本件授权人于操纵期间购入升贸公司股票之拟制真实价格,应以上诉人不法操纵行为开始前10个交易日之平均收盘价格即每股46.2元,加计操纵期间升贸公司同类股于操纵期间之平均涨幅7.09%后之每股49.45元,即46.2元×7.09%+46.2元=49.45元,以为认定。各授权人因上诉人不法操纵行为所受损害,即应为授权人于操纵期间购买升贸公司股票之实际买入价格与该拟制真实价格之差额据以计算。
次按基于同一原因事实受有损害并受有利益者,其请求之赔偿金额,应扣除所受之利益,台湾地区“民法”第216条之1定有明文。投资人于操纵股价期间内如买入后复卖出股票而获得利益,所获利益与其先前因支出较高股价购入股票所受损害,显然均系基于上诉人不法操纵行为诱使投资人购买股票之同一原因事实;自应将渠等于操纵期间内卖出股票之获利(即实际卖出价格与拟制真实价格间之差额)予以扣除。至于投资人于操纵股价期间后始将股票出售,无论渠等卖出股票价格如何,是否高于购入价格,甚或有迄尚未出售者,因操纵行为既已结束,其股票市值乃由非诈欺原因事实之正常市场因素决定,与上诉人操纵行为无关,则投资人于形式上纵有获利,所获利益与所受损害即非基于同一原因事实,即无损益相抵原则适用。
(二)毛损差额法
毛损益法系将操纵行为结束后因其他市场因素造成之涨跌,均列入损害金额之计算,对于投资人与不法操纵行为人均属不公:亦即于操纵行为结束后,如有金融风暴致股价下跌,则计算损害之结果将对不法行为人不利;反之,如有政经市场有利因素介入致股价上扬,则计算损害之结果将对投资人不利。然损益结果既均因操纵行为以外之因素所造成,自不宜于本件损害赔偿计算时予以采用。况结算授权人于操纵行为结束后实际出售升贸公司股票之价格,形式上虽有获利者,然采取净损差额法计算损害,既着眼于授权人于操纵期间本得以较低之真实价格购入股票,却因上诉人不法操纵行为致需以较高买价购得之情,则授权人此项垫高成本支出之损害,实不因授权人日后结算股票买卖盈亏之结果而不存在。
有论者建议无论系采“毛损益法”或“净损差额法”,对于投资人于操纵期间内买入复行卖出股票者,因其买入或卖出之价格均系受操纵行为垫高,故所生涨跌差额均系操纵行为以外之市场因素造成,不能认为受有损害,而应予剔除。然审酌行为人于操纵期间,该公司之股价既因行为人操纵行为而涨跌互见;则行为人以投资人于操纵期间买入及卖出之股价均因操纵行为而垫高,故应互为抵销之前提,已非的论。况且最高法院所以认为以被上诉人主张之净损差额法为可采取,乃在限制投资人所得求偿者,仅以因诈欺原因事实所发生之损害为范围,故将损害计算限制于投资人实际买入股票价格与真实价格间之差额;至于投资人于操纵期间购入股票后,无论系于操纵行为期间内或期间外,其出售结果是否另有损益,因其股价均无法排除非诈欺原因事实之影响(即使于操纵行为期间内,除操纵行为外,亦尚有其他市场因素影响股价之涨跌);故无论投资人出售股票另有损害或获益之结果,均不在本件损害赔偿计算予以考虑,俾将与操纵行为无因果关系之损益,排除在投资人可求偿之范围之外。准此,授权人之损害既在其于操纵期间以较高价格购入升贸公司股票时即已发生,自不因其于操纵期间内再予卖出而异其认定。至于授权人于操纵行为期间内买入又卖出股票因而获益之情形,既得以前揭损益相抵之方式予以调整。
综上,以升贸公司案来说,众多投资人所受损害,宜采“净损差额法”,即以投资人购买升贸公司股票之实际买价,与该股票真实价格间之差额据以计算;至于升贸公司股票于操纵期间之拟制真实价格,则应以被告不法操纵行为开始前10个营业日之平均价格即每股46.2元,加计操纵期间与升贸公司同类股之平均涨幅7.09%为每股49.45元,其中投资人于操纵期间买入复卖出升贸公司股票者,并需依民法第216条之1规定为损益相抵。又投资人于操纵期间买入、卖出升贸公司股票之时间、股数及单价,以及依上开计算方式去计算各别投资人因被告不法操纵行为所受损害金额。
四、刑事犯罪所得之计算
由于操纵证券市场行为之犯罪所得多寡攸关刑度的长短,被告更要仔细计算。然两岸证券法针对不法所得的相关规定均无明确定义,造成司法实务上的认定困难。基此,以下援引台湾就该命题的立法理由、学理上探讨、以及实务上判决认定所采用的若干方法,进行比较分析。
(一)立法者示意的计算方式
台湾地区“证券交易法”第171条第2项规定:“已依本法发行有价证券公司之董事、监察人、经理人或受雇人,以直接或间接方式,使公司为不利益之交易,且不合营业常规,致公司遭受重大损害。”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得并科新台币一千万元以上二亿元以下罚金。又其犯罪所得利益超过罚金最高额时,得于所得利益之范围内加重罚金;如损及证券市场稳定者,加重其刑至二分之一。又因犯罪所得财物或财产上利益,除应发还被害人、第三人或应负损害赔偿金额者外,以属于犯人者为限,没收之。如全部或一部不能没收时,追征其价额或以其财产抵偿之。
立法者对于上开第171条第2项行为的犯罪所得说明:“所称犯罪所得,其确定金额之认定,宜有明确之标准,俾法院适用时不致产生疑义,故对其计算犯罪所得时点,依照刑法理论,应以犯罪行为既遂或结果发生时该股票之市场交易价格,或当时该公司资产之市值为准。至于计算方法,可依据相关交易情形或账户资金进出情形或其他证据数据加以计算。例如对于内线交易可以行为人买卖之股数与消息公开后价格涨跌之变化幅度差额计算之,不法炒作亦可以炒作行为期间股价与同性质同类股或大盘涨跌幅度比较乘以操纵股数,计算其差额”。立法者明示计算操纵证券市场行为的不法所得,采用“类股指数比较法”,或称“大盘指数比较法”,〔1〕赖英照:“内线交易的所得计算”,载《中原财经法学》2013年第31期。亦即,以行为人操纵拉抬股价后,比较该股票之价格与其他同性质同类股之价格,再以二者之差距价格作为行为人违法炒作之结果,另乘上操纵的股数,所得结果为不法获利。惟,此种计算方式欠缺一个清晰标准化的公式,导致法院因在裁断时运用不便而于日后拒绝使用〔1〕“台湾最高法院2016年台上字第2215号判决书”。。
(二)学理上建议的计算方式
有学者认为,计算操纵证券市场行为之不法所得,倘若是与同类股或大盘涨跌幅度比较,其计算结果仅属“拟制犯罪所得”而非“实际犯罪所得”〔2〕王志诚:“证券市场操纵行为之规范构造及犯罪所得”,载《台湾法学杂志》2010年第165期。,故不应以操纵期间内所有买卖行为作为不法所得之计算依据,而是应先判断该行为是否不法炒作的一部环节,倘若为真,即操纵行为与股价波动之间具有因果关系,那么方得据以计算不法利得〔3〕“台湾最高法院2014年台上字第2256号判决书”。。所谓“拟制犯罪所得”之计算,本质上应以“收盘价格扣除买进价格”之差价,作为操纵股价之不法所得,然考虑到股价之变动有时并非全面受到操纵行为的影响,尚可能受到同类股或大盘涨跌幅度所影响,果尔,宜应比较该股之涨跌幅与同类股涨跌幅之差距,并以两者之差额比例作为“操纵行为所引致的涨跌幅比例”。
易言之,以上开两者之“差额比例”乘上“收盘价格扣除买进价格”后为拟制所得。最末,再考虑到立法者例示的“差额说”,即扣除行为人支出之交易成本后,以该数值乘上行为人实际买入之股数,即可计算出不法所得〔4〕王志诚:“证券市场操纵行为之规范构造及犯罪所得”,载《台湾法学杂志》第165期,2010年,第50页。:[(收盘价格-买进价格) ×与同类股涨跌幅之差额比例-交易成本]×买入股数=拟制犯罪所得〔5〕王志诚:“证券市场操纵行为之规范构造及犯罪所得”,载《台湾法学杂志》第165期,2010年,第76页。。惟须注意,当收盘价格低于买进价格时,尽管相减后所得为负数,有学者认为仍应将之列为不法所得之利损,而直接将该部分损失一并计入不法所得〔6〕王志诚:“证券市场操纵行为之规范构造及犯罪所得”,载《台湾法学杂志》第165期,2010年,第50页。。
(三)实务上的计算方式
台湾地区各审级的刑事法庭除少数案件采特殊计算方式外,大多数案件采用“实际所得法”或“拟制所得法”计算行为人操纵证券市场的不法所得〔7〕赖英照:“内线交易的所得计算”,载《司法新声》第120期,2016年。。此所指“实际所得法”,是曰行为人实际买卖股票再扣除相关成本,如手续费、证交税等后所得之价差,以该金额计算不法所得;至所谓“拟制所得法”,系指行为人仅有买入而尚未有卖出之行为时,便以“操纵市场期间”之尾日收盘价作为卖出价格,然后计算价差后为不法所得〔1〕赖英照:“内线交易的所得计算”,载《中原财经法学》第31期,2013年,第49页。。以下兹就台湾法院计算不法所得所采用之计算公式:
1.违约不交割
查广三集团案中,多名被告因违约不交割的金额高达新台币54亿2933万5300元,而导致受委托买卖之证券商蒙受损害,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审理后,重新计算被告等人共同犯罪所得,应以违约不交割的总金额再扣除:(1)各证券商再次处分股票之金额(即证券商代垫买入股票后,再行卖出之款项)。(2)冲抵股款之金额(即证券商以应支付广三集团之交割款,冲抵广三集团应支付之交割款)。故扣除上开金额后,被告等人因违约不交割之不法犯罪所得修正为60亿5655万497元〔2〕“台湾最高法院2004年台上字第2555号判决书”。。此部分与台中地方法院所持“无需扣除上开款项,径以违约不交割之金额”作为犯罪所得之见解不同。惟从本案历审判决以观,违约不交割的犯罪所得不得径以被告违约不交割之总金额直接计算其犯罪所得。
2.相对委托
在全汉公司案中,一审法院采取计算不法所得的方法,分别有“实际所得法”及“拟制所得法”两种计算方式去得出“已实现之获利”即实际获利金额,及“未实现之获利”即拟制获利金额,惟未实现之获利计算方式遭到二审法院推翻,故目前只有已实现获利的计算方式,一、二审级法院所采公式一致:
(1)已实现之获利=[(卖出总金额-卖出总手续费-卖出总证券交易税) ÷卖出总股数-(买入总金额-买入总手续费) ÷买入总股数]×买入或卖出股数。
二审法院在计算“未实现之获利”部分表示,被告既无卖出,则无从认定卖出金额,故不应将期末收盘价拟制为卖出金额,而应直接以“未卖出之股票”本身,加上配发之股利、股息,再扣除平均买入成本(包含买入金额、手续费),作为被告之买超部分之犯罪所得。其理由指出,被告之不法所得固然是“已实现之获利”加上“未实现之获利”,就未实现之获利应以“股票本身”为主,而非以期末收盘价拟制为卖出金额,倘欲没收行为人之犯罪所得,应没收“股票”以及股利、股息、相关交易成本〔3〕“台湾台中高分院2013年重金上更(一)字第23号判决书”。。从而,建议公式如下:
(2)未实现之获利=买超股票张数+该买超股数所配发之股利+该买超股数所配发之股息-{[(买超总金额+买超总手续费) ÷买超股数]×买超股数}。
3.连续买卖
参照天刚公司案,一审法院认为计算连续买卖之不法所得时,无庸扣除证券交易税、手续费,盖因行为人操纵股价之目的在“为自己创造不受允许的获利或避损机会”,而非“所取得的股票或价金”。因此,不法所得之认定应详细区分行为人每次买卖之金额、股数等,并以会计学上之“加权平均法”计算买卖之价差;至行为人如有买超或卖超之情形,则另采拟制的计算公式。其试算公式为〔1〕“台湾台北地方法院2011年金诉字第31号判决书”。:(1)如无买超或卖超之情形:将行为人所有之“买入股数*买入价格”相加后,再除以全部之买入股数,即得出平均买价。次以平均卖价与平均买价之差额乘上买入或卖出股数,得出不法所得。(2)如有买超或卖超之情形:买超部分,以分析期间最末日之收盘价与每股平均买价之差额,乘以买超股数计算之,此部分系以期末收盘价拟制为行为人卖出之金额;卖超部分,以每股平均卖价与分析期间第一日收盘价差额,乘以卖超股数。(3)嗣将前开“实际获利金额”加上“拟制性获利金额”后,以该加总结果再乘上“该股票涨幅较同类股指数超涨之比例”。然本案上诉二审法院后,法官却认为应再扣除行为人买卖股票时所支出之手续费及证券交易税,始符合立法者所采“差额说”之本旨〔2〕“台湾高等法院2013年金上诉字第13号判决书”。。嗣后,最高法院肯认二审之计算方式〔3〕“台湾最高法院2016年台上字第1255号判决书”。。
4.冲洗买卖
又在宝岛极光案中,法院并未采以往的“实际所得法”或“拟制所得法”计算方式,而系完全以“实际所得法”去计算不法所得。法院认为被告在第一次操纵期间,总共买进15721.7张股票、合计买进金额为361,031,459.45元,平均每股买进价格为22.96元;又卖出总数量为16640.545张、合计卖出总金额为422,322,642.5元;平均每股卖出价格为25.35元。所以总计不法所得为(25.35-22.96) ×16640.545×1000=40,270,544.9元。被告不服上诉,最高法院认为应得再扣除所支出之手续费及证券交易税等才是不法所得,故重新发回更审〔4〕“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2011年金上更(一)字第46号判决书”。。
5.散布不实信息
针对故意散布不实信息的操纵市场行为,参见庆丰富案,法院主要以“实际所得法”及“拟制所得法”去计算行为人之不法所得。其计算公式〔5〕“台湾高等法院台中分院2015年金上更(一)字第14号判决书”。:
(1)买卖股数相等时,采“实际所得法”:(平均卖价-平均买价)×买入或卖出股数=[(卖出总金额-卖出手续费-卖出证券交易税) ÷卖出总股数-(买进总金额-可分配现金股息+买进手续费) ÷(买进总股数+配发股票股利股数)]×买入或卖出股数。
(2)买超时并采“实际所得法”和“拟制所得法”:(平均卖价-平均买价)×卖出股数+(分析期间之期末收盘价-平均买价) ×买超股数-拟制性卖出手续费-拟制性卖出证券交易税=[(卖出总金额-卖出手续费-卖出证券交易税)÷卖出股数-(买进总金额-可分配现金股息+买进手续费后) ÷(买进总股数+配发股票股利股数)]×卖出股数+[分析期间之期末收盘价-(买进总金额-可分配现金股息+买进手续费后) ÷(买进总股数+配发股票股利股数)]×买超股数-拟制性卖出手续费-拟制性卖出证券交易税。
(3)卖超时并采“实际所得法”和“拟制所得法”:(平均卖价-平均买价)×买入股数+(平均卖价-分析期间之期初收盘价) ×卖超股数-拟制性买入手续费=[(卖出总金额-卖出手续费-卖出证券交易税) ÷卖出股数-(买进总金额-可分配现金股息+买进手续费后) ÷(买进总股数+配发股票股利股数)]×买入股数+[(卖出总金额-卖出手续费-卖出证券交易税) ÷卖出股数-分析期间之期初收盘价]×卖超股数-拟制性买入手续费。
6.概括条款
除上揭所列行为外的其他操纵证券手段,在兆丰金控案中,法院计算出被告犯罪所得共达新台币一亿元以上,系被告等人以分工方式,共同达成操纵兆丰金控股票之目的,造成兆丰金控股票价格上涨,经扣除应支付予中信银行香港分行之款项后,于账面上获得美金3047万4717.12元获利(折合新台币约10亿1450万5050元)。同时,被告间接操纵兆丰金控股票之交易价格之行为,因控制取得兆丰金控股票之成本,而获得减轻购入成本达2亿6169万5500元之利益,换言之,被告客观上行为虽仅有一种操纵股价之行为,却同时造成“哄抬”以及“压低”股价之情形,是被告以拉抬股价之手法赚取利润,又一面压低股价,始其保持在一定之区间,以节省购入成本。最后,法院认定被告等人应共同对前开结果负责,并裁断每一被告之不法所得均达新台币一亿元以上〔1〕“台湾高等法院2010年金上重诉字第75号判决书”。。
五、刑事责任之认定
(一)南港公司案——违约不交割
本案中法院认定被告林学圃、林维雄、林胜正三人共同违反对于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有价证券,不得有在集中交易市场报价,业经有人承诺接受而不履行交割,足以影响市场秩序之行为之规定,判处林学圃有期徒刑二年;林维雄处有期徒刑十个月,减为有期徒刑五个月;林胜正处有期徒刑八个月,减为有期徒刑四个月确定〔1〕“台湾高等法院2009年上重更(二)字第30号判决书”。。林学圃不服向最高法院提起上诉,上诉意旨称:“他既未于证券商开立账户,个人无法买卖股票,自非违约不交割罪之犯罪主体,本件向七家证券商买进股票,乃林维雄个人及借用林胜正名义下单所为,与他无涉,他既无犯意,又无行为,自非共同正犯。”
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并于意见书中说明〔2〕“台湾最高法院2012年台上字第4269号判决书”。:1.上诉人等明知已无支付买进价款之资力,竟为操控南港公司等三家公司之上市股票,以免因股价下跌,致质押于金融机构之南港公司等三家公司股票遭断头卖出,遂基于共同犯意联络,委托不知情之骆雅英于2000年5月29日上午九时起,以电话向世界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世界证券)等七家证券公司下单,利用不知情之该七家证券公司营业员,在证券交易市场报价,大量买进南港公司等三家公司股票,其报价要约业经有人承诺接受而成交,买进价款及手续费合计达新台币三亿七千六百三十九万二千六百九十五元,乃上诉人等竟于办理交割期限,即同年月三十一日前,确有不支付款项以履行交割,嗣由世界证券等七家证券公司代为办理交割手续,致使南港公司等三家公司之上市股票价格自同年九月一日起多日以跌停价格收盘,且成交量明显萎缩,而影响证券交易市场秩序等情。
2.共同正犯,系共同实行犯罪行为之人,在合同意思范围内,各自分担犯罪行为之一部,相互利用他人之行为,以达其犯罪之目的,其成立不以全体均参与实行犯罪构成要件之行为为必要;参与犯罪构成要件之行为者,固为共同正犯;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参与犯罪构成要件以外之行为,或以自己共同犯罪之意思,事前同谋,而由其中一部分人实行犯罪之行为者,亦均应认为共同正犯。分析本案事实可以发现,林学圃为南港公司等三家公司之负责人;而与南港公司有交叉持股关系之国翔国际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以其所持有之南港公司、杨铁公司股票向泛亚银行质押借款,嗣经泛亚银行通知还款或补足担保品。林维雄、林胜正遂以其所有南港公司等三家公司股票质押借款,其等所贷得款项,供林学圃统筹运用;又林维雄无法说明提供资金之人;林胜正则无资力,其等自无从大量买入巨额股票。且林学圃于八月三十日即与证券公司洽谈善后,并提供国强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所有土地之所有权状为担保,林学圃确为本件股票买卖之主导者。则林学圃虽未参与在集中交易市场报价之犯罪构成要件行为,依上说明,仍为同谋共同正犯。原判决因而认林学圃等就上揭违约不交割犯行,有犯意联络及行为分担,合于共同正犯之要件。
(二)亚化公司案——相对委托
本案中法院依凭被告叶斯应、邱奕志二人坦承谋议抬高亚化公司股价于一定价位之自白,佐以证交所2013年10月5日台证密字第○○○号函所提供相关投资人成交委托买卖明细表、特定时段投资人委托成交对应表等亚化公司股票之交易信息,认定叶斯应自2005年1月5日起至2009年6月19日止,担任亚化公司董事长,为避免其所有经设质或融资买进之亚化公司股票因股价持续下跌而遭“断头”,自行或与邱奕志共同连续以高价买进、相对委托等操纵股价方式,而人为操纵使亚化公司股价维持不坠,自具有抬高价格之意图等情。并说明叶斯应个人自行使用其所控制之账户,于原判决附表四编号1至31所示之交易日,连续以高于前盘成交价或涨停价委买而成交,并因而使股价上涨或维持与前盘成交价同一水平;其中更有于尾盘以高于前盘成交价或涨停价大量委托买进而成交,致使股价因而上扬或维持在前盘成交价之情形;且拉抬股价同时并有相对委托成交情形,其中等十四个交易日,相对成交量均达一百张以上〔1〕“台湾最高法院2016年台上字第2173号判决书”。。
叶斯应共同违反不得有意图抬高集中交易市场某种有价证券之交易价格,自行或以他人名义,对该有价证券,连续以高价买入,而有影响市场价格或市场秩序之虞之规定,处有期徒刑一年六个月。邱奕志共同违反不得有意图抬高集中交易市场某种有价证券之交易价格,自行或以他人名义,对该有价证券,连续以高价买入,而有影响市场价格或市场秩序之虞之规定,处有期徒刑壹年陆月〔2〕“台湾高等法院2014年金上诉字第14号判决书”。。
(三)唐锋公司案——连续买卖
本案中上诉人兼被告周武贤于2010年7月10日同意炒股协议、并依炒股协议出借杨、周、罗等人名下之唐锋公司股票供王宝荭出售、上诉人与张世杰等人对于本件连续买卖、连续冲洗唐锋公司股票等违反证券交易法之行为,具有行为分担与犯意联络。上诉人并付一千万元获利予王宝荭,王宝荭亦自账户付一亿五千万元炒股获利予苏美蓉,张世杰确自苏美蓉处取得公司方因炒股所得获利之部分款。又上诉人与张、苏、伍、王、曾等人共同以散布不实数据之方式意图影响唐锋公司股价、制作“唐锋研究报告”,以应付柜买中心查询等情。上诉人因本案自2010年7月10日至5月30日间之共同犯罪所得为五亿五千九百四十九万六千零三十四元。最高法院维持原审判决周武贤以他人名义,对该有价证券,连续以高价买入之规定,其犯罪所得达新台币壹亿元以上,处有期徒刑柒年确定〔1〕“台湾最高法院2016年台上字第1596号判决书”。。
(四)洪氏英案——冲洗买卖
本案中被告洪登顺、黄俊谚使用人头账户,于2003年12月4日至2004年11月5日期间买进或卖出洪氏英公司股票,其成交量占各该营业日成交量达20%以上。再进一步分析查核期间内各阶段洪氏英公司股价涨跌情形、交易量占总成交量之比例,与同期间电子类股、OTC大盘指数比较情形,依序依附表四至九所示客观事务数据,说明其等如何连续以高价买进、相对成交等操纵股价方式,以维持其股价于一定价格。黄俊谚对于提供部分人头账户以供洪登顺买卖股票使用,并觅得配合券商下单买卖如上开客观交易情形之事实,亦不否认,乃认其客观上除确有于分析期间内连续以高价买入股票外,更以相对成交冲洗买卖之方式,“左手买进、右手卖出”,实际上持有之股票总数并未变动,反而支出手续费及证券交易税等交易成本,以制造交易活络之假象,诱使其他投资人参与买卖,以拉抬股价,认定黄俊谚主观上确有操纵股价之意图。且其为维持洪氏英公司股票于特定价格,持续以人头账户买进洪氏英公司股票,且委买价格高于前盘成交价,以避免股票价格滑落,诱使他人将来参与洪氏英公司新股发行之认购,其藉“护盘”而人为操纵使洪氏英公司股价维持不坠,仍具有抬高价格之实质效果,自属上开规定所指之“以高价买入”之行为。嗣后,上开被告等人上诉最高法院〔2〕“台湾最高法院2014年台上字第3799号判决书”。遭驳回,蔡秋美处有期徒刑贰年;黄俊谚处有期徒刑年陆月确定。
(五)庆丰富公司案——散布不实资料
本案中被告洪谊静于侦查时认罪坦承提供资金供林茂荣拉抬庆丰富公司之股价。洪谊静、许培祥于2007年6月间与林茂荣达成协议,由许培祥、洪谊静承诺提供六千张庆丰富公司股票计算之差价,供林茂荣等人炒作庆丰富公司股票所需交割款,嗣又陆续提供四千二百万元、八千万元、四千五百万元予林茂荣炒作庆丰富公司股票。而庆丰富公司于2005年3月25日始经董事会决议成立庆丰富生质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许培祥、洪谊静既知悉林茂荣操纵“庆丰富公司”股票股价,会配合锁码,提供庆丰富公司将朝生化及生质能源产业转型之重大不实利多信息、支应短缺之交割资金等条件,以拉抬庆丰富公司股票之交易价格,并制造该只股票交易活络之假象,诱使投资人购买投资庆丰富公司等情,纵“生质替代能源棒”投资评估报告及营运企划书非许培祥、洪谊静所亲自制作,惟此等数据嗣由林茂荣提供予王继贤,经王继贤主动联系媒体记者,由林茂荣以庆丰富公司越南厂董事长名义,于各大报章及网络媒体,刊登庆丰富公司将转型为生质能源产业之不实利多消息,自为许培祥、洪谊静之授权范围,且与林茂荣间有犯意联络及行为分担甚明。被告洪谊静遭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许培祥判处有期徒刑二年四个月确定〔1〕“台湾最高法院2016年台上字第2063号判决书”。。
(六)京城公司案——概括条款
基于“证券交易法”第157条之1的授权,台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于2006年5月30日订定发布“证券交易法”第157条之1第4项重大消息范围及其公开方式管理办法,嗣于2010年12月22日修正并改名为现行《证券交易法》第157条之1第5项及第6项“重大消息范围及公开方式管理办法”。又为因应特殊具体个案情况,增订概括条款涵盖了“其他涉及公司之财务、业务,对公司股票价格有重大影响,或对正当投资人之投资决定有重要影响者”,其目的系在使有价证券之价格能在利伯维尔场正常供需竞价下产生,避免遭受特定人操控,以维持证券价格之自由化,而维护投资大众之利益。举例,2004年9月间,台湾营建业正值复苏期,被告三人为拉抬京城公司之股价,制造该股票交易活络之假象,诱使投资人购买投资京城公司股票,基于意图抬高上市之京城公司股票股价之犯意联络,利用多名人头证券账户,委托不知情之证券公司营业员等人,连续以高价委托买入京城公司股票,用以制造该股成交量而图逐步抬高京城公司股票之价格,其中连续以高于委托当时成交揭示价23文件之价格或以当日收盘涨停参考价之价格,于盘尾大量委托买进京城公司股票,致使京城公司股票各该次成交之档次上涨3至14档不等、股价相应上涨0.2元至1元不等,确已影响该股之开盘价、盘中成交价及收盘价,被告三人即藉由上开高价委托买进京城公司股票且顺利大量成交之手段,达其逐步抬高京城公司股票于集中交易市场之价格之目的,且成功致使京城公司股价由2004年9月1日收盘价11.50元上涨至2004年11月5日收盘价23.9元,涨幅高达107.53%。被告等人均遭法院宣告缓刑二年〔2〕“台湾高等法院高雄分院2005年上诉字第936号判决书”。。
六、结论
我国台湾“证券交易法”第171条第2项、第4项至第7项,列有犯罪所得之规定,并以犯罪所得之金额为刑度加重之要件,亦即以发生一定结果(犯罪所得达一亿元以上)为加重条件。其立法理由指出:“各种金融犯罪之危害程度有所不同,对于严重危害企业经营及金融秩序者,以犯罪所得金额逾一亿元为标准,因其侵害之法益及对社会经济影响较严重,应有提高刑法之必要。”从而,立法者推定行为人犯罪所得越高,对影响整体经济秩序越大,故应加重刑罚。然“证券交易法”或该法条并无如洗钱防制法第4条明文就“犯罪所得财物及利益”之界定为解释,因而自文义解释,容有复数解释之可能,司法实务乃有参酌该条第2项规定之立法理由说明“第2项所称犯罪所得,其确定金额之认定,宜有明确之标准,俾法院适用时不致产生疑义,故对其‘计算犯罪所得时点’,依照刑法理论,应以犯罪行为既遂或结果发生时该股票之市场交易价格,或当时该公司资产之市值为准。”
至于“计算方法”,可依据相关交易情形或账户资金进出情形或其他证据数据加以计算。例如对于内线交易可以行为人买卖之股数与消息公开后价格涨跌之变化幅度差额计算之,不法炒作亦可以炒作行情期间股价与同性质同类股或大盘涨跌幅度比较乘以操纵股数,计算其差额,而认计算犯罪所得应采取差额说,即应扣除犯罪行为人之成本后,再扣除应发还被害人、第三人或应负损害赔偿之金额,而有正数之差额者,始属犯罪所得之金额,即应以犯罪行为人之财产有因而积极增加者,该增加部分始足认属犯罪所得,若行为人仅消极减少财产之支出,并未有何积极财产之增加者,则应认非属犯罪行为人之“犯罪所得”〔1〕“台湾最高法院2016年台非字第135号判决书”。。
基于公平意旨,行为人拉抬、操纵股价、违法信贷与违约交割,倘若前后时间密接及前后行为具有关连性,已无从将拉抬与操纵股价之行为与嗣后之违约交割分别独立切割时,更无法判定何者方为造成股价损害之唯一原因、以及各个违法行为所造成之损害为何,也不能去否认操纵、拉抬股价与股价下跌二者间之因果关系。又基于证券案件之特殊性及不法行为前后之关连暨被害人就损害之发生难以具体判断系何不法行为所造成,倘若被告无法举证证明投资人所受股价下跌之损害与其操纵拉抬股价之行为间无因果关系存在者,财团法人证券投资人及期货交易人保护中心主张被告拉抬操纵股价系造成其等股价下跌之原因致投资人受有损害,依民法须对投保中心及投资人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亦即以投资人买入股票之价格与起诉时之市价、或真实信息揭露后出售价格之差价作为投资人得请求损害赔偿之计算基础(即毛损益法),较符合实际情况及公平原则〔1〕“台湾最高法院2013年台上字第914号判决书”。。
不论如何,对于在证券交易市场所上市之有价证券,不得有“直接或间接从事其他影响集中交易市场某种有价证券交易价格之操纵行为”,立法目的在防止证券价格受操纵,属强制禁止规定。该条款禁止对某种有价证券交易价格之操纵行为之目的,涵摄了意图以人为方式影响证券市场价格,诱使或误导他人为交易,使某种证券之市场价格以异于正常供需方式而变动者而言,其目的在维持证券价格之自由化,使交易市场在公平、公开的情况下,充分发挥供需之价格机能,避免人为操纵之投机行为影响市场价格而误导投资人,致影响市场交易秩序,亦即使有价证券之价格,能在自由市场正常供需竞价下产生,避免由自由供需关系决定价格演变为有计划之人为价格,以保护一般社会投资大众〔2〕“台湾最高法院2007年台上字第260号判决书”。。
*张玮心,河南科技大学法学院特聘教授;台湾地区中央警察大学法学博士;英、美法律学双硕士;台湾法官学院、司法官学院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