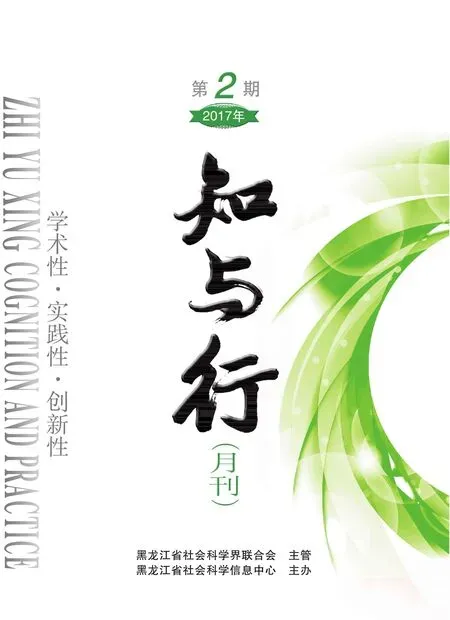公私游移:网络社会逻辑及其后果探析
2017-01-23门豪
门 豪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长春 130012)
公私游移:网络社会逻辑及其后果探析
门 豪
(吉林大学 哲学社会学院,长春 130012)
“合私为公”是古已有之的社会传统,“公私群己”边界不清、公域私域互侵杂糅。匿名脱域、收编整合,超空间的网络是一种新的社会存在结构,网络拓扑节点平等多发、热度叠加、行动串联。通过“自我技术”实现微权力、吸附力及话语建构,造成社会整体处于“混沌纷争”,公私游移即为网络社会之表征。立体可视化平台、市场商业化产品实现了实体脱域与场景再现的统一,社会存在由实化虚,情感情绪、观点立场“瞬时变幻”“顺势倾倒”。网络行动范式自主、规范悬置,话语原创多元,建构解构共生,公私区隔模糊暧昧,出现了“去中心主义”的“小叙事”后果。信息交互异步、社会情境线索缩减、临场感丧失与“全景敞视主义”,投射且加剧了“公私游移”的社会意涵及其后现代危机实质。去规范、消解过程结构,公私游移是后台展演与现代“自我技术”的夹逼,复杂社会系统的治理情境亟待回应。网络社会包纳收编“生活世界—系统”的本质,是行动者由私及公微权力的肆意蔓延,公力及私最终又导致个体化的困惑无奈和孤独失语。网络空间及其营造出的内爆与空虚,是“网络青春期”的逆反,即公私游移。这需要网络文化“否定之否定”的转型整合,需要参与自觉。
公私游移;网络社会学;后现代主义
马克斯·韦伯曾言明:不管是共同体化还是社会化,一种社会关系只要对外来者是“开放的”,即如果而且只要每一位事实上能够并且愿意参与社会行为的人,都没有受到其制度的排斥,那么这即是一种开放社会关系[1]。显然,网络社会自千禧年以降至今,其在中国社会到来、发展演化直至渗透生活领域、收编一切面向,对于整体社会系统和单个行动者而言,都是一种范式革命。
网络穿透现代社会的运行进程,参与者身在其中并作为独立节点,平等地发声;网络行动瞬时自由,在后现代主义脉络之中,人们的利益诉求及其表达割裂纷争,但在技术手段层面掌握了共享共治的能力,只不过尚处于转型“青春期”的未启蒙混沌状态;抽离高效、缺场脱域等特征,不同于传统社会的运行规则和文化逻辑,重组了原有稳定的地域社会,达成了另一种路径的虚拟秩序再整合;在带来信息交互便利与互联网范式革命的历史范畴中,我们不可避免地要对其场域内社会行动的匿名隐蔽性、契约缺失、道德无感、部分社会成员的共同体缺位等社会事实及其后果进行反思。马克思主义学派社会学不仅是以认识论为前提,更是要对当前社会现象及其问题进行前提批判,以期达致解放全人类、实现社会团结的“理想型”乃至无限逼近“乌托邦”。
一、公私的常与变:地域社会传统
当我们试图解释一种社会现象时,必须分别研究产生该现象的原因和它所具有的功能。一种社会事实的决定性原因,应到先于它存在的社会事实中去寻找,而不应到个人意识的状态中去寻找;相应的,一种社会事实的功能应该永远到它与某一社会目的的关系中去寻找[2]。“不分公私”是传统中国社会文化核心与中轴的外化,它时刻伴随着地域社会的亡盛兴衰——“政治依附性”这一隐形脉络横亘千古,贯穿华夏文明形态流变;正是“家天下”这一显性主线支配了传统乡土;基于此,无从谈起对于“共同体”与“社会”的辨析与切割,不论自上而下无边界扩展、控制凝聚的社会,抑或自发自组织的团结共同体,集体主义话语的源流与形塑机制,均与西方传统封建时期的社会基础不同。
公与私在中国历史上,无论是作为一种抽象的哲学范畴、道德或政治理念,还是具体的民间社会与日常实践,都有错综复杂的发展历程。现代中国的公私观念,须推溯至宋明理学的传统,而不能以西方的“public”“private”勉强训解。宋明理学将一切道德与不道德的问题化约为“公与私”的问题。这奠定了传统社会与历史惯习中“公私游移”的合法性、制度化与社会思想基础。然,社会脉络总体上会呈现“恒常”与“多变”的二元性,并在其二者中游离传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互为参考。及至清末西学东渐,社会对于传统公私观念的认知与界定也多少产生了演变。“私”转而成为国民所具有的自由与权利,“公”除意指社会正义外,更具现代国民对国家认同的意涵。此一转变固然使个体之“私”得到更多尊重,然因“私”之合法性来自“合私以为公”的本体逻辑,使得“公私”“群己”之间仍旧存有密切的关联与互动,也因而使“私”未能建立起根本的独立性,故与西方个人主义的“自我”概念有所不同[3]。时至今日,“自私自利”对中国人来说仍是一个无法负荷的道德谴责,“灭私存公”也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道德诉求。以私园公用为例,熊月之将我国早年个体生活与群体凝聚的变迁焦点转移到了空间因素。通过对上海的“张园”“愚园”等私人花园对公众开放这一现象,透过“私园公用”说明近代城市公共活动空间的拓展,认为“公共活动空间”是休闲活动空间、社会活动空间、政治活动空间的重合[4]。此种“私域及公”的界限拓展,或者说“领域侵占”,究竟是以社会历史传统作为尺度标准,还是社会样态推演、思想开源作为考察维度,恐怕很难在场域内开展普遍共识的现象学“因果解释”。
“公共领域”系指公共的事物、公共的空间以及与此相关的一系列制度和规范,如社会组织、国家、政府、法律等。“私人领域”主要是指个人本身及其所拥有的东西和活动空间,如个人的财产、婚姻、家庭、隐私、人际关系等。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就像井水和河水的关系一样,二者并不一定绝对对立冲突,可以共依共存[5]。由于人们对社会生活、系统世界的前提性认知和辩解成本高、时间长,特别是在当下的信息内爆作为常态的网络社会中,公私领域之间不可避免地会相互侵蚀。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从宏观社会系统考量,现代社会中各种社会设置在一定程度上因社会分工的专业化、隔离化、系统化等,催生出了公私界限相对明晰的产权制度、法律归属;但就具体的个体行动者及其日常性的网络行动而言,信息指令的发送与接收,在互联网信息输入与输出之间逐一辨识“公与私”需要付出的机会成本、时间成本是极为巨大的,而即便如此做出的“主观辨识”,与所收获的规模效应也是微乎其微,甚至可能产生辨识无用的负增长;加之呼应于传统社会文化特性,人们应然自在地处于“公私无意识”,个体几乎无能力也没有潜在意识分辨究竟是处在对“公”的强力审判,或是对“私”负有色眼镜的状态。
二、公私脉络与网络议题的交织杂糅
在韦伯行动理论的二分法中,他选择目的合理的、价值合理的、有感情的、传统的四种类型学划分作为“正式的表达”;在“非正式的表达”层面,他描摹的以“行动合理性程度”“合作化”“行动方向”“行动状况”等指标为量度的社会行动体系及概念图式,却也未能使非正式的行动类型学有效地解决社会合理化难题[6]。欲图探知个体行动者在何种程度上,可以同时满足“理性”与“自由”的折中,毋宁枚举网络社会行动中个体化与个人主义、处处随意的非标准化、非制度化与非理性化;可以说,线下科层支配逻辑中的不可言明性、实体存在的“集体主义”,映射到网络交互状态下,变成了另外一种社会真实与展现模式;这是一种不可考的维度,一种精神放纵和肆意性场所;与其说是社会伦理规范在网络中的“匿名”,不如说网络共识与文化自觉的缺失;与其说网络社会作为新的存在空间及范式,挑战了人类共同体凝聚联结,毋宁说我们的规范机制和责任伦理尚处于空位运行。也因此,网络沦为了自由主义横行的发泄场与“隐形实在”的实践空间;人类所共同面临的网络社会挑战,即“公私游移”,其背后作为支撑的,应当是一种社会规约或新型自觉地调整。在社会发展转型阶段,并非任何事物都可以做出类型学划分,也并不是任何文化养成都经由“外部牵制”得以自觉,这种“自我规训”不应当仅仅是民族国家与社会的产物,更是行动者的内源规整与现代自适应。改革开放引致的阶层区隔与断裂本质上是经济分层的产物,而比经济划分更为高阶和棘手的,是进一步碎片化了文化整体及其大叙事,切割了原有文化梯度。可以说,开放的刺激是社会整体变迁的直接动因,经济的发展造就了辉煌,市场的嵌入也带来了结构异动,网络社会就是最为深刻,也最值得长时段研究的一种社会存在形态。它是流动的,是充满着微权力、微意识、微表达的微型场,当社会整合方式由政府直接控制,演变为社会管理,直至今日的“市场、政府、社会”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始终离不开网络行动尤其是公民社会的线上参与,与此同时,后现代范式情境中的“多元一体”何以可能何以可为,这对于国家和地方政府来说,将成为“瞬时性”“即时性”“权宜性”的治理难题。
就网络社会目前的状况来看,发展一种“实名制”的外部系统作为对内所施行的规约,这本身就是对“网络匿名及无线流动”的现实挑战;实于虚可感,虚于实而言则是无尽的索引与理所当然;虚和实就是“线上网络空间”与“线下真实可感”这对矛盾中所呈现的二律悖反;意欲全描二者一统的真实图谱并将其规范化,亦即达到了网络社会治理的“无管理之管理”的双重情境。这不仅是对传统“公私领域”文化惯习的挑战,更是回应了现代社会人与人关系重塑的迫切需求。费孝通在描绘“乡土中国”全景时指出,缺乏变动的文化里,长幼之间发生了社会的差次,年长的对年幼的具有强制的权力;而从血缘结合转变到地缘结合是社会性质的转变,也是社会史上的一大转变[7]。时空流转到了现代复杂社会,我们的治理情境与总体伦理模糊暧昧,旧时“皇权不下县,县下皆自治”,以县为分水岭,二元双轨,如今网络社会重新大洗牌,新旧双轨同时支配。流动真空的网络社会如看不见的手,其运行规则和内部逻辑的实时流变,加剧了整体社会撕裂程度;自媒体、数据流媒体、公众媒体层出不穷,表现出利益纷争、阶层对立,话语多元、范式自主,时尚瞬息、规范悬置等特征,这是与传统的决裂,是完全不同的新发展轨迹。
哈贝马斯区分出原始社会、传统社会、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等的形态、组织原则与危机类型,认为原始社会存在的是外因诱发的认同危机,传统社会则充斥着内因决定的认同危机,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则表现出——自整体社会系统独立分化出的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出的子系统危机[8],此种困境也使得“生活世界殖民化”,即科层理性、市场机制侵蚀了私人领域和公共空间,现代人处在整体疏离的状态。到了现今人人可及的网络社会,市场、信息、“关系”等交错纵横而诞生出“新新人类”。“金钱、权力、地位”等社会资本要素,对其受益者的馈赠经由网络输入输出,原有的资源依赖、路径依赖只能降低效率,在网络社会中使得单一主体很难成为绝对的垄断,行动者出于理性,出于“合法性”与“有效性”的权衡,做出选择的机制更为繁复;作为权力载体的信息,其正反两用导致了“无声信息战争”。可以说,线上社会中的信息侵吞一切,网络嵌入社会,资本重新整合,结构更为复杂,秩序源于自发,这实质上就是无形的社会革命。谁没有了交织网络的“线”,谁就缺少了社会资本的“弦”,那么他就无法获得发生的权力,在“无形社会”中完全失联。在这种情况下,私人生活无法与共同体的“公”有效链接,在闭环的线上公共服务领域中,无法享受可视化快感;无法参与公共空间的讨论,相较之网络原住民而言,这不仅仅是“落后”,而成了“原始人”;同时致使线上的“发财机会”永久性地成为可见而不可能,线上经济活动参与缺失。总地来说,网络参与几近等于线上的微权力,这种“微弱的私”与“强大的公”仅仅是“一线之隔”。微权力它有对公权力和公共权力的蚕食能力,它有使个人通过由私及公的延伸发生命运翻转、地位逆袭的超能力,也能使某些事件发生三万里奔流直下的强悍动能,这是一种可以介入“公”的“私”,是一种“细线”的本能,可以触及世界的无限不可能,使社会地位“非正常化”只是冰山一角。
三、网络社会:新型组织形式及其范式革命
曼纽尔·卡斯特认为,网络社会的社会结构由基于微电子的信息和通信技术推动的网络组成,人类在生产、消费、再生产、经验,以及富有意味的文化交流、所表达的力量等方面的组织安排均有所改变[9]。网络与自我即辩证对立的两个假设,都建立于两个原创的、有说服力的假定基础之上。第一个假定是结构,归因于网络的崛起以及社会关系和技术革新的辩证互动。第二个假定以自我重要性为前提,社会群体的认同方式形塑着社会组织,“每种认同建构类型导致不同的社会组成结果”[10]。
(一)收编统合:全新社会过程及其运作机制
围绕着信息流动(information flows)与符号操控(symbol manipulation)组织起来的社会结构,卡斯特区辨出三种认同。合法化认同(legitimizing identity),由社会支配制度(institution)建立,以扩展并制度化其对于社会行动者的统治。抗拒式认同 (resistance identity),由被排斥于统治谱系之外或被贬抑、污名化的社会行动者所产出,该认同引发了社群的形成,以此来回应其无法忍受的压迫条件,建立主体性。规划性认同 (project identity),指当社会行动者基于自身可获得的文化资本,建立一种新的认同以重新界定其社会位置,并借此寻求社会结构的全面改造。如女性主义挑战父权家庭、人格结构依赖及其再生产等[11]。权力置于网络信息符码(codes of information)与意象再现(images of representation)情境中,社会据此进行组织和制度建设,人们据此营造生活并决定其行为。信息,权力与行动者,均以“网络”作为中轴展开社会情景,创生新型权力秩序与社会凝聚。全球信息流、信息高速公路,网红引领时尚制造权威发言、网民甘为信徒自愿服从等语汇投射出新型社会组织模式;这种全新技术针对人类群体,不是将人们归结为肉体,而是使人群组成整体大众——网络社会群体划归分层与操控的方式不是在人——肉体方向上,而是在人——类别的方向上完成的,即隐藏着背景操作的“生命政治的诞生”[12]。
现代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指在个体与国家的社会之间出现的,由政治群体和志愿者组织网络构成的实体。它的异质多样性、事务疏散功能与权威得到居民支持,并对政治生活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3]。市民社会的踊跃,人人可见、触手可及的参与,即受益于网络空间所直接提供的通道,最低准入和低廉成本生产了匿名化自由的想象。身处在网络时代,人们勇敢追寻个性与自由,注重权力表达、能量释放,将社会的担子加以“言说”,以实现个体解放;网络社会内部庞大的亚群体频频互动博弈,营造出“集体欢腾”之效果,使得网络如同一面镜子,把行动者在现实层面的困扰“虚拟化”,并将叙事问题在外在物化,一一映射;也好似一把放大镜,把社会焦点以极端的形式逐一展示[14]。市民社会在网络空间中,受制于网络个体与网络共同体的冲撞对立,其整合状态就是一种“群体不整合”。真正的公共领域,是否因网络社会表现的“原子化”与“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而受到侵袭?网络机制中的“公”与“私”的边界到底是否明晰?公私区隔到底在哪里?模糊暧昧的公私界限会导致何种社会形态与后果产生呢?
(二)解构重组:隐性话语的真实与幻象
德国社会学家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认为,单个个人身上总带有来自某一群体的习性,并且正是这种具有群体特征的习性在他或她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或多或少也随之被个体化了。自我——我们认同构成了个人社会习性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且其本身也在走向个体化的过程[15]。网络行动认同的建构过程不单是自我认同建构,其中还藏匿有一种主观无意识的随意与欺骗。基于信息输送节点的内外极端不对称,使之在法律结构中生产自媒体话语系统,构筑另一套看不见的、抗拒外部性的框架,“私”时刻利用着“公”,戒备着“公”,而“公”又反作用地建构或影响着“私”;人们既可使用刻意渲染、主观营造,也可将事态相对主义并逐渐合法化,塑制出外部社会对内的认知盲区。一旦这种操作流程不幸暴露为外部所熟习,那么自我建构、人人自危的自媒体与避风港不远矣。看似合理的机制,却可能随时面临塌方式的自我消解危机,外部对该系统合法性的运作模式不断复制传散、迅速同质化且手段毫无创新,网络行动者彼此认同的“表演操作”,却也足以摧毁实体社会信任系统。
个性形成的时代充斥着喧嚣与愤怒,对个性的寻找各自分道扬镳,孤独的个性建设及其不稳定性,促使个性的建设者去寻找属于自己的领地,以便他们能够一起把各自体验到的恐惧悬挂其上,并在同样感到恐惧和忧虑的其他个体的陪伴下共同捉鬼驱邪[16]。身在场域,行进与实践的网络行动者,熟习焦虑制造与释放的流通规则,不但营运自媒体而且“拿得起放得下”,整日操演,制造看似平静的线上认同。通过“文化工业的自明性”,非公众舆论便通过“公众”舆论,被整合到现存的体制中[17]。“公私游移”的现象背后,实则带有巨大不可知的企图心。根据滕尼斯对“共同体”与“社会”的区分,社会团体(Gemeinschaft)是靠自然本能欲望或自然生活凝聚培养起来的,而社会则是深思熟虑后选择之结果[18]。如若沿袭这种认知轮廓,那么“公共主义”或“自发结社”在内里、前提下就存在极大的暧昧与模糊,因为现实生活中我们几乎很难透过情感性或所谓的“理性选择”准确辨识究竟何为公何为私,这将使人陷入“生活类型学”区辨的泥淖中。枉费气力区辨“共同体”与“社会”,“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不如利用互联网本身的交互便捷性,使得私人生活与社会分工“去边界化”而“公私合营”,“共同体社会”合二为一体。最终“生活世界与系统”相互殖民侵蚀、一片混沌。互联网有机嵌入“社会肌理”,满足了“混沌”后的无知和便利。软件信息交互平台的“互联网”,后工业时代的“人—物质实体—生活”为架构依托的“物联网”,它们互联互通的特质,几近收编了随处可见的生活世界及其任何议题,解构了惯性与传统,简单化、数字化、愚昧化了内爆的世界,意义不再充分和重要,零碎的信息重组了庞大的认知系统和知识体系。
(三)“书写通信”:主体性的构筑与操演
福柯对“书写”作为“自我技术”进行解构时,言明日记和通信尽管有不同的特点,虽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演进与发展,但它们的一个共同特征就是为了自我关注、自我塑造[19]。书写的功能就是去建构一个“身体”,将其转变成“组织与血液”,成为书写者本人的一个理性行为原则。在网络行动中,在一种深刻地铭刻着传统的文化中,借助那些已被言说的公认价值,借助话语的重现,利用技术可以轻而易举地实现“情景再现”;借助古老与权威封印之下的“印证”实践,网络独立发展出了一套伦理,“关注自我”极其明显地引导了这种伦理的目标:网络自媒体及其作为系统的行动流程回归自我、接触自我、与自我一起生活、相信自我、从自我中受益和自我享乐。去伦理的行动范式是为了达成对自我书写、价值传承和再造,进而形成了外部系统的又一套规范,网络伦理再造的过程就是书写的外化,同样也是对原有自我的、元叙事的否定及创新。全新网络书写环境的颠覆及重置,带有与原有语境决裂的、非常明显的张力,“节点输送”同实体文化“传诵”机制的另类衍生过程,既是现代语境的全新脱出,又是传统隐喻的新生。内外交通、“公私之争”,其实也是“后现代社会”多元共生、建构再解构、混沌流离、模糊不定与自我小叙事“成长”的表征。
原初的通信置于具体实践性的网络社会场景中,不应被简单视为个人书写实践的延续。它不只是借助书写而完成的自我训练,也构成了某种展示方式——自我展示,向他人展演。这是关乎个人生活的、成败祸福的直接呈现、近乎肉体的存在。网络书写通信、展演行动等一套“自我操作”流程,把“个人资产”主体化,同时它也构成了灵魂的客体化,既能够带来个体性的享受,也为相互凝视检查、同化转化,社会异质网络、社会资本系统——微观共同体想象提供了平台基础。按照福柯的解释,主体塑造的模式有三:作为主客体同时建构出的“真理”的塑造;权力的塑造,即排斥权力塑造出疯癫,规训权力塑造出犯人;伦理的塑造,即自我塑造。这些支配技术或治理术,在网络文化资本营造与演变的过程中,伴随着社会资本、人际联带以及囊括各类型受众在内的所有社会成员,始于整体网络情境,终于主体个案节点。主体性、权力操控、伦理订定均与信息流相伴而生,公与私若是因此丧失了伦理性的边界,便也合乎于情理。因之,可以说,网线是“公私游移”的助力管道,公私区隔与网络社会展演操作流程、生产动力机制水火不容。
(四)后现代表达与“去中心主义”行动危机
依据行为主体更多受到自身内化标准的影响,如情感、态度、价值观等,还是更多关注自我所承担的社会性角色因素,如行动更切合于群体的行为标准等,可因此划归出个体性自我意识与公众性自我意识。在客观全廓上,网络认知的节点环境异质性高,真实与幻象很难辨别,很容易理解诠释网络社会中“用虚假的身份,说真实的话”、缺乏社会临场感、存在信息交互的异步性、社会情境与线索缩减[20]、主客二元差异、“线上下”二分法、双重行动逻辑。奥特加在《人与人们》中指出交互主体性的实践悖论,即我们习惯于伪装着去生活,但我们实际上并没有过我们真实的生活,而假使我们一定要过这种真实的生活的话,它会使我们自己从所有这些为他人所接受的解释中解放出来,在这些他人中间,我们发现了我们自己和被大家共同称之为的“社会”,这样,我们就在不时地创造一种富有生气而又明确的与我们作为彻底实在的生活的联系。从反思的立场上来看,他人是作为一个本质上的陌生者而显露的,而社会则是作为一种伪实在、一股趋同性的意见、一种巨大的作用构造组织而出现的。集体性确实是某种人类的事情,但它是一种没有人的人类,是没有精神的人类,是没有灵魂的人类和反人性化的人类[21]。我们的生活受到媒介信息轰炸的饱和程度,暗示了“已经再现”与社会本身之间没有区别[22]。历史将人类沟通的书写、口语和视听模态整合到一个系统里。自发的、非组织的意图与成员实践了的集体行动存在相当的分歧。网络交互规范由外部推力、安排管束到内源性实践自觉、网络惯习养成、非正式制度向正式制度演进。无缝表演、肆意宣泄、自我建构“社会人”,网络社会所形现的自反性的“公私区隔”,我们试图去自我主体般地生活,最后终究发现在表演大众自我的系列行动中,背离了本意,营造了虚假的自我和建构了陌生的社会。
地域性解体,脱离了社会场景中文化、历史、地理的意义,重新构筑起功能性的网络或是模拟意象,使得流动空间取代了地方空间。在网络系统这种“真实虚拟”(real virtuality)文化场域中,制造同意或相信(make-believe)即相信造假(believe in the making)。超空间(hyperspace)的网络就是结构,开放并无限制地扩展,只要能够在网络中沟通,即可分享相同的沟通符码,即可整合新的节点,无穷尽地解构与重构文化[23]。先前离散的无组织的个体可能形成的是比较小的、高度局部的团体,当他们将交流网络连接起来,并将意见传递且普遍化到其他网络的时候,就形成了运动,他们也就变成了有效的集体行动者。这种公共意见的组织化能够汇聚必要的资源和能力,使得团体引起公众注意,将“意见”转化为社会问题[24]。因此,互联网个体化的组织形式,有助于公共空间的诞生,进而衍生出新阶层、亚群体间的信息交互,这也是现代社会流动性特征的表现;但,与之相反并可能出现的极端化形式则可能是,个人主义散漫终将导致网络社会中公域的利益对立其无法实现整合,网络共同体契约缺失与存在危机则随处可见。
四、复杂社会系统的伦理反思
进入网络联结的低廉成本及其普及化,造成了社会资本边界的模糊。个人的实质理性并没有增加。局限于日常生活的有限社会环境,普通人通常不能理智地了解庞大的结构,包括那些合乎理性与不合理性的结构,而他们的生活情境是这些结构的附属部分[25]。个人爱情、隐私、色情内容、犯罪信息等,相较于传统印刷可见的媒体,借助网络所能接触到的内容具有前所未有的庞杂;同样,与传统社会网络相对照,人与人间的关系对于共享资源的流动与内容所加诸的限制不同之处在于,网际网络使得这类关系和限制降至最低[26]。我们精心诠释和扩展规则,以适用于新的情况,强行地把规则套到客观现实上,用我们先前对规则的约定来限制这种现实。这种“正常化—规范化—行动”[27]的“社会养成”是必要的。新制度能侵蚀现存的观念,战胜既得利益,按它自己的需要重新制定新制度,但这一过程需要相当长的时间[28]。
当公众舆论潜入到涉私道德和社会关系时,一方面其进行强行的道德宣判和方向裁决;另一方面又为个人表演与网络默会知识传散提供了实践层面的“同一合法性”;社会网络同质增强、个性弱化,自我认同危机显现——“自我认同并不是个体所拥有的特质,它是个人依据其经历形成的作为反思性理解的自我”[29]。化私为公,因此使得私人领域在后现代符号媒介中日益标签化、表浅化。网络节点的主体性呈现以符号为媒,相较于传统社会互动,由“私”虚化而集成的“公”,按照表演意愿在“台前”和“幕后”定位不同角色,虚拟空间的契约缺位与共识缺失使得网络应然性伦理弱化。个人淹没在技术中并逃离社会,而在现实中又形塑了新的网络与实体空间。不止于此,随着技术的发展,公私领域的融合使隐私显性化成为常态。现代化科技迅猛发展进而使得网络节点时刻处在“全景敞视主义”笼罩中,搜索引擎、网格监控、黑客侵袭等见缝插针,令人猝不及防;“公”话语外显并成为穿透网络、钳制一切文化的武器,“自我——他人”技术将“私”一览无余,微观权力监视无处不在。网络空间主体的自由切换、“博客”“空间”等私人领域公共化;同时,网络论坛、新闻网站等公共空间呈现“公共领域私人化”;公私领域边界模糊、不具有公共性的私人话题、私人事件大量进入公共领域或公共空间,成为公共空间、公共领域的探讨话题;“伪公共空间”、公私情境的合并现象大量出现。有学者认为,私人领域的透明化,实质上就是公共空间的结构转型[30]。而笔者却将此种“公私情境混沌”的网络生活视为一种伦理错差,一种后现代主义的网络横行与扩张,更多地会带来个体生活与集体行动的游离紊乱,网络行动机制表现为“去标准范式”“去本质主流”“去大叙事”的特征,种种“流动性”进而强行对现代社会规范的模糊、生存规则的裹挟与夹逼。制度化的网络标准缺失并非可以解读为“生活辩证法”,在此种种不甚确定、流态质的社会情境和网络的行动者,如果我们连“人人即可挑战规则、人人均有主体契约”这种网络话语都可以包容的话,那么涂尔干式的经典提问不得不重新反思:网络社会又何以可能呢?
网络本身所提供的低成本发声、信息交互便捷高效、叙事空间与手段的“无边界”等前所未有的主观行动图式便利性,又在客观结构层面使得“公私统合”“规则游移”“范式自治”成为可能;与之呼应,在传统社会机制尚未及时转型进而呼应“网络流态”的“空档期”,一些行动者无力企及“文化自觉”的高度,遂使得看似平静的网络空间存在无限遐想与博弈空间。不妨试想,某些独具企图心的行动者穿梭流离于文明的现代社会,任随互联互通规则对其毫无拘束,或成就中心自我,或挑战主观规则,又或线上线下双重脱轨;公私游移、逻辑变幻、规则暧昧、行动游离,复杂社会系统的治理情境及回应,因之值得跨学科深入探究。
[1] [德]韦伯. 社会学基本概念[M].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10:82.
[2] [法]E·迪尔凯姆. 社会学方法的准则[M]. 北京:商务印书馆, 2011:109-122.
[3] 黄克武,张哲嘉.公与私: 近代中国个体与群体之重建[M]. 台北:“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2000:1-57.
[4] 熊月之. 晚清上海私园开放与公共空间的拓展[J]. 学术月刊, 1998,(8):73-81.
[5] 刘畅. 中国公私观念研究综述[J]. 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3,(4):73-82.
[6] [德]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第一卷)[M].洪佩郁,蔺菁,译.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357-363.
[7] 费孝通. 乡土中国生育制度[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69-75.
[8] [德]哈贝马斯. 合法化危机[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9:26.
[9] Castells M. The Network Societ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M].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Incorporated, 2004:3-48.
[10] [美]斯塔尔德.网络范式:信息时代的社会组成[J].刘伟,译.国外社会学, 2003,(6):77-82.
[11] Castells M. The Power of Identity: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J]. John Wiley & Sons, 2011:6-11.
[12] [法]米歇尔·福柯. 必须保卫社会[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229.
[13] [英]罗宾·科恩. 全球社会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553.
[14] 门豪. 网络共同体的实体缺位与权力重塑[J]. 理论界,2016,(5):54-64.
[15] Elias N. Society of Individuals[M]. Bloomsbury Publishing USA, 2001:176-190.
[16] [英]齐格蒙特·鲍曼. 个体化社会[M].上海:三联书店, 2002:192.
[17] Habermas, Jürgen, 曹卫东,王晓珏,等. 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M]. 上海:学林出版社, 1999:295-297.
[18] [德]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M].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56-119.
[19] [法]米歇尔·福柯.自我技术:福柯文选(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219-246.
[20] 陈曦. 网络社会匿名与实名问题研究[D]. 北京邮电大学, 2014.
[21] [美]弗莱德·R·多迈尔. 主体性的黄昏[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51-52.
[22] Hodkinson P.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An Introduction[M]. UK:Sage, 2010:309.
[23] Castells M.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The Information Age: Economy, Society, and Culture[M]. New Jersey:John Wiley & Sons, 2011:460-509.
[24] [美]詹姆斯·博曼. 公共协商: 多元主义、复杂性与民主[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6:116.
[25] [美]米尔斯. 社会学的想象力[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2:182.
[26] Lin N. Social Capital: A Theory of Social Structure and Action[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210-242.
[27] [美]亚历山大. 社会学二十讲[M].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189.
[28] [美]刘易斯·A·科塞. 社会思想名家[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7:237.
[29] [英]吉登斯. 现代性与自我认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8:58.
[30] 陈长松. 论网络空间公共领域、私人领域的融合及影响[J]. 学术论坛, 2009, 32(11):156-159.
〔责任编辑:徐雪野〕
2016-12-19
门豪(1994-),男,山东曹县人,硕士研究生,从事社会理论与社会治理研究。
C91-06
A
1000-8284(2017)02-0104-07
社会热点论坛 门豪.公私游移:网络社会逻辑及其后果探析[J].知与行,2017,(2):104-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