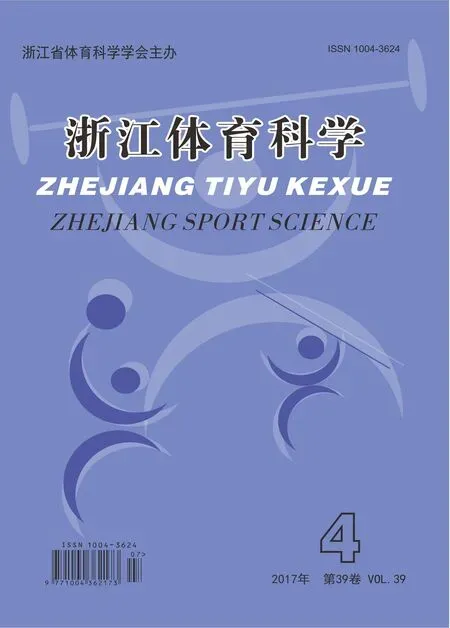野外治疗心理干预模式的研究述评
2017-01-23张宇
张 宇
(温州医科大学 体育部,浙江 温州 325035)
野外治疗心理干预模式的研究述评
张 宇
(温州医科大学 体育部,浙江 温州 325035)
在查阅大量国外文献的基础上,文章介绍了欧美国家上世纪90年代初已经开始研究的野外治疗心理干预模式。采用文献资料、逻辑分析法,从野外治疗的起源、定义、理论体系、疗效因子、治疗过程几个方面分别展开论述。结论:①野外治疗定义尚未完全统一,不利于行业健康发展;②野外治疗理论体系尚未完善,引发争议。③野外治疗有效,疗效因子和过程有自身特色。
野外治疗;体验教育;外展训练
在欧美国家,野外治疗(wilderness therapy)被认为是一种针对个体的情绪、行为、物质成瘾等心理问题极具潜力的心理治疗方式,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群体的青睐,并逐步成为解决青少年心理问题的一种可替代性的干预方式[1]。野外治疗在美国已经有60多年的发展历史,研究者普遍认为Outward bound是其前身,根源可追溯至上世纪初的帐篷治疗( tent therapy),并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迅速发展[2]。大量的研究结果表明,野外治疗对参与者有积极正向的干预效果,参与者的行为、情绪、物质滥用与成瘾等问题等够得到有效改善[3]。尤其是在青少年心理治疗领域:青少年性侵犯,青少年辍学,青少年抑郁及其他临床症状,以及青少年犯罪等问题上,野外治疗取得了较好的治疗效果,得到广泛认可。从专业的心理治疗角度来说,野外治疗可以改变个体不成熟的防御机制,改善个体适应不良问题,情绪表达问题,精神健康相关的临床症状,以及功能不协调的人格模式[4]。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和进步,野外治疗的受用群体覆盖更加广泛,涉及的范围更加宽阔。上世纪90年代初,鉴于野外治疗在心理治疗实践领域的迅猛发展和影响,学术领域,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对野外治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展开了多方面的深入研究。研究内容涵盖:野外治疗的定义、概念、起源、理论基础、性质、治疗效果、疗效因子、效果评估、伦理规范、治疗设置等等。我国香港、台湾地区于2000年以后开始了野外心理治疗模式的实践和研究,越来越多的青少年正受益于此。以谢智谋为代表的学者将其称为"冒险治疗"。香港地区称之为历奇为本的咨询[5]。
反观国内,关于野外治疗的相关实践和研究都还在处于萌芽阶段。为了引起国内学者对该领域的关注,推动该心理治疗模式在中国的发展,文章试图从野外治疗的概念、定义、起源、理论基础、疗效因子等几个层次对野外治疗做尽可能详细的介绍。
1 野外治疗的定义及其发展演变
Kimball and bacon (1993)第一次试图给野外治疗下一个广泛性的定义,认为野外治疗起源于外展训练(outward bound) ,主要包含以下几点:①野外治疗是一个团体历程;②包含一系列看似危险实则安全而且具有挑战的冒险活动;③在野外或者陌生的场地进行;④利用治疗性技术,如反馈、日记、个体咨询、自我暴露等促进个体的成长;⑤治疗周期变化依据资金状况,和参与者的具体情况来设定。他们认为野外治疗的领导者是一个掌握野外生存技能和有较强判断能力的老师,没有提及领导者是否需要心理治疗相关的背景,以及相关的职业资格[6]。
Powch(1994)认为野外治疗也是源于outward bound的教育理念,特别强调野外治疗必须发生在真实的野外环境,同时坚持活动必须具有治疗性的目标。野外治疗的定义必须包含4个要素:①锻炼团体成员直面恐惧;②建立团队信任;③野外情境下即刻具体的反馈;④营造平等公正的氛围[7]。
Davis-berman and berman(1994) 认为野外是治疗是利用传统的心理治疗技术,特别是团体治疗,在户外情景的设置下,利用户外冒险活动来促进个体成长的一种治疗模式,包含以下几个要素:①基于临床评估的参加者;②详尽的每个个体治疗计划;③户外技能教练指导下的冒险活动;④基于朝向目标行为改变的活动设计;⑤专业人员指导下的团体心理治疗规则,和个体治疗进程评估[8]。Russell认为此定义建立了第一个公认的、基于经验主义的用以理解野外治疗的理论框架。但是他们认为野外治疗项目的工作人员并不需要专业的心理咨询技能,只是提出随队的临床督导者,必须具备相关的资质。
Russell(2001)在总结大量文献和实际考察的基础上提出了整合性的野外治疗的定义。他认为野外治疗必须包含以下四个要素:①设计和理论基础应该涵盖简明清晰的治疗假设、治疗目标和效果评估;②治疗个体的招募和筛选应该基于详细的临床评估,并建立个人治疗计划;③利用户外冒险活动和野外生存、反思等技能,促进个体以及人际关系的成长;④户外冒险活动应该在专业技能人员和执业心理治疗师的指导和帮助下进行,保证活动的设计有利于个体朝向治疗目标发生改变;⑤同时治疗过程以及后续维持阶段需要家庭的配合,以提供有利于个体成长和维持的治疗环境[9]。此定义在野外治疗的历史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明确了野外环境和专业资质的必要性。
Crisp (2004)在Russell的基础更加具体的,并且从关系和界限的角度提出了野外治疗的定义。首先野外治疗的基本要素包括:①个体问题的评估;②利用人格、行为和心理问题与改变的理论为基础来解释问题的形成的原因和本质;③选择与理论假设相关的准确的干预活动介入个案的问题;④根据个体的需要和现实状况不断地修正治疗方案和策略。同时必须明确野外治疗中治疗师与个体的专业关系:①治疗师提供的关系训练能够满足个体朝向治疗目标的需求;②治疗师与个体建立治疗约定,内容包含目标、限制、方法、预期结果和治疗风险;③治疗师需要提供个体最佳的治疗方向,坚守治疗原则,以避免个体身心受到伤害[10]。
在野外治疗漫长发展历史中,无论从实践方面还是学术研究层面,许多野外活动都以野外治疗的名义如火如荼的开展,经常会以Adventure course (冒险课程) adventure therapy (冒险治疗) challenge course,(挑战课程) wildness therapy(野外治疗),wildness adventure-based therapy (野外冒险治疗) 等定义出现,交替使用,来试图描述野外治疗。不统一的概念,带给了这个行业很多问题,同时也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带来了难度[9]。因此,需要更多的学者潜心深入的研究,争取早日能够建立一个公认权威的野外治疗的名称和定义。
但无论是野外治疗以什么名称来定义,研究发现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至今,越来越多的学者趋于统一的认为:①是否发生在野外环境,②有没有心理学专业资质人士的指导,有没有心理学及相关治疗理论的支持和介入,是区分野外治疗和治疗性野外活动的两个主要因素。 Williams(2004) 指出,野外治疗必须界定个体所要处理的问题,对界定的问题必须进行有目的的介入,并且根据理论基础进行野外及冒险活动的设计与决策。对于那些没有进行个体问题界定,没有特定预期结果,采用普遍性的野外冒险活动,没有相应心理学基础的活动只能称之为治疗性的野外冒险[11]。
综上所述,本文倾向于认为野外治疗是一种以野外环境和冒险性活动为背景和载体,以激发个体体验为契机,充分利用户外环境及冒险活动的疗愈功能,在心理治疗理论指导下的,综合运用各种心理治疗技术,针对个体不同情况,制定有利于个体心理健康成长计划的一种心理治疗模式。
2 野外治疗理论体系的研究述评
2.1 体验教育理论是野外治疗的基础理论
2.1.1 Outward bound教育模式是野外治疗的实践前身。从杜威的明日之学校开始,体验教育哲学思想不断被以各种方式进行实践。其中与野外治疗起源密切相关的Outward bound 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体验教育理论的发展。库尔特·哈恩(Kurt Hahn)从实践出发进一步强调了个人体验的重要性,引领了户外活动和相关教育机构的蓬勃发展。上世纪60年代,受outward bound在青少年人格塑造、团队精神、社会责任心等方面取得巨大成果的影响,Outward bound 开始被引入作为针对一些被关禁闭和接受心理治疗的问题青少年的一种替代性方式出现,并且取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此举吸引了大量学者的研究兴趣,由此以 Outward bound 作为前身的野外治疗干预方式得到了高度的发展。Kurt Hahn 的outward bound的教育哲学思想不仅仅是以体验为中心的,而且是以价值为中心。从做中学的理念目标不在于教授学生学术技能,而重在学生人格个性的发展,多数学者倾向于认为Hahn的理念更适用于心理模式的改变而不是教育层面的改变[9]。Outward bound在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上取得的良好成绩,进一步推动了体验教育理论的发展,丰富了体验教育理论的体系,加深了内涵,拓展了外延。 Outward bound教育模式一直被认为是体验教育思想的伟大实践先行者,甚至有人认为有了Outward bound才有了当今多彩多样的体验教育模式,才有了体验教育理论的建立和发展[12]。虽然以Outward bound为基础的野外治疗的前身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野外治疗,但是它是野外治疗的实践基础,是野外治疗的理论起点。
2.1.2 体验教育理论是野外治疗的理论出发点。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狄尔泰赋予体验概念性功能以来,“体验”一词逐渐成为哲学、心理学、教育学等领域常用词汇[13]。梅洛-庞蒂认为我们生活于能够感触大的世界之中,人类所有心智能力都只能通过“体验”才存在[14]。20 世纪 70 年代莱考夫等人发展了体验哲学,体验哲学的核心思想是人类的范畴、概念、推理和语言均源自人们与客观外界的互动体验和认知加工。“从根本意义上说,心智是基于身体经验的,意义是基于身体经验的,思维也是基于身体经验的。这就是体验实在论的实质。”众多学者的研究趋于一致的认为:体验教育理论的哲学和发展基础为杜威的经验主义和课程哲学,他认为教育的本质为“经验的改造和重新组织[15]”。
20世纪 80年代,伴随建构主义的兴起,人们对学习的看法发生相应转变。在许多教育和心理学家看来,学习是“通过经验转化创建知识的过程。知识来源于经验的获得和转化过程的综合”;单纯依赖体验和反思,并不能使学习效果达到最佳。”[16]
20 世纪 80 年代初,组织心理学家库伯 (D.Ko l b) 吸收杜威、罗杰斯等人的合理思想,提出了著名的“体验式学习循环模式”。在库伯看来,体验式学习要经历 4个阶段:①具体体验。学习者在真实情境中活动,获得各种知识,产生相应感悟。②观察、反思。学习者回顾自己的经历,对体验进行分析、反思。③抽象的概念化。学习者把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建构一种理论或模型。④主动检验。学习者在新的情境中对自己的理论假设进行检验。库伯指出,这四个环节分别代表了感知学习、反思性学习、理论学习和实验四种最为有效的学习方式,因而体验式学习本质上是一种综合学习。库伯的体验式学习循环模式宣告了体验教育的理论体系的科学建立[17]。紧接着美国体验式教育学会将体验式教育定义为“一种教育哲学和方法论,在这种哲学和方法论的指导下,教育者有目的地把学生置于直接经验和专心反思中使其增长知识、发展技能和澄清价值”[18]。
重视体验教育,实质是关注学生在日常生活中形成意向结构,让学生意识到与周围世界交往活动的方式、向度和敏感性,使学生自觉体验日常生活世界,感悟生命活动,反思人活在世上的意义,关注人与周围世界的和谐,实现人的主体性[16]。
更多学者的研究让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个体现实生活的认知、情感、态度、行为等反应方式是个体在过往的生活环境中,与外部世界相互作用时产生的体验及其结果。库伯的体验学习圈认为学习是“通过经验转化创建知识的过程。知识来源于经验的获得和转化过程的综合,是一个螺旋循环不断地向前的过程”,为我们提供了“利用此时此刻的体验重温和修复过往经历糟糕体验,利用此时此刻体验带来的感悟和反思检验和改变过往不良认知结构和行为模式提供了理论假说和治疗契机。因此野外治疗借助野外生存、冒险性活动来激发个体的体验,利用此时此刻强烈震撼的体验来修复和改变过往不良的体验和认知结构就有了理论的起点和基础。
2.2 大自然是野外治疗理论体系中的特色存在
Russell认为野外治疗的的理论特性是大自然特有的的疗愈功能。自然因素和心理治疗的整合通常意味着某种特别的仪式和典礼。全世界所有的文化都认为人们能从自然环境中获得自我洞察和鼓舞[9]。野外这个比大自然更显孤独和野性韵味的词汇,似乎更能让人联想起人类的本能求生欲望和意志。野外求生更像是现实生活中的隐喻,因为野外生存中的团体动力、人际交流、课程任务设置能从各个层面影响个体的现实生活。虽然目前我们仍然无法准确地说出自然和野外在治疗中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作用,但是脱离了自然环境的治疗不是真正意义的野外治疗。就像“让山自己说话”这句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名句所传达的感动,野外治疗中经历的大漠落日、狂风暴雨、清新空气会让人一次次在无法用言语描述的体验中落泪,让生命和灵魂在一次次欢心鼓舞和感动中得到修复[1]。
2.3 心理学理论是野外治疗的理论核心
判断一个活动是不是心理治疗,首先要看的是有没有心理学理论基础。正式的心理治疗需要在系统的心理学理论基础的指导下进行,有了理论基础,才可以建立治疗的基本框架,解释个体问题的原因和本质,建立基本的治疗假设和治疗目标,让治疗结构化。野外治疗必须在心理理论指导下界定个体所要处理的问题,对界定的问题必须进行有目的介入,并且根据理论基础进行野外及冒险活动的设计与决策。大量学者的定义也不难发现,治疗师的资质,常规的心理治疗原则,心理治疗技术的运用,人际界限的伦理准则成为区分治疗性野外项目和野外治疗的核心要素。目前的野外治疗活动最多的被认为是一种基于家庭系统观点的融合了野外活动的折中的认知行为治疗心理治疗模式。除此之外也有以精神分析依恋理论、客体关系理论、人本主义理论为指导的野外治疗项目。无法自成体系地对个体问题进行原因解释、治疗假设,只能借助现实的心理学理论,并在其指导下进行的现状,引发了不少学者和机构对于野外治疗是否是一种独特的有别于其他传统心理治疗模式争论和质疑。
3 野外治疗疗效因子的梳理与归纳
3.1 野外与求生冒险挑战
野外治疗的主要活动是野外生存和冒险性活动挑战为主。自然的疗愈功能是野外治疗的特有的也是区别一般心理治疗的本质的疗效因子。另外未知的环境,看似危险和高难度的冒险挑战能够直接地唤起个体焦虑、恐惧、脆弱、兴奋的情绪,直接地创造了心理干预和治疗的机遇。面临危险挑战时候,如何接纳不良情绪,如何带着焦虑、恐惧的强烈感受去完成任务,必然使个体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能量,带给个体深刻的体验。而人类所有心智能力都只能通过“体验”才存在[14]。成功的体验能够显著的增强个体的自尊水平,提升自我效能,自我认同,提升个体内控倾向[19]。
3.2 关系
关系是一切心理问题产生的根源。在野外治疗中,个体面临者三种关系,个体与自然的关系,个体与野外治疗师/野外领导者的关系,个体与个体即团体成员的关系。
3.2.1 个体与自然的关系。生态心理学认为人与大自然存在着天然的、原始的、本能的联系。现代社会文明,切断了人与自然的联系,导致了一系列的所谓心理问题的现代文明症状。野外治疗带领个体置身自然之中,有目的让个体亲近大自然,让个体通过野外求生及冒险活动,深刻地唤起原始的求生欲望,在努力挣扎的生存体验中厘清人与自然的深层关系,获得内心的完整感与控制感,恢复内心的平衡。国外学者称之为自然的结果,并认为这是区分是否为野外治疗的关键因素[20]。
3.2.2 个体与野外治疗师的关系。野外治疗过程中,移情不可避免的会出现。心理动力学认为,移情的发生是心理治疗的关键。个体在野外治疗过程中会将治疗师投射成父母或者重要他人,为治疗师利用反移情技术进行干预带来机会。野外治疗过程,治疗师与团体成员真实地生活在一起,共同徒步、露营、登山为治疗师利用此时此刻的针对性的具体行动来代替传统的语言解释移情问题提供了机会。野外治疗过程是无论从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是一个相对艰辛的过程,治疗师提供的稳定的、鼓励的、包容的抱持性环境能够让个体直接地获得与以往不同的体验。治疗师及时地反馈与引导,能够更直接地让个体宣泄不良情绪,修复过往的破坏性关系。同时从社会学习理论角度来说,治疗师以身作则的躬亲示范也会对个体产生深刻的影响。Russell的调查研究发现,个体反馈最多的是野外治疗师更像是一个真实的人,能够让他们敢于接近,打开心扉。
3.2.3 团体关系。 团体关系可以更专业地表述为团体动力。首先从团体成员是经过严格筛选,背景和问题相似,为成员确立了归属感。其次野外团体需要个体与个体之间身体力行的接触和协作,共同努力去完成任务挑战,为团体成员深入交流和了解提供机会,有利于团体凝聚力的形成。同时,团体成员会直接地感受和体验到鼓励与支持,帮助与友爱,冲突与矛盾,个人利益与团体利益。最后在治疗师的观察与反馈中,在民主与公平、信任和包容的氛围中,成员能够更加深刻地理清自身与别人的关系,自身与团队的关系,获得心理上的滋养。研究表明,相比传统的团体治疗,野外治疗中的个体似乎更愿意分享自身情感与经历,这可能与成员在野外冒险挑战的共同经历有关,“劫后余生”、“不抛弃,不放弃”的深刻体验能够更容易建立深厚的情感。
3.3 个人独处
个人独处野外治疗活动一个关键的疗效因子。独处活动为个体提供了一个陌生的、新奇的气氛,让他们从一个全新的视角去审视他们的问题,感激现实生活中他们所拥有的一切。
3.4 隐喻
Bacon 认为隐喻技术是野外治疗取得良好的效果的不可获取因素。所谓隐喻是指个体在野外环境中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在很多层面上都象征和代表了他们当前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困境。此时此刻的经历和体验能够自然而然地让个体和他现实的困境产生链接,相比传统的谈话治疗,隐喻技术的运用能够更有效地打开个体的心扉,产生更持久的治疗效果[1]。
4 野外治疗的基本过程
4.1 团体成员招募与甄选阶段
包括野外治疗主题的设定、招募和甄选符合主题的个体。主题的预先设定有利于团体成员的招募,有利于针对性活动的设计和操作,有利于治疗目标的制定和效果的评估。此阶段开展的好坏,将决定整个项目的后续进行。
4.2 个体及团体目标制定阶段
包括对确定个体问题的评估,个体问题的心理学假设,治疗目标和效果评估,以及针对性野外环境与冒险活动的设计。
4.3 准备阶段
个体远离破坏性的生活环境,现代物质文明,实行健康饮食,开展适度运动调整身体状态,学习露营、徒步、登山等野外求生技能,为进一步野外活动和挑战打好基础,Russell称之为清零阶段。
4.4 挑战与治疗阶段
在完成了基本技能的学习和清零准备阶段,团体所有成员在团队共同目标和个人目标的指引下开始野外生存,冒险性活动挑战和个体、及团体心理治疗活动。此阶段是野外治疗的核心阶段。首先大自然和冒险性活动会潜移默化地让个体学会如何自我生存、自我照顾,促进个体的成长。其次野外治疗是一个团队过程,个体不可避免地需要与他人配合,共同协作完成挑战任务。此过程将促进个体学习合适的社会交往技巧,提升社交能力和树立正确的社会责任意识。同时心理治疗师的陪同与观察,及时回馈与心理干预,能够有效地促进个体朝向治疗目标发展。
4.5 维持与回归阶段
野外治疗活动的大强度、高密度、历程长、封闭的特性决定了在治疗结束后需要一个相对稳定的后续维持阶段。从完全的野外环境回归到现实生活本身对于个体来说就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个体在野外治疗过程中的所学、所用、改变和成长如何维持下去,需要家庭、社会和相关专业机构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并开展针对性的辅助治疗[1-9]。
5 结 论
5.1 野外治疗在是欧美国家干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一种可替代方式,颇受青睐,效果较好。
5.2 野外治疗目前仍然缺乏统一权威性的定义,是否发生在野外生存环境和是否有专业心理学资质是区分野外治疗和一般的治疗性野外活动的关键因素。
5.3 野外治疗的理论基础尚不完善,借助其他心理学理论和技术引发了关于野外治疗是否独立区别于其他心理治疗的争议。
5.4 野外治疗的疗效因子和过程和一般心理治疗有类同之处,但也有凸显自身特色的不同之处,且起到重要的疗愈作用。
[1] Ebony A. Rutko.where is the wilderness in wilderness therapy.Journal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2013,36(3):218-232.
[2] Keith C. Russell,Dianne Phillips-Miller.Perspectives on the Wilderness Therapy Process and Its Relation to Outcome.Child & Youth Care Forum,2002,31(6):415-437.
[3] Joanna E. Bettmann,Keith C. Russell.How Substance Abuse Recovery Skills, Readiness to Change and Symptom Reduction Impact Change Processes in Wilderness Therapy Participants.J Child Fam Stud,2013,22:1039-1050.
[4] Clark, J. P., Marmol, L. M., Cooley, R., & Gathercoal, K. The effects of wilderness therapy on the clinical concerns (on Axes I, II, and IV) of troubled adolescents. Journal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2004,27(2):213-232,6.
[5] 谢智谋.冒险治疗[J].国立体育学院学报,2005,16(3):193-204.
[6] Kimbal R.O,Bacon.S.B. The wilderness challenge modal.adventure therapy:therapeutic applications of adventure programming.IA:Kendall-hunt,1993.
[7] Powch.I.Wilderness therapy:what makes empowering for women.Women and therapy,1994,15:11-27.
[8] Davis-Berman.J,Berman,.D. S. Wilderness therapy: Foundations, theory, and research.Dubuque, IA: Kendall/Hunt,1994.
[9] Keith C. Russell.what is wilderness therapy.The journal of experiential education,2001,24(2):70-79.
[10] Crisp, S. Envisioning the birth of a profession: A blueprint of evidence-based ethical, best practice. In S. Bandoroff &S. Newes (Eds.), Coming of age: The evolving field of adventure therapy,2004:209-223
[11] Williams, I. Adventure therapy or therapeutic adventure? In Bandoroff, S., & Newes, S.,Coming of Age:The Evolving Field of Adventure Therapy,2004:195-208.
[12] Scott.Bandoroff,David.G. Scherer.Wilderness Family Therapy: An Innovative Treatment Approach for Problem Youth.Journal of Child and Family Studies,1994,3(2):175-191.
[13] 伽达默尔.真理和方法(上卷)[M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2:79.
[14] Lakoff.G.Johnson.M Why cognitive lin guistics requires embod ied realism,2002(3):245.
[15] 约翰·杜威.明日之学校[M ].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8:69.
[16] 黄衍.体验式教育理论的原理与应用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6.
[17] 库伯.让体验成为学习和发展的源泉[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
[18] 钱永健.拓展训练[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
[19] Daniella.Margalit,Amichai.Ben-Ari.The Effect of Wilderness Therapy on Adolescents Cognitive Autonomy and Self-efficacy: Results of a Non-randomized Trial .Child Youth Care Forum,2014,43:181-194.
[20] 吴建平.基于生态心理学视角下的生态疗法新探索[D].北京:北京林业大学,2011.
Research on the Psychological Intervention Model of Wilderness Therapy
ZHANG Yu
(Wenzhou Medical University, Wenzhou 325035, China)
On the basis of reviewing foreign literature,the article try to introduce wilderness therapy program since 1990’s in Europe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 methods of documentary collection and logic analysis,this paper has discussed the root,definition,theory system,therapeutic factor and process of wilderness therapy.Conclusion:①Without a unified definition is not conducive to the wilderness therapy.②The theory system is imperfect.③Wilderness therapy is effective with its own character.
wilderness therapy; outward bound; experiential education
浙江省2015年度高等教育课堂教学改革项目(kg2015230)
2017-03-20
张 宇(1987-),男,江苏徐州人,讲师,硕士,主要研究户外运动与青少年心理健康,体育健康心理学.
1004-3624(2017)04-0089-06
G804.82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