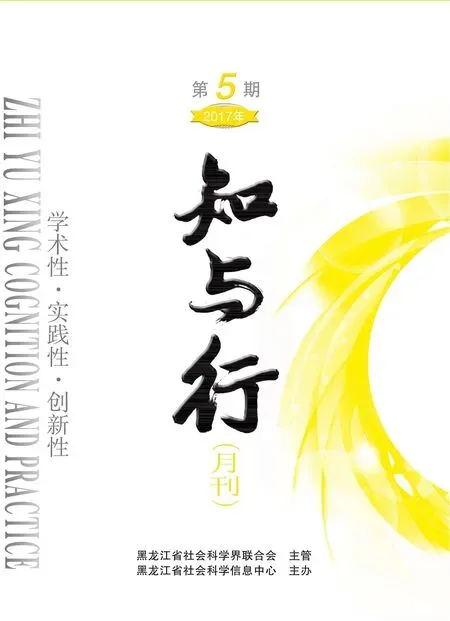改编权相关基础问题研究
——以《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为视角
2017-01-23符诗
符 诗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著作权法》研究专题·
改编权相关基础问题研究
——以《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为视角
符 诗
(苏州大学 王健法学院,江苏 苏州 215000)
网络文学的产业化发展带来了影视作品改编热潮,随之而来的改编权侵权问题此消彼长,冲击着传统的著作权保护制度。就改编权而言,现行《著作权法》只有原则性规定,权利保护和侵权认定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往往难以解决司法实践中遇到的实际问题。《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在第13条第8项中修改了有关改编权的内容,赋予了改编权新的内涵,明确了改编的三种方式,重新界定了改编权与其他权利的关系。改编权与其他权利的主要区别在于其改变或者使用原作品的方式,改编权最大特点就是改编行为的具有独创性,改编会创造出新的作品。送审稿取消了修改权,由改编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覆盖其权能。在改编权的侵权认定方面,首先应当明确“思想与表达二分法”这一前提,然后以三步走来判断被控侵权作品与原作品之间的关系,一是判断被控侵权作品是否侵犯原作品的独创性部分,再判断被控侵权人是否已经接触了原作品,最后来看被控侵权作品是否与原作品构成整体或部分实质性相似,且这种实质性相似是否已达到可能影响著作权人财产利益的程度。
改编权;送审稿;著作权
在现代网络信息技术和数字技术的催化下,网络文学蓬勃发展,随着《三生三世十里桃花》《欢乐颂》《锦绣未央》等影视剧在各地热播,网络文学走上银幕已经成为一种大众潮流。但是,正如蒋胜男诉《芈月传》片方、琼瑶与于正对簿公堂一般,侵犯著作权的案件也屡屡发生。这也凸显了现行《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的滞后性和局限性,因此国家版权局组织了著作权法的第3次修改工作,形成《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以下简称“送审稿”),送审稿对改编权的权利内容实现了重大突破,受到了学界内外的广泛关注。
一、 改编权的法律解读
改编权是著作权人改变原作品,形成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的权利。《送审稿》第13条将改编权定义为“将作品改变成其他体裁和种类的新作品,或者将文字、音乐、戏剧等作品制作成视听作品,以及对计算机程序进行增补、删节,改变指令、语句顺序或者其他变动的权利”。
(一) 改编权的内涵
《著》对改编权只做了基本的原则性规定,即改变原作品,创作新作品的权利。通说认为,文学艺术领域内的改编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后作品在先作品的基础进行创作,先后作品形式不同,如从小说《红楼梦》到连环画《红楼梦》;第二,先后作品形式相同的,但是在改变作品过程中体现出独创性,如从电影剧本《墨子之战》到电影剧本《墨攻》。郑成思教授认为,我国著作权立法中翻译成“改编”二字词不达意,“编”将行为对象限于文字作品上,若“编”用在美术和音乐作品上不甚妥当。而英文的“adaptation”一词,含有“适应”“改编”“改制”的意思;德文的“Bearb Eitung”一词,也有“加工”“耕作”的意思。因而,郑成思教授认为,在著作权领域将该词翻译成“改制”或者“改作”更为合适[1]。
送审稿以具体的内容来定义改编权,确认了改编的三种方式:第一,将原作品改变成其他体裁或种类的新作品;第二,将文学、音乐、戏剧等作品制作成视听作品;第三,对计算机程序进行增补、删节,或改变指令、语句顺序等其他变动。值得注意的是,送审稿首次明确将第二、三种方式引入改编权的范畴。送审稿取消了摄制权,其权能由改编权覆盖,也就是改编的第二种方式。李明德教授曾建议,废除现有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在《著作权法》中增加计算机程序的定义和必要权利限制来填补[2],第三种方式就是专门针对计算机程序的改编,体现了我国著作权立法的进步。
(二) 改编权的法律特征
送审稿将改编权列为著作权中的财产权,改编权是权利人本人或者许可他人,通过改变原作品的种类或者用途等方式,产生独创性新作品的权利。由此可见,改编权具有了以下三个法律特征:
1.改编权是一种专有财产权。著作财产权,是指权利人自己使用或者许可他人使用其作品,并因此获得报酬的权利。尽管各个国家或地区的著作权法或版权法对著作财产权的名称、保护种类、保护期限的规定有所不同,但是各国均将著作财产权纳入法律保护范围内,这点毋庸置疑。举例来说,将金庸的小说《天龙八部》在内地拍成电视剧,或在日本改成漫画书,或在美国做成动画片,都必须经过金庸本人或其继承人的同意并向其支付报酬。
改编权是一项重要的著作财产权,著作权人对其作品享有全面支配权,著作权人以外的人对原作品进行改编,必须取得原著作权人的同意,并向其支付报酬,否则就是侵犯著作权。实践中存在这样一种情况,即先擅自改编他人作品后,再向著作权人说明并支付报酬,这实质上侵犯了著作权人的改编权,只有经过原著作权人的追认,才可以免除侵权责任。
2. 改编权是一种演绎权。演绎权,是指著作权人本人或者许可他人对其作品进行改编、翻译、注释、整理、汇编和摄制等活动的权利。演绎权包括摄制权、改编权、翻译权、汇编权等四项权利[3]。通过上述演绎活动而产生的新作品为演绎作品,该作品从原作品中派生出来,但并未改变原作品的基本内容和创作思想[4]。
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专家建议稿”认为,使用复制权、发行权、演绎权、传播权、展览权和出租权六个概念,就可以容纳现行著作权法中的经济权利[2]19-25,但送审稿并未采纳,也未使用“演绎权”这一概念。演绎权可以分为改编权和翻译权两类,而改编权又可以分为一般改编权和制片权。我国著作权立法一直以来都与《伯尔尼公约》保持一致,将翻译权和改编权分别列出。制片权在《著》中称为摄制权,送审稿中改编权包含了将文字、音乐、戏剧等作品制作成视听作品的权利,取消了摄制权,由改编权覆盖摄制权的权能。而《伯尔尼公约》中,翻译权、改编权、制片权均分别列出。
3. 改编权控制派生新作品的改编行为。改编是通过改变原作品的体裁、种类或用途等,形成独创性的新作品的过程。改编是改编者自身创造性劳动的过程,“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是改编者的劳动成果。
改编是改编者的再创作,是对原作的一种利用。笔者认为,改编者的再创作要满足以下两个条件:第一,改编应当以现有作品为蓝本,即忠于原著;第二,改编应当形成新的创造性作品,即具有独创性。改编是忠实性与独创性既统一又矛盾,因此,改编应当允许对原著进行符合影视艺术要求的改动和加工,赋予改编者进行创作的一定“自由度”,允许改编者将原作品的情节等作为素材,对原作品内容和形式进行充分挖掘、调整。当然,这个“度”则是认定改编权侵权的重要依据,如在王庸诉朱正本等著作权侵权案中,《十送红军》和《送同志哥上北京》均由民歌《长歌》改编而来,两者都是再创作的作品,《十送红军》借鉴了《送同志哥上北京》的部分曲谱,但尚未达到一个完整乐句,这个借鉴的“度”未达到整体或部分实质性相似,因此,《十送红军》不构成侵权。
(三) 改编权的立法模式
关于改编权的立法,国际社会主要采取两种模式。一种是法国模式,即由复制权涵盖改编权的权能。《法国知识产权法典》第122条规定:“属于作者的使用权包括表演权和复制权”,“未经作者或其权利所有人或权利继受人的同意,进行全部或者部分的表演或者复制均属非法。通过任何技术和手段的翻译、改编、改动、整理或者复制亦均属非法”。另一种模式为英国、德国及日本等国所采用,即作者享有独立的改编权。如《德国著作权法》第3条规定:“作为演绎者个人智力创作的对作品的翻译及其他演绎,不管被演绎作品的著作权而如同独立的作品受到保护。”《日本著作权法》也有类似的规定。《伯尔尼公约》也采用第二种模式,明确授予了著作权人改编权,第12条规定:“文学艺术作品的作者享有授权对其作品进行改编(adaptions)、安排(arrangement)和其他变动(alterations)的专有权利。”我国自著作权立法以来,一直采用第二种模式,送审稿也延续此种模式,赋予作者独立的改编权。
(四) 我国改编权的发展
互联网的力量打开了影视剧的新世界,网络文学“后来者居上”,引起一阵阵追剧热潮,网络文学改编影视作品逐渐成为一种趋势,对改编权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著》自1991年6月1日起施行以来,至今已有二十五年,曾在2001年和2010年进行过两次修改,但是限于法律的滞后性和被动性,始终无法赶超日新月异的社会大潮。
《著》对改编权的原则性规定比较抽象,并没有明确地表述出改编权的内涵,即改变什么作品、从哪些方面改变作品、如何改变作品三个方面的问题,只是强调了改编的结果是“具有独创性新作品”。自2012年起,国家版权局开始进行对著作权法的第3次修改工作,此次修订共形成3个草案,值得注意的是,草案中关于“改编权”这一内容差异较大。修改草案第一稿第11条和第10项规定,改编权是指将作品改变为除视听作品外其他种类的新作品的权利;修改草案第二稿第11条和第8项中,增加了对计算机程序的改变,一定程度上涵盖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内容;修订草案送审稿第13条第8项中,又增加了将文字、音乐、戏剧等作品制作成视听作品,至此,改编权覆盖了摄制权的权能。总地来说,送审稿明确了改编权的外延和内涵,看似扩展了改编权的内容,实则限缩的改编的方式和种类。
二、 改编权与其他权利
由于《著》的权利内容界定模糊,各项权利之间存在交叉,司法实践中常常对改编权、修改权、复制权、汇编权等难以理清,各地法院对相关案件的处理结果千差万别,导致社会各界议论纷纷。
(一) 改编权与修改权
修改权,即著作权人自己修改或授权他人修改其作品的权利。狭义上来说,修改权与保护作品完整权代表了同一权利的两个方面,两者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从正面来讲,作者有权修改自己的作品;从反面上来讲,作者有权禁止他人修改自己的作品。郑成思教授认为,广义上的修改权还包含了“收回权”的内容,即以修改为目的将已经发行和流通的自己的作品收回的权利[5]。修改权的修改,是指不改变原作品基本内容,增删作品的部分内容,或对作品的错漏部分进行必要的更正和补充。修改权是著作权人享有的人身权利,未经权利人同意,任何人不得修改其作品,除报社、期刊社可以对作品进行必要的文字性修改。
改编权和修改权都是著作权的重要权利内容,但是二者存在着明显的差别,笔者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分析:(1)权利的性质不同。改编权属于著作财产权,改编是对作品进行实质性的、全局性的改变,体现改编者一定的独创性,保护作者的财产利益;修改权属于著作人身权,修改是对作品进行表面性的、局部性的改变,体现修改者运用了一定的技术手段,但不具有创造性,保护作者的精神利益。(2)权利的保护期限不同。根据《著》的规定,改编权的保护期有时间限制,修改权没有保护期的时间限制问题。(3)权利行使的法律效果不同。改编权的行使会产生新作品,出现新的著作权人;修改权的行使修改权并不产生新作品,修改后的作品仍属于原著作权人[6]。一言以蔽之,改编之后形成一部具有独创性的新作品,修改之后还是原作品。(4)表现形式不同。改编是对于原作品种类和体裁的改变或者对计算机程序的变动,即主要改变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而修改权是对实质内容的变更,不会影响作品的外在表现形式。
送审稿取消了修改权,修改权的权能由改编权和保护作品完整权覆盖。回想2011年腾讯公司诉“彩虹显”软件侵权案,法院认为彩虹显通过增减腾讯QQ程序指令及原有函数等,改变了QQ的计算机程序,因此判定虹连和我要公司侵犯腾讯公司的修改权。现在看来,依据送审稿腾讯公司诉“彩虹显”软件侵权一案应当认定为侵犯了著作权人的改编权。
(二) 改编权与复制权
复制权是著作财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复制行为的理解可以分为狭义上的复制和广义上的复制。狭义上的复制,是指将原件制作成一份或多份复制件,制作过程没有智力贡献的行为。这一意义上的复制不会产生新的作品,只产生多份单纯的等同的复制件。送审稿重申了对复制权的定义,我国仍采用狭义上的复制权概念。广义上的复制,是指一切将原件制成一份或多份复件的行为,这不仅包括上述的狭义上的复制,还包括在制作过程有独创性智力贡献的行为,这种抽象的复制权涵盖了翻译权、改编权等权能。对此,郑成思教授认为,可以把复制权解释为对所有原作品的“再现”,除原封不动的复制外,以改编、汇编、翻译等方式进行的再现,也是改变了原作品外在表现方式的一种“再现”,这种“再现”增加了再创作的成果,但并未离开原作品的“基本构成”[1]181。比如,《伯尔尼公约》第9条(1)规定,复制权是指作者享有授权以任何方式或者形式复制该作品的专有权。《德国著作权法》也采用这一观点,将复制权定义为制作作品复制件的权利,而不管是否是临时或长久的,以何种方法及数量多少。
改编权与复制权的区别主要在于调整对象的不同,即改编行为和复制行为的区别,而改编行为和复制行为的区别在于对原作品的使用是否具有一定的独创性。改编权所控制的行为是利用原作品,形成另一种独创性的新表达的行为;复制权所控制的行为包括两种:一种是原封不动地使用行为,另一种是对作品进行非实质性改动的使用行为[7]。有的学者提出,若后作品使用与原作品相同的最终呈现形式,则属于复制权的控制范围。例如临摹,无论何种方式的再现,无论创作者的技艺或能力,它均未脱离原作的具体表达,仍属于复制[3]140-157。简言之,改编行为体现独创性,而复制行为不体现独创性。
对此,笔者以薛华克与燕娅娅等侵害改编权纠纷案为例进行分析,在该案中,判断被告的油画《阿妈与达娃》侵犯原告的摄影作品《次仁卓玛》的复制权还是改编权,关键在于是否承认涉案油画本身的独创性。首先,由摄影作品到油画,是一种人工化的活动,而复制需要借助一定的设备被动地再现现有作品,因此被告的涉案行为与著作权法的复制存在区别。其次,被告以油画的方式再现摄影作品的画面形象,需要进行构思和安排,呈现出一种不同于摄影的艺术效果,这不是原搬照抄,而是对原有的摄影作品的再创作,我们应当肯定燕娅娅在绘图过程中进行的创造性劳动。对原作品的再创作,改变了原作品的表现形式,这属于改编权控制的行为,被告未经著作权人许可,也未支付报酬,故侵犯了原著作权人的改编权。
(三) 改编权与汇编权
汇编权,是指权利人经过选择或者编排,将作品或其片段汇集成新作品的权利。汇编过程具有一定的创造性,是演绎权的一种,著作权人享有汇编权,他人未经许可,不得将其作品或其片段汇集成新作品。改编权与汇编权有以下异同点:
(1) 二者都是一种著作财产权;
(2) 二者都是在现有作品的基础上,通过后来的他人创造性过程,产生新作品;
(3) 改编者或汇编者对新产生的改编作品或汇编作品享有著作权;
(4) 二者改变作品的方式存在着巨大的差异。汇编是将他人的作品经选择或编排后汇集成册,改编是改变作品的种类、用途、体裁等。
在大多数情况下,对现有的作品进行汇编是一种复制行为,著作权人可以行使复制权来禁止他人对其作品的汇编行为,汇编权是否有必要与复制权分别规定一直都是学界的争议点。在力美健公司诉艾尚力健中心侵权案中,法院认为艾尚力健中心未对其宣传手册中使用的涉案图片进行选择或编排,不构成汇编权侵权,但对侵害涉案图片的复制权、发行权的事实予以确认。可见,在司法实践中,将是否对内容进行选择或者编排作为判断汇编权和复制权的依据,送审稿不再严格区分这两项权利,取消了汇编权,其权能主要由复制权来代替。
三、 改编权的侵权认定
著作权是特殊的民事权利,相应地,著作权侵权也同样具有特殊性。基于改编权对“独创性”的严格要求,笔者认为,改编权侵权认定应该坚持“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在首先考虑独创性的基础上,再以“接触+实质性相似”的标准来衡量,具体来说分为三个方面:第一,判断被控侵权作品是否侵犯原作品的独创性部分;第二,判断侵权人是否已经接触了原作品;第三,判断被控侵权作品是否与原作品构成整体或部分实质性相似,且这种实质性相似是否已达到可能影响著作权人财产利益的程度。
(一) “独创性”的判断标准
送审稿将“作品”定义为,文学艺术和科学领域内具有独创性的智力表达。所谓“独创性”,是指作品的完成取决于作者个人的选择、编排、设计,该作品既不是对现有形式的复制,也不是对现有程序的推导,而是集中体现了作者创造性的智力劳动成果[8]。对于“独创性”的理解,笔者认为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独”是指著作权人独立创作、源于本人,即作品是由作者本人独立创作完成的,而不是抄袭、剽窃、挪用的结果。“创”要求达到一定的智力创造高度,但并不要求是首创,也不意味着要具备某种高度的文学艺术价值。实际上,“接触+实质性相似”判断标准正是来源于“独创性”的两个部分,“接触”考察的是“独”的问题,“实质性相似”考察的是“创”的问题。
在文学艺术领域,“借鉴”是一种常见现象,但是“借鉴”达到何种程度会构成侵权长期以来一直困惑大众。对此,送审稿认为,著作权保护只延及表达、不涉及思想,所以作品的思想可以借鉴使用,但是独创性的表达不可使用,这也就是“思想表达两分法”。著作权法所要保护的表达,不仅包括文字、图形、音乐等,在某些特定情况下作品的内容、情节甚至人物关系也属于作品的表达。就同一主题创作的作品,只要该作品是作者独立创作完成且具有独创性的表达,应当具有独立的著作权。
司法实践中,一般由被告承担证明被控侵权作品独创性的举证责任,即若被告无法证明涉案作品中的独创性组成部分,则推定该作品不具有独创性。在薛华克与燕娅娅等侵害改编权纠纷案中,法院首先认定被告的油画《阿妈与达娃》借鉴了原告的摄影作品《次仁卓玛》,然后认定被告改编权侵权的关键在于判断被告是否使用了摄影作品的独创性表达。对于摄影作品而言,其独创性在于摄影者通过选择拍摄对象、拍摄角度、拍摄技巧等所呈现的画面形象,经对比法院最后认定两涉案作品的画面形象基本相同,表明被告使用了原告作品中的独创性表达,侵犯了原告的改编权。双方当事人的另一案件中,法院认为摄影作品《窗边的塔吉克女孩》和油画《左拉》所表现的人物以及表现人物时所选择的角度均属于创作题材或思想的范畴,作品所呈现的画面形象才属于作品的表达。经对比法院最后认定两涉案作品的画面形象存在一定的相似,但表达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属于不同作者就同一题材创作的作品,肯定了被告作品中的独创性表达,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
(二) “接触”的判断标准
所谓“接触”,是指先作品公之于众,或者因其他理由而使他人有机会获得该作品。通说认为,接触是著作权侵权不可或缺的构成要件。接触主要可分为两种方式:第一种是作品已发表,任何人都可以获得该作品;第二种是作品未发表,但权利人有证据证明被控侵权人已实际接触了该作品。笔者所指的接触包含直接触碰、感知或阅读,甚至是在正常理性人的理解下,侵权人存在获取已有作品的“合理可能性”时,就可以推定构成接触。
在改编权侵权案件中,由原告提交直接证据证明被告的实际接触行为,也可以列举间接证据来证明被告存在接触的“合理可能性”。也就是说,原告需要承担涉案作品是否构成接触的举证责任。如在琼瑶诉于正改编权侵权一案中,电视剧《梅花烙》的播出即意味着剧本《梅花烙》的公开,并不需要原作者专门公开发表该剧本,任何人都可以获知该剧本的内容,故推定被告的后作品《宫锁连城》有接触原告先作品的可能,达到了改编权侵权的接触要件。有些特殊情况下,当后作品与先作品具有相同或类似的错误,这种错误在正常理性人看来又难以用巧合来解释,那么就可以推定侵权人构成接触的“合理可能性”。
(三) “实质性相似”的判断标准
如果原告能够证明被告满足直接接触或接触“合理可能性”的条件,那么下一步就需要证明涉案作品的独创性部分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所谓“实质性相似”,是指后作品与先作品在表达上含有实质性的相同或相似,使受众对于前后两作品产生相似性感知及欣赏体验。
关于判断涉案作品是否构成“实质性相似”的问题,司法实践中最常用的是美国的“一般读者(听众、观众)测试法(Ordinary Audience or Average Audience or Lay Observer)”,即指一般的非专业的评判者认识到被告的作品抄袭了原告的版权作品。可见,实质性相似以一般大众为切入点,把一般大众的经验和直观感受作为依据,将涉案作品分别作为不可分割的整体来评判,以此来推测涉案作品的相似程度。当然,这种“一般读者(听众、观众)测试法”也存在缺陷,前提必须是已经证明后作品对前作品有直接接触或接触的“合理可能性”,否则不得适用这种判断标准。当前提不具备时,便需要后作品与前作品在独创性表达部分达到“惊人相似”时,才可以认定该作品侵权。另外,“实质性相似”仅针对作品的独创性部分,若被告有证据证明该部分是公知素材或者源于第三方作品的,则不构成实质性相似。
判定“实质性相似”的方法,可以分为部分比较法和整体比较法两种,二者的区别在于:部分比较法在检验实质性相似之前先排除了作品中不受著作权保护的内容,再将涉案作品进行对比,这样可能导致作者对作品中通用元素所做的独创性“表达”也一并排除在著作权保护之外。事实上,对于某些素材来说,如果采取部分比较法难以得到准确的结论,如果采取整体比较法,就会发现某些情节、场景、语句等的相同或近似是整体抄袭的结果。在王庸诉朱正本等侵权案中,两审法院均认可被告作品《十送红军》与原告作品《送同志哥上北京》有4个小节的曲子相同,且均认定被告未侵犯原告的改编权,但裁判理由不同。一审法院采取分段分句比对和综合比对相结合的方法,认为在风格、曲调变化、情感基调、词曲结合等方面,两作品均以民歌《长歌》为蓝本进行改编,《十送红军》对《送同志哥上北京》是合法借鉴,不构成改编权侵权。二审法院采用分段分句比对和歌谱单独比对的方法,认定原告实际接触过被告作品,但因两作品中相同的4个小节并没有形成连续的完整乐句,未达到实质性相似,故维持了一审法院判决。
四、结语
送审稿第13条关于改编权的最新规定,包含了改编权的内容和方式,覆盖了《著》中摄制权和《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的部分内容,有利于区分改编权与修改权、复制权、汇编权,理清司法实践中的各种法律关系。由于著作权只保护独创性的表达,笔者认为,改编权侵权认定应该优先认定作品“独创性”的基础上,以“接触+实质性相似”为判断标准。毋庸置疑的是,送审稿许多方面仍然存在较大争议,需要学界进一步讨论、完善,以期立法者尽早规范改编权法律保护制度。
[1] 郑成思.版权法[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211.
[2] 李明德.我国《著作权法》的第三次修改与建议[J].知识产权,2012,(5):19-25.
[3] 梁志文.论演绎权的保护范围[J].中国法学,2015,(5):140-157.
[4] 吴汉东,等.知识产权基本问题研究(第二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110.
[5] 郑成思.知识产权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319-320.
[6] 吴伟光.著作权法研究——国际条约、中国立法与司法实践[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244.
[7] 苏志甫.参照他人摄影作品绘制油画行为的司法认定[J].中国版权,2012,(6):32-46.
[8] 孙海龙,姚建军.知识产权审判研究[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2008:149-150.
〔责任编辑:张 毫〕
2017-03-16
符诗(1993-),女,江苏常州人,硕士研究生,从事知识产权法研究。
D90
A
1000-8284(2017)05-0056-06
依法治国研究 符诗.改编权相关基础问题研究——以《著作权法(修订草案送审稿)》为视角[J].知与行,2017,(5):56-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