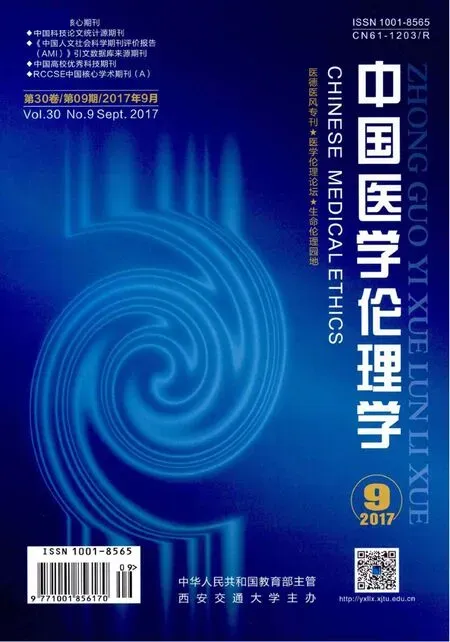“生命尊严”系列讨论之二:生殖性克隆是否冒犯人的尊严
2017-01-20张新庆杨同卫韩跃红詹心怡
张新庆,杨同卫,韩跃红,贺 苗,詹心怡
(1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北京 100730,zxqclx@qq.com;2山东大学医学心理学与伦理学系,山东 济南 250012;3昆明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4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5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生命尊严”系列讨论之二:生殖性克隆是否冒犯人的尊严
张新庆1,杨同卫2,韩跃红3,贺 苗4,詹心怡5
(1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学院,北京 100730,zxqclx@qq.com;2山东大学医学心理学与伦理学系,山东 济南 250012;3昆明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云南 昆明 650504;4哈尔滨医科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黑龙江 哈尔滨 150081;5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北京 100872)
在上期的生命尊严讨论中[1],我们围绕“人的尊严”的含义、适用范围、尊严与权利关系展开探讨,从多角度解释了尊严的丰富内涵、类型和表现。本期开始将从克隆人、终末期病人、代孕者等特定人群,试图渐进地揭开“生命尊严”的神秘面纱。
1 问题的引出
张新庆:克隆技术是指生物体通过体细胞进行的无性繁殖,分为治疗性克隆与生殖性克隆(俗称克隆人)两种。当1997年克隆羊“多利”降生后,国际社会开始热烈讨论是否该克隆人类自身,最终达成一致意见:禁止克隆人。宗教人士普遍认为,克隆人在不恰当地扮演上帝,这是在亵渎生命的尊严;有些法学家称,克隆人可定为“反人类罪”;伦理学家反对克隆人理由主要有两条:对克隆人的身心伤害以及使之尊严受损。回顾世纪之交那场关于克隆人的伦理争论,“冒犯了人的尊严”是反对克隆人的最有力的论证之一,但也有不少重量级的生命伦理学家(如Ruth Macklin和 John Harris)明确质疑尊严与克隆人的相关性,甚至主张应该在克隆人伦理讨论中排除尊严论证。
在克隆羊“多利”降生的十年间,有关克隆人的伦理备受关注。论证与反论证,此起彼伏;赞同或反对,各执一词。20年过去了,克隆人没有降生,关于克隆人的社会、伦理和法律讨论也似乎在一致反对声中渐渐平息。不过,学界还是有必要掀起这个似乎已经尘埃落定的“老话题”,至少“克隆人的伦理讨论与尊严是否相关”这一问题尚未得到有效解决。此外,即便那些主张“克隆人冒犯了人的尊严”的学者的道德立场、论证也不尽相同。
韩跃红:关于克隆人的尊严问题,延绵20年依然有人继续追问,说明确实没有在理论上得到有效解决。2002年,我在《中国应用伦理学》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从尊重生命原则看生殖性克隆》的文章。文章指出,国际社会反对克隆人的理由有很多,但其中唯一不可辩驳的理由就是生殖性克隆试验因为存在诸多安全问题而有损克隆婴儿的生命尊严。这一判断已经蕴含着人的尊严首先是人的生命尊严的理论认识。正如您所说,首要的理论问题就是:克隆人伦理讨论是否与尊严概念无关?如果说Harris和Machlin等人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就没有必要在此专门讨论克隆人之尊严问题了。如果说克隆人确实冒犯了人的尊严,由此延伸出来的问题就是:克隆人是否具有独立的人格?克隆人是否仅仅被当作一种手段?克隆人是否冒犯了人的自主权?父母是孩子尊严的赋予者吗?
杨同卫:“生殖性克隆是否冒犯了人的尊严?”这一问题分为递进的两个子问题:①克隆人是否应该享有和普通人一样的尊严?②基于其独特的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克隆人能否享有和普通人一样的尊严?上述问题实质上也无外乎这样几个老生常谈的问题:①克隆生殖方式是否确有必要?②生殖性克隆能否无损生命质量?③克隆人能否被社会所接纳?
2 克隆人语境下“尊严”的含义
贺苗:克隆人有尊严吗?作为讨论的前提和起点,我们应该明确“克隆人”这一概念。克隆(cloning),即无性繁殖,而克隆人应理解为通过无性生殖方式出生的人。既然作为人来界定,克隆人就不是实验室里生长出来的科学怪物,而应视为多元文化价值体系中的社会成员,也应有其后天成长发育的环境,并受其所在的家庭、社会与文化的诸多影响。
詹心怡:是的,讨论“人类克隆与人类尊严”时,我们有必要首先回答“何为克隆”“何为尊严”等基本问题。
尽管美国总统生命伦理学咨询委员会的报告费了很大工夫对各种概念进行定义与细化,却始终没有对“尊严”这一概念进行进一步的说明。James F. Childress虽说没有像Macklin一样直接否定“尊严”这一概念存在的意义,但也对其适用性提出了质疑:“尊严”仅仅作为一种“直觉性的正确”。
我虽然承认,在克隆人语境下的“尊严”概念具有模糊性、多义性与直觉性,却不认为这些特性会减损尊严的适用性。在G.E. Moore的元伦理学中,“善”同样是一个不可定义的单一概念。正是由于“善”的不可分割为其他概念、不可被其他概念定义,它才能作为一个无可替代的出发点。在生命伦理学中,“尊严”的地位恰如“善”在伦理学中的地位一样重要。如果执着于用“独特性”“知情同意”“不伤害”等原则机械地界定“尊严”,恐怕同样陷入了“自然主义的谬误”。如果伦理学存在的合法性建立在对道德相对主义的否定上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承认的确存在某些基础性的“道德共识”。这些共识让“直觉性的正确”不是在各说各话。因而,“尊严”这一概念并不会如同Childress所担心的那样,对尊严合法性、适用性构成威胁。
张新庆:借助“善”与“尊严”之间的类比推理,合理地得出“尊严”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基本伦理学概念。这是一种与Childress和Macklin等知名生命伦理学家意见相左的学术观点。人们对“尊严”所包含的多重含义有较为广泛的共识,也对那些冒犯人的尊严的行径有较为一致的认知。本次探索与争鸣的主题是“克隆人”的尊严,一种指向未来人类社会新型人际关系背景下的尊严问题讨论。为了大家讨论的话题更加集中和有的放矢,我们首先对“克隆人的人格独特性及其限制”进行讨论。
3 克隆人的人格独特性及其限制
贺苗:我倾向于下列看法:只要克隆人作为人而存在,自然要赋予其做人的价值与尊严。从人的本质而言,人是生物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每个人都具有人格的独立性、完整性和唯一性。因而,严格来说,人是不可能被复制的,否则就破坏了人格的唯一性,也丧失了人存在的尊严。
克隆人真的破坏了人格的唯一性吗?从生物属性来讲,通过克隆技术出生的婴儿与其父亲或母亲的遗传基因及其表达形态并非完全绝对一致,这在遗传学理论中已得到证实。而且克隆技术产生的胎儿不仅在年龄上与基因提供者存在巨大差异,而且后天生长的环境也不可能完全相同。
马克思说,在现实意义上,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从社会属性来看,人只有在人与人之间的现实交往中才能逐渐确立起人格的独立性和唯一性。不同的家庭、社会环境,不同的教育程度与社会文化熏陶都会对人的性格、智力与精神状态产生不同的影响。即使是基因存在一致性的克隆人也会在各自不同的社会文化中形成自己独特的心理、性格及文化品位。既然每一个生命个体的存在都是唯一的,不可替代的,那么他就享有生命的尊严,克隆人自然也不能例外。克隆人作为一个独特的生命体,不仅与有性生殖的普通人不同,而且也有别于与他基因存在一致性的父亲或母亲。他必然会在属于他自己的行为交往模式和社会生活经验中镌刻下自己的独特的生命烙印。因此,我们不能抹杀克隆人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格独特性,克隆人也应享有人之为人的尊严。
詹心怡:我认同贺苗老师所言的克隆人具有人格独特性,因而应和普通人一样享有尊严。但“应当”享有尊严是远远不够的。论证得出克隆人应当享有尊严,并不意味着我们就此不必担心克隆人的尊严受损。尊严固然是人之为人所固有的内在价值,但在现实社会中,尊严感的满足需要同时考虑自尊与他尊。除了需要考虑克隆技术本身是否会损害克隆人的人格独特性,还需要考虑社会中大多数人对克隆人的认可度。即便伦理学家成功论证了克隆人先天具有内在的尊严,但如果在现实社会,克隆人的内在价值得不到大多数人的认可,克隆人的基本权利得不到保障,克隆人仍会受到各种各样的歧视甚至压迫——那么,所谓克隆人的“尊严”,不过是一纸空文。
韩跃红:我始终不太赞同把人的独特性、唯一性看作是一个人享有尊严的根据的观点。在我看来,一个人享有尊严不在于他与众不同,而恰恰在于他与众相同。克隆人也与众相同,他拥有人类基因组,也将生活在我们的世界,他就理所应当地享有人之为人的生命尊严和人格尊严。以人的尊严为价值基础的人权保障就理所当然地要覆盖克隆人。在克隆动物都不能保障其健康的技术背景下,贸然开展生殖性克隆试验,实质上是将一个人类个体当作了没有达到安全标准的非法试验的操作对象,伦理上完全不能接受。如果技术成熟到安全有效后还有什么理由反对克隆人?我们可以反问:什么情况下能够判断“技术成熟”?如何鉴定生殖性克隆的“安全有效”?靠几个动物实验可以下这个结论吗?况且,目前来看,克隆动物的前景并不乐观,克隆狂人也似乎销声匿迹了。
张新庆:贺苗教授从人的社会属性的立场出发,来论述克隆人的人格唯一性是合理的。经验事实也告诉我们,即便是同性别的双胞胎,也会因自身身心健康状况、智力和情商水平、工作和生活环境、社会人际交往等方面的差异而在为人处世、态度和行为等方面表现出巨大的差异。为此,我不否认在社会生活层面,克隆人享有与我们完全一致的尊严。贺苗刚才谈道:“克隆技术出生的婴儿与其父亲或母亲的遗传基因及其表达形态并非完全绝对一致”,换句话说,克隆人基本上是复制了父母一方的遗传基因和表达形态,在生物属性方面抹杀了代际遗传基因的多元性和独立性。另外,来自同一父本的遗传基因的克隆人之间至少在生物属性上是可以相互取代的。这是否意味着,站在生物属性的视角,克隆人的尊严是否受到削弱呢?
贺苗:即使是从生物属性来看,克隆人技术也不可能像洗照片那样完全复制。遗传基因是一个相互制约、相互联系的复杂工程,还存在着基因突变和表达形态的差异。克隆人无论是其在母体子宫的内环境,还是他长大以后生活的外环境,都会导致他在生物属性与其同一遗传基因的亲本存在差异。只要存在差异,无论大小就相互取代。不过,我们既然强调人的自由、价值与尊严,更多还是从作为人的社会属性来看待而非生物属性。
韩跃红:上述以相同性而不是独特性来鉴定某些个体是否享有生命尊严的办法,貌似简单,却是以人类大家庭有可能就“生命至上”达成价值共识为依据。我们欣喜地看到,生殖性克隆试验的道德禁令和法律禁令有效发挥了作用,表明生命尊严作为人类的价值共识具有强大力量,也说明通过鉴定与人相同,进而通过人权保护来保障克隆婴儿不遭到伤害是可行的。反之,把是否具有生物唯一性和人格独立性作为个体有无生命尊严的考量标准既无必要,也会遇到麻烦。当某天一个在生物遗传性上无异于另一个人时,难道他就变成复制品而丧失尊严了吗?显然这是一个荒唐的结论。要让生命尊严成为保护所有人的价值基础,就不能人为地对生命尊严规定过多的标准。只要一个个体拥有人类基因组且生活在世界上,就足以享有人的生命尊严,就应受到道德关怀和法律保护。
4 克隆人自身的尊严
张新庆:显然,如果真有“克隆人”的话,那他或她也只是在生殖方式上与“我们”不同而已。克隆人自身是无辜的,当然应当得到尊严,不应该受到“我们”的歧视、凌辱、排斥。这一点似乎很有说服力。如果这个结论成立的话,人类社会就不应该从“尊严”的视角反对克隆人了。但是,问题似乎没有那么简单。
按照贺苗教授的论证,只要生殖性克隆技术成熟,又有恰当的医学理由,甚至非医学理由(同性恋婚姻家庭对自己子女的需要),加之也不必担心克隆人的尊严受损,人类社会就没有理由阻止克隆人的降生了。这种带有效用论色彩的论证会遭到有力的反驳。如果真正做到技术成熟到不伤害克隆婴儿的地步,就需要先开展克隆人临床试验。而一旦开展了此类研究项目,有些克隆人就难免受伤害。那么,这样的克隆人试验存在可接受的风险受益比吗?人类社会应该允许此类医学目的不甚明确的人体试验吗?20世纪70年代的试管婴儿技术也面临类似的伦理难题,但最终没有阻止技术进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解决了困扰千百万家庭的不孕不育问题。然而,我感到,生殖性克隆因医学目的不明确而没有试管婴儿技术幸运。
贺苗:我的观点是,克隆人应有作为人的尊严,但目前的克隆人技术发展并不成熟,仍存在很多人类无法预估和判断的风险,很可能会给人类造成不可挽回的伤害甚至是灾难。同时,现在也并不能确保人的尊严不受贬损,尤其是将他们视为无生命、无感情的特殊工具,去做一些非常危险的人类无法完成的工作。这是非常可怕的。所以我还不是效用论者,更倾向于人是目的的人道主义者。人体实验需要进行风险受益评估。我想还是会存在人类可接受的风险受益比的,既然人们可支持胚胎干细胞研究和治疗性克隆,生殖性克隆也能找到合理的风险受益比。比如用冷冻的无人认领的或者将要废弃的胚胎作研究,也可沿用国际通行的14天法则。生殖性克隆的医学目的的确不像试管婴儿技术那么明确,但它也算是一种特殊的生育方式吧,可以满足个体的自我延续的需求。不过,这些目的还不足以支撑技术的开展与应用。即使技术成熟,也必须有严格的监管和规范,以及社会的接受度与宽容度。所以,目前,禁止克隆人技术的研究与应用是有道理的。至于何时能开启这扇神秘之门,还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韩跃红:克隆人为什么享有人的尊严?不是因为他在人格上独一无二,而是因为他和自然生殖的人一样,也是一个承载着最高价值的人类生命个体。克隆人的尊严首先是其生命尊严。我们严禁克隆人,首先不是因为担心这种技术破坏了某个人的唯一性,而是明摆着在现有技术条件下任何克隆人试验都将构成对克隆婴儿的人身伤害,都不可避免地侵犯了他的生命尊严和生命健康权。至于等到技术成熟以后等等假设,根本没有科学根据和实验可行性。若真有这一天到来,那时我们再进行伦理讨论也为时不晚。但目前,联合国以及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克隆人禁令是有充分道德理由的。对这一道德理由的解读,无须牵强地借助独特性、唯一性等虚设的尊严标准,而是直接诉诸人的生命尊严以及在此基础上建立的人权保障就足够充分了。
詹心怡:我认为,韩跃红老师的“一个人享有尊严恰恰在于他与众相同”这一主张,其实与以“独特性”作为尊严衡量尺度之一的主张并无冲突。为什么我们在论证“克隆人应享有尊严”时要考察其“独特性”?这恰是因为社会中每一个享有尊严的人,都具有自己的“独特性”,都不是另一个人的复制品。对“独特性”的诉求,恰是一种对“与众相同”的诉求。即,如果克隆人具有与众相同的“与众不同”,那么他们应当具有与其他人相同的尊严。
杨同卫:韩跃红教授提出了三个观点:①不太赞同把人的独特性、唯一性看作是一个人享有尊严的根据。②把人的尊严归结为人的理性、人格独特性、自主性、思想自由等精神品质的观点都是片面的。③克隆人为什么享有人的尊严?不是因为他在人格上独一无二,而是因为他和自然生殖的人一样,也是一个承载着最高价值的人类生命个体。
我认为,所谓人的尊严,无非是指人的优越性、人的尊贵与人的威严。某个人之所以优越,之所以尊贵有威严,一方面是因为他具有人类之所以尊贵的共同本质——理性与美德,另一方面是因为他的独特性,他不能被别人所完全替代,他有不同于其他人的特质——能力、身份、情感与气质等。因此,我赞同把人的独特性、唯一性看作一个人享有尊严的根据之一。当然,这种独特性与唯一性不一定非得是基因组或者是遗传物质上的独特性与唯一性,只要是年龄、表现型、情感气质等生物学意义甚至是社会学上的独特性与唯一性就足够了。我也认为不能把人的尊严归结为人的理性、人格独特性、自主性、思想自由等。但是,人的理性、人格独特性、自主性、思想自由等都是人的尊严的体现,人的理性、人格独特性、自主性、思想自由等等分别在不同角度表征了人的尊严。
克隆人为什么享有人的尊严?一方面他和自然生殖的人一样,是承载着最高价值的人类生命个体——这正如韩跃红教授所言;另一方面他具有不同于其他人的独特性,并在事实上展现不同于其他人、不能被其他人所替代的独特性——这虽未被韩跃红教授认可,但也是客观的、不应被抹掉的克隆人拥有尊严的重要根据之一。
5 结束语
韩跃红:由克隆争论所带出的尊严问题发人深省。究竟什么是人的尊严?人为何享有尊严?如何捍卫人的尊严?国内外对这些理论问题争论不休。我会在即将出版的一本书里对这些问题作出尽可能逻辑一致且可以被应用于指导实践的回答。在这里,可以和大家作一些分享:“人的尊严”是对人的价值地位和道德地位富有感情色彩的表达,它内在包涵了人的生命尊严和人格尊严两个方面。也就是说,人在物质生命和精神生命两个方面都享有无与伦比的价值地位和道德地位。那种把人的尊严归结为人的理性、人格独特性、自主性、思想自由等精神品质的观点都是片面的。把生命尊严从“人的尊严”概念内涵里逐出,是理性主义尊严观的痼疾,不对这种理论偏见进行历史和逻辑的全面清算和批判,就无法重塑生命尊严的哲学基础,使用“人的尊严”就不可避免地会遭遇逻辑悖论,甚至遭遇“尊严无用”的理论困境。
詹心怡:在讨论“克隆人的尊严”时,仅进行“克隆人应享有尊严”这一应然层面的论证是不够的,还要考虑在实然层面,克隆人的尊严感能否得到满足。在我们追问“生殖性克隆是否冒犯了人的尊严”时,我们不仅需要考虑克隆技术本身是否会减损人的尊严,还要留心以克隆这一特殊生殖方式降生的人,是否会因为他的出生方式,其尊严不被身边的人认可。正因尊严感的满足需要同时考虑自尊与他尊这两个向度,所以我们在讨论“克隆人的尊严”时,不得不顾虑社会对他们的认可程度,而社会认可度的重要体现之一,正是法律层面的规定。
杨同卫:我想补充说明的是:“以克隆方式降生的人,其尊严是否被冒犯了?”这个问题要有意义须有一个假定的前提:克隆技术已经成熟但不够完善,就会对克隆出来的人造成伤害,并冒犯他的尊严。在克隆技术成熟这一假定条件下,我们还必须前置一个条件:克隆技术的运用必须有正当的理由——舍此没有其他技术途径且应用此技术的目的是合理的。在满足上述假定条件和前置条件的情况下,克隆人是否冒犯了人的尊严呢?我的答案是没有冒犯。相反,正是克隆技术的应用使得被克隆出来的人拥有了人的要素,并进而成长为人并拥有作为人的尊严。
刚才詹心怡提到,尊严感的满足需要同时考虑自尊与他尊这两个向度。我很认同这一观点,我也认为:与“生殖性克隆是否冒犯了人的尊严”紧密相关、一体两面的另外一个问题是“克隆人是否被社会所接纳——克隆人在普通人心目中是否拥有尊严?在社会中是否真的被敬重?”这又是一个复杂的、充满挑战的问题。
张新庆:看来,大家对克隆人尊严问题的讨论有浓厚的兴趣,在争鸣中形成一些共识,也有不少认识上的分歧,我们正是希望把学术思想的多元性和复杂性展现给大家。或许,参与讨论的专家和学生在论点呈现、论据提供和伦理论述中有不少纰漏,这也是学术争鸣中难以避免的。学术争鸣是不同观点、立场或知识背景的人就同一论题进行的带有竞争性的思想表达,论争者无法靠长篇大论、引经据典来系统展示自己的观点和论证过程,强调了不同观点的交锋和应答,而忽视了自身观点和论述的完整性。不过,我们总是要秉承一种开放包容的学术心态,欢迎各方学者的批评指正,理越辩越明。
[1] 张新庆,韩跃红,曹永福,等.“生命尊严”系列讨论之一:何谓“人的尊严”[J].中国医学伦理学,2017,30(2):151-157.
2017-07-06〕
〔修回日期2017-08-14〕
〔编 辑 吉鹏程〕
TheSecondSeriesofDiscussionon“LifeDignity”:DoseReproductiveCloningOffendHumanDignity?
ZHANGXinqing1,YANGTongwei2,HANYuehong3,HEMiao4,ZHANXinyi5
(1SchoolofHumanities,BeijingUnionMedicalCollege,Beijing100730,China,E-mail:zxqclx@qq.com; 2FacultyofMedicalPsychologyandEthics,ShandongUniversity,Ji’nan250012,China; 3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KunmingUniversityofScienceandTechnology,Kunming650504,China; 4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HarbinMedicalUniversity,Harbin150081,China; 5SchoolofPhilosophy,RenminUniversityofChina,Beijing100872,China)
R-052
A
1001-8565(2017)09-1089-05
10.12026/j.issn.1001-8565.2017.09.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