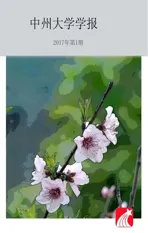知识分子启蒙话语何以走向式微
——以1990年代文学生态为考察对象
2017-01-12卢月风
卢月风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知识分子启蒙话语何以走向式微
——以1990年代文学生态为考察对象
卢月风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1990年代随着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社会公共空间建构趋向多样化,文学逐渐失去了轰动效应,不再成为折射政治和思想事件的重要载体。整体上来看,这一时期的文学场域呈现出作家群体精英意识的淡薄,文学作品的通俗化与大众化,话语言说形式的多元化等面貌。知识分子的启蒙话语虽然在推动社会进步、实现人的现代化方面意义深远,但随着这一话语所依存的文学样态倍受冷落,同时在民间话语、个人话语等不同文学表达方式的夹击中走向式微,在“无名”的文学场景中面临两难处境。
知识分子启蒙话语;无名的文学场域;启蒙的两难
知识分子是近代社会的产物,同古代社会的“读书人”“士”等称呼有着相似的内涵,自古以来,他们不仅承担着文化使命,还深切关注国家发展,铁肩担道义成为一种责任。五四新文化运动伊始,鲁迅、钱玄同、陈独秀、刘半农等先进知识分子由对这次运动的向往发展成广泛的启蒙运动,他们以反传统的姿态致力于国民思想劣根性改造。鲁迅以文学作品的形式揭露封建礼教痼疾、批判国民性,在他影响下的“乡土小说流派”,创作旨归亦是批判封建宗法制度与民众精神的不觉醒。这一主题一直持续到1930年代,随着民族矛盾不断激化,面对“覆巢之下,安有完卵”的现实环境,革命、救亡的呼声逐渐湮没了五四时期的启蒙传统,反帝救国的紧迫性压倒了反封建以启蒙的初衷。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发表,更是对作家的创作规定了方向,知识分子试图“化大众”的启蒙话语走向尾声,取而代之的是民众启蒙知识分子的“大众化”。从新中国成立到文革结束,知识分子启蒙话语一直处于被压抑状态。直到1980年代,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出现了经济复苏、文化相对繁荣的局面,在反思文学、寻根文学、改革文学的创作中再次看到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复归的迹象。1990年代,在市场经济的作用下促使昔日被无限压抑的欲望表面化,大众文学逐渐登上历史舞台,知识分子的地位受到冲击,他们在文学书写中所坚持的启蒙话语也受到强烈冲击并走向式微。同时在这一时期的文坛曾出现”告别革命“的呼声,社会发展中心由政治转向经济,文学格局也很难用一种话语模式来概括,那么以这一时期的文学生态为考察对象来分析知识分子启蒙话语衰弱的原因意义深远。
一、大众文化对启蒙话语主要载体的冲击
文学与文化既相互独立又密切联系,所以每一部文学作品中都渗透着文化的因子。而中国社会的大众文化真正兴起在改革开放之后,根植于市场经济的沃土,并在1990年代成为博人眼球的文化现象。戴锦华说:“90年代,大众文化无疑成了中国文化舞台上的主角。在流光溢彩、盛世繁华的表象下,是远为深刻的隐性书写。在似乎相互对抗的意识形态话语的并置与合谋之中,在种种非/超意识形态的表述之中,大众文化的政治学有效地完成着新的意识形态实践。”[1]283这时期文学形态的多元化发展就是大众文化实践的结果,90年代之前的文学格局是二元对立模式,代表国家意识形态的精英文学一直处于文坛主流,而精英文学正是启蒙话语的主要载体。在市场经济浪潮席卷下的1990年代,大众文化逐渐成为显学,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影响着人们感知世界的方式,带给文学最大的影响是精英文学从中心滑向边缘。而知识分子多是这一文学样态的书写者,他们试图以文学的手段启蒙民众,实现民族文化心理的重铸,但这一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所坚持的启蒙话语不可避免地出现衰落境况。
大众文化从文学生产、流通、接受方式等方面影响精英文学的生存环境。恰如丹尼尔·贝尓指出的“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印刷文化”。[2]156“视觉”强调的是文化对文学流通的影响,在大众文化娱乐性、消遣性的刺激下,文学的流通不再局限于纸媒,而更多是诉诸于读者试听觉的电子声像、影视等新形式的媒介。同时读者也养成了“快餐式”的接受习惯,那些大部头的文学经典如果不加以包装和改编很难进入他们的视野,比如把当代文学文本改编成影视剧本成为一种潮流,读者对《妻妾成群》《活着》《手机》等当代文学作品的接受最初源于以此为依据所改编的影视剧。随之读者的审美期待发生转移,金庸的武侠小说、琼瑶的爱情小说、无厘头文学、网络文学成为追捧对象,曾经位居边缘的文学形式受到青睐,实际上这是大众文化加速了这些通俗文学的兴盛。不可否认的是,文学符号化不断侵蚀其审美性,同时文学创作被戏剧化,曾经所承担的探索、追求复杂心灵世界的使命被消解。这一趋势给精英文学带来新的挑战,那些一直有着强烈精英意识的作家面临文学创作的瓶颈,加之文学整体上失去社会轰动效应而逐渐逃逸社会话语中心的趋向。新写实作家把日常生活神圣化,先锋作家由“怎么写”到“写什么”的集体转向等,迎来了大众文学繁荣的局面。读者阅读作品不再是单纯地获取知识而是以消遣娱乐为目的,昔日精英文学的生存空间愈加稀薄。从文学思潮的精神脉络来分析这一现象,无论是作者的创作心态还是读者的阅读兴趣,亦或是文学市场的商业化导向都在无意中认同了“欲望辩证法”的价值取向,而依然坚持知识分子启蒙话语书写的创作者失去了训诫和启蒙读者的思想资源,他们心中启蒙的使命感出现了危机。于是在社会从“官本位”到“金本位”的转轨中,大众文化在一定程度上规约了文学的发展方向,众多作家尝试改变叙事方式以获得市场认可,出现了作家向影视传媒靠拢的现象,甚至有的作家依据电影剧本的要求进行文学创作,剧本仿佛成了衡量作家文学创作的标杆。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精英文学的生存空间受到挤压而边缘化,作为其主要书写形态的知识分子启蒙话语难以逃脱逐步衰落的命运。
二、“民间话语”与“知识分子话语”的对峙
诗人于坚在1988年在《穿越汉语的诗歌之光》中提出了“民间写作”与“知识分子写作”这一对立范畴,1990年代仍继续发酵,在诗歌创作中围绕语言、汉语写作的思想资源、诗人的立场等方面展开了以王家新、欧阳江河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写作”与韩东、伊沙、于坚等为首的“民间写作”之间的论争。于坚认为,知识分子写作是纯粹的知识罗列,而只有民间写作是对日常生活原汁原味的呈现。虽然最终没有得出多少有价值的结论,但却使坚持“民间写作”立场的作家重新得到文坛重视,其影响力从诗歌波及到小说、散文等文学体裁,促使民间话语成为多元化文学格局中的一翼。
何为“民间话语”?陈思和指出:“这是一种非权力形态也非知识分子精英文化形态的文化视界和空间,渗透在作家的写作立场、价值取向、审美风格等方面。”[3]其实,“民间话语”既可以是学者进行文学史研究和文学批评的阐释视角,也可以是作家在文学创作中所持有的立场,这里主要指向后者。在现当代文学史上,作家所坚持的民间话语、国家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现代性启蒙话语一直有着相当复杂的张力关系。五四时期新型知识分子阶层的出现,他们可谓是古代士人阶层的现代延伸,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化价值观,清醒认识到封建传统文化的弊端,并欲以思想启蒙的方式彻底抛弃传统文化的痼疾达到社会变革的目的,所以知识分子启蒙话语成为主流。在20世纪30年代到70年代内忧外患的社会环境决定了象征着国家意识形态的革命话语占据时代制高点,这就相对抑制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发展空间。文革结束后的新时期,文学创作告别了极左思想的控制并获得一定自由,在刘心武《班主任》、徐迟《哥德巴赫猜想》、谌荣《人到中年》等作品中看到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复归。而“民间话语”在1990年代大众文化、商品经济大潮的推动下引起文坛重视,走出国家意识形态话语的遮蔽,并在合适的土壤中日益强劲,挤压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生存空间。
造成这两种话语言说方式对峙的关键是作家在不同叙事立场引导下产生了迥异的文学形态。就拿人性书写来说,当作家把“民间话语”奉为圭臬时,就不再以社会导师的身份自居,从某种程度上接受了民间“藏污纳垢”“多元性”等特征,他们笔下的人性,超越启蒙话语所恪守的伦理底线,也不以“阶级”和“政治”为标准,我们看到的是完全自然、自由、本真的人性。作者坚持“知识分子话语”立场时,其强烈的历史使命感承接了古代士人阶层的主体意识,“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社会责任感灌注始终,在人性书写中,以消解封建话语为支撑,指向人性的真善美和尊严,至于人性中丑恶与阴暗多是极力批判的对象。所以”启蒙”成为知识分子的话语核心,康德在《何为启蒙,答复这个问题》一文中强调“启蒙运动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4]22。启蒙的最终实现,离不开知识分子的理性批判精神,对黑暗的社会、不合理的制度、民众思想的不觉悟毫不留情地给以否定,同鲁迅所说的“一个都不宽恕“有相通之处。李新宇在其著作中指出:“知识分子话语面对的最严重的挑战来自获得民间话语发言人资格者对知识分子的劝说与招降。他们认为在这个新时代,知识分子不应该试图站在大众之上教训和引导大众,而应该彻底放弃启蒙导师的立场。”[5]这是在新的社会语境中,民间话语对知识分子启蒙话语发起的进攻,但是中国社会无论在新时期、后新时期亦或是新世纪等不同阶段,知识分子文学书写中的启蒙话语都不能缺席。纵观20世纪90年代的文学生态,尽管呈现出多元的景象,新体验、新生代、新写实、女性市民、新都市、新人类等不同的文学风格,但不难发现作者在叙事中的“民间话语”立场。市场经济成就了以民间话语为主的通俗文学,同时诱发了精英文学的低谷,而其主要言说方式的启蒙话语不可避免地走向式微。这时期尽管有张炜《九月寓言》、张承志《心灵史》、梁晓声《又是中秋》《荒弃的家园》等彰显着作家启蒙意识的作品构成文学多元走向中的一个侧面,但却难成气候,因为读者期待的是消解权威、弥漫着消遣娱乐气息的文学作品。引用米兰·昆德拉的话“假如小说真的应该消失,那并非是因为它已精疲力竭,而是因为它处在一个不再属于它的世界之中”[6]22。面对1990年代的历史语境,知识分子启蒙话语衰弱的原因之一正是社会转型时期时代对文学新需求之间的错位使然。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文学面貌,从某种意义上讲,贾平凹、余华、阎连科等作家纷纷搁置知识分子启蒙话语,表现出对“民间话语”的倾斜足以说明新的文学发展趋势。
三、“无名”的文学场域与启蒙的两难
陈思和最早以“共名和无名”来指称现当代文学不同时期的特征,其中1990年代因碎片化、多元共生的文学形态而被冠以“无名”的称谓。在这一文学场域中,启蒙话语由新时期文学之初的主流走向边缘,其历史合理性受到质疑;尤其是文学思潮与创作手法的多样性,文学话语向不同路径延伸,启蒙逐渐失去了“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社会效应,出现了两难的窘态。
在后现代主义、后殖民主义、魔幻现实主义等文学思潮启发下,不同的创作形态涌现于文坛。追求对生活原生态呈现的新写实写作,关注个人经验及感情变化的私人化叙事,以否定历史的客观真实,嘲弄其本质与规律的新历史主义小说,重视市民群体生存的奋斗与挣扎,性爱与欲望的新市民文学等不同类型,构成了“无名”现象的具体所指。尽管表现对象不尽相同,但作者的人文主义精神淡化,强调文学的非意识形态化是相同的,即使哪一方都不能占据文坛主导,但却共同加速了知识分子启蒙话语的弱化。“新写实”作家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对启蒙理性的反叛,当“身体“以及相关的欲望、潜意识、无意识成为新生代作家关注的焦点时,朱文《弟弟的演奏》《什么是垃圾,什么是爱》等作品面世,林白、陈然在极端个人主义价值观支配下的“身体叙事”,无不是对启蒙话语的有力拒绝。当“去掉一切遮蔽”几乎成为一种创作姿态时,我们看到了王朔“我是流氓我怕谁”“一点正经都没有”“过把瘾就死”的创作模式仍在继续;莫言对人类生命意识中原始强力的肯定,文学中出现了对暴力和丑陋的欣赏,呼吁对历史本身的回归这是文学多元发展的表征,但文学创作中人文精神的恶化也是显而易见的。1993年,王晓明《旷野上的废墟:文学与人文精神危机》的发表可谓是文坛的及时雨,由此引发的王蒙、王朔与张承志、张炜之间的论争尚未得出实质性结论,但对扭转整个文坛沉闷的处境与文学书写中现实终极关怀的匮乏有一定的意义,不过依旧难以改变启蒙话语式微的局面。这是启蒙的两面性使然。五四时期知识分子以启迪民智、呼唤民众思想觉醒为能指的启蒙话语成为时代最强音,这是积极的一面。但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的1990年代,人们的思想观念发生了巨变,市场经济以“利”为主导的价值观冲击着中国传统“义”的价值取向,这就致使文学书写中的启蒙叙事在新的时代潮流面前处于两难处境。同时知识分子作为现代性的产物,其主要言说方式的启蒙话语走向式微,也是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现代性内部冲突的表现形式。
史铁生的《务虚笔记》描写了几代知识分子对理想的追求与悲剧命运,他们心中所坚守的宗教情怀是其人文精神的写照。这正是知识分子在社会嬗变中恪守启蒙话语的两难处境之象征。于是,作家的创作理念出现分化。张承志和张炜以道德理想主义来对抗世俗化的文学环境,但一些作家选择了叙事转向,贾平凹在《高老庄》的后记中说,他所坚持的叙事立场是“平民地位和写作的民间视角”[7]277。余华在谈到《许三观卖血记》时说:“在叙述的时候,试图取消自己作者的身份,觉得自己应该是一位读者。”[8]135莫言表达了他“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立场”[9]。同时阎连科的《耙耧天歌》《天宫图》,刘庆邦的《种在坟上的倭瓜》《响器》等作品,表达出对民间信仰的认同,而放弃了知识分子启蒙批判的话语立场。莫言的《檀香刑》体现出民间伦理对社会国家伦理的挑战;《丰乳肥臀》虽写了战争和历史,但在作品中毫无顾忌地呈现女性的“丰乳”,这是坚持启蒙叙事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接受的,其充满着前现代性底色的文学书写也一直是启蒙话语批判的对象。
借用狄更斯的名句“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可以概括1990年代的文学风貌,可谓是生机与危机并存。当我们为文学卸下沉重的负荷,获得自由欢呼雀跃之时,也不能忽视文学因无所承受而失重的危机。张志忠在《1993:世纪末的喧哗》中说:“在缺乏普遍的人文关怀的时节,倡导重建人文精神;在信仰贫乏的年代,呼吁并召唤理想的回归。这些努力几乎无不例外地受到嘲弄和抵制。”[10]7识分子启蒙话语正是在这种多元话语模式的挑战下走向式微,比如,以自我情感表达为中心的“个人主义”,忽视理性的欲望叙事等话语方式都是对启蒙的解构。当“消费”“市场”走向时代前沿,人们沉溺于文学的速度和数量,而忽视了其质量。于是出现了非文学与文学的竞争,大众文学与精英文学之间的博弈,在这样的文学生态中,尽管启蒙话语在两难的处境下走向式微,但人的精神的现代性并没有真正实现,对民众的思想启蒙依旧是一个未完成的话题。所以知识分子不能“自我放逐”,同时其精英意识在推动文学健康发展中的作用不可小觑。
[1]戴锦华.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
[2]〔美〕丹尼尔·贝尓.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3]陈思和,何清.理想主义与民间立场[J].中山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1999(5).
[4]〔德〕康德.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
[5]李新宇.知识分子话语建设散论[N].作家报,1998-04-02.
[6]〔捷〕米兰·昆德拉.小说的艺术[M].孟湄,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
[7]贾平凹.高老庄[M].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2006.
[8]余华.我能否相信自己[M]//余华随笔选.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8.
[9]莫言.文学写作的民间资源[J].当代作家评论,2002(1).[10]张志忠.1993:世纪末的喧哗[M].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刘海燕)
Exploring the Reason of the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of the Intellectuals to Decay——Taking 1990’s Literary Ecology as the Investigation Object
LU Yue-feng
(College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234, China)
Along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attern transformation in the 1990s, the social public space construction tends to diversification and the literature gradually loses its sensationalism, no longer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the refraction of politics and thought events. The literature field of this period presents elite consciousness weakness of the writers group, the popularization of the literature, the diversity of discourse expression forms, etc. Although intellectual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in promoting social progress and realiz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people has the far-reaching significance, it faces a dilemma in “unknown” literary scene as literary forms of the words are neglected, at the same time, it fades in the attack from the different literature means of expression, such as folk discourse, personal discourse expression and so on.
enlightenment discourse of the intellectuals; nameless literature field; the dilemma of the enlightenment
2016-11-25
卢月风(1986—),女,河南郑州人,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2015级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潮。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03
I206
A
1008-3715(2017)01-0015-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