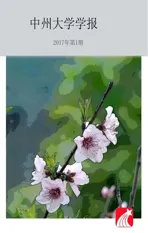“文学身体”的多维符码
——桂西北当代小说的一种读法
2017-01-12鹿义霞
鹿义霞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文学身体”的多维符码
——桂西北当代小说的一种读法
鹿义霞
(广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广西 桂林 541004)
身体既是肉身的存在,也潜藏着丰富的政治、经济符码,承载着复杂的社会、人文讯息。从大山中走出的桂西北作家们虽文学开掘领域各有不同,却大多孜孜于身体叙事。解读桂西北当代小说“文学身体”的存在方式与修辞策略,揭示其生物身体之外的各类附着和累积,可以更深入地了解地域的基因链条与时代的不同侧面,透视现代人的生存状况和精神处境。
身体;苦难;城乡;权力政治
在桂西北当代小说中,身体书写是相当突出的,透过它,生活的苦难被赋形,身份的焦虑被凸显,现代的忧思被呈现,政治的创伤被隐喻……文本中一再被凝视、被特写的“身体”成为桂西北作家群重要的叙事对象,它渗透着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与思考,潜隐着丰富的社会、文化与政治指涉。
一、在生物身体之外:生活苦难的赋形
桂西北由于多山多石、滩陡流水急、岭谷相间、地处边缘,长期以来几乎与外界隔绝,被称为“南蛮之地”,“七山一水二分田”,甚至被称为广西的“西伯利亚”。贫瘠、粗粝的“石山王国”,使在这里生活过并从这里积蓄写作原料的作家尝尽了底层的辛酸,看尽了生存的艰难,从而引爆了作品中喷涌而出的苦难意识。他们更倾向于把目光投向“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群体,挥笔勾勒生存的疼痛。伤痕与疼痛往往是通过感官体验出来的,于是身体被频频推上前台,联接了严酷的生活现实与更为隐秘的精神天地。
文学是有出生地的,从桂西北走上文坛的作家们常常将复杂的目光扫射到身边的山石、暗河、野草、黑森林等,并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意象化,借助身体与自然的通感来叙述生活。比如李约热的《涂满油漆的村庄》,“在我们村,最高的山是加广山,然后依次是加脉山、加料山、加饭山、加权山。我们要在这五个山顶上,砍掉五棵大树,之后在将倒未倒的树下,安排一个人在树下守望。加权山是我弟,加饭山是我哥,加料山是我,加脉山是我妈,加广山是我爸。”[1]东西的《草绳皮带的倒影》中,草绳、皮带、倒影与人的身体、人的命运构成双关。蓝怀昌的《一个死者的婚礼》中,一面是自然的受虐:活了一百多年的老树奄奄一息,整个格鲁苏城都沉浸在黑暗的雾海里;一面是巴楼人惨遭大屠杀。作家们好似剪辑师,借助大自然与人的身体的蒙太奇混剪,书写底层人野草般的生命,展现其身体的承受哲学,对苦难进行了极富张力的书写。
桂西北当代小说有多篇涉笔身体的残缺,或先天残疾,或后天致伤,或偶然受难,或宿命“阉割”……生理身体的描摹与生存现实的不堪互为表里、盘根错节。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既有大社会的长焦,又有小家庭的短距,全面立体地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冷酷荒诞的世界。小说中被欺辱、被隔绝的王老炳一家,父亲瞎,儿子聋,媳妇哑,身体的灾难和生活的艰辛共存。李约热的《李壮回家》中的弟弟李壮,原本是生活在千张镇上的一个青春蓬勃的男子,在经历现实的打压和理想的挫败后如同被抽干了汁液的、蔫了的植物,悲怆地向那个“有狐臭”“一只腿长一只腿短”“已经和十二个男人睡过觉”的杨美求爱。而小说中的哥哥,最大的希望是打捞到一网银鱼,因为“银鱼可真是件好东西,我看见它们,我就感觉我那只被摘掉的眼球又回到我的眼窝里”。故事的最后,他仍然没舍得去为自己装一只假眼。李约热的另一小说《巡逻记》中,甘湾村被戏谑为“肝大村”,因为连续十几年,村里的小伙子在新兵体检时都是因肝大被刷了下来。在底层人物的世界里,关于身体的叙事闸门一打开,生存的不易就如同一层层剥开的洋葱,那么辛辣,让你眼泪汹涌。随着生活的内核被一点点裸露,屈辱、苦难、挣扎被物态赋形。这些小说中,残疾或者阉割已经超越了医学的生理范畴,携带着呼啸而来的疾风骤雨和丰富驳杂的想象,它们在诉说一种人生,讲述一种困境,咀嚼一种苦涩。
在身体的残疾之外,身体的“流通”更是一种难言的伤痛。它不但关系到身体本身,更指涉精神创伤。东西的《耳光响亮》中的姐姐牛红梅在短短的时间内经历了多重身份的变迁:作为少女的她、作为姐姐的她、作为恋人的她、作为妻子的她、作为母亲的她、作为第三者的她。“牛爱”“牛恨”“牛感情”三个生命在她的子宫里夭折,其身心都经受了不堪承受之重。岁月对于她而言,一撇一捺都是被动的承受和人情的凉薄。凡一平的《圩日》,写妻子迫于生计去镇上为米店老板做女人,夫妻二人的尊严折腰于斗米。东西的长篇《篡改的命》中,贺小文为生活所迫做了暗娼,竟然得到了婆婆和丈夫的哑忍和默许。家人从愤怒、冷嘲热讽、尴尬直至帮着掩饰,这背后,搅拌着多么悲怆的况味!
关于身体与生存多艰更极端的故事是身体的殒灭与消亡。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中的晓雷,因为向采石场老板索要工资没有成功而愤激杀人,最后又被人所杀。《上午打瞌睡的女孩》中,生活困窘的母亲因为捡了一块脏肉因而被戏谑、被侮辱,悲剧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父亲离家出走,女儿被强奸,母亲不堪生活的多重折磨而自杀。凡一平的《女人河》中的船伙计在河上讨生活,下水去探触礁的船只,不幸沉入了河底。黄佩华的《百年老人》中的农保田,妻子依月、依达姐妹被红水河吞噬。《涉过红水》中的巴桑、《红水湾上的孤屋》中的无名老者,在红水河打捞起无数溺水者。极端的故事里渗透着复杂的生存悲情。故事中的主角都是底层最无力的小人物,他们越是挣扎,加在其身上的绳索就勒得越紧。
桂西北作家群笔下聚集了一大批生活在苦难中的小人物。如果说身体的“不正常运行”是小说的发生装置,那么生存的苦难则是其小说叙事的推动机制。作家们站在底层群体的立场,以身体为媒介,既书写人们对苦难的坚忍承受,也揭示人们对苦难的无奈应对。他们在各自的小说世界后面隐藏着忧郁与悲悯的目光,表现出对人性的观照和反思。
二、拨开身体叙事的表层:城乡二元生态的表述与想象
桂西北作家多有乡村生活经历,又有从乡进城的足迹。刚刚洗去脚上黄泥巴的他们对农村有着特别深刻的认知,对都市也有着十分清醒的体察。那一份都市外乡人视角下的审视,根植于现实的土壤。作家们以身体书写为时代、社会的病象把脉,其身体叙事下的城乡世界,在他们笔下发酵为城乡二元生态的表述和想象。
城乡的两极分化呈现在身体叙事上,常常是惨烈的姿态。鬼子的《农村弟弟》中的马思,是城里干部因当年婚外情在农村生下的儿子,他为了回到城里,用尽各种手段,甚至不惜杀母。凡一平的《上岭村的谋杀》中的唐艳,是以卖身的代价与屈辱的经历圆了进城梦。而东西《篡改的命》中的汪槐、汪长尺父子为了进城,亦是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汪槐不惜耗尽家财、赔上健康、赌上所有,以换取儿子的城里人身份。作者以苦涩荒诞的黑色幽默把荒谬与平静、残忍与柔情并列在一起。农民进城的生存状况以及城乡的两极分化,令人触目惊心。
桂西北当代小说没有把乡村浪漫化,也没有美化都市的喧嚣与躁动。作家们聚焦现代化视域下乡村的破败与当代城市文明下迷惘的人性,文本中的身体叙述传递出对社会的深沉思考。李约热的《巡逻记》与《一团金子》中,赌博正像毒蘑菇一样生长蔓延,村镇的一些年轻人像中毒的植物,沉湎其中不可自拔;同时,乡村也失去了作为乌托邦乡土的特征,呈现出枯萎凋零的气象。而那些进城的青年,或者在现实中失去了诗心,或者在都市的大染缸中被扭曲异化,都市的欲望泥沼吞噬了传统文化诸多的伦理品质。鬼子的《瓦城上空的麦田》,讲述了一个看似荒唐实则悲怆的事件——三个进城之后儿女不认父亲。李四曾把他的三个儿女看作自己心中的“麦田”,他所希望的只是让孩子们记起自己的生日,但多次暗示换来的仍然是一片冷漠。自杀的他也许到最后才明白,进城后的孩子们就像瓦城上空的麦田与漂浮不定的云朵,看得见却够不着。
桂西北作家还敏锐地看到,在现代化大潮中,人们身心的漂泊和无所依托已是典型的文化症候。李约热的《墓道被灯光照亮》中,做保安的老李自诩儿子留学德国,在西门子公司任职,在青山有别墅。外人所不知的是,老李的皮箱里除了换洗的衣服之外,还藏有儿子的骨灰盒。其子死于都市现代化下的病症——“得的是败血症,他长期跟一个老板搞家装,检查出来时,已经是晚期”。特别悲情的是,老李因为失去乡土而难寻可以安放儿子尸身的地方,儿子的灵魂难以“回家”。
进城受伤或致残的例子,在桂西北当代小说中比比皆是,密集呈现的情节已不是单纯的事件,而成为复杂的现象。李约热的《涂满油漆的村庄》中,“我”和兄弟们厌倦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日子,放弃土里刨食的困境改去城里打工,结果不但没有赢得财富,反而运交华盖:我哥的三个手指被机器锯断,我因讨要工钱差点送命,我弟为了有烟抽而偷钢材遭受一顿痛打。鬼子的《被雨淋湿的河》中的晓雷不甘留在农村,向老板索要工资无果而杀人,最后也死于别人设计的谋杀。故事似以酷烈的姿态暗示如下问题:在都市化的滚滚洪流中,“进城”的他们只能是城市的局外人或者过客,最终被城市所践踏或牺牲。
面对条件优越者或者围观者过度的热情和强加的善意、悲悯,弱势者、被救助方如何守护尊严?李约热的《火里的影子》,通过姐姐杀人之谜将探照灯探进了苦难者的心理迷宫。小说中,姐姐杀人的真相一直是个谜。记者的长枪短炮对准了她出身的家庭,来小村寻找“恶基因”的由来;医生也来村里寻找源头,怀疑“我姐”得了精神病……但这些都非杀人的真正诱因。姐姐之所以杀人,是因为她只能看到黑色和白色,不幸的她总想躲在自己的壳里,而类似“施舍”的“暴力慈善”让她无以躲藏。“那种悲悯对她来说就是一种侵犯,会压得她喘不过气来。”为了躲开这种过度的热情,免得自己被围观被曝晒,她只有“拿着一把水果刀,追逐杀戮帮助她的同学”。身体,成为“进入精神和心灵世界的敏锐切口”[2]。小说以肌体的苦难与极端的杀戮说明,高调而粗暴的慈善给弱势群体带来的可能是更大的伤害,比如自卑的泛滥、尊严的缺失。
在桂西北当代小说的世界里,身体修辞播撒在文本中的许多角落。拨开身体叙事的表层,文本的深层涌流的是作家对人生的严肃思考和对社会的忧患意识。
三、撬起身体的沉重分量:权力政治的象征与寄托
权力的疆域无所不在,政治的影响绵延不绝,它们不但搅动起社会风云,也大肆侵入私人领域,投影到身体上。“身体”的压抑、“身体”的戕害、“身体”的流动、“身体”的张扬,背后掺杂了大量社会性元素。“在身体上,一直遮蔽着厚厚的历史帏帐,充满了沉重而荒诞的政治文化负荷。”[3]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有相当多的作家通过身体叙事阐释时代和社会的密码。十七年文学中,身体叙事几乎被终止,文学负载起将革命圣洁化的使命;知青文学中,张贤亮以情爱表象凸显生存真相,其偏离宏大叙事的私人叙事别具一格。身体叙事投影着时代,表现着灵魂的悸动。桂西北当代小说家们也热衷于勾画身体符号,他们更倾向于展示身体荒诞的存在状态,以夸张、反讽的笔调,撬起身体的沉重分量,书写一代人的身心创伤史。
东西的《后悔录》与李约热的《我是恶人》都重在揭示“文革”造成的心理创伤难以治愈。故事中的主人公,无论“性失败”还是精神病,都浓缩着一系列时代病症,寄寓着作者的复杂认知。作家东西和李约热擎起身体的旗帜,喊出了宏大的生存命题,映射出政治荒谬的辐射力与精神疼痛的持续性。东西的《后悔录》以“我”(曾广贤)为轴心,串起两代人的“性挫败”,描写文革中与文革后的身体怪圈,从而在身体叙事的幕布之下揭示政治后遗症,书写心理创伤。文革语境下,“我”妈是绝对听话的“好学生”,把领导教诲当作信仰与宗教。在她看来,同志之谊高于一切,革命情怀不容玷污;哪怕是夫妻,生殖之外的性事都是不道德、不高尚的,从而导致“我”爸近十年未近女身。“我”也受此观念影响,泄露了父亲与赵山河的事情从而导致父亲屡遭磨难。作为故事主人公的曾广贤,因在男女情事方面的单纯、执拗或者说心理障碍而失去了一次又一次可以接近幸福的可能。即使在文革之后,其身心仍然在自制的禁忌内原地踏步。从性禁忌的文革时代到性自由的开放时代,性与政治的非正常关系并没有随着时代的改变消失,巨大的副作用仍然禁锢着故事中的人们。李约热的《我是恶人》中的马万良亦是走不出“文革”积重的创伤,最后身患精神病,于恍惚之间命丧于白露岩。东西与李约热书写身体的荒诞史,其深刻之处在于:他们不但瞄准了文革禁忌中的身体,还书写了政治禁忌的延续性、放射性,多侧面透视了未能治愈的身体与心灵。在此,身体“提供了瞭望世事变迁的窗口”[4]。
桂西北当代小说还有把镜头对准失语者,以身体为符号书写心理之殇。李约热的《殴》以知青梁燕三十年后回黄村为切入点,将时代政治的风风雨雨、个人命运的起起伏伏纳入一个经纬圈内。梁燕与黄村的最大联系,除了当初的知青经历,除了男友在此的遇难,还有方承运的一个肾。当年,梁燕因为得了一场病必须换肾,那个瘦弱的富农方承运为了能早一点“脱帽”,竟跑到公社革委会主动为标兵梁燕捐肾。几十年后,梁燕再到黄村时,方承运已化作一抔黄土。黄村人依旧太容易冲动,当年的斗殴造成的巨大灾难没有改变他们火爆的脾气;方承运的卑微依旧,他付出一个肾的代价,不但没有改变自己的命运,也没有被人记住;梁燕对农村人的误解没有改变,她接受了农村人的一个肾,反倒觉得是累赘,甚至找到医生欲把肾摘下来,“再换一个新的”。小说书写知青下乡后与黄村人彼此的不理解、暴力冲突以及双方都受到的伤害。这正如一张钞票被截成两半,一半在知青手中,一半在黄村人手中。知青会时不时借助话语优势向人们倾诉悲情、展览苦难,其实钞票残缺的另一半——那沉重的另一部分,“早已被黄村的人苦苦吞下……”时代大潮滚滚向前,青春只是一闪而过的影子。畸形的岁月带来的并不仅仅是肉体的创痛,还有心灵的扭曲、信念的失落与理想的幻灭。无论是知青群体中失去身家性命的丘阳,还是黄村人中被枪毙、被判无期的年轻人以及被摘去一个肾的方承运,没有谁是社会的赢家。小说借助身体叙事,将疼惜的目光投向了为时代买单的一代人。
东西的《一个不劳动的下午》《雨天的粮食》,围绕乡村权力,勾画了两个以职务换取钱色的干部。陈裕德、范建国多次利用职务之便抢占女性资源。小说中的性叙事不但昭示着自古以来就存有的男性强烈的占有欲以及父权统治逻辑,还揭示着乡村权力政治的魔障。这些小说通过身体叙事,体现了“社会力量与权力是如何渗透与宰割了个人的生活及命运”[5]。
梅洛·庞蒂曾言:“世界的问题,可以从身体的问题开始。”[6]13桂西北当代小说家,正是借助对身体的呈现,来关注生存之艰,呈现城市化进程中的问题,影射权力政治,揭示人性黑洞,从而展示更为宏观的社会生活。身体之痛的背后,是身体的社会学、身体的政治学、身体的经济学和身体的人类学。
[1]李约热.涂满油漆的村庄[J].作家,2005(5).
[2]李梅.我们的身体就是社会的肉身:论“身体叙事”的文学含义[J].理论与创作,2007(1).
[3]崔红涛.身体的叙事:阎连科小说的一种读法[J].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2).
[4]权雅宁.论阎连科底层写作的身体叙事[J].小说评论,2012(4).
[5]夏豫宁.论毕飞宇小说的身体叙事[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4).
[6]谢有顺.身体修辞[M].广州:花城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 刘海燕)
Multidimensional Code of “Literary Body”——a Reading Method of the Contemporary Fiction in Northwest Guangxi
LU Yi-xia
(College of Literature,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Guilin Guangxi 541004, China)
The body is not only the existence of the body, but also contains a wealth of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ode, carrying a complex social and cultural information.The writers of Northwest Guangxi walk out of the mountains, though they dig in different fields of literature, but most diligently in the body narrative. Deeply reading the existence and interpretation of rhetorical strategies of“literary body”in Northwest Guangxi Contemporary novel, revealing all kinds of attachment and accumulation outside its biological body, we can more deeply understand the different nuclear gene chain and the region of the era, then see modern people’s living conditions and spiritual situation.
body; suffering; urban and rural areas; power politics
2016-12-30
广西高校中青年教师基础能力提升项目“桂西北作家群当代文学叙事研究”(KY2016YB045);桂学研究协同创新中心资助项目“地缘文化与生命诗学:广西壮族当代文学意象研究”(201608)
鹿义霞(1977—),女,河南开封人,文学博士,广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与文化研究。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04
I206
A
1008-3715(2017)01-001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