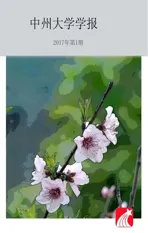追逐与抵抗虚妄的虚妄
——论郭昕的长篇小说《驯风记》
2017-01-12司真真
司真真
(郑州师范学院 初等教育学院,郑州 450044)
追逐与抵抗虚妄的虚妄
——论郭昕的长篇小说《驯风记》
司真真
(郑州师范学院 初等教育学院,郑州 450044)
郭昕的小说多以进城者为书写对象,展现他们进城后对钱权的追逐,他们进城后虽然物质上不同程度地得到满足,精神上却依然难逃束缚,时刻感到虚无、烦躁、疲惫。他们开始寻求救赎、解脱的方式,马立找到了诗歌,刘湘民找到了听风,而回乡成为他们心灵获得片刻宁静的一致方式。小说中城乡对立模式的书写,隐含了作者对乡村的诗意想象,体现了作者对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肯定。最终,回乡等方式的救赎也陷于虚妄,在宗教文化的阐释中沦为命定的悲剧。
郭昕;《驯风记》;虚妄;传统文化价值观;宗教文化
郭昕的长篇小说《驯风记》以几个由农村进入城市奋斗的不同领域的人物为核心,展现了他们在拼搏的过程中,所遭遇的种种精神危机。小说内容庞杂,却不失头绪,紧紧围绕虚妄,将人物的救赎方式一一道来,展现了不同人物的人性和大时代下生活的众生相。
一、追逐钱权与抵抗虚无
对金钱、权力、欲望的追逐是新世纪乡土小说经常书写的对象。其中,对权力的追逐与我们社会中根深蒂固的“权力崇拜”意识有关。“中国思想史流传至今的那些概念,诸如入世与出世,兼济与慎独,庙堂与江湖,中心与边缘等等,皆出自政治为轴心的官本位文化,一切以权力为转移,以此为参照,则权力无疑是天下最具威势、最具价值的。”[1]81对金钱的追逐也与我们的封建文化有关。春秋战国时期的杨朱公开宣扬“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孟子:尽心上》)。民间也有“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有钱能使鬼推磨”之说。在《驯风记》中,由农村奔向城市的诸多人或逐钱,或逐权,展现了传统文化和当代商业时潮对他们的巨大影响力。小说中的马立、刘湘民是主动奔向城市的。马立对名利、金钱的追逐丝毫不落于人后。他经常在电视及其他传媒上露脸,成为被业界熟知的专家,然后,他待价而沽,不断地调整自己被采访节目的价格。追逐完金钱后,他有了更高的追求:研究所所长。他认为,“名,是虚的。位,才是实的。他只有得到一个职位才真正成为社会的中坚力量”[2]。但在权力的追逐中,他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刘湘民对权力最为热衷,“从小到大,当官都是刘湘民的理想,是他的追求”[2]。这与他父亲的影响有关。幼时,他在孩子们中称王;上小学后,他想尽办法做班长;大学时施计当上学生会主席;毕业时,因善于表现被系主任推荐给一位县长做秘书;到了社会上,因有女学长县长的帮助,他轻轻松松当了副科长、科长。……一路上对权力的追逐,刘湘民很是享受。“他喜欢听人汇报,喜欢在各种文件上签字,他觉得这个城市在他的笔尖下在不断地发生变化。那样的感觉,让他的心理得到了巨大的满足,那是权力带给他的满足感。”[2]
在城市生活的这些异乡人,虽然他们能从金钱、权力和欲望的追逐中获得满足,但也时常会感到一切都是虚妄,感到烦躁、疲惫。马立在学术上取得了一些成绩,这一点令他自信、满足,但其他诸如升迁、调资等很多跟生活品质与社会地位有关的事情,一直都不如意。有时候,他会感到“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其实很多事情都是很虚妄的”[2]。刘湘民在当上蜜如市市长后,经常会觉得“一切都索然无味”,“生活总是无聊”,“随着官越当越大,生活越来越像一场接着一场的表演,他感觉越活越假,越活越累”[2]。
为了缓解心中的虚妄、烦躁与疲惫,马立采取的方式是阅读诗歌和回乡。马立读书时代就喜欢上了惠特曼,他觉得惠特曼是一个能让人产生能量的诗人。当他无情地嘲弄自己卑微的出身与命运,看不到希望时,他接触到惠特曼的诗歌,“在一豆灯火之下,惠特曼的诗让他的内心充满了灵光。他一读起那些诗,好像鲜花在春天的阳光里开放,如同树叶在细雨中沐浴,身体都会产生一种通透的感觉”[2]。以后每次遇到精神危机,他都会读惠特曼的诗。不同的情境之下,他会选择不同的诗。当他在学生时代忍受穷苦和无聊时,他读《戴假面具者》,领悟到这个世界是由一重重的秘密组成的,化解了心中的一些积郁。当他到北京读大学时,他读《大路之歌》,心中的不安被万丈豪情所取代。当他在生活与工作中出现虚幻的感觉时,他读《幻象》。当他竞选失败想要轻生时,他心中浮起《现在你敢吗,啊灵魂》,从中生出了向前走的勇气。但由于这次的打击过于强大,马立在读诗的同时选择了第二种方式:回乡。回乡对于马立来说,是医治心灵的良药。他每隔一段时间都要回乡“接地气”,因为“生活在北京这样繁华而拥挤的大都市里,他的心灵感到干渴,常常有被榨干的感觉。回到老家院子里,呼吸着湿润的空气,嗅着野花的香味,心里就万物复苏,充满着希望”,“让人产生打拼的勇气与信心”[2]。
刘湘民采取的方式是听风与回乡。每当他被难事困住了心,或者有不快烦闷的事儿,他都到山里去听风。他觉得“不同的地方,风的声音不一样,味道也不一样,带给他的感受也就不相同”[2]。在风里,他把自己的隐私一点一点藏起来,并且常能产生出很多灵感,那些灵感刺激着他的头脑产生出很多处理难题的办法,他困顿的心灵便会在刹那间解脱出来,听风是他整理思想、调整灵魂的优良方式。回乡也是刘湘民经常采取的方式。蜜如山是他出生成长的地方,他的父母亲、初恋都在蜜如山。蜜如山是他的“命之所系”,给予他爱、安慰、灵感、智慧与甜美的梦。离开大山后,他无数次地回来,“这里是他的智慧之地,是他的灵感之源”,“每回一次,心灵好像就丰富一些,心智就成熟一些,处理问题的手段也就会圆润一些”[2]。
二、城乡对立书写与传统文化价值观的肯定
新世纪乡土小说中,普遍存在着城乡对立书写的情况。乡村代表着贫穷、善良与正直,城市则代表着财富、堕落与丑恶。农村人往往渴望进驻城市,但最终或重返乡土,或回归乡土,再重返城市。面对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作家们在两种文明冲突中所表现出来的多是价值理念的惶惑。这可以说是百年来乡土小说所面临的困境。
在《驯风记》中,马立、刘湘民等人都积极主动地选择进城,他们对农村生活极为厌烦,觉得在蜜如山里的生活十分痛苦。马立这种心理产生的根源在于贫困。马立读乡中学时,每天要赤脚走过很窄的坎坷不平的碎山石路,碍于面子与尊严,他宁愿把鞋子脱掉,原因就在于贫困。刘湘民也厌倦农村生活,他厌倦的原因与马立不同,他不想“被那种小环境拘囿着……他想拥有自由的生存空间与自由的生活环境”[2]。马立与刘湘民所代表的物质与精神的束缚是小说中人物选择进城的两大原因。他们在城市中虽获得了物质上的享受,精神上却并不快乐。他们时常感到虚无、心累,他们的精神逐渐被扭曲,他们的品行发生了变化,朴实、纯真逐渐少了,坏心眼多了起来,官气十足。马立刚开始参加论坛收红包还会觉得羞涩,随后就变得期待了。刘湘民任市长期间,送礼、玩弄权术,“有多少人被他玩残了,玩废了,玩得消失在茫茫人海,没有踪影了”[2]。他以权谋私、谋财害命,权术被他玩得索然无味。这些论述显然隐含着作者对城市的批判,批判的矛头指向的是“拜金主义”“拜权主义”及其造成的人性扭曲与道德败坏。
进城的农村人逐渐道德败坏,小说人物产生出远城市近乡村的心理。在他们看来,城市不再具有神秘性,反倒是乡野山川更具有吸引力。马立和刘湘民对故乡的多次回归,就体现出了故乡的魔力。另一方面,对于没有走出大山的农民,城市却一直诱惑着他们,充满了神秘感,“山里的乡亲们仍然觉得那是一个神秘的地方,是一个大城市”[2]。他们一辈子最大的心愿就是去城里看一看,走一走。和城市里人们精神的扭曲异化相对比,蜜如山里的人们虽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影响,但他们之中仍有人未失赤子之心,保有善良、勤劳、朴实的美德。毛姑姑年轻时喜欢刘湘民,后来刘湘民做了官,她反而离他越来越远,原因就在于“毛姑姑,喜欢他的书卷气,不喜欢他的酒色财气,更不喜欢他十足的官气”[2]。燕双来受父亲连累,下放插队到蜜如山,得到村长和村人的帮助,干最轻的活,吃的却是最好的饭;他和姚丽娜双双失踪后,村里一位老人收养了他们的孩子。
在对农村贫困狭小、城市富裕神秘,农村人善良、朴实、城市人腐化、堕落的对比书写中,小说把侧重点放在了对乡村/传统文化的认同上。“侧重于礼赞乡村生活的古朴、和谐与宁静,凸现和张扬农民具有传统文化中的美与善的人性和人情。这可以说是新世纪乡土小说创作中一种自觉的艺术追求。”[3]116郭昕也是自觉追求的,他在小说中多次写到乡村对马立、刘湘民的精神感召,他们源源不断地从乡村获得前进的动力、生命的活力。刘湘民最初踏入仕途与大学系主任的推荐有关,后来他每次去北京,都要去看看退休在家的系主任,“没有功利目的,也不是作秀”[2]。来钱进城后一直保有善良、淳朴、勤劳的品德,他跟扬州师傅学艺,为了报恩,在扬州师傅被关起来后,经常看望;无私帮助二毛学习搓背技艺,后两人合开澡堂。马立有时也流露出淳朴的心性,他会鄙视那些善于经营人脉关系的人,自己也不愿意去做这样的事情;他会觉得在男女之间,金钱与欲望的关系是最低等、也是最为庸俗的关系,努力想追求一份纯粹的爱情。
作者把批判的重心放在了城市生活的欲望上,“外面的世界坏了,外面的风不断去地吹进山里。那是什么样的风啊,那是由物与欲组成的淫风与妖风啊。山里的人啊,他们怎么经得起这样的风,经得住外面世界的引诱,怎么经得起金钱与美色的勾引。他们的心灵被物欲所害,他们的身体与灵魂被物欲之火点燃,他们成了这个世界的灰烬”[2]。这种在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下的价值选择,弱化了批评的力度,在建构新的价值观上亦无多少拓展。乡村在现代生活的强势影响下,日益发生着变化,乡村在多大程度上还能作为进城者的灵魂归属地?这种归属的诗意想象又能持续多久?这些都需要我们深入思考。郭昕对宗教文化的书写就体现出了他对此的思考,只不过他的思考暴露出的是和多数乡土作家类似的价值观的紊乱不定。
三、宗教文化、神性的返魅与救赎的虚妄
新世纪以来,农村发生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土地日益减少,生态遭到破坏,人们的精神生活出现危机。于是,乡土小说中宗教文化开始返魅。“乡土小说中宗教文化的‘返魅’,是在世纪末精神沉沦与拯救的思潮下产生的,体现了知识分子在无常人生下对民间的恒常关怀,在对现实的批判中饱含着对未来的寄托。”[3]392郭昕的小说中出现了多种宗教文化,显然与救赎有关,因为无论是阅读诗歌、听风,亦或是回乡,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生虚妄的问题。这是整个人类遭遇的难题。
在郭昕的小说中,共出现了三种宗教文化或神性资源,一是基督教,二是佛教,三是通灵。基督教仅在题记中出现,透露了小说的主题。“我又专心察明智慧、狂妄和愚昧,乃知这也是捕风。因为多有智慧,就多有烦愁:增加知识,就增加忧伤。”这句话取自《旧约·传道书》,意思是人在世上的一切追求,都只是捕风,是虚妄,若不相信神(上帝),智慧、知识的增添,只会带来更多的忧愁烦恼。小说所着力描写的就是几个由乡村进入城市的人物对金钱、权力、欲望的追逐,以及由此带来了一系列的烦恼与虚妄感。但小说并未让人物转向上帝、信仰来获得救赎,而是以诗歌、听风、回乡等方式获得心灵的片刻宁静。这主要是因为我们国家没有普遍性的宗教信仰。
燕双来的故事与佛教相关联。故事背景关涉“文革”。“如何回忆和叙述文革的过程和细节,如何梳理和解释文革的来源和影响,这是中国(特指大陆)当代作家不能忽视和回避的题目”。[4]2小说没有对“文革”的来源梳理解释,只叙述了燕双来一家受到“文革”的影响。燕双来出身于红色革命家庭,父亲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革命者,因性格耿直在“文革”中被以莫须有的罪名投入监狱,后病死狱中。燕双来为躲避迫害躲进蜜如山,虽受到村长与村民的保护,但和他一起逃到山里的李家印被抓后为自保把他供了出来,结果害得村长死于山沟,恋人/孩子的母亲逃入深山,后生下孩子再次进山,杳无音信。燕父“文革”后被平反,燕双来被重新分配工作,而李家印在大觉寺出家做了和尚。两人晚年成了朋友,经常喝茶谈禅。小说没有过分渲染“文革”的苦难,没有耿耿于怀于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及身心受到的严重创伤。相反,在燕双来的意识里,他更在意的是蜜如山善良的农民,尤其是他的恋人及村长。故在被安排工作时,燕双来提出到蜜如山工作,目的就是想尽自己的能力回报善良的山民。他在总结自己的一生时,认为论起亲情与人伦,自己不称职,但在政治生活中是成功的,他对自己的出身具有优越感,他教导女儿应为革命者的后代而感到骄傲。小说从村长之口也道出了他光明的政治远景:“他说我是一个落难的公子,被恶风刮进了穷苦的山里,等风头一过就会飞黄腾达的。他劝我不要因为儿女私情而影响了前程。”[2]燕双来后来确实飞黄腾达了,他也确实谨记村长的教诲,宁愿抛弃亲情与人伦,也不愿割舍他的政治前途。这样,燕双来的“文革”经历就被作者叙述成了“公子落难记”(外加“多情女子记”),对文革的反思则被置换为道德伦理叙事;甚至对“文革”,流露出了怀旧的情绪:“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父亲经常做梦,梦见又回到了蜜如山中,梦见找到了你的母亲。太阳出来时,我跟她一起上山劳动。太阳下山了,我跟她一起回家,我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那是多么美好的生活,可是这样的生活只能在梦中出现啊。”[2]小说缺乏从政治、制度角度对“文革”进行反思,于是“文革”中对立的双方在宗教(佛教)的掩护下,轻而易举地就和解了。
小说中神性描写的重心是蜜如山的通灵者。这些一代一代的通灵者,掌握着天的秘密,指导着山里的人平平安安地生活下来,其中最有名的是程大仙,他自诩劝人们“避害趋利”,指导人们“去恶意生善心”。在小说中,他指导刘湘民“当官如开车,安全为上”,帮助刘湘民化解贿赂县委书记的事情,显然属于“避害趋利”;但从中并未看到半点教导他“去恶意生善心”的意图。在马立的读书时代,因暗恋上一位出身干部家庭的女孩,陷入不可自拔的痛苦之中。他的母亲请来程大仙为他算命,这时的马立已读了大量的书,有了一定的分析判断能力,但小说最后,马立听到程大仙讲述蜜如的神话传说时,不仅激起了倾听的欲望,而且也不再发出质疑的声音。可以看出作者的态度,他对程大仙前后并非一致的态度,显出了他在启蒙理性与神性之间的犹疑。
程大仙最后讲述了一个神话传说,这个传说是关于苍公、泌娲与蜜娲的三角恋情引发的一场悲剧。而蜜如山人的生活悲剧与这个悲剧神话密切相关。程大仙讲述的这一神话,为蜜如人的痛苦寻找到了源头,如同亚当夏娃被赶出伊甸园,蜜如人在泌娲杀死蜜娲,上苍惩罚苍公、泌娲,将他们投入人间,蜜如人也开始背负着罪与罚。他们注定要受到各种诱惑,经历各种灾难。精神的异化,道德的滑坡,不再是城市文明惹的祸,而是神的过错,“我们的先祖,培育这一个地方的先祖动了淫心,坏了神人之间的规矩”[2]。救赎与抵抗变得毫无意义,马立、刘湘民们抵抗虚妄的努力便如西西弗斯推巨石上山,陷入更大的虚无之中。“救赎时代的精神危机与信仰危机,宗教文化虽然是有效的,但绝不是万能良药。乡土小说对宗教文化的表现,不能成为宣扬宗教教义的布道场,更不能制造新的蒙昧,而应该从中发掘有益于价值重建的精神资源。”[5]郭昕小说中对宗教文化的书写虽然试图救赎时代的精神危机,但多少有些空洞,对“文革”的反思批判力量也因此而削弱,马立等蜜如山人的虚妄在神性的解释下被注入命定的成分,对乡村、城市的反思批判也被置之一旁。这是小说存在的遗憾之处。
[1]夏中义.九谒先哲书[M].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0.
[2]郭昕.驯风记[J].莽原,2015(4).
[3]丁帆.中国乡土小说的世纪转型研究[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4]许子东.为了忘却的集体记忆:解读50篇文革小说[M].北京:三联书店,2000.
[5]李兴阳.新世纪乡土小说折射时代焦虑[N].社会科学报,2010-06-24.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Falseness of Chase and Resistence——on Guo Xin’s Novel The Wind Down
SI Zhen-zhen
(College of Elementary Education, Zhe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44, China)
Guo Xin often writes the migrant workers as his novels’ object to show their chase after money and power after they come into the city. Although they get material satisfaction to some extent, their spirit is still in the bondage, and they often feel nothing, irritable and fatigue. Then, they begin to seek the way of salvation and deliverance. Ma Li finds poetry, Liu Xiangmin find listening to the wind, and returning to the hometown become their consistent manner of achieving the quiet mind for a moment.The writing of the opposite pattern of urban and rural areas in the novel implies the author’s poetic imagination of the country, which reflects the author’s affirmation of the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Finally, the salvation way of returning to the hometown falls in vain and becomes a doomed tragedy in the interpretation of religious culture.
Guo Xin;TheWindDown; falseness; traditional cultural values; religious culture
2016-10-10
司真真(1983—),女,河南郑州人,文学博士,郑州师范学院初等教育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17.01.006
I206
A
1008-3715(2017)01-0027-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