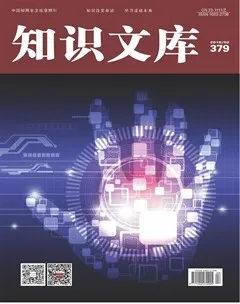我国民事诉讼既判力客观范围的立法建议
2016-12-29王月
由于种种原因,我国民事诉讼立法对既判力的相关体现几乎为零,特别是关于民事诉讼既判力的客观范围,这必将成为一种缺憾。在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事诉讼立法,通常做法是:将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局限于判决主文的判断事项,例如德国《德国民事诉讼法》第322条第1款“判决中,只有对于以诉或反诉而提起的请求所为的裁判,有既判力。”日本《日本民事诉讼法》第114条第1款“确定判决,只限于包含在判决主文之内的判断才具有既判力。”
确定判决的既判力客观范围与判决标的之间应当是一种对应关系,也就是说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与裁判标的的范围是相同的。但传统的民事诉讼法学理论主张,诉讼中有什么样的争议事项,就有什么样的判决出具。“当事人在诉讼中发生争议的东西都应当进行裁判。因此,诉讼标的和裁判标的之间没有区别,正如多位作者所主张的一样。和诉讼标的一样,裁判标的也是原告希望作出与诉讼请求(和案件事实)相符的裁判的请求。”因此,“裁判标的和诉讼标的是同一的”。并且,判决文书的主文就是法官具有既判力的判断,这个判断是针对诉讼中出现的代表着民事实体法律关系的诉讼标的的判断事项,又因为诉讼标的的内涵与判决主文的判断具有相应的等同关系,进而得出这样一个公式: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判决标的的范围=诉讼标的的范围=判决主文中判断事项的范围。故而,这个逻辑推导,自然而言也就演变成,“既判力的客观范围在一般情况下应该限定于判决主文中的判断事项”。而最早的诉讼标的理论,又主张,双方当事人之间的诉讼争议标的,是民事实体法上的请求权,而法院的裁判对象,就是法律上的双方的争议。因此,上述结论也就进一步可以转化为,所谓的既判力的客观范围,一般的情况之下,应该局限于裁判主文之中的判断,并且这种判断应当是针对以起诉或反诉的诉讼形态主张的以某项民事实体法的请求权而作出的。
根据这种传统的既判力客观范围理论,民事诉讼中的裁判主体,针对当事人提出的某一个争执所为的判断,想要拥有判决主文中的位置,并自然地取得既判力作用的的客观范围之内,应当拥有二个因素:首先,这项争执应当涵盖民事实体法上的相关的请求权(在给付之诉中),或者涵盖与民事私法上的权利之类别,如支配权(在确认之诉中)和形成权(在形成之诉中);其次,这个当事人之间的争议是双方当事人之一任何一方提起诉讼或者提出反诉的状态。对此我国民事诉讼法典中关于既判力客观范围提出几点立法建议。
一、我国既判力客观范围的理论的选择
由于我国相关的理论属于起步阶段,相当的不完备,因此我国应当先在既判力客观范围领域从零开始,一步一个脚印,慢慢探索属于我国的理论路径。由于德国的传统理论已经相当成熟,而日本的相关理论又较为偏激且尚处于探索阶段,因此我国应当在将来的民诉立法过程中,采用传统模式。结合我国自己的司法实践和理论研究,找出更加适合我国的道路选择。具体而言,就是:原则上既判力的客观范围,限定于确定判决的主文部分,判决的理由部分不具有既判力。判决理由部分的事实认定判断、先决性法律关系的判断、抗辩权判断和甄别抽象法律规范的判断,不具有相应的既判力。但作为例外,当事人主张的抵销权抗辩权,裁判者在判决理由作出判断的,也就是所谓的抵销权抗辩权判断,应当赋予其既判力。
二、我国民事诉讼中诉讼标的理论采纳
由于既判力研究尚属于初期阶段,并且我国的民事诉讼法典对此等于空白,我国应当采纳具有发展前途的新实体法学说,作为诉讼标的理论的理论基点。也就是说,诉讼标的的识别,仍应当以实体法律上的请求权为基础,民事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应该作为诉讼标的的核心内核。只有如此,才能在诉讼标的理论上,与传统的既判力客观范围理论衔接一致,也能保证既判力客观范围的理论体系保持完整统一。而日本的相关的代表学说,偏离传统理论太远,不仅不利于保障体系的完整性,也容易导致在司法实践中自身识别的困难。故而,德国的新实体法说,应该值得我国在初创阶段借鉴。
三、判决理由部分具有既判力的程序规制
既判力客观范围的传统理论在解决司法实践中的问题时,明显不从心,但是这并不能阻止其占据学说理论的主流位置。在个别的情况,尤其是传统理论不能胜任的时候,需要借鉴类似于中间确认判决的制度,来扩展既判力的效力范围。但是萨维尼主张的中间确认判决在诉讼中相当于独立的民事诉讼,需要在程序上进一步予以简化,如可以口头提出,与本诉合用一份判决书,将判决理由部分的判断,上升至判决主文部分等等。在程序保障非常充分的情况下,特别是法官再三释明相关先决性法律关系或诉讼请求的状况下,如果当事人选择不提起主张或要求,法官可以在判决书中注明,并赋予这一部分与既判力,防止限于传统理论的限制,而使实质上同一主张或给付的诉讼请求,当事人以变换不同的手段来再次起诉。
(作者单位:太原科技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