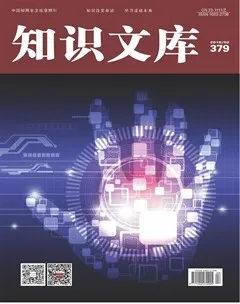魂归何处
2016-12-29张岚
任何读过毛姆文学作品的人,都会被其对人性的深刻洞察,冷淡而优雅的讽刺手法留下深刻的印象。毛姆对罪恶的绝望,对神职人员的虚伪的揭露,有意无意的对基督教义的讽刺几乎贯穿他的每部作品,淋漓尽致的表达了他的反基督教的倾向,正如他一再宣称,自己为不可知论者。本文通过对他最具代表性的几个文本的分析,探究毛姆极其矛盾的宗教观,他的作品中时隐时现的救赎观恰恰是基督教义的最好体现。对宗教的依赖,对宗教的否定,最终求助于东方神秘哲学,在作品中不断变化的精神救赎之道,也展示了毛姆在寻求精神归属的征途上的矛盾与不确定性,也是他不能成为最伟大作家的重要原因。
毛姆反基督教倾向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人物塑造。
人物塑造一直是毛姆最擅长的,他塑造的人物精细,复杂, 很少脸谱化,十分鲜明。然而可疑的是,在两种人物的塑造上,毛姆表现出了高度的重复性和单向性,一类是女性角色,一类是基督教神职人员。在这两类人物的塑造上充分表明了他的反基督教立场,却也因为其人物刻画的 重复性被批评界诟病。
1.对待女性和婚姻的观点 。众所周知,基督教中的最典型女性形象就是夏娃。神从亚当的肋骨中取下一节,造了他的妻子。由此告诉男人,女人是你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在基督教义中,男人与女人的关系是头与肢体的关系。然而,在毛姆各个时期的作品中,都充满了对男女关系的嘲笑。在《月亮与六便士》中,他借着斯特里克兰德的口说“女人把爱情看得非常重,还想说服我们,叫我们也相信人的全部生活就是爱情。实际上爱情是生活中无足轻重的一部分。我只懂得情欲,这是正常的,健康的。爱情是一种疾病。”“女人除了谈情说爱不会干别的”。同时,他 对女性表达的态度几乎是蔑视。“女人是我享乐的工具,我对她们提出什么事业的助手,生活的伴侣这些要求 十分讨厌。”从他最主要作品中塑造的女性人物来看,绝大多数都是虚荣,浮华,浅薄而粗鄙。从《月亮与六便士》中出轨的斯特略夫夫人到《人性枷锁》中用爱情绑架男人的米尔德丽德,从《面纱》中的自私自利的凯蒂到《刀锋》中的 物质女人伊莎贝尔。即使被评论界誉为他笔下最丰满的女性角色,《寻欢作乐》中的酒吧女招待罗西也不例外。毛姆对这个角色是倾注了真实的喜爱“罗西身上这种金黄的色彩确实给人一种奇异的月光似的感受。她就像象夏天傍晚阳光逐渐从明净的天空消失时那么宁静。她的这种安详的神态一点都不显得呆板迟钝,反而跟八月阳光底下肯特海岸外那风平浪静闪闪发光的大海一样充满生气”。他又写到“她生来就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当她喜欢一个人的时候,她觉得与他们同枕共衿是很自然的事。 她对这种事从不犹豫不决。这并不是道德败坏,也不是生性淫荡,这是她的天性”。如果再联想到毛姆的另一篇短片小说《雨》中妓女汤普森小姐,就会发现毛姆笔下偏袒喜爱的女性都是在性上极度开放,在男人间周旋自如,有种天然野性的魅力。由此也可见他对基督教义中温柔节制谦卑忍耐的女性形象发出了最强有力的反叛。
2.对神职人员的刻画。无独有偶,毛姆最有影响力的几篇长篇小说,《面纱》《月亮与六便士》《 人性的枷锁》都有对传教士,神父等神职人员的描写,而且都有极其相似的特征。《人性的枷锁》作为毛姆最有影响力的作品,也被公认为他的半自传体小说。小说主人公菲利普先天跛足,父母早亡,笃信基督教。然而他的叔叔,一个牧师,他传播爱的宗教,却不知如何爱身边的家人, 菲利普渐渐觉醒,最终摆脱了信仰的束缚。毛姆对神职人员的人物刻画有着高度趋同的气质,在他的短篇小说《雨》中,有最为直接的刻画。“他禀性冷淡甚至有些乖张,他那副长相也是绝无仅有的。他的身材又高又瘦,他看起来死气沉沉,可是当你看他那丰富而富有性感的嘴唇时,你会大吃一惊。他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那抑制的欲火”。毛姆对基督信仰的深刻怀疑拉开了不可逆转的怀疑之路,继而对爱情,对人性,对一切怀疑和幻灭。
然而悖论也恰恰在此产生。 毛姆在刻画这两种人物时不加节制的讽刺挖苦,对人性深处的罪恶的刻画,却恰恰符合基督教最重要的教义,人性本恶。“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上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基督教教义的基础,就是要世人承认本性中的罪,无论在世界上如何善良仁义之人,在神的面前也不过是罪人。一切善都是伪善,一切义也是不义。毛姆的人物刻画却在这里与他想极力撇清的基督教义高度重合。
二、写作主题—诺斯替主义与基督教义的冲撞
毛姆的一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然而他很少有作品涉及到宏大的战争叙事,他近乎偏执的关注着小人物的情,欲,爱,以及在这一切之下的人性之恶。他擅长疏离的观察人性,用最准确的语言刻画和表达,他的写作主题几乎都是人的情欲和可笑的本性,扯下温情的面纱,赤裸裸的呈现在读者面前。毛姆的作品持续的对人类罪恶本性的嘲笑,而关于人类精神救赎的出路,作者却表现出了矛盾和不确定性。《月亮与六便士》《刀锋》最后提供的精神救赎之路, 可以看出毛姆深受诺斯替主义的影响。诺斯替主义是希腊哲学晚期的一种思想。这是一种神秘的关乎拯救的智慧,它不可言传的,而是需要隐秘的启示而获得的自上的智慧 。在《月亮与六便士》的结尾,据说以高更为原型的主人公 斯特里克兰德最终放弃了中产阶级的生活,在荒蛮的塔西提岛,找到了内心的平静,在荒蛮的孤岛摆脱了内心的荒凉。相似的主题也出现在了另一部作品《刀锋》里, 毛姆以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为原型,主人公最终在东方的经学找到了精神归属,重返生命的意义。然而,悖论又再次产生,诺斯替主义并非是毛姆作品中唯一的救赎之道。在另一部作品《面纱》中,背叛的妻子凯蒂守在为救治病人染病的丈夫旁边,死亡到来,爱情复活。凯蒂的爱情向死而生,如同圣经里说:“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救赎以死亡的面目出现,这是基督教文学的重要主题,毛姆甚至把这一主题直接在结尾处从修女的口中明确的点明,修女对失去丈夫的凯蒂说“把手弄脏了,洗干净,才是责任。我18岁就恋爱了,爱上了我的神,50年过去了,我有时也感觉他不听我的祷告,就像老夫老妻坐在沙发上,并不说话,但心里直到彼此相爱。当有一天,爱与责任汇合在一起时,恩典就与你同在。”这样具有基督教宗教情怀的主题,难以想象是出自毛姆之手,其作品反映的人类精神救赎的不同道路也折射出作者本人极其矛盾的宗教观。
三、毛姆其人
作为一个同性恋者,毛姆一生憎恨基督教道德 ,作为一个信仰的幻灭者,他一直在作品中寻求人类精神的救赎之道。他敏锐的洞察力发现了人类精神的空虚“我猜我们的心上都有一个缺口,它是个空洞,呼呼的往灵魂里灌着刺骨的冷风 ”。他也在他的作品中揭示,情欲,财富都无法填满这个空洞,能填满他的只有精神上的信仰。然而,笔者认为,一个伟大的作家,必须超越个人体验,将之升华出一种相对统一的思想,毛姆的局限在于将个人体验,个人经历,个人感受置于万物之上,由于其个人感受的变化,也造成了其作品主题的不确定性。 他说:“我一定天生缺乏强烈的宗教感情,要不就是由于我年轻刚正,对我接触到的一些教士的言行不一大为震惊”。毛姆的基督信仰的破灭直接导致了他作品中的反基督倾向,然而在情感上,毛姆毕生都没有脱离同上帝的联系,他说:”在理智上我不再相信上帝了,我感到获得了一种新的自由而欣喜,不过我仅是在理智上不信神,在灵魂深处仍然萦绕这根深蒂固的对地狱之火的恐惧。所以我的欣喜在一段时间里夹杂这祖祖辈辈遗传下来的惶惶不安,我不再相信上帝,却始终深信魔鬼“。
(作者单位:西南民族大学文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