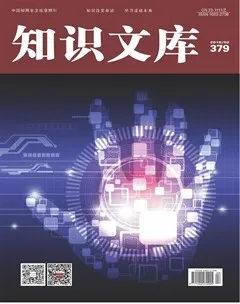公民记者在国际新闻实践中的维度和模式
2016-12-29黄斐
随着网络新媒体的不断发展,人们逐渐习惯于“通过大众媒介和个人通讯工具向社会发布自己在特殊时空中得到和掌握的新近发生的、特殊的、重要的信息”。“公民”作为参与社会公共事务的主体,已经从“被告知”的角色转变为“告知”的角色,摆脱了单纯“接受信息”的被动地位。公民在参与社会事务的同时,还积极主动地制作与传播信息,职业记者和公民记者一起记录社会事件,成为新闻的报道者,历史的见证者。
新媒体环境下,公民参与国际新闻传播的的热情和积极性不断高涨,呈现出国际新闻传播主体多元化的趋势。公民记者参与到国际新闻的报道中,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国际传播媒体在新闻采集的过程中难以避免的“新闻盲点”,扩大了消息源,提高传统媒体的报道能力。
而另一方面,由于缺乏缺乏专业训练和规章制度的约束,公民记者参与国际新闻实践的弊端也不断显现。笔者认为公民记者参与国际新闻实践首先要解决的便是“权限”问题,它是公民记者进行国际新闻报道和评论的一把“钥匙”,这把名为“新闻自由”的钥匙却在内涵上与传统意义上的新闻自由大有不同。
一、国际新闻中公民记者“新闻自由”的三个维度
“让我凭着良知自由地认识、自由地发言、自由地讨论吧!”英国政论家、文学家约翰·弥尔顿(John Milton)最先发出争取言论自由之声,他认为真理是通过各种意见、观点之间自由辩论和竞争获得的,而非是权力赋予的。必须允许各种思想、言论、价值观在社会上自由地流行,如同一个自由市场一样,才能让人们在比较和鉴别中认识真理。“观点的自由市场”以及“观点的自我修正”构成了新闻自由主义理论的根基。而新闻自由与言论自由在具体内涵上有一定的差别。言论自由权更多地强调广义的、大众的表达权利,而新闻自由是专门指言论、出版自由在新闻活动中的体现,更强调了新闻媒体、新闻记者的采访报道自由,即新闻媒体基于新闻自由享有一些一般人基于言论自由所无法享有的保障,社会对新闻媒体的赋权使其在获知信息、传播信息方面比普通大众更具优越性和权威性。
在新闻传播事业发展的初期,并不强调内容生产者的专业性,普通印刷商就可以创办报纸并取得经营权,而后,在新闻社会责任理论的助推下,新闻从业人员的专业性问题才逐渐得到重视,社会言论特权就此产生。公民新闻强调“新闻自由”不是少数人的特权,不只是记者采访报道、表达观点的自由,更应该包括让公民自由地知晓、自由地评论乃至自由地报道,亦即强调公民记者与普通记者在新闻传播实践中的地位不相上下,从而为公民记者争取了更多的施展空间和自由。
考虑到国际新闻在信息的发出者和信息的发送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遭遇到“新闻主体中的把关人与新闻选择因素、技术与经济因素、制度与观念因素、国家利益与国际政治”多层面的影响,笔者认为,公民记者在国际新闻传播实践中的“新闻自由”包括三个维度:一是在某一国际新闻事件发生过程中,获知新闻信息的自由,积极地享用媒介、利用媒介来获取知识,更好地了解国际事务,成为“知情”的公民;二是对于国际新闻事件、国际社会事务进行评论的自由,通过民意产生舆论压力,不断影响事件的发展,从而更好地参与到国际格局建设和改造的进程中来;三是由公民记者最先掌握并传播新闻信息的自由,成为国际新闻内容的生产者和制造者。这些方面都强调了公民记者与媒介在国际新闻传播实践中享有同等的新闻自由权,平权传播恰恰也是公民新闻的核心所在。
当前国际关系格局下的媒介环境并未对话语权实现完全开放,当影响国际新闻传播的诸多干扰因素邂逅公民新闻浪潮,带着镣铐舞蹈的公民记者们竭力争取新闻自由的权利,正在积极地推进国际新闻传播领域中公民新闻的实践和探索。
二、公民记者国际新闻实践的三种模式
随着公民记者参与国际新闻报道程度的加深,参与传播活动时间的增长,参与公民新闻实践方式与平台的增多,公民记者也发展出不同的类型,从不同的维度也有不同的类型划分。关于公民新闻的实践模式,美国学者史蒂夫·奥丁曾列举了11种之多,其中公民参与、公民报道、公民媒介、公民传播、公民共享是公民新闻的几个关键词。公民参与是公民新闻实现的方式,公民报道与公民媒介可看做公民参与新闻内容的制作与报道,而公民传播和公民共享,则强调公民作为非内容制作人的次级传播者,其在新闻事件传播、影响扩散过程中的重要地位。中国传媒大学有学者从公民记者与报道内容关系、公民记者身份和发布新闻的频率三个维度对公民记者进行解析——从公民记者与报道内容关系视角出发,可以分为自报道型公民记者、目击证人型公民记者和调查型公民记者;从公民记者身份之维度可以分为草根型公民记者、专家型公民记者和全能型公民记者;从发布公民新闻频率之维度可以分为偶发型公民记者和职业型公民记者。
审视公民记者的角度是多面性、多角度的,考虑到国际新闻新闻三要素错位这一特性,笔者则从“实践”层面对参与国际新闻报道的公民记者进行类型的划分,继而提出了公民记者新闻实践的三种模式:一是公民记录,即全程参与新闻信息的采集制作。亲临突发性事件的“现场”报道,当面临突发事件时,新媒体使用者本能地会利用新媒体来进行现场报道抑或是现场记录,因这类事件的不可预见性,并不是公民记者的“主动”记录,而是在事件发生后公民意识作用下的条件反射。另一种则是主动记录,公民记者通过多种社会资源获得新闻信息继而报道出来,这类公民记者不仅对于新闻报道活动怀有热情,并且往往具有高度的社会责任感,敢于说出真相、伸张正义。二是公民申诉。当公民自身利益收到侵害时,往往通过“自报道”的方式披露或者揭露社会问题,通过新闻报道来满足自身的利益诉求,以期获得关注、最终解决问题。三是公民观点,即公民对于自身联系密切的领域,在网络上发布对于某类问题、某类事件的观点(排除对于问题本身不理解而胡乱发表言论的“网络暴民”非理性行为)。
1.公民记录
(1)“被动”报道突发性事件
公民新闻的发展与突发事件、公共危机、自然灾害、政治丑闻等重大公共事件密切相关。尽管现代社会媒体与交通的发达已为新闻传播活动提供较为便捷的条件,但是由于新闻事件的发生具有偶然性、不可预测性和时空不可重复性,因此在有些新闻事件发生后,媒体记者并不能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只能通过在现场的公民记者进行先行记录和发布。2014年“7.28新疆莎车恐怖袭击事件”中最早的一批照片就是由现场目击者拍摄并发送至网络的。
公民参与突发事件新闻报道,也能为主流媒体提供宝贵的现场信息与一手资料,减少新闻盲点,及时准确深入地报道新闻,促成了传统国际媒体机构与新媒体公民记者的合作。发生在2004年12月的东南亚海啸被认为是公民新闻发展的一个决定性时刻,这一事件中,许多当时在现场的普通人向主流新闻报道贡献了独一无二的内容——第一人称叙述、摄像机拍摄的视频、手机和数码相机快照等。
公民记者“自由地记录”是实现“新闻自由”权利的重要途径,也是公民记者参与国际新闻传播实践的最直接、最易得的路径。
(2)“主动”挖掘新闻资源
再枝繁叶茂的媒体机构都有它延伸不到的触角。公民记者的出现,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填补了国际新闻报道的部分漏洞,其中最为明显的便是在战争新闻的报道方面。
前往战地报道往往需要办理诸多手续,危险系数较高的战地甚至会拒绝非参战国记者入境报道。公民记者报道战地新闻的优势在于,身处事件发生的微环境中,对事件的动因、发展、结果比专业的新闻记者更加熟悉。在报道新闻的过程中,公民记者能够综合多方面因素,调动社区资源进行采访报道,因此更全面和直观。香港著名战地记者张翠容曾介绍说自己在伊拉克战争时遇到一位美籍阿拉伯的独立记者一个人深入许多传统媒体不愿意派记者过去的地方做了很多优秀的报道,并把他们都放在自己的网站上工人阅读。新闻爱好者发布社区新闻的议题都是和传送者、接收者相关的,在共同分享利益的再制与再现中,社区媒介遂产生了社会与政治上的意义。公民记者的大量出现,使得无数“在与自身接近的地域”连结起来,使国际新闻成为了“你家门口的新闻”。
战争新闻报道是公民记者实现国际新闻传播中“新闻自由”权利的绝佳途径,既满足了新闻爱好者自身对于新闻报道活动的偏好诉求,在推动国际社会信息传播方面也大有裨益。
2.公民申诉
在发生的各类新闻之中,还可以看到一种情况,通常某人因新闻事件而成为新闻人物后,往往成为新闻媒体采访报道的对象。而如今,新闻人物可以利用微博进行‘自报道’”。中国传媒大学有学者称其为“利益诉求型公民记者”,是指以维护个人政治、经济等直接利益为目的发布新闻的普通民众,是抗争政治的表现,也说明了普通民众现实社会中的政治参与、利益维护与利益诉求渠道的缺失。在越来越开放的传播环境中,公民通过媒介进行权利申诉以期得到满足的愿望日益强烈。
作为集信息发布者、意见表达者以及信息接受者角色于一身的公民记者来说,公民新闻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话语权的解放,但开放性的网络媒体不可避免地存在着网络暴民和虚假性新闻,个别人和集团为了谋求自身利益,利用公民新闻自由权损害公众利益,使得谣言盛行,甚至引发社会恐慌或其他群体性行为,提高公民记者的媒介素养是当下公民新闻时代亟待探讨和解决的问题。
3.公民观点
由于国际新闻涉及到文化、制度、国家利益等敏感因素,涉及主流的、精英的、政治性的事件时,公民新闻自由中的“自由记录”功能往往不能在传统媒体得到实现,只能通过新媒体平台来发表对这类事件的观点,新媒体的互动性、包容性激活了公众理性思考的能力。这里提到的新闻事件必须要与公众利益密切相关,是具有广泛意义的公共议题。
公民新闻跟随新媒体的发展脚步进入国际新闻传播领域,并成为这一领域重量级的概念,在实际的公民新闻实践中,公民新闻的社会影响与作用日益彰显,已在我们难以察觉的微小空间里挥动起了威力无穷的“蝴蝶翅膀”。在公民新闻发展的早期,公民言论自由权缺乏一个施展的平台,随着媒介平台的逐渐开放,公民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对国际新闻事件进行评论,而这些反馈往往能够成为“二次新闻”,成为媒体争相报道的内容,这大大增强了新闻事件的原有影响力。
在公民记者进行新闻实践的过程中,会对国际新闻事件展开社会层面、道德层面、政治经济层面的多重思考,并将自己的思考通过转发或者评论的方式传播给其他公民,这种n对n的开放式传播使得“观点的自由市场”日益丰富,通过观点的碰撞、思想的交流,公民的媒介素养得以提升。而另一方面,媒介素养较差的公民记者,辨别信息的能力较差,加之新媒体核裂变式的传播方式,容易形成错误的舆论导向,自由开放的公民新闻也因此遭受诟病。
随着公民新闻在国际新闻领域的不断发展,其问题和局限性不断呈现,例如内容的个人化、不具备成为公共议题的条件等等,除此之外,公民新闻逾越了其外延,“失范”情况屡见不鲜,隐私披露、虚假信息泛滥等问题成为公民新闻良性发展的瓶颈。公民新闻面临着引发法律、版权等等问题。这与当下全球特别是我国的文化环境、传播生态有直接关联,也与公民记者群体自身的媒介素养状况密不可分,“从根本上说,只有公民记者乃至广大民众的媒介素养真正提高了,公民新闻的品质才能得到实质性提升,也才能够使其积极有效地参与到舆论监督和社会公共事务中来。”
(作者单位: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