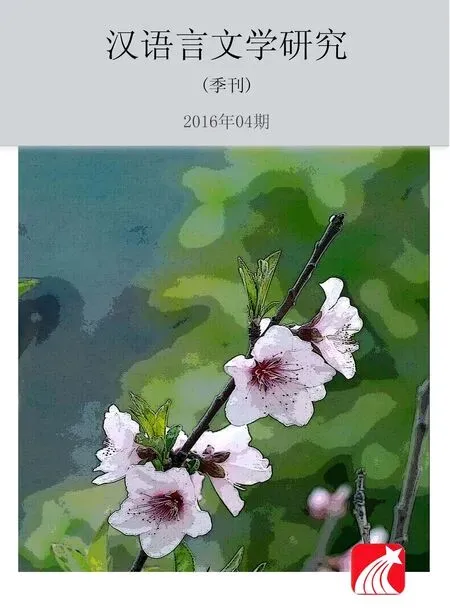上海符号的建构与拆解
2016-12-29赵青
赵青
上海符号的建构与拆解
赵青
《匿名》似乎是王安忆的转型之作,她放弃了自己擅长的创作方式,主动尝试去写一部“不好看”的小说。尽管如此,上海符号的书写作为与之前作品一脉相承的内容仍然是《匿名》的重要内容之一。但与之前不同的是,这种书写不再以文本主要内容的形式出现,更甚者,作者通过对上海符号书写的逐渐隐匿,对其实现了某种拆解。
乍看之下,在内容上,王安忆似乎放弃了自己历来十分擅长的上海市井生活的书写,转向更大的叙述空间,开始进行哲学意义上的思考;在写作手法上,王安忆开始尝试使用意识流的写作手法,更加注重语言本身的力量。但尽管如此,我们仍能从中读到其作品中一脉相承的东西,那就是永恒不变的上海符号。这种上海符号体现在衣食住行等生活的细枝末节之中,构成了王安忆小说的独有特色。
王安忆对上海的符号化书写首先体现在语言上面。语言,我们每天都在说,是最能体现一个城市的符号,而沪语又是上海的识别标志。正因如此,王安忆的作品对方言格外敏感和关注,这在《匿名》中多处都有所体现。
失踪者——他在回忆吴总的时候,文中有这样的描述:“唯一流露个性的地方,是他的本地口音,听得出是川沙一带的人。就在方才说的辉煌期,黄豆迸出得热火朝天,吴总亲临现场,因为兴奋和紧张,将‘黄豆’说成‘绿豆’,‘绿豆’呢,说成‘六豆’。就觉得有意思,想他这个年纪的人竟然说不好普通话,通常的情况是,这个年纪的人只会说普通话,不会说方言。吴总乡音里的朴素气质,倒给他好感,同时呢,多少让他也生出一些些鄙夷,这一些些鄙夷,刚好用来平衡他的失意。如此心情很可以反映上海中心城区市民今天的处境,成见不减,地位却在式微。”
吴总的乡音在他的心中成为唯一个性流露的地方,语言在这里超越了一切,成为最能代表一个人的符号,而语言的最终指向是一个人社会地位的体现。一方面,本和他不属于同一代的吴总因为说方言而不说普通话的缘故使他在心理上与之更觉亲近,因为方言意味着两人同是上海人;另一方面,他对吴总又稍含鄙夷,因为吴总的方言是不纯正的,是带有川沙口音的,因此尽管他在给吴总打工,内心仍然坚持一份优越感——他的语言是纯正的上海话。作者由对语言的描写最终指向了对上海市民心理的准确刻画。
文中类似的描写还有很多。如对阿妹的描写是“听口音阿妹是西南地方人”;对腰子弄里住户的描写是“老板操河南还是山东一带口音”,不同于上海的地方方言自觉将这些人设定为他者;老葛与刘教练发生争执时,也都涉及到了语言问题。老葛这样说道:“但是,你们知道,修钟表是什么人玩的?老克勒,是海派的传统,上海人玩钟表的时候,河南地方还是鸡报时呢!”处处显示出上海人的高贵,而刘教练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原计划河南话作国语,华夏中原之声嘛!”直接对上海话的优越地位予以否定;萧小姐的话中更是不时蹦出几句“不懂经”“猪头三”之类的上海俚语,给文章增添了几分上海特色在里面。
除了语言之外,王安忆对上海的符号化书写还体现在生活细节的描写与刻画中,处处显示出作者的用心观察在里头,也构成了王安忆小说的特色。
王安忆对朋友那一类人做了如下描写:“眼睛一定是近视的,然后又老花,就配了分上下远近视的眼镜,镜片是蔡司,因为相信德国老牌子。款式中庸,不过于时尚,也决不落伍,是细镜架无边框。”作者在这里特别强调了“镜片是蔡司”,这种强调正是为了突出上海人对生活的品位与讲究,于是“蔡司”镜片就成为代表上海人生活态度的一种符号。
他回想起自己的师傅时,对师傅的印象是这样的:“他其实并不十分看得上师傅的做派,一头厚发上了发蜡,乌黑锃亮,上身工作服,下面是毛料裤,无论工作服还是毛料裤都留有明显的熨烫的痕迹,皮鞋也是铮亮。”师傅虽然是在冷藏库工作,但其上海老克勒的派头并不随着工作环境而改变,仍然上发蜡、擦皮鞋、穿毛料裤、将衣服熨帖齐整。显然,这种派头已经融入其骨血,成为其所代表的上海市民生活中根深蒂固的一部分。这种派头本身就代表着上海二字,是上海的形象代表。
在描写年轻时的他与当时还是女朋友的妻子约会的场景时,文中这样写道:“她拉开她的女式背包,取出两颗大白兔奶糖,一人一颗。”大白兔奶糖是上海的特产,在王小帅描写上海知青生活的电影《我11》中也曾经有大白兔奶糖的出现。大白兔奶糖作为上海的一个代表,成为上海市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物品,王安忆通过对大白兔奶糖的描写,使得大白兔奶糖在这里不再仅仅指涉一种食物,而是超越了食物本身,具有了更加丰富的含义,它成为一个城市的符号,所反映的是在这个城市中生活的人们对于生活的期待。
除了大白兔奶糖之外,文中对母女两人饮食的描写十分精彩,仿佛又回到了王琦瑶的小居室里,三个人于乱世之中借食物寻求一点慰藉的时光。王安忆对上海的吃食以及吃法很有研究:“一个人慢慢地吃饭,筷子尖挑着醉蟹螯里的肉,再加一个皮蛋,算作冷盘,热菜是爆鳝和炒菜心。”“醉蟹的肉一丝一丝挑空,余下一堆透明的壳,其余的冷热菜略动了动。然后盛一碗泡饭,配腌笋尖和酱油肉,汤就免了。”“杨莹瑛进厨房看鸡汤,在汤里放蛋饺、鱼圆、粉丝。女儿大声道:你不要弄,弄了我也不吃的!杨莹瑛不理睬,兀自忙碌,不时,砂锅大滚,便端上桌子。”在这两段描写中,上海人对于食物的讲究、对于吃饭的规矩跃然纸上。菜要有冷有热,炖汤一定要用砂锅,锅中放的是有上海特色的蛋饺、鱼圆,醉蟹的肉要一丝一丝挑空,切不可粗鲁,菜心、泡饭这类上海经典家常饭菜是一定要有的。上海人对于饮食的考究正是上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体现了上海人的文明与生活的艺术,这一切都深深吸引着王安忆,因此,她在不同的作品中不厌其烦地描绘着上海人家洗手作羹汤的景象,将沪上人家的生活场景当作理想生活的范式。
文中诸如此类的生活细节还有很多,这种细节的描写处处体现了上海这个大都市所独具的生活特色,成为王安忆小说中独具特色的部分。
但是随着文本上部的完结,当杨莹瑛决定将他的户口进行销户,家人寻找失踪者的这条线索戛然而止,随之而来的,是颇具王安忆特色的上海符号的书写的中止,或者说是实现了对上海符号化书写的拆解。
这种拆解首先体现在内容方面。文本的下部随着“家人寻找”这条线索的中止,将上海以及与上海有关的生活搁置,重点描写的是畸零人的生活图景,描写“老新”是如何从林窟到小镇到县城,一步一步与上海靠近,但作为最终目的地的上海则很少以正面形式出现,即使偶尔的出现,要么是从人物的口中进行侧面描写,要么是以局外人的角度进行客观描写,真正具有上海特色的符号书写已经销声匿迹。
其次体现在细节描写方面。文本下部也间或出现具有上海特色的语言,例如在文中数次出现的上海歌谣。“所长高兴了,戏谑地学一句:乡下人,到上海——老新接下去念:上海闲话讲勿来!这句歌谣方一出口,在座三个大人,包括老新自己都是一惊。原来在普通话之外,他还能说上海话,接着,第三句歌谣也出来了:米西米西炒咸菜!”尽管这几句歌谣数次出现,但很显然已经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它只是作为激发起“老新”对于上海记忆的外力而存在,是工具性的存在,已经失去了其本应具有的文化内涵。当“老新”在所长面前唱起沪剧时,沪剧这一本应是代表上海的典型符号,也完全从文化内涵、城市代表变成了证明自己身份的工具。“从前有一个小姑娘——自己都被吓一跳,收住了,瞠目结舌的,不发一声。所长拍一下桌子,大声道:真是上海人啊!受此激励,上海人又开口了:金陵塔,塔金陵,金陵宝塔一层又一层!惭愧一笑,唱不下去了。所长说:上海的文化呀!面前的上海人谦逊地笑道:沧海一粟。”“老新”一句“沧海一粟”,无论是谦逊也好,还是真实作答也好,都将上海文化从原本优越的位置拉扯下来,变成最为普通的“沧海一粟”。
上海符号的书写最终随着“老新”的溺水而亡,实现了彻底瓦解。当“老新”从林窟到小镇到县城,与上海逐渐靠近,并且在不断地刺激之中,记忆被不断地唤醒,当他与上海仅有一步之遥时,却一脚踩空,溺水而亡。随之溺亡的,是他身上所有关于上海的印记。作为一个会唱沪剧,有着老克勒派头,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上海市民,他最终没能在上海这片土地上死去。这种结局既是偶然也是必然。随着他在上海以外的地方不断地进行自我重构,他身上的上海印记被不断地一点点擦拭,仅存的印记也不再具有任何文化意义。此时他已完全脱离了上海的母体,即使回到上海,也不可能再像之前一样与上海融入一体。至此,上号符号的拆解彻底达成。
从《长恨歌》到《遍地枭雄》再到《匿名》,我们可以看到,王安忆对于上海的书写经历了一个从建构到拆解的过程。王安忆怀着对上海的热爱,凭借着自己对上海的细致观察,将自己观察到的上海融入到自己的文本之中,构造出一个独一无二的具有王安忆特色的上海,这种建构到了《长恨歌》实现了高度完成。
然而王安忆在融入上海之余,仍然与上海保持着一定的距离,正是这种距离感,使得王安忆既能“进得去”,又能“出得来”,从而对上海保持着一个较为清醒的认识,能够在精心刻画上海之余,仍然站在一个较为客观的立场上,自觉对上海进行拆解。
再者,王安忆作为一个对自我要求很高的作家,显然希望在她的每部作品中呈现不一样的东西,因此,在近些年的创作中有意识地求新求变。正如她本人所说,“从《遍地枭雄》开始,我一直就有一种欲望,想做这样一种叙事的努力——把一个人从他原本的生活环境中连根拔起,把他放到一个没有任何参照物的虚空茫然之中”。这种“连根拔起”正是王安忆试图超越自己,试图逐渐解构之前建构成熟的上海符号化书写。
《匿名》作为王安忆的一次“实验”,至少在对于上海符号化书写的解构方面来说,称得上是取得了成功。我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也应该从中可以看到作者不断试图推翻自我、超越自我的努力,而这,也是每个文化工作者所应该具有的专业态度。
赵青,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当代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