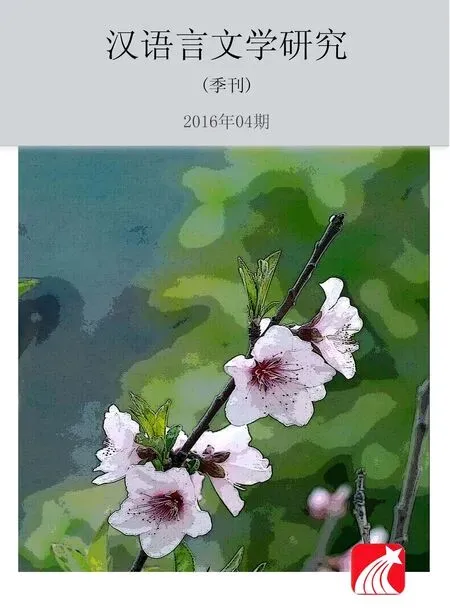周作人集外文三篇*
2016-12-29宫立
宫立
周作人集外文三篇*
宫立
大量的周作人集外文陆续被发掘、整理和研究,但仍有遗漏。《这一年》《希腊人的好学》的《附记》《看报经历》即是证明。在辑录的同时,结合周作人的相关研究资料对其略作梳理。
周作人;集外文;辑佚
周作人集外文的辑佚工作,是一项宏大的系统工程。经过众多研究者的“探幽发微,钩沉辑逸”,大量的周作人集外佚文已被发掘、整理和研究,但仍有遗漏。于是,笔者将新找到的周作人集外文《这一年》等三篇公之于世,以纪念周作人诞辰130周年。
一
鲁迅关于北大的名篇《我观北大》,最初发表于1925年12月17日出版的《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笔者在国家图书馆数据库中无意中找到这期创刊号。该期为北大27周年纪念特刊,由北大学生会宣传股编辑,除刊有鲁迅的《我观北大》,还有 《愿听青年的觉悟声》《这一年》《与北大同学会诸君笔谈》《北大的使命》《北大此时此地应负的责任》《我们为什么要举行二十七周年纪念》《怎样纪念北大二十七周年》等各类纪念北大成立27周年的文章,这都是应北大学生会的约请而写的,撰稿者有蒋梦麟、李石曾、周作人等。
《这一年》,署名周作人,照录如下:
本校二十七周年纪念,学生会要出特刊,叫我做一篇文章,在二十四小时内交卷。二十四小时就是一天,要做文章也可以做出一篇,但是这一天里却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余下来可以作文的只有三个钟头,这在我真是不够用,因为我是文思极滞的。总之,有这一点工夫在这里,且来写写看罢。
工夫总算有了,但是题目呢?讲什么东西呢?什么读书救国咧学而优则仕咧,这些人云亦云的文论,我是不会做,也不高兴做。讲点学问吧?我又是没有专门的,只如高翰林所骂过的看点“杂览”,是三脚猫、四不相;倘若一定要调查我的户籍,那么我是海军出身,现在所还未忘记,可以献丑的,是放几枪,虽然未必一定中靶。将来本校纪念会余兴中添设射击一项的时候,我或者可以参加,现在只好做罢。让我回过头来再想题目。
最适宜的题目当然是“赋得纪念”。但是纪念室每年有的,这样做去一定话要说完,弄成千篇一律。于是不得不缩小范围,改为今年的纪念,在从民国十三年十二月十七日至十四年十二月十六日这一年的事情上着眼,想到这里遂添上题目字一行曰 “这一年”。
这一年有什么特色?这就是段执政执政。这执政有什么特色?除了章士钊朱深掌权之外于我们没有什么意义。教育经费是照旧而且更加的困难,积欠已经有十足一年了,在这种境况之下学校的发展是不必谈的了,虽然因了教授们的努力,本校于本学年已添设了生物学系,是很可喜的现象。据我个人看来,这一年中最可纪念的有两件事,却都与学问研究无关的。一是教员学生的游行被打,一是反章与反反章两派的争斗。关于前者大家都已有评论,可以不再说。我只想谈后者这一件公案。平常外边有一种论调,说北大对外一致;这在以前历史看来确是如此,虽然我们知道内里总不免有暗流的,但到了反章事件发生,这一致便完全破裂,毋宁说不一致完全暴露了。有些人见了就抱悲观,以为这非北大之福,或者简直是北大之祸也未可知,但我却不是这样想。我觉得意见之一致是很难得,与其暗地分离,实在还不如明白地表示出来,更为正确,更为畅快。只要真是有绅士态度,不用反正瞒不过人的手段以退为进。这回的事情我也有点关系,所以不好加以批评,但我相信本校反章议案终于执行至少是于本校有利无害的。以学校名义反对教长,自有他的历史,凡在本校三年以上的人都该记得;这个传统的行动好不好是别一问题,但传统总是传统。今年因了反章事件的争斗使学校有审查并订正那个传统的机会,我也很是赞成,而且觉得可以纪念。现在这件事情过去了,我们急于等待民国十年“那一年”到来,看他给本校带来了什么好运,不必回头去批评陈迹。况且本校同人对于此也已有无形的公评,本年评议员选举,大家对旧评议员仍加信任,可见北大对外还是一致的了。我希望本校任“那一年”中于学术方面更有发展,可以供给我们一点新材料,在二十八周年纪念时作起文来能够更愉快些。
《这一年》位列《我观北大》前一篇。好玩的是,鲁迅在文末说,“今天所想到的就是这一点。但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流所谋害,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了。一则,命题作文,实在苦不过;二则,说起来大约还是这些话”。①鲁迅:《我观北大》,《北大学生会周刊》创刊号,1925年12月17日。而周作人在《这一年》中所注重谈的正是关于北大“反章与反反章两派的争斗”。查《胡适年谱》可知:“(1925年)8月21日,与陶孟和、王世杰、李四光等17位教授联名发表《为北伐脱离教育部关系事致本校同事的公函》,极力反对学校卷入论争。当时北京各校为反对章士钊而与教育部脱离关系。25日,胡适代表王世杰、高一涵等12位教授致函代校长蒋梦麟,要求召集教务会议与评议会联席会议,重议脱离教育部案。8月26日,鲁迅、朱希祖、朱家骅等30多人发表反对章士钊的宣言。”②耿云志:《胡适年谱》,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2页。周作人在《这一年》中提到的“反章与反反章两派的争斗”指的正是他自己、鲁迅、朱希祖等与胡适、王世杰等的分歧。另外,周氏两兄弟对于来年纪念刊的态度也颇值得玩味,鲁迅说,“如果北大到二十八周年……又要出纪念刊,我却要预先声明:不来多话”,而周作人却说“我希望本校任‘那一年’中于学术方面更有发展,可以供给文末一点新材料,在二十八周年纪念时作起文来能够更愉快些”。
二
关于《希腊人的好学》,张菊香与张铁荣编的《周作人年谱》、钟叔河编的《周作人散文全集》、徐从辉编的《周作人研究资料》均注明《希腊人的好学》,1936年8月作,载当年12月20日《西北风》第14期,署名知堂。收《瓜豆集》。
无论是钟叔河编的《周作人散文全集》还是止庵校订的《瓜豆集》,在收录《希腊人的好学》时,都依从周作人的写法,篇末仅注明“廿五年八月”。但是查阅这期的《西北风》,笔者发现篇末并未注明“廿五年八月”,不过另有编者《附记》,“上文发表一个校刊上,看到的人不多,故转载于此”。幸运的是,笔者无意中在1936年8月16日出版的《新苗》第6册上找到了这篇《希腊人的好学》,署名知堂,更为惊喜的是,篇末还有《附记》,照录如下:
《新苗》规则,须本院教员学生可以投稿,不佞则两者皆不合格,唯上遂兄以三十年老同学资格来相拉,苏甘君又曾来坐索,重违尊意,只得写此塞责,对于投稿规则姑且写作前教员罢。廿五年八月二日夜雷雨时记于北平。
《新苗》版权页上仅注明“国立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出版委员会编辑”,创刊于1936年5月1日,共出18期。许寿裳作为该校的院长,事务繁忙,但一直十分关注该刊,几乎每册都有他的文章。查《周作人传略》知:“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北平大学成立,原北京女子大学附入,称女子文理学院。周作人到北平大学任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及日本文学系主任。同时兼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一九二九年十月,辞去北平大学文理学院国文系主任职。”①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传略》,《周作人研究资料》,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页。《新苗》的投稿规则共7条,其中第1条 “投稿人限于本院教职员及同学”,第4条 “来稿如用笔名,请在稿端附书真名”。周作人曾说“许寿裳君是我的小同乡,在日本留学时曾经和他同住过两年 (一九○八至○九),所以很是熟悉”,“上遂”正是许寿裳在《新苗》刊文时用的笔名。由此,周作人才说“唯上遂兄以三十年老同学资格来相拉,苏甘君又曾来坐索,重违尊意,只得写此塞责,对于投稿规则姑且写作前教员罢”。
这期的《新苗》《编后记》也提到了周作人:“这一期得到周岂明先生一篇文章,非常感幸!周文附记,说‘新苗规则须本院教员学生可以投稿,……姑且算作教员罢。’尤其亲切。同时感想连前教员都不惜霖雨,新苗一定更有望,那末周先生的好意不光是寓于文章之中,且给本刊以莫大的活力,谨在此表示感谢。”
三
《看报经历》,署名知堂,刊于《新学生》1943年第2卷第3期,照录如下:
不佞开始阅报是庚午年以后,在南京的学校里,大家关心时务,聚资买上海报看。其时除了上海以外,并无报馆,《新闻》《申报》觉得稍旧,顶新的是《苏报》。
这后来成为有名的苏报案,记得的人现在还不少,我们受了苏报的影响,也不免想说话活动,几次弄得几乎记过,有朋友终于以此退学转投将学堂,成为名人的。但是讲到养成看报习惯,仿佛是香烟瘾似的,那还在其后,即是日俄战争之后在日本留学的那几年里。平常学生看的大抵是《读卖新闻》,后来夏目漱石进了朝日社,起手写《虞美人草》,于是《朝日新闻》也为文学青年所爱读,我们那时所看就是这两种。不知怎的归国以后却只订阅《读卖》,直到现今改为《读卖报知》,还是在看,大约这也就是惰力的缘故吧。在南京的时候,无论冬夏什么时候,一醒过来,枕头边就放着报纸,洗过了脸,第一件就是看报,懒惰的可以躺着看过了再起身。这几乎是日课一样,接连五六个年头,便成了习惯。还有傍晚出门的时候,大抵是散步或买物,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务,在换车站就有许多卖报的嚷着晚报是一分,晚报是一分,也往往摸出一个铜元来买一份,明知道里面不会有什么消息,姑且看他一下,随即折了塞入怀中了。到了这时候,这已是成了瘾了,假如真是袖底没有零钱,晚报不买尚可,但是早上起来洗了脸,沏好了茶,靠着火金钵坐地,这时如没有一张报捏在手里,正似吃烟家没有香烟,不但觉得极是无聊,便是手指头也似乎很空闲似的。
天下事一成为瘾,便没有法子,即使是香烟,虽然比鸦片烟较好,也总是再也省不下,戒不掉。看报也正是一样。我以前曾说,看旧书有如抽香烟,意云藉以消遣,现在又说看报,这未必可消遣,乃是因为成了瘾也。差不多四十年只一跳,说到现在,别的虽然变了不少,这瘾是依然存在。现今在食堂内玻璃门的食器厨上每日放着不知几天前的《读卖报知》,因为总不能每天来,大抵送到时多是一叠,上盖红戳云迟到二日分,所以我也不及细读,只看看新书广告以及大题目,而已。不过报有好几分,不必一一列举,总之北京天津有名的报纸大概都有了,其中有赠阅的,也有订阅的,说也奇怪,出了钱定的到的很晚,平均总在十二时至一时之间,叫早送毫无效验,说这样迟到就不要了,他也情愿你停阅,反正不能提早,这有多年历史,于今也已习惯了。一时以后回家来再看也不妨,而且在外边也会看到的。义务报迟到更是莫怪,有些报大抵隔一天送两日分,既是白看的,岂能再说闲话,不过隔日报在受者别无用处,在送者还是耗废了一分,实在很觉得对不起的。然而一面也有很早的《实报》送给我看已有八九年了,午前总是按时送到,差不多没有一天缺少,这很是难得。
本来吃烟吃不饱肚子,看报也是那么一回事,不必太计较,但是看报的瘾也有时候的,及时能让人看到,自然是更可感激的事。旧书与香烟近来都大大的涨价了,只有报纸还算公道,普通一月份只领得三四斤榆树皮面,这又是每天非看报不可的人的福音了。
(转载北平《实报》)
关于 “看报的经历”,周作人除了写有这篇《看报经历》,还写有 《读报的经验》《读报者言》《报纸的盛衰》等。他说“我们平常的习惯,每日必要看报,几乎同有了瘾一样,倘若一天偶然停刊,便觉得有点无聊”,①周作人:《读报的经验》,《周作人散文全集》第3卷,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51页。“报到每天必看过一套,虽然,如吾乡孙太史说过,结果只看了一个该死。我的报有送看的、有定阅的,计外国二种,北平五种,天津南京上海各一,共十种”②周作人:《读报者言》,《周作人集外文(1940-1948)》下册,海口: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第451页。。周作人不单痴迷于看报,更是各类报纸 “不折不扣的专栏作家”,单是1949年11月22日至1952年3月9日的上海《亦报》,他就发表了随笔多达712篇。孙郁说:“周作人一生和多少报刊发生过联系,已难以统计。早年的《天义报》、《绍兴公报》上的文章,已初具神态,气韵不凡。后来在 《新青年》、《新潮》、《语丝》撰写的短章,自成一格,曾被同代人看成美文的大家……周作人一生,和报人的联系很多,他的朋友中,报界人士可数的就有几位。孙伏园、林语堂、曹聚仁,与其都有神交,倘不是报刊的存在,周氏也只能写写讲义而已……周作人在难处见易,在易处见难,那是只有曹聚仁这样的报人,才能真正领略到的。”③孙郁:《报刊文章》,《周作人左右》,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3-124页。“周作人一生和多少报刊发生过联系”,虽然难以统计,但并非不能统计,《周作人散文全集》索引卷就列有周作人发表报刊及栏目名索引。可见周作人与报纸的“亲密无间”。
【责任编辑 郑慧霞】
宫立,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后期资助“中国现代作家佚文佚简考释”(15FZW052)的研究成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