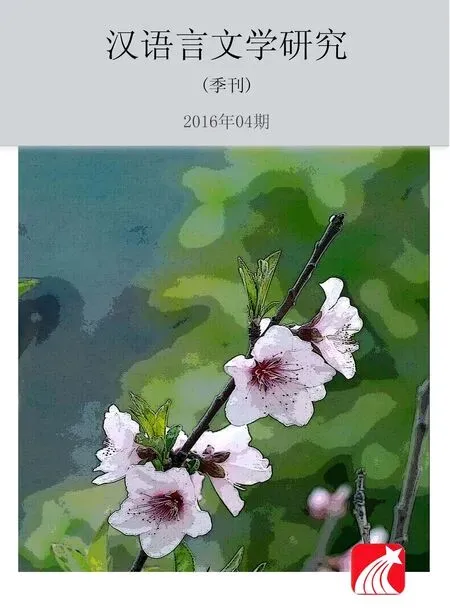从教为文三十年
2016-12-29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编委会
《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编委会
从教为文三十年
《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编委会
编者按:在王向远教授①王向远,1962年生于山东,文学博士,著作家、翻译家。1987年北京师范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1996年破格晋升教授,2000年起担任博士生导师。获“北京师范大学教学名师”称号。现任北京师范大学东方学研究中心主任、中国东方文学研究会会长、中国比较文学教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1项,独立承担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2项,重大项目子课题1项,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1项。两部著作入选“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外国文学评论》《外国文学研究》《中国比较文学》《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人民日报》等刊物发表论文200余篇。著有《王向远著作集》(全十卷)及各种单行本著作20多种、合著4种,译作有《日本古典文论选译》(两卷四册)等日本名家名著10余种,共约300余万字。曾获首届“高校青年教师教学基本功比赛”一等奖、第四届“宝钢教育奖”全国高校优秀教师奖、第六届“霍英东教育奖”高校青年教师奖、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奖。有关论著曾获第六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第六届“中国人民解放军优秀图书奖”、首届“‘三个一百’原创出版工程”奖等多种奖项。从教满30周年(1987-2016)之际,台湾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全十卷,选收1991-2016年间作者在各学术刊物上公开发表的220余篇学术论文、50余篇学术序跋等,共计200余万字,与十年前出版的十卷本《王向远著作集》互为姊妹篇。十位编委会成员分别撰写的《编校后记》,围绕《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各卷的编校,从不同角度谈了读书教书、求学治学以及学术史、学科理论等一系列普遍性问题,有一定参考价值,特加以整理删节,刊发于后。
中国东方学的开拓
李群(湖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博士)
我编辑的《国学、东方学及东西方文学研究》是《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的第一卷,所收二十多篇文章都是2008年后,也就是最近八年间陆续发表的,反映了王老师近年来关于学科建设的理论思考与实践的一个侧面。本卷书名中的三个关键词“国学”“东方学”“东西方文学”是相互连带的概念,最关键的是“东方学”。实际上,老师最近几年的主要精力也是在做“东方学”研究,特别是在2014年开始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方学”体系建构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以后。但是在此之前,他关于“东方学”的理论思考和建构早就开始了,最显著的是在《宏观比较文学讲演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一书及相关文章中提出的“宏观比较文学”这一范畴,以及与此相关的“民族文学”“国民文学”“区域文学”“东西方文学”等一系列概念。本卷所收录的若干文章,如《论阿拉伯文学的民族特性》《论犹太-希伯来文学的特性》《试论波斯文学的民族特性》《论欧洲文学的区域性构造》《论俄罗斯文学的宏观特性》《从宏观比较文学看法国文学的特性》《论德国文学的民族特性》《拉丁美洲文学区域特性论》《黑非洲区域文学特征简论》等,都体现了老师在这些方面的思考。然后,由文学研究出发,老师的研究进一步超越了文学而进入跨学科研究,于是顺乎其然地跨入了“东方学”。
正如王老师所说,中国的“东方学”研究有丰厚的历史积淀,但是关于“东方学”学科原理意义上的学科理论却一直处在空白状态。王老师的“东方学”研究首先聚焦于“东方学”学科理论的建构,要说明“东方学”是什么,就要清理“国学”与“东方学”、“国学”与“涉外研究”、“西方学”与“东方学”的关系,由此,他提出了“国人之学即是国学”“涉外研究是外传中国文化的有效途径”“中国的东方学是‘国学’的自然延伸”等一系列重要论断。不仅如此,他还把东方学的学理与现实关怀联系在一起,写了《“一带一路”与东方学》等文章,强化了东方学的应用性。这一切都令人耳目一新,体现了可贵的理论创新与学术勇气。
“东方学”的理论建构及中国的东方学学术史研究,是王老师眼下正在进行的课题,也是未来若干年老师的工作重点。他所努力提倡的“东方学”学科,目前在我国学科体制下从事的人很少,但却有重大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我辈愿追随王老师,为中国的东方学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
比较文学的改革与我的亲历亲证
周冰心(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教师、博士)
2016年8月,我一边为即将开设的“比较文学概论”课程备课,一边为《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第二卷《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研究》做最后的统稿工作。按理说编辑校对工作稍显枯燥,不想当我面对一篇篇文章,同时准备一节节课程的时候,屏幕上的语字却分明变得生动起来,每一篇文章的诞生、发表、回响乃至争议,都恰似在眼前一般,而距离我第一次聆听先生关于比较文学理论的见解,已经过去了整整15年。
2001年夏天的夜晚,我选修了文学院开设的“学术研究导引”课,值得庆幸至今的是,我曾一动不动地听了三个小时王老师关于比较文学学科前景与发展的讲座。现在想来,这个讲座应该是本卷论文集的首篇 《21世纪的比较文学研究:回顾与展望》的扩展版。也因为此次讲座,促使我今天成为了比较文学研究者中的一员。
2002年春季学期,北师大当年破旧的“新一”教室里,200名左右的本科生齐聚 “比较文学概论”课堂,我们一边用着陈惇等教授的《比较文学概论》教材,一边颇有些困惑地听着讲台上王老师对这本经典教材的一些建议与评述。平心而论,厚厚的《比较文学概论》我们看起来有些吃力,而王老师相应的讲解,我们听起来也并不那么容易。到底影响研究与传播研究是怎么回事?平行比较为什么容易做不好?所谓的“可比性”是什么意思?比较诗学和比较文论的不同究竟在哪里?甚至什么叫“诗学”……诸如此类的疑问,困扰着大二的我们。当然,我们并不知道的是,正是在课堂上侃侃而谈的同时,王老师的这些关于比较文学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新见解也迅速在各大核心期刊公开发表,并引起了热烈反响,而懵懵懂懂的我们成了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的亲历者,只是不自知而已。十几年过去了,当我再看到这些论文的时候(如论文集中的《论比较文学的传播研究》《大胆假设,细致分析——比较文学“影响研究”新解》《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功能模式新论》《比较诗学:局限性与可能性》《论比较文学的超文学研究》等),不禁有些悔意,悔的是面对这些充满睿智与锐气的文章,我们似乎没有格外“珍惜”当年的时光。当然,这种悔意姑且也算作是一种学术上的成长吧。尤为重要的是,十几年后,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意识到:比较文学中很多关键的理论与概念在引进的原初阶段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界定、厘清,乃至造成了混淆。这些现象,先生早在上述论文中一一进行了指明、解析与论证。
更难能可贵的是,在中国比较文学的发展历程中,老师一直站在中立客观的角度,耐心地等待着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的成长。上世纪90年代,当比较文学学科发展表面看来欣欣向荣之际,大量“时髦”的文章充斥在“时髦”的杂志期刊上,甚至发出了建立“中国学派”的呼声,而王老师在已经建构了一系列学科新论的同时,却又清醒地意识到,需要给中国比较文学的势头稍微降降温。于是,就有了《“阐发研究”及“中国学派”——文字虚构与理论泡沫》这篇文章的诞生。这篇论文言辞犀利、有理有据却又苦口婆心,直击当时中国比较文学发展的要害,引发了诸多学人连锁性的思考。
而若干年之后,当有西方学者不看好比较文学的发展,甚至提出了“比较文学危机论”的时候,王老师又及时写出了文章回应(见论文集中的《世界比较文学的重点已经移到中国》)。他在列举了中国比较文学近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中国比较文学学者所付出的大量艰辛劳作之后,鲜明地指出:中国比较文学超越了法国学派与美国学派的“学派”局限,将东方与西方文化相融合、文化视阈与文本诗学相整合,从而形成了“跨文化诗学”这一新的学术形态与新的学术时代。这看似简单的寥寥数语,背后却是中国比较文学同仁们走过的百余年的历程,也是王老师审慎看待中国比较文学学科发展史之后的冷静思索。而我们,当时忝列于王老师笔下的“青年学子”之列,幸运地成为了这一历史发展的亲历者。
2006年9月开始,作为研究生助教的我,全程跟听了王老师的本科新课程“宏观比较文学”。先生曾提起,这是他从教近30年来讲课最累的一学期,因为所谓每周“备”的课,是每一周都要真正完成一篇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然后直接在课堂上宣读讲解,同时也嘱咐我观察学生的接受情况。不得不说,这似乎也是我做学生以来听得最累的一学期,这种“累”不再是一知半解的懵懵懂懂,而是源于巨大的信息接受量,以及课下需拼命补充相关知识才能跟上老师思路的“累”,当然这种“累”,更意味着巨大的收获和无比的满足。我相信当年听课的学生和我的感觉是一致的,因为在学期末的时候,学生对这门新课程的评价创下了历史新高,或许,这是对本卷论文集中关于比较文学教学改革方面的文章(如《“宏观比较文学”与本科生比较文学基础教学内容的更新》《比较文学学术史上的宏观比较及其方法论》《打通与封顶:比较文学课程的独特性质与功能》等)最好的回报吧。
与此同时,老师在研究生课堂上的教学改革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这一思想主要体现在本卷《从“外国文学史”到“中国翻译文学史”:一门课程面临的挑战及其出路》等论文中。虽然这篇论文主要是针对中文系本科生的基础课程,但是王老师也在研究生的小范围课堂 “翻译文学导论”上试了一下水,正如他在论文中所提到的,这门课程“除了纵向的加强中外文学关系史的线索的梳理和描述外,在横向上,还要进行对名家名作的赏析与批评。特别是注意对翻译文学文本自身的鉴赏与批评。理想的状态就是在必要的时候对重要的译文与原文进行比较分析,看看翻译家如何创造性地将原文译成中文”。本次“试水”借由王老师的点拨,当时我身边的很多同学选择了不少颇具创新性的翻译文学的题目,继而写出了优秀的翻译文学的论文并公开发表,我想,这无疑是对王老师以上文章最有力的“证明”。
时至今日,作为书稿编校者,作为一名教师,再重新感受先生当年课程改革的系列观点时,我似乎更加理解身为一个拓荒者,先生推进改革的不易。有创见、有勇气、有胆识,也有未知,但这种“未知”,经由课程改革真刀实枪的实践之后,在众多学人的见证之下,变成了“真知”与“灼知”。
2015年9月,我进入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工作,第一次为学院的本科生开设“比较文学概论”课程。这一学期,我选用了王老师的专著《比较文学学科新论》作为上课教材。
这本书的诞生,如上文“亲历”部分所述,曾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也“打”了几场笔战(如论文集中的《拾西人之唾余、唱“哲学”之高调谈何创新——驳〈也谈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创新问题〉》),从另一侧面也凸显了当时比较文学学科理论争鸣的繁荣。但是在我看来,这本书所引起的“教材”争论却更为重要,由教材的选择、使用情况等所激发的反省与思索,对后来中国比较文学教学发展的影响甚为深远。
在与夏景先生的论战文章《逻辑·史实·理念——答夏景先生对〈比较文学学科新论〉的商榷》中,王老师系统阐述了学术专著与教材的关系,他指出:只有好的学术著作才配用作教材,凡有资格作教材的都必须具有“学术著作”的品格,而且是“好的学术著作”的品格,那种拼拼凑凑、“只编不著”的东西绝不能算是“好的教材”。
这场争论十年后,我学识素养尚浅,还未达到先生所要求的用自己的书讲自己的课的程度,但是我对先生的“教材”观却深以为然。此时,我并不是作为先生的门下学生选择了这本书,而是作为一名比较文学的青年教师,在经过认真的比对与考虑之后,出于对学生学习的需要,慎重地选用了这部书作为教材。
在恩师30年的教学生涯面前,由仅仅教授一学期课程的我来谈论使用教材的情况,未免显得渺小而狂妄。但我想,经历了15年之后,一直得益于先生比较文学学术思想滋养的我,以另一种角色、另一种立场,开启后来的年轻学子们对比较文学的兴趣和选择,是一种责任,更是一种历史的传承。我也很欣喜地看到,在这一学期的讲授中,学生们喜爱这本教材,甚至根据教材后面例举的论文也尝试着写出了自己人生中第一篇学术论文。这种结果,我想,无论对于哪一位老师来说,都是莫大的鼓励与安慰。
所以,一篇论文的选择与收录或许很快就能决定,一场笔战争论的硝烟或许很快也会退散,但是从论文与笔战中所诞生的思想与创见,在很多年之后却依旧在无声而有力地发挥着它的影响。
学在现场,忆在当下,乐在其中,仅以此篇小文总结我对本卷论文集的些许感想。我期待下一个“现场”,依然能够追随着先生。
厚重精深的学问来自学术史的研究
卢茂君(中央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副院长)
承蒙王老师信任,这些年来不断地校阅他的著译文稿,在这个过程中我也受益多多。记得我第一次帮老师校对的是《日本物哀》那本书。当时,一想到自己手中的打印稿将来要成书出版,像自己以前在书店看到的老师其他著作一样陈列在店头,就深感责任重大。一个半月时间,我反复校对书稿三遍。最近一年帮老师校对的书稿是《日本文学研究的学术历程》(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外国文学研究60年”的结项成果之一),我反复看了七遍,并写了长达万字的书评。
校阅书稿之外,就是听王老师的课。王老师的课既有学术史的深邃与厚重,又有学术前沿的活跃与开阔。我在工作之余,只要能抽出空来,就跑到北师大蹭王老师的课。尽管每学期的课程类型一样,但是王老师每次的讲授都有不同。他把新思考、新思路不断加进去,还有更多的即兴发挥,因而我每次听讲都会有不同的启发与收获。听完他的课,许多疑惑都没了,甚至连参加学术会议的愿望也大减了。
我负责编辑的 《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第三卷是比较文学学术史研究的论文集,除最后一篇《“百年国难”与“百年国难文学史”》外,都属于中国比较文学学术史方面的文章。但即便是对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的研究,也是运用比较文学的观念与方法。收录的20篇论文大多是王老师在写作《中国比较文学20年》一书时边写作边发表出来的,这也是王老师从博士论文《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开始就形成的一贯做法,也是他著述的一个特点。王老师曾反复说,学术刊物可以起到一个检验过滤的作用,著作的重要章节经学术期刊的过滤检验,就能保证成书时的质量。这确实应该是著述上的一个不二法门。
我常想,王老师学问厚重精深,大概与他常年注重学术史、学科史的研究密切相关。写学术史,就要多读书,也要研读历史上各家的学术成果,一个学者也就有了底气和底蕴,也就能够从历史走出来而站在最前沿。这些年,王老师为东方文学、日本文学、比较文学、翻译文学等学科领域写出了五六种学术史,可以说他是学术圈中为数很少的写学术史写得最多的人之一。
“译文学”与独辟蹊径的“少数派”
尹玥(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投入王老师门下学习和研究东方文学,是一件很巧合的事情,但这个巧合却成了我最大的幸运。王老师喜欢和学生聊天,将自己的想法娓娓道来,润物有声。不过,按老师自己的话说,无论是课上还是课下,说得再多也都是有限,主要还是希望能够启发学生,让思想活跃起来,不被现有的观念禁锢。如果能对思维有一定程度的“撼动”,那就达到了目的。
印象最深刻的是我们刚入校,与王老师交流今后的研究课题时,老师说:“年轻人做选题,不能仅仅出于现有的兴趣,不能只因为自己现在喜欢什么就去研究什么,‘喜欢’是因为你熟悉;不熟悉甚至不知道的,你不可能‘喜欢’,但是那里却有很多有价值的课题。越是以前没有人或很少人触及的领域,就越是有研究的价值,所以要了解既往的学术史,要了解学术研究的现状,然后找出问题,定下路子。”换句话说,研究不是个人爱好,不是赶时髦凑热闹,而应该甘受寂寞,独辟蹊径,有意识地努力做开路者。
这不仅仅是对我们莘莘学子的告诫和教诲,也是老师一直以来贯彻和坚持的做法。他常讲,他在学术上属于 “纯粹的少数派”。这个 “少数派”,在我鄙陋地揣测看来,就是他现在所做的事情都是独辟蹊径,很少有人做的,因而呼应者寡。例如,十多年前他做的日本侵华文学、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的研究,便是筚路蓝缕之举;近些年做的对日本古典文论与美学原典的系统的翻译与研究,在中国似乎也没有几个人做;现在正在做的“东方学”,在偌大的中国恐怕没有多少人做。而“译文学”这个学科范畴,恐怕即便是翻译研究界的人,乍听上去都不一定耳熟。试想,作为“少数派”写出来的文章,哪能有那么多“引用率”“关注度”呢?哪能以此“出名”呢?但孔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老师的态度似乎就是如此。
翻译研究与翻译理论研究,是王老师近年来投入精力较多的一个领域,并且做了深入的开掘。他最重要的建树,是将长期被忽略的“译文”作为研究的重心和主体,从而提出了“译文学”这一概念并与“译介学”相对。老师首先从中国传统译论文献中,首次发现了“译”与“翻”这两个基础概念作为“译文学”体系建构的基础与出发点。然后,提出了“迻译/释译/创译”“正译/误译/缺陷翻译”“异化/归化/融化”“创造性叛逆/破坏性叛逆”等一系列概念,论述了这些概念之间的关系,建起了不同于以往的“翻译学”即“译介学”独特的框架体系,为翻译学以及比较文学研究输送了新的观念与方法,拓展了研究领域,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研究前景。
我负责编辑的第四卷 《翻译与翻译文学研究》,共收录了21篇相关论文,前半部分是关于翻译文学宏观理论体系的构建和一些个案研究,从《“翻”、“译”的思想——中国古代“翻译”概念的建构》一文之后,都属于“译文学”的内容。老师的“译文学”体系建构逻辑严密,论述精深。我在编辑校读的过程中收获很多,感触也很多。其中,对老师论证的“翻译度”这一概念感触尤深。在翻译实践与翻译评论中,都会接触到关于译文的“还原度”与“翻译度”的问题。翻译家杨绛先生曾用 “翻译度”来表达译文对原文的还原程度,从“经验谈”的感性角度较早使用“翻译度”这个概念。王老师则将“翻译度”作为译文生成与评价的延伸概念,无论是 “迻译/释译/创译”“正译/误译/缺陷翻译”“创造性叛逆/破坏性叛逆”,还是作为译文风格判断的“融化”,都可以用“翻译度”来进行统筹和评价。翻译行为原本就是较为主观的,除了译词、译意的准确性之外无法进行精确判断,老师用这一系列概念来规制“翻译度”,将原本虚无缥缈、不易衡量的“感受”评价,变成了一个具有“模糊的精确度”的学科概念,认为无论是译文生成还是译文评价,都可以归结到一个“翻译度”问题。这是很有理论价值和启发性的。
“译文学”以及相关翻译理论的构建,只是王老师丰硕学术成果的一个方面。但从这一个方面,我们不仅能清楚地看到老师的治学态度和学术方法,也能看出他的学术价值观。那就是不为成见所囿,不为时潮所湮,不为名利所牵,用他的话说,“做学问就是不能走群众路线”,要把学术成果“留给后代”,做真正有价值的、不会被时间湮没的学问。与此同时,几十年如一日的笔耕不辍,没有周末、没有节假日的工作模式,将读书思考变成一种习惯,将研究写作视作一种生活方式,也让我们学子从心底里深深地敬佩。
翻译家与研究家
姜毅然(北京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教师,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
十年前,王向远先生《源头活水》一书的《后记》一开头就写了这样几句话:“我写了七八十篇与日本有关的文章,也写了多部与日本有关的著作。但迄今为止,除少量论文外,我并没有写过单纯研究日本或日本文学的书。换言之,我所研究的实际上大多是中日文学与文化关系。”王先生强调自己的研究是属于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或中日文学与文化之关系,而不是“单纯的”日本文学研究。我觉得,这一表白对于我们理解其日本文学研究很有参考价值。王先生历来主张中国人研究日本一定要有自己的立场、视角与方法,而不能一味地模仿、转述、祖述日本人,特别强调对于日本学者所普遍使用的“作家作品论”的模式,不能再无条件地苟同了。现在十年过去了,王先生较为“单纯”地研究日本文学的论文,也已经有20多篇了,本卷从中选取了19篇,独立编为《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第五卷 《日本文学研究》。
在编辑校对第五卷的过程中,我深深感到,即便是这些“单纯”研究和评论日本文学的文章,也反映出了王先生作为中国学者的独特角度与鲜明立场,在选题范围与论题上的拓展,以及学术研究方法上的更新与探索,而且篇篇有新意。例如,对日本文学的特征加以概括的文章,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都有人写过,日本学者吉田精一的相关文章早就有人翻译成中文了,但是有谁能够像《日本文学民族特性论》这篇论文一样,从文学史的实证研究与文艺理论的逻辑思辨的结合中得出如此扎实而新颖的结论呢?关于日本古代文论,日本人固然写出了一些大作(如久松潜一的《日本文学批评史》),但是有谁能用一万来字的洗练篇幅,把日本文论千年流变的规律与五大论题清楚地揭示出来呢?对于日本近代文论亦复如此,王先生的《日本近代文论的系谱、构造与特色》一文,理论概括依然是如此的强有力。能够做到这一点,是因为这些高度概括性的文字是建立在对日本古典文论原典文献的翻译基础之上的。王先生在此前翻译出版了《日本古代文论选译》(两卷四册)、《日本古代诗学汇译》(两卷)等二百多万字的相关译文。在翻译基础上的研究,保证了研究的扎实可靠。
同样,王先生对日本作家作品的研究,也建立在对原作翻译的基础之上。例如,对于井原西鹤,王先生翻译出版了该作家的五部代表作,包括《好色一代男》《好色二代男》《好色五人女》《好色一代女》《日本永代藏》《世间胸算用》。只有对西鹤的小说艺术有了切实的体验,才能写出像《浮世之草,好色有道——井原西鹤“好色物”的审美构造》那样的文章,得出“物纷”方法、“饶舌体”、“伪浅化”等新颖的结论。将翻译与研究结合起来,同样也表现在王先生对日本现代作家的研究中。1990年代初,王先生翻译出版了三岛由纪夫的长篇小说《假面的告白》,正是因为有此翻译在先,王先生在《三岛由纪夫小说中的变态心理及其根源》一文中表现出了对三岛创作心理的精到体察。至于村上春树,据王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的《后记》中说,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他曾翻译了村上春树的中篇小说《1973年的弹球游戏机》和长篇小说《寻羊冒险记》,虽然最终因版权问题未能出版,但也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基础,才有了《日本后现代主义文学与村上春树》这篇文章。1994年发表的这篇文章,被后来的村上研究者公认为是中国大陆最早的两篇相关论文之一,最早将村上春树定性为“后现代主义”并概括其创作特色,此后也被广泛征引。
王先生关于日本文学研究另一方面的文章,是中国题材的日本文学。在这方面,其《中国题材日本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6)一书是学界公认的一部开拓性著作,而现在收录在《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第五卷中的有关论文,就是作为该书的阶段性成果发表的。相关的作家作品大多是王先生在“中国题材的日本文学”这一视域中最早加以观照并做出系统、透彻的分析和论述的。王先生这些文章中所论及的作家作品,不仅具有文学史上的价值,而且在中日关系史上也具有重要意义。
作为一个外国文学研究者,像王先生这样,把翻译作为文本细读的方式与途径,将翻译与研究结合起来,我觉得是很值得效法的。
学者之道与学问之美
寇淑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生,日本菲利斯女学院大学客员研究员)
我所编校的第六卷 《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上)中收录的22篇文章,是王向远师早期的作品,是1995年至1998年间作为博士学位论文《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的阶段性成果陆续发表的。那几年老师几乎每年都要发表10多篇论文,所载刊物又都是重要期刊,到最终成书之前,博士论文的全部章节内容都作为单篇论文发表出来了。这要在今天,又有多少人能够做到呢?而且据《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后记》记述,那几年他还兼做中文系副主任。教学、研究与行政管理三管齐下,还有这么大的发表量,足见当时向远师的勤奋与创造力。现在二十年过去了,这种勤奋与创造力一直保持,甚至“变本加厉”了。我们做学生的随着对老师的了解逐渐增多,知道老师的几乎所有时间都在读书写作。二十多年前行政工作兼做了一届,之后再也不干了,只管教书、写书,这是他至乐所在。在今天这样追名逐利的浮躁社会,有多少人能够甘心坐冷板凳,淡泊名利,只为学术而学术,一坐就是三十年呢?而且还会继续坐下去。他所安坐之处,是他的书斋,这是老师所拥有的自己的天地与宇宙。
编校过程中,我对这些文章反复细读,不断感受其中的风格魅力。我一直在琢磨:为什么本来枯燥的学术论文,读起来非但不枯燥,而且反复品味,每次都有不同的感受呢?我在心里自问,也试图从中寻求学术创作的底奥。感到老师文章最大的特点,就是能够深入浅出而又逻辑严谨地将深奥的道理讲得明白,从不装腔作势、强词夺理,从不故作高深、无病呻吟。他善于发现问题,并以问题的新颖性而使人耳目一新,以问题提出的方式而给人启发,以解决问题的步骤与方法而使人入彀,以水到渠成的结论而令人信服。用字用词十分精准,许多地方让人觉得无可代替,而且不同文章的风格又摇曳多姿,如《从“余裕”论看鲁迅与夏目漱石的文艺观》轻快舒畅,《新感觉派文学及其在中国的变异》雄辩滔滔,《日本的侵华文学与中国的抗日文学》冷峻凝重,《“战国策派”和“日本浪漫派”》慷慨激昂。无论哪种风格,都以丰富的资料实证、细致的文本分析、科学的比较研究而运思行文。
向远师也常跟我们说:不仅文学作品应该有审美价值,好的学术论文也应该具有审美的价值,学术文章也可以当美文来写、当美文来读。记得有一次我在本科生课堂上旁听,他说自己在学术著作阅读中所得到的快感,往往比在虚构性的小说中所得到的快感更多;又说,假如是出于休息消遣,身边放着两本书,一本是虚构性作品如小说之类,一本是非虚构的学术著作,两者选其一,那么自己很可能会不由自主地把学术书拿过来。这话,大多数年轻学生恐怕都难以理解和共鸣。对知识与思想的接受消化,本身就是艰苦的劳作,因而读学术书会觉得很累,这应该是不少年轻人的感受吧。但是,像我这样已经做过几年大学教师的人,现在是能够充分理解向远师的话了。的确,读学术书、读论文原来是很有快感的。这种快感来自于多方面。满足了求知欲,觉得满足;发现了新材料,觉得欣喜;有了新的发现,觉得振奋;获得了新的思维方法,觉得茅塞顿开;搞懂了逻辑与论法,觉得酣畅淋漓。而且那些准确、洗练、严谨而又文气沛然的语言,也有相当的美感。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向远师的文章特别耐读。常见许多论文,时过境迁变作故纸,内容上浅陋,基本上用眼睛扫描一下就够了,因为其选题、材料、观点都是旧的。而向远师的这些文章,需要一字一句地读。读的过程却一点也不艰涩枯燥,常常会充满发现的喜悦与顿悟的豁朗。但即便如此,读完之后,仍觉得难以完整复述,因为这些文章从选题、材料到观点与论证都太新颖了。我们以前的知识储备太少,往往一时难以全部消化,也难以全面理解掌握,于是就需要再读、三读。人都说艺术欣赏是有重复性的,例如一首音乐作品需要聆听多次,体味与理解才能逐渐加深。其实,好的学术论文的阅读何尝不是如此。它也需要反复阅读,每读一遍都会有新鲜的获得。也正因为这样的缘故,老师的这些关于中日现代文学比较研究的文章,虽然问世已二十多年,读起来却旧文如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与读者的检验。在相关论题上,这些文章是很难被覆盖掉的,已经成为学术史上坚实的存在。
俳人、寂心与学问
龙钰涵(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生)
其实王老师是个不折不扣的“俳人”。作为学者,老师对俳句的创作历史进程与美学理论构造有深入的探讨。而闲暇之时,老师亦喜欢创作汉俳,并喜欢与他人交流切磋。犹记得本科时上“东方文学史”课程,讲到松尾芭蕉与“寂”之美学时,老师便鼓励大家尝试创作汉俳,并发送与他加以“品鉴”。一天早晨,我照例早早地去中学实习,匆忙出门后才发觉忘了戴近视眼镜,于是拿出手机,写了一首自嘲的汉俳——“眼镜忘了戴/眼前一片印象派/五颜又六彩”,然后顺手发给了王老师。不久收到王老师的回复——“眼镜忘了戴/眼前一片印象派/无霾也有霾。”那年北京的雾霾确实很严重,老师给我改了最后一句,至今难忘。
而这次,作为“王门”刚“入门”的学生,我有幸负责编辑校对第七卷,即《中日现代文学关系研究》(下),当校到《“汉俳”三十年的成败与今后的革新——以自作汉俳百首为例》这一篇时,不由得在心底一笑,同时也感慨不已。王老师的这篇文章,首要主旨当然是以自作汉俳为例为汉俳的创作与理论提供参考,而我从中读出的是老师日常生活中的谐趣与童心,不禁感叹:三十年来老师笔耕不辍,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学术成果,而在如此繁忙的学术研究之余,还保持着汉俳创作这般闲情逸致。不过,转念一想,这不就是一种“俳心”或“寂心”么?
我们从老师的论述中知道,“寂”是俳谐美学的核心概念。创作与鉴赏俳句,就要去听“寂之声”、观“寂之色”、品“寂之心”、作“寂之姿”。其中,“寂心”是“寂”之美学构造中最核心、最内在、最深层的内容与范畴,是充分体悟“寂”之美感的审美状态与精神品位。同时,亦可看作是在寂寞平淡乃至寂寥清贫之中保持独立、淡泊、自由、洒脱的人生境界,是对某一客体不过分偏执、胶着乃至沉迷的游刃有余的主体状态。老师多年来从事教学与研究的状态,相当接近于这种“寂心”的境界。
老师在《论“寂”之美》一文中,对日本俳论关于“寂心”的四组范畴——虚/实、雅/俗、老/少、不易/流行——做了深入阐发,指出其中“不易”与“流行”也就是永恒与变化的矛盾统一、“动”与“静”的矛盾统一。记得在与老师的闲谈中,他也曾提到,做人做事也要讲究“不易”与“流行”。从这一点上看,王老师的“不易”首先表现在,三十多年如一日,把学术以外的活动减少到最低限度,不出风头,不掺和校园政治,不追名逐利,集中精力,坚持按照计划有板有眼地做学术、写文章。王老师曾在一篇访谈文章中自述:“学术研究本身就是一种修行,需要培养长年累月甘坐冷板凳的耐力。”(《社会科学家》2007年第6期)正是靠着这种“苦中作乐”的坚持与耐力,老师才有了今日这样的学术成就。另一方面,老师的“流行”表现在,对某一领域有了足够、充分的研究之后,或者说有足够启发他人进行进一步探讨的成果之后,就去挖掘新的问题、探索新的领域,不吃老本,不走轻车熟路。三十年来,老师的研究课题与方向已经从最初、最基础的东方文学史、日本文学研究、中日比较文学研究,扩展到比较文学、翻译文学学科理论、翻译学、美学、东方学等众多领域,在各个领域都有自己的创新。老师学术生涯中的“不易/流行”,是值得好好玩味的。
勇于揭开日本文学与文化的阴暗面
祝然(大连外国语大学《东北亚外语研究》编辑部,博士、副教授)
2001年,当第一次在大连外国语大学图书馆读到王向远先生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一书时,我心底掀起的波澜是前所未有的。这本书使读者看到了日本文学的另一面,也是黑暗的一面。继此之后,王先生又陆续发表日本对华文化侵略以及日本右翼历史观的研究文章,到2005年,《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日本右翼言论批判》两部著作同时推出,与之前的《“笔部队”和侵华战争》一并构成对日本侵华史研究的 “三部曲”,被列入国家新闻出版署重点出版项目、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全国百种重点图书”以及解放军总政治部全军读书书目,堪称学界献给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的一份大礼。
阅读《“笔部队”和侵华战争》时,我还只是一名普通的学生读者,手捧《日本对中国的文化侵略》与《日本右翼言论批判》时,我已经是一名初涉研究领域的研究生了。在这些著作中,先生不但为我展开了全新的学术视野,他的学术品格与学术精神同样对我产生了极大影响。日本右翼势力的嚣张气焰众所周知,很多学者对其都抱有避之唯恐不及的态度,不愿对其进行研究,更遑论对其进行揭露与批判。然而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右翼势力越是嚣张,先生越是认为自己有责任对于这种文化挑衅做出反应,即便存在危险,同样在所不辞。这是一种强烈的责任感,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学者良知。由于先生的这部分论著大都写于他在日任教期间,《中国青年》的记者亓昕曾打趣说这是“跑到日本右翼的身边去反右”。对此,先生笑而答曰:“对。感觉身临其境,也很痛快。”这句简单的回答,透出些许侠义,更有满满的大家器量。同时,由于国内针对“文化侵略”的研究少之又少,先生需要在国内外大量搜集、整理各类资料,这个过程不但耗时、耗力,想必也很孤独寂寞,然而先生却凭借自己对于研究的执着追求坚持了下来。这种铁肩担道义的学者良知、执着研究的学者态度教会了我如何在研究领域做人,如何树立起自己的学术品格,使我受益终生。
而今,我借着编辑《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第八卷《日本侵华史与侵华文学研究》的机会,将先生的有关单篇论文收编为一卷,同时完成了对于先生的相关研究成果的再次阅读。面对案头这摞厚厚的文稿,感慨良多。
最为感慨的一点,是先生勇于解开日本文学、文化的阴暗面,在这个领域中敢为人先。在十多年前乃至二十年前,当“中日友好”曾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主旋律的时候,先生却敢于呈现“非友好”的一面,研究日本的侵华文学和文化侵略,研究和批判日本右翼的历史观。最近这些年当中日关系翻转变冷的时候,先生却改变了方向,去研究日本的审美文化、美学与古代文论了,这是从历史文化研究向审美文化研究的转向,先生自嘲是“逆潮流而动”,但这样可以更多地摆脱时局的制约而更为超越。据我所知,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时,许多媒体、杂志社、出版社跟先生约这方面的稿子,先生却告诉他们:那都是十多年的研究了,现在不再写这些了。他只是应杂志要求把早先的书稿发给他们使用,于是至少有《作家通讯》《海内与海外》等三家杂志在2015年中连载了他的旧文。与此同时,他的侵华史研究三部曲也在2015年出版了精装第三版。我觉得这一切至少表明了两点:第一,先生确实喜欢做学术上的“少数派”,而不愿随大流、走轻车熟路,喜欢不断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第二,先生十几年前的研究到今天仍没有过时,仍在持续地发生着影响。若翻一翻现在已通过答辩的各校相关选题的博士、硕士论文,在综述先行研究成果的时候,都不能不提到先生的开拓性的贡献。如今我再读先生的这些文章,看不出时光流逝对这些文章有什么影响,而只有一种痛快淋漓的新鲜感。
日本审美文化的发现
(郭雪妮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师、博士,日本创价大学访问学者)
六月初,忽受恩师王向远先生吩嘱,说台湾万卷楼图书公司要出版《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十卷,问我能否负责编校其中的第九卷。老师已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蔚为大观,能系统编纂出版,是一件大好事。特别是在恩师从教满三十周年之际,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纪念。特别是先生让我负责第九卷《日本古典美学与文论研究》,我很感念他的良苦用心。先生定是知我近几年一直在藤原定家及其周边歌论上艰苦用力却收获不多,故特别嘱我分校这一卷吧。遗憾的是,我学术根基尚浅,这次所谓的编校,其实只是逐字拜读学习领悟的过程,这里的编后记,至多是一篇读后感而已。
《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第九卷《日本古典美学与文论研究》所收17篇文章,绝大多数是先生于2010年至今陆续发表的新作,是以其对多部日本古代经典文论的翻译为坚实基础,围绕日本古代文论的诸多核心概念生发出来的一系列重要研究,实践他提出的“比较语义学”的构想,将“考”与“论”结合起来,篇篇有新意。这些文章中有一部分是我在北师大读书期间曾在先生课堂上听过的,如《日本的“哀·物哀·知物哀”》《入“幽玄”之境》等,又有一些篇目是先生在门里聚会时讲过,如《日本身体美学范畴“意气”语义考论》中涉及的“意气”概念。大约在2012年9月,先生门下的新老硕博士生齐聚一堂,席间无酒,先生侃侃而谈九鬼周造的《“意气”的构造》,从九鬼周造的身世说到冈仓天心,继而畅谈九鬼“意气”所指的媚态、意气地、谛观三个层面,最后又自然引申到现实中如何处理恋人关系的问题,并谆谆教诲在座的女生们如何谈一场高品质的恋爱。我觉得大家当时都有些醉。
关于《论“寂”之美》所涉“寂”之问题,我最深刻的感受莫过于2011年5月底在华山之巅听先生论“寂”了。恰逢机缘巧合,我和几位师兄师姐陪同先生登华山南峰。尽管乘了一段索道,但至中途众人还是被眼前绵延无尽的苍莽奇峰给震慑了,于是索性坐在绝壁边一颗老松下,俯眺如帛铺展的漠漠平原。这时,一枝干枯的松桠掉落在石桌上,惊吓了一只小松鼠慌忙逃窜。那枝干松弯曲在石桌上,背后是近在咫尺的天与缠绵缭绕的云,那场景真是美极!先生看着这一幕,忽然说,你们看,这就是“寂”啊!接着顺口吟咏了一首“五七五”格律的汉俳(可惜当时没有记下来)。这是先生如诗人的这一面。
当然,《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第九卷中更多的内容是我所未读过的,如 《日本 “物纷”论》,现在这篇文章和本居宣长的《物哀论》,已经成为我和学生解读《源氏物语》时的座右之书。另有《日本的“侘”、“侘茶”与“侘寂”的美学》是刚刚发表的新作,深度阐释了“侘”字所蕴含的“人在宅中”之美学,提出在离群索居中体味和享受自由孤寂的美感,是与茶道之美密切结合的。校对此篇文字时,我已暂时移居至东京近郊的武藏野,独自就着山中寓所之四壁。怕是此情此景之故,读这篇论文时毫无涩滞之感,甚至多处让人生感动虔敬之心,这也是我此番校对的最深刻感受吧。是为后记。
三十年的翻译与研究——从文学史研究到理论建构,再到超学科的“东方学”
王升远(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我记得老师是1987年开始在北师大执教的,到今年正好是三十周年。前些日子与老师通电话时,我说:“老师执教满三十周年了,当教授也都二十年了,该举办个活动纪念一下吧?我可以来张罗。”老师说:不用做什么活动,但是李锋建议出一套书作个纪念。于是我们分工合作,在王老师的指导下,将这套书编了起来。
我负责编辑的《序跋与杂论》是《王向远教授学术论文选集》最后一卷,内容也较为特殊。所选的是三十几部著作、译作的序跋,而且大部分是跋文(后记)。因为老师的序文大部分是作为正规的学术论文来写的,分别编在了头九卷,而老师写“后记”仿佛是干完活儿之后的小憩与闲聊,是随笔散文的笔法,虽然聊的仍然是干的活儿,但毕竟都如大汗淋漓或长途跋涉之后的歇脚,透露出一种轻松惬意,这类文章都编在了第十卷。
这些序跋杂论文章,是老师三十年的学术历程的印记,显示了老师在研究领域上的选择、开拓与转换,从中可以看出一个基本轨迹,那就是:从早期的文学史研究到中期的学术史研究,再发展到理论研究与理论建构,再到眼下正在做的跨学科的“东方学”研究。
老师的早期研究是先从文学史入手的。其中,1994年初版的《东方文学史通论》是我国第一部个人撰写的、形成了自己的理论体系的东方文学史著作(这一评价参见陶德臻先生为初版本写的序言)。第二部《中日现代文学比较论》则进入了中日比较文学领域,而所依托的仍然是中日近现代文学史。第三部《“笔部队”和侵华战争》可以看作特定侧面的日本文学史研究。而《二十世纪中国的日本翻译文学史》(再版改题《日本文学汉译史》)则是第一部日本文学汉译史著作,也属于文学研究的一种门类,但此书是这一门类文学史的开创者,也就是说,它是我国第一部国别的翻译文学史。接下来的《东方各国文学在中国——译介与研究史述论》则是把翻译史的研究由日本扩展到整个东方。最后是王老师率领几届研究生用十几年时间写成的《中国百年国难文学史》。这些都属于文学史研究,但不是一般的文学史研究,而是一方面运用了传统文学史研究的严格的资料实证、文本分析的方法,另一方面也有着比较文学、翻译文学、战争文学、国难文学等特定的新颖角度,从而成为填补文学史空白的文学史研究。我认为,这是王老师对文学史研究的一个贡献。
进入21世纪后,老师的研究重心由 “文学史”研究进入了“学术史”研究。前者是对作家作品的研究,后者是学者的学术著作的研究。很显然,对学术史的研究与王老师的学科建设的构想密切相关,其目的是为了在学术史的研究中总结汲取学科建构的历史经验,为此,他主编了《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学科建设丛书》《中国比较文学论文索引(1980~2000)》和《中国比较文学年鉴》(合作)等书,在这些文献学资料学工作的基础上写成了《中国比较文学研究二十年》,这是第一本1980至2000年中国比较文学的断代史。接着,王先生又与乐黛云先生合作写出《20世纪中国人文学科学术研究史丛书·比较文学研究》,进而最终以一人之力写出了《中国比较文学百年史》。从文学史到学术史,研究领域有所变换,但不变的是选题上填补空白的学术价值。
在学术史研究的坚实基础上,王老师的研究顺乎其然地进入了文学理论的研究,特别是比较文学、翻译文学学科理论的研究,写出《比较文学学科新论》《中国文学翻译九大论争》(合著)《翻译文学导论》《宏观比较文学讲演录》等著作。这些著作在比较文学、翻译文学、宏观比较文学三个方面都提出了一系列令人耳目一新的观点,形成了独特的理论体系。而近几年连续发表的关于“译文学”以及比较语义学(特别是中日文论范畴关联考论)的系列文章,虽然还没有来得及结集成书,但已经清楚显示了老师的理论研究与学术思想上的进一步拓展和深化。目前老师正在做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方学”的研究,则在“东方学”的学科平台上跨越了学科,将文学与其它学科相贯通,又将学术史研究与学科理论建构相结合。
除了上述学术研究之外,王老师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翻译。既有学术理论著作的翻译,也有文学作品的翻译。收入本书的有老师为他的十几部译作所写的《译者后记》。可以看出,翻译与研究,这两个方面在王老师那里是相辅相成的。他常说翻译是一种“调节”,可以换换工作方式,减轻单纯的学术写作的单调感,但翻译对王老师而言绝不是纯粹的消遣,因为他翻译的那些文献和作品大都是古典或经典,难度很大。他常年坚持不懈地翻译这些东西,每天拿出三分之一的时间做翻译,竟然已经译出了三百多万字。对翻译的投入和执着,根本上是出于老师对“翻译”本身的重视,而他的翻译理论研究也需要翻译实践做支撑。并且,正如《翻译的快感》一文中所言,他在“翻译”中感受到了语言与文化转换所具有的创造性,体会到了其中的“快感”,所以他说翻译会“上瘾”。在中国,一般搞翻译理论研究的人往往翻译实践做的不多,而做翻译实践的人对翻译理论则不甚措意。王老师既有翻译理论的建构,又有大量的翻译实践,是很不容易的。另一方面,翻译做得好的人不少,研究做得好的人也不少,但像王老师这样翻译与研究做得又多又好的,恐怕就很少了。
收入本卷的序跋与杂论都有着独特的见地,固然可以当学术论文来读,但比一般的学术论文含有更多的感受与体验,又可以看作学术散文,因为读起来很有美感。我常想,王老师实际上是很擅长写这类随笔散文的,甚至是很能写诗的(他发表了不少汉俳),因为他很有诗心,很有感受力,充满知性而又不乏情趣,文字老到而又灵动,文气充盈而又内敛,格调洒脱而又儒雅。特别是他为前辈学者所写的怀念文章、为后辈学者所写的那些序言,更表明他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人。当然,作为一个研究人文学科的著作家,作为一个翻译家,这些都是必须的,也颇值得我们晚辈效法。
2016年8月
【责任编辑 孙彩霞】